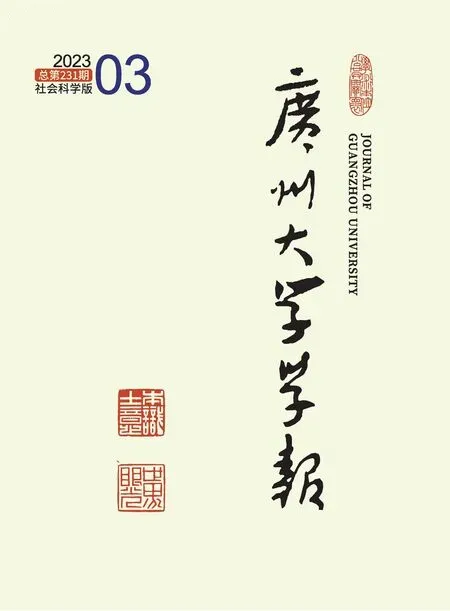“粤港融合”视域下重审陈残云笔下农民形象谱系的发生及变迁
2023-08-08王文艳
王文艳
(广东工业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6)
陈残云是著名的广东作家,但他与香港文坛有很深的渊源,他的创作生涯起步于香港。1933年冬,他在香港《大光报》发表了处女作《一个青年的苦恼》,引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解放战争时期,他于1946—1950年旅居香港,出版了中篇小说《南洋伯还乡》①,短篇小说集《小团圆》,成为其乡村题材创作的发端。创作文类也在这一时期从诗歌、小说延伸到电影剧本、影评、政论时评。他编剧的《珠江泪》,被誉为香港粤语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因此,香港是其创作生涯中具有关键意义的“起点”和“节点”。
陈残云从1950年返回广州直至去世,乡村始终是他创作生涯最重要的题材。但对他的研究与他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不相符的。以至到了2009年,仍有学者指出:“令人不解的是,时下,当众多的批评者与文学史家对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给予热切关注,并力图从其创作模式中挖掘体制的、风格流脉的或潜在的民间形态的影响时,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文学史教材,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从未纳入他们的视野之内。”[1]代表作尚且缺乏足够的关注,香港时期的创作更是遭到冷落。②
陈残云在抗战时期以知识分子题材的中篇小说《风砂之城》成名,之后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力以赴进行乡村题材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仍深耕不辍,“文革”遭受打压之后仍然执着,创作生涯延续大半个世纪。其选择和坚持背后的思想文化逻辑,作为知识分子精神探求的个案,本身就深具意义。他笔下的农民形象,更是形成了系列具有丰厚美学价值以及文学史意义的人物谱系,深刻地折射出广东大半个世纪以来农民社会地位以及精神世界的变迁,理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在香港时期创作的小说集《小团圆》,更是一个具有丰富生发意义的原点,贡献了具有复杂性格内涵及心理深度的岭南农民形象和原生态的民间世界,表现出未完全被现实诉求所限制的左翼文学特征,具有不应忽视的文学史意义。
因此,本文拟在“粤港融合”的视域下,以小说集《小团圆》为出发点,兼及《南洋伯还乡》,在陈残云乡村文学版图中补上久被忽略的发端,并以此作为新的起点,在完整的创作脉络和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对其笔下的农民形象进行重新阐释。
一、“受难牛”人物系列:短篇小说集《小团圆》与农民形象的发生
短篇小说集《小团圆》收录了陈残云从1946到1949年创作的6部短篇小说③,作为黄谷柳主编的“南方文艺丛书”系列之一,于1949年10月由南方书店在香港出版。陈残云在1982年曾予以评价:“这是当时的真实生活。但我在描写农民的思想和行动时,缺乏阶级分析,使一些人的性格带有流氓性或小市民气习。这个问题,在我参加了土改以后,有所认识,才获得了解决。”[2]这里暗含的评价尺度值得进一步思考,“带有流氓性或小市民气习”的农民是不是影响了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这个问题”在陈残云参加土改“有所认识”后,获得了怎样的解决?“解决”后的作品又该如何看待?
回到短篇小说集《小团圆》创作的历史语境。短篇小说集《小团圆》是以同名小说《小团圆》命名的,小说于1946年12月发表在《文艺丛刊》第二辑,同年发表的还有《财路》《救济品下乡》。这些创作均未引起学者的重视,谈及陈残云解放战争时期的创作,一般都以《风砂的城》为讨论起点。《风砂的城》从1946年开始陆续刊载在《文艺生活》,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但随着1948年左翼文艺政策在香港文坛的诠释和推广,陈残云发表了《〈风砂的城〉的自我检讨》一文,这一事件对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风砂的城》发表的同一时期,他已经开始从事乡村题材创作。因此,这一时期的创作虽然受到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④,但更多还是创作道路上的自由探索以及个人乡村生命经验的自然投射,这是我们探讨这一时期的乡村题材创作必须注意的。正因如此,其笔下《小团圆》集子里面的农民性格确实“带有流氓性或小市民气习”,但这正是“当时的真实生活”,体现了陈残云对农村生活本来面目的尊重,折射出农民文化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这还意味着陈残云在用一种未被现实诉求所限制的视角在观察农民,这种视角带来丰富的人性内涵,从根本上体现了陈残云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方言的大量运用,使得这些农民形象真正脱胎于岭南乡野,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在中国乡村文学的版图上独树一帜。
以《小团圆》为例。主人公“黑骨球”,“像一条命带煞星的好汉”[3]33。他是“一个烂皮烂骨的赌仔”[3]33,但作战又极为英勇;他有朴素的民族大义和道德观念,得知要打的“共产党也是打日本鬼的中国人,他就有些不自在”[3]34,但转念间就去油麻地找妓女;与分离八年的妻子聚首,他想的是“说不定又欢喜地给他一点私积钱”[3]38,但相逢之后,在意的是妻子的眷念;得知妻子沦为妓女,他感到莫大的耻辱,又踢又骂,但念及自己从不寄钱养家,“不免有些气恼与内惭”[3]46。在陈残云笔下,“黑骨球”的性格充满了矛盾的张力,自私、狭隘、虚荣、粗鄙的同时又具有仗义、善良、纯朴的一面。
除了“黑骨球”之外,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有类似的性格特点和文化习性。《救济品下乡》中的“牛精桐”有着“粗笨的蛮横相,硬碰是碰不过的”[4]18,最后放火烧了古庙;《财路》中的“大头炳”“脾气很硬,又野,做事要做些明明朗朗的事,偷偷摸摸是不干的”[5]2,结果偷运货物时被打死;《乡长的儿子》里的“铁脚良”是个“捞底”,但“捞得义气”[6];《受难牛》中的“受难牛”靠“胆正,命平,力大”[7]62,“打”开了一条生路。总体而言,这一系列人物都是饱受乡间官匪压迫,以“硬骨头”精神向命运抗争的农民,被称之为“受难牛”人物系列[8]。但人物性格却相当浊,张扬着野性的生命力同时富有鲜明的个体生命意志。这种描摹反映了农民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生存为基点决定了其内涵往往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表现形式上粗鄙,又带着不受礼教束缚的自在。
不仅如此,“受难牛”人物系列还呈现了农民复杂的内心世界,显示出陈残云对农民心理的谙熟和精细的表现力。仍以《小团圆》为例。“黑骨球”经历了八年的枪林弹雨,随部队在香港休整。一天,他乘着酒意摸了一回妓女屁股后,他的内心开始发生变化。
今早起来,黑骨球又有些莫明(名)的怅惘。一种难言的焦躁,盘据在他心底里。他在床铺上无聊地拿着枪杆来擦,擦不上两分钟,又疲怠似地靠着墙壁抽烟,迷胡(糊)之间,他想到那个圆额扁鼻,乳房胀得发跳的小冤家。他想,那时候,他对她是有点过火的,她样样都服从他,打她搥她也不回手,搥得重时也只是偷偷的揩眼泪。“唉……”想得出神时,他忏悔地叹一口气,直觉到自己似乎受到一些良心的责备。然而不久,一种强烈的“英雄心”把他克服了,原来他是被称为一位英勇的机关枪手的,他从来没有不干不净的恋念。[3]35-36
这段描写极为精彩,写出了一个在长期战争中身体和精神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下的士兵,在松弛的状态下,被压抑得很深的性欲慢慢被唤醒,由此引发的系列心理活动。既有对性欲的渴望,更多的是对日常家庭生活建构的人情温暖的渴望。而以“英雄心”克服这种“不干不净的欲望”,实际上揭示了抗战神圣、保家卫国等宏大口号对个人合理欲望的“遮蔽”和“扭曲”。及至天未亮,“黑骨球”换上干净新衣去等待妻子,甚至发出“奇怪的问”,“她……她会认得我么,四婶?”[3]39及至见面,他“心里又喜悦,又疑惑”。[3]39他看出妻子的装扮和神色异样,却不敢询问,只一个劲与四婶搭话。到了安静的火车桥底,“很想伸手去摸她,却又有些胆怯”[3]42。这一系列“反常态”行为,营造出了一种啼笑皆非的喜感。在烘托出农民淳朴、害羞、拘谨的心理特点之余,揭示了战争对夫妻正常伦理的破坏,对人情人性的深度压抑,显示了陈残云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
正是基于陈残云关注的重点始终是人,人物具体的生存困境以及精神世界,因此他更习惯于从日常生活层面,特别是伦理的角度切入主题。《小团圆》中,作者虽然通过“黑骨球”对交战对象的反应以及逃离部队的决心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动本质作了批判,但这些是作为背景的“淡写”,作者“浓描”的是战争对夫妻伦常的影响;《救济品下乡》没有充分描写“牛精桐”的阶级仇恨,倒是对乡绅蠢蠢欲动的性欲刻画得入木三分;《乡长的儿子》中“烂颈胡”欺压乡民的虚伪狡猾,“铁脚良”的反抗,均通过日常的饮茶和对话来凸现。作者的“浓描”与“淡写”,使得小说主题的表达始终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因此,如果将他的创作纳入左翼文学的谱系,那么这一阶段的创作更切近左翼文学的本质,即从人民立场出发的人道主义关怀、坚持思想高度的现实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本小说集开始,陈残云对方言的运用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在真实地呈现出岭南农民本身的生存逻辑、伦理法则、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的同时,营造出了浓郁的岭南文化色彩。
首先,作者抓住人物外貌特征或从生活习性、职业出发进行命名,如黑骨球、大胆发、牛精桐、大只忠、烟屎积、长腰成、大头炳等,凸显了人物鲜明的形貌和性情特点,既符合农民擅用朴素的形象思维表达的习惯,亦体现了农民自由活泼的审美态度。
其次,陈残云运用了地道的方言俗语。比如,“契弟”这一詈言。“契弟”本意是“干弟弟”,但这个用法已无人使用,原因在于“契弟”在粤方言里有男妓的意思。因此,“契弟”是针对男性的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称谓,表示极度愤怒。《财路》中,“长腰成”被怀疑串联王排长,导致“大头炳”被打死,于是“当天发誓,我是给王排长那契弟累死呵!”[5]13。《救济品下乡》里,乡民对假公济私的唐乡长发出讽刺和詈骂的声音,“卖‘喽柚’的契弟,串通日本鬼,又串通新一军……”[4]27。“喽柚”应为“啰柚”,粤语指“屁股”。因为“屁股”长得像柚子,而粤语称呼柚子为“椂柚”,为发音方便,就用“啰柚”一词表示“屁股”。在这里“喽柚”与“契弟”叠加在一起,加强了言语侮辱的意味。“契弟”一词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但均指涉土豪劣绅以及腐朽的国民党部队,微妙地传递出作者的情感和价值取向。
此外,小说中具有岭南特色的职业语或行话也运用得非常丰富。譬如小偷叫“夜摸”,吸鸦片的人叫“烟精”,赌博叫“捞番摊”,佣人叫“婆妈”,妓女叫“老举”,价格便宜的牛肉叫“平牛肉”,购买叫“帮衬”,等等,都极为传神地营造出了地方感。
对方言运用的成功还在于陈残云真实地呈现出岭南农民生存逻辑的同时表现出人物个性化的性格特点。《财路》中,三个农民围绕着出路问题各抒己见:“默想了半刻,烟屎积重重地吸了一口浓烟,又道‘我说呀,大头炳,这还是个捞家世界,你不信!’‘是的,田耕不得,工没得做,不拿枪吃饭,靠什么?’盲四擦一擦那双腊(应为蜡)烛油似的眼睛,抢着说。‘丢!你的鸡屁眼看见条鸠,国军这样多,靠枪,问你有几条性命呀,盲四!’大头炳不服气,扯起爽朗的喉音,斥责盲四。”[5]3对话中,人物形神毕肖。“烟屎积”惯走偏门,“捞家”指的是没有正当职业,靠坑蒙拐骗手段挣钱的人。这个词表明他以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以及阴暗世故的性格特点。“盲四”的“抢着说”以及靠枪吃饭的想法,显示了他的急躁、直率和单纯。“鸡屁眼”“鸠”都是生殖器的意思,显示出“大头炳”粗放、泼辣的气质,对现实的考量又显示出他“粗中有细”的一面。
香港学者郑树森提及以香港为背景的《小团圆》和《受难牛》时认为:“小说作为文类,当时最大的突破可能是运用方言以面对华南读者,……但使用方言,有时也须提炼取捨(舍),如陈残云在作品中大量写粗话,其实是不必要的。”[9]25
20世纪40年代是陈残云方言运用的探索阶段,在提炼取舍上确实存在做得不够的地方。但大量写“粗话”是对民间文化形态某种程度的真实还原,是饱受压迫的农民在拥抱生活过程中自然迸发出的爱憎,是任何道德说教、政治律条都无法规范、约束的。民间拥有自己的传统和语汇的表达方式,对于精英知识分子来说,其中一些表达或许有悖于新文学惯常容忍的审美原则,但是并不意味着因此丧失独特的审美价值。
与郑树森不同,黄继持肯定陈残云在语言方面有所开拓,但认为:“小说模式的突破不大……虽以华南为背景,但这不过是把三十年代北方作者写过的农村题材放在华南的背景来重写,让广州人与香港人更添切近之感。因此,这是接续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主要流派。”[9]2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够公允的。小说即便放置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乡村文学的版图当中去看,也有不能忽视的文学史意义。
最重要的在于小说呈现出对华南地区乡村生活精确而深刻的写实能力。赵园曾说过:“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些非写实,或曰非严格写实的乡村小说,……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写实作品的某种浪漫倾向,农民形象的意义膨胀。‘农民’,是某种程度上被作为‘民族’的形象刻绘的。”[10]这种看法相当精辟。实际上在沈从文、萧红的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文化象征的意味胜过写实。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写作虽然树立了写实的传统,但总体上还是较少见的。正如贺仲明指出:“我们新文学视野里的乡村世界也主要成为了黑暗型、浪漫型、政治图画型,却很少乡村自在型。”[11]因此,陈残云的创作不是简单地重写“北方作者写过的农村题材”,而是贡献出了有复杂性格内涵及心理深度的岭南农民形象,并通过方言还原了原生态的岭南民间文化,因此在中国乡村文学的版图应占一席之地。
如果在“粤港融合”的视域下去审视陈残云的创作,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在地区文学史的层面上,不管是香港文学,还是广东文学层面,都能得到更有价值的彰显。《小团圆》中刻画的“黑骨球”和“苏女”,《受难牛》中的“受难牛”和“花头九”都是因生活所迫,从广东农村赴港谋生乡民的真实写照。由于地缘相近,香港人口构成及流动均以广东为主。⑤由此看来,这两篇小说以艺术化的手法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香港人”的生成,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二、1949年之后:小说集《小团圆》传统的“断”与“续”
1948年,陈残云发表了《〈风砂的城〉的自我检讨》一文。文中指出由于自己“小所有者思想意识的作怪”,导致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灰感,苦闷消极和沉落”,违背了“文艺是服从于政治的,服役于政治的”[12]原则。陈残云的检讨无疑是真诚的,是对无产阶级文艺政策提出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积极响应。但问题在于:作为继承了“五四”以来人道主义传统并逐渐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陈残云来说,是如何在当代文学“规范化”的一体化进程中调整自己以“服役于政治”?在实际创作中又产生了怎样的罅隙?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残云的农村题材创作可粗略划分为两个时间段:一是50年代开始到“文革”爆发以前,即俗称的“十七年”时期;二是“文革”结束后的创作。这两个阶段的创作有不同的变化,但从总体上呈现出类似的特征。
首先,“受难牛”人物系列从农民谱系中消失了。当陈残云参加土改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重新审视这些农民形象时,这些代表着先进阶级的贫雇农身上的“流氓性或小市民气习”被剔除了,政治的标准同时成为伦理判断的标准,明显的变化体现在人物的命名上。“受难牛”人物系列的命名体现了具有戏谑意味的乡村美学,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类型的命名只存在“地富反坏”身上。譬如《山村的早晨》中当过国民党警察的“单眼照”、恶霸“三角凳”和“蛇头耀”等。这些命名往往还具有贬抑的意味,是对“反动本质”的有效提示。“社会主义新人”则直接以姓名称之,如《山村的早晨》中的平三嫂、刘平,《喜讯》中的根生二嫂、杨九。
随着“受难牛”人物系列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与阶级成分相对应的形象序列:以“地富反坏”分子为代表的反派人物以及以“贫雇农”为代表的正面人物,其中从贫雇农中涌现出的“社会主义新人”成为陈残云农民谱系中的主角。此外,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大量减少了对方言的运用,这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语言政策密切相关。由于方言文学可能带来的地方主义与新中国谋求建立民族共同体的需要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缝隙,方言文学在新时代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限制。⑥但这并不意味着陈残云放弃了对方言运用的探索。到了60年代初,在稍宽松的政治语境下完成的《香飘四季》,他又开始大量运用方言,并对方言的锤炼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美学境界。以上诸种变化都体现了政治规范与时代精神对陈残云创作发生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十七年”时期,陈残云的人道主义精神始终未被政治所遮蔽,他关注的依然是人具体的生存困境及精神世界,这使得他的小说依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描摹出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给农民带来的精神面貌的嬗变。
20世纪50年代的中篇小说《山村的早晨》《喜讯》,土改只是背景,关涉的焦点在于从家庭内部反映出农村妇女“翻身”并未“翻心”,作者思考延续的依然是“五四”时期关于“人”的解放这一沉重的命题。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短篇小说《前程》《装车记》等反映的是合作化运动,均从日常人伦切入,关注点在于表现农民面对新生事物时,精神上由于各种积习产生的顾虑,逐渐由“不通”到“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残云把农民对党的政策产生的疑惧、抵触以及对新生活的向往及渴望,种种复杂纠葛的内心世界极为生动地刻画了出来,表达了对人物高度的共情和理解。究其原因在于陈残云出身贫农家庭,与农民始终血脉相连,所以他既能够对农民在旧社会被盘剥的痛苦感同身受,亦能够对农民在新中国发生巨变时因袭的思想包袱寄予深切的理解,因此塑造出的农民形象并未完全受到政治视角的遮蔽,依然具有饱满的人性内容。
1958年到1960年,陈残云到东莞水乡蹲点工作。他发现,即便政治因素对乡村生活进行了强大的组织和渗透,一个充满活力的民间文化形态始终没有消失。由此他在《香飘四季》中再次接续上了之前以方言表现岭南农民的传统,并下了一番琢磨洗练的功夫,营构出了一个经岭南精神血缘浸泡,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民间世界。
《香飘四季》的方言运用与之前相比,更全方位地呈现了粤方言的审美质素。之前由于“受难牛”人物系列的气质属性,方言的运用更多呈现出俚俗粗放的一面。但实际上,由于粤方言对古汉语的保存特别丰厚,又兼之粤剧在民间的流行,即便是活跃在民间的语言,亦有古雅的一面。于是小说用“珠圆玉润”[13]8形容妇女主任何桂珍胖而富态的美;形容在银行工作的小李叫“白面书生”[13]30;用“一年望一年,好比犀牛望月”[13]2形容看戏希望的落空;形容徐金贵在共产党来之后被打击得“面白唇青”,“只好俯首顺从,大叹‘人财两空’”[13]21;生产队长许火照劝何桂珍返家“细斟细酌的吃顿开年饭”[13]92等,这些“雅言”与“俗语”,如“屎得很”“剥光猪”“赶狗不出门”“指冬瓜说葫芦”等,共同构成了粤方言丰富的审美内涵。此外,民间曲艺的直接融入,如粤曲、民谣等,多角度呈现了粤方言的韵味和腔调。特别精彩的是,小说讲述大跃进“大鸣大放”期间,有群众贴出的大字报,是用“数白榄”⑦的说唱形式对徐金贵进行揭发,抑扬顿挫之间生动地传递出了民间的智慧和活泼的生命情调。
为了体现方言的韵致,又不导致方言区外读者的阅读障碍,作者通过精心设置具体语境或对方言进行改写。如“画公仔画出肠”意思是画人物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会把内脏画出,比喻说话过于明显、露骨,有些不必说的话也说了出来。这句俗语出现在水生询问阿秀喜不喜欢自己之时,“阿秀轻骂道:‘你怎么画公仔要画出肠的?’说完,转过身去,双手捧着羞红的脸颊”[13]285。阿秀面对爱情的羞涩通过这句俗语表露无遗,一般的读者都能心领神会。譬如“鸡蛋那样密都孵出小鸡,总归藏不住的”[13]110是对俗语“鸡春咁密都菢出仔”的改写,作者把外地读者易产生疑惑的方言词,“鸡春”“咁”“菢”都删掉。虽然从称呼到语气及语法都发生了改变,但还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韵味。
通过方言,陈残云还鲜活地表现出了岭南文化精神中重商好利、讲究实用、灵活变通的一面。许三财带女儿去广州相亲,欲捞取聘金。荣茂表叔声称“我就喜欢知悭识俭的乡下女子”[13]105。“知悭识俭”指的是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地过日子。但他实际的想法是“一则可通过许三财搭个农村线,二则讨个来自农村的媳妇,少花钱,有人顾理家务,又不知晓他作买卖的底子”[13]105,真是机关算尽。两人在聘金上锱铢必较,直至许三财考虑到以后到广州,“住的吃的都有个落脚处,卖点东西,也有个好门路”[13]109,“那就算啦,往后还得要你多多带挈”[13]109。“带挈”是“提携并带领”的意思。一个“知悭识俭”,一个“带挈”,充分显示出两人的精明世故、圆滑变通。
除了用方言刻画出岭南文化的精神气韵,水乡儿女的生命状态在陈残云笔下是水分饱满、元气淋漓的,即便在“合作化”和“大跃进”时期,农忙之余,他们依旧下棋、打牌、田头讲故事、吃宵夜、饮早茶、看大戏、龙舟竞赛等等,这固然是对生活真实面貌的描摹,同样亦有着作家对人性欲望合理的尊重。正是这份尊重,使得他笔下不管是对“地富反坏”还是对贫雇农的刻画,都没有落入理念化的窠臼。在一定程度上,又接续上了小说集《小团圆》开创的传统,塑造的农民形象有一定的复杂性格和心理深度,而且极具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对中农许三财的刻画,其精明、重商好利的个性气质是真正属于岭南乡土的。
陈残云在1979年出版了从正面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山谷风烟》,重新接续上了从《小团圆》开创的农民谱系。但这部小说并没有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来反思土改运动,亦没有挣脱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题材写作僵硬的文学规范,与“十七年”时期的创作相比,反而呈现出浓重的图解政治痕迹。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秩序对立森严,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矛盾尖锐,但没有予人印象深刻的人物。陈残云一贯擅长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欲望的表达并没有在这部小说中得以体现,对方言的锻造,对民俗的表现,也没有得以延续。与已有的土改小说相比,《山谷风烟》并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思考。
三、香港作为始终内嵌于乡村文本中的“城”
在“粤港融合”视域下对陈残云创作的探讨,不仅是对他乡村文学版图的补遗和激活,亦是要进一步探讨香港经验是否在陈残云内在的精神世界留下了可辨识的烙印。
如果深入到文本内部的肌理,可以看到“香港”不仅是陈残云创作生涯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时段,同时作为一种“城”的文学形象以及美学经验渗透到文本内部,在不同时期与“农村”形象构成“镜像”关系,成为探索文本意义的有效途径。《小团圆》中,“香港”在“黑骨球”眼里是个“红红绿绿的城市”[3]36,但比起乡下的荒凉,母亲惨遭饿死,又是孕育“彩色的希望”[3]48的城;在《受难牛》中,香港“是个狗反之地,三句唔埋就讲打”[7]58,但比起在乡村被盘剥得无处容身,凭着“一身牛力”,“换碗粗饭总是可以的!”[7]58;在《怀乡记》中,关于香港的描写比较充分,它是一个“从海边拖到山顶的城市”,“这是一个奇迹”[14]165,但“香港的偷和抢,随时随地都有”[14]170。而同时期的乡下充斥着的是“骷髅似的饥饿的孩子和老妇人的脸形”[14]210。新中国成立以前,陈残云笔下的“香港”,是一个在物质层面具有诱人的现代性,但亦是一个道德失范的地方。至于是什么造就了繁华地,造就了“奇迹”,为什么凭牛力可以“换碗粗饭”,其中是否蕴含着乡村文明中所匮乏的积极性和合理性的因素,陈残云并没有进一步反思。如果结合陈残云在1941年发表的诗歌《海滨散曲十章》,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在对待香港上,陈残云的个人视角几乎完全被政治视角、阶级视角所遮蔽,“香港”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罪恶的渊薮。
1950年,陈残云回到广州,但“香港”始终内嵌于他的小说当中,并未消失。香港作为一个“城”的文学形象依旧被涂抹上了浓烈的政治意味。写于1955年的《异地同心》,小说中主人公旺娣嫁到新界并未过上好日子,丈夫长期失业,生计难以为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地欣欣向荣的农村新貌。在《香飘四季》中,香港是“地富反坏”逃离之所,又是一个道德沦丧之城,来自香港的浪荡子徐宝伪装成“工人阶级”,骗取了农村姑娘许细娇的情感。
在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题材创作中,对香港着墨最多的是《深圳河畔》。《深圳河畔》讲述居住在深圳边界的乡村女子亚芬拿不到通行证,与在香港当海员的丈夫分居十年,因不堪乡邻嘲弄,私自逃港的故事。陈残云当时敢于完成这样一个与边防政策有抵触的题材,并对亚芬寄予了高度的同情和理解,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言:“这篇小说是五十年代深圳河边的一幅生活小影。深圳小河是一条边防线,隔开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作品反映了小河北面一些年轻妇女的精神境界,她们对新社会热爱,对幸福生活追求。同时又揭露了小河南面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15]正是这种呈现“两个不同世界”的意图,使得小说在描写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时依然将之简化为资本主义文明罪恶的渊薮。
但细读之,不管是20世纪50年代的《异地同心》《深圳河畔》,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香飘四季》,都存在着文本的罅隙。在《异地同心》里,群娣对嫁到新界的姐姐一顿斥责,火生娘劝解道:“我们乡里姑娘们有个坏风气,叫‘三不嫁’,不是干部不嫁,不是教师不嫁,不是‘新界’人不嫁。嫁到外面去的不只她一人。”[16]在《香飘四季》中,徐宝听说“他们村子里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本村的农民,想嫁到城里去。特别是想嫁到香港去”[13]254。而《深圳河畔》,亚芬的通行证十年难求,丈夫十年不曾返乡,都是颂歌主题无法统摄的细节。
1954年,陈残云曾到宝安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兼县边防办公室主任。陈残云对深圳农村的情况是熟悉的。但是,他并没有顺着“三不嫁”风气进一步探究城乡差距的原因。尽管他在香港前后待了近十年,但始终无法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障,对现代文明建立起理性的思考。因此,香港作为“城”的形象,在文本中始终是扭曲的、片面的。对香港片面性的描述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亦无法成为反哺乡村题材写作的有效资源,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四、结语:在“粤港融合”视域下重审岭南作家之必要
1949年以前粤港两地由于地缘及文化上的亲缘,许多粤籍作家经常在两地之间往返,甚至作为一个突出的“群体”,参与了香港文学的建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自穗迁港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文协)香港(港粤)分会⑧。近年来出版的香港文学著述,亦可发现大量1949年以前粤籍作家在港从事文学活动的资料。
以陈残云为例,在《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的“新诗卷”“散文卷”“小说卷二”“评论卷一”“评论卷二”中都收录了他的作品。陈智德《板荡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中列有《陈残云:抒情和斗争的写实》专节。以上著述较为全面地肯定了陈残云居港期间对香港文学作出的贡献,也提示我们应该在一个更开阔的视域下看待他的创作。尽管与其他南来文人相比,粤籍作家的贡献在香港文学史的建构中依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反观内地出版的广东文学史或相关著述中,粤籍作家在香港时期的文学创作常常是缺失的,或有提及,也非常简单。如张振金的《岭南现代文学史》,对陈残云的创作只简单论及了1938出版的诗集《铁蹄下的歌手》。如果说这本著作的写作时间是在1989年,搜集整理资料还比较困难,但2015年出版的《岭南现当代散文史》对陈残云散文的解读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亦忽略了他在香港时期的创作。
总的来说,两地作家多数进入的是地方文学史(香港、广东),所以各自关注各自的一段成为一个现象。这样一来,作家在两地的文学史中都未得到完整呈现,影响了对作家的整体理解和评价。诸如秦牧、黄药眠、黄宁婴、黄秋耘、华胥、于逢、楼栖等粤籍文人,在1949年以前都积极参与了香港文学的建构,都需要在“粤港融合”的视域下把断裂的香港部分研究接续上,在完整的文学流变轨迹中重新阐述及定位,才能在深层次上揭示粤港文学之间的深厚渊源以及现代岭南文学源头的丰富性。
【注释】
① 《南洋伯还乡》先是由香港南侨编译社1947年出版,后收入《陈残云自选集》及《陈残云文集》时均更名为《还乡记》,本文引文以来源处的命名为依据。
② 对陈残云香港时期乡村题材创作进行关注的学者较少,许翼心曾发表过《陈残云在香港时期的文学成就》进行过概括性的总体论述,何楚熊著的《陈残云评传》也有一定程度的涉及,专门进行深入的个案解读的研究成果尚未看到。
③ 分别是《财路》《救济品下乡》《小团圆》《乡长的儿子》《受难牛》《兵源》。
④ 陈残云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就已经接触到了蒲风等左翼作家,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1945年陈残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创作自然不可能置身于左翼思潮之外。可以参看陈残云回忆其早期诗歌创作的文章。陈残云:《〈南国诗潮〉序》,载陈残云文集编委会(编):《陈残云文集(十)》,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4年5月第1版,第592页。
⑤ 根据1901年香港的人口普查资料,原籍广东者占总人口比例为97%,1931年香港人口普查改为出生地统计,出生于广东者占比为65%。具体参看刘蜀永主编的《简明香港史》(新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3月第一版,第202页。
⑥ 从20世纪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方言政策的改变,可参考王丹、王确:《论20世纪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理性》,《学术研究》,2012年第9期。
⑦ 数白榄,广东民间曲艺。白榄,是一种凉果小食。艺人沿街卖唱,有时会结合卖白榄说唱,以招揽生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曲艺形式。
⑧ 具体可参看谢力哲:《1946—1949年文协香港(港粤)分会考论》,《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