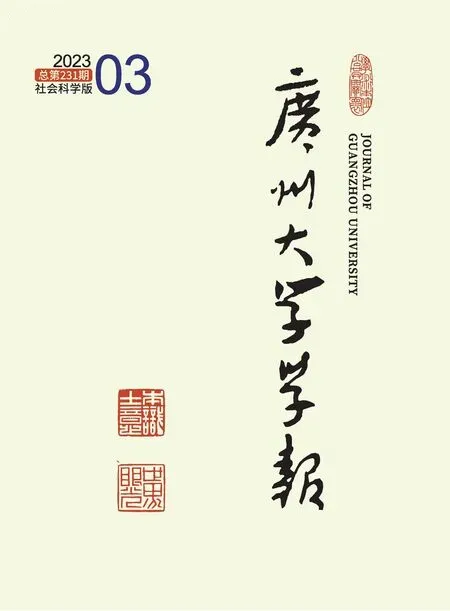奥德修斯3.0:新媒介现实与第三个神话时代
2023-08-08黎杨全
黎杨全
(华中师范大学 a.文学院; b.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一、数码神话与新媒介现实
面对数字时代的文学,比较突出的印象就是其中充满了大量魔法、仙侠、玄幻、奇幻、重生、穿越等要素的描写,这不仅包括中国网络文学中各种大开脑洞的想象,也包括国外的《指环王》《星球大战》《哈利·波特》等类型作品中的神奇写作。学术界将之称为“神话复兴”或“新神话主义”,知名学者叶舒宪概括了这一趋势:“如果从现在的主流消费群——青少年的文化消费状态来看,可以说‘新神话主义’正在席卷文化消费领域,包括文学、出版、动漫、影视、游戏等。”[1]
这种“新神话主义”显然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同,它似乎不是对日常现实的“反映”,而恰好是一种超越,或者说,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作家阿来认为,“新神话主义”是对文化传统的逆反:“过去我们整个文化,就是以反映现实为主旨,而现在超现实、幻想性的元素成为了文化的主流,不被现实文化拘束。……有一些文化对生活和历史有解读和阐释作用;而另一部分文化是对现实的逃避,让我们的灵魂和心灵得到休息。”[1]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学与现实过于紧密的关系压抑了幻想性写作,现在则是“被压抑事物的回归”,因此当代文化有两种趋势:一部分仍紧跟文化主流,反映现实生活;另一部分则具有消费属性,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试图超脱生活。叶舒宪认为新神话主义的产生是基于电脑技术的想象力:“当一个孩子每天被作业、分数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到‘新神话主义’里面就能找到一种宣泄。现代人只不过用了电脑技术这个现代手段而已,而古代用其它的方式来释放。”[1]朱大可有类似观点,认为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迅速降临,为神话的制作、传播和观看提供了新的介质。[1]
这些看法当然有道理,不过也忽视了一些重要方面。一方面,这种神话确实与技术特别是电脑技术等存在联系,不过这仍然只是从工具、手段层面来思考问题。我们应从本体层面来理解,我们认为新神话主义的生成是因为数字化社会形成了整体意义上的超越性生存氛围,神话表现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形态,而不是偶一为之的行为。另一方面,这也不只是幻想,而是生活虚拟化的投射,幻想仍是主体生发的产物,虚拟则是整体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的意识改变,或者说,这恰好不是对现实的脱离,而部分地是以神话方式呈现的新媒介现实,剥离开各种神鬼叙事的表象,背后展现的正是数字化社会的崛起。
麦克卢汉曾认为电流瞬息万里的速度给今天普通的工业和社会行动赋予神话的特点[2],而当下的数字技术显现的神话性远超电流带来的影响,它表现为整个社会的虚拟化,这种虚拟化使得神话性弥布于日常生活中间。这不仅表现为人类世界的一部分转化为赛博空间、虚拟环境,也表现为数字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互联网络遍及世界,硬件与软件带来的虚拟空间、虚拟时间重构了现实,生成了神话性与日常性相结合的新媒介现实。这并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仿像,仿像让现实消失不见,而这种虚拟维度却具有可生存性,这是数字化社会的虚拟生存,如同荷兰学者穆尔所说:“不同于鲍德里亚,我们不应该把虚拟现实想象为现实消失的一种形式,而应当视之为另一种现实的展开。”[3]150虚构不再是逃避现实,而是创造了一种异质现实,这不仅导致事实与虚构之间不再清晰可辨,也导致日常现实日益按虚拟性的维度进行改造。
这种神话性(虚拟性)与日常性相交织的新媒介现实必然影响人们的生存体验。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说法,表明媒介会深刻影响信息的内容和使用者的思想过程,而当它构成了一种可生存的媒介时就更是如此。媒介不是透明的,人们体验现实的方式部分地是由媒介建构现实的方式所决定的。如果说自现代社会以来,神话要素往往只是点缀,其基底仍是稳定而固化的物质世界观,而对数字化社会来说,神话性构成生存的一部分,这必然导致人们对世界与人的观念的改变。
从世界来看,新媒介现实带来的感受就是世界从物质的硬直性走向了可塑性(plasticity),呈现出“液态”的流动。世界是可以生成与建构的,表现出从传统的机械论世界观走向信息论世界观。在机械论世界观的图式里,自然的实际规律是预计和掌控的基础,而在信息论世界观的图式里,这些规律本身就是掌控的对象。也就是说,重点不再是什么是现实,而是现实如何可能;不再是模仿自然,而是创造新的自然。这一点通过人们对网络空间的随意操控,尤其通过玩家在游戏中对世界的开拓与建构而得到内化。
从人来看,新媒介现实带来的感受就是人有了多个化身,成为虚拟化身与现实自我的多重叠加。如果按照利科的看法,把自我视为一种故事的编织,网络带来的多重自我就加重了主体的分裂,并将这种分裂可视化了。借助虚拟化身,我们可以在网络世界中穿越、重生,可以像仙人一样生活。身体由生物学意义上的固定、硬性存在而具有了变形性(metamorphosis),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首先会被当做信息处理实体,本质上类似于智能机器”[4]10。总之,互联网的风行带来了社会后地理、后历史的本质,赛博空间拓宽了社会的神话性。
这种对世界与人的感受并不一定是明确观念,而往往呈现为人们的存在无意识,而这必然渗透在文学上。数字时代的文学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它构成了一种“现代神话”,不仅表现在它具有罗兰·巴特所说的现代神话的意识形态功能,如它突出的造梦心理(YY),也表现在它以神话的方式呈现了新媒介现实。这种现代数码神话并不是弗莱所说的神话的循环,而是新媒介现实带来了神话性,表现为整体上的世界观与潜在的思维框架,构成了规范社会群体思想与行为的一整套文化环境。从数码神话去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学,有助于认清它的意识形态性质,也能看清文学的某种深层变化,它呈现的架空、随身、穿越、重生、代入等现象,表面上是神话,实际上是现实,或者说是神话表象下的现实。
二、诸神的复活与第三个神话时代
联系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数字时代诸神的复活可视为第三次神话浪潮。第一次是上古时期的纯真神话,第二次是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主义,第三次则是当下数码时代的神话。
由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早期产生了神话,以神话来解释周遭事物。此后文化史总的趋势是“非神话化”,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与19世纪的实证论,堪称“非神话化的高峰”。世界的祛魅过程不利于神话的生存,不过在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却兴起了一股神话浪潮,如梅列金斯基所说:“文学和文艺学中的这种神话主义,为现代主义所特有。”[5]2现代主义文学中荒诞、变形的写法取代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如实呈现,即使是20世纪的现实主义,也开始大量吸取现代主义的神话手法。在梅列金斯基看来:“神话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无疑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觉察,即对整个文明危机的觉察。”[5]3这话说得有道理。由于对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焦虑,现代主义文学普遍采用神话模式,这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艾略特、乔伊斯、福克纳等诸多作家的创作中。艾略特的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存在大量与荷马史诗中神话的联系,代表作《荒原》中则暗含了死而复生的神话隐喻。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人物关系与《奥德修纪》类似,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时间与基督的受难、复活相重合。与这种明显借用古代神话题材、情节或象征含义的写法不同,卡夫卡的创作更具有代表性,在他的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神话化描写具有某种自发性。也就是说,它不是诉诸理性,而是日常生活本身荒诞性的折射。而到了数字时代,如前所述,诸神同样复活了,这可视为第三个神话时代。
这三个神话时代呈现出一些相似性,具体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神话性与日常性的结合。对原始人类来说,他们无法区分神话与现实,将自身情感投射于周围环境,意识与环境是浑融一体的。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神话主义的兴起是因为生活本身有了变化,产生了日常性与荒诞性相结合的感受。这尤其表现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他的创作不是直接取材于神话,笔下的主人公并非祖先、神祇或造物主,而恰好是现实的普通人,是世俗化的时间与空间,但却构成整个人类的象征与隐喻,他们的日常生活本身涌入了荒诞性。比如在小说《城堡》中,城堡并没有聘请土地测量员却认可了K;K没有进行工作却得到奖赏。K给城堡打电话,全部电话铃会一起响,每次通话都以嗡嗡声或玩笑声结尾。K跑到一个既不需要也无法安顿守门人的学校去当守门人。……种种荒诞性,却又体现为日常生活的细节。对卡夫卡来说,K这种生活就是存在的象征。人类就是生活在彷徨之中,在种种滑稽可笑的情形里企图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情。诚如加缪所说的那样,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销作用,贯穿着卡夫卡的全部作品。卡夫卡的笔下总是呈现两个世界的混淆:肉身凡胎的人物,从事尘世间的职业,突然摇身一变,一切行为成了象征性的行为,他们自己则与象征性的人物直接混在一起。而这正是生活的异化产生了神话性(荒诞性):“这种幻想较准确、较契合地展示‘现代主义的’意识状态和卡夫卡其时所处周围‘世界’的状貌,特别是异己现象、人性的同一化、个体在现代社会集体中的存在主义孤独感,等等。”[5]393这种神话性与日常性的结合也表现在数字时代,现实(日常)与虚拟(神话)日趋混合。如前所述,数字化社会并不是体现为别一空间的存在,而是呈现为数字网络对日常生活的内部改造与殖民,这表现在数字时代的文学中,也往往充满了人与神的混杂、学院与江湖的混同、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广泛连接。
二是命运感。古代神话往往有命运感,比如在俄狄浦斯神话中,太阳神的预言成为高悬于俄狄浦斯头顶的命运,他越是挣扎反抗越是陷入命运的魔掌。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主义同样呈现了深沉的命运感。在卡夫卡的《城堡》中,K想进入城堡,想尽各种办法都无能为力,而高高在上的城堡以命运的威严拒绝人类的思考。在《审判》中,约瑟夫·K无故被捕,最后被像狗一样杀掉,表现了外在于个体的权威对人的绝对统治,而人的努力只能是无结果、无意义的求索。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人物行为、性格及小说情节都呈现出重复性,表现的也是不断轮回与原地踏步的宿命感。如果说古代神话中的命运往往体现为某种超越于生活的神迹,现代主义文学却没有这种凌驾于人之上的超人观念,恰恰相反,它体现为司空见惯的、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本身的恐惧感。越是这种无形的恐怖,越让主人公的压抑感和孤独感真实可信。与纯真神话及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主义”相比,数字时代的文学似乎很少体现这种命运感,取而代之的是主体性的张扬,或者说对命运规则的蔑视与打破,比如在中国网络文学中,常见叙事模式是描写一个初始是普通人甚至“废物”的主人公,面对惨淡人生,他要逆袭,他的口号是“逆天”,要改变命运,凭借各种开挂的“金手指”走向成功,小说的题目也表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逆天”意味,如《吞噬星空》《遮天》《斗破苍穹》《仙逆》之类。然而“金手指”本身是命运的黑洞,表现了主体对它的依赖。比如在《斗破苍穹》中,随叫随到的老爷爷就是金手指,它投射的实际上是玩家与系统的关系,进一步看也就是人机关系的隐喻,机器成为肢体的延伸,人借助机器变得强大,不断走向成功,但一旦离开机器,则退回类似婴儿的无能状态。如果说古代神话中命运往往是自然的化身,现代主义文学时期则表现为社会对人的主宰,而在数字时代,技术/机器既增强了人的主体性,也成为笼罩在人头顶的未来阴影。
三是死而复生模式。在古代神话中,死而复生的情节模式构成了一个原型。死亡意识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只有人类才能对死亡进行思考与审视,这种反省意识在先民神话中就表现出来了,先民试图从自然界的循环中实现永生的梦想:“原始人通过赋予时间以循环方向的办法来消除时间的不可逆性。一切事物均可在任何瞬间周而复始。……生命的高峰也就是死亡的前奏,而死亡则又是生命(复生)的准备。”[6]或者说,这表现了神话与历史的对抗。历史代表着过程、不可逆转,而神话则意味着稳定;历史在运动中摧毁着旧秩序,而神话在永恒中寻求安慰。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生活的自然循环遭到破坏,因此作家引入神话的死而复生模式,意图实现文明的再造与新生。在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中,面对枯寂的荒原,惟有骑士拿着长剑,找到生命的圣杯,社会才能获得拯救。在诗人焦灼的呼吁中,包含了一个死而复生的原型。现代主义中的轮回表现的是生活的困局以及对改变困局的渴求(如希望循环后回到以前的有机世界)。死而复生的冲动在网络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企图将死亡驱离我们的生命乃是新文化的独特性质”[7]。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为了驱逐死亡,对抗时间,总是以各种方式来铭记当下、留住永恒,而为了获得永恒(哪怕是象征性的),也注定会有权力与身份的差别,然而这种差别在网络中却淡化了,虚拟性的死而复生让每个人获得了“不朽”的权力,个人的生活与经历可被永久记录,永恒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性。在此情况下,死亡不再神圣,死亡不再标志着永远缺场,而成了一种消失行为(disappearance acts):“消失者仅仅是临时缺场,而不是永远缺场——他们在技术上是存在的,安全地被储存在虚拟内存的硬盘上,总是准备着不费吹灰之力地在任何时候得以复兴。”[8]受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数字时代的数码神话中,同样包含了死而复生的情节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数码神话与纯真神话中希望获得永生的梦想是一致的,在根源上正是借助“循环”的时间观来医治人类的心灵创伤(表现为大量重生小说试图弥补过往的遗憾)——而这正是神话的功能。
在数字时代,诸神再次复活了,数码神话构成了第三个神话时代。
三、奥德修斯3.0与后人类形象
第三个神话时代表现了人类命运的演进与新趋势,如果我们借用奥德修斯的形象来理解,数字时代的人类形象可称为奥德修斯3.0。
“奥德修斯的形象……深深打动我们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命运在很多方面代表着人类的总体命运。”[3]6从东非第一种灵长类动物出现,人类历史一直表现为持续不断地跨越地平线的旅程。在此意义上,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成为人类化身的原型,他的漂泊故事在西方文学史中有诸多描写。古罗马作家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以荷马史诗为范本,前半部分写漂泊,与《奥德赛》情节相似。前面提到的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情节模式上也正是戏仿《奥德赛》。还有根据科幻作家亚瑟·查理斯·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的小说改编、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科幻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2001:ASpaceOdyssey,1968,国内往往译为《2001太空漫游》),也是以“奥德赛”命名,其重要性在于,这是第一部以人工智能(超级电脑“哈尔”)为主角的电影。
如果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科幻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三部作品为代表,其中不同版本的奥德修斯正好对应了三个神话时代的人类形象及对世界的探索。
《奥德赛》类似于对波普尔所说的第一种世界即物理世界的探索,奥德修斯与巨人、塞壬等的关系可视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隐喻,而奥德修斯代表的是第一个神话阶段的人类形象。这种探索时至今日仍然在发展,不过,“在文化史的进程中,随着高效的交通工具不断地发展,这种对物理和地理空间的文学探索已经过时”[3]56。而波普尔所说的第二种世界即对人类主体内在空间的探索也得到快速发展,这不仅体现在笛卡尔等人意识哲学的演进、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的创立,也表现为从塞万提斯以来一直在发展嬗变的现代小说传统中,“几百年来的小说的伟大传统是文学重点从第一种世界向第二种世界转移的结果”[3]56。而第二个神话时代即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主义正体现了对心理世界的探索。现代主义文学试图摆脱现实主义传统,物理空间中发生的事件不再是中心,而呈现“向内转”的趋势,而这又典型地体现在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中,小说最后40页的长篇内心独白正是探索第二世界的极致表现,而心理学家荣格对小说的浓厚兴趣也佐证了这一点。小说题名的“尤利西斯”是罗马神话的英雄,对应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而小说中的主角布卢姆正是现代版的奥德修斯,只不过与古代英雄相比,现代版的奥德修斯变得猥琐、无能,隐喻的正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而科幻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中的人工智能超级电脑“哈尔”,预示的则是当下及未来数字技术、生命技术生成的虚拟世界与后人类形象。如果说第二个神话时代表现的是向内部意识经验的突进,在第三个神话时代,意识开始摆脱身体,变得可视化了,开始悬浮在电脑空间中。这种情况也渗透在文学中:“在这些小说中,对物质世界的探索不是中心,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也不是中心,中心是对无限拓展的、自主性不断增强的‘客观心灵’的‘非空间’的探索。”[3]57第三个神话时代的奥德修斯代表的正是后人类时代的人类命运:“或许我们正站在新新石器时代(the Newest Stone Age)的门槛上,在这个时代,地球上的智能生命将获得一种人类尚未认识的新形式和新方向。而谁又知道,那时人类是否会在穿越时空的生命奥德赛中,分享曾经为人类留下化石(活化石或死化石)的无数物种的命运。”[3]249
既然奥德修斯3.0代表的是数字技术社会的后人类形象,数字时代的文学就具有了文学人类学的意义,应该站在人类学的视野与高度来理解与研究它,可凭此深入揭示数字化社会的文化变迁与人类心理结构的转型。数字时代的文学表现的是向第三种世界的转向:“在20世纪,随着现代传播工具、大众传媒和电脑技术的发展,空间探索的重点又发生了转移。这一次是转向了对第三种世界的虚拟空间的探索。赛博朋客文学可以视为这种穿越赛博空间的奥德赛的文学表现。”[3]57其中的主体关系开始呈现从人类意识向后人类意识的渐变,如阿斯科特所说:“21世纪的艺术可能会形成一个调节人类和后人类意识的模式,就像在过去的文化中,它经常被用于人与神的沟通。”[9]
这就表明,数字时代的文学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它呈现出表层与深层的分离,表面上是各种神鬼情节与大众欲望,但深层折射的是数字化社会的来临,是以神话方式反映的社会现实。以网络文学为例,网络文学中兴起了聊天群小说,代表作是网络作家“圣骑士的传说”的《修真聊天群》。这部小说在2018年第三届“橙瓜网络文学奖”的评选中,获得年度十大作品奖。此后陆续产生了不少以“聊天群”为名的小说,形成了一种写作浪潮。这种小说以聊天群推动故事的发展,往往写一个主角在前行过程中遇到诸种障碍,但由于一直有聊天群相伴,借助聊天群里众多网友的主意,主角总能逢凶化吉,不断走向成功。这种小说表面看来似乎是网络文学常见的欲望叙事,但如果深入分析,其实表现了网络社会兴起后网络共享与社群智慧的社会症候。网络上各种社交软件、论坛与聊天群,各种问答网站、咨询与攻略的广泛兴起,都表现了因网络讨论而生成的社群智慧。因此,网络小说主角的强大似乎张扬了主体性,表现了个人意志的自由人本主义观念,但如果从深层来看,呈现的却是后人类的主体性:“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4]4-5在聊天群小说表现的社群智慧中,个体融入了众多的“他人意志”。从网络中成长出来的常常是“群体生物”。这种集体异源性不仅表现在融入了他人的意志,也表现在融入了机器的“意志”(如网络搜索)。在这种后人类状态中,数字时代的分布式认知取代了传统的自主自律的意志。在此意义上,我们就不能将数字时代的文学简单理解为所谓大众文化、通俗文学,而应基于文学人类学,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从中考察人类社会从“部落化”到“非部落化”再到“重新部落化”的历史过程,这是数字时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这也涉及到对数字时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一般来说,印刷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文学往往强调形式的实验与人性的深度,在此标准下,数字时代的文学往往遭受歧视。按照穆尔的看法,这是因为各种文学经典以及相应的评价体系是与第二种世界,即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紧密相关,而对数码神话时代的文学来说,对物质世界的探索与精神世界探索都不是中心,它们更关注客观心灵的非空间探索,于是这类小说往往很少关注人物性格的心理发展问题,也因此在经典文学世界中容易遭到否定性评价。联系前面提到的三部象征性的作品,即荷马史诗《奥德赛》、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科幻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可以发现它们的媒介形式(史诗、现代小说与电影)也别有意味,实际折射了与三个神话时代相对应的口头文化、书面文化与超媒体文化。书面文化表现的是人类思想的不断抽象化与内化,而口头文化与当下的超媒体文化则呈现出类似的碎片化特征,“存在于希腊神话中的深度的匮缺与数字世界肤浅的辉煌可说是异曲同工”[3]215。在此意义上,不能以印刷文化时期形成的评价标准来理解口头文化与超媒体文化,这种标准具有历史性,人们把它当成了不证自明的东西,从而把书面文化的理想寄托在错误的传媒上。对数码神话时代的文学来说,应发展与建构自己的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