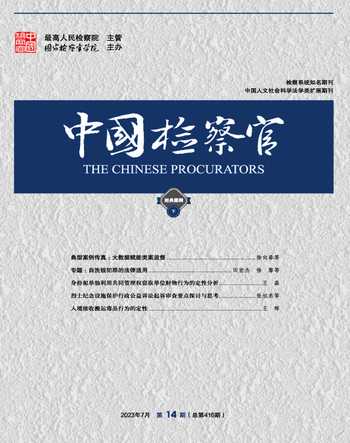被告人品格证据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运用及对我国的启示
2023-08-07姜宝成魏琪
姜宝成 魏琪
摘 要: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具有性侵犯罪隐秘性和被害人低龄化的双重特性,这导致该类案件在办理过程中面临着证据收集难、证明难度大的困境。U.S. v. Castillo案在审理过程中上诉法院对《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4条的正当性和合宪性進行了分析与论证,明确了被告人品格证据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可采性。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在被告人品格证据运用上,可以在满足“必要性”“关联性”“程序合法性”的情况下予以借鉴。
关键词:品格证据 性侵未成年人 例外规定
一、《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被告人品格证据概述
(一)被告人品格证据的一般规定
被告人品格证据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品格证据中最主要的内容,《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条(a)(1)项规定,关于一个人的品格或其品格特征的证据不能用来证明该人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的行为符合其品格或品格特征。同时第404条(a)(2)项规定了被告人的品格证据适用于刑事案件的三种例外情形:一是当被告人提供与其品格特征的相关证据时,如果该证据被采纳,公诉人可以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二是在遵守第412条规定的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当被告人提供刑事被害人品格特征的相关证据时,如果该证据被采纳,公诉人可以提供相对证据予以反驳,并可以提供被告人具有相同品格特征的证据;三是在凶杀案中,公诉人可以提供被害人性情温和的品格特征证据,以反驳被害人是事先挑起事端者的证据。[1]即在一般情况下,公诉人不得以被告人的品性来证明其行为与品性具有一致性,被告人的品格证据与案件事实没有必然联系。
(二)性侵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例外规定
1994年,美国联邦议会通过了《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3条、414条和415条。其中第413条和第414条是性侵刑事案件的相关规定,第415条是性侵民事案件的相关规定。第413条(a)规定:在被告人被指控涉嫌性侵犯罪的刑事案件中,美国联邦法院可以采纳被告人曾经实施任何其他性侵行为的证据,并且该证据可以在任何与之相关的事项上加以考量。[2]第414条(a)规定:在被告人被指控涉嫌性侵儿童犯罪的刑事案件中,美国联邦法院可以采纳被告人曾经实施的任何其他儿童性侵扰的证据,并且该证据可以在任何与该指控犯罪相关的事项上加以考量。[3]
根据第413条和414条的规定,被告人曾经性侵他人这一事实,可以用来证明在当下被指控性侵犯罪的案件中,被告人实施了性侵犯罪。同时,对于被告人曾经性侵他人的行为是否被正式起诉或定罪,都不是该证据具有可采纳性的前提条件。该法条明确了先前特定的不良行为可以作为品格证据用于证明某人从事与其品格相符的行为。该法条颁布以来,学者对于第413条和第414条的争议不断,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第一,该规则允许用被告人的先前行为来证明其不良品格是不公平的;第二,该规则认可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第三,使用发生在多年前未被指控的行为的证据来证明当下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不合理的;第四,根据有关排除被害人性经历证据的法律规定,对被告人的性经历应采取类似的处理方式;第五,第413条和第414条规则是违反《美国宪法》的。[4]但这些反对意见,遭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反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3条的适用,即如果证据带来的不公平偏见、混淆争议焦点或是误导陪审团、不当拖延、浪费时间、不必要地出示重复证据的风险大大超过该证据的证明价值,则允许美国联邦法院排除该证据,该条规定已经保证了所采纳的品格证据不会受到不公平偏见的影响,因此第413条、第414条的规定并不违反美国宪法[5],且其对性犯罪的有效起诉起到促进作用。第413条的立法历史表明,立法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该规则因性侵犯案件存在独特特征而具有合理性,这些特征包括性犯罪案件往往依赖于无法确定可信度的证据,该规则如果无法适用,这类案子将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同时,在性侵儿童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对儿童的性兴趣极具证明价值。[6]
二、U.S. v. Castillo案与案件争议焦点
(一)U.S. v. Castillo案的基本情况
被告人Serefino Castillo住在新墨西哥州克朗波因特的纳瓦霍保留地,他和妻子共育有五个孩子。1994年的夏天,Castillo对其女儿N.C.和C.C分别实施了性侵犯。1996年,Castillo因涉嫌对未成年人实施性虐待罪被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实施了四起性虐待犯罪事实,其中三起是针对其女儿N.C.实施的,一起是针对其女儿C.C.实施的。在审判中,初审法院不仅允许N.C.对起诉书中指控的针对其实施的前三起性虐待行为作证,还允许其对起诉书中指控的针对C.C实施的第四起性虐待行为作证。同时,除了起诉书中指控的第四起性虐待行为外,C.C.还对被告人曾对其实施的其他两次性虐待行为进行作证。初审法院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4条的规定确认了证据的合法性。
被告人Castillo因对未成年人进行性虐待被美国新墨西哥州地区法院定罪,后被告人提出上诉。其辩称:(1)第414条规则在审判时无效;(2)第414条规则侵犯了其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享有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权利,以及根据《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享有的免受残忍和异常惩罚的权利;(3)第414条规则所引入的证据具有极大的偏见应被排除。[7]上诉法院对被告人的辩解一一作出了回应。
(二)上诉法院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的回应
1.第414条规则在审判时是否有效
美国联邦议会在制定规则时规定,《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3、414、415条适用于1995年7月10日之后开始的所有审判。本案的审判开始于1996年5月,在1995年7月10日之后,因此第414条规则可以适用于该审判。
2.第414条是否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
当一项规则违背了“基本公正”这一概念时,才能考虑它违反了《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这一基本原则。“基本公正”即是所有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并定义了社会公平竞争和行为准则。[8]另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违反“基本公平”的行为类别的定义非常严格。上诉法院认为第414条规则并不违反“基本公平”,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表示,在确定一项规定是否具有“基本性”时,主要依靠历史实践。[9]而早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一些州就制定了“好色倾向”规则,该项规则允许公诉人提供被指控以外的性行为证据,以证明被告人有实施性犯罪的倾向。直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州在涉及性犯罪的案件中保留了“好色倾向”规则,其中包括涉嫌性侵儿童犯罪的案件。且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Egelhoff案中所提及的,应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规则所违反的程序原则,而不是国家机关。[10]第二,被告人认为当提出其行为倾向性证据时,如被告人先前犯罪的证据,就会产生陪审团将因被控告的罪行以外的行为而被定罪的风险,或者,在不确定有罪的情况下,陪审团会因为“坏人应该受到惩罚”的想法而认定被告人有罪。事实上,允许出示被告人先前犯罪的证据是令陪审团结合该事实对当下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判断,而并非已经认定被告人有罪。第三,当一个州在有罪判决阶段,提供被告人先前犯罪的证据仅与其量刑有关时,该州并不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第四,被告人辩称第414条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理由是,第414条具有极大地偏见以致于侵犯了其获得公平审判的基本权利。然而,第403条的适用,已经排除了具有这种不利影响的证据。因此,如果初审法院已经充分考虑到第403条所规定的不利影响,那么适用第414条并不违反正当程序原则。
3.第414条是否侵犯了被告人享有的平等保护的权利
尽管《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没有平等保护条款,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对正当程序原则的规定体现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平等保护原则。根据平等保护原则的规定,如果一项法律规定既不会加重被告人基本权利的负担,也不会被视为可疑分类,即在判断该法律所用“分类”是否合理时,要看“分类”是否为政府立法目标所必须的,只要它具有某种合法目的,就应当坚持将法律规则进行分类。而第414条所引入的品格证据符合该要求,虽然该规则确实将那些被指控性侵儿童的被告人与其他刑事被告人区别对待,但这种区分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目的性。在 Enjady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提到 ,立法机关加强对性侵案件的有效起诉是具有正当性目标的。国家机关需要在性侵儿童案件中提供确凿证据,因为这些性犯罪往往具有极高的隐蔽性,而通常唯一可用的证据就是儿童的证词。因此,第414条规则没有侵犯被告人享有的平等保护权利。
4.第414条是否侵犯了被告人享有的免受残忍和异常惩罚的权利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国家机关如果是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如一个人是瘾君子),而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如一个人去购买毒品),而对其实施刑事处罚,则侵犯了其根据《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所享有的免受残忍和异常惩罚的权利。根据被告人Castillo的辩解,第414条的规定是对其作为对未成年人有性兴趣的个人身份进行处罚的。而事实上,第414条的规定所引入的证据是针对其曾经实施过的行为而非个人身份,且在第402条[11]和第403条规则的保护下,第414条的适用已经排除了任何可能存在偏见的情况。同时,该规则仅仅是一条证据规则,无法据此对被告人直接施加刑事处罚。因此,第414条并没有侵犯被告人依据《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所享有的免受残忍和异常惩罚的权利。
5.第414条是否通过了第403条平衡测试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4条在适用前要通过《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3条的平衡测试,即在判断品格证据是否能够采纳时,必须结合该证据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进行综合判断。如果证据所引起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其证明价值,则该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如果证据所引起的负面影响远小于其证明价值,则该证据具有可采性。因此,在本案中上诉法院认为,由于品格证据的独特性质,初审法院应在排除第403条所规定的负面影响后,对根据第413、414、415条规则引入的证据予以确认时做出合理的解释并记录在案。但初审法院对这一问题的简易处理使上诉法院无法审查其裁决的适当性。因此,上诉法院要求初审法院对此作出详细解释并记录在案。
(三)上诉法院最终结论
最终,上诉法院法官Tacha得出结论:(1)在性侵儿童犯罪的刑事案件中,允许采纳被告人性侵其他儿童行为作为其品格特征的证据,不违反《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2)允许采纳被告人性侵其他儿童行为的证据规则不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原则;(3)允许采纳被告人性侵其他儿童行为的证据规则不违反《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规定的免受残忍和异常惩罚的权利;(4)要求初审法院解释其裁决,即被告人涉嫌其他性侵儿童行为的证据所引起的偏见没有极大地超过该证据的证明价值;(5)有证据支持定罪。[12]
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运用被告人品格证据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发展现状与证明困境
近年来,我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不断增长,从最高检统计的数据看,2018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万人,每年平均上升3.6%。其中,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万人,占比45%。[13]可见,此类犯罪已成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占比相对较大的犯罪。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犯罪背景复杂、证据分布不均衡,导致该类案件在办理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其中证据收集难、证明难度大是办理此类案件的主要困难,其原因在于:一是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地通常较为隐蔽,如学校、当事人的住所、宾馆等地。由于此类场所的隐蔽性和私密性较强,案发现场往往不存在除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外的其他人员,同时也少有电子監控等设备,因此缺少电子证据以及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二是未成年人仍处于身心发育阶段,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尚未完全成熟。在受到侵犯后,并不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或是即使其意识到也会因为羞耻心而不愿寻求法律帮助,这使得许多案发时存在的证据,如犯罪分子留下的体液、指纹等未能及时得到有效的保存而灭失,而这些证据对案件性质的认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受身体和智力发展的影响,未成年人的记忆力、感知力、表达能力有限,不能准确回忆起案发的详细过程,导致其陈述的内容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从而使其陈述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四是因大多数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往往严重缺乏客观证据,被告人往往拒绝作有罪供述,此时则需要通过大量的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进行印证,进一步加大了证明难度。
上述事实导致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只能将被害人的陈述作为主要证据。当出现所谓“一比一”证据的情况,即案件中只存在被告人的供述与被害人的陈述作为证据,且二者的言词内容又处于对立面时,根据印证证明标准的要求,应有其他证据与被害人的陈述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确定被害人陈述的可信度,否则可能会陷入证据不足导致无法追诉犯罪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引入,能够有效分析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动机以及其行为的倾向性,帮助解决该类案件中的疑难问题,从而应对在办理该类特殊案件过程中证据不足的局面。因此,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引入被告人品格证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二)我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运用被告人品格证据之思考
尽管中美两国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在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上有着共同的诉讼理念和价值目标。首先,从犯罪性质来看,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严重挑战社会公德,有必要严格打击此类犯罪。其次,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證明困境亟待解决,有必要对证据制度进行调整,以实现有效追诉犯罪。最后,可以通过引入被告人品格证据来实现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平等保护。当然,《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仍存在不完善和争议之处,但通过对此规定的诉讼理念、相关案例进行深入探析,能够为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提供理念与具体操作上的借鉴。基于以上阐述,现对我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运用提出以下几点思考意见:
1.运用被告人品格证据应以“必要”为原则
在涉及性侵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中,品格证据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化解该类案件难以证明的困境。然而,我们要注意到此类证据在定罪量刑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并在运用中对该类证据加以限制,加强审查其与案件的“关联性”以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保证其运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如果通过品格证据所证明的案件事实能够用其他更为准确、便利的方式予以证明,有其他证明力更强的证据证明相同事实,运用品格证据会对被告人造成明显的不公正,或是品格证据不具有足够的证明价值时,该品格证据应予以排除。
2.“关联性”应为判断被告人品格证据可采性的基本条件
从美国的立法经验及判例来看,对于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可采性,并非简单地采取一律采纳或一律排除的方式,法官应当结合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而“关联性”是作为法官排除或采纳该品格证据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关联性”进行考量:(1)先前的行为与被指控的行为的相似性,如被告人实施性侵时所使用的方式、手段或工具等是否存在一致性。(2)先前事实与当下事实中被害人与被告人关系的相似性,如在上文的Castillo案中,C.C和N.C均系Castillo的女儿,二者都系亲属关系。同时在判断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是否相似时,应当主要以关系的本质而非关系的形式为标准,如“继父和继女”的关系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看,在两种关系中,被害人都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此种情况仍可以认为二者具有关联性。(3)事件发生背景的相似性,如前后事实发生的时间均在凌晨、地点均在宾馆等隐蔽场所。(4)案发时间的接近性以及案发频率的相似性,一般而言,当前性侵行为案发时间和之前性侵行为案发时间越相近,则关联性越强,证据的证明力也相对越高。另外,如果发现被告人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持续实施性侵的行为,则可以证明被告人的这一行为倾向较为稳定,行为倾向越稳定,则关联性越强。[14]
3.保障运用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合法程序
被告人品格证据运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对被告人产生的不利影响,因此要充分考虑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诉讼权利之间的平衡。《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4条(b)规定,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如果公诉人准备提供品格证据,应在审判前至少15天以内或因正当理由经美国联邦法院允许的延迟时间内向被告人进行告知,告知内容包括证人的陈述或预期证言的概述。[15]参考该规则,对于公诉人拟提出品格证据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我国可以利用庭前会议机制。法院召开庭前会议,允许被告人对提出的品格证据予以反驳,以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