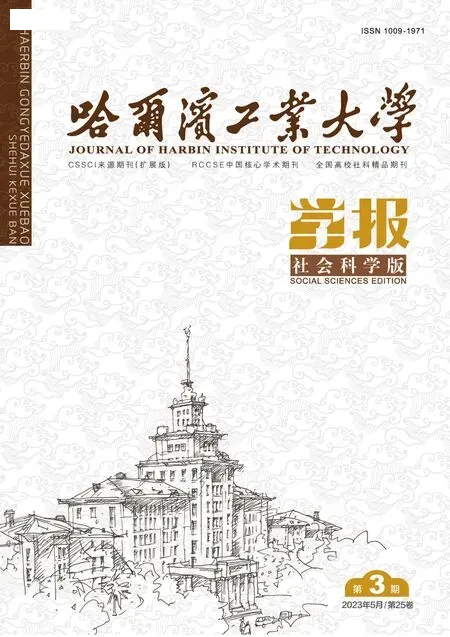清小说《绿野仙踪》中辞赋的形态、艺术效果及其成因
2023-08-07丁涵
丁 涵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李百川的百回小说《绿野仙踪》创作于清乾隆中叶①本文选用的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旧藏百回抄本《绿野仙踪》是最接近此著原貌的底本(见周晴《陶家鹤与〈绿野仙踪〉试探》,载《文学遗产》2009 年第6 期)。 关于百回本和八十回本两种版本系统的优劣,一般认为百回本“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结构方面”都优于八十回本,且百回本不仅内容充实、文字准确,还难得保存有反映作者李百川生平和思想的一篇自序(见侯忠义《论抄本〈绿野仙踪〉及其作者》,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1 期)。 不过也有少数持异见者,见陈新《〈绿野仙踪〉的作者、版本及其它》,载《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1 期。,在问世之初便被友人陶家鹤叹赏为“说部中之极大山水也”[1],然而在之后的近两百年间却长期遭受遗珠弃璧的命运。 迨及近世,黄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就在《小说林》开始连载《小说小话》[2],首次将其引入小说研究视野。 随后这部小说影响日著,好评如潮。 鲁迅《小说旧闻钞·杂说》就曾激赏《绿野仙踪》的部分章节“能别出机杼”[3];郑振铎也曾将其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举为“清中叶三大小说”[4]179-180。 回顾自20 世纪初以来中外学者涉及《绿野仙踪》的批评,大致集中在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作者籍贯、版本比勘、情节来源、叙事结构、人物形象、语言样本、评点译介和价值定位[5],相对而言,于小说与内部其余文体交融的关系上略为薄弱。 恰恰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演变进程中,杂交参融不同类型的韵文文体是小说创新和扩容的一种重要模式。 自宋至清,小说与诗词曲赋融合现象的批评经历了从评点诗词曲赋本身的属性品格到审视诗词曲赋之于小说整体构成意义的演进过程[6]。 时至今日,这种交叉取径已成明清小说研究的一大趋势和热点。 与《绿野仙踪》中夹杂的诗、词、曲等使用情况还有显著不同,置于其间的辞赋,于习见的韵文套式作用之外[7],更具有塑造人物和谋篇布局的情节与内容意义。 对孱入辞赋的独特形态方式、美学效果和背景规律的分析,非但对考察这一部小说有益,同时还将对明清小说与韵文体裁融织互补的整体机制有所发明。
一、辞赋在《绿野仙踪》中的出现位置、展开场合及表现形式
《绿野仙踪》夹带的辞赋文字所处章回文本的位置、故事发生的场合和内容表现的形式均较为多元。 试先看一些小说中的对称性结构定式①美国学者浦安迪指出对句形式的回目常常意味着回内情节内容的对应均衡(见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52 页)。 其实,这种对称性也往往适用于开篇和结尾诗词中。,例如,辞赋文字密集出现的第七回,该回目“走荆棘投宿村学社,论诗赋得罪老俗儒”一联提纲挈领,标明“论诗赋”是后半回故事的梗概;开篇词《贺圣朝》下半阙云:“投宿腐儒为活计,过今宵。因谈诗赋起波涛,始开交。”[8]上册99提示以“谈诗赋”导引本回情节进入正题;收尾诗“腐儒诗赋也相同,避者可生读者死”两句[8]上册123,着重用“腐儒诗赋”作点睛之笔。 这些辞赋文字出现的指定位置和承担的常规功能、角色与附着于小说中的诗、词等其他韵文体部分并无二致,或许充其量仅是明清章回小说以词起、以诗结的寻常章法[9]。 但是,小说中更出彩的是灵活分布于章回正文各个部位的例证,而它们的出现位置又通常与其具体的展开场合和表现形式相应。 安置于每半回篇幅开头或末尾的辞赋,一般发生于回中故事的开端或尾声,并以小说人物对话的口头形式呈现辞赋意见;而杂错在每半回篇幅当中的辞赋,则一般发生于回中故事的高潮,并以小说人物阅览的文本形式呈现辞赋作品。同样再以第七回为例,在后半回的一开始,下半段故事的领起标记是始于以辞赋作为闲谈之资的活动。 腐儒陈继苏兴之所至,向借宿的主人公冷于冰泛泛介绍他的包括古赋等各种体裁在内的众多“大作”。 随着后文中冷于冰对陈继苏个人赋集细致展读的推进,陈继苏所作《臭屁赋》和《畏考秀才赋》的全文自然而然地在读者面前逐一呈示。 在这两篇完帙中间,另有陈继苏《十岁邻女整寿赋》《八卦赋》《汉周仓将军赋》等二十余篇、《大蒜赋》《碾磨赋》《丝瓜喇叭花合赋》三篇,还有人物、山水、昆虫、草木等题旨无所不有的众多辞赋篇什。 伴随冷于冰披览赋集过程的带动,陈继苏各篇辞赋虚实相生、繁简配合的面目,或是以全录的方式、或是以存目的方式、或是以归类的方式居于下半回篇幅的正中,同时也恰好处在下半回故事的高潮阶段。 临近回末,故事终于在陈、冷二人对待《楚辞》名篇的态度、比较古今辞赋的论辩交谈中告一段落。 再如,第六十五回,由“游异国奏对得官秩,入内庭诗赋显才华”双句回目,概括“诗赋显才华”是后半回故事的精要;又借开篇词的末联“水晶帘外会蝉娟,题诗赋挥笔洒瑶笺”云云[8]下册255,标识“题诗赋”是本回故事的紧要处;而正文中段经由内官们“传出个纸条儿来”的活动,带出了纸上承载的文字,即颁布主要人物之一——温如玉此次应试需撰作的赋题为《并蒂莲花赋》,并接下来再通过传递,一字不漏地展示温如玉交出的答卷,借以完整地呈显了全赋的文本,而整回故事的情节亦因之峰回路转。
综上所述,《绿野仙踪》在相关章回的不同位置融引用赋题、改写赋语、自创赋篇的主要用赋手段于一炉,穿插着以小说人物对话形式而呈现的辞赋观念,和以小说人物阅览形式而呈现的辞赋文本两种常见用赋形态,其所合成的一套辞赋话语又或隐或显地化为了小说文本的组成要件、人物的活动方式和情节的转换媒介。
二、《绿野仙踪》引进辞赋后的艺术效果
《绿野仙踪》中的辞赋篇目和辞赋话题往往流溢着浅俗、诙谐的风貌,初读之下或许令人容易留下对其谑而近虐的单一表面印象。 然而就在这层印象外衣之下,却隐藏着学者文人辞赋之典雅醇正的语句笔法和严肃深沉的寄托内核。 以致植入此小说中的赋作、赋论既有别于正统的雅赋范畴,亦区分于纯粹的俗赋范畴,甚至某种程度上,使得整部小说的艺术效果也接近在介乎雅、俗或庄、谐之间。
比如第七回,陈继苏的《臭屁赋》赋题已属荒诞无稽,之后他交代“予本意实欲标奇立异,做今古人再不敢做之题”[8]上册117,则此作赋缘由更是谐趣横生。 陈继苏赋集中其余如《十岁邻女整寿赋》等赋②这些赋作在题面上已见离奇,而在小说前后文内又能找出相关文本互文性。 就如这篇《十岁邻女整寿赋》虽出现在第七回,但第二回中冷于冰在为严嵩捉刀撰写赵文华儿子寿文前曾笑道:“凡人到耄耋期颐之年,有些嘉言懿行,亲朋方制锦相祝,那有个二十岁人就做整寿的道理?”所以在小说内部又形成了一层呼应。,评点参与者接连用“奇”“更奇”“他都是这些题方做奇极”之语[8]上册117,表达了目睹这批不登大雅之堂的赋题后的惊愕感。 就连陈继苏最为自得的《畏考秀才赋》,其标题的鄙陋卑下、荒谬不经也可一目了然。
不过,倘若《绿野仙踪》一味如此用赋,则后来的有识者就断然不会对此小说作出诸多高度评价,如郑振铎就有言:“然其笔墨之横恣可爱,却使人决不至以其荒唐无稽而弃之。”[4]185无论在遣词造句、吏事用典、行文构篇的任一方面,《绿野仙踪》中的赋作大都暗含着与雅赋趋同的文体特征,具体展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直接征引名赋成句。 如《臭屁赋》中的“天地为护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8]上册116,《畏考秀才赋》中的“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8]上册118,是分别对贾谊《鵩鸟赋》和屈原(一般认为是屈原所作)《远游》原文径引的实例。 其次,点化经典辞赋句式。 如《臭屁赋》“乃如之人兮,亦窃效其陶熔:以心肺为水火兮,以肝木为柴薪,以脾土为转运兮,以谷道为流通”一段[8]上册116,层层推进地将《鵩鸟赋》中人与万物聚散生灭的转化道理演绎为屁的产生原理。 至于《畏考秀才赋》,对班固心目中的一批“贤人失志之赋”(《汉书·艺文志》)稍加置换变形之例就更多了,如“恨天道之迫厄兮”[8]上册118(化用《远游》“悲时俗之迫阨兮”句),“遭鼠辈之秽污兮,暗呜咽而谁语?”[8]上册118(化用《远游》“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句),“何予命之不辰兮”[8]上册119(化用《九辩》“悼余生之不时兮”句),“羡彭咸之所居”[8]上册119(化用《离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句和《九章·悲回风》“讬彭咸之所居”句),等等,兹不复赘,以省繁文。再次,取法辞赋通行的表现体式。 如《臭屁赋》将屁之声形铺采摛文、写物图貌道:“其为声也,非金非石,非丝非竹。 ……其为物也,如兽之獍,如鸟之鸱,如黍稷之稂莠,如草木之荆棘。”[8]上册115透露出小说作者分明拟效欧阳修《秋声赋》中描摹秋之为状、为声的痕迹(“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 丰草绿缛而争茂, 佳木葱茏而可悦”)[10]。 论者在小说文中“句句雕琢,尽致雅韵不俗。 …… 于其声形容到详且 尽也” 的 夹批[8]上册115,注意到此赋措辞的雅致,且准确把握到了辞赋致力于对描述客体进行全方位表现的体式特征,即文学理论家陆机、刘勰所说的“穷形而尽相”(《文赋》)、“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 小说作者最后还依照辞赋卒章显志的惯例,为《臭屁赋》补缀上“予小子继苏,学宗颜孟,德并程朱。 接斯文于未坠,幸大道之将行。 既心焉乎贤圣,自见异而必攻”[8]上册116。 这样一段曲终奏雅的尾巴,将全赋要归引向义尚光大。
质言之,寄生于《绿野仙踪》全书内的此类俗中见雅、寓庄于谐的作赋、论赋之语,在其表面庸俗的主题与内在雅饬的文辞、标准的体式之间构成了巨大反差。 其命辞遣意的侧重点实则并非强调陈继苏之流不谙赋艺,而在于颠覆像他们这般自视为“接续道统之人”的腐儒形象。 是故,以雅写俗、用庄衬谐的用赋之法使小说倍增了反讽效果,提升了批判主旨。
三、文体互参面貌在《绿野仙踪》等小说中的生成与成功原因
《绿野仙踪》不吝笔墨地提及和援引辞赋,并且在小说中营造俗中见雅、寓庄于谐的艺术效果。细绎此独特文学景观的造成,实隐含着小说文本内外的双重原因。
(一)辞赋生态
辞赋文学参伍因革至清季,和当时的整体学术水平相匹配,可谓“集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之大成”[11]。 清代辞赋的盛况不唯体现在赋作数量的空前,也体现在赋论建树的卓越,其辞赋中兴的局面又以康熙朝以来特别是乾隆朝为开始标志。 《绿野仙踪》的故事尽管拟讬明世,但实际上却充当了一个清代辞赋生存状态的文本佐证。 胪述其要,略有数端:
1.“赋兼才学”的衡量意识
小说频频推尊辞赋,第七回,陈继苏起先与冷于冰奇诗共赏,意犹未尽,相继又隆重推荐其赋道:“年台见予屁诗,便目荡神移如此,若读予屁赋,又当何如?”[8]上册114于是从其牛皮匣中取出珍藏的四大本个人自选集,赋集便荣列首本。 第四十八回,温如玉因金钟儿的朝秦暮楚而心生不甘,在唱《混江龙》一曲时不忘标榜矜夸“俺也曾伴酸丁,笔挥诗赋”[8]上册907,颇以当年能诗会赋而自许。 第六十五回,温如玉在施法下梦游异国,先是被当作奸细而身陷囹圄,继而经受一系列考验,最终顺利交出了压轴的一份辞赋答卷而逢凶化吉,应验了“入内庭诗赋显才华”[8]下册255。 辞赋之所以成为故事臧否人物、定夺走向的工具,一方面,固然与辞赋长期在中国古代文体之林中占据的崇高地位息息相关,诸如东汉班固在《两都赋序》里引述的“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断,以及表明辞赋“抑亦雅颂之亚也”的立场[12],重心都在抬高辞赋的思想价值;复如今见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文选》,始将“赋”列为众体第一,辞赋的举足轻重地位不言而喻,此后历代的总集、别集也多参酌这一编纂体例。 另一方面,又久已与辞赋成为可以和才学等量齐观的基本认识密不可分。 东汉王充《论衡·自纪》所谓“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13],《北齐书》载魏收所谓“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14],无不倡言征材聚事的辞赋是才学的彰显和象征。 这一见解到了清人那里几近达成了共识,如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云:“故工于赋者,学贵乎博,才贵乎通”[15]册三1;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兼才学。 ……故才弱者往往能为诗,不能为赋”[16]133,不一而足。
2.“祖骚宗汉”的学术风气
小说中的赋学批评反映了作者饱受清代辞赋复古思想的浸淫。 第七回,陈继苏问过冷于冰是否读过《离骚》后,煞有介事地品评道:“《离骚》变幻瑰异,精雅绝伦,奈世人止读《卜居》《渔父》等篇,将《九歌》《九章》许多妙文置之不顾。”[8]上册118陈继苏显然对《楚辞》是推服有加的,并指摘世人未能全面赏识其中个别篇章,进而回应前作《臭屁赋》遭到的选题质疑,归结为系效仿“富丽有余,而骨气不足”的“今赋体”所致,接着抛出他的得意之作——一篇古赋,以为冷于冰读过会觉得与今赋相比高下立判。 冷于冰阅后建议他既爱古赋,《离骚》又最难取法,不妨将《赋苑》并《昭明文选》等选集择浅近者读之,如此至少能得古赋之皮毛,又讥之“若必与《离骚》较工拙,则嫩多矣”[8]上册120。 这段插曲的背后潜伏的是元明清赋论中的古律论争。古赋,清人陆葇《历朝赋格·凡例》释曰:“古赋之名始于唐,所以别乎律也”[15]册三366,即用以区别唐已降兴起的律赋体式,又可称作楚汉体。 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带来了晚明辞赋选集的集体涌现,有明一代的第一本和最完备的辞赋总集便是以《昭明文选》作为编选范式的《赋苑》。 《赋苑》不录唐宋以下辞赋的义例定下了其时选赋贵古贱今的复古基调。 应当说,冷于冰针对如何师法古赋的建议是切中肯綮的。 孰知陈继苏勃然大怒道:“汝系何等之人,乃敢毁誉今古,藐视大儒。 吾赋且嫩,而老者属谁?”[8]上册120陈、冷对古、今赋的探讨最后演变为对“老”与“嫩”这对古代诗文理论重要范畴的论战[17]。 二人在结论上持论相反,却在崇古抑今的意见上所见略同。 以楚汉体为楷式的意识在终清之世都堪称是赋学主流的看法之一[18],如程廷祚《骚赋论》提出“祖楚而宗汉”[19];张惠言师法《文选》,所编《七十家赋钞》录至庾信而止;刘熙载《赋概》追踪《楚辞》和汉赋。 即便为律赋张本的清人在指导律赋写作时,亦主张宪章古赋[20],如李调元《赋话》卷二所标举的“以古赋为律赋”理念[21]。
3.“诗赋取士”的考选制度
小说中渗透着以赋取人的观念。 第六十五回,温如玉在梦境中被请入朝,经过在殿前忐忑的等待后,内官率先询问的就是他可否会做诗赋。 决定前程的大考的最后一道考题竟是命题赋,除却没有题下限韵的标记,温如玉完成的辞赋在擒题、开篇、韵律、对偶、藻饰、偶对、承转、收束上,与题下限韵之清代常规馆试赋无异。 温如玉因赋见赏而时来运转非全然凿空而构,史上以赋显名而改变命运者不乏其例。 辞赋既可以充分展示才学,就有了与政治缔合的可能,也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之谓[22]。 从汉代礼乐与献赋(散体巨制)、唐宋科举与考赋(律体小篇)、迨至清代翰林清选与考、献赋(馆阁体赋),贯穿着辞赋随着人才选拔制度发展而嬗变的轨迹。 在清代,辞赋依然是一种为国家选贤任能的致用文体。 康熙在《历代赋汇》序中论述:“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 ……朕以其不可尽废也,间尝以是求天下之才。”[23]乾隆朝辅政大臣张廷玉《丁巳馆课序》也体认道:“且唐以赋取进士,名臣将相皆出其中。”[24]在常科之内,清承明制,举人、进士系的乡试、会试及殿试均不考赋①明代不需考赋也有例外,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1701 页。,但此际诗赋取士又凭借他途得以落实:一是制举增设的“博学鸿词”科,考一赋一诗,清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于体仁阁开制,赋题为《璇玑玉衡赋》。 清乾隆元年(1736)九月召试保和殿,赋题为《五六天地之中合赋》,次年七月又补试于体仁阁,赋题为《指佞草赋》[25]。 二是名目繁多的“翰林院”考试,有为庶吉士专设的馆课“朝考”,乾隆朝始考诗赋;有庶吉士学业期满之“散馆试”,雍正元年即试以诗、赋、时文、论四题,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侍郎方苞奏请专试一赋一诗;有翰林官数年一决升黜的“大考”,初考论、疏、诗、赋,乾隆后以一赋一诗为主[26]。 上述政策对清赋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如黄爵滋《国朝试律汇海》序声称:“国朝试律之盛,远轶三唐。 ……数十年间,风雅蔚兴”[27]。 尤其“以诗赋课翰林”(蒋攸銛《同馆律赋精萃叙》)的举措由上至下、从幼到老地对清人产生了影响深远,余丙照在《增注赋学指南》序言中反思道:“自有唐以律赋取士,而赋法始严。 ……钦试翰院既用之,而岁、科两试及诸季考,亦藉以拔录生童,预储馆阁之选,赋学蒸蒸日上矣。”[15]册五5考虑到“赋法始严”,加之事关学子的叙进之阶,为此有必要从童蒙学馆开始就注重对辞赋这一“限制性的写作”培育素养和训练技能[27]。 辞赋对清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人物塑造
作者广泛吸收辞赋元素,且因人而异、因事制宜地使用了正反对比的手法,细针密缕、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人物的个性、身份、心理,盖因形形色色人物形象的经营设定需求使然。
小说对主人公冷于冰一向不吝赞美之词,第一回起首就说他“到了十二岁,于经史、诗赋、引跋、 记 传、 词 歌、 四 六、 古 作 之 类, 无 不 通晓”[8]上册7。 足见擅长诗赋是冷于冰年少得志、见重于世的一项标准。 第六十五回的《并蒂莲花赋》假借代言者温如玉呈诸笔端,但其实是冷于冰采用道术传递授意而成,故本质上归属于后者。此赋迭用“红衣瑟瑟,翠盖离离;花名君子,并蒂为奇”两联起手,紧扣题眼,先声夺人,然后围绕题意大作文章,用并蒂莲的高华气象笼罩全文,譬如“况夫一本交顾,两蒂相连,浓丽并美,雅淡分妍”,批点者赞曰:“此题极难,四句可谓雅切。”[8]下册270只是,全赋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而是不时地借题发挥,巧妙地插入“承恩辉于雨露兮,分绣采于翟榆”和“虽出身于泥沙,多见赏于君王”等句,以表露干禄求进、知恩感遇的心迹,使全赋立意上升到颂圣美君,公主读罢心折首肯道:“此题极难着笔,那官儿做的虽未能句句切住并蒂,却也敷演的富丽。”[8]下册271-272此赋困难见巧、意外出奇,其典雅堂皇、出手不凡,衬托的正是冷于冰的儒雅风流。 第四回中新履职的知县潘士钥,与冷于冰意气相投,一见如故,谈经论史之余特意将己赋求教冷于冰笔削,第三十回“已做到兵部尚书,素有名士之称”的胡宗宪据说也“做的极好的诗赋”[8]上册546,字里行间不难窥见人物既定的文化底蕴。
赋可誉人,亦可毁人。 故事的负面角色与以上可相映成趣。 前举第七回,陈继苏的系列赋作和赋论,已把他的腐儒形象刻绘得入木三分。 第七十九回,周琏在庭房内偷窥蕙娘,情不自禁地浮现《洛神赋》中“肩若削成,腰若约素;罗袜生尘,凌波微步”的典故,将他的纨绔子弟形象不着痕迹地拟诸形容。 赋作的质量与作赋的能力还能对应到小说人物的个体形象。 第二十八回,林桂芳讽刺“酸丁”(其幕僚),“不但诗词歌赋他弄不来,连明白通妥一封书启、一扣禀帖,也做不到中节目处”[8]上册510。第六十五回,温如玉进入梦乡内的朝中,初闻考诗赋时仓皇失措,小说跳出内视角,从旁观者的角度传达“大抵这些少年公子们看曲本、读嫖经的最多,融经贯史的甚少。 再讲到诗词歌赋、四六古作,他做梦儿也不知道”的实情[8]下册267,符合他们不学无术的群体肖像。 刘熙载《艺概·赋概》言:“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 ……所以使读其赋即知其人也。”[16]129小说中的辞赋既可使我们感知其中人物文化修养的差异,又微妙地寄寓了褒贬,塑造了丰满的各色人物形象。
(三)情节运作
此小说中交织的辞赋描绘性特征被淡化,而叙事性特征被放大,辞赋的运用不复是增色调味之点缀,而是连缀章回、襄助叙事不可或缺的组成。 为了摆脱“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表现”[28]的束缚,借助辞赋组织牵引情节、衔接结构版块、辅翼行文叙事的策略,在这部跨越世情、神魔、讲史的复合型题材小说中显现得尤为突出①学界关于《绿野仙踪》的题材类型争议较多,有神怪与历史二分说(见鲁迅:《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年版,第167 页);有仙道、历史与世情三分说(见李国庆精校:《绿野仙踪·前言》,上海书局2001 年版);有历史、英雄传奇、神魔与世情四分说(见徐君慧:《一部不该冷落而被冷落了的优秀作品》,载《明清小说研究》1989 年第4 期);还有依附于世情和历史下进一步细分公案、战争等多向型之说(见章因之:《〈绿野仙踪〉:清代“多向型小说”的特色及其产生背景》,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1 期)。。
第七回,冷于冰在初期出走修行的路途上遭遇老虎,死里逃生后与陈继苏谈诗论赋的环节“是别有用意的,是为了给冷于冰舍弃一切、入山求道寻找理由”[29]。 腐儒诗赋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冷于冰从中否定了腐儒的同时也否定了曾经的自己,体悟到传统读书求取功名的徒劳无益,致使他对尘世最后的一丝留恋也熄灭了。 正如回尾诗“凶至大虫凶极矣,蝎针蜂刺非伦比。 腐儒诗赋也相同,避者可生读者死”所揭示[8]上册123,与腐儒诗赋诀别的冷于冰坚定了信念,开启了一段新的生命征程,故事因而由读书用世过渡到访求仙道的版块。
冷于冰自从掌握道行,便被赋予了全知全觉、知来藏往的能力,小说的时空和场景也藉以自由超越和切换。 第六十四回,冷于冰赠温如玉道符箓与锦囊妙计以备后患,并有先见之明地相告:“至于做文墨、用诗词歌赋等项,万一做不来时,你只暗中叫我的姓名几声,我自助你成功。”下有批注道:“伏下第六十五回考试事。”回尾诗又云:“欲醒痴儿须用假,假情悟后便归真。 真真假假君休论,假假真真是妙文。”[8]下册253-254第六十五回,温如玉从现实踏入梦境,果遇麻烦,临场幸赖冷于冰的法力相助,在《并蒂莲花赋》的难题前“不但千言,觉的万言亦可立 就, 提 起 笔 来, 如 风 雨 骤 至, 顷 刻 而就”[8]下册269-270。 未有此赋,又何来后文在梦中的华晋国驸马和甘棠岭侯之封? 而这场梦在全书的情节脉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看似它只关联七回(第六十四至第七十回),然则实质贯穿了始终。卷首诗云:“愁添潘岳梦魂羞”,诗下有《蝶恋花》词云:“梦醒南柯头已雪。”[8]上册1第一百回殿尾诗亦云:“事业百年梦一场。”[8]下册970一头一尾,都在隐晦呼应第六十三回火龙真人传授冷于冰助人度脱苦海的妙策:“此人虽具仙骨,痴迷过甚。 你可造一富贵假境,完他一生的志愿,若仍前不省,乃下愚不移之人,速弃之可也。”[8]下册232第六十四回冷于冰对众人解梦,点破设置梦的深层用意道:“他世情过重,若不着他大大的富贵一番,他就做鬼也必抱屈地下。 我已劝化过他几次,此番要如此如此,满他的志愿。”[8]下册254第七十回又借连城璧之口道尽寻梦章节的关键:“今日大哥领你来寻梦,是怕你思念梦中荣华富贵、妻子情牵,弄的修道心志不坚,所以才椿椿件件或虚或实都说明白,教你今后再不可胡思乱想。”[8]下册359回尾诗重申:“他年再世成仙道,皆是甘棠梦里来。”[8]下册363起初在尘世痴迷不悟的温如玉历经人生幻灭,梦醒时分被拉回现实才幡然醒悟,弃旧重生,随冷于冰入山修道。 批点者多次示意梦在小说架构中的起伏显隐:如第六十五回“从此回至六十九回极难下笔……逐回看去,自见作者用心用意处”[8]下册262。 又如第六十九回“从入梦至醒梦数回写的恍恍惚惚,若真若假,使读者莫测,亦且用意精细”[8]下册340。 言下之意,都在提醒读者莫要忽略看似游离于情节外的梦之寓示意义。
辞赋的输入加强了逻辑的照应,又推动了情节的跳跃,使本小说在总体上以冷于冰修仙学道、伏魔降妖、济世安民的亲历见闻际遇为线索的单线型结构,在局部交替着以糅合两世以上的生命修炼历程转换为表征的网状型结构,故事时空得以拓展,叙事结构也得以丰富,最终“在结构形式上具有了回环兜锁、圆如转环的特点,从而形成了明清小说特有的形式美感”[30]。
结 语
诚如《绿野仙踪》“会评本”的首位抄录者和主要评点者——陶家鹤在此书序中所点明的:
其前十回多诗赋并仕途冠冕语……十回后虽雅俗并用,然皆因其人其事,斟酌身分口吻下笔,究非仆隶舆台略识几字者所能尽解尽读者也。 至言行文之妙,真是百法俱备,必须留神省察,始能验其通部旨归。 ……而立局命意、遣字措词,无不曲尽情理,又非破空导虚辈所能比拟万一。[8]上册序6
陶氏的序言浓缩了《绿野仙踪》中辞赋与小说联姻互动的图景。 作者通过引用、改写、自创的援赋途径,在立传造像、设场布景、构思立意中镶嵌赋作、赋论、赋选等形态的辞赋话语,凸显出俗中见雅、寓庄于谐的浓郁色彩。 考量该小说艺术上的戛戛独造之处,又要取资小说文本内外的因素以为参照:首先,清中叶“赋兼才学”“祖骚宗汉”“诗赋取士”的制度氛围是小说自觉选择汲取辞赋的外部条件;其次,正反人物的塑造、前后情节的推进、时空结构的拓展则是辞赋服务于小说的内部需要。 由此看出,理解明清小说文体交互的独特文学现象,不单要立足小说文本的本位,还要结合小说所调动的这种文学体裁自身所在的历史发展节点。
当然,必须指出,《绿野仙踪》中对辞赋的利用也存在着少数不尽合理的地方。 比方说,第七回,冷于冰指点陈继苏宜从《赋苑》入手习作古赋的情节,与假托的史实景况不侔。 小说故事发生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而《赋苑》当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赋苑》八卷不著编辑者名氏。 前有蔡绍襄序,但称曰李君,不著岁月。 凡例称甲午岁始辑,亦不署年号。 相其版式,是万历以后书也。”[31]因此《赋苑》不该是小说人物能够目见到的。 还有第三十回,胡宗宪能诗擅赋的表述也有不实成分,此又与小说夹杂着明季社会舆论等复杂因素而对胡宗宪采取欲抑先扬的处理方式攸关①胡宗宪,仅有少量散文和诗歌散见于方志中(见富路特《明代名人传》第3 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年版,第871 页),且文学价值平平,而其作有辞赋的记录更是未尝一见。 对于胡宗宪在明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偏差,见吕靖波、张文德《试论〈绿野仙踪〉对胡宗宪形象的重塑》,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12 年第3 期。。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许失当案例对《绿野仙踪》小说整体上参用辞赋的成功是瑕不掩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