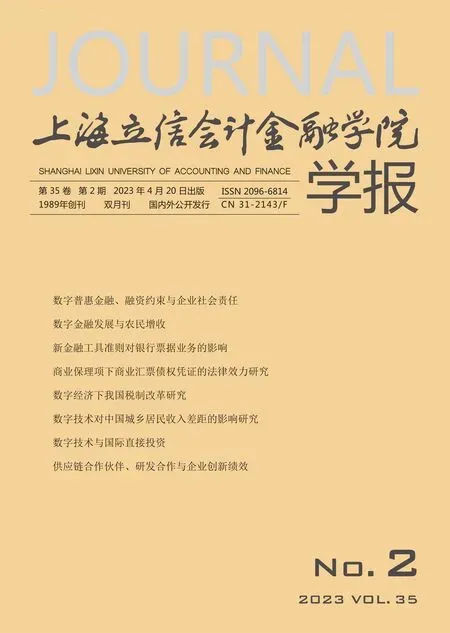供应链合作伙伴、研发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地与海外知识互补的角度
2023-08-05张珺涵罗守贵
张珺涵,张 天,罗 津,罗守贵
(1.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金融学院,上海 201209;2.上海市知识竞争力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上海 200030;3.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4.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上海 200030)
一、引言
随着创新复杂程度的提升,开放式创新成为企业寻求多样化创新资源、弥补自身创新知识不足的重要途径,寻找和整合创新链合作伙伴的知识、寻求研发合作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Teece,2014;Hannigan 等,2015)。一些研究认为,企业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如供应商、客户的知识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有重要影响(Nieto 和Santamaría,2007;Baldwin 和Von Hippel,2011;Clegg 等,2013;黄千员和宋远方,2019;吉利和陶存杰,2019)。现有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单一供应链合作伙伴比如供应商(Clegg 等,2013;李勃等,2020;祝明伟和李随成,2022)或者客户(Dyer 和Nobeoka,2000;Baldwin 和Von Hippel,2011;Fidel 等,2015;吴祖光等,2017)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其次,同时分析供应商和客户的同一特征比如集中度(黄千员和宋远方,2019)、多样性(Nieto 和Santamaría,2007)或者相互作用(杨金玉等,2022)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论述不同知识禀赋企业对两者的差异化互补性需求(Holl 等,2014)。基于知识基础理论(Grant,2013),本文认为内外资企业知识禀赋存在差异,因此他们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创新合作也存在差异(Mezias,2002)。对具有海外知识优势的外资企业,应考虑从本地化的合作伙伴比如本地客户获取知识,与其海外知识形成互补(Un,2019)。对具有丰富本地知识的内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供应商获得更为丰富的海外知识,与其本地知识优势形成互补。同时,研发合作是促进供应链合作伙伴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向企业转移、整合的有效手段(Husted 和Michailova,2010),在内外资企业对本地客户和海外供应商知识的整合、利用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因此,本文拟从本地与海外知识互补的角度,依托2008—2017 年61496 家内外资科技企业150428 个样本点的非平衡数据库,实证检验两个问题:一是对具有海外知识优势的外资企业来说,具有本地知识优势的本地客户对其创新绩效是否有显著正向影响及研发合作的调节作用;二是对具有本地知识优势的内资企业,具备海外知识优势的海外供应商是否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及研发合作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从本地与海外知识互补的视角,聚焦不同知识禀赋的内外资企业,探讨特定客户和供应商群体在不同知识禀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不同作用,完善了供应链上创新合作伙伴选择的理论;第二,突出特定研发合作在管理企业供应链创新合作伙伴中的重要作用,完善了供应链合作伙伴研发合作相关的理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企业知识基础理论认为,知识是维持企业持续创新能力的关键资产,个体和组织之间的知识差异使企业可以从外部创新合作伙伴获得互补性知识(Kogut 和Zander,1993;Grant,2013),更善于获取、整合外部知识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优势(Teece,2014),企业的供应链合作伙伴比如供应商与客户能为企业带来大量的互补性知识。
(一)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外资企业的资金来源遍布全球,在海外知识网络中的嵌入程度较高,比内资企业拥有更丰富的海外知识(Scott-Kennel 和Giroud,2015),这些海外知识可以帮助外资企业在创新方面享有外来优势(Un,2019)。这种外来优势体现在外资企业的资金来源往往具有国际视野和明确的投资方向,通过投资选择可将知识和创新直接转移到企业(Baldwin 和Von Hippel,2011),帮助企业创新产品,将新产品或者服务引入当地市场。此外,外资企业的员工更容易形成全球化思维模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搜索和转移知识(Un,2019)。基于这种创新上的外来优势以及对互补性知识的需求,外资企业可从当地知识禀赋更高的本地客户那里获得互补性知识。客户作为企业重要的创新来源,为企业创造了市场(Hienerth 等,2014),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方面,客户能够为企业带来满足他们需求的新产品或者服务的新想法(Mahr 等,2014),且不受企业文化或操作惯例的约束(Poetz 和Schreier,2012)。另一方面,客户倾向于与企业分享想法,期望企业能够投入资源和技术生产出满足他们需求的新产品或者服务(Franke 和Schreier,2010)。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客户获得更多的创新知识。同时,相较于其他合作伙伴,客户的知识尤其是终端用户的知识,往往更本地化,本地客户对企业现有产品或服务的满意程度以及当地其他客户的偏好包含丰富的本地知识。外资企业可以从本地客户那里寻找新产品的创意,从而将海外知识与本地客户的本地知识相补充,开发出既符合当地需求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Lukas 等,2013)。
综上所述,基于外资企业和本地客户知识互补性的考虑,本文提出假设1。
H1:本地客户能够提升外资企业的创新绩效。
(二)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紧密的关系和对国内市场的关注,当地市场是内资企业的主要市场(Mata 和Freitas,2012)。内资企业拥有比较丰富的本土知识,比外资企业更容易获得有关当地市场条件的显性和隐性知识,具有创新的本地优势(Un 和Asakawa,2015)。一方面,内资企业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以及对当地知识网络的更高融合,使他们能够不断创新、生产出符合当地客户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有效满足当地客户的需求。另一方面,内资企业具有较为成熟的、能够满足当地客户需求的商业模式和理念,熟悉当地制度环境,有能力在当地的制度、规范和法规内进行管理(Peng,2002),为其更好地开展创新活动提供管理优势(Martin,2014)。同时,对当地市场的深耕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内资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关注不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海外知识的欠缺会影响企业创新竞争力的提升。内资企业可以通过与拥有更多海外知识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合作,补充其海外知识的不足(Perri 等,2017)。
供应商作为重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为企业提供原材料和其他投入来帮助企业生产或改善流程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Un 和Asakawa,2015)。供应商和企业建立了相互依赖的长期关系,双方人员存在持续合作与互动,有利于跨越组织边界转移各自的知识,从而促进创新(Squire 等,2009),使合作双方从中获益。此外,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供应商有强烈的动机推动其客户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因此,更有可能分享知识以改善客户的产品和流程,从而使企业可以相对轻松地获取供应商的知识。一般来讲,海外供应商不仅向内资企业及其直接竞争对手销售产品或服务,还向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销售,这使得海外供应商对前沿产品的应用更为了解(Un 和Asakawa,2015;Un,2019),从海外供应商那里获得的相对全球化的知识可以补充内资企业海外知识的不足,提升其创新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海外供应商正向影响内资企业的创新绩效。
(三)研发合作的调节效应
一些学者发现,研发合作能够激励合作伙伴之间知识的转移、整合和新知识的创造。首先,正式的研发合作减少了知识溢出中知识转移的激励问题(Husted 和Michailova,2010)。其次,研发合作不仅能促进显性知识的转移和整合,而且能通过合作双方人员的交流,促进创新价值更高的隐性知识的整合(Takeishi,2002)。最后,研发合作为合作双方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条件和利益分配机制(Dyer 等,2004),有利于创新知识的整合与利用。
本地客户的知识能够正向影响外资企业的创新绩效,为了更好地提升对本地客户知识的整合效率,具有外来优势的外资企业需要引入更了解本地知识同时具备全球视野的当地大学、科研院所甚至竞争对手进行研发合作,这种研发合作能够促进本地知识的转移、整合,有利于减少外资企业创新与客户需求特征之间匹配的不确定性(Nahuis等,2012)。因此,与具备本地和海外知识的组织或个人的研发合作会提升外资企业对本地客户知识的消化和吸收能力,提升外资企业的创新绩效。
同时,由于海外供应商不是直接向终端客户供应产品或服务,而是通过向企业销售原材料、中间品和服务来间接提供产品,供应商可能无法直接了解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往往对区域的市场特征不够敏感(Govindarajan 等,2011),海外供应商多样化销售渠道所形成的知识的广泛性,使内资企业需要通过研发合作促进知识更有效地转移和整合(Un 和Asakawa,2015),这需要内资企业加强研发合作,合理利用、整合海外供应商提供的海外知识。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和假设4。
H3:研发合作能够正向调节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H4:研发合作能够正向调节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依据研究假设,本文提出理论模型,如图1 所示。从本地与海外知识互补的角度来看,具有海外知识优势的外资企业(Un,2011),能够从具有本地知识优势的本地客户获取互补性知识,提升其创新绩效;具有更丰富本地知识的内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供应商获得更丰富的海外知识,与其本地知识优势形成互补,有效提升其创新绩效。同时,研发合作是促进本地客户和海外供应商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向企业转移、整合的有效手段(Husted 和Michailova,2010),在内外资企业对本地客户和海外供应商知识的整合、利用中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图1 理论模型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的科技活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每年对全市范围内从事科技活动企业的创新和经营情况进行统计①统计途径和方法:http://stcsm.sh.gov.cn/zwgk/tzgs/zhtz/20190423/0016-153934.html。,形成了包含企业科技创新投入、科技成果、经济产出等相关信息的2008-2017 年的年度数据,剔除部分无效数据,最终得到61496 家科技企业150428 个样本点,构成了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库。其中,内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有限企业和有限责任企业)49766 家,128130 个样本点;外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国港澳台地区企业)11730 家,22298 个样本点。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创新绩效(hts):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高新科技来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和技术含量,以达到更高质量的企业创新(余吉安等,2020),为了更真实地衡量企业的创新效率,本文采用已经实现创新商业化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来衡量企业创新绩效。
2.解释变量
本地客户(users):本文中数据库里的企业均是在上海地区经营的企业,32.7%的样本点的产品或服务会投向上海地区,63.75%的样本点的产品或服务会投向国内其他地区。本地客户和企业物理距离的临近,使本地客户对企业产品或服务满足其需求的特性包含较多的本地知识,考虑到上海地区相对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企业可以在上海本地客户的知识获取中,创造出更好地满足多个区域客户需求的新产品以及服务,因此本文采用是否有上海客户为虚拟变量衡量是否有本地客户,是取1,否取0。
海外供应商(supf):本文采用主要原材料、半成品(服务)供应商是否来自海外作为海外供应商虚拟变量,是取1,否取0。
研发合作经费支出(efo):本文采用企业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衡量研发合作经费支出。
3.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age)、所属行业(ind)、是否高新技术企业(ht)也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参考柳卸林等(2018)、张珺涵和罗守贵(2020)的做法,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的具体含义
表2 列示了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 可知,创新绩效(hts)的均值为0.309,说明目前企业的高新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水平还不是很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本地客户(users)的均值为0.327,说明样本中产品或服务投向上海本地的企业数量相对不多,大部分的产品或者服务投向了本地以外的区域;海外供应商(supf)的均值为0.061,说明有海外供应商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企业年龄(age)均值为8.486,说明样本中企业年龄相对较小,未来成长空间较大;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ht)的均值为0.231,说明样本中有相当数量的高新技术企业。所有变量的取值范围均处在合理区间内,本文不再赘述。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构建
基于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文构建非平衡面板静态回归模型,采用豪斯曼检验确定面板数据模型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检验结果支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由于本文样本的年份跨度较短,因此不考虑动态面板的情况。为了防止交乘项与本地客户(usersit)、研发合作变量(efoit)存在高度共线性使模型估计产生偏差,本文对研发合作变量进行中心化修正,得到新变量c_efoit,然后生成一个去中心化后的交乘项,再进行固定效应回归。通过中心化降低交乘项与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便不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基于此,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1.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为考察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验证研究假设H1,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htsit指企业的创新绩效,usersit指本地客户虚拟变量,c_efoit指去中心化研发合作经费支出变量。
2.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为考察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验证研究假设H2,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htsit指企业的创新绩效,supfit指海外供应商虚拟变量,c_efoit指去中心化研发合作经费支出变量。其他为控制变量。
3.研发合作的调节效应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本地客户(usersit)与研发合作(c_efoit)的交乘项,考察研发合作在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调节作用,验证研究假设H3,本文构建如下调节效应回归模型:
其中,htsit指企业的创新绩效,usersit指本地客户虚拟变量,c_efoit指去中心化研发合作经费支出变量。
在模型(2)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海外供应商(supfit)与研发合作(c_efoit)的交乘项,考察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过程中研发合作的调节作用,检验研究假设H4。
其中,htsit指企业的创新绩效,supfit指海外供应商虚拟变量,c_efoit指去中心化研发合作经费支出变量。其他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部分采用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依据模型(1)和模型(2),检验供应链合作伙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1.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为检验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本文按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 列(1)所示。结果显示,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的创新绩效(hts)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H1 得证。即对于具有海外知识优势的外资企业,具有本地知识优势的本地客户的知识能够与其海外知识优势形成互补,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

表3 供应链合作伙伴、研发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固定效应实证结果
2.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针对内资企业,实证分析海外供应商(supf)对其创新绩效(hts)的影响,验证研究假设H2。回归结果如表3 列(3)所示,可以看出,海外供应商(supf)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企业的创新绩效(hts)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假设H2 得证。即对拥有本地知识优势的内资企业来说,拥有海外知识优势的海外供应商能够有效补充其海外知识的不足,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二)调节效应检验
本部分依据模型(3)和模型(4),检验研发合作(c_efo)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3列(2)和列(4)所示。
1.研发合作在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通过本地客户(users)和研发合作(c_efo)交乘项的引入,实证结果显示研发合作(c_efo)能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调节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积极作用,假设H3 得证。即研发合作能够有效调节外资企业对本地客户知识的吸收与整合,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2.研发合作在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通过海外供应商(supf)和研发合作(c_efo)交乘项的引入,得到交乘项实证结果如表3 列(4)所示,结果显示,研发合作(c_efo)会正向调节海外供应商(supf)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积极作用,假设H4 得证。即研发合作在海外供应商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能够有效促进海外供应商向内资企业的知识转移和整合。
(三)异质性分析
内外资企业对海外供应商或本地客户知识的整合,需要研发合作的调节作用,从海外和本地知识互补的角度来看,这种研发合作是否有最优的研发合作广度选择?是否来自某个区域的研发合作更有利于发挥调节作用?由于本文的样本在统计企业研发合作开发广度时,对来自国外的研发合作统计口径较粗,未能体现研发合作的国际差异性,为进一步检验内资企业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带来了限制,但本文的样本对国内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统计较为细致,为检验外资企业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提供了可能。
本部分基于外资企业研发合作的不同开放广度(采用企业研发合作伙伴的区域广度衡量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企业研发合作伙伴分别分布在上海、国内其他地区以及海外,企业的研发合作只有一种地区取1,有两种取2,三种都有取3),分析本地客户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1.不同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考虑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依据不同开放广度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本地客户(users)对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及研发合作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如表4 所示。表4 列(1)、列(3)和列(5)的结果显示,只有在开放广度为1 时,本地客户(users)对企业创新绩效仍然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随着外资企业研发合作广度的提升,本地客户(users)对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不再显著,即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过高的研发合作广度,不利于其对本地客户知识的利用。同时,列(2)、列(4)和列(6)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开放广度水平下,研发合作(c_efo)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表4 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分析固定效应实证结果
2.不同区域研发合作的异质性分析
表4 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1 时,本地客户(users)对企业创新绩效(hts)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下面探索企业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1 的情况下,即研发合作的伙伴分别只来自上海、国内其他地区及海外一个区域时,采用分组回归,实证分析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影响过程中,来自不同区域研发合作(c_efo)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5 所示。表5 列(1)为研发合作伙伴仅来自海外的实证结果,列(3)为研发合作伙伴仅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实证结果,列(5)为研发合作伙伴仅来自上海本地的实证结果,三个模型的实证结果均显示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有显著正向作用。进一步考虑不同组别研发合作(c_efo)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5 列(2)、列(4)和列(6)所示。列(2)为研发合作伙伴来自海外时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来自海外的研发合作不能显著调节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而列(4)和列(6)显示,研发合作伙伴来自国内其他地区或者上海本地时,研发合作(c_efo)在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即外资企业虽然有外来优势,但仍然需要本地客户的本地知识对其形成补充,需要与既了解当地情况又相对具有海外知识的当地研发伙伴合作,才更有利于对本地客户知识的开发和利用,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表5 异质性检验结果: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1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供应链合作伙伴、研发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
1.对基准回归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 所示。表6 列(1)和列(2)结果显示,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提升仍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研发合作(c_efo)仍然显著正向调节这种影响,与原模型结果一致。表6列(3)和列(4)结果显示,海外供应商(supf)对内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合作(c_efo)仍然正向调节这种影响,与表3 中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稳健性检验结果支持原模型的结果。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基准回归和调节效应
2.对内资企业研发合作开放广度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仍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 和表8 所示。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研发开放广度异质性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1
表7 列(1)和列(3)可以看出,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1 和2 时,本地客户(users)对于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提升仍然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研发合作开放广度的提高,在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3 时,列(5)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不再显著,基本支持了表4 中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即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过高的研发合作广度,不利于其对本地客户知识的利用。
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为1 时,来自不同区域的研发合作(c_efo)调节作用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8 所示。表8 列(5)显示,在研发合作(c_efo)仅来自上海时,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有显著正向影响,列(4)和列(6)的结果显示,来自国内其他地区和本地的研发合作(c_efo)能够正向调节本地客户(users)对外资企业创新绩效(hts)的影响,基本支持表5 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从本地与海外知识互补的角度,研究具有不同知识禀赋的内外资企业如何利用不同供应链合作伙伴的知识提升其创新绩效。基于获取互补性知识的诉求,研究发现,具有海外知识优势的外资企业,可以从与本地客户的合作中获益,后者为它们提供了互补性的本地知识;具有本地知识优势的内资企业,可以从具有更全球化知识的海外供应商获得互补性知识,且企业的研发合作正向调节这种海外与本地知识的互补。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外资企业应重视对其本地客户的开发与利用,并加强与本地和国内其他地区相关组织的研发合作,合理控制研发合作开放广度,以提升其创新绩效。本地客户对当地情况更为了解,与外资企业本身的海外知识优势形成互补,可以补充外资企业本地知识的不足。同时,应加强引入外界特别是来自本地和国内其他地区相关组织的研发合作,提升外资企业对本地知识的消化吸收和利用水平,以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此外,外资企业应控制自身研发合作的广度,过于广泛的研发合作有可能造成知识过载,不利于企业对其本地客户知识的开发利用。
(2)内资企业应加强与海外供应商的对接与合作,同时加大研发合作力度,提升海外知识利用水平。拥有更多本地知识的内资企业,应从海外供应商获得更全球化的知识支撑;同时,海外供应商的知识需要研发合作的整合,才会更有效地形成内资企业本地与海外知识的互补,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二)建议
本文的结论为管理者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价值,当企业需要从外部获取创新知识时,管理者应基于企业自身的知识禀赋,考虑互补知识的获取需求,并基于这种需求建立研发合作。原则上,管理者可能希望探索与所有类型合作伙伴知识的互补性,然而,过多的合作主体会增加企业知识管理的复杂性,找寻互补性相对较高的合作伙伴,对企业来说是较为理性的选择。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外资企业应加强与本地客户的合作,获取企业需要的互补性本地知识,可以将一些部门安置在客户物理位置附近,降低获取客户知识的交易成本,同时加强与本土即具有本地知识优势又具有国际视野的相关组织的研发合作,提升对本地客户本地知识的消化吸收水平;内资企业应加强与具有海外知识优势的海外供应商的合作,与自身的本地知识优势形成互补,同时需注重在对海外供应商海外知识的转移和利用中研发合作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