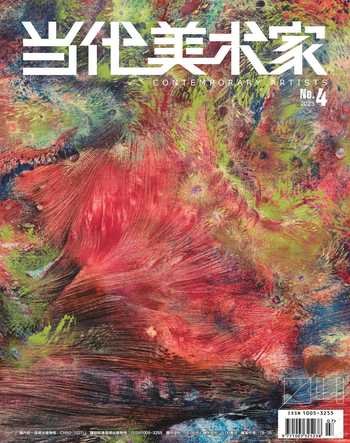晦涩、真美与商业骗局:毕加索在民国“黄金十年”的接受状况研究
2023-08-04陈能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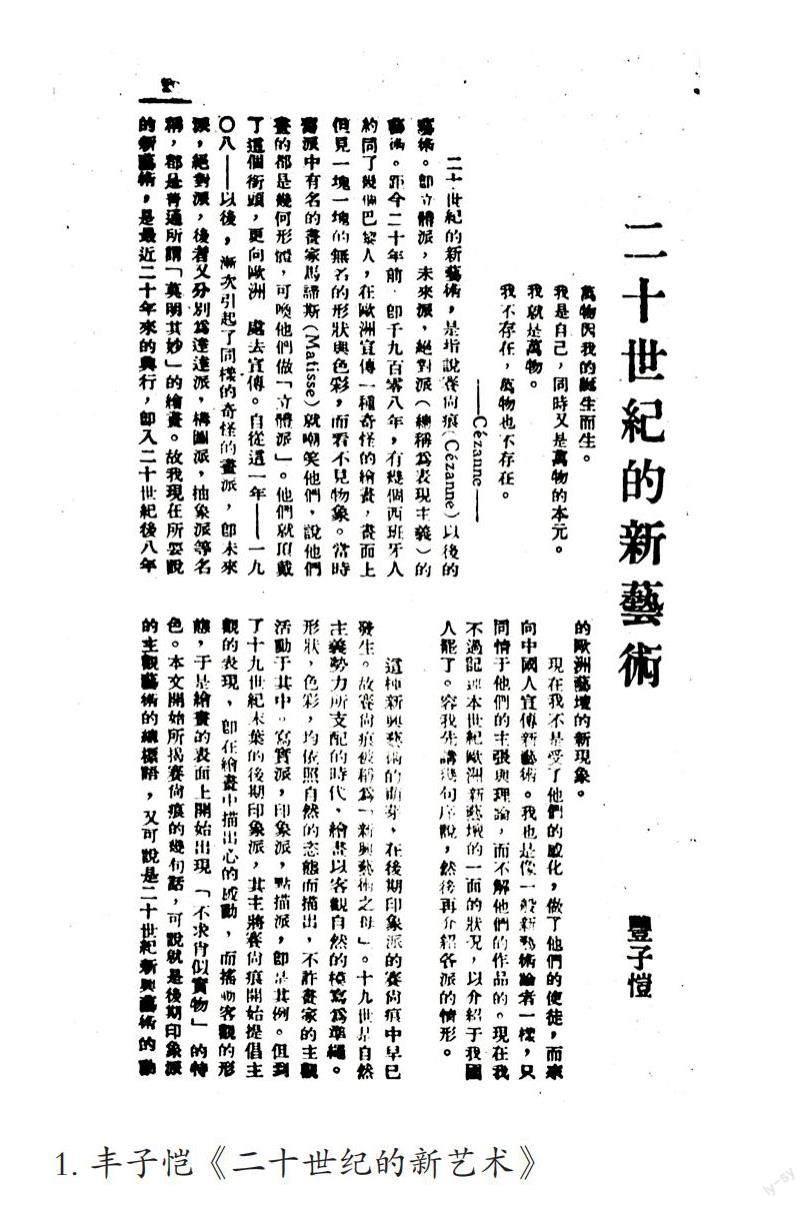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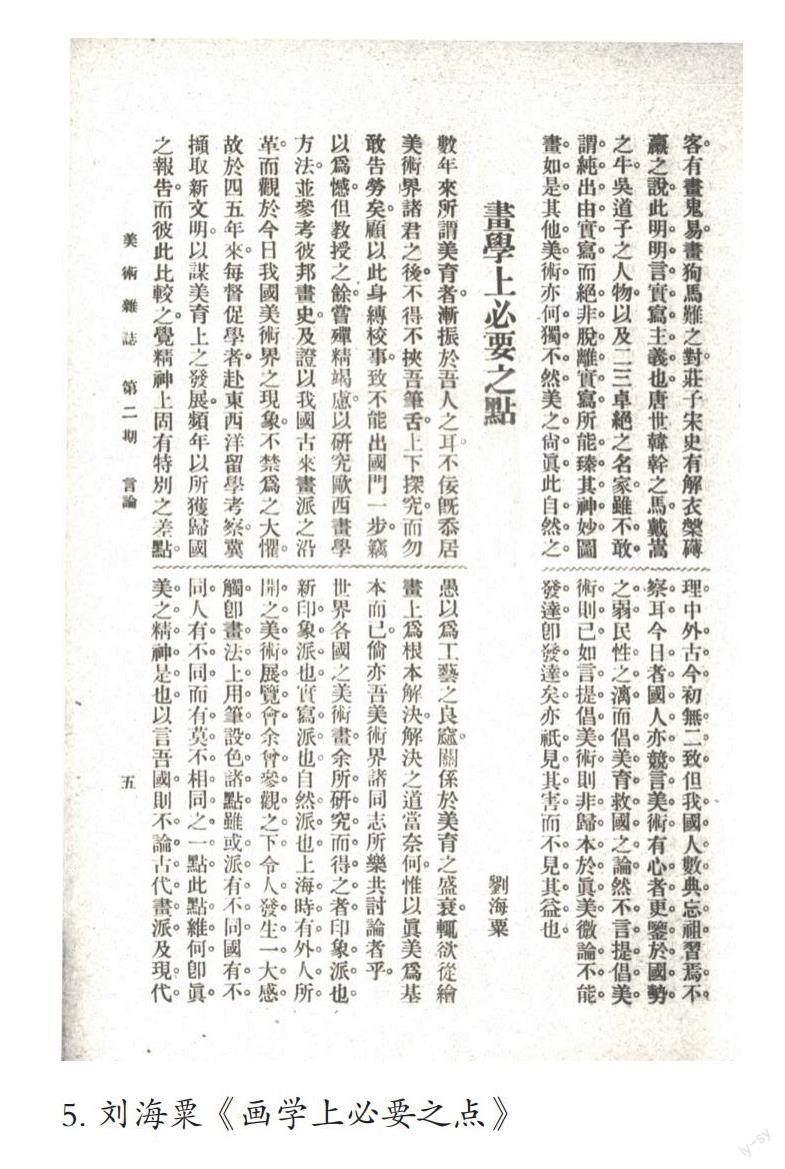
摘要:西方现代艺术的译介工作在民国“黄金十年”取得较大进展。本文从“黄金十年”的报刊文献入手,从译介者、阐释者和反对者三方面分析了毕加索在民国知识分子间的接受状况,进而还原西方现代艺术在民国接受状况的具体侧面,揭示译介过程的再塑造在西学接受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黄金十年,毕加索,立体主义,西学东渐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odern art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during the “Golden Deca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newspaper literature of the “Golden Decade” and analyzes Picassos acceptance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translators, elucidators, and opponents. It then restores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modern art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veal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shaping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studies.
Keywords: Golden Decade, Picasso, Cubism,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eastward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是年内,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蔡元培担任第一任院长,负责全国教育和学术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其美育思想;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大会召开,通过筹备国立艺术大学的提案,同意在杭州设立国立艺术院;“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开始筹办,在蔡元培、李毅士和刘海粟等人的努力下于1929年4月10日在上海顺利召开。美术事业的建设如火如荼地推进,为“黄金十年”的繁荣奠下了基础:美术史的专著和教材初具规模、学生群体对新兴的现代画派津津乐道、各类报刊对新画派的引入工作不断深入、毕加索的照片和作品开始被刊登在各类报刊中、对毕加索进行专门性报道文章开始出现,对西方现代艺术的了解较民国初期近乎空白的状况取得了进步。[1][2]
在此背景下,面對新兴但纷乱的西方现代艺术,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立场的民国知识分子会产生怎样的接受态度?本研究以此问题为出发点,以毕加索为个案展开研究,借此管窥“黄金十年”的民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接受态度。
一、如实地转述:理念玄深的艺术大师
1927年后,汪亚尘的《近代底绘画》和《近五十年来西洋画的趋势》、郑锦的《西洋新派绘画》、丰子恺的《现代艺术潮流》、俞寄凡的《法国近代的绘画》等文章相继发表,逐渐在中文世界中构筑起了西方近现代艺术流派的基本框架。但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构建出这些框架的译介者们理解起西方艺术的艺术流派依旧艰难。
1929年,丰子恺在《二十世纪的新艺术》(图1)中直接表明了他对现代艺术的不解,认为“看了立体派、未来派等的作品,又觉得不知所云”。[3]但面对不解,还是根据其生活经验对立体派的艺术意义进行了揣摩:
他们描写人骑马,两只脚都看见,马的肚子犹如玻璃制的……因了这乡下孩子的壁画的暗示,我似乎摸着了对于立体派绘画的理解的线索。回家翻开比卡索(Picasso)的画集来看,虽仍是不知所云,但是“这种表现法是可以有的”的信念,从此加深了。[4]
在丰子恺看来,立体派可能有与乡间小孩相似的“自然观”,并且这种“自然观”与以“透视法”和“明暗法”为原则构建起来的“自然观”是不同的。因此,虽然不能确定这一“自然观”引导下的画作的更深层次的价值,但是如尊重儿童的天性一般,这一“自然观”的存在应该被尊重。在表明自己的不解和试图理解立体派的努力后,丰子恺并未止于此,他还是按照阿波利奈尔的理论对立体主义进行了引介,将立体主义分为了科学的立体派、物理学的立体派、音乐的立体派和本能的立体派。丰子恺对音乐的立体派的描述如下:
音乐的立体派。这是全然脱离现象——视觉的物像的。到了这地步,绘画的要素,对现实完全断绝关系了。这在艺术家是完全的创造。与音乐的全部摹写现实的音响同样,立体派画家也不借现实的形体,而描出所谓“纯粹美学”的一种构成。皮卡比亚是属于这派的人。[5]
这段文字相较于对乡间孩童绘画的描写而言显得较为晦涩,但仍可大致读出丰子恺对所谓“音乐的立体派”的理解,即:与音乐的抽象性相似,“音乐的立体派”也摆脱了现实形体,追求“纯粹美学”的构成。这里,丰子恺不了解他所谓的“音乐的立体派”与希腊神话中俄耳浦斯的联系,也不懂这一流派实际上的创始人是德劳内和阿波利奈尔,皮卡比亚仅仅是短暂进行过这一风格的尝试。因此,丰子恺只能用“‘纯粹美学的一种构成”来作为“音乐的立体派”的解释,因为如果要对“纯粹美学”进行更进一步的展开,那么上文所涉及的种种知识便成为不可不知的前提。
可以说,丰子恺在试图理解这些现代艺术,但是遇到难以理解的“硬骨头”时,便选择按照他所见之外国文本进行如实地翻译。这种如实转述的态度构成了这一时期引介外国艺术家的主流。叶秋原的《现代艺术主潮》和《世界民族艺术之发展》、王子云的《欧洲现代艺术》、王溎的《新兴艺术的主将毕加梭氏》、影梅的《毕加索》、陈士文的《比加索》、郑阿甲的《辟卡索先生》、倪贻德的《近代绘画的代表作》、梁锡鸿的《辟卡梭艺术的阶段》和《现代世界名画家:三、碧加索》、林文铮的《由艺术之循环律而探讨现代艺术之趋势》、刘海粟的《现代艺术》、德明的《最近世界艺坛》、邵素贞的《近代欧画的趋势》、Wiegand的《人物种种:当代两画家齐里科和辟加索》、陈抱一的《辟卡梭》和《最近巴黎画坛概观》、林镛的《辟卡梭与辟卡梭主义》、施蛰存的《辟卡梭的艺术方法》、华宾的《法兰西新画坛》、洛平的《马提斯、卢柯、毕加梭、特朗访问记》等,都属于这种如实转述类的文章。这类文章中,如王子云、倪贻德、林文铮等皆行文清楚,观点突出。王子云的《欧洲现代艺术》(图2)对立体派的影响做了清晰地描述:
然而立体派作风,确是一种富有智慧的艺术……举凡现代之建筑装饰、工艺艺术,以及妇女时装、商店窗饰、零星图案等,几无处不有立体派之踪迹。[6]
倪贻德的《近代绘画的代表作》对立体派的平面性因素和形式审美的解释也较为到位:
这里不能详细说明立体派的理论,只能简单地说一点,最初立体派的画家,主张绘画为二种延长的艺术(长与广)。以前的画家,加以第三延长(深),应用远近法和瞒视法,是违反绘画的本性,所以应排斥之。[7]
林文铮的《由艺术之循环律而探讨现代艺术之趋势》(图3)则笼统而不失实地概括了立体派背后的思潮脉络:
由18世纪卢梭之人权说,而19世纪末叶尼采之超人观,都是解放的运动,亦即是个人主义之进化。在艺术方面,也有同样的倾向,到了20世纪初期的未来派立体派等,可以说是解放到极点了。[8]
但并非所有作者对立体派的引介都能如上述作家一般清晰。叶秋原的《世界民族艺术之发展》中对马蒂斯、毕加索和皮卡比亚等艺术家进行了介绍:
马蒂斯努力于以最经济的手段显示最丰富的色调与结构,其他诸人,亦均以塞尚奈为他们的出发点:他们都以简单的结构而含有丰富的内容。[9]
叶秋原将立体派等人的艺术理念总结为“简单的结构而含有丰富的内容”便再无展开,然而“简单的结构而含有丰富的内容”这种大而化之的概括如何成为立体主义其独家的特质?立体主义的结构为何简明?内容又丰富在哪些领域?这些具体问题皆被叶秋原搁置。
林镛在《毕加索与毕加索主义》(图4)的表述,所谓毕加索“一到立体派便豹变了”究竟指的是什么?立体派的一半“其脱壳从立体化解体变形”究竟作何解释?“其他一半原理”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未能在文中得到解决:
为立体派之生母的毕加索,一到立体派便豹变了。因此,立体派的一半所有的立体化,便与其脱壳从立体化解体变形,一方面为当然的趋势,把立体派的其他一半原理的同时性展开来。[10]
与上述观点不明或表述不清的文章不同,华宾的《法兰西新画坛》简洁明了地对毕加索进行了介绍,但《辟卡苏夫人像》究竟是哪般?文中并未配图解释。且毕加索一生所作不同风格、不同夫人的《辟卡苏夫人像》多幅,文中“《辟卡苏夫人像》是新古典主义的极作”也容易令人生疑:
毕加索他的才气纵横、一时无出其右、他的不离的天才使他作出种种不同的作品,如毕加索夫人像是新古典主义的极作、最近他的作品、又可以看出入于新写实主义的范围了。[11]
作為反启蒙理性的艺术流派之一,立体主义其艺术理念本身便存在着诸多的荒诞性、晦涩性和不可解性。加之不同理论家的阐释,如阿波利奈尔的《美学沉思录》和《艺术散论》、罗杰·弗莱的《毕加索》、阿尔弗雷德·巴尔的《毕加索及其艺术50年》《立体派与抽象艺术》等都对立体主义有过分析和阐释);不同艺术家实践倾向的差异性和冲突性,如以德劳内为首的俄耳甫斯立体主义重视作品的抒情性和音乐性,而同时期以布拉克和毕加索为首的分析立体主义则重视画面的形式秩序;以及立体主义艺术家的发言的晦涩性,毕加索本人便是这一代表,因此常被冠以“不善讲谈”“不谈学理”的评价。[12]上述诸多因素都对国内知识分子了解立体主义的理念提供了阻碍。最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知识分子消化了这些外国理论,对立体主义的理念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解,如王子云、倪贻德和林文铮,能够清晰准确地概括出立体主义的艺术特征及影响,并在国内进行译介工作。二是知识分子未能消化这些理论,或如丰子恺一般如实地保留着理论本身的晦涩,或如王溎、陈士文、影梅和林镛等人一般,企图以昏昏之语使人昭昭。
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的学习者艰难地在良莠不齐的文章中了解毕加索,或者通过昭昭之文把握到一些有关毕加索的真实情况,并产生了一些自己的感受。或者通过一些昏昏之文了解到毕加索,但是可能反复阅读而不解,最终感慨立体主义理念玄深,甚至怀疑自我,认为能力未到能够参悟这一流派的地步。这些怀疑情绪、玄深难以理解的感受也是读者接受的一种情况。然而毕加索的艺术成就很难否定,因为已经有如此多的文章对其进行阐释和歌颂,由此一个有着玄深理念的艺术大师的形象便渐渐形成了。
二、试探性地阐释:“真美”和理性精神的彰显
相较于保守的转述,一些知识分子更倾向于结合自己的理解对毕加索的意义进行阐释。在已考据到的文章中,对毕加索的阐释性理解大致表现出两个倾向,即关注毕加索艺术中对内在精神(即“真美之精神”)的表现和作品的形式秩序。
“真美之精神”于1919年由刘海粟在《画学上必要之点》(图5)中提出。刘海粟认为“真美之精神”是中西方艺术的最大的差异(刘海粟原文:以言吾国,则不论古代画派及现代人所习之西画,较之各国,差度虽大,总不若此点差度之为尤。[13])也是建设好民国美术事业的关键因素(愚以为工艺之良麻,关系于美育之盛衰,辄欲从绘画上为根本解决。解决之道当为何?惟以真美为基本而已。[14])但真美之精神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刘海粟将其归纳为在理法中自然地释放天赋和本能:
天赋才能,各不相同,美者完全天赋之本能,此西哲真、善、美三者一体说之所由来也。
……
或曰:然则子于画学之教授,主自由涂抹而反对定法,主意笔而废工笔乎?曰:非也。吾所谓自由者,求理法中之自由,非理法外之自由也。[15]
在刘海粟看来,中国传统绘画和近代西洋画都以强制的技法限制了天赋才能的抒发,提出“真美之精神”,实际上是对激发和保留天性和本能的重要性的强调。但是,刘海粟所谓对本能和天性的释放,必须是在“理法”之内释放。所以他提出了“养成其创造性与主动性”“养成其观察能力”“注意光色变化之原理而证其观察力”和“须端正其平日之习惯”共四条美术教学的原则。对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强调放在第一条,其后又用养成观察力、注意光色变化和倾向于自然这些“写实主义”倾向的要求加以限制。刘海粟有关“真美之精神”的强调,在写实主义倾向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为表现性和非写实性的倾向留了一定余地。
因此,所谓“真美”精神,实际上是指民国知识分子在对毕加索的阐释中,对他作品的内在性、非写实倾向的强调。因为在民国知识分子的眼中,写实主义与科学精神联系密切,而现代主义的抽象语言则很难用科学解释。因此,立体主义的抽象语言被从各种角度解释为“表达真美之精神”的产物。虽然不同作者在不同语境中,对毕加索的阐释可能与刘海粟的“真美之精神”并不完全一致,但普遍倾向于将立体主义划作写实主义的对立面,并将其艺术风格解释为重视表现内在精神最终导致了非写实倾向的画风。持这种观点的有俞寄凡、鲁少飞和曾鸣等人。
俞寄凡在《近代西洋画的精神》中,提出了20世纪艺术有两大倾向的观点,即,由头脑感受绘画的精神和由内心感受绘画的精神,并作了如下表述:
后者之倾向(即头脑感受绘画的精神),是热情的绘画精神……不是“知”的,而是“情”的,是由心之感激所爆发而产生之绘画的精神,不是视觉的问题,是怎样获得感受于心之感受性问题……毕加索亦努力探求绘画的精神。[16]
在俞寄凡看来,毕加索的作品,是由内心的情感爆发的产物,因此这些作品关心的不是视觉的问题,而是内心的感受性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下给予毕加索的抽象画风以合理解释,即他是因为关注内心感受、探求绘画的精神而摆脱了具象的,因此欣赏他的作品不能靠视觉,而应依赖内心感受。
鲁少飞在《西班牙的近代绘画》的表述:“(立体派)尚是西班牙一种极灵敏的团体,真正能够恢复古有的精神,他们这种意志的作用,全在找觅一种感化力最活动的优占势。”[17]和曾鸣在《最近碧加索的艺术》的表述:“永远是他自己的感受性,魂不断的兴奋、绝望的好奇心等,常存在他心中,唤起无数实现和欢迎的关联,这个关联他的即兴做了凄怆的样子,灵魂和年龄一样,顺顺地进入幻觉之境,形容出他生命的本质来,有神秘的表证,产生深奥的真理。”[18]也都表现出了大致的倾向。
但“真美之精神”并非对毕加索唯一阐释,对毕加索作品中的理性精神的强调也普遍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各式报刊中,且常常与“真美之精神”相伴随。如提出“真美之精神”这一概念的刘海粟,其实在《论艺术上之主义——近代绘画发展之现象》便做了如此表述:
立体主义则要将艺术建立在纯理的、分析的、哲学的上面。此是二派(另一派为偏重表现主观情感的表现派——笔者注)不同之点也。他们相同的一点,则为表现物体的实体,而排斥物体的表面观念。[19]
在刘海粟看来,表现主义倾向于主观情感,立体主义则建立在“纯理的、分析的、哲学的上面”,但是二者相同点是关注物体的实体,而非表面的观念。所谓“排斥物体的表面观念”,实际上强调了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对再现性要素的排斥,而“表现物体的实体”,则可以理解为“格物致知”式的,对感受到的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的表现,其实也是“真美之精神”的表现形式的一种。可见,在刘海粟这里,“真美之精神”是立体主义的前提,而“纯理的、分析的、哲学的”表现特点是建立在对“物体实体”的感受的基础上的。
与刘海粟相似,强调毕加索“亦努力探求绘画的精神”的俞寄凡,其实还作了这样的表述:
此二种绘画的精神之表现能很明白的区别。前者之倾向。是采取理智的绘画的精神。发展而成为“立体主义”(Cubism)这立体主义之先驱……全然是由理智的要求所产生这便是立体主义。[20]
同一篇文章中,俞寄凡将立体主义阐释为“采取理智的绘画的精神”的代表,但是却将毕加索视作“探求绘画精神”的代表,认为毕加索在意的“是由心之感激所爆发而产生之绘画的精神,不是视觉的问题,是怎样获得感受于心之感受性问题”。[21]可见,在俞寄凡的观念意识中立体主义的理性和毕加索对内在性的关注是并不矛盾的,他们都是现代艺术的共同特征。通过他在《近代西洋画的精神》一文中对库尔贝以来的绘画精神的概括可知(图6),现代艺术在他眼里都是沿着塞尚以来“主观之人格”的倾向发展的,在“表现主观之人格”的倾向下,才细分出“由头脑感受绘画的精神”和“由内心感受绘画之精神”,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感性的,但是二者都是对主观人格的表现。
前文所言,李宝泉的《碧加索与特兰》虽强调了立体主义继承了自塞尚以来“表现的物的内心”的倾向,但是在该段话之前却也作了这样的表述:
由于数学上对一切自然形态研究的结论,是证实了最真实的一切自然底“原形”都得在解析的几何体(Geometrie Analytigue)之下各种几何形态组织成功。[22]
可见,立体主义的运用几何形体进行形式秩序上的创作阐释,在李宝泉眼中是以数学原理作为背书的。与李宝泉相似,倪贻德在《现代十大画家评传》作了如下表述:
毕加索之所以为毕加索,而在巴黎画坛上获得大名者,得力于此时代。但是最有名的杰作,便是“畢加索夫人”那种有深味的表现和理智的清洒的才能,的确是非凡的……毕加索的超写实主义,具有强力的理性的透明和敏锐的感觉的表现。[23]
以及其以尼特为笔名,发表的《立体主义及其作家》(图7)中的表述:
当时的毕加索和集团的许多人交际着。这些人都是在巴黎的艺术界造出一种特色的……天才的数学家和他相识,他是根据“X”“Y”的方法及对无限性的数学的极数来说明世界的。这集合中不论哪一个,都具有能刺激他人的理性的集合。[24]
倪贻德对毕加索的阐释中多次提及理性要素,所谓“理智的清洒”“强力的理性的透明”和“他是根据‘X‘Y的方法及对无限性的数学的极数来说明世界”的表述,都是为了毕加索作品中的理性要素。但倪贻德这里的理性要素更倾向于画面的形式秩序,而并非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精神。
总的来说,毕加索在民国知识分子的阐释中被赋予了“真美之精神”的内涵,并以此将其与写实主义艺术相区别,并通过这种阐释赋予其作品意义,即:对成法的突破、对内在真实情感的抒发以及对事物内在精神的表现。[25]但这种阐释并不只针对毕加索,是对这一时期现代主义艺术的普遍阐释。换言之,通过对“真美精神”的重要性的强调,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诸多抽象流派获得了在民国艺坛的生存空间,毕加索就是诸多受益的艺术家中的一个。
因此,重视作品形式法则和构图秩序的立体主义风格作品,往往都可以被视作表现“真美精神”的代表,被视作释放天性和本能的求真率性之作。但是,在对毕加索作品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时,作品对形式秩序的追求不得不谈。因此,毕加索便被塑造为既表现“真美之精神”,又重视理性精神的矛盾的综合体。而这种矛盾性恰合了刘海粟对“真美”的理解,即在理法中自然地释放天赋和本能。而之所以用理性精神来对毕加索的作品进行描述,一方面可能由于当时并未发展出完善的中文系统来与西方的Formal Order 相对应,另一方面可能是受科学、理性精神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关,人们很难列举出反对科学和理性的理由,因此以这一概念出发对毕加索的意义进行阐释更容易获得认同。最终,在民国知识分子的阐释中,毕加索既与科学相区别,是表现“真美之精神”的代表;又与科学相联系,是形式法则和理性精神的拥护者。
三、反对者的视角:图案把戏和商业骗局的操弄者
与试图理解毕加索的知识分子不同,反对毕加索的知识分子的观点较为鲜明。在费成武看来,毕加索的作品便是一种故弄玄虚的骗人话术(图8):
他们根据几何学的观点,看一切物像,把自然的实形改变到抽象的几何形体,这是他们根本的理论。至于立体派绘画的技巧,可以分为两种:平面的四方构成和立方的构成,他们就定哪些名词——Cubisme Scientifique,Cubisme Physique, Cubisme Orphique 和Cubisme Instinctif,成为一套骗人的术语。[26]
……
吹了一大套,还不过是图案上的一点原理,所以与其说他是绘画,我以为还是说他是图案来得妥当些。[27]
在徐悲鸿看来,毕加索的作品是画商操弄下的产物,并在不同文章中多次对毕加索进行了攻击。1929年的“二徐之争”中,徐悲鸿虽还未旗帜鲜明地反对毕加索,但是已经开始对艺术中的商业炒作进行否定了(图9),认为马奈、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是因为“卖画商人之操纵宣传”才能“震撼一时”:
动物如排理(Barye),虽以马耐(Manet)之庸,勒奴幻(Renoir)之俗,腮惹纳(Cezanne)之浮,马梯是(Matisse)之劣,纵悉反对方向所有之恶性,而藉卖画商人之操纵宣传,亦能震撼一时,昭昭在人耳目。欧洲自大战以来,心理变易。[28]
1935年1月在上海《大众画报》第15期中刊载的《悲鸿漫谈》,便将毕加索作品形容为狗屎,认为毕加索是受画商包庇的趋利之徒:
彼辈类多伊斯莱之苗裔,多财善贾,手段与方法灵妙莫能比……其敢抗议者必多方设计,使其言议论不能发表,且联络国际画商,令倾向趋于一致,得畅销其货品以分利。其最大之力量,并勾结各国现代美术馆主持人,上下其手,狡谋益逞。故法国近塞尚、马蒂斯、薄奈儿,又比干索、大冷、于脱理窝之辈,并日本人嗣治等,皆受该类商人庇护,大亨其名,其作品皆狗矢之类。[29]
1936年1月1日,徐悲鸿在《中国学生》上发表的《艺术之品性》,将毕加索的作品形容为粗制滥造,“硬捧他为杰作,当然俗人之情”的产物:
苟有人赴罗马西斯廷教堂,一观拉斐尔壁画,雅典派之《圣祭》。或见荷兰伦勃朗之《夜巡》,虽至愚极妄之人,亦当心加敬畏。反之倘看到马蒂斯、毕加索等作品,或粗腿,或直胴,或颠倒横竖都不分之风景,或不方不圆的烂苹果,硬捧他为杰作,当然俗人之情。[30]
1947年,由于毕加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法西斯行为和法国共产党员的身份的影响,国内对毕加索的介绍已经趋于政治化,且以歌颂为主。但徐悲鸿在1947年9月4日于《广播周报》中发表的《世界艺术没落与中国艺术复兴》中,仍然坚持将毕加索的艺术價值视为画商操弄的产物,现在之所以能够在苏联留存,是因为他的政治功绩:
现在巴黎艺坛之红人,一为毕加索,一为马蒂斯。马为40年前俄国资本家捧出来的人,酷好美术,当时俄国有名画家如列宾、苏里科夫、隋洛夫、来维当等的杰作几乎尽为他所收藏。他生前即将他的收藏公之于众,所以现在莫斯科的俄国美术馆,仍旧保有他的名,此乃唯一资本家留传的名。因为苏联共产党认为他对文化有功绩也。[31]
相较于毕加索的支持者在引入过程中对毕加索的复杂阐释而言,反对者的观点清晰明确至近乎武断。费成武将立体主义的形式秩序归结为“图案之把戏”。这一评价虽是针对立体主义发出的评价,但他的判断几乎否定了所有带有抽象化、形式化特征的现代派艺术。徐悲鸿从商业化角度出发对立体派的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欲加之罪”的嫌疑。相较于传统的学院派艺术而言,现代派艺术更加依赖商业画廊,而学院派艺术的评价体系依旧是传统的沙龙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学院派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都有商业化的成分。在这一层面上,徐悲鸿避重就轻地从商业化角度出发对现代主义艺术进行了全盘否定。
徐悲鸿和费成武为师徒关系,他们的观点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以徐悲鸿为首的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们对立体主义为代表的抽象派艺术的态度。在主张“作物必须凭实写,乃能惟肖”的徐悲鸿看来,西方学院系统中的写实主义才是西画正统,各类现代风格不过是新近产生的浮躁趋利之作,引入西方的传统写实技巧是改良中国画凋敝状况的重要举措,学习西方的现代派风格对中国艺坛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32]徐悲鸿等人对现代主义的反对,本质上来源于其对写实主义的推崇。在对现代主义的态度上,徐悲鸿为首的现实主义者们持消极的否定态度,吕澂、刘海粟、丰子恺和鲁少飞等人则持相对积极的态度,或支持先客观引进,或于现代主义的作品中阐释出其对中国艺坛的意义。基于美术创作引发的争论很难有定论,因而在对现代主义的价值的判断上,拥护者和反对者们产生了长足的争论。就徐悲鸿和费成武而言,无论将立体主义定性为装腔作势的图案把戏、商人逐利炒作出的浮躁之作、抑或是迎合大众庸俗审美的粗陋作品,徐悲鸿和费成武都未上升至政治立场的高度对毕加索进行否定。后期毕加索因为其政治身份而饱受推崇,但徐悲鸿仍是从艺术创作立场出发对其给出了否定性评价,认为毕加索的艺术价值并不能与出于政治立场而赋予其的崇高威望相匹配。
四、结语
“黄金十年”中,民国知识分子从各个立场对毕加索进行了引介和讨论。在强调如实转译的译介者的影响下,西方语境中对立体主义理念晦涩玄深的表述同步出现在中文语境中,加之译介过程中的失真,进一步导致了中文语境中的毕加索形象的难以理解。与此相矛盾,知识分子对毕加索的译介行为赋予了毕加索在中文世界中的权威性,加之毕加索在西方艺坛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一个有着玄深理念的艺术大师的形象便渐渐形成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毕加索做出了颇具个人感悟的演绎。毕加索艺术创作中的直觉要素和形式要素被阐释为“真美之精神”和理性精神。这种阐释迎合了民国画坛对新艺术的期待,塑造出了既能以真性情反“四王”以来陈陈相因的艺术传统,又具备科学、理性的先进思想的立体主义艺术。在这种阐释下,毕加索被接受为运用科学法则表现真性情的艺术大师。与上述两者不同,毕加索在反对者眼中变成了“卖画商人之操纵宣传”和“图案之把戏”的产物。反对者眼中的毕加索形象,也构成了“黄金十年”中毕加索接受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黄金十年”在炮火声中进入尾声,美术事业的建设被迫搁置,“美术救国”开始取代“美术革命”成为新一阶段美术事业建设的重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真美之精神”的赞扬性说法、还是图案把戏和商业骗局的批判性说法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都失去了意义,变成了脱离实际的“象牙塔”之谈。基于美术创作立场给出的评价逐渐被基于民族立场、政治立场给出的评价取代。正如徐悲鸿所言,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毕加索的声望更多地来源于其反法西斯的行为和共产党员的身份,所谓“真美之精神”、图案把戏和商业骗局的说法都被隐没在这一光芒之下。当毕加索的威望来自政治而非艺术,更进一步地挖掘和理解毕加索的艺术理念也变得不再重要,如实转译的研究性文章被出于政治立场的赞颂性文章取代,因而“黄金十年”存留下的如实转译的晦涩文本便被视为对毕加索的客观叙述而日益受到重视。在这些文献和毕加索的政治威望的共同作用下,毕加索被塑造为颇具影响力的、理念晦涩艰深的反法西斯艺术家。毕加索的新形象颇具政治色彩,不再具备此前的可争鸣性。在此之后,毕加索的艺术价值不再受到质疑,但其艺术作品中的晦涩思想却再未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厘清,这种局面一直到改革开放掀起新一轮的译介热潮后才开始好转。
毕加索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无可避免地带有反启蒙理性的集体无意识,存在着很多的不可解因素。而“黄金十年”的中国正处于启蒙理性的高峰,科学原理和理性精神的影响力巨大。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中,毕加索作为先进的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被引入,但其精神内涵中的反理性思潮却偏离中国主流思潮而不被需要。面对这样的矛盾,其作品中的晦涩不可解被翻译者如实引入,其作品中的反理性被阐释为“真美之精神”被用来弥补“四王”以来陈陈相因的中国画传统,其作品中的形式秩序则与理性精神作了连结。在这样复杂的阐释下,毕加索终于在中国立稳了脚跟。抗战爆发后,“美术革命”的理想信念被“美术救国”的现实需要所取代,政治立场和民族立场的重要性先于艺术价值。在这样的变革下,毕加索的政治性身份取代其艺术价值成为其在民国艺坛的新立足点,其作品中的不可解部分则被藏在政治的外壳下不再被谈及。
由毕加索在民国“黄金十年”中的形象变化可以看出,对西方艺术的引介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工作,它还涉及跨文化背景下对艺术意义的重新阐释。每一时期所塑造出的毕加索形象,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赋予了毕加索在中国艺坛生存的能力和意义。在以往的接受史叙述中,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和“吸收”的部分往往更被强调。但事實上,接受一旦发生,塑造也一并发生。毕加索在中国的接受史也是其在中国的塑造史。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艺术的引入,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转译,而是基于中国的文化背景、经济状况、艺术发展状况等因素做出的塑造性的引入。在这种塑造性的引入中,凝结着不同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和前途、艺术命运和前途的深刻考量。在这种考量中,外来艺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联系了起来,最终赋予其在中国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塑造性的引入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变形,但正是这种变形赋予外来艺术在中国以存活下来的生命力。在对这些变形的考据中,中西文明的差异、知识分子对艺术前途和家国命运的思考便清晰地显现出来。
注:文中出现辟卡梭、辟卡索、辟卡苏、毕加梭、碧加索均为出版物中毕加索的不同译名。
作者简介:陈能泳,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现当代艺术与民国美术。
注释:
[1] 1917年,姜丹书的《美术史》出版,用上下两篇分别对中西美术史进行了介绍。1922年,黄忏华编述的《近代美术思潮》的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吕澂编译的《西洋美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3年再版)。1926年郭沫若的《西洋美术史提要》出版。1928年鲁迅译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1929年再版)。1928年,萧石君编的《西洋美术史纲要》在中华书局出版(1934年再版)。截止1929年,已有6本西洋美术史的专著出版,郭沫若和萧石君将印象派作为他们美术史写作的终结,其余四本外国美术史专著都对西方现代派艺术有所论述。
[2] 1929,徐志摩的《我也惑》在《美展》上发表:在最近几年内,关于欧西文化的研究也成了一种时髦,在这项下,美术的讨论也占有渐次扩大的地盘。……我亲自听到过(你大约也有经验)学画不到三两星期的学生们热奋地争辩古典派与后期印象派的优劣,梵高的梨抵挡着科雷乔的圣母,塞尚的苹果交斗着波提切利的维纳斯——他们那幼齿的便捷与使用各家学派种种法宝的热烈,不由得我不十分惊讶地钦佩。
[3] 丰子恺:《二十世纪的新艺术》,《贡献》,1929年第5卷第1期,第1-19页。
[4] 同上。
[5] 同[3]。
[6] 王子云:《欧洲现代艺术》,《艺风》,1936年第4卷第7-9期,第18-38页。
[7] 倪贻德:《近代绘画的代表作》,《青年界》,1931年第1卷第1期,第191-203页。
[8] 林文铮:《由艺术之循环律而探讨现代艺术之趋势》,《亚波罗》,1932年第6期,第2-34页。
[9] 叶秋原:《世界民族艺术之发展》,《前锋月刊》,1930年第1卷第1期,第32-57页。
[10] 林镛:《辟卡梭与辟卡梭主义》,《美术杂志》,1937年第1卷第5期,第121-125页。
[11] 华宾:《法兰西新画坛》,《申报》,1930年6月15日,第23版。
[12] 陈士文:《比加索》,《艺风》,1933年第1卷,第5期,第25-27页。
[13] 刘海粟:《画学上必要之点》,《美术》,1919年第2期,第5-9页。
[14] 同上。
[15] 同[13]。
[16] 俞寄凡:《近代西洋画的精神》,《申报月刊》,1935年第4卷第3期,第80-86页。
[17] 鲁少飞:《西班牙的近代绘画》,《艺术评论》,1923年第17期,第3-4页。
[18] 曾鸣:《最近碧加索的艺术》,《艺风》,1935年第3卷第8期,第22-25页。
[19] 刘海粟:《论艺术上之主义——近代绘画发展之现象》,《时事新报》,1923年10月10日,第25版。
[20] 同[16]。
[21] 同上。
[22] 李宝泉:《碧加索与特兰》,《新世纪》,1936年第3期,第37-38页。
[23] 同[7]。
[24] 尼特:《立体主义及其作家》,《艺术》,1933年第2期,第20-28页。
[25] 在民国知识分子眼中,写实主义与近代科学联系密切,引入写实艺术便意味着对近代科学和经验主义精神的引入。而抽象艺术较难与近代科学产生联系,因此“真美之精神”的阐释便赋予其科学之外的另一重意义,即对成法的突破、对内在真实情感的抒发以及对事物内在精神的表现。
[26] 费成武:《谈立体派绘画》,《校风》,1935年第231期,第922-923页。
[27] 费成武:《谈立体派绘画(续)》,《校风》,1935年第232期,第926页。
[28] 徐悲鸿:《惑》,《美展》,1929年第5期,第1页。
[29] 徐悲鸿:《悲鸿漫谈》,《大众画报》,1935年第15期,第7-8页。
[30] 徐悲鸿:《艺术之品性》,《中国学生》,1936年第2卷第1至4期合刊,第67页。
[31] 徐悲鸿:《世界艺术没落与中国艺术复兴》,《广播周报》,1947年第261期(复刊第六十五期),第7-8页。
[32] 徐悲鸿:《中國画改良论》,《绘学杂志》,1920年第1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