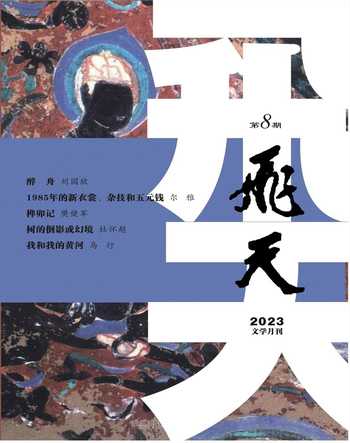在明亮的柔光里
2023-08-02吴梅英
吴梅英
一次意外的死亡
我感觉脚下忽地一软,像踩在一团棉花之上,又像踩着一个毛线团。我那时候急着往外跑,不知跑去做些什么。那是春日的午后,整栋老屋好像没有一个人。这肯定是我的错觉,老屋那么大,不可能没有一个人。也许老人们正坐在内堂自家的窗户下晒太阳呢,但我是在外堂的天井里,外堂幽暗的空间里堆着许多柴垛,透过狭窄的通道,我看见内堂空空的,没有一个人。
阳光落在外堂天井前面的猪栏上,很亮很亮的阳光。天井里没有阳光,但却一片明媚。我猛地停下脚步,像一座雕塑,将奔跑的姿势卡在那一片明媚里。
我当时究竟跑什么呢?我一点都想不起来。那个午后那么静谧,风轻轻吹,鸭在池塘里慢慢游,洗过的衣服在竹竿上微微飘动,小鸟们悠闲地掠过天井上方的天空。一切都不急。母鸡咕咕叫着,它的周围跟着一群小鸡,它不紧不慢地在土里刨食,小鸡们毛茸茸的,抖擞着小身子,碎步跟在母鸡身边,叽叽着一路争抢母鸡啄出来的食物。公鸡歇在柴垛上。那可真是一个无比惬意的午后啊。
可惜我不知为什么舍命奔跑。我的脚步迈得很大,我从老屋朝东的大门跑出来,百米冲刺的运动员一样,冲出外堂,冲向天井。我的目标是天井外那条小路。那条小路通向操场,通向小溪。姐姐和妹妹呢,她们为什么没有出现?也许姐姐上山干活去了,妹妹有可能就在操场上玩闹。我正要去找她,去凑那一份春天无法言说的快乐。
如果我到达天井之前慢下来就好了。飞奔间,我已经注意到,天井里密密麻麻都是觅食的鸡,我心里也提醒过自己要小心,我是踮着脚尖跑的,我在鸡群里快速拣择着可以落脚的空隙。
可那个午后的老屋天井,完全被鸡们占领了,它们没给我让出一寸地方来,供我的脚尖跳跃着前进。许多熟悉的不熟悉的鸡都汇聚到一起,也许它们正在举办一场春的聚会。天井石缝间,小虫子们都嗅到了春的气息,它们蠕动起来,急于长大,想要钻出地面。母鸡的尖嘴帮了它们的忙,也破碎了它们生的幻想。有什么办法呢,小鸡们需要长大。一个生命的成长,依赖于另一些更小生命的成全。
我是颤抖着停下来的。一颗心怦怦直跳,似乎就要蹿出喉咙口,蹦到柴堆上、瓦背上,远远地逃离这个天井,逃回到几秒钟前的胸膛。几秒钟前多好啊,一切都那么祥和,我的脚步那么轻盈,脚底下外堂的泥地那么厚实,没有一只鸡阻挡我飞跑,没有脚下突然一软的恐怖。现在,鸡们惊恐万状地叫喊着、飞奔着,它们跳起来、飞起来,离开地面,飞上柴垛,妄图飞到天上去。只有天堂永远安宁。
这一瞬间成了我生命至痛的起点。它将幼年的我撕裂,讓其中一部分永远停留在那个春天的天井里,永远不会长大,一直颤抖不已。
回头的瞬间,我看见了那只小鸡。毛茸茸的,只有拳头那么大。它倒在那里,小嘴巴小脚还是生前的模样,小眼睛却不动了。我用脚尖轻轻碰了它一下,想唤它起来,想让它跟着母鸡,像其它小鸡那样,惊惶地迈动两只小脚丫碎步快走。但它没有起来,它整个身子借着我的脚力动了动,就那么僵硬地挺着两只细腿,卧在冰凉的石块上。它死了,我悲伤地想。
我转头朝四周看看,没有一个人。仔细看看那只母鸡,不是我家的。我踩死了别人家的小鸡!我想起一些邻居生气地追讨赔偿的表情,左看右看,确定没有一个人,我暗暗庆幸。深吸口气,飞快转身,跑出天井,跑向小路,跑进操场热闹的人群。
我在操场上玩了一个下午。玩闹中,我近乎忘记了那只小鸡。也一直没有什么人拎着一只死去的小鸡走到我面前声讨我。我稍稍安心。快吃晚饭的时候,我慢慢走回家,我从小路上走来,走到天井,鸡们已经不见,应该都已被各自的主人唤回家了。我也没有看见那只死去的小鸡,想来是被什么人捡起来扔了吧,是扔到小溪里了么,它的主人可曾想着寻找凶手?我心里有些忐忑,如果家里人知道我踩死了一只小鸡,肯定是要骂我的。
走进家门,看见饭菜已经上桌。祖母还在厨房忙碌着,母亲正呼我们吃饭。一切都很平静,这是一个寻常的傍晚,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记忆中的那窝猫
母猫叼着一只老鼠走进来,灰黑的地板上,它轻手轻脚又大摇大摆。煤油灯昏黄的光照着它黑白混杂的毛发、竖起的两只尖耳朵、叼在嘴里还没完全死去的老鼠。老鼠四只小脚还在踢腾着,肥硕的肚皮暴露在光里,露出一片惨烈的白。
走至床前,母猫把老鼠放下,看着老鼠在地板上惊恐地翻腾。它伸出前爪,轻轻拨了一下老鼠的肚皮,神态里满是戏弄的意味。老鼠惊惶失措,却怎么也爬不起来。母猫终于不想玩了,“呜”一声,白胡子抖动着,两只前爪捉住老鼠,一口咬了下去。
三只小猫趴在床沿上看。三只不同花色的小猫,大花、小花,还有一只身子全黑,四只脚却呈现雪白的颜色,像踩着四朵祥云。它们前爪搭着床栏,头伸出床外,喵喵叫着,却不敢跳下床去。母猫又拨弄了一下老鼠,确定死了,一口叼起老鼠,神气地一个箭步蹿上床,三只小猫转身,兴奋地跟着母猫,小尾巴轻轻摆动。母猫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至床靠近墙壁那一边,母猫放下老鼠,三只小猫迅速围了过去。
这时候我们也趴在床沿上观看,我们是猫们亲密的朋友。白天吃饭时,猫们守在桌子底下,等待分享我们碗里的食物。天黑下来后,它们跟我们一起爬上二楼房间,在床上玩耍。
它们,我和我姐,祖母和祖父。两铺床床尾相接在房间的一个转角处。每天晚上,我们从这铺床跑到那铺床,猫们也从这铺床跟到那铺床,就这么来来去去,人和猫一起,两铺床上玩得不亦乐乎。
小猫是在他们的床上出生的,不是我们的床,我姐坚持说。她说她亲眼看着小猫一个个出生,母猫一个个吃下自己的胎盘。我记忆里的场景是母猫叼着小猫在两铺床间来来去去。我那时候特别担心,总怕母猫会咬破小猫脖子上的皮,怕母猫走动过程中一不小心,小猫会从床上掉到地上。有时我忍不住抱过小猫,将小猫抱到某个自以为母猫想要的位置上。母猫走过来,再次叼起小猫。三个都成功转移后,母猫坐下来,将小猫揽到怀里,伸出舌头,一只一只地舔。
我们很高兴小猫出生在我们床上,终日守在床边,凝视它们的一举一动。我们说话的声音很轻,都是脸对脸地,彼此靠近了用气声说话。不是怕惊动小猫,而是怕楼下卧室里跟我父母睡的妹妹。我妹小时候像男孩子,健壮又刁蛮,小动物到她手里必死无疑。我们担心小猫出生的事被她知道,都当一个天大的秘密守着。
夜里,小猫依偎在母猫怀里睡,我依偎在我祖母怀里。母猫像是怕我踢到小猫,远远地卧在我脚那一头。一些夜里,半睡半醒间,我会感觉自己的脚碰到了母猫,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从脚底传来。我缩回脚,转动身子,再次抱紧祖母,又安然睡去。人和猫有节律的呼吸,响起在阁楼漆黑的夜里。
小猫稍大就藏不住了,它们是活泼的家伙,常常我还没醒就蹿到楼下,在我妹卧室门口探头探脑。我妹跳出来,一把抓起小猫玩耍。那只最弱的小花经不起我妹折磨,越来越瘦,毛发也越来越干。我于是常常抱起白蹄,我姐抱起大花,我们都高度警惕,时刻防备我妹突然伸出魔爪。可怜的小花有一天终于死了,我祖父编了只简陋的小竹篮,把它装起来拎出了家门。我姐跟了去,回来说,小猫被挂在了村子西边那棵高高的榧树上。
白蹄和大花长大了,我妹好像没有玩耍大猫的兴趣。也许,大猫行动敏捷,她也捉不住。冬天,祖父和父亲出门去江西,我妹和母亲睡到我祖父床上,跟祖母、我姐三人一床。
一个夜晚,我母亲睡梦中突然惊恐地哭喊起来,婶啊,我压死母猫了,我压死母猫了!我母亲叫我祖母婶。我们都被她凄厉的哭声惊醒,内心升腾起凝重的恐惧。夜那么黑,天那么冷,父亲和祖父不在家,什么样的风吹草动都让人心惊。更何况,她说母猫死了,死,这是多么恐怖的字眼,我们平常很忌讳说它。我们全睁着眼睛,从被窝里伸出头来。我祖母迅速爬起,划根火柴点亮油灯,走到母亲那边,伸手往床底下一摸,母猫一个翻身从被窝里钻出来,低着头不声不响走到我们床上,很快又在我脚边卧下。它淡漠的神色里透露着一种不耐烦,好像是怪我母亲大呼小叫,惊扰了它的睡眠。我祖母回到我们这边床前,吹灭油灯,掀开被子躺进来,人和猫又开始睡梦中的漫漫长夜。
说来也奇怪,三个孩子,三只猫,都横七竖八的,却从来没有压死猫的情况发生。我们一起玩耍,一起睡,相依相偎着,共同抵御冬夜的寒冷与寂寥。
五个人、三只猫的快乐日子持续了一个冬天。春天一到,人和猫都按捺不住地想往外跑,老鼠从洞里钻出来,探头探脑地,招摇着从我们眼皮底下跑过。猫的心被春风吹散了,虽然寒潮还牢牢控制着龙井,祖父和父亲也还没回家,猫们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似的,家里經常看不见它们的踪影。
一天晚上,我们上楼时,发现只有母猫和白蹄跟着,大花不见了。我祖母下楼,喵呜喵呜地连连呼唤,大花也没有出现。我姐跟她一起点着火篾,里里外外地找,终于在柴房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已经死去的大花。祖母说,可能吃了死老鼠。老鼠四处流窜,与人争抢着不多的粮食,有些人家投放了鼠药。
又有一天,母猫也死了。母猫吃死老鼠时,我们是看见的,它叼了老鼠进来,像往常一样,还想与白蹄分享。是我祖母发现了异常,她说不好,好像是只死老鼠,她大声叫骂着,甩着正拿在手里的火钳子要打母猫,母猫急忙丢下死老鼠逃出门去。但已经晚了,那天夜里,母猫没有上楼。
只剩下白蹄了,我们都很紧张,生怕白蹄也误食死老鼠。我们姐妹出去寻找过鼠药,没有找着,我们只好一遍遍教育白蹄,让它一定不能吃死老鼠。我们单纯地以为,只要它一天到晚吃饱饭就不会出去瞎吃,三餐都把它喂得饱饱的。没事的时候就喵呜喵呜唤它过来,经常抱她。白蹄很反感,它好像感觉到我们想要控制它,从我们怀里蹿下来,箭一般冲出门去,有时似乎仅仅是为追逐门前一缕阳光,甚至风卷起的一张纸屑;有时不知它跑什么,好像远处有什么在呼唤。
白蹄死的那天,我们都不在家。我们上山去了,老屋的女孩,大的小的,只要天晴,都一伙一伙上山砍柴。我们扔下柴,没看见白蹄,问母亲,母亲笑着说,死了。我们以为她开玩笑。我母亲有时像个孩子,会跟我们开玩笑。里里外外找,还是没看见白蹄,我慌起来,问祖母,祖母说,又吃死了。我大声哭起来,我姐也哭起来。想不到的是,我妹也哭了,她的声音很大,坐在地上踢腾着,叫喊着要白蹄,好像白蹄是她的最爱。
我和我妹去找了那棵大榧树,我们从桥头的小路进去,往西走到村口,在大榧树下仰着头观望。高处荫蔽的某个枝丫上,似乎有个篮子,不知里面躺的是不是白蹄。
初二那年,我祖母去世。此后,我们家再没养过猫,但一只一只的猫,一直在我记忆深处走动着。它们走过我家堂屋、厨房,跑上楼梯,进入卧室,直接就跳到了我们床上。有时,它们从阁楼外一个缺口爬上去,在矮墙、瓦背之上轻盈跳跃。我站在阁楼光线明亮的地板上,仰头朝它们喵喵叫唤着。它们回头,就那样定定地看我一眼,又跳跃着继续前去。我就在那光里睁着眼睛,看着它们消失在瓦背之上,青山之前,天空之下,消失在无比明亮柔软的光里。
小狗欢欢
欢欢从楼上跑下来。厨房里,木板楼梯一阵响动。它冲出厨房门,跑到我们身边,摇着尾巴,绕我们激动地转了三圈。三圈转完,它停下来,在我们脚边慢慢卧倒,全身蜷缩成一团。
三天没下楼了,妹妹说,狗就这么有灵性,你们进门它就知道了。
我的心沉下来。蹲下身子,伸手一下一下抚摸欢欢变得干枯的毛发。三天前,妹妹打来电话,说欢欢不知吃了什么,无精打采的,卧在家里一动不动。我在手摇电话机那一端干着急,嘱咐妹妹带到就近乡镇去看看,妹妹带去拿了药来吃,可还是不见效。
我叫了几声欢欢,它抬眼看看我。那双我所熟悉的眼睛,已完全没有昔日的神采。几天时间,它已经瘦得连我都要认不出来了。
都没吃东西,就那样卧在楼上。妹妹说。
匆匆吃了中饭,我和先生离开龙井,带欢欢去安仁治疗。我们搭乘来村里的班车,欢欢俯卧在我脚下。
“治不好了。”司机回头看了欢欢一眼说。
我在背后狠狠瞪了他一眼,赶紧低头看着欢欢。路不好,车子颠簸不停,欢欢的身子一震一震,看着让人难受。我轻轻呼唤它的名字,它的头耷拉着,似乎已经无力回应我了。我心里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龙井到安仁,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不知道欢欢能不能挺住。
为什么要让欢欢离开呢,三天来,我不断自责。其实,早在欢欢刚被妹妹带上船时,我就开始后悔了。
我眼睁睁看它离开太王庄码头。妹妹牵着绳子带它上船,我和先生跟在后面。也许,它以为我们也会上船,但我们走到码头就止步了,它欢快地跑上船,转一圈,回头,看见船离岸,我和先生没有上船。它站在船头,被一根绳子牵着,怔怔地看着我们。船越行越远,水面愈见辽阔,它看着我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我的心就在那一刻感觉到一种剥离。为什么要让它走呢,我问自己,看先生,他也一脸落寞。
那是1999年,妹妹来王庄看我。当时我病休,跟着先生住在王庄管理区。欢欢是一个月前我回龙井时带出来的,家里的母狗一窝生了三只小狗,只欢欢是棕黄色,妹妹送给了我。我带回王庄,给它取名欢欢。
也许是因为王庄气候跟龙井不同,一个月时间,欢欢迅速长成一只好看的少年狗,神采奕奕,棕黄的毛发变得金灿灿的,像涂了一层油。它每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早上,我们打开房门,它摇着尾巴候在门外,夜晚我们回房间,要走过王庄管理区宿舍二楼长长的走廊,它总是走在我们前面。到房门口,它停下来,或者进门转一圈,看着我们开门、开灯、关门。它就在门外漆黑的走廊里躺下来。门内门外,人与狗,一夜夜静谧相随。
妹妹看见欢欢,大呼小叫的,惊讶得不得了。简直不是一窝狗,她说,龙井那两只,不知要小多少。她坚持要带欢欢回龙井玩几天,说让它们兄弟几个见见面,也让村人看看,不同地方养的狗有多大区别。
我笑着答应了,就像答应让一个小孩子回外婆家小住几天,我没有征询这个孩子的意愿,擅自做了主。为什么要答应呢?先生说。一天夜里,先生回房间,路上遇见一条蛇。如果欢欢在,他说。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车好不容易到了安仁,先生抱着欢欢,我走在前面,焦急地向路人询问兽医店。欢欢的喘息已经很艰难了,肚皮一起一伏,好像随时会停止呼吸。
终于找到兽医店,却发现店铺关门,主人不知去向。先生把欢欢放到地上,它身子笔直地躺着,头靠在水泥地面上,只剩出的气了。
“赶紧放血吧。”旁边一个店铺的人走出来,看欢欢一眼,冷静地建议。我眼巴巴看着他,以为他有什么救命的良策。“马上要死了,现在把血放了,死了还能吃。”他解释說。
我的悲怆在那一刻化成声声嚎啕。安仁马路边,太阳热烈地炙烤着,我的心却跟随欢欢的血一点点变冷。我不停地呼唤它的名字,随着它呼吸的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急。我妄图用这样的声声呼唤挽回它逐渐流逝的生命,让它重新站起来,抖擞着尾巴,绕着我转。但它再也不理会我了,一阵急促的呼吸之后,它闭上了眼睛,它的身子直挺挺的,一副痛苦模样。
先生借了辆自行车,打算把欢欢驮去水边。我站在路旁继续哭泣。先生抱起欢欢,把它放到自行车后座上,驮着它向着马路对面走。夏日午后的阳光落下来,照着他脸部黯然的神色,和自行车后座上欢欢仰躺着的僵直的身子。
责任编辑 维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