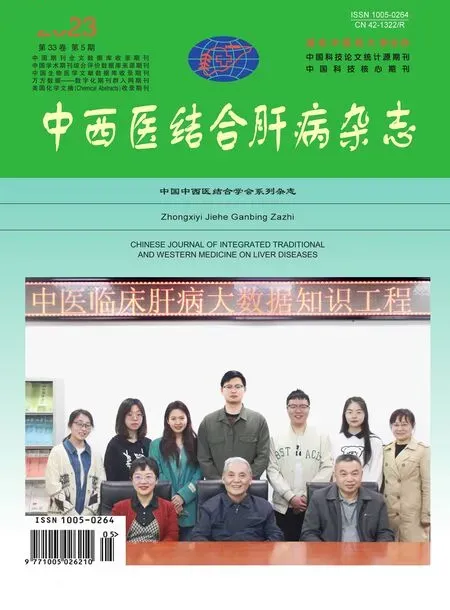肝衰竭预后模型及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展*
2023-08-01蒙荫杰朱玟霜王梓塨王倩倩毛德文
蒙荫杰 邱 华 李 旺 朱玟霜 王梓塨 王倩倩 毛德文
1.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广西 南宁, 530023) 2.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科
肝衰竭是各种损伤因素多重打击下,导致肝功能严重障碍或失代偿,出现以黄疸、腹水、凝血功能不良等为主要表现的一组临床危重症候群。我国2018版指南将肝衰竭分为4类:急性肝衰竭(ALF)、亚急性肝衰竭(SALF)、慢加急性(亚急性)肝衰竭(ACLF)和慢性肝衰竭(CLF)[1]。肝衰竭病情进展迅速,缺乏理想的治疗手段,病死率仍居高不下。近年来,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方案在降低本病病死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早期准确评估肝衰竭患者的病情,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应用,有利于制定最佳的临床治疗方案。
1 肝衰竭多因素预后模型
肝衰竭的发病涉及多种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且不同患者的病因、诱因、病程及并发症等有较大差异,这决定了对其预后影响是多因素的,因此,在临床上一般采用多因素的预后模型,对于预判肝衰竭患者的病情将更为准确。目前常用的肝衰竭预后模型如下。
1.1 CTP(Child-Turcotte-Pugh)评分 1964年Child和Turcotte对131例行门腔静脉吻合术(ITP)的肝硬化患者术后的病死率进行了分析,由此提出了Child-Turcottc(CT)评分。1973年经Pugh等[2]将模型中的肝性脑病(HE)进行分级并调整了每一组别的血清白蛋白(Alb)的范围,同时将CT评分中营养状况这一指标替换为凝血酶原时间( PT),最终形成了CTP评分。CTP评分模型包含5个指标,即对总胆红素(TBil)、HE分级、Alb、PT及腹水程度进行评估,并依据评分将患者肝功能分为A、B、C三级。修改后的CTP评分具有简便、实用等优点,在很多肝病中心被应用于判断肝衰竭患者的预后,是评估肝脏代偿及储备功能的有效工具。CTP评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①HE分级和腹水的判断受主观影响大;②指标中未纳入对肾功能的评价;③病情分级较狭窄,同一评分的患者预后可能存在较大差异;④未对预期生存时间进行设定。因此可考虑联合其他的肝衰竭预后模型进行综合判断,进而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1.2 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及其衍生模型
1.2.1 MELD评分 2000年Malinchoc等[3]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231例行经颈静脉门腔静脉分流(TIPS)术的肝硬化患者的资料进行分析,确定了能较好预测终末期肝病患者3个月生存期的4个指标,包括血清肌酐(Cr)、TBil、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及病因。随后Kamath等[4]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大研究及优化,得到公式:MELD=3.8×log[(TBil mg/dl)]+11.2×log(INR)+9.6×log[血清肌酐(mg/dl)]+6.4×病因(胆汁淤积性肝硬化或酒精性肝硬化为0,其他为1)。MELD评分具有显著优势:①观察的指标均为客观的实验室指标,且数值连续;②纳入了血清肌酐,可预测肝硬化发生相应并发症的风险或严重程度。国内外学者对MELD评分模型进行了大量临床验证,证实了该评分模型预测ACLF或肝硬化患者死亡风险方面优于CTP评分[5-7]。然而,该评分模型并未考虑HE、腹水、感染等并发症对预后的影响,因此,为了使其预测效能更佳,很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对MELD评分进行修改。
1.2.2 MELD-Na评分 Biggins等[8]开展了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对753例终末期肝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将其纳入MELD公式中,由此衍生出 MELD-Na评分,计算公式为:R=MELD+1.59×[135-Na(mmol/L)],并认为该模型比MELD评分的预测效能更佳。Goudsmit等[9]对5 223例终末期肝病患者3个月的预后进行评估,发现MELD-Na评分比MELD评分的准确率更高。2016年美国应用MELD-Na评分指导移植肝的分配,调查结果显示[10],等待肝移植患者的死亡率明显下降。但另一项研究显示[11],在预测肝衰竭行肝移植患者早期(3个月)预后方面,MELD-Na评分与MELD评分预测能力无明显差异。
1.2.3 iMELD评分 考虑到血清钠和年龄这两个因素对患者预后的影响,Luca等[12]通过将两者与MELD评分结合,由此衍生出iMELD评分,即iMELD=MELD+(0.3×年龄)-[0.7×Na(mmol/L)]+100,并认为其提高了预测效能。Saldaa等[13]评估了多种预后模型对818例等待肝移植患者90 d生存情况的预测能力,发现iMELD评分是一个更可靠的工具,代表移植的紧迫性高于meld评分。同时我国的刘海燕等[14]分别采用iMELD、MELD、MELD-Na评分模型对100例HBV-ACLF患者的预后进行评估并比较三者的预测价值,结果iMELD敏感度67.4%,特异度80.8%,MELD敏感度62.3%,特异度86.4%,MELD-Na敏感度65.4%,特异度83.6%,表明3个评分模型对患者预后均有较高评估价值,但效能相当。这可能是群体特征的差异影响了iMELD和MELD-Na的预测能力。
1.2.4 △MELD评分 Merion等[15]通过回顾性分析8 096例肝移植患者的资料,发现动态MELD(△MELD)是肝移植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数据表明△MELD值为10或更高的患者移植后死亡风险最高,并提出了△MELD评分。Colmenero等[16]对肝移植术后患者的预后进行了评估,研究表明△MELD>10表明死亡风险增加1.6倍。我国的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17],预测ACLF(120例)、ACF(171例)患者的预后,△MELD比MELD评分预测价值更高。
1.3 KCH标准 KCH标准由O′Grady等对采用内科治疗的588例ALF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后提出,用于评估ALF患者的预后,根据病因分为乙酰氨基酚(APAP)相关和非乙酰氨基酚(如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相关的ALF。Shakil等[18]对177例ALF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KCH 标准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但阴性预测值较低,同时未达到KCH标准的患者不能预测不行肝移植的存活率。一项荟萃分析结果显示,KCH预测APAP相关ALF患者死亡的敏感性为58% ,特异性为89%,而MELD评分的敏感性为80%,特异性为53%;KCH预测非APAP相关ALF患者的住院死亡率,敏感性为58%,特异性为74%,而MELD评的敏感性为76% ,特异性为73%,表明KCH标准的特异性较高,但敏感性较低,而敏感性差说明KCH标准未能识别不行肝移植治疗就会死亡的患者[19]。国内的韩璞青等[20]比较KCH标准、MELD及MELD-Na评分对妊娠期急性肝衰竭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结果KCH标准、MELD及MELD-Na评分的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548、0.885、0.873,敏感度分别为57.1%、71.4%、78.6%,特异度分别为52.7%、94.4%、88.9%,说明KCH标准对妊娠患者急性肝衰竭的预测价值不如MELD、MELD-Na评分,可能是由于KCH标准是基于非妊娠患者急性肝衰竭所建立的,纳入的指标不能充分反映妊娠期患者急性肝衰竭的肝脏损伤程度。
1.4 序贯器官衰竭及其衍生评分
1.4.1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1994年序贯器官衰竭(SOFA)评分由欧洲重症监护学会建立,基于6个不同的评分,每个评分对应于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肝脏系统、凝血系统、肾脏系统和神经系统,每个评分从0到4,能够全面评估患者器官衰竭的严重程度,评分>12分预示着疾病转归不良。Craig等[21]对138例APAP相关ACLF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SOFA评分预测价值高于钠基MELD衍生模型。Rodrigues等[22]对40例ALF患者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比较SOFA评分、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MELD评分的预测价值,结果表明只有 SOFA评分与死亡风险相关,且SOFA<12组生存率较高,证明SOFA评分是预后评估的最佳指标。然而,SOFA评分也存在着局限性,如肝衰竭患者的凝血功能障碍以凝血因子生成减少为主,而模型中用的是血小板计数,同时,对于神经系统的评估,采用格拉斯哥昏迷(GCS)评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后续的研究者对SOFA评分进行了完善。
1.4.2 慢性肝衰竭(CLIF)-SOFA评分 欧洲肝病学会肝衰竭合作组在SOFA评分的基础上,分别采用INR、肝性脑病分级对凝血功能和神经系统进行评估,由此建立CLIF-SOFA评分[23]。Dhiman等[24]评估CLIF-SOFA、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评估(APACHE)-Ⅱ、Child-Pugh和MELD评分对肝硬化急性失代偿患者28 d死亡率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CLIF-SOFA评分对短期死亡率的预测效能最佳。张其坤等[25]采用CLIF-SOFA、CTP、MELD-Na、iMELD等16种预测模型,分别对135例乙肝相关ACLF患者肝移植术后早期生存进行评估,结果CLIF-SOFA和MELD-Na评分对肝移植术后3个月生存的预测价值最高(AUC分别为0.707和0.716),而且CLIF-SOFA评分在肝移植术后28 d的预测准确度更高(AUC 0.721)。
1.4.3 CLIF-C ACLF评分 2014年,Jalan等[26]对CLIF-SOFA评分进行简化,提出简化版CLIF-SOFA评分,即CLIF-C器官衰竭(OF)评分,考虑到年龄和白细胞计对预后的影响,该研究团队将这两个独立的死亡预测因子与CLIF-C OF评分结合起来,形成了CLIF-C ACLF评分,为ACLF建立了一个特异的预后评分,计算公式为CLIF-C ACLFs=10×0.33×CLIF-OFs + 0.04×年龄+0.63×In(WBC)-2]。Engelmann等[27]对202例ACLF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CLIF-C ACLF、Child-Pugh、MELD、CLIF-C OF评分预测患者入院后48 h的预后评分,并观察患者28 d的预后,结果CLIF-C ACLF评分对患者28 d的预后准确性最高,AUC为0.8(Child-Pugh,0.66;MELD,0.68;CLIF-C OF,0.75),而且CLIF-C ACLF评分界值≥70的患者在28 d内的死亡率100%。这与Ramzan等[28]的研究结果一致,认为CLIF-C ACLF评分≥70是ACLF患者48 h发生死亡的更好预测指标,且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国内的Li等[29]回顾性分析了300例HBV ACLF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了CLIF-C ACLF、MELD和MELD-Na评分的预测效能,结果CLIF-C ACLF评分的预测准确性最佳,表明该预后评分也适用于亚洲的HBV ACLF患者预后的评估。
1.5 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估测评分(APACHE评分) 1981年,Knaus等[30]分析了805例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患者的临床资料,选取客观的生理学参数来评估危重患者的严重程度,并提出了APACHE评分,包括急性病理生理性指标(APS)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CPS)。为了提高APACHE评分的预测效能,Knaus等先后提出了APACHE Ⅱ/Ⅲ评分[31,32],APACHE Ⅱ评分包括年龄、APS和CPS,其中简化后的APS包括12项参数,肺泡动脉氧压差或动脉血氧分压、平均动脉压、pH、动脉心率、呼吸速率、温度(直肠)、钠(血清)、钾(血清)、Cr、红细胞压积、白细胞计数、GCS评分,APS分值为0~60分,年龄分值0~6分,CPS 2~5分,最终APACHE Ⅱ总分值0~71分,评分越高,病死率越高;APACHE Ⅲ评分是在APACHE Ⅱ的基础上增加了5个参数,即Alb、BUN、TBil、24 h尿量和血糖。
APACHE Ⅱ/Ⅲ评分主要应用于评估ICU危重患者的预后,在肝衰竭预后方面的研究较少。Mitchell等[33]纳入102例APAP相关ALF患者,比较APACHE Ⅱ评分和KCH标准的预测价值,结果APACHE Ⅱ评分对死亡的预测能力与 KCH标准相似(敏感度分别为82%和65%,特异度分别为98%和99%),同时APACHE Ⅱ评分>15可以高度预测患者死亡结局或肝移植的必要性。
2006年,Zimmerman等[34]对110 558例符合纳入标准的ICU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队列研究,并在APACHE Ⅲ评分的基础上提出了 APACHE Ⅳ评分,删除血钾、血糖,将是否机械通气、尿酸纳入APS指标中,CPS包括各系统的7种疾病。巴西的一项前瞻性、单中心队列研究,纳入了371例终末期肝病肝脏移植术后患者,采用 APACHE Ⅳ评分预测患者术后的转归,结果该评分对肝移植术后有较高的临床预测价值(AUC:0.797)[35]。
1.6 AARC-ACLF评分 2016年,Choudhury等[36]分析了1 402例符合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诊断标准的ACLF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TBil、Cr、INR、HE分级和血清乳酸均是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由此建立了AARC-ACLF 评分体系。AARC-ACLF 评分总分为5~15分,分为3个等级,Ⅰ级:5~7分,Ⅱ级:8~10分,Ⅲ级11~15分,对应ACLF分级Ⅰ~Ⅲ级的患者,在没有肝移植的情况下,28 d累计死亡率分别为12.7%、44.5%和85.9% ;研究证实,AARC-ACLF评分具有较高的临床预测价值(预测28 d的死亡风险,AUC为0.804,敏感度为72% ,特异度为78%),其预测价值高于MELD、SOFA及CLIF-SOFA 评分;同时AARC-ACLF评分的动态变化提示了疾病预后的风险,即确诊为ACLF后,1周内评分每增加1分,患者短期内病死率增加10%,但评分>10分,任意7 d内评分每增加1分,病死率增加20%。AARC-ACLF评分使用简便,指标易获取,易于推广,适合亚洲人群,临床应用价值较高,但该模型应用时间较短,仍需进行临床验证。
1.7 COSSH-ACLF评分 中国重型乙型肝炎研究组(COSSH)通过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分析了国内13家肝病中心1 322例重症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资料,提出了HBV相关的COSSH-ACLF评分体系,研究证实,该评分对HBV-ACLF患者28/90 d的死亡率具有较高的预测效能(预测28/90 d的死亡风险:AUC分别为0.829和0.828),同时预测能力优于CTP、MELD、MELD-Na、CLIF-C OF、CLIF-C ACLF评分[37]。田小利等[38]开展的一项研究证实了COSSH-ACLF评分对HBV-ACLF患者短期生存预后的评估效能优于传统的肝衰竭预后模型。由于COSSH-ACLF评分计算程序复杂,不便于临床应用,该模型的研究团队进一步扩大研究,纳入2 409例HBV-ACLF患者,分析后发现年龄、HE、TBiL、INR、血尿素(Ur)和中性粒细胞计数(NC)为HBV-ACLF患者28 d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了COSSH-ACLF Ⅱ,计算公式为1.649×ln(INR)+0.457×HE+0.425×ln(NC)+0.396×ln(TBil)+0.576×ln(Ur)+0.033×age,修改后的评分系统简化计算过程,且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39]。COSSH-ACLF Ⅱ评分的研究对象均为乙型肝炎患者,适用于我国HBV-ACLF患者的预后评估,但该模型建立时间短,其预测价值仍需进行临床验证。
1.8 P4和P8评分 2019年,Sun等[40]通过比较三者(HBV-ACLF患者、CHB患者、健康者)血液蛋白质组学之间的差异,发现ACLF患者血浆中与免疫反应、补体和凝血系统等多种功能相关的蛋白明显缺乏,研究者进一步筛选出4个蛋白:载脂蛋白C3(APOC3)、富组氨酸糖蛋白(HRG)、转铁蛋白(TF)、血浆激肽释放酶(KLKB1) ,据此建立了P4评分,该评分用于诊断ACLF,当阈值为0.313 9时,P4诊断ACLF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4.4%和89.1%,AUC为0.961。该研究团队继续进行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发现4种蛋白[(GC球蛋白、HRG、触珠蛋白相关蛋白(HPR)、皮质类固醇结合球蛋白(SERPINA6或CBG)]和4个临床参数(INR、年龄、中性粒细胞、总蛋白)与HBV-ACLF患者3个月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提出了P8评分。研究证实,P8评分对HBV-ACLF患者28 d预后的预测能力优于MELD、COOSH、CLIF- C ACLF评分,而对90 d预后的预测能力则与这三者相似,同时研究者发现P8评分对ACLF患者凝血和脑功能衰竭具有较高的预测能力(AUC分别为0.815、0.842),并且能预测患者短期发生肝外器官衰竭的数量。P4和P8评分的研究人群均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有助于HBV-ACLF患者的精准诊断和预后判断,但其计算过程复杂,指标不易获取,同时研究的样本量较少,预测的准确性仍需进步一验证。
2 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衰竭
目前对于肝衰竭的治疗主要包括西医内科综合治疗、人工肝治疗和肝移植。肝移植由于肝源紧缺、费用昂贵等因素限制了它的开展,内科治疗和人工肝治疗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我国肝衰竭治疗的整体格局并未实现质的改变,发病率及病死率仍居高不下。近年来,国内有多个研究团队对中医药治疗肝衰竭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发现中医药可通过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清除内毒素(LPS)和改善肠道菌群等方式来拮抗肝衰竭[41-43],证实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方案在降低肝衰竭病死率方面确有成效,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及相关临床循证医学证据的增多,形成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衰竭的诊疗指南和专家共识[44,45]。
2.1 中医联合西医内科治疗 肝衰竭的主要病因为湿热、疫毒、瘀血,三者胶结是该病的基本病机,因此解毒、凉血、化瘀、利湿是中医药治疗肝衰竭的重要治则。刘巧红等[46]开展的随机对照研究将68例SALF和ACLF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予西医内科综合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解毒化瘀通腑颗粒(由大黄、赤芍、茵陈、金钱草、黄芩、郁金组成),治疗30 d后,结果显示解毒化瘀通腑颗粒能够改善SALF及ACLF患者临床症状及肝功能。娄海山[47]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自拟解毒凉血化瘀方(由大黄、赤芍、厚朴、元胡、白花蛇舌草、败酱草、茵陈、栀子、黄柏、牡丹皮、郁金、枳实、甘草组成)治疗102例HBV-ACLF患者,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生存率为71.6%,显著高于单纯西医常规治疗组的44.4%(P<0.05);同时在改善肝功能、凝血功能和提高HBV-DNA转阴率也优于单一西医。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共纳入934例HBV-ACLF患者,观察(凉血解毒化瘀方或益气解毒化瘀方加减)加用西医治疗对HBV-ACLF患者48周病死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在4~48周降低患者病死率方面优于单纯西医疗法[48],这与另一项多中心研究结论一致[49]。研究表明凉血解毒化瘀法可以调节HBV-ACLF T细胞免疫紊乱状态,降低LPS水平,改善患者肝脏合成功能[50]。进一步研究证实[43,51,52],解毒凉血化瘀类中药(如大黄、赤芍、地黄、白花蛇舌草等)及其复方通过调控免疫、减轻肝细胞炎症、调节肠道菌群及改善凝血功能等途径来实现抗肝衰竭的作用。肝衰竭后期往往阴阳俱损、气血亏虚,病机为“本虚标实”,因此多在解毒化瘀利湿的基础上加以扶正。王秀峰等[53]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温阳化浊退黄汤(由白附片、干姜、生大黄、赤芍、虎杖、茵陈蒿、人参、白术、甘草组成)治疗HBV-ACLF阳虚瘀黄证患者64例,结果表明该方能降低肝衰竭患者的 MELD评分,提高8周疗程及12周随访期的存活率。由上述可见,以解毒化瘀凉血法为主,在辨病辨证的基础上凝练成的经验方药对治疗肝衰竭有明显的临床疗效,证实了中医药治疗肝衰竭的有效性。
2.2 中药外治法(保留灌肠)治疗 HE是肝衰竭的严重并发症,王娜等[54]认为本病“发于肝、酿于肠、损于脑,大肠为本病发病核心环节”,并首次提出采用“通腑开窍法”即大黄煎剂(由大黄、乌梅组成)保留灌肠治疗HE,临床研究发现该治疗方案能缩短HE患者苏醒时间,降低血氨水平并改善肝功能。罗海燕等[55]在人工肝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汤剂(由大黄、乌梅、 赤芍 、酒黄芩、生薏苡仁、白及 、白芍 、茯苓组成)保留灌肠治疗 HBV-ACLF患者65例,结果治疗4周后加用中药灌肠的早、中期患者的临床疗效优于常规治疗组( 76.19%vs91.83%),并能显著降低患者LPS水平。李海凤等[56]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赤芍承气汤(由赤芍、厚朴、枳实、乌梅、生大黄组成)高位保留灌肠治疗30例HBV-ACLF患者,结果显示赤芍承气汤可改善患者的肝功能、凝血功能,促进肠道有益菌的繁殖,同时减少真菌感染,进而降低患者死亡率。
3 小结
肝衰竭病情危重,预后差,病死率高,早期真实、客观、精准评估病情和预后,可为临床医师制定适合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经过长期研究,众多成熟的评分模型如MELD、MELD-Na、KCH标准、SOFA评分等被用于临床实践,有效的指导肝源的合理分配,挽救了大量急性或终末期肝病患者的生命。然而,由于病因、诱因、种族等差异,当前的评分模型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肝衰竭,因此,各种评分模型仍需不断总结、改进,以期更好地服务于肝衰竭的防治。
中医药被证实可以有效地防治肝衰竭的并发症,提高临床综合疗效,降低肝衰竭病死率,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法有望成为更多肝衰竭患者的选择,也是更有效的治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