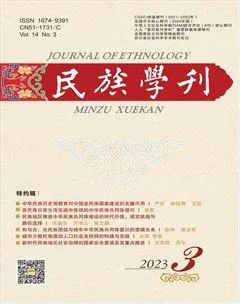现代道路与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变迁
2023-07-31杨梅



[摘要]普雄镇是成昆铁路线上的重镇,其社会经济发展与成昆铁路密切相关。通过考察不同时期成昆铁路对普雄彝族社会的影响,不仅可以管窥普雄彝族社会近五十年来发生的剧烈变迁,同时可以提供一种现代道路视域下研究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变迁的新路径和新视角。普雄镇的个案研究表明,对于深处西南边远地区的凉山彝族而言,道路是其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载体。尤其在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凉山的交通基础设施正不断完善,在建以及规划建设的道路将不仅为凉山打开“互联互通、对外开放”的新局面,而且为凉山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保障,同时也将带来文化异质性的输入。普雄的个案亦启示我们,面对道路带来的文化异质性输入时,地方社会应该加强自身文化转型的主动性,从而在规划自身发展与实践上获得更多自主性,进而增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内生性資源和动力。
[关键词]成昆铁路;普雄,现代性力量;乡村振兴;转型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3-01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道路建设对凉山彝族社会的影响研究”(20CMZ022)、西昌学院博士启动项目“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状——以凉山州境内段为例”(YBS202214)、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科建设70周年发展成就研究”(2022ZGYXYJZX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梅(1987-),女,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道路人类学、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四川 西昌 615000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1]“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2]以及“时空张缩”(time-space expanding-compression)[3]等特征的现代道路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现代道路本身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格局而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意涵,道路不仅是人和物等诸多要素在生活或物理意义上进行流动的载体,同时也是思维或思考方式等诸多文化要素进行传播和交流的媒介,以及社会变迁的动因。
在中国,“要致富,先修路”的口号已深入人心。诚然,交通基础设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体系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中国提出“四好农村路”①,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作出重要指示时指出:“‘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4]四好农村路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改善了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对于各民族的流动、接触和交融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和世界级港口群,中国高铁、中国路和中国桥已经成为响亮的“中国名片”。这些路网不仅在客观上带来了通达性和便捷性,同时这些强大的国家工程项目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也是凝聚人心和激发各族人民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和载体。此外,“一带一路”交通互联互通不断取得新突破,中老铁路、中欧班列、西部海陆新通道等国际大通道不仅赋能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有效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互利共赢发展。因此,这些国际大通道充分发挥着连接、过渡和融合的意义[5] 。无论是“四好农村路”、村村通公路工程,以及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等路网,抑或是中老铁路中欧班列等国际大通道,无一不彰显党和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和关注。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学者将道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探讨诸如道路与全球化以及道路与地方社会文化变迁等关系,从而对道路带来的复杂影响展开相关研究。道路可以提供一种地方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交流的媒介,如欧金尼奥·阿里马(Eugenio Y Arima)等学者指出“道路是传统的封闭社区实现与外部世界接轨的途径,道路的修建使得边远的地区也能卷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6] 。便捷的交通使得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以及物质交易可以跨越空间得以实现,边远地区可以与更广泛的区域、都市、国家甚至国际获得连接媒介。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Conrad Kottak)的研究表明,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由于一条阿伦贝皮与州府萨尔瓦多之间公路的修通运行,使得该社区原有的生计模式、职业结构以及经济方式等发生了巨大变迁,它“从一个相对孤立、平等主义和同质的社区,变成一个职业分化、信仰多样、社会阶级与地位存在高低的社会”[7] 。这些研究均表明,道路是地方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动因之一,也是地方社会融入全球化以及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和转型,现代道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载体更是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翁乃群等学者较早从人类学的视角关注铁路建设对沿线村落社会文化的影响,其中主要研究了沿线云南、广西和贵州的八个村落铁路修筑前后在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8] 。作为通往西藏腹心地区的第一条铁路,青藏铁路成为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对社会转型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有力推动了区域和城乡间的流通、物流和信息流的流动,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社会进步[9]。在少数民族村落的道路修建和使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和“地方性”与“全球化”等二元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10]。路既是少数民族村落变迁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它们之间是一种“生死相依”的关系[11]。同时,通过考察少数民族地区因道路而发生的社会变迁,还可以揭示道路与民族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②。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道路与少数民族村落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村落的发展与道路建设之间是一种变动之中的空间形态与村落社区的互动关系[12],且在当前高速公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积极主动思考次区域和次节点的利益,从而尽可能整体关照新型道路与社会的关系[13]。当前学界对道路与少数民族村落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表明:其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与道路建设密切相关;其二,有些少数民族村落在道路变迁中获得了发展机遇,进而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为“区域中心”,而有些则被进一步区隔或边缘化。但无论是中心化还是边缘化,不同地方都会运用地方性知识,并借助国家力量,作出调整并探索出一条适合新环境的发展之“路”;其三,无论道路是作为一种物质实体,还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和文化意涵的抽象空间,它都可视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交流和社会变迁的一种隐喻或象征,更是少数民族村落地方社会赖以生存的空间和载体。
综上,当前学界对现代道路建设和少数民族村落社会变迁进行了不少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有关道路与凉山社会变迁的研究却寥若晨星。因此,本研究以成昆铁路为研究切入点,以普雄镇为田野点,历时性考察了成昆铁路对普雄彝族社会的形塑和影响,旨在提供一种现代道路视域下研究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和新视角。普雄火车站是成昆铁路线上最大的三等站,普雄也因此曾成为凉山州美姑县、布拖县、金阳县、昭觉县、雷波县(以下简称“东五县”,是凉山彝族腹心地区)以及越西上、中、下普雄片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以及人流、物流的集散地。全镇辖区面积45.56平方千米,距越西县城35千米,位于县城东南部,普雄河中段,属二半山区。普雄镇共辖10个行政村、2个社区、33个村民小组,2020年末戶籍人口2.8万余人,其中除瓦吉木社区有1400余人为汉族外③,其他均为彝族。
笔者于2019年11月至2021年12月在普雄镇展开了累计8个月的田野调查,文中凡未明确标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此外,按照学术惯例,本文中的人名均为化名。
一、成昆铁路开通前的传统普雄彝族社会
普雄彝语称“坡合拉达”,“坡合”是因其曾经是坡合土司居住的地方,属于坡合土司的统治势力范围;“拉达”则指“沟”的意思,是因为其居两山(西边为彩洛瓦波火,东边为洛古瓦波火)之间,使其整体上呈“沟”的形状。由于普雄四面环山,普雄河从南到北直贯其中,出入普雄的交通极为不便。彝族先民何时进入普雄地区尚难确知,据说在大约三四百年前,若干黑彝小支率领不同数量的娃子来此垦殖,新开垦的土地由垦殖人所有,因此,普雄地区曾有不少地名均源于当时垦殖者的名字(如表1)。历史上,普雄彝族是坡合土司管辖的属民,而后随着各黑彝家支势力陆续深入普雄,坡合土司在当地的势力逐渐减弱,其立足之地亦日益不稳,最终被赶出普雄,退至越西县城附近。此后,普雄地区逐渐成为阿侯、果基和勿雷等黑彝家支势力的角逐地带。
新中国成立前,普雄境内除南北贯通的干线驿道“零关道”外,其余多为行人踏辟的羊肠小道,因此交通整体而言相对闭塞。此外,普雄地区曾经是黑彝家支冤家械斗的主战场,各黑彝家支割据普雄,无论是内部彝族老百姓还是外部彝族、商人、官员等行人,凡经某黑彝家支领地,均须请“保头”担保其往返财产、生命安全,这极大限制了普雄内外交通的通畅。如,普雄河东岸为阿侯家的集中居住地,普雄河西岸则为果基家的势力范围,而阿侯家和果基家因掳掠奴隶,争夺土地、财物以及婚姻纠纷等经常发生冤家械斗,从而使得东西两岸彝族百姓通过普雄河到对岸都是极为困难之事。据一位家住普雄河东岸的阳坡村老年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其父亲曾经常往来于普雄和西昌附近汉族地区(如礼州等地),从事商品交换工作,主要用彝族地区的皮毛、药材、牛羊、鸦片等,交换汉族地区的布匹、食盐、白酒、烟草或红糖等,然而每次往返经过普雄河西岸果基家势力范围时,他都需要多次缴纳“保头费”,因而商品交换所得利润支付完保头费后几乎所剩无几。为了避免交“保头费”,不少普雄河东岸的彝族购买食盐、布匹等日常生活用品时,通常绕道申果庄至200公里外的雷波县,然而即便是年轻人步行往返普雄和雷波也需要三五天。可见,新中国成立前,普雄内部各黑彝家支间的矛盾极大影响了当地彝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增强民族团结,开发民族地区经济,促进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政府在整修古驿道的同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以泥石混合路面为主的新驿道。至1958年,修通驿道630公里,形成可南北纵贯、东西连接、沟通邻县、辐射大部分村寨的驿道网络。[14]该时期的驿道基本都是一米左右宽的石板路,大路两旁有一条条转去转来的马道,全部是泥巴路,平路则无马道,骡马往来要走石板路,再走马道。整体而言,交通十分不便,条件极为艰苦。
综上,成昆铁路开通运行前,普雄镇各村落为典型的传统彝族村落,地方社会结构建立在紧密的亲属关系基础之上,村落整体呈现地缘共同体和亲缘(血缘)共同体特征,其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同质性。在这个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共同体内的村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共同劳作,休戚与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其经济和社会结构均较为简单,村落内部在职业、政治权力、教育、财富等方面并无明显差异。虽然村民间细微的贫富差异确实划分了他们之间的等级格局,但这绝非社会分层 [7]40。由于日常生活互帮互助的需要,传统彝族村落从空间形态上形成一种“大群居,小聚居”的居住模式。此外,由于彝族社会各家支间形成的团结互助的传统,使得传统彝族社会有较强的平均主义思想,这在物质生活条件较差的年代,固然有利于社会稳定,然而这也限制了内部成员的分化,从而导致发展动力不足。
二、因路而兴:普雄镇的快速发展期
成昆铁路北起成都,南抵昆明,跨越岷江、青衣江,沿大渡河横贯大小凉山,跨过牛日河⑤、安宁河和金沙江,穿越横断山脉,全程建筑长度1083.3公里,营业里程1100公里 [15],其中凉山州境内经甘洛、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六县(市),计车站44个,过境里程375公里 [16]。成昆铁路于1970年7月1日正式开通运行,它的开通运行不仅为普雄镇村民带来了新的生计模式,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职业机会,同时大量从事与铁路相关工作的外地人流入该镇,为其输入了异质性。火车站所在地什木地村也从过去单一、同质的社区逐渐转变为中心村庄(什木地村本身)和外来者的社区(由旅馆、餐馆、卡拉OK厅、超市、铁路行车公寓、货运站、工务段、铁路派出所等构成)。
(一)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东五县”人流和物流集散地
成昆铁路开通前,普雄地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为骡马,其他交通运输方式主要为背夹子、和滑杆等,即俗称的“人背马驮”。而成昆铁路的开通运行改变了普雄过去较为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并促进了普雄通往其他彝族地区的公路建设。纵贯普雄境内的成昆铁路以及普雄通往其他彝族地区的公路共同组成了普雄的现代道路网络,这些现代道路网络不仅成为普雄兴盛发展的重要动因,也促进了后来火车站“外来者社区”的形成和发展。这表明“道路与聚落的发展密切相关,聚落创造了道路,同时道路也成就了聚落”[17]。
在成昆铁路开通初期,由于其他彝族地区的公路交通网络欠发达,火车成为很多彝族村民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尤其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地区“打工潮”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凉山彝族地区大量中青年外出务工,越西县和东五县的彝族大多都在普雄站进行中转。据普雄火车客运站杨站长介绍,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每年彝族新年和火把节期间,仅K166(昆明—成都南)次列车每天在普雄站上下车的乘客就高达1000余人,而每个月普雄站的客运量则高达17-20万。最高峰时期,经停普雄站的客运列车有16列,其中彝族年、火把节、春节或寒暑假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成都铁路局会增开经停普雄的两三趟临时客运列车。
此外,普雄火车站设立了货运站、粮转站、散装站等物流中转站,其中货场占地面积15464m2,设计能力为45万吨/年。自20世纪70年代开通以来,普雄货运站一直扮演着凉山州东五县物流集散地的重要角色(普雄货运站货运相关数据见表2),而与货运站紧密相关的装卸队也一直为普雄镇当地村民,尤其是火车站所在地什木地村村民,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综上,自成昆铁路开通运行以来,普雄境内已形成驿道、公路和铁路分流,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使其成为凉山州东五县以及越西上、中、下普雄片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人流、物流的集散地。
(二)装卸队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分层到社会再分层的载体
上文已述,普雄火车站是凉山州东五县和以及越西上、中、下普雄片区的物流集散地。最主要的输入货物有化肥、磷肥、水泥、白糖、大米等,而输出货物主要有木材、矿石,以及土豆、荞麦等农产品。如表2所示,每年普雄镇的货运量约为30-35万吨,需要约3500-4000人次的装卸工进行装卸。什木地村大多数青壮年(尤其是男性)⑦都曾有过当装卸工的经历,且他们均表示装卸工这份工作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主要经济来源。
20世纪70年代,铁路大集体负责组织装卸工作,“集体”这一概念以一种严密的组织方式进入什木地村,由国家政权支撑的“集体身份”和“人民主体性”给了什木地村村民一个可以替代传统家支⑧模式的新共同体身份,而这一时期什木地村的空间文化对其村民有着规训与动员的特点[18]。这一时期国家政权主导的大集体统一组织车站附近彝族村民从事装卸货物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铁路工作人员与彝族老百姓有了相互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在交流交往过程中,不少彝族学会了汉语,与汉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由于这一时期彝族村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只有空闲时间才能从事装卸工作,这使得装卸工来源极为不稳定,装卸效率较低。因此,自80年代开始,铁路大集体便将装卸工作承包给什木地公社,而该村村民对公社的依赖程度较高,从而使得该村文化呈现出了高度的集体化特征。
在公社负责装卸工作期间,村主任LAN牵头组织村民以村农业社的形式从事装卸工作。每家每户轮流上班,除去做工期间所花费用,剩余部分最终由村民一起平分,LAN从未抽取任何中间费用,这也体现了当时村民的平等主义价值观。LAN制定“每户轮流上班”的规范,这是对群众负责的表现,虽然她从中并未追求物质利益,但却无形中提高了其在村民中的社会地位和威望。这一时期装卸工作不仅给什木地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很多村民在与铁路相关工作人员交流交往过程中,吸收了先进的思想观念。这一时期不少村民将自家种植的蔬菜、土豆等農产品以及猪、鸡等家畜家禽售卖给铁路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了经商意识。同时,从事装卸工作的村民每天都可以从铁路上购买诸如食盐、酱油、针线等其他彝族地区非常稀罕的生活用品,这让邻村的彝族老百姓羡慕不已。
装卸队农业社公有时期,全村村民共同参与劳作、共享劳动成果,充分体现了在当时简单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背景下,村民始终保持一种平均主义的价值观。这一时期,村民的基本关系仍然建立在亲属关系或婚姻关系之上,由于亲属和婚姻关系所带来的责任与义务,LAN在组织村民从事装卸工作时,不得不采取平均主义原则,这又进一步巩固和维持了该村非分层的社会结构。
随着每天装卸的货物量不断增大,且LAN年事已高,很难再从事高强度的装卸组织工作,因此自1991年开始由其小儿子MSDT协助装卸队管理工作。他充分利用母亲在村民中已建立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于1998年将装卸队成功私营化。这也许是政治与权力在什木地村最明显的展演,同时也标志着其打破了该村传统的平均主义原则,也是其社会发生分层的开始。这一期间什木地村村民的生计模式仍然较为单一,除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外,装卸工作是该村的第二大生计模式,装卸工成为村民们人人向往的“紧俏”职业。
MSDT在经营装卸队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财富,在本世纪初修建了小洋房,这也是该村第一座楼房,后来他将自家多余的房间外租给外来人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与其他村民的贫富差距,这使其在村里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在其母亲“退休”后,他顺理成章成为新一任村支部书记。社会声望分层和经济分层是社会整体分层的两个重要维度,而社会声望分层是由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所决定,因而具有稳定性特征[19]。最初,MSDT受伴随铁路输入的异质性的影响和启发,充分利用其母亲的政治与权力为自己谋利益,成功将装卸队私营化。而装卸队私营化的直接后果是其积累的财富不断增加,这进一步巩固了其社会声望,如是,经济分层和社会声望分层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互构”关系,而MSDT也成为了经济分层到社会再分层的实践者。同时,装卸队给MSDT带来了资源分配的不平均和流动的可能性,这成为了乡村生活异质性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和仪式差异的基础[20]。
(三)“外来者社区”的发展:普雄地方社会文化格局的型构
伴随成昆铁路的开通运行,大量外来人员流入什木地村火车站附近,其中有铁路职工家属,外地来做生意的汉族,以及来自拉白、贡莫、上普雄、中普雄以及下普雄等地的彝族等,他们共同构成了有别于什木地村中心的“外来者社区”,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五湖四海”。旅馆、餐馆、卡拉OK厅、超市、理发店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成昆铁路的建设和开通运行极大地带动了普雄镇的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⑨,“外来者社区”的街道整晚灯火辉煌,街道两边的餐馆、旅馆和卡拉OK厅等一直营业到午夜,其热闹和繁华程度甚至远超瓦吉木社区(普雄镇政府所在地),普雄镇在当时彝区也因此享有“小香港”之美誉。成昆铁路对普雄镇彝族社会的发展尤为重要,因为“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着社会组织的规模和社会结构的形式。交通的发展水平又规定着社会生产的发达程度。原材料的运输、劳动力的组织以及产品的流通,都不能离开交通的作用。而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改良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又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演进。相反,在交通落后,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每一种发明往往必须重新开始”[21]。
随着成昆铁路的开通运行,铁路行车公寓、工务段、电务段、水务段、军供站等单位也相继在普雄建立。此外,不少外地彝族和汉族陆续到火车站经营生意,他们最初租用彝族的简易土房,后来因生意好,直接购买土房所在土地,修建砖结构楼房。就地势而言,火车站所在地整体为一个斜坡,且当时修建房屋时并未进行统一规划,因此“外来者社区”的房屋布局不尽合理:房屋大多修建在斜坡上,且每两栋房屋间的楼间距非常小、过道非常狭窄。走进“外来者社区”就如同走入迷宫(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地道”)。
综上,成昆铁路的开通运行给普雄镇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成昆铁路不仅促进了当地彝族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也促使外来人口(尤其是彝族)通过火车站这一空间不断流动,从而使得什木地村从过去单一、传统的彝族村落逐渐转变为中心村和复杂的外来者社区。外来者社区这一空间虽然狭小,但可谓“五脏俱全”,理发店、茶楼、卡拉OK厅等日常休闲和娱乐场所应有尽有,这些因素共同使得外来者社区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并一时成为周围彝族地区的交通、经济和文化中心。
三、因路而变:普雄镇的转型期
随着成昆铁路全路段实现电气化改造,大量铁路相关单位逐渐撤离普雄镇,外来资本大量减少,普雄镇“小香港”时代已结束,地方城镇化发展亦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因此,当普雄镇地方政府和村民在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不能再依赖于曾经作为东五县人流和物流集散地的交通优势,而需另谋地方社会转型发展新路径。虽然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即“成昆铁路复线”)⑩后并未规划在普雄镇设立站点,但成昆铁路复线的开通也将为普雄镇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加之当前普雄镇通往申果庄、美姑、昭觉、西昌、喜德等地的公路已逐渐完善,该镇将发展目光转向文化发展和复兴,大力发展以文化为核心的第三产业,逐步打造出“成昆铁路上最美梯田”和“成昆铁路上彝绣第一村”等独具特色的普雄文旅项目,并积极申报各类非遗项目,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从而使得成昆铁路在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而普雄镇也在新时代享有“成昆铁路上的明星小镇”之美誉。
(一)成昆铁路线上最美梯田:“车史则”民俗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车史则”为彝语音译,“车”意为“稻谷”,“史”意为“新”,“则”意为“吃”,“车史则”意为“尝新米”,当地普遍将其译为“尝新节”。据当地人介绍,普雄镇彝族村落庆祝“车史则”传统民俗活动由来已久,但具体年份已无从考证。自脱贫攻坚以来,为充分利用地方生态文旅资源,以全力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为地方彝族村民构建新的经济增长点,该镇先后连续组织举办了六届大型“尝新节”民俗活动。据了解,越西县也有其他彝族地方庆祝“尝新节”,但得益于成昆铁路带来的交通优势,越西县全力打造普雄镇“尝新节”。通过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打造,以及地方彝族群众的积极参与,2017年普雄镇“彝族尝新节”被列入凉山州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普雄镇且拖村被确定为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彝族尝新米节”体验基地,普雄镇梯田被称为“成昆线上的最美五彩梯田”,而“尝新节”也成了普雄镇一张响亮的地方文旅新“名片”。
“车史则”由彝族村落自组织的传统民俗活动,逐渐演变为由政府主导、彝族村民和外来人员共同参与的大型乡村文化展演活动,其活动主题与时俱进,活动内容丰富多彩。这是地方政府将旅游作为地方转型发展实现途径的体现,而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旅游业时,充分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内涵,这为旅游提供了生命力,并创造了传统文化表现的载体。当地政府在组织“尝新节”活动的过程中,保留了传统的抽稻穗活动,正如其主题“体验乡愁、激发内生动力”,通过保留传统乡村文化的方式,既留住了乡愁记忆,也让游客更好地体验和感知了地方文化内涵。同时,地方政府在传统“车史则”基础上加入彝族服饰、彝族刺绣、彝族漆器、彝族银饰等非遗产品展示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活化了彝族传统文化,达到了乡村文化再生产的效果,从而实现了“以旅游为载体彰显文化灵魂、激活文化记忆、传承文化精神、增强文化魅力和繁荣文旅产业”[22]之目的。此外,政府还依托“尝新节”这一活动空间,进行一系列表彰活动,如禁毒防艾先进个人、禁毒防艾优秀家支、优秀党员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移风易俗之目的。
总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建设不仅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建设,更需要激发村民的共同历史记忆、情感归属以及身份认同,而这些都可以通过乡村文化复兴和再生产得以实现。然而,文化复兴并非简单地复活,而是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文化空间获得新的生命活力,是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态更新的过程。[23]而“尝新节”则为彝族服饰、漆器以及银饰等非遗产品的展演提供了新的载体,从而使得彝族传统文化空间、历史记忆以及身份认同的建构得以实现。
(二)成昆铁路线上彝绣第一村:普雄镇彝族刺绣助力乡村振兴
凉山彝族刺绣(以下简称“彝绣”)是彝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手工艺,被誉为彝族人的“指尖瑰宝”或“指尖艺术”。因其具有色彩浓烈、纹样丰富、绣工精巧、技艺高超、蕴含文化等特点,2021年凉山彝族刺绣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普雄镇呷古村彝绣更是因其做工精湛、配色新颖以及构图精巧等特征,成为凉山彝族刺绣中的佼佼者,并在2020年被列为凉山州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19年,为打造“一村一品”B11项目,普雄镇政府和地方村民积极主动思考地方发展,充分挖掘地方非遗项目,以搭上“非遺+扶贫”的末班车。呷古村在打造“一村一品”项目时,考虑到该村农业耕地面积少,不适合发展养殖业,且该村属于非贫困村,不能获得足够的政府扶贫资金以推动产业发展,因此他们将目光锁定在投资小但容易发展的产业。该村绣娘较多,且她们的绣工在彝族地区“远近闻名”,发展彝绣产业对他们而言可谓轻车熟路,于是普雄镇政府和呷古村领导最终选择彝绣作为该村的“一村一品”项目。同时,镇政府和村领导认为宣传标语对于项目是否能成功至关重要,他们在拟定宣传标语时主要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第一,不能简单使用“呷古村彝绣”等字样,因为同一时期昭觉县也在积极申请彝绣项目,该县素有“彝族服饰之乡”之美誉,呷古村的村名跟其相比没有任何竞争优势;第二,该时期普雄镇打造的“尝新节”民俗活动已经在凉山州打响“成昆铁路线上最美梯田”的品牌,因此呷古村彝绣也可借“成昆铁路”这张名牌,与尝新节相互呼应,从而为普雄镇打造“成昆铁路”系列品牌,于是“成昆铁路线上彝绣第一村”便应运而生。
“成昆铁路线上最美梯田”和“成昆铁路线上彝绣第一村”这些宣传口号,揭示了成昆铁路对普雄彝族老百姓的深刻影响,虽然尝新节和呷古彝绣与成昆铁路并无实质性关联,且同样的产业在成昆铁路线上的其他彝族地区更具规模、发展得更好B12,但普雄彝族仍然借助“成昆铁路”这张名片为其地方发展谋福利,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核心要素,因为“乡村振兴是以文化自信为核心的整体性实践,若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遵从文化自信生成之规律”[24]。
四、结论与余论
成昆铁路是西南地区的陆地交通大动脉,更是沿线大凉山深处彝族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交通基础设施。成昆铁路的开通运行不仅加快了普雄镇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普雄彝族社会的变革。1970年开通以来,成昆铁路无疑促进了普雄镇物资和人员的流动,使其成为凉山州“东五县”的人流和物流集散地,并逐渐成为周边彝族地区的交通、经济和文化“中心”,从而推动了普雄镇的整体发展。然而,成昆铁路对普雄镇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着成昆铁路输入的异质性和外部力量,普雄镇彝族老百姓的生计方式、个体命运、社会观念、族群关系乃至普雄镇火车站的空间形态等不断发生变化。
随着周边彝族地区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且成昆铁路复线不在普雄设立站点,普雄镇交通枢纽中心地位式微,因此新时期普雄镇亟须转型发展。在普雄镇转型发展过程中,成昆铁路并未扮演实质性、根本性作用,然而成昆铁路运行五十余年来所积淀的历史得以让其继续享受成昆铁路带来的“红利”。这一时期,普雄镇将发展目标转向文化复兴和旅游发展,并借助“成昆铁路”这张曾经深刻影响普雄地方社会发展的响亮名片,积极打造诸如“成昆铁路线上最美梯田”“成昆铁路线上的彝绣第一村”等具有普雄特色的文旅项目和地方产业,大有借“路”转型之势。在新时代,对于普雄而言,成昆铁路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文化遗产”,地方政府和彝族村民积极主动思考,充分利用这一“文化遗产”,为地方发展谋出路,从而逐渐改善过去与成昆铁路之间某种笨拙、沉重的关系,[25]进而使其地方发展更加多元、更具活力,更加持久稳定。
普雄镇的个案研究表明,对于深处西南边远地区的凉山彝族而言,道路是其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载体。尤其在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凉山的交通基础设施正不断完善,在建以及规划建设的道路将不仅为凉山打开“互联互通、对外开放”的新局面,而且为凉山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保障,同时也将带来文化异质性的输入。在这一过程中彝族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交流、交融,彝族传统文化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那么彝族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彝族文化在保留自身特点的同时如何开拓与其他文化的相处之道?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彝族面临的文化自觉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自身主体性的问题。无论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适应,其主体和动力都是彝族本身,自觉必然带动自主,这就加强了自身文化转型的主动性,进而在规划自身发展与实践上获得更多自主性。一旦具备了文化自觉,便能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从而也就增加了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内生性资源与动力。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提出“四好农村路”,并指出“要求农村公路建设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与优化村镇布局、农村经济发展和广大农民安全便捷出行相适应,要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的保障。”
②代表性论文有:郭建斌:《路与时空政治:一百年来云南独龙江地区的路与社会变迁》,周永明主编:《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16:114-129页;杨梅:《道路建设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民国时期乐西公路的个案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年第6期。
③这些汉族主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在普雄镇经商的外地人。
④本表根据当地老人口述和《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第53页整理所得,其中的名字大多为音译,有的地名和垦殖者名字完全吻合,有的则有紧密的关联。
⑤牛日河为长江支流岷江支流大渡河的支流,于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尼日汇入大渡河,又称“尼日河”,是大渡河的一级支流。
⑥本表根據货运站莫站长提供的数据整理而得。对于本表作如下说明:第一,因火车站货运系统只能保留近15年相关数据,故未能列出2005年以前的数据,但据货运站莫站长介绍,2005年前货运站的年装卸货量也约为31-35万吨。第二,本表中2019年的装车数为零,其原因是当年因普雄货运站进行货场改造,未开展装车业务。
⑦什木地村共有468户,1803人,其中19-55岁的男性有403人,装卸工大多为19-55岁的男性,从这些数据便可知,该村大多数男性均从事过装卸工工作。
⑧“家支”在彝语中称为“此威”或“措西”。血缘是“家支”形成的基础和纽带,是“家支”的核心要素,由血缘构成的“家支”是彝族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和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相关内容参见林耀华:《凉山彝家》,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60页。
⑨2000年9月30日,成昆铁路全路段完成电气化改造,这使得火车运行速度极大提高。笔者调研发现,大多数当地人都将成昆铁路的电气化视为普雄镇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⑩成昆铁路复线未在普雄设立站点,其开通后将会对普雄的客流量产生较大影响,届时只有慢火车会经停普雄。但货运列车大部分还会经停普雄,因此货运量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B11“一村一品”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村为基本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使一个村(或几个村)拥有一个(或几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
B12实际上凉山州境内、处于成昆铁路线上的甘洛县普昌镇因其盛产水稻,拥有3万亩稻田而被誉为“鱼米之乡”,普雄镇的水稻与其相比实属相形见绌;而云南省楚雄州地处成昆铁路线上的禄丰县高峰村和中村的“纳苏彝绣”因其精湛的绣工与普拉达和爱马仕等奢饰品牌合作,共同开发民族高端品牌,与其相比呷古村的彝绣产业仍处在起步阶段。
参考文献:
[1]Giddens Anthony.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M].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4-64.
[2]Harvey David.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Cambridge[M].MA:Blackwell,1990:260-284.
[3]Ben Campbell.Rhetorical Routes for Development:A Road Project in Nepal[J].Contemporary South Asia,2010,Vol(18),No.(3).
[4]新华社.习近平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EB/OL].(2017-12-75)[2017-12-25].http://www.gov.cn /xinwen /2017-12/25/content_5250225.htm.
[5]朱凌飞,马巍.边界与通道:昆曼国际公路中老边境磨憨、磨丁的人类学研究[J].民族研究,2016(04):40-52+123.
[6]Eugenio Y Arima,Robert T Walker,Stephen G.Perz et al.Loggers and Forest Fragmentation:Behavioral Models of Road Building in the Amazon Basin[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September 2005.
[7][美]康拉·德科塔克.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M].张经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5.
[8]翁乃群.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广西卷、贵州卷、云南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9]文化,朱茜婷.青藏铁路沿线地区居民感知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105-113.
[10]朱凌飞.修路事件与村寨过程——对玉狮场道路的人类学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4(03):69-78.
[11]张锦鹏,高孟然.从生死相依到渐被离弃:云南昆曼公路沿线那柯里村的路人类学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5(04):98-104.
[12]张辉,李志农.道路、发展与认同——滇藏公路与奔子栏藏民国家认同的构建与维系[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12(01):123-131.
[13]李志农,张辉.边疆民族地区道路建设与村落社会变迁——基于滇藏线重镇奔子栏村的考察[J].思想战线,2021(05):10-17.
[14]越西县志编纂委员会.越西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22.
[15]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交通志(下册)[M].成都:四川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39.
[16]凉山州交通志编纂委员会:凉山彝族自治州交通志[M].西昌:凉山州交通志编纂委员会,1992:3.
[17]胡振洲.聚落地理學[M].北京:三民书局,1977:171-177.
[18]刘世奎,陈永平.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宗族势力兴衰的历史考察[J].江汉论坛,1994(07):44-48.
[19]Wber.Max.Class,Status and Power: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M].(eds.) by Beinhard Bendix & Seymour Lipset.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6:21.
[20][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
[21]王子今.交通与古代社会[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1.
[22]黄震方,黄睿.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J].地理研究,2018,37(02):233-249.
[23]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文化复兴[J].人文杂志,2010(05):96-104.
[24]方坤,秦红增.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文化自信:内在理路与行动策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2):41-48.
[25]袁长庚.方位·记忆·道德:道路与华北某村落的社会变迁[A].周永明.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C].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145-162.
收稿日期:2022-12-23 责任编辑:秦 艳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民族学刊的其它文章
-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 On the Building and Practice of a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Urban Ethnic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A Case Study of “Ethnic Homes” in Guangzhou
- The Early Practice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Visual Ethnodanceology
- Core Issues in the Philological Study of Ethnic Literary Integration History in Ancient Southwest China
-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Trend of Red Revolutionary Tourism Symbiosis Atlas in Sichuan Province
- A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Homestay Industry in Qiang Area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Based on a Survey in Wenchuan County, Aba Prefe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