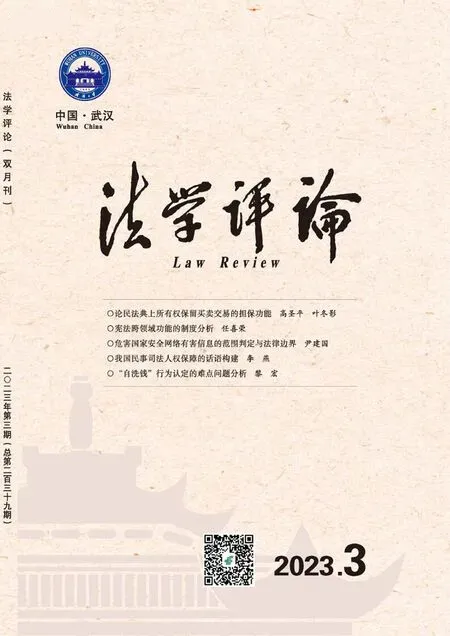论劳动法上的工资*
2023-07-31战东升
战东升
一、问题的提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工资不仅是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是影响劳动关系甚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我国《劳动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工资支付形式、支付保障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劳动基准法”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该法旨在对工资、工时等劳动基准进行规范化、体系化立法。(1)参见林嘉:《加快劳动领域重点立法 不断完善我国劳动法律制度》,载《工人日报》2023年2月6日第7版;肖竹:《推动基本劳动标准立法 强化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载《工人日报》2023年2月20日第7版。由此可以看出,对作为劳动基准的工资问题进行研究正当其时。那么,何谓工资?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不言而喻,却由于立法和理论研究均未提供精确指引,而成为滋生劳动领域实践乱象的本源性问题。从劳动基准法(2)理论上,工资有劳动基准法上的工资、劳动合同法上的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法上的工资之分,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学界莫衷一是。参见陈建文:《劳基法工资定义的争议与思议》,载台北大学法律学院劳动法研究中心主编:《劳动法文献研究——理解、分析与重构》,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59-84页。本文主要从劳动基准法视角探讨工资认定问题。的视角来看,工资的界定不仅涉及劳动关系认定等劳动法基础理论问题,也牵涉劳动者和雇主各自的切身利益,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尽管我国《劳动法》对“工资”进行了专章规定,但并未明确规定工资的定义。原劳动部的部门规章虽对工资的定义有所涉及,但由于缺乏对工资本质的认识和一套具有实质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当雇主与劳动者在某项给付是否属于工资的问题上产生纠纷时,当事人往往不是从工资的定义出发,而是从现行立法所列举的工资形式来论证某项给付是否属于工资。从现有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当前立法中对工资概念的规定逐渐被“工资构成”与“工资总额”的司法适用边缘化。然而,借助工资总额构成对个案中的雇主给付性质进行判断,具有明显的简单化处理倾向,也必然会为雇主提供脱法的空间。(3)参见李海明:《从工资构成到工资定义:观念转换与定义重构》,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鉴于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从工资的国际立法、司法以及理论出发,明确工资认定的一般标准;其次,需要对我国工资立法进行改革,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工资立法体系;最后,还应从司法适用层面明确工资概念适用的基本路径,正确认识和澄清几种常见类型给付之性质,从而有效减少实践中有关工资认定争议的发生。
二、理论构建:工资认定的一般标准
(一)他山之石:域外的工资立法与司法
法国《劳动法典》第L3221-3条规定:“本章中的报酬,是指雇主基于劳动者的劳动,直接或间接地,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基本工资或收入,以及所有其他福利和额外收入。”(4)田思路主编:《外国劳动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4页。长期以来,法国最高法院将工资概念与劳动者的工作联系在一起,认为工资必须是劳动者付出直接工作的对价。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法国最高法院将工龄奖、出勤奖、集体效益奖金排除在工资范围之外。其理由在于,工龄奖仅是对劳动者忠诚的鼓励,而出勤奖是对劳动者按时上班的鼓励,集体效益奖金则与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无关,因而均不应当认定为工资。(5)同前注④,田思路主编书,第48页。
英国《雇佣权利法案(1996年)》第27条规定,工资是指支付给工人所有与其雇佣有关的报酬,无论是合同约定支付还是其他。(6)See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1996 c. 18), Pt. II s. 27.,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6/18/contents,last visited on May.1,2022。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第3条规定,工资是指由劳动部长规定的,支付给雇员的合理费用。(7)Se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1938, 29 U.S. Code §203 (m)(1)。日本《劳动基准法》第11条规定,工资系不论名为工资、薪水等名称,作为劳动之对价,所有由雇主向劳动者给付之物。(8)参见[日]井上正仁編:《判例六法》,有斐閣2014年版,第1194页。从该条规定来看,工资应当具备“劳动对价性”和“雇主向劳动者为给付”两个要件,只要符合这两个要件,无论其名称为何,均可以认定为工资,这也是现今日本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通说。(9)参见[日]菅野和夫:《労働法》,弘文堂2013年版,第276-278页。
我国澳门地区《劳动关系法》第2条规定,基本报酬(工资)是指雇员因提供工作而应获得的所有定期金钱给付,而不论其名称或计算方式。(10)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印务局:《劳动关系法》,https://bo.io.gov.mo/bo/i/2008/33/lei07_cn.asp,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5月1日。我国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第2条第3款规定,工资谓劳工因工作而获得之报酬;包括工资、薪金等其他任何名义之经常性给予均属之。(11)同前注②,陈建文文。针对该条规定,台湾地区劳动行政部门出台了大量的行政解释;而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也积累了丰富的判决,其中79年度台上字第242号判决(12)参见吴启宾:《论劳动基准法上之工资》,载《法令月刊》1990年第8期。的说理论述,被台湾地区各级法院广为援用。(13)同前注②,陈建文文。
综上所述,除美国等国家外,大多数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工资定义(14)国际劳工组织(ILO)制定的《保护工资公约》(第95号)第1条也对工资的定义作出了规定。均包含两个重要要素:一是须为劳动者劳动的对价,二是雇主向劳动者为给付。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将经常性、连续性、规律性或定期性等作为工资认定的要素。一般而言,形式与实质相统一是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哲学方法。在法学研究领域,也有学者从形式与实质的层面对法学概念展开研究。(15)参见陈兴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刑法学的反思性检讨》,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结合比较法上的立法与司法经验以及理论上的既有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将工资认定的标准,区分为实质标准与形式标准。
(二)工资认定的实质标准:劳动对价性
1.学说概览
基于对工资内涵的理解不同以及学者研究视角的差异,对于劳动法上的工资认定,学界至少发展出以下三种不同的学说。(16)除此之外,还有“补充认定说”、“综合判断说”等学说。参见林良荣:《退休金给付差额争议与劳基法上工资之认定》,载《月旦裁判时报》2018年第6期;郭玲惠:《劳动契约法论》,台湾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129-131页。
其一,劳动对价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程贯认为工资之认定,应以雇主之给付是否构成劳工劳务之对价,亦即应视是否为劳工因工作而获得之报酬而定。(17)参见黄程贯:《劳动法》,空中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林良荣也认为,只要是劳工因提供劳务而由雇主所支付之对价,即均应认定为工资。退一步而言,即便某项报酬同时兼具一定程度之恩惠给付性质,也并不能完全否认该给付的对价性。(18)同前注,林良荣文。我国大陆地区也有学者认为,工资与劳动之间存在对价关系,(19)参见喻术红、程凌:《违法解雇期间劳动者所得之性质与范围》,载《河北法学》2019年第12期。工资认定的核心问题是雇主对劳动者提供劳动所应给付的对价。(20)参见王天玉:《工资的对价学说及其法律解释力》,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其二,关系正义说。该学说主要由我国大陆地区学者曹燕所主张,其从关系正义理论出发对劳动对价理论展开批判,认为工资与劳动之间不可能存在对价关系。关系正义说主张工资的本质不是劳动价值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如何符合正义原则的问题。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工资任由劳资自治,可能使财富分配背离正义,因此需要通过正义原则来引导强制、习俗、互惠三种力量使劳动关系趋向合作,进而实现对包括工资概念在内的整个工资法律制度的构建。(21)参见曹燕:《劳动法中工资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家》2011年第4期。
其三,经常性给付说。该学说主要由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所提倡,这是因为我国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在其工资定义中加入了“经常性”之要件。给付经常性主要考量雇主的给付频率,或者是否已经实现制度化。(22)参见林炫秋:《最高法院判决中的工资认定要件与类型》,载《万国法律》2009年第167期。该说依据法条定义,采限缩解释,将工资的经常性与劳动对价性等同视之;假设不具备经常性要件,即使具备劳动对价性的要件,也有可能被排除在工资之外。(23)同前注,郭玲惠书,第129-130页。受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和学说的影响,我国大陆地区亦有学者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24)同前注,王天玉文。
2.学说评析
关系正义说在反思劳动对价说的基础上,为工资概念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但是这两种理论并不完全冲突,相反关系正义理论为劳动对价理论的完善与深化提供了良好的视角。然而,相较于劳动对价理论,在关系正义原则下构建一套能够有效应对理论与实践困境的工资定义体系,却并非一件易事。经常性给付说发端于我国台湾地区,主要受我国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立法的影响。然而,早在立法过程中,对于应否保留“经常性给予”这一要件,就颇有争议。(25)同前注②,陈建文文。之后,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在早期阶段,虽然强调以“经常性”作为工资认定的主要标准,但是后来法院意识到“经常性给予”之要件对于劳动者保护显为不利,转而采用所谓“制度上经常性”之扩大解释立场,近年来甚至转向于直接以“劳动对价性”作为工资内涵之判断基准。(26)同前注,林良荣文。此外,我国台湾地区亦有学者认为,“经常性给予之认定要件之是否符合,并非为解释某一项给予是否为具工资属性之绝对认定标准,而亦应系以其给予是否为劳动之对价”。(27)谢棋楠:《台美劳基法律中奖金名义给与之法律性质分析》,载《海峡法学》2017年第4期。由此来看,“经常性给付说”在其发源地已逐渐转向“劳动对价说”,因而我们似乎也没有再继续坚持下去的必要。(28)值得注意的是,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日本劳动基准法》中除工资的概念之外,还存在“平均工资”的概念。与工资概念本身并不强调经常性相比,平均工资则强调经常性和连续性。该法第12条明确规定,在计算平均工资时,应将“临时支付的工资”、“支付间隔超过三个月的工资”(例如每半年支付一次的夏季或冬季奖金等)从工资总额中扣除。平均工资的这一立法目的在于尽可能让其真实地反映劳动者当时的收入水平,不使劳动者的收入出现大的波动。在此意义上,对于工资概念本身的判断,亦不应将经常性作为工资本身的判断要素。参见[日]西谷敏、野田進、和田肇編:《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ール労働基準法·労働契約法》,日本評論社2012年版,第43页。此外,为了解决我国实践中关于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基数计算混乱的问题(如某项补贴或津贴是否应当计入等),我国似乎也有必要确立类似日本法上的“平均工资”概念。
与此相反,一般认为工资是劳动者所提供劳动的对价,劳动对价说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均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有学者将劳动对价学说的演进路径归纳为“劳动力对价说”“劳动支配对价说”“劳动关系对价说”,并认为“劳动关系对价说”能够充分适应劳动关系多样化、弹性化的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29)同前注,王天玉文。然而,一方面,学界尚未厘清“劳动对价说”与“经常性给付说”的关系。具体而言,工资的判断标准究竟是“劳动对价性”还是“经常性”?例如有观点虽然主张劳动关系对价说,但同时也认为工资支付应具有经常性。倘若如此,如果劳资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雇主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向劳动者为某一特殊给付,虽然合同双方当事人已作出明确约定,但该约定的给付只是一时的,此时能否被认定为工资仍然存在疑问。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劳动对价”只不过是解释论上的一种努力,仅是一种说明的论理而已,并不能从“劳动对价”就直接推导出有关工资的具有很强实用性的判断标准。(30)同前注,[日]西谷敏、野田進、和田肇书,第39页。而有学者则认为,劳动对价这一概念的价值主要有二:一是否定由劳动关系之外的法律关系所产生的雇主给付(无“劳动”给付);二是排除雇主无支付义务意义上的任意恩惠性给付(无“对价”给付)。(31)参见[日]金子征史、西谷敏編:《新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ール労働基準法》(第4版),日本評論社1999年版,第38页。由此来看,对于劳动对价说在学界也未达成共识。
3.劳动关系对价“二阶段”说之提倡
如前所述,对于工资认定的理论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劳动对价说”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劳动力对价说、劳动支配对价说和劳动关系对价说三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对“对价”内涵认识上的不一致,(32)同前注,王天玉文。由于前两者在解释上陷入了困境,于是理论上又发展出了“劳动关系对价说”,而关系正义说在反思劳动对价说的基础上,为工资概念的重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因此,我们可以在借鉴其他学说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劳动关系对价说”的认识,同时还可以通过列举方式增强对“对价”内涵的理解。基于此,笔者认为在依据“劳动关系对价说”认定工资时,可以从以下两个阶段加以判断。(33)同前注,[日]西谷敏、野田進、和田肇书,第35-39页;林更盛:《劳动法案例研究选辑(一)》,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3页以下。
第一阶段,判断给付是否具有狭义的劳动对价性。在判断某项给付是否属于工资时,其中最为本质的要素是劳动对价,而非其他要素(如经常性)。所谓“劳动对价”,不仅是劳动者具体劳动给付之对价,同时也是劳动者基于其劳动关系地位所应获得之对价。其中,“对价”是指劳动的一种交换(exchange)或者补偿(compensation)。(34)同前注,[日]西谷敏、野田進、和田肇书,第37-40页。从历史维度看,对于“劳动对价”内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狭窄到宽泛的嬗变过程,这与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在民法的雇佣合同时代,雇主与雇员之间是单纯的债权与债务关系,劳动者不付出劳动将不会得到任何报酬。但是劳动法产生之后,为了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健康权,即便在某些特定期间(例如医疗期)劳动者并未付出劳动,基于其劳动关系地位,也能获得一定的工资。上世纪90年代末,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体面劳动”的概念,标志着劳动法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35)参见陈超:《论实现体面劳动的法律政策支持体系》,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不再止步于生存权和健康权,而愈发重视劳动者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逐步转向以提升生活品质为目的之工作权、人格形成发展权等方面。(36)参见张鑫隆:《特别休假之法律效果》,载《台湾法学杂志》2017年第318期。在工资基准立法领域,劳动者即使在带薪年休假等期间,基于其劳动关系地位,作为劳动的一种“补偿”,仍然可以享有工资的请求权。(37)同前注,[日]西谷敏、野田進、和田肇书,第39-40页。总体来看,劳动法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与直接劳动相对应,到现阶段劳动者基于其劳动关系地位即可获得工资的发展过程;而对于“对价”的理解,则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对等交换到现阶段仅需要达到“补偿”程度即可的发展过程。
第二阶段,即便某项给付不具有狭义的劳动对价性,从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场(38)参见许建宇:《“有利原则”的提出及其在劳动合同法中的适用》,载《法学》2006年第5期。出发,若劳资双方依据劳动合同、规章制度、集体合同以及劳动惯例等能够明确支付条件,由此雇主受约定给付之约束,则该给付具有规范上的依据,据此亦可认定为工资。(39)同前注,[日]西谷敏、野田進、和田肇书,第35-39页;同前注,林更盛书,第33页以下。对此,日本劳动法学者荒木尚志称之为“广义的劳动对价性”。(40)参见[日]荒木尚志:《労働法》(第3版),有斐閣2016年版,第126页。然而,如果将劳动关系中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约定的所有给付都评价为劳动对价,似有扩大了劳动基准法上工资概念范畴之嫌,但这并非不具有合理性。其一,工资作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所产生之请求权,其内容本来就是由当事人的约定而决定,这不仅包括劳动合同,当然也包括规章制度、集体合同等形式。(41)参见沈建峰:《劳动基准法的范畴、规范结构与私法效力》,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其二,劳动基准法对于工资规制的重点不在于对工资金额的确定,而在于确保工资的支付,因此只要支付条件明确就应当将其视为工资,这符合劳动基准法的立法目的。(42)参见[日]毛塚勝利:《賃金·労働時間法の法理》,载日本劳动法学会编:《講座21世紀の労働法》(第5巻),有斐閣2000年版,第6-7页。其三,这既不意味着当事人通过约定就能无视给付的“劳动对价性”,也并不意味着将工资作为“劳动对价”来进行规定是无意义的。一方面,对于与具体劳动关联性较高的给付,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将其作为非工资项目有脱法之嫌,其支付方式完全交由雇主裁量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对于结婚礼金等“劳动对价”关联性较低的给付,即便将其作为劳动基准法上的工资来看待,也并不能完全排除雇主在支付金额、支付对象等方面的自主决定权。(43)同前注,[日]毛塚勝利文,第7页。
(三)工资认定的形式标准:经济给付性
劳动关系的基本内容是雇主雇用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而作为劳动的对价,雇主向劳动者支付一定的劳动报酬。根据劳动关系对价“二阶段”说,工资由雇主支付给劳动者是其应有之义,工资的给付主体和给付对象虽较为明确,但是对于给付形式却存在不少争议。即,雇主向劳动者所为之给付除了法定货币之外,是否还包括实物等非货币给付。首先,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大多数国家例如法国、日本等均规定工资的给付形式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实物等其他利益。其次,立法上规定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可理解为这仅是就给付形式而言,其与某项给付是否属于工资的判断本身并不属于同一层面问题,不可混淆。最后,无论雇主是以货币形式给付还是以实物形式给付,从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来看,工资的本质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由此来看,工资的给付形式似不应仅限定在金钱的现实收受范围,实物给付乃至广义的利益提供等也应当包括在内。(44)参见[日]厚生労働省労働基準局編:《労働基準法》,労務行政研究所2011年版,第162页。但是,如果允许工资以实物等形式进行发放,则有可能被雇主滥用,侵害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而有必要作出相应限制。
三、立法省思:我国工资立法的缺陷及改进
(一)我国工资立法的历史嬗变
我国目前关于工资的规定比较分散,工资的制度框架主要由《劳动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和相关部门规章所确立。1994年出台的《劳动法》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工资总量等原则,明确了工资的立法空间。工资总额控制可追溯到1951年颁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该规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目前已经被废止。为了保证国家对工资进行统一核算,国家统计局于1990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以下简称《工资总额规定》)及其具体范围的解释两个文件。前者不仅规定了工资总额的概念和组成、奖金和津贴的种类、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而且还明确了不属于工资总额的项目。后者则对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奖金的范围、津贴和补贴的范围、工资总额不包括的项目的范围等作出了进一步规定。
我国《劳动法》虽然设专章对工资进行了规定,但是既没有规定工资的定义,也没有规定工资的构成。1994年12月,原劳动部发布《工资支付暂行规定》,首次对工资的概念作出规定,同时明确了工资的支付方式、支付对象等内容。翌年,为了配合《劳动法》的实施,原劳动部颁布《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执行劳动法意见》),对工资的定义、构成以及例外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随后,地方各级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关于工资支付方面的文件,其中关于工资的定义、构成等基本上沿袭了原劳动部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比较原劳动部和统计局的规定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劳动立法关于工资的定义、构成等方面的规定,基本上源于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的规定。(45)同前注③,李海明文;[日]森下之博:《中国における賃金の概念と賃金支払いをめぐる法規制》,载《労働法律旬報》2012年第1771号。此外,在其他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也存在一些关于工资方面的规定,例如《最低工资规定》对“最低工资”的规定等。
(二)我国工资立法的缺陷
其一,工资的立法体例存在问题。(46)参见刘汉伟、刘金祥:《我国劳动基准立法体例探究》,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首先,法律位阶较低。目前国家层面关于工资的有效规定主要限于部门规章,由此造成法律效力低、约束力较弱等问题。其次,规定分散,未形成体系化立法。除劳动行政部门的规定外,其他行政部门例如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工资总额规定》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起到了工资基准的作用。由于缺乏一个科学严谨的工资立法体系,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立法随意性较大,相互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配合。最后,规范文件较为陈旧。我国与工资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大多制定于上世纪90年代,然而二十余年间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法律条文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实务中很难发挥规范作用。
其二,《劳动法》未规定工资的定义。作为我国劳动基本法的《劳动法》未对工资这一基本概念作出规定,可谓《劳动法》立法的重大缺陷。由此带来如下弊端:首先,法院在审理工资类案件时,没有形成统一适用的法律依据和裁判标准,致使法官可能滥用自由裁量权;其次,从原劳动部制定的规章来看,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的规定对我国劳动法上的工资认定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该局的规定更多是为了统计核算的需要,显然与劳动基准法的立法目的存在根本上的差异;最后,我国目前对工资的规制仍遵循对工资的列举式规定,虽然这种封闭式的外延概括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但是这样的工资定义思路不包含价值判断,不仅限制了对现实工资形式的涵括,也难以满足司法实践中对工资认定的本质需求。(47)参见侯玲玲:《劳动法上工资概念之研究》,载《现代交际》2009年第6期。
其三,既有的工资定义存在问题。尽管原劳动部发布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和《贯彻执行劳动法意见》对工资的概念有所规定,但存在定义不周延、相冲突等问题。(48)参见孙国平:《论工资争议中的小费问题》,载《法学》2018年第11期。首先,两者在定义工资的条文中又出现了“工资”字眼,有循环定义之嫌。其次,从法源上看,前者仅规定“依据劳动合同的规定”,后者则规定为“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两相比较,前者似乎遗漏了法定情况下劳动者也能取得工资的情形。最后,工资的本质不明确。有学者认为,因为以上两个规定并未明晰工资的本质,一旦没有法律规定或劳资双方的明确约定,也就无法断定某种给付是否属于工资。(49)同前注,侯玲玲文。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两规定基本确立了“劳动关系对价”的认定标准。同前注,王天玉文;同前注,[日]森下之博文。
(三)我国工资立法的改进
1.工资的立法体例
我国关于劳动基准的立法体例,大致有综合性立法和分散式立法两种选择。(50)同前注,刘汉伟、刘金祥文。前者,即单独制定一部包括工资在内的以“劳动基准法”为名的综合性法律;后者,则对工资进行单独立法,即制定《工资法》或《工资条例》。两种立法体例可谓各有优劣,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各国也都有选择。实际上,自2008年开始,《工资条例》就已经被有关部门提上立法日程,但由于各方争议较大,至今仍未出台。(51)参见耿雁冰:《〈工资条例〉搁置内情:或将分拆按单项推出》,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0月30日第002版。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人社部相关课题组发布了一项有关劳动基准立法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议我国应制定专门的《劳动基准法》,并设置了“工资支付”与“最低工资”两章。(52)参见王文珍、黄昆:《劳动基准立法面临的任务和对策》,载《中国劳动》2012年第5期。如前所述,2018年,劳动基准法作为第三类立法项目,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9年,人社部启动立法草案制定工作。据报道,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已完成《劳动基准法》的专家建议稿。(53)参见庄德通:《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劳动基准法专家建议稿研讨会》,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21年7月27日第004版。由此来看,综合性立法体例正受到我国学界、行政和立法部门的青睐。
2.工资定义的立法模式
从域外的立法例来看,各国家或地区对工资的界定不尽相同,大抵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抽象式;二是列举式,又包括正面列举和反面列举两种方式;三是两相结合式。(54)同前注③,李海明文。对于我国将来的工资定义模式,有学者认为受我国工资立法历史的影响,这三种立法模式皆有可能。其中,两相结合式立法最难,却最有意义。(55)同前注③,李海明文。但是,该观点所主张的两相结合式立法模式主要是“抽象式+正面列举”。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重视对不属于工资情形的反面列举。原因在于通过反面列举可进一步增强各方对“对价”内涵的理解,既可有效预防劳资双方有关工资争议的产生,也可满足解决纠纷的司法实践需求。例如,在日本,反面列举甚至成为日本理论界和实务界认定工资的主要方法,以至于与什么应被认定为工资相比,什么不应被认定为工资反而变得更为重要。(56)同前注,[日]荒木尚志书,第125页。并且,长期以来,根据相关行政解释,日本逐渐确立了反面列举的三大类型:即以结婚礼金、疾病慰问金等为代表的“任意恩惠性给付”,以企业借款给员工、运动设施的使用等为代表的“福利性厚生给付”,以及以工作服、差旅费等为代表的“企业设备与业务费”。(57)参见[日]東京大学労働法研究会編:《注釈労働基準法》(上),有斐閣2011年版,第177-178页。
然而,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工资的定义中多规定正面列举的一致性相比,对于反面列举的规定方式却不尽相同。例如,我国香港地区(58)参见电子版香港法例:《雇佣条例》,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7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5月8日。将正面列举与反面列举都规定在一个法律条文中。与之相反,日本仅在《劳动基准法》中规定了工资的正面列举,之后再通过大量行政解释进行反面列举。虑及法律条文不宜过细,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劳动法》或未来的劳动基准法中仅规定正面列举,而对于反面列举,可借鉴日本的经验,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交由行政解释(59)有学者认为,我国人社部的解释规定作为一种政策,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阶段性。同前注,侯玲玲文。进行规定。
3.工资的立法定义
目前,我国《劳动法》对工资的定义长期缺位,虽然原劳动部发布的《贯彻执行劳动法意见》和《工资暂行支付规定》对工资的概念有所规定,但是该定义不仅对工资的本质未予明确,缺少对工资本质的认识,更未提供一套具有实质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加之其法律位阶不高,受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影响,我国反而逐渐确立了工资总额构成的立法模式,最终导致工资概念在司法适用中“被边缘化”。
为改变这一现象,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在现有的《劳动法》或者未来的劳动基准法中规定工资的定义,明确工资的构成要件。从域外的立法例来看,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也都在劳动基准法或劳动法的基础性法律中规定了工资的定义。同时,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定义工资时也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对于工资予以抽象定义(限定内涵),例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一种是对于工资不予以抽象定义(内涵宽泛),例如英国和美国立法。(60)同前注③,李海明文。然而,两相比较,一般认为通过抽象概念式的体系建构不仅可以实现法学的体系化,还能够保证法的安定性,这种体系具有巨大的魅力。(61)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6页以下。
基于前述对工资本质的认识以及对域外立法例的借鉴,笔者认为我国可将工资定义为:“工资是指不论名为工资、薪水、津贴、补贴、奖金或其他名称,作为劳动的对价,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所支付的金钱或其他价值物”。该“工资”定义包含两项重要要素:一是劳动对价性,二是经济给付性。其中,劳动对价性是认定工资的实质标准,对于劳动对价宜采用相对宽泛的理解,即工资不仅是具体劳动之对价,同时也是劳动者基于其劳动关系地位所获之对价。如果劳资双方依据劳动合同、集体合同、规章制度以及劳动惯例等能够明确雇主的支付义务,亦可认为具有广义的劳动对价性。
四、实践应用:工资概念的解释适用
(一)工资概念解释适用的基本路径
针对实践中与工资认定有关的给付性质争议,为了给司法提供精确指引,我们可以在前述对工资认定理论和立法探讨的基础上,确立“合意判断(广义劳动对价性为主)——反向排除——个别判断(狭义劳动对价性为主)”的解释适用路径。首先,根据劳资双方的合意进行判断。如果劳资双方在劳动合同、规章制度、集体合同中有约定,且该约定有利于劳动者,则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其约定。一旦劳资双方约定雇主对劳动者的某项给付属于工资,即便不具有狭义的劳动对价性,只要存在规范上的依据,亦可视为具有广义的劳动对价性,应当认定为工资。反之,如果劳资双方的约定不利于劳动者,如后所述,则有必要采取实质判断原则,进行严格判定。其次,判断是否属于工资的反面列举。具体而言,未来我国可以在梳理和反思现有规定的基础上,通过行政解释的方式,明确将以下三种类型给付确立为非工资的典型。(1)任意恩惠性给付,例如婚丧礼金、疾病慰问金等;(2)福利性给付,即雇主为了劳动者福祉而给付的费用或利益,例如过节费、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借款和健身运动设施所产生的利益等;(3)业务性给付,即企业为了达成业务所必须之给付,此类给付本来就应当由企业负担,比如工作服、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这三种类型给付均与劳动对价无关,即便由企业向劳动者给付,也不应当认定为工资。但是,如果劳资双方在劳动合同、规章制度、集体合同中预先明确规定了各种给付的支付条件,由此形成劳动者的支付请求权与雇主的支付义务,则具有广义的劳动对价性,应当认定为工资。最后,进行个别判断。即对于某种特殊给付,还可以结合工资认定的狭义劳动对价性和经济给付性这两个标准进行个别判断。
(二)通过合意排除工资性质给付之认定
现实生活中,雇主可能通过明示或默示的合意遮掩某些给付的工资属性,以达到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之目的。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有关工资认定的纠纷,是雇主有意识地将“工资给付”之报酬的性质予以“去劳动对价化”的结果,例如通过明示的合意使实质工资移向“恩惠性”之给付性质,也可以称之为工资的“恩惠性伪装”。(62)同前注,林良荣文。另一方面,如果雇主之给付没有明确与立法的列举式规定相契合,而且劳资双方依据劳动合同、规章制度、集体合同以及劳动惯例等无法确定某项给付之性质,一旦发生争议,法院往往依据其默示的合意而倾向于否定该给付具有工资性质,(63)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民申2035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申3305号民事裁定书。这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很多国家或地区对工资认定中都有“无论其称呼或计算方式如何”“其他任何名称之给与”“任何形式之报酬”等字眼,其目的就在于防止一些无良雇主通过将雇员的某项收入指定为非工资项目而规避法律对劳动者工资的保护。(64)同前注,孙国平文。因此,我们在判断某项给付是否属于工资时,不应只观其外在名称形式,而应采取实质判断原则。具体而言,当劳资双方仅通过合意就将某项给付从工资中直接排除且不利于劳动者时,这种做法通常不具有合理性。特别是对于与具体劳动关联度较高的给付,若当事人通过约定,将其作为非工资项目处理,则有脱法之嫌,应当无效。如前所述,是否具有“劳动对价性”,应当成为判断某项给付是否属于工资的实质标准。不论雇主给付的名称为何,即便是用家庭补贴、物价补贴等似乎与劳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名称,只要其具有广义的劳动对价性,并由雇主向劳动者为给付,亦应认定为工资。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劳资双方对某项给付是否属于工资约定不明确,或者对某项给付是否具有劳动对价性不易辨别时,应当从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立场出发,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判断。
(三)常见争议类型给付性质之认定
1.补贴、津贴
目前,我国大多数工资规范性文件都将津贴和补贴作为工资的构成之一。然而,值得怀疑的是,现实生活中所有被冠名为“津贴”“补贴”的给付都应当被认定为工资吗?实际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补贴、通讯补贴以及餐费补贴等是否属于劳动法上的工资,认定并不统一。(65)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5791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5号民事判决书。
按照前述所构建的工资认定路径,可做如下判断。首先,如果劳资双方在劳动合同、规章制度、集体合同中预先明确规定了通讯补贴、交通补贴等各种补贴津贴的支付条件,从而形成劳动者的支付请求权与雇主的支付义务,则这些补贴就具有广义的劳动对价性,应当认定为工资。其次,结合具体的给付类型,判断是否属于工资的反面列举。(1)关于通讯补贴,通常是雇主为补贴劳动者因联系业务而产生的通讯费用,该费用本身是企业为了达成业务所必须之费用,本来就应当由企业负担,故属于“业务性给付”范畴,不应认定为工资。(2)关于交通补贴,多是企业为了补贴员工因完成业务而支出的交通费用,其性质与通讯补贴相类似,也不应当认定为工资。(3)关于通勤补贴(上下班交通补贴),应当认为这是劳动者因提供劳务而自身所需负担之费用,不具有劳动对价性,可视为单位的一种“福利性给付”,故不宜认定为工资。(66)同前注,[日]荒木尚志书,第128页。(4)与通勤补贴类似的还有餐费补贴,如果雇主未从劳动者的工资中扣除相关费用,且金额也不大,可视为单位的一种“福利性给付”,不应认定为工资。(67)同前注,[日]西谷敏、野田進、和田肇书,第38页。(5)关于住房补贴,如果雇主享有完全自主的发放权,可视为单位的一种“恩惠性给付”或“福利性给付”,也不宜评价为工资。
2.奖金
现实生活中,奖金的种类较多,性质也比较多样。《贯彻执行劳动法意见》第53条将奖金界定为工资的一部分,从该规定来看,除创造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等不属于工资的范围之外,似乎其他名目之奖金均可以被认定为工资。与之相反,《工资总额规定》则将奖金限定为生产奖、节约奖、劳动竞赛奖以及其他奖金。实践中,雇主是否负有支付奖金的义务以及所支付的奖金是否属于工资,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因而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予以讨论。
首先,如果劳资双方在劳动合同、规章制度、集体合同中预先明确规定了各种奖金的发放条件,据此雇主承担相应的给付义务,则该给付具有广义的劳动对价性,应当认定为工资。其次,如果奖金的发放与否以及发放的标准、额度,完全由雇主自由裁量,且与劳动者的工作或考核结果无关,则该给付不具有劳动对价性,可视为雇主的一种“恩惠性给付”,不宜认定为工资。最后,如果雇主发放某一名目之奖金,系基于出勤率、产品质量、销售状况而发放,对应于劳动者的服务、生产力或效率,则可认为该给付具有狭义的劳动对价性,应当认定为工资。(68)同前注,谢棋楠文。但是,为了提高劳动者对于某种奖金是否属于工资的预期性,今后我国的工资基准立法可以作出明确规定,即将奖金的发放与否以及发放要件、计算方式、发放方式等事项作为雇主的义务,鼓励雇主记载于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之中。
3.小费
目前,我国与工资相关的规定并未对小费的性质予以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针对小费是否属于工资尚未形成定论。小费与一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现实和价值选择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小费能否纳入工资争议背后折射着该国劳动法之理念和价值判断。(69)同前注,孙国平文。
对于小费是否属于工资以及能否冲抵工资等问题,按照前述所构建的工资认定路径,可做如下判断。首先,在有利于劳动者的情况下,可以有约定的从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加之又不符合工资的反面列举,则应结合工资认定的狭义劳动对价性与经济给付性这两个标准,视情况分别进行处理。通常而言,小费有两种收取方式:一种是由劳动者自行向顾客收取,另一种是由雇主统一向顾客收取后,再统一分配给劳动者。前一种小费因其来自顾客而非雇主,可理解为属于顾客的赠与行为,故不应认定为工资。但是,后一种小费是由雇主统一收取,统一分配,雇主对收集和分配小费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和干预,并最终由雇主向劳动者进行支付,此种小费与雇主业务紧密联系,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均已具备工资之特性,故应认定为工资。(70)同前注,孙国平文。
4.非货币给付
目前,我国的工资立法仅允许雇主以法定货币方式向劳动者支付工资,不允许用实物或有价证券等非货币形式来代替。(71)参见《劳动法》第50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5条。但是,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法国、日本等国家并未将工资的给付形式限定为货币给付。
根据前述对工资认定标准的探究,首先,判断某种给付是否属于工资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劳动对价性,而不能仅以给付形式(例如实物)就断然否定其工资的性质,否则就违反了工资的客观性原则;(72)同前注,[日]西谷敏、野田進、和田肇书,第36页。其次,如果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达成一致,并在集体合同中明确约定将实物等作为部分工资的给付形式,法律似乎也没有强行干涉的必要;最后,劳动基准法关于工资规制的重点不在于给付形式的确定,而在于确保工资能够得到及时足额支付等其他方面。(73)参见[日]土田道夫:《労働契約法》(第2版),有斐閣2016年版,第239页。基于此,笔者认为货币不应成为工资支付的唯一形式,非货币给付也应当予以认可。但是,如果允许工资以实物等非货币形式发放,这不仅与工资的货币支付原则等发生冲突,而且容易被企业滥用进而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而有必要予以限制。因此,今后我国的工资基准立法可以规定,只有在法律、行政法规、集体合同等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雇主才可以通过非货币形式向劳动者为给付。(74)日本《劳动基准法》第24条规定:“工资必须用通货直接向劳动全额支付。但法律或劳动协约另有规定时,或者根据厚生劳动省令确定的支付方法,可用通货以外之物支付”。
五、结语
工资虽然是劳动法中的基础性概念,但我国《劳动法》并未明确规定工资的定义,由此造成实践中劳资双方、法院以及仲裁机构判断某种给付性质时的不一致。通过对域外工资立法与司法的考察,并在梳理与反思劳动对价、关系正义以及经常性给付等工资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倡将劳动关系对价“二阶段”说作为认定工资的实质标准,同时构建“劳动对价性”与“经济给付性”相结合的工资认定标准。这样一个实质与形式相结合的工资认定标准,今后若能在《劳动法》或未来的《劳动基准法》的工资定义中得以明确,不仅对我国的工资立法大有裨益,还将有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工资认定的争议,进一步缓解“同案不同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