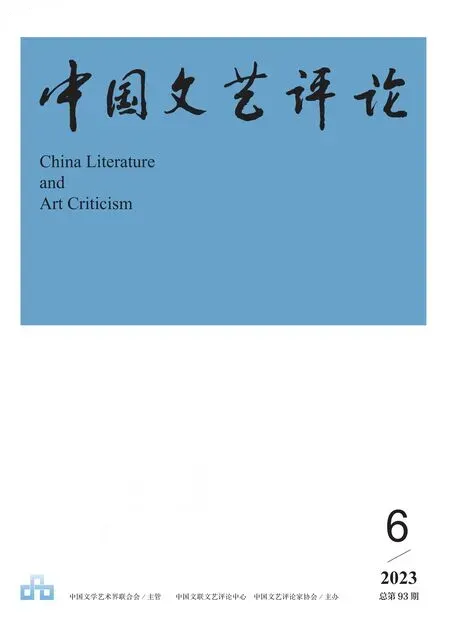汉魏乐论与“和”的转型
2023-07-21■韩伟
■ 韩 伟
汉魏是中国思想史和美学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多将这种转折的节点定位在魏晋,实际上思想观念和审美倾向如同一条绵延的河流,优美的浪花或灿烂的景象绝不是突然之间的产物,它需要源头的底蕴,需要奔流过程中的积蓄,最终才会在某一时间或某一阶段呈现壮丽的景观。因此,讨论魏晋离不开轴心时代,也更加离不开作为其近邻的两汉。“和”不仅是中国美学的元范畴,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其与音乐关系密切,在不同时代的乐论中都有“和”的身影。可以说,乐论是“和”产生、发展、成熟的重要疆域,汉魏乐论对“和”的建构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考察“和”的演变线索,并试图强化古代乐论对美学史、艺术史的价值。
一、气和:汉代乐论的自然转型
早在中国文明发端期,“和”的内在潜质便已经蕴蓄。只要谈“和”,《尚书·尧典》便是无法绕开的材料。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古代音乐审美的原型,这个原型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教胄子”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道德改良。通过音乐熏陶,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境界。其二是“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体系,这个体系强调音声形式对神与人的感召性。如若抛开第一个体系的限定,第二个体系包含着对音乐形式、技巧等因素的肯定,这些因素构成了万物和谐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这两个体系的存在,导致后世对“和乐”的认知出现复杂情况。就周代雅乐而言,在义理层面和技艺层面都达到了和谐水准,且两者相得益彰,但春秋以后的礼崩乐坏导致了义理与技艺的分裂,这也就形成了后世对“和乐”的不同认知。
《乐记》[1]对《乐记》作者及成书年代的讨论由来已久,沈约、孔颖达、张守节、姚鼐、钱大昕等历代学者均有涉及。进入现代以来,郭沫若1943年发表的《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为最早研究上述问题的专论,其后,宗白华、余嘉锡、杨公骥、朱光潜、蔡仲德、杨荫浏、周来祥等人都有相关文章,诸家文章后以《〈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为题结集出版。至今,尽管众多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发表了大量成果,但并未得出推进性的结论。此种情况下,本文倾向于同意郭沫若、李学勤等人的观点。前者认为《乐记》作者是公孙尼子,并认为他就是七十子中的公孙龙,李学勤在《周易溯源》的“从《乐记》看《易传》年代”一节中,在合理继承郭说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作者公孙尼子实有其人,为战国初年人物。对于版本问题,吕骥等学者认为现存的《礼记·乐记》为刘向校定的另一个版本,即公孙尼子的版本,现存11篇。本文凡涉及《乐记》处俱以上述结论为出发点。中含有大量关于“和”的论述,可以将“和”看作《乐记》的重要关键词。“和”在《乐记》中起码包括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三个维度。就天地之和而言,《乐记·乐论》篇纲领性地指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就人性之和而言,《乐记·乐本》篇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论断,进而又有“乐以和其性”的补充,遂将静、性、和勾连于一处。就社会之和来讲,《乐记·乐化》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2]杨天宇:《礼记译注》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05页。强调乐在社会中发挥的和谐作用。蒋孔阳曾对《礼记·乐记》在中国思想史和美学史上的地位加以肯定,认为《乐记》“不仅是第一部最有系统的著作,而且还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3]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客观而言,尽管《乐记》对“和”的讨论仍有不够完善之处,但将之看作先秦“和”论的缩影亦并不为过。或者换个角度说,它如同一个路标,为后世乐论对“和”的言说提供了中介和参照。
在汉代乐论中,“和”亦是高频词,它充当着精神内核的角色。对“和”的推崇并非抽象式的义理言说,其载体是“气”,故汉代乐论呈现出独特的“气和”倾向。在以《乐记》为代表的先秦乐论中,不仅提到了“气”,也提到了“阴阳”,前者如“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乐言》)、“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乐言》)、“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乐象》);后者如“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乐礼》)、“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乐礼》)。一方面,这里提到的“气”更多时候是指人的“血气”,接近于内在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即使偶有提到“地气”“天气”,但主要是作为自然现象而言,并未真正上升到阴阳二气的抽象维度。
汉代“阴阳二气”的进步意义在于,将先秦时期异常抽象的“阴阳”概念向形而下的层面拉近了一大步。“气”在汉代虽然仍带有明显的抽象意味,但相较于“道”“有”“无”等概念,它的物质性、客观性更加明显。所以,从“阴阳二气”的角度讨论乐的发生在汉代相当普遍,《乐纬·动声仪》言:“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灰,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灰,重而衡低。”[1][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4页。《乐纬》作为汉代依经而作的乐论经典,是折射汉代音乐观念的镜子,这段话中的阳气、阴气不仅按照“同类相动”的逻辑与冬、夏相关,更加与音律相合,在神秘中也体现出难得的唯物倾向。这种情况在《史记·律书》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
十月也,律中应钟。应钟者,阳气之应,不用事也。……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十二月,律中大吕。大吕者,其于十二子为丑,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万物簇生也,故曰泰簇。……二月也,律中夹钟。夹钟者,言阴阳相夹厕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万物洗生。……四月也,律中中吕。中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为已。已者,言阳气之已尽也。……五月也,律中蕤宾。蕤宾者,言阴气幼少,故曰蕤;痿阳不用事,故曰宾。……六月也,律中林钟。林钟者,言万物就死气林林然。……七月也,律中夷则。夷则,言阴气之贼万物也。……八月也,律中南吕。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2][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43-1247页。
《律书》一方面将十二律吕、十二月份相配,体现出汉代万物互联的五行思维;另一方面也赋予阳气、阴气以运动属性,两者升降变化俨然成为季节轮换、音声差异的根据,而且它们与普通人日常认知的距离进一步拉近。某种意义上,可将上述表述看成是“阴阳二气”具体化、现实化的缩影。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阴阳二气”化生产物的音乐,也呈现出一定的客观化倾向。班固《白虎通德论·礼乐》曰:“声音者,何谓也?声者,鸣也,闻其声即知其所生。音者,饮也,言其刚柔清浊,和而相饮也。”[3][东汉]班固撰:《白虎通德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页。这段话难能可贵,原因是班固乐论虽然整体上仍带有道德化乐论的影子,但却呈现出了其对声音的进步性认知,已经从相对自然的角度看待声音问题了,即声音的本体就是各种鸣响,当这些鸣响彼此协调之时,美妙的音乐便产生出来了。贾谊《新书·六术》云:“是故五声宫、商、角、徵、羽,唱和相应而调和,调和而成理谓之音。”[1][西汉]贾谊撰:《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7页。以此来看班固口中的“和”,可知这是一种单纯自然音声协调悦耳意义上的“和”,不仅有继承《尚书·尧典》“八音克谐”传统的味道,更加具有开启魏晋音乐审美的意义。
从艺术生产的全过程来看,上段文字呈现的是物化阶段的“和”,除此之外,“和”还具有发生学的意义。不妨从董仲舒“声发于和”的观点说起。在董仲舒看来,“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2][东汉]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9页。,声音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人的外表(所谓“手舞足蹈”)和精神(所谓“成于乐”)的影响可以从常识层面加以理解,但“发于和”则具有较大模糊性。这里的“和”既是一种现实世界的存在样态或性质,更加是一种先验性存在,其应有之义当与阴阳二气有关,即阴阳二气相得益彰便是“和”。与此相关,“和气”就成了阴阳二气化合之后的呈现态。类似的意思在《乐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乐纬·叶图徵》言:“五乐皆得,则应钟之律应,天地以和气至,则和气应,和气不至,则天地和气不应。”[3][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6页。魏人宋均注曰:“和气,上下相得之气。” 在汉代气论背景下,天地上下相和,实际上就是阴阳二气相和,所以可以说《乐纬》将《乐记》所强调的“乐者,天地之和”的笼统性观念,发展为“乐者,与天地阴阳之气和”的时代新思想。
与《乐纬》带有神秘色彩的“和气”观念不同,王充的“和气”观在其乐论中得到了唯物性呈现。王充在汉代思想家中独树一帜,“忌虚妄”不仅是其文学思想的反映,更是他整个哲学倾向的缩影。在《论衡·感虚篇》中,他对带有神秘色彩的师旷鼓琴一事加以分析。在他看来,《国语·晋语》所载的晋平公强令师旷演奏《清角》之曲,引来玄鹤之事尚可理解,因为鸟兽也有基本的声音感知能力;但招致风雨大作、瓦裂物毁,以及国君罹病、国家赤旱等事则过于神秘,属不实之言。理由是:“乐能乱阴阳,则亦能调阴阳也,王者何须修身正行,扩施善政?使鼓调阴阳之曲,和气自至,太平自立矣。”[4]黄晖撰:《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45页。即是说,音乐有如此神力,国君不必励精图治,只需创制出美妙的乐曲便可国家大治。这段话中提到了“和气”,虽然并未进一步展开,但基本逻辑较为明显,即他虽然否定了具有虚妄色彩的音乐功能论,但不妨碍表述“和气”与“太平”的关系,“和气”至则“太平”境界就会实现(此处体现了他的唯物思想不够彻底之处)。王充的“和气”论建立在其唯物哲学基础上,这一点与上文《乐纬》的“和气”观念在出发点上有所不同,但两者还是存在相似之处的:首先,对音乐的讨论都是它们建构或阐发“和气”思想的重要维度;其次,相比于先秦“和”论,两者对“和气”的理解都带有客观化、唯物性色彩。
从以上分析可知,汉代乐论是从本体维度看待阴阳二气的,“和”作为阴阳二气化合的结果,便也相应具备了本体意味,“和气”的概念应运而生。若从“和”的状态而言,此时的“和”已经逐渐从先秦或神秘或道德的限定中挣脱出来,具备更多的客观意味。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的“和”又可称为“气和”,在其统御下汉代音乐审美开始重视声音自身的和谐,向客观化和去神秘化的方向发展。
这种倾向到了魏晋时期开始变成主流诉求。如果说汉代之“和”为“气和”的话,那么魏晋之和则进阶为“美和”。“美和”概念并非产生于魏晋,而是源自汉代。《淮南子·说山训》中有这样一段话:“欲学歌讴者,必先徵羽乐风;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1]张双棣撰:《淮南子校释》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98页。按照吉联抗先生的译法,这段话的意思是“要想学唱歌的,必须先学会唱徵音羽音等等以及各种民歌。要想唱得美妙的,必须从‘阳阿’‘采菱’这些学起”[2]吉联抗译注:《两汉论乐文字辑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65页。。其中提到的《阳阿》《采菱》应为楚地民歌,《襄阳耆旧传》载:“昔楚有善歌者,王其闻欤?……中而曰《阳阿》《采菱》,国中唱而和之者数百人。”[3][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84页下。不同于世俗气更浓的《下里》《巴人》,也相异于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阳阿》《采菱》居于楚地民歌中雅俗适中的位置。由此反观“美和”,意义就较为明晰了。冠以“美”名的重要前提是音声美妙、雅俗适中,既不能只是少数读书人欣赏的“高贵之乐”,也不能是贩夫走卒唱烂了的民间俚调。汉代帝王从刘邦开始就表现出对楚地民歌的青睐,上行下效,民间的审美风尚必然受到影响。但与此同时,其中亦渗透着辩证因素,整个社会试图构成一种感性与理性、高雅与通俗相互结合的和谐美学旨趣。
二、美和:魏晋乐论的审美自觉
汉代乐论的“美和”风尚,成为了魏晋时期音乐审美的潜在基础,并得以系统展开。具体而言,“美和”呈现为音声之和与乐器之和两种形态。为了言说方便,姑将前者称为“音和”,后者称作“器和”。
首先来看魏晋时期的“音和”追求。音与乐的最大区别是,在形式背后是否被人为地灌注义理。魏晋是古代艺术开始自为性存在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在音乐审美中也发生了由“乐和”向“音和”的转型。这个话题无法绕开的人物就是嵇康。在其著名的《声无哀乐论》中有一段总括性表述:“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1]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97页。虽然《声无哀乐论》仍或多或少地带有汉赋的行文体征,且在反复论说过程中也不免存在内容抵牾之处,但总原则相当明晰,这段话就相当于全篇题眼。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宫商集比”的强调,“集”为集合,“比”为相邻,五音配合得当,和谐的声音便自然产生。
与“集比”同类的概念是“和比”,两者在《声无哀乐论》中频繁出现,且互相通用。出现“和比”的句子如“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等。综合来看,嵇康一方面强调音声“和比”是内在情感的基本诉求,和谐之形式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指向;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人性与“和比”的密切联系,正因这种联系才使得和谐而规律的声音最能打动人心。这就与传统乐论明显不同,无论是对人性诉求的考察,还是对音乐功能的言说,都最大限度地将伦理、道德乃至先入为主的“意义倾向”剥离出去,还音声本有的自然属性。
谈到“意义倾向”,还需指出,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士人并非将挑战的触角直接伸向先秦儒家伦理化乐论,而是以汉代“悲”性音乐审美为直接攻击的靶子。刘向《说苑·善说》、桓谭《新论·琴道》中都曾记载雍门子周与孟尝君讨论音乐的故事,雍门子周通过语言描述,配以缓缓琴音,终令孟尝君“涕浪汗增”,顿生悲感,心满意足。类似的例子或理论言说在《淮南鸿烈》《论衡》等著述中都可见到,表现最明显的是枚乘《七发》以及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等文学作品,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展示出悲音的美妙。[2]参见韩伟:《汉代乐论的美学贡献及对文学之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期,第188-194页。这种情况在嵇康等人这里受到了极大挑战。嵇康的另一篇重要文献是《琴赋》,它一方面延续了汉代音乐赋的体例、风格,另一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文章开篇即言“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赋予音声以表现情感、协调情志的作用。其不同于汉代乐论之处在于,它所强调的音声属于自然而然之声,并不具备悲哀、愁怨等先在属性,以此为出发点,嵇康对汉代音乐审美进行了反思:“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3]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84页。很显然,这是对汉代音乐审美“尚悲”倾向的反拨。这种认识在魏晋时期具有普遍性,尽管阮籍乐论仍带有传统儒家乐论的味道,表现出对“先王雅乐”的推崇,但却更多地呈现出对自然之声的肯定。在“悲音”问题上,阮籍同嵇康相似,指出:“诚以悲为乐,则天下何乐之有?天下无乐,而有阴阳调和,灾害不生,亦已难矣。”[4]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9页。今天看来,乐音也许源自人的经历和社会环境,但不能将这些看成是乐音的直接源头,与其直接关联的只能是创作者或演奏者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音乐的节奏会有轻重、缓急之别,这些形式因素也是令接受者产生不同情绪体验的现实基础,若抛开这个层面而空谈形式背后的天道、伦理、政治,必然会滑向神秘主义的深渊。诚然,阮籍、嵇康等人的音乐观念中还带有明显的阴阳五行色彩,但相较于先秦乐论已经有明显进步。“音和”观念最大限度地削弱了伦理、政治因素对音乐审美的干预,也从根本上取缔了汉代“悲音”对乐音之自然属性的干预。在这种背景下,声音的“和比”成为音乐审美的首要关注要素,并在“和声无象”(嵇康《声无哀乐论》)观念的促动下,获得了充分的独立空间。每个人欣赏“和比”乐音所产生的感受,本质上是内在情绪的投射,和声本身并无固定之象。
如果说“音和”是魏晋“美和”风尚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器和”则不仅是这种风尚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同时也扮演着物理基础的角色。实际上,声音与乐器是一个统一体,和谐优美的声音必然源自独特的乐器。从这个意义上说,音和与器和共同构建了魏晋音乐审美的理想情貌。嵇康《琴赋》提到了“器和”概念,在谈到琴音之美时,有“器和故响逸,张急故声清”的表述,将乐器精巧看成是产生美好音声的前提。很显然,这里所言之“器”当为古琴无疑。若要实现琴音的自然之境,琴器的完善当然是必要保障,其应有之义包括材质、丝弦、徽位、工艺等方面的考究。由于现有材料的缺乏,已经无法看到魏晋时期有关制琴工艺的详细记述了,但从一些其他材料中还是可以窥得大略。顾恺之《斫琴图》(见图1)距嵇康时代稍晚,多少可以起到为理论言说提供实物佐证的作用。全图14人,分为斫琴匠人、贵族指导者、随从仆役等三类,画面中直接与制作琴器有关的共七处,由左至右,分成粗刨琴材、打磨细斫、听弦调音、制作部件、面板造型、底板展示、制造琴弦等单元,而且清晰可见琴身的额、颈、肩,底板上的龙池、凤沼亦非常明显。在匠人身边存在或坐、或立的贵族(从身后的侍者可见其身份),从他们的手型可以推断他们很可能充当技术指导者的角色。由此足见,至迟到顾恺之时代,不但琴器有了完备的形制,而且斫琴技术已经较为成熟,这些物质保障使嵇康口中的“器和故响逸”成为可能。

图1 [东晋]顾恺之 《斫琴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有关“器和”,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即魏晋时代丝竹之器对金石之器的取代。对金石之器以及金石之音的重视是先秦庙堂审美的产物,无论在商周还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审美品味的形成都带有自上而下的性质,天子及其主导的庙堂往往起到塑造时代审美风尚的作用,礼与乐也主要在贵族阶层才有效。庙堂审美的重要特征是注重仪式感,呈现出宏大、高贵的倾向,金石类乐器恰能扮演这种角色。作为金石之器重要代表的钟、磬,很少单独演奏,它们往往成组出现。在乐悬制度下,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表现为乐悬布局以及乐器数量的差异。按《周礼·春官·小胥》所载,西周乐悬之制为“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1]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36-337页。,无论哪种陈列方式,都蕴含着浓厚的等级意味,无怪乎《乐记》中魏文侯发出“听古乐,唯恐卧”的感慨。
从魏晋时代开始,丝竹类乐器的地位获得空前提升,这与汉末以来庙堂地位的衰落以及民间士人身份的觉醒有密切关系,主流审美开始不再遵循自上而下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音乐既是潮流的呈现者,也是潮流的构建者。与厚重而略显沉闷的金石之声相比,丝竹之声以其轻盈而民间的特征开始成为审美领域的主要青睐对象,所以嵇康才有“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的说法。在他看来,金石代表了最初的和谐之美的营构,但理想的、最高层面的和谐之声则非管弦莫属。笔者曾在《从金石到丝竹——魏晋审美变革的潜在路径》一文中列举过诸多魏晋六朝时期的实存证据,包括江西南昌出土的东晋雷陔墓“彩绘宴乐图漆盘”、南京西善桥南朝古墓中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浙江出土的魏晋葫芦神青瓷器、江苏金坛东吴墓出土的青瓷谷仓罐,等等。[2]参见韩伟:《从金石到丝竹——魏晋审美变革的潜在路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1期,第82-88页。在这些文物中,琵琶、古琴、长笛、箜篌、排箫等丝竹类乐器大量出现,不仅呈现出完整的民间社会生活图景,也反映出丝竹类乐器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尤其在文士生活中更是如此。再结合魏晋史书中大量有关士人鼓琴的记载,可以说魏晋时代的审美变革与丝竹类乐器的盛行密不可分。
丝竹类乐器除了凭借琴音的悠扬、轻巧,实现文人精神的俯仰自得之外,还充当着外化雅士品味的角色。它们往往成了文人阶层不随流俗、自我崇高化的外在意符,甚至有时是否掌握弹琴之技已不那么重要(陶渊明就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琴具自身的形制因素就备受重视,“器和”的意义得以凸显。器物审美本就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琴具在众多器物中尤具地位,魏晋以后文人更是将这种潮流发扬光大,比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将“(唐敬宗)宝历三年雷会所斫”的古琴称作家中的“宝玩”;宋徽宗在内廷中设立“万琴堂”,流连忘返;金章宗驾崩后,以“春雷”琴陪葬,等等。
总而言之,汉代乐论及音乐审美对“气和”的建构,一方面具有对“和”的内涵进行充实、转型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魏晋时代崇尚音声、器形的新审美风尚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魏晋时期,客观化审美潮流逐渐生成,各艺术门类呈现出对“美和”的向往。就音乐领域而言,“美和”通过“音和”与“器和”两个维度得以呈现,且产生了持续性影响。丝竹之音、丝竹之器的地位提升,使轻盈的审美取代了厚重的审美,自为的艺术追求取代了他为的艺术实践,个体品味取代了群体意识。尽管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免还会出现伦理、政治干预艺术的情况,但魏晋作为极端的个案,其突破意义绝不可忽视。“美和”最大限度地以客观化审美取向置换了“和”范畴固有的伦理化审美倾向,并将“和”的所指从形而上世界向形而下世界拉近了一大步。
三、余续及影响
汉代“气和”的贡献是将“和”从神秘、先验的维度,拉向实在、可感的维度,这为魏晋“美和”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魏晋时代在“美和”的统御下对“音和”“器和”的强调,亦构成了唐代以后“淡和”“感官之和”的先导,从而最大限度凸显出了汉魏乐论的历史贡献。
唐代具有开放的文化胸怀。就音乐审美而言,唐太宗表现出了难得的开放心态,“乐在人和,不由音调”(《贞观政要》卷七)是这种心态的具体表现。他的这种态度也促进了唐代社会高雅与通俗、华夏与夷狄的深度融合。于是,武后朝奉敕编纂的《乐书要录》直言“乐之克谐,以声为主”,其中“声”已经不完全是儒家高雅正声。玄宗更是对俗乐青睐有加,设立教坊和梨园。表面看来,盛唐之前的音乐审美与魏晋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却是对魏晋时代形式之“和”(“美和”)的否定之否定,此“和”乃是容量更为丰富的新型之“和”。本文姑且称之为“淡和”,取其内容博大、沟通华夷、质朴自然之义。安史之乱以后,盛唐之前被建构起来的“淡和”风尚遭到颠覆,音乐重新被赋予了硬性的社会职能。除了主流的礼乐政策之外,在文人中,白居易称:“序人伦,安国家,莫先于礼。和人神,移风俗,莫尚于乐。”(《策林·议礼乐》)这不仅重新回到了礼乐相济、礼乐协政的老路上,而且对“和”的认识也并无新意。韩愈、柳宗元等同时代诗人面临的情况具有相似性,也表现出了共性的心路历程,“文”与“乐”都承载了共同的“明道”使命。如果说“道”是一种抽象境界的话,那么“和”则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可感性,只不过此时的“和”没有了盛唐之前的从容气度,变成了一种功利的、急切的、显性的存在。
盛唐时期初具雏形的“淡和”,经历了中唐的伦理化反复之后,在宋代更为完善,获得了哲学性身份。其形态既高于盛唐“淡和”,效果又超越了生硬的伦理化灌输所能达到的境界。在宋代乐论中,周敦颐对“淡和”尤为看重。在《通书·乐上》中,他将雅乐乐声以“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加以界定,同时将“淡且和”“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视作它的功能。如果说周敦颐是宋代理学奠基性人物的话,那么欧阳修、梅尧臣等文学家则是宋代艺术潮流的引领者,他们从相对形而下的层面建构了“淡和”旨趣。这种旨趣的形成与他们对民间歌谣的吸收关系密切,秉承着民间歌谣的怨刺内容,同时吸收其自然随性的形式样态,“淡和”审美由此形成。[1]参见韩伟:《民歌与淡怨:欧阳修文风的形成及美学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第49-54页。总体来看,作为理学奠基者的周敦颐在哲学层面建构了人们对“淡和”的信仰,身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则在艺术实践层面塑形了“淡和”的审美旨趣。一方面他们仍然带有“和”的历史基因,既在人性层面升华了“和”的高度,又在艺术功能层面秉持着“和”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淡和”观念在理学和文学的双重建构下,不仅包蕴了汉魏以来偏于形式且融通夷狄风格的通变之和,也兼容了中唐以来以社会和谐为指向的明道号召,遂令“淡和”旨趣获得最终形成。
与宋代“淡和”的音乐审美旨趣不同,明清两代表现出对“感官之和”的推崇。实际上,无论上文谈到的魏晋的“美和”,还是唐宋时期的“淡和”,都不可能离开感官的感知。不同的是,明清之际官方限制的松动以及民间审美的多元化,使感官享受的和谐成为时代整体风貌,“和”也从哲思层面、社会层面进一步解放出来。明代乐论对感官之和的推崇,源自社会音乐实践的通俗化潮流,而这种潮流的形成又是庙堂审美和阳明心学共同作用的结果。早在朱元璋为吴王之时,就有意识地废除朝堂上的女乐,令道童担任乐舞生。这样做的初衷是好的,但道童毕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礼生、乐员,这为世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土壤。到武宗时期,甚至达到了“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的程度。尽管世宗即位后,通过旷日持久的“议大礼”活动,加强了皇权在礼乐建设中的统治力,但却埋下了礼乐可以凭借帝王喜好随意处置(“礼乐自帝王出”)的隐患。这不仅动摇了礼乐传统的权威性,更加损伤了国家文化建设的严肃性,为民间话语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这一时期,借势而起的阳明心学是促使世俗文艺发展的另一个推手。其对“人情”的肯定以及百姓对“人情”的世俗化理解,为民间文艺的繁荣提供了学理依据。
在官方和心学的双重作用下,感官的地位获得了凸显。比如宋濂在《〈太古正音〉序》中对琴音之美加以展示,其中既没有以往琴论的玄虚言说,也没有用过多笔墨描摹琴具、指法、徽位,而是侧重展示“瞑目而听之”的感受,将视觉、听觉连接起来,在通感中获得“心气之平,神情之适”。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琴学的集大成专著徐上瀛的《溪山琴况》之中。该书以“况”定“品”,位居首位的就是“和”况。其中,出现了“散和”“按和”“真和”这样的表述。“散和”“按和”既是技法,又是听感,“散”“按”为弹琴指法无疑,而“和”则属于感官感受。同时,以“真和”为最高的感觉之境,当按音与泛音参差互现时,此境界便呼之欲出。“和”作为《溪山琴况》众况之首,不仅是在演奏层面强调指、音、意之间密合无隙,更主要的是在界定一种审美风格,而审美风格的形成除了依靠演奏者高超的技巧之外,更加与欣赏者的感官品味关系密切。总之,“感官之和”成了“和”强调的对象。
清代乐论是中国古代乐论的终结期,呈现出实学化、现实化的总体征象。在这种背景下,“和”范畴的抽象属性变得愈发淡弱,明代乐论对“感官之和”的推崇,在清代乐论中更为明显,并走向深入。作为新的审美风尚,很多文人雅士不再纠结于今乐与古乐的区别,往往以能够带来感官平和、安静为“雅”的衡量标准。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如毛奇龄、江永、汪烜等。在《竟山乐录》中,毛奇龄以琴为对象,对一些“近世琴家”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以乖反为主,东勾西劈,时按时泛,全不晓和平二字安在,只拗声劣调以为能”[1][清]毛奇龄撰:《竟山乐录》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7页上。。他所崇尚的“和平”,本质上就是一种审美感知。清代文人不再执着于从天地、伦理等层面观照“和”,往往以“全在音调调和”(陈幼慈)[2]吴钊、伊鸿书等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444页。为衡量音乐好坏的标准,“感官之和”充斥整个社会。
综上所述,汉魏以来“和”的音乐之旅总体上经历了“气和”“美和”“淡和”“感官之和”的历史阶段。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汉魏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使先秦乐论中初具规模的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的逻辑体系更为严密,以“气”为纽带,使玄虚性质的“和”具有了现实性质;另一方面也开启了艺术自觉的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汉代的“气和”进展就不会有魏晋的“美和”呈现。所以,可以将汉魏看作音乐美学发展史上的自觉时代。在“和”的维度,这一时期对现实的接近,对形式美感的重视,都为后世以“和”为核心的音乐审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唐代以后,虽然伦理化、政治化的风潮不时重回乐论园地,但总体上体现出的“淡和”“感官之和”的审美追求,都无法脱离汉魏时代的开启之功。另外需要强调的是,音乐与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绝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互渗关系。因此,我们讨论音乐就是在讨论美学和艺术学问题;勾勒乐论中“和”的沿革问题,本质上就是在梳理审美之和、艺术之和的理论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