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圆形流散视角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的主题研究
2023-07-19王刚
王 刚
内容提要: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是2020年诺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的代表作,其主题是自我身份的模糊焦虑和心理漂泊游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浑然一体而不能分离。前者通过自我身份的迷失、自我身份的找寻和自我身份的回归得以体现,后者通过流散的世界、隐藏的世界和神话的世界得以彰显。而这些都是全球圆形流散的典型特征,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探究以及对灵魂深处的审视,超越了现实语境下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混杂,上升到抽象的全人类精神层面。文学全球圆形流散在理论建构上跨越时空、融合文化、深研生死,并具有全球普遍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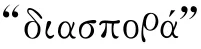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美国著名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1943—)的诗歌着重描写现代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细腻感知与心理变化。格丽克早期的作品聚焦于自白体叙事诗,后期的诗歌具有“后自白诗”特征(宋宁刚127)。她通过奇妙的想象改写神话故事、典故、文学作品,格丽克流露出自己对生命、死亡、个人身份、爱情等的细腻感知,并通过构建生活中的真实场景与虚幻想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传达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对身心的深刻思考,使带有自传色彩的诗歌具有了普遍意义,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鲜明的共同体意识,而“共同体是历代作家文学想象的重要客体,也是繁衍最久、书写最多、内涵最丰富的题材之一”(李维屏77)。
国外对格丽克诗歌的研究众多,主要集中于其语言风格及美学价值方面。美国诗歌评论家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1933—)认为格丽克谦卑、朴实和平常的语言具有高度的可读性,正是它们富有层次的、神秘的口吻使其与众不同。“这不是一种社会预言,而是一种精神预言——一种没有多少女性有勇气发出的声音”(Vendler 16)。美国诗人亨利·柯尔(Henri Cole,1956—)提到格丽克的诗歌受到一种美学的影响,在这种美学中,美总是不完美的、无常的或不完整的。“在她的诗歌中,生活似乎不断地被反映在季节的流逝中。灵魂在身体里苏醒,就像一棵开花的李子树,秋天来了就会凋谢”(Cole 97)。
随着格丽克诗歌在国内受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国内现有的对其诗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死亡、神话、自然主题及创造性改写等方面。宋宁刚(2019)从女性视角解读格丽克,认为格丽克颠覆了原有的暗指主体性,在充满创造的重写中赋予了诗歌新的意义。他特别强调了女性的观点: 一方面,它使其诗歌更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它更巧妙地展现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和她们的命运。胡铁生(2021)探索了格丽克诗歌的美学价值,认为格丽克的生命诗学立足于个体的存在和个体的生命经验,使其生命哲学美学从个体经验的特殊性上升到集体意识的普遍性。
国内外学者对格丽克作品的研究已涉猎颇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但其中关于格丽克作品中独特的自我身份和灵魂深处的研究仍比较匮乏。然而这两点也是绝大多数现代人的共同感受,能穿越时空,直击人的灵魂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因此值得深入探讨。
《直到》的核心内容是生、死、爱和性,它们不是按照传统的模式推进,而是一直循环往复地演变,甚至有时相互转换,这使作者对它们的揭示鞭辟入里,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直到》的主题是自我身份的模糊焦虑和心理漂泊游移,它们分别涉及身体和心理两个维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浑然一体而不能分离。它们与上述全球圆形流散理论十大主题中“自我身份的模糊焦虑与寻根寻家之旅” 和 “身心的漂泊体验与四散漂移的呈现”两个主题(王刚101—102)也是高度契合的。为此,本文在全球圆形流散理论视角下,深入分析这两个主题,旨在揭示该作品中变幻无常的身心体验与飘忽不定的心灵居所,生与死的对立和转化,爱与性的冲突和融合。这是格丽克的命运写照,是美国人的命运写照,也可说是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写照。
一、《直到》中自我身份的模糊焦虑
格丽克通过诗歌中自我身份的变化来传达其反思爱情、渴望控制身体以及体验死亡等经历。格丽克为不同的感受营造独特的情境,将自我代入其中,传递不同的自我在不同情境下的身心感受。在这一过程中,格丽克通过想象变换身份,始终在寻找真正的自我,其内心的声音也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格丽克探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主要表现在自我身份的迷失、自我身份的找寻与自我身份的回归三个方面。
首先,自我身份的迷失在该书中成为共性。爱情是使人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情感,容易让人迷失自我。恋爱中的男女既有含情脉脉时,也有冷眼相对时。格丽克通过书写现代女性面对爱情时的焦虑与彷徨等感受,细腻地刻画了现代女性的内心世界。在《直到》中,格丽克借描写妻子被迫按丈夫的想法做饭时的内心活动,来表现婚姻生活中的“被迫牺牲”,“他是要我变一个人,一个根本不是我的人,/他觉得这很简单——/把鸡剁了,往锅里扔几个西红柿”(格丽克2016:207)。爱情往往使人被迫做出改变,而这种改变很容易使人迷失自我,在为爱妥协与坚持自我的纠结中,女性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并由此使自我产生分离。
在格丽克眼中,自我是处于潜意识中的“个体存在感”。在经历爱情带来的对于自我身份的迷茫后,格丽克将目光转向自省式的身份认知,并以其青年时期与身体、灵魂“博弈”的经历来体现对自己的身份感到陌生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格丽克曾出于“建设一个可信的自我”(格丽克2017:152)的意愿,在青少年时期便开始长期节食,并最终患上了厌食症。对此,她这样描述:“但这些持续的行动、拒绝,本来是打算用来将自我与他者相隔离的,如今也将自我与身体隔离了开来”(同上)。格丽克在青年时期感受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但使自己独立于物质、贪婪、依赖的尝试未能实现,反而使身体状况恶化,引发身心矛盾以及自我身份的迷失。格丽克是这样,其笔下的人物亦是如此,“那时我的灵魂出现了。/你是谁,我问。/我的灵魂说,/我是你的灵魂,那个迷人的陌生人”(格丽克2016:66)。
在爱情带来的被动和妥协中,在对自身的执着苛刻却又适得其反的控制中,格丽克对自我身份始终持有的怀疑态度使她对多样的自我身份、自己与他人身份的关系进行了深思。一般来说,出生、成长、壮大、死亡是人类生活的普遍轨迹,死亡则代表个人身份的消失。而在格丽克的笔下,死亡与新生并非截然对立或毫不相干。在格丽克的眼里,新生是死亡的延展。格丽克出生前,她的“妹妹”(亦可视作其姐姐)不幸夭折。她在谈到这位“妹妹”时说,“我没有经历过她的死亡,但我经历了她的缺席;她的死使我出生”(Glück 127)。对这位“妹妹”的追思一直影响着格丽克对死亡、对孤独的看法。诗中“我”与另一个妹妹玩耍,听到家人呼喊自己的名字后并未应答,也未走进门廊内暖黄的光线内,尽管名字使“我”认识到自己真实存在而为“我”带来安全感。诗中的“我”具有格丽克自传性的叙述特征,“我”陪伴死去的“妹妹”玩耍,并将自己代入“妹妹”的身份中,体会她的孤独。在这一过程中,“我”的自我身份分离,原本的“我”消失,“妹妹”成为另一个自我。
其次,对自我身份的找寻成为根本。自我身份的迷失并没有使格丽克停止探索的脚步。格丽克通过精细的观察和思考,以敏感的视角通过生活中的爱情体验与亲子关系来探寻自我身份。在格丽克笔下,女性恋爱、分手、结婚、离婚的情感历程以及亲人之间紧张的代际关系被刻画得丰富而细腻,并在她找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体现出身心游离的变化状态。
在这一过程中,格丽克将自传性的爱情视角转向希腊神话故事,通过“改写”“重构”神话故事,揭示女性找寻自我身份的情感历程。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和农神得墨忒耳的女儿——珀耳塞福涅在丛林中采花时被冥王哈得斯劫持为妻。格丽克在《直到》中通过对珀耳塞福涅的一系列猜想,传递出女性面对爱情时细腻的自我身份变化状态,揭示出爱情易使人违背意志、丢掉自我身份的真相,“令人讨厌的/少女身份的斗篷依然贴着她。/在水里,太阳似乎很近。/那是我的叔叔又在监视我,她想——/自然界的每样事物都是她的亲戚”(格丽克2016:91)。被劫掠前,珀耳塞福涅在格丽克笔下是一个厌恶自己身份、因时刻受到监视而渴望爱情与自由的天真烂漫又毫无恋爱经验的少女。随后,冥王哈得斯出现,从池塘边带走了她,“从这一刻起/她再不能没有他而活着”(同上91—92)。这时,格丽克笔下的珀耳塞福涅已对哈得斯产生了依赖,在与哈得斯相恋时,她开始达到身心合一的状态,自我身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变。由此,珀耳塞福涅又怀念起逝去的少女身份,并极力找寻,但“从池塘消失的那个女孩/再不会回来。将要回来的是一个妇人,/寻找她曾是的那个女孩”(同上92)。在这期间,珀耳塞福涅的自我找寻又产生了内在矛盾: 她已为人妻,却怀念身为少女的自己。
格丽克在该作品中还通过母女关系探索身心矛盾和自我身份寻找的主题。在格丽克的眼中,最初,女儿与母亲“在某个点上的确是同一个人”(同上194—195)。自母亲怀孕到女儿拥有自我意识期间,女儿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彼时的女儿都依附于母亲。随着成长,女儿感受到个体的意识,并试图寻找自我,“她已认出这东西,这个自我,/开始珍惜它,/而现在,它将被裹在肉里,丢掉——”(同上195—196)。在女儿试图形成自我意识时,母亲仍将女儿看作另一个自己,忽视其自我意识。囿于母亲的控制与身体的不成熟,女儿无法认识到自我的身份,并为找寻自我身份而殚精竭虑,“我看到以明确的边界分隔自我、建立一个自我的方式,是让自己反对其他人已宣布的欲望,利用他们的意志形成我自己”(格丽克2017:152)。在这种找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女儿控制自己身体的愿望更加强烈,与母亲的冲突亦愈发加剧:“在她看来,身体/依然等同于她的心思,那么一致,似乎/透明,几乎如此,/而她又一次/爱上了自己的身体,发誓要保护它”(格丽克2016:196)。就这样,女儿在与母亲的相处过程中成长,她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曾经依赖于母亲,承认与母亲曾是同一人后,苦于心思成熟但无法掌控身体后,又坚定寻找身心契合的自我。
最后,自我身份的回归成为必然。经历自我身份的迷失与探寻的过程后,《直到》中的人物通过更为深刻地感悟爱情、体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而使自我身份变得清晰,自我身份回归成为必然。
在《直到》中,有关爱情的诗作丰富多样,既有前述给人带来绝望色彩的爱情诗,也不乏充满希望和憧憬的爱情诗,它们成为自我身份回归的催化剂,“他与每一个女人生活中,都将一个全新版本的自己活到/极致”(同上151)。在此基础上,格丽克进一步推演,把自我身份的迷失和自我身份的找寻抛在脑后,为身份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先认识的那个人已不复存在。/他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被她们遇见,/而相遇结束,他走开,他便随之消失”(同上152)。诗中“他”全身心地投入爱情,扮演全新的自己,在爱情结束之后,果断地离开,回归真实的自己。与上文“被迫牺牲”的妻子不同,“他”为爱甘于主动隐藏自己的身份,将每一个新的身份活到极致,且沉浸于其中。这样,爱情与身份就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爱情中蕴藏着身份,以身份促进爱情。
在《直到》中,自我身份的回归不仅体现为人们在人际交往中所选择的角色,也蕴藏在人们体察周围环境的过程中。如该作品对“蚯蚓”所描述的那样,“做不了人并没什么可悲的,/完全生活在泥土中也不会卑贱/或空虚: 心智的本性就是要守护自己的显赫”(同上216)。一个人的位置对其感受有决定性的影响。格丽克认为,对蚯蚓和人来说,心智与身份都具有统一性。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蚯蚓生活在泥土中,它的感受是泥土带给它的,蚯蚓不会因自己的生活条件而自惭形秽。人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位置,也会感知到所在位置传递的信息,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特定身份而妄自菲薄。这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中生态化的平等意识的体现,其强调所有生命的平等,认为所有生命都可以生存、发展、实现自身权利。这也正如老子所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转引自陈剑51)。
格丽克通过类比蚯蚓的生活来映射她自己和整个人类,其基于自然中的生物来呈现个人特质,体现了生态化、女性化的价值观以及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具有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特征。格丽克渴望个体的感知与身份相一致。在格丽克眼中,守护自己的思想就是心智的本性;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心智便会形成感知,从而使人真正地了解自己,这样的沉浸式生活让人的自我身份得以回归。
二、《直到》中的心理漂泊游移
在《直到》中,除了自我身份的模糊焦虑,与其相辅相成的心理漂泊游移同样值得探讨。格丽克将其对情感、死亡、内心感受等的思考寓于其心理漂泊游移的经历。格丽克渴望激发内心的形象,表达深层的感受。而生活中心灵共鸣的缺失使得格丽克在心理体验上有了更深刻的孤独感,也使得她变幻无常的心理始终游走在寻找心灵寄托的路上,并在流散的、隐藏的以及神话的三个世界中漂泊游移着。
首先,流散的世界是心理反应的共性。格丽克笔下的沉浸式爱情具有典型的流散特征。在该诗集的《夏天》这首诗中,在格丽克的笔下,爱情带来的愉悦使人迷失并进入想象的世界,进入虚幻的“漂流”中。他们放下天性与烦恼,进入忘我之境,在“漂流”中流浪,在流浪中更为惬意地“漂流”,从而领略到陌生环境中新奇的景象。而在这一奇特的景象中,他们所在的床便是漂流之圆的圆心,从而为其情感上的流散提供了避风的港湾。
爱的缺席使人流浪于心灵的归处,如格丽克在该诗集的《镜像》一诗中写道,父亲的离开使她意识到: 人一旦不能爱别人,就会在世界上消失。这就是说,一个人若没有爱的能力,便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立足之地。爱使人在世界上有所期待、有所寄托,寄托之处便是心灵的寓所。一个人若爱另一个人,所爱之人便成为他/她的生命的中心,对所爱之人的想念与依恋使心灵有了寄居之处。进一步来说,个人在表达爱的过程中也与他人、与世界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心中有爱之人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或者说,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心中无爱之人则处于流散的状态,其存在就像一朵漂浮的云,没有根基,没有固定的位置,转瞬即逝。这首诗也如“镜像”般反映了格丽克的爱情体验: 经历过两次婚姻,向往爱情却始终难以企及理想的爱情。
生死循环形成了全球圆形流散世界。在格丽克笔下,生与死并非完全的阴阳相隔,死是新生的开始,如“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在一个不同的地方,/人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后来你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上”(格丽克2016:119)。从中可以看到,格丽克关于死亡的思考是对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死亡观的革新。萨特认为,死亡是对生命意义的取消,“死永远不是将其意义给予生命的那种东西;相反,它正是原则上把一切意义从生命那里去掉的东西。如果我们应当死去,我们的生命便没有意义”(萨特654)。在格丽克眼中,死亡虽然剥夺了个人生命的意义,但是生与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是永恒变换的,人们将经历从现实世界到冥界再回到现实世界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人们始终处于无身体、无家园、无清晰意识的流散状态。同时,这种无尽的轮回也构成了全球圆形流散。
其次,隐藏的世界是心理的神秘魅力之源。格丽克的诗歌反映了诗与内心形象“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关系,这使得《直到》有着披上面纱的神秘魅力。格丽克曾说:“我并不认为更多信息总能让一首诗更丰富。吸引我的是省略,是未说出的,是暗示,是意味深长,是有意的沉默。那未说出的,对我而言,具有强大的力量”(格丽克2008:51)。格丽克的这一见解使我们想到了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的“冰山原则”——“如果一位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海明威193)。由此看来,格丽克在《直到》中所构建的隐藏世界,类似绘画中的白描手法,是用极其简洁的架构,几笔勾勒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格丽克在《直到》中寻找心灵寓所,将一个个细小而又耐人寻味的瞬间拼凑成诗中的一个故事、一段记忆抑或一个梦,促使读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寻这些被隐藏的美,正如在海边的乱石堆中寻找光滑靓丽的鹅卵石一样。
更进一步来说,格丽克在《直到》中所刻画的隐藏世界并非单层易感的,而是多层深奥的,读者需要反复细读才能感受其迷人的魅力。《直到》中这些故事、记忆或者梦传达的并不仅限于她真正想要表达的想法,更多的是揭示关于这些想法的预兆。换言之,这其中承载的不仅仅是一段段我们读到的反映事实的文字,更包含格丽克对于内心和周围世界的细腻感知与思考。在该诗集的《预兆》一诗中,格丽克写道,“我们诗人放任自己/沉迷于这些无休止的印象,/在沉默中,虚构着只是事件的预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格丽克2016:118)。这也是该诗集名字的出处,由此可见隐藏的世界在格丽克心中的重要性——它是深深埋在格丽克的灵魂最深处的。
诗人笔下的预兆只是其内心形象的冰山一角。诗人写诗,像朝平静的湖面投掷一块石子,石子落入水中的声音是轻易可感的,就像诗歌的文字;而石子入水后泛起的阵阵涟漪则是需要密切观察才能感觉到的,是容易被忽视的。这与格丽克写诗反映的灵魂深层的需要完全一致。这种对未显露的预兆的深层思考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 BC—322 BC)的诗歌理论不谋而合:“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或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81)。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应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格丽克正是通过描述现象来表达对生活的深刻思考。由此可见,格丽克通过《直到》为自己构建了一个隐藏的世界,她将内心的声音隐匿在有形可感的诗歌之下,吸引读者通过《直到》这把“钥匙”解读作品中人物丰富多彩、波荡起伏的内心世界,这些人物也因《直到》的存在而具有了隐性、含蓄的寄托。
最后,神话的世界是心理漂泊游移的升华。格丽克在《直到》中营造的神话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反映了诗人的内心形象,也更深入、更彻底地揭示了流散的世界和隐藏的世界中的事物,是心理漂泊游移的升华。
《直到》收录的诗集——《阿基里斯的胜利》(The Triumph of Achilles,1985)、《阿勒山》(Ararat,1990)以及《阿弗尔诺》等——都较多地借用了希腊神话与《圣经》中的典故。格丽克从神话人物的经历中汲取灵感,在叙述神话故事的同时,通过神话表达其在现代社会情境下的经历与思考。这正如诗歌评论家文德勒所说,“(格丽克)以沉着冷静的语气讲述了伊甸园里的男女,讲述了达芙妮、阿波罗以及神秘的动物。然而,在这些神话故事的背后却隐藏着作者萦绕于诗歌中的半透明的心理状态”(Vendler 16)。
格丽克将《直到》中女性在爱情中的被迫与压抑、女性对理想的爱情的呼唤、对死亡的感知以及内心挣扎矛盾的声音寓于神话,并通过神话世界这一奇异的视角,寻找心灵的安放之处。在《直到》的神话世界中,格丽克笔下人物的内心形象得以完整呈现,他们的所思所想和身心变化借神话人物得以完全表现出来。因此,神话世界成为最佳的心灵寓所。与此同时,读者透过格丽克所改写的神话,与内心深处的思考产生共鸣。因此,格丽克的《直到》在具有自传性的同时“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因而具有了全球性意义。
《直到》中人物的心理一直在流散的世界、隐藏的世界以及神话的世界中漂游,其圆心是心灵的寓所。围绕这一圆心,格丽克进行了由浅入深的层层探寻;随着内心形象逐渐清晰,格丽克的心灵寓所也随之显现。在流散的世界中,《直到》中人物的心理在情感与生死循环中处于不同的位置;爱情带来愉悦后的迷失感,寻爱无果时灵魂无所寄托的状态,生死循环中无家园、无身份的状态都体现出诗人的身心处于彷徨无依中的流散之路上。在隐藏的世界中,格丽克借助含蓄的诗歌传达内心形象的“预兆”;那些未曾言说的弦外之音因诗歌有迹可循,原本漂泊无依的心理体验也因诗歌这一载体而有所寄托。而在神话世界中,《直到》中人物的心理感应被寓于神话中,通过改写神话人物形象、描写人物内心状态而发出灵魂深处的声音。
结语
全球圆形流散贯穿《直到》的始终,是其核心特征。《直到》所揭示的男女主人公们在环境变化中寻找自我身份,在流散状态中寻找心灵寄托。格丽克在该作品中从自己的视角探究各色人等的身心历程,并通过他人的身心历程挖掘并审视真正的自己。在深入的自我剖析中,我们感受到格丽克对自我身份的迷失、找寻和回归的丝丝入扣,对流散、隐藏与神话三个世界的魂牵梦系,并通过把它们升华到生死的高度而将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样一来,作者所揭示的《直到》中的主题——自我身份的模糊焦虑与心理漂泊游移——既是现实的也是虚幻的,既是自我的也是他人的,既论述身体也论述心灵,既涉及生存也涉及死亡,成为典型的全球圆形流散写照。《直到》所揭示的命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发人深省,它不仅属于该作品中的人物,更属于全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