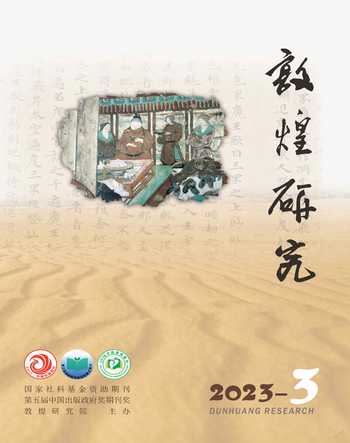哈密大像窟遗迹新探
2023-07-13罗尔瓅魏文斌
罗尔瓅 魏文斌



内容摘要:开凿大像窟是哈密地区佛教建筑、造像艺术的突出特征。哈密现存大像窟遗迹主要集中在今哈密东部、天山南麓的庙尔沟佛寺遗址,本文对其形制、造像题材、窟内装饰、营建背景等分析后认为,庙尔沟大像窟始建于唐安史之乱之前,与唐代大规模经营西域战略有紧密的关联。唐代中原地区的弥勒信仰经河西走廊向西域传播在哈密留下痕迹,遂使哈密大像窟既融合了龟兹大像窟的形制特点,又与中原佛教信仰、塑造弥勒大像以及河西弥勒造像风格一脉相连。
关键词:伊州;庙尔沟佛寺;大像窟;弥勒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3-0098-12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Remains of the
Large Buddha Caves in Hami
LUO Erli WEI Wenb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Buddha caves together with statues of a sitting Maitreya Buddha wa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Buddhist architecture of the Hami region. The extant remains of the large Buddha caves of Hami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Miaoergou Cave Temple site located in the east of Hami, and at the southern foot of Tianshan Mountain. By analyzing and studying the form, themes, dec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history of the cav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large Buddha caves at the Miaoergou site were built prior to the An-Shi Rebellion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ang dynasty's strategy of managing the Western Regions on a large scale. The Tang dynasty belief in Maitreya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spread westwards along the Hexi Corridor and left its traces in Hami, which led to both an integration of the form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rge Buddha caves from Qiuci (Kucha), and an inheritance of the style of Maitreya statuary from the Hexi and Central Plains regions.
Keywords:Yizhou; Miaoergou Cave Temple; large Buddha cave; Maitreya
佛教洞窟形制中,大像窟是規模宏伟、体例最大的一类。窟内一般于主室正壁造一尊或站立或倚坐或结跏趺坐的大佛,空间整体庄严伟岸,我国新疆、甘肃、山西、陕西、河南等地都存有不同时期开凿的大像窟。新疆的大像窟主要集中在古代龟兹地区,学界已多有研究,现存于哈密的大像窟遗迹则关注不多。哈密的大像窟主要发现于庙尔沟佛寺遗址,虽其洞窟及窟内造像损毁严重,但从遗址规模和残留的造像痕迹仍可看出这些洞窟内原塑有十余米高的佛像,其形制应属大像窟。本文旨在从庙尔沟大像窟的形制、造像题材、营建特点等方面着手,对其开凿背景、宗教信仰、始建年代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 哈密庙尔沟大像窟现存遗址考察刍议
哈密在历史上先后称为伊吾卢、伊吾、伊州。从文献资料看,唐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敦煌文书《沙州伊州地志》等史料中存有反映伊吾佛教活动的零星记载。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
(玄奘)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出迎,抱法师哭,哀号哽咽不能已已,言:“岂期今日重见乡人。”[1]
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
(伊吾县)寺二:宜风、安化;……(纳职县)寺一:祥麰,尼。[2]
随着近现代考古调查的开展,在哈密庙尔沟佛寺遗址和拉甫却克古城外的佛寺遗址中陆续发现了一些大像窟遗迹。20世纪早期至今的100余年里,先后有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和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以及新疆考古所、西北大学考察团队等在此进行过考察调查。斯坦因调查较早,其报告载此处分布五座大像洞窟,自西向东排列,依序编号为AⅢⅰ—AⅢⅴ[3]。西北大学在调查时认为斯坦因编号AⅢⅰ的洞窟应为房址,于是对洞窟进行了重新编号[4]。笔者2019年对庙尔沟佛寺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认同斯坦因对大像洞窟的认定,同时形成了一些新看法。为便于研究叙述,笔者将洞窟自西向东编号为K1至K5(表1)。
(一)庙尔沟大像窟开凿位置及其独特之处
新疆的大像窟多居高占据着山崖的突出位置,并与其他形制的洞窟交织错落分布于崖壁一面。这样的位置彰显着大像窟高大庄重的地位,达成了大佛像遥望远观的效果。庙尔沟大像窟是庙儿沟佛寺遗址中僅有的洞窟,开凿形态呈现出一些独特之处:
其一,洞窟组合类型单一。庙尔沟五窟东西相邻,其间或周围少有其他形制的洞窟分布,这种连续相邻开凿大像窟的布局在新疆其他石窟寺中还未曾见到{1}。
其二,大像窟选址的山丘整体高度不如其他石窟寺所在山体那样高耸,五窟都开凿于近地位置(图1)。
其三,五窟形制皆为上圆下方的穹隆顶洞窟。主室平面近正方形,从建筑技术的角度来说,方形的下层基础是上层发券为半球状穹顶的先决条件之一。K2—K5,穹隆顶与主室方圆衔接处皆以突角拱穹隅过渡,形状近似弧边三角形,这是上圆下方的穹隆顶佛殿的典型内部特征。
在哈密,现存的几乎所有的穹顶寺院建筑内部的方圆衔接处的四角都以突角拱穹隅作为过渡。
(二)五窟形制及其分类
庙尔沟五座大像窟内造像皆已残毁,参考西北大学团队调查时测量的主室正壁残高以及塑像残迹判断,窟内主尊高度皆应在10米以上。其中造像最高的在K5,至少在12米以上。斯坦因在调查时也发现K5要高于其他洞窟,西北大学的数据与之相合。
K1和K2为平面呈方形的穹隆顶洞窟。K1位于山脊最西侧,仅残留部分北壁及东壁,窟内整体布局已塌毁难辨,正壁前似有低矮的佛坛痕迹。斯坦因的报告中记载该窟原为穹隆顶洞窟,主尊紧贴北壁(正壁),造像背后无甬道[3]29。K2位于K1东侧,穹隆顶至今可辨,北壁尚可见残缺的圆形头光及舟形背光。北壁上部残存数个凿眼,内嵌有木构件,应是用于固定大佛的构件,北壁下部未见此类痕迹。
K3居于五窟的中心,系前后室结构的大像窟。主室为穹隆顶,北壁前残存方形坛基,原塑大佛。大佛身后有通顶背屏,背屏后修有一条狭窄的后甬道,与大佛左右两侧甬道口相通。西北大学在实地考察中,观察到K3坛基下的偏东位置有一圆拱形洞穴,并在报告中指出此洞原本很深,洞内存有壁画,开凿原因有待清理发掘[4]12。笔者倾向于此处为一处甬道出口,甬道现已塌陷,仅可看到尚未完全掩埋的甬道口。斯坦因报告中关于窟内有环绕大像的“回廊”的记载[3]29,此甬道口当可与之对应①。
K4中同样可以看到佛像腿部两侧暴露出的两个呈半圆形的洞口,西北大学报告认为此两处原系圆拱形佛龛[4]16。鉴于斯坦因在考察日记中已说明K3、K4和K5主尊背后都有甬道,因此笔者认为这里也应是两个尚未被完全掩埋的甬道出入口(图2—3)。K5的甬道口应被掩埋,今已不可见。
综上描述,笔者将庙尔沟大像窟从形制上分为三类(表2)。
A类:K1、K2。方形穹隆顶洞窟,主室正壁有坛基,其上塑像。
B类:K3。由前后室组成的穹隆顶洞窟,后室(主室)正壁建有坛基,其上塑倚坐大佛,大佛背部是通顶的背屏,围绕大佛有绕行的甬道。
C类:K4、K5。方形穹隆顶洞窟,主室正壁有坛基,塑倚坐佛像,围绕坛基有绕行甬道。
在新疆地区,龟兹是一处大像窟的集中开凿地。宿白先生通过对龟兹石窟的研究认为,开凿大像窟和雕塑大型立佛是龟兹佛教艺术的一个特点,之后影响到葱岭以西的巴米扬和新疆以东的云冈[5]。哈密地处龟兹东向输出其造像影响力的传播线路上,庙尔沟K3、K4、K5在形制上有明显的龟兹中晚期大像窟的特点:即以大像作为前后室的分界,主尊两侧是甬道的出入口,后室简化为狭窄的后甬道,与左右甬道相通。这种形制的大像窟在本质上是中心柱窟的一种,高昌石窟寺中也开凿有中心柱大像窟,应都受到了龟兹大像窟的影响。庙尔沟大像窟的特殊之处在于窟内主尊不再是龟兹样式的立像,而是坐佛。K1与K2的洞窟形制在龟兹的大像窟中尚无类似,甬道的消失则可能是一种简化,反映出窟内礼拜方式的改变。
(三)窟内造像或皆为倚坐佛
斯坦因考察后认为五座洞窟内各有一尊巨大的佛像[3]29。综合西北大学的调查研究和笔者的实地调查,以坛基、主室正壁残留头光、背光以及凿孔等作为判断大佛位置及形态的依据,目前基本可以认为除K1以外,其他四窟内主尊佛像皆坐姿。K1塌毁严重,难以判断造像形态及题材。
K2正壁残存非常明显的舟形背光及圆形头光。曾有学者对莫高窟和克孜尔石窟中的舟形背光进行研究,认为舟形背光在莫高窟多出现在坐佛背后,在克孜尔多出现在立佛背后[6]。正壁上方可见用于固定大佛的凿眼,但下方却不见类似痕迹。北壁下部原是与墙壁一体的佛坛,根据窟内残迹目测,坛基高度约占北壁的三分之一,这个高度建造的更有可能是坐佛,坐姿可能为倚坐或结跏趺坐(图4—5)。
K3主尊为坐佛。正壁前残迹可辨明佛身、佛头位置,佛头后方还残留头光痕迹。佛像似倚坐于坛基上,目测坛基高度约占正壁残高的三分之一左右。西北大学调查时发现正壁前还可见疑似大佛右腿的残部,由此推断主尊是倚坐弥勒佛[4]10,本文认同这一观点。大佛上半部、略靠东的位置有两个倾斜排列的圆洞,西北大学认为圆洞有安插木楔固定泥塑之用,本文进一步认为其作用或在于固定大佛胸前手印(图6—7)。
K4残存造像痕迹不多,仅正壁前留有比较明显的坛基,坛基较高,在这样的坛基之上再修建大型立佛的可能性不大,其上原应有倚坐或结跏趺坐的塑像。
K5正壁前可见坛基和倚坐大佛的右腿残部,正壁上部残留部分头光,头光高度与倚坐佛的头部高度相符,这些残迹较清晰地说明窟内主尊为倚坐弥勒佛(图8—9)。
庙尔沟大像窟的造像中虽然有倚坐的弥勒佛像,但是对于五窟的造像组合及其佛理上的意义尚难定论。弥勒信仰风靡于唐,如果将东都洛阳视为弥勒大像的发源地[7],龙门石窟出现了大量弥勒造像,但早期尚无将弥勒作为主尊供养、单独开龛的现象。唐高宗之前弥勒造像规模不大,其高度没有超过2米以上的。但是唐高宗后期、武则天执政时期,龙门出现了独立开龛供奉弥勒为主尊的新形式,且造像的规模也不断增大,还发展出以弥勒居中的三佛题材。看来新的供奉方式虽然传至哈密,不过三佛造像组合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庙尔沟五座大像整体布局的含义,遂使五座大像呈现为一种独特性。倚坐的弥勒造像表明弥勒下生信仰曾盛行于哈密。
(四)窟内装饰构造体现了东西方元素在佛教建筑中的融合
笔者调查时发现,庙尔沟大像窟除K1之外的其他四窟的穹隆顶与四壁相接的四角皆凿出贝壳形圆拱浅龛。斯坦因报告中也提及这种构造,他稱之为“方形墙壁四角安置的很薄的突角拱”[3]29。这种装饰造型还见于敦煌莫高窟五代、宋时期的一些洞窟,如第55、152、98、61、454窟等(图10)。
庙尔沟大像窟与莫高窟部分洞窟中出现的浅龛在视觉上极为相似。它们形状接近,都出现在主室顶部与四壁的交汇处,表面绘有壁画。据斯坦因记载,K2贝壳形浅龛上“残存较早的花卉图案装饰痕迹,其风格均与千佛洞中见到的相似”[3]29。K3窟顶东北角的浅龛内似绘制人物一铺,西北大学认为是结跏趺坐的佛像,斯坦因则称“龛内可辨认出护世天王的形象”[3]29。笔者调查时,该图像的头部彩绘已脱落,仅在头部下方残留以红绿色为主的图案,似天王的腰带或鹘尾。
庙尔沟大像窟与莫高窟部分洞窟所见贝壳浅龛的一些异同不容忽视:
第一,它们所处的建筑环境不同。莫高窟是内嵌于山体的洞窟,而庙尔沟大像窟却并不完全是在山体内开凿的,这些洞窟的顶部都高出其所在山体,呈一种“半开凿半筑砌”的构建特点;
第二,莫高窟的浅龛是四壁与覆斗顶之间的连接,洞室底部平面为长方形,而庙尔沟大像窟的浅龛连接的是穹隆顶与四壁,洞室底部平面近正方形。
重要的是这些差异表明此两地的浅龛,并非同一类建筑构造,所采用的建造技术也不尽相同。这种被描述为贝壳形浅龛的构造,又称为突角拱穹隅,是伴随着在非圆形平面上砌筑穹隆顶技术而出现的,它改变了早期穹隆顶下只能衔接圆形平面的状况。方底穹顶建筑的源流虽学界说法不一,但其建造技术来自于外域是较为明确的[8]。庙尔沟大像窟内四角穹隅结构,正是中亚方底穹顶技术运用的结果,其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建筑角度的构造需要。而莫高窟覆斗顶之下出现的形似突角拱穹隅,则不属于同种建筑技术。学者徐永利曾指出,莫高窟洞窟中的覆斗形窟顶四角下接贝壳形浅龛的结构,从砌筑结构角度看是不需要的,这仅仅是一种壁画艺术表达的需要[9]。笔者进一步认为,莫高窟覆斗顶与突角拱穹隅的组合,是继承了汉地工匠所创的“四阿顶”建筑风格,其中也许运用了一些域外砖券技术,但是其建筑理念本质是本土的。庙尔沟大像窟出现的突角拱穹隅则很好地或更多地体现了东西方艺术元素在哈密佛教建筑中的融合。
二 庙尔沟大像窟营建方式及礼拜空间设计
庙儿沟大像窟“半挖半砌筑”的营建方式及其礼拜空间设计表现了其自身存在的一些布局和功能特点。
(一)庙尔沟大像窟的营建方式
大像窟皆采用减地留墙与土坯砌筑相结合的方法修筑。即先依崖面下挖出洞窟的下半部分,之后沿四壁向上垒砌土坯不断收拢,最终形成一个高于崖面的穹隆顶结构。土坯间抹填黄土与沙砾搅拌而成的灰浆。窟内大佛同样以减地留墙和土坯砌筑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下挖洞窟时预留佛像躯干,再以土坯砌筑头部,后于表层涂泥整塑,最后进行塑绘[4]10-16。
以土坯砌成的穹隆顶建筑在哈密佛教遗址中非常多见,除庙尔沟这几处洞窟外,哈密现存的一些佛殿遗址也都是以土坯砌出穹隆顶的造型。庙尔沟大像窟的穹隆顶高出山体,具有“半挖半砌筑”的建筑特点,使大像窟呈现出佛殿与洞窟相结合的视觉体验。这种修筑方式是“因地制形”的结果,原因在于开凿洞窟的山体不够高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安置大佛需要的洞窟深度和高度要求。
比较龟兹和庙尔沟两地大像窟的营建方式后发现,龟兹的洞窟是从崖面向内开凿而成,主室顶部为纵券顶,无土坯砌筑构造;另外,窟中的大像是木骨泥胎。哈密庙尔沟的大佛则是在开凿洞窟时下挖出佛像的骨干,后以土坯打造出佛像的身躯和头部。这种差异的出现除了因地制宜的客观因素外,也应与在两地传播和接受的佛教造像技艺有关。
(二)庙尔沟大像窟的信仰空间及寺院的礼拜方式
犍陀罗是塑造佛像的起源地,公元5世纪,大型塑像堂和大型佛像已广泛流行,大佛像多为地面寺院中的立像[10]。从犍陀罗到西域再到中原诸地,大佛礼拜的空间发生着由地面寺院转向石窟寺院的明显变化。
大像窟的礼拜空间一般可分为洞窟外空间和洞窟内空间。庙尔沟大像窟在空间规划上是以内部为主要礼佛空间的。五座洞窟的开凿位置相对偏低,人们在距离较远时仅能看到高大洞窟的外观,难以看到窟内的大佛,重要的礼佛活动唯有进入洞窟后才能举行,而其所在的近地位置则正好方便了人们的出入和聚集。
五窟的内部空间布局不尽一致。居中的K3功能最为完备,有前、中、后三个功能区,分别对应前室、主室和后甬道。笔者调查时其前室已经塌毁,但仍然能够感受到其空间可以供多人聚集;前室与主室经甬道相连,主室正壁大佛是整个洞窟崇拜的主体,正面空间相对宽敞,信徒可驻足于佛前礼拜。佛像背面后甬道与左右两侧甬道围合成一个可右旋绕行的“凹”型甬道,反映了佛塔崇拜向佛像崇拜的变化。K4和K5没有前室,窟内的聚集功能有所减弱,礼拜空间由主室和甬道组成。K1和K2空间变的既无前室,也无甬道,信徒仅可于像前礼敬观佛。
从K3到K4、K5再到K1、K2,洞窟形制逐渐简化,礼佛方式和礼佛空间也相应趋于简化。笔者认为,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五窟极可能开凿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造像时的佛教流行背景也有所不同。五窟中最早建造的应是K3、K4和K5,这三窟都具备绕行的通道,满足绕塔右旋礼拜的需求。在佛教发展过程中,塔崇拜是早于像崇拜的,庙尔沟前三窟的大佛和绕行的通道并存的现象应该是塔崇拜向像崇拜过渡的产物。在这之后的某个时期才营建了K1和K2,这两窟从形制上看已经完全脱离了绕塔的礼佛方式,礼佛方式发生的这一明显改变或指向五窟开凿时期的不同。
整体上,五窟的设计有别于云冈昙曜五窟“洞窟空间为大像服务”的设计思路[11]{1},庙尔沟大像窟内的空间布局与大像主体同样重要。虽然大佛依旧是崇拜主体,但这五窟绝不只是为了容纳大像而修筑的半封闭空间,它还透露出庙尔沟佛寺在不同时期内信仰的流行情况及寺院规模的演变与发展的一些信息。寺院在建造伊始应规划实施了大像窟K3、K4、K5的开凿,洞窟由南侧嵌于山体,僧房和佛殿则分布于山顶及山的北坡,另有僧房、小型佛殿依山而建,后期又规划了K1及K2。大像窟及其所在山体顶部的僧房和小型佛殿共同组成了庙尔沟佛寺核心部分,这个部分功能逐步完备,构成了一座兼具礼佛场所加修行居所的寺院。山脚下的大像窟是寺院组织重要活动的主场所。随着僧人增多,寺院中增修了僧房和佛殿,寺院的规模得到不断扩展,礼拜功能也更趋完备。
三 庙尔沟大像窟营建年代问题
学界对庙尔沟大像窟的营建年代尚无明确结论。现存遗迹现象和文字资料皆缺乏指向洞窟始建年代的直接依据。本文试从考古类型学及历史背景两方面予以探讨,并进一步阐述其与中原弥勒造像的关系。
(一)借助考古类型学方法探讨庙尔沟大像窟的开凿年代
龟兹大像窟与庙尔沟大像窟的造像题材明显不同,但是不可忽视这两地大像窟具有的相似性。国内最早对龟兹大像窟进行类型学分析与考古测年的学者是宿白先生。以克孜尔石窟为例,宿白先生将其开凿营建年代大致归为三个阶段[5]24:前两个阶段是克孜尔石窟开凿的繁盛期,其典型特征是大像立于中心柱前壁正中,信徒沿甬道右向绕行礼拜,体现着佛塔崇拜和佛像崇拜两重含义;第三阶段及其以后,克孜尔石窟的开凿虽已日趋衰微,但仍有少量大像窟的开凿,大像窟中已无中心柱,主尊是紧贴前室后壁塑造的立佛,立佛的腿部成为前后室的分界线,信徒于洞窟内右绕大像完成礼拜。
将庙尔沟大像窟的窟型与克孜尔各时期大像窟进行对比后发现,庙尔沟K3、K4、K5在形制上更接近克孜尔第二、三阶段开凿的洞窟,主要体现在主室内无中心柱,主室正壁的坛基及其上坐佛成为前后室的分界,围绕主尊有繞行甬道。不同之处是庙尔沟洞窟主尊造像为坐佛而非立佛,这反映了哈密本地流行的佛教信仰对造像题材的影响。
李瑞哲先生的研究中,将克孜尔石窟的大像窟形制划分为三类[12]:第一类大像窟形制上与中心柱石窟类似,主要开凿于克孜尔石窟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二类大像窟中已无中心柱,洞窟分前后室,以立佛作为前后室的分界,有绕行立佛礼拜的甬道,洞窟的后室已简化为后甬道,有明显的佛像崇拜性质;第三类大像窟仅第60窟一例,出现基坛、通顶的背屏等结构特点,李瑞哲先生认为这种大像窟建造时间较晚,约属于第三阶段开凿的洞窟。庙尔沟K3、K4、K5于主室正壁建造坛基、其上塑倚坐佛像的大像窟在形制上相应于李瑞哲先生所列的第二类及第三类洞窟。既然庙尔沟大像窟的形制与克孜尔中、晚期大像窟最为接近,那么两者在建造时间上应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表3),或是一种不易中断的“时代性”关联。虽然仅凭洞窟形制的对比,难以对庙尔沟大像窟的始建年代做出准确的判断。
斯坦因曾以庙尔沟大像窟内的壁画装饰残片与莫高窟千佛洞晚期洞窟内的壁画图案极为相似推测庙尔沟佛寺遗址的年代应为回鹘统治时期(9—12世纪)[3]31。笔者认为,凭此一点便认为该寺院始建于回鹘时期依据不足,其表层壁画也有可能是回鹘时期的重绘。虽然目前还无法以考古材料证明庙尔沟大像窟在历史上是否有过重修的情况,但是在吐鲁番、吉木萨尔、焉耆、库车等地发现的高昌回鹘佛教寺院遗迹,均属早期开凿而沿用至高昌回鹘时期,并不是高昌回鹘始建的[13]。庙尔沟大像窟即使呈现出一些高昌回鹘佛教寺院的特点,也有可能类似这类情况。
西北大学报告认为大像窟的开凿年代应该在8—10世纪[4]64,笔者认同这一年代上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政治历史背景给出将年代上限进一步提前的看法。
(二)稳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官道的畅通是哈密大像窟开凿的基本条件
自贞观四年(630)唐朝设西伊州开始,这一地区先后发生了包括与突厥、回鹘、吐蕃等势力的交战和管辖交替,在归属问题上几易其主,除了隶属于唐中央政权之外,伊州还曾归附于一些民族政权或地方势力,如吐蕃政权、归义军政权及西州回鹘政权[14]。因此,辨明伊州归属问题及各个政权在伊州存续的时间长短,对该地佛教遗址的断代研究很有意义。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朝攻灭东突厥汗国,唐始设西伊州。贞观八年(634),唐改西伊州为伊州,正式开始了对伊州的统治[15],伊州进入一段政治、社会较为稳定的历史时期。
安史之乱(755年)爆发,伊州稳定的政治局面逐渐被打破,直至伊州陷落于吐蕃,唐朝统治结束。吐蕃在伊州持续统治了近百年,其风俗、文字也与汉地出现了不同[16]。
大中四年(850),张议潮归义军收复伊州,在伊州复设刺史以治之,迁沙州民户充实其地[17]。
咸通七年(866),西州回鹘政权建立,天山东部南北统一于高昌回鹘,咸通八年(867),纳职回鹘占领伊州{1}。乾符三年(876),高昌回鹘消灭纳职回鹘,吞并伊州{2}。此后,伊州进入延续四百年之久的回鹘化时期[16]237。
从各政权在伊州统治期的长短来看,唐中央政权统治期、吐蕃统治期和西州回鹘统治期是最有可能开凿大像窟的。归义军政权虽然存在了约170余年,但其对伊州的有效统治仅有十余年。结合庙尔沟大像窟与中原相一致的造像题材、河西地区弥勒大像的分布情况及开凿年代相关因素等分析,笔者提出庙尔沟大像窟后三窟K3、K4、K5更可能开凿于唐代国力强盛、在伊州统治力度最强的阶段,故其开凿造像年代在唐安史之乱即公元755年以前是大概率事件。
从社会发展逻辑角度看,开凿大像窟,工程量巨大,建造周期长,若没有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持续支持,建成如此规模的大像窟是难以实现的。自唐贞观四年起的130余年间,伊州社会得到稳定发展,中原流行的倚坐大佛风尚在统一的政治环境下经河西走廊影响到伊州的佛教寺院,庙尔沟大像窟的开凿与落成,正是这段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宁、民商殷实、文化发展的重要印证。
伊州虽是西域的门户,但自汉代起,伊吾与中原之间的联系时通时断,伊吾路只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之一。隋时伊吾郡设立之后,伊吾才成为与高昌、鄯善并重的西域门户。到了唐代,伊吾路逐渐成为伊州与河西走廊之间的官道,伊州作为连接西域的军事重镇和交通要塞的意义才愈发凸显[18]。据《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伊州”载:“伊吾……东南至上都四千四百三十里,东南至东都五千一百六十里,西南至西州(高昌)七百三十里,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晋昌,今安西东南,玉门镇正西)九百里,正南微东至沙州(敦煌)七百里。”[19]此时,伊州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伊州与丝路北道、南道、中道皆相通。道路的畅通必然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庙尔沟大像窟的集中开凿显然成为伊州沟通河西走廊之“官道”的生动场景之一。从这一背景可得出结论:庙尔沟大像窟的始建年代,不应早于伊州成为沟通西域的“门户”之地的年代。
四 庙尔沟大像窟与中原弥勒造像的密切关系
前文已论及庙尔沟大像窟K3与K5中主尊极可能是倚坐弥勒佛的问题。除了庙尔沟大像窟外,哈密三堡的白杨沟佛寺遗址中也发现一尊大型倚坐造像,仅残存下半部分,塑于一座大型佛殿的后室。这是新疆地面佛寺遗址中仅存的一尊倚坐大佛造像,因其姿态多被认为是弥勒佛。
弥勒造像是探求庙儿沟大像窟开凿时间的又一判断因素。这三处倚坐弥勒造像遗迹说明,古代哈密曾流行弥勒下生信仰。季羡林先生曾指出,新疆许多地方流行弥勒信仰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是印度佛教东传的首达之地,传布最集中的地区是龟兹和焉耆。克孜尔、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石窟中多铺弥勒菩萨说法图皆反映出弥勒上生信仰的流行程度[20]。哈密倚坐弥勒造像所代表的弥勒下生信仰与新疆其他地区流行的弥勒上生信仰的佛教文化源流不同,这或许是因为弥勒上生信仰多为佛教僧团内部信仰,而弥勒下生信仰则深入民间的缘故,二者之间的不同是佛教出世与入世两种信仰观不同的体现[21]。本文认为,庙尔沟倚坐弥勒的造像题材更可能来自于哈密以东的河西地区,是中原佛教文化沿丝绸之路回传的结果。
日本学者宫治昭在其《涅槃与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一书中写道:“很多弥勒大佛的建造都是以皇帝崇拜为背景,在依靠皇帝权力和财力的情况下完成的。”他还认为河西地区及丝路沿线弥勒大佛是一种造像式样由外向内的输入,其源头可追溯至北印度陀历的弥勒菩萨立像[22]。基于此认识,哈密倚坐弥勒造像的源头,似也可以向西溯源。但是罗世平对唐朝多地出现的弥勒大佛的来源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一种造像样式的流通多是由政治文化中心向外传播推广的,唐朝弥勒大佛的营造并不是沿印度到中国这一佛教早期传播路线而出现的,而是以皇帝崇拜为背景、在皇权和财力的推行之下建成,整体上形成了以洛阳、长安为中心,逐渐向各州郡辐射的传播模式[7]42。笔者认为,哈密的弥勒大像窟符合这一传播规律,与河西地区弥勒大像一脉相连。
哈密以东距离最近的弥勒造像遗迹分布在今甘肃瓜州塔儿寺、榆林窟和敦煌莫高窟。据李正宇、惠怡安等学者考证,塔尔寺北朝称阿育王寺,北周被毁,唐武周时期在原阿育王寺的基础上重建,改称大云寺[23-24]。贞观三年(629),唐玄奘西行求法曾停驻该寺,并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1]13。由此可知玄奘西行时,这里已供奉有弥勒大像。榆林窟第6窟为唐代始建,主室东壁通顶塑倚坐大佛,高约23米,是榆林窟第一大佛[25],反映弥勒信仰曾在瓜州流行。
敦煌莫高窟北大像是建于武周延载二年(695)的弥勒大佛,通高约43米,系敦煌阴氏一族迎合武周朝廷而建的。贺世哲先生推测北大像可能是敕建于沙州的大云寺[26]。莫高窟南大像系开元年间所建倚坐弥勒大像,高26米,从开凿到建成,历经30余年,既是开元、天宝时期国力强盛的象征,也是敦煌地区弥勒信仰盛行的体现。
除瓜州、敦煌以外,唐代营建的弥勒大佛还出现在甘肃炳灵寺石窟、天梯山石窟、大象山石窟等地,这些遗迹说明中原的宗教政策力度很大,河西地区弥勒信仰及开凿弥勒大像之风盛行,与东都洛阳弥勒大佛的建造密切相关。既然唐代沙洲有开凿弥勒大像窟以示边地忠孝之心,那么伊州有可能也效仿了这种举动。伊州地理位置与河西走廊接壤,在公元630年之后,唐朝弥勒信仰在这种大一统的政治生态下传播到伊州应为当然。武则天推行的一系列宗教策略,成为敦煌、伊州甚至西陲碎叶城建造大云寺的政治推动力。久视元年(700)八月,武则天还下令“敛天下僧钱作大像”[27]。这些造像既可能建于地面寺院中,也可能内嵌于洞窟之内;既有新建,也有在过去旧寺基础上的改建。虽然目前尚缺少资料证明哈密白杨沟佛寺系武周时期敕建的大云寺,但是这种可能性或可备一说。不论是出现在庙尔沟的洞窟内,还是修建于白杨沟的佛殿中,都应视为唐代弥勒下生信仰由中原向西传播的印证。
五 结 语
哈密庙尔沟佛寺遗址中的大像窟既具备龟兹大像窟的形制特点,又在造像题材上与中原弥勒大像一脉相通,是佛教文化沿丝绸之路双向传播的结果,也是不同地域的佛教艺术元素在哈密融汇一体的体现。龟兹虽是大像窟的发源地,但或较少直接对古代哈密发生影响,其传播路径应当是南北朝时期先由龟兹抵达平城,在中原历经了一个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发展阶段后,于唐代作为大规模经营西域的一部分由中原西传至哈密的。在造像题材上,庙尔沟大像窟直接受到了中原佛教文化西传的影响:
其一,目前所知的哈密以西的大像窟中,其主尊皆为立像,尚未有一例主尊为坐佛的大像窟;
其二,哈密以东的甘肃、陕西、河南、四川等地,都发现唐代开建的主尊为倚坐弥勒佛的大像窟,造像题材与哈密大像窟部分一致;
其三,唐代大一统的政治背景推动了弥勒造像之风向西域的渗进,哈密地区入唐后社会稳定以及丝绸之路交通便利等因素皆使开凿大像窟成为可能。
综合洞窟形制与造像题材特征以及社会政治历史背景诸因素,本文认为庙尔沟大像窟开凿于唐代,大约在公元755年之前,其上限应晚于公元690年。
日本学者长廣敏雄曾针对云冈石窟大像窟提出过一种认识,即“巨像是纪念碑性的造像,巨像不是为一个个体,而是为一个族群、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存在的”[28]。其揭示的大像窟开凿活动与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关系,具有较普遍意义。在古代哈密这样一个胡汉杂居之地,佛教是当地居民长期的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因此在洞窟营建者那里,政治意义先于佛教信仰,理性成为他们首要考虑的内容。庙儿沟佛寺不仅是一处宗教场所,还是一处以寺院为依托的集政治性、宗教性、文化性于一体的文化活动中心,其规模或逐渐由最早的佛教洞窟发展扩大为包含佛殿、洞窟、僧房等的大型寺院聚落,由此成为该地区独特的文化景观。
{1} 有一种说法,认为庙尔沟开凿的洞窟自东至西排列,原有7座,现仅剩5窟。详见哈密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处《民族宗教志》编辑室编《哈密地区民族宗教志》,第180页。但本文认同斯坦因的看法,他的调查年代最早,遗址保存状况也应更加完整。
{1} 2022年笔者再次前往庙尔沟大像窟实地考察,恰逢大像窟的遗址保护施工正在进行。K3主室正壁后的甬道完全呈现,印证了早期斯坦因的记载和笔者的前期判断。
{1} 彭明浩认为,昙曜五窟的设计思路以五座大佛为核心,并不强调洞窟空间,只为雕琢大像,未完全安排洞窟内的礼拜空间,人们主要是在外礼拜。
{1} 敦煌写本P.2962《张议潮变文》记载:“敦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这是一支存在于在伊州西部与归义军敌对的回鹘势力,学界称其为“纳职回鹘”。付马认为,至晚到大中四年,纳职回鹘便盘踞于今拉甫却克古城,之后多次以纳职城为据点侵扰伊州,与归义军争斗不断,张议潮曾于大中十年(856)讨伐纳职回鹘,但并未攻下纳职城。据《敦煌变文集》记载,回鹘人战败之际“各自仓惶抛弃鞍马,走投入纳职城,把牢而守”。见王重民《敦煌变文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15页。
{2} 高昌回鹘夺取伊州之前,伊州属于哪个政权,学界有不同观点。当时,与归义军政权并行的还有依附于吐蕃的回鹘势力、河西回鹘、纳职回鹘。争议较多围绕在归义军政权和纳职回鹘政权之间。荣新江认为高昌回鹘从归义军政权手中夺去了伊州,钱伯泉认为是从依附于吐蕃的回鹘势力夺去了伊州。李军认为在高昌回鹘占领伊州之前,其地所属的政治势力是河西回鹘。努力牙·克热木、杨富学、葛启航《高昌回鹘取伊州及与沙州归义军政权之关系》(敦煌研究2020年第2期第99页)则认为纳职回鹘攻陷原属归义军的伊州。
参考文献:
[1]慧立,彦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8.
[2]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67-68.
[3]奥雷尔·斯坦因. 西域考古图记:第4卷[M].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9-30.
[4]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文物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三师黄田农场. 新疆哈密庙尔沟佛寺遗址考古调查报告[J]. 西部考古,2011(第5辑):6.
[5]宿白. 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M]∥宿白. 中国石窟寺研究.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7.
[6]顾虹,卢秀文. 莫高窟与克孜尔佛教造像背光比较研究[J]. 敦煌学辑刊,2014(4):122.
[7]罗世平. 天堂法像:洛阳天堂大佛与唐代弥勒大佛样新识[J]. 世界宗教研究,2016(2):29.
[8]常青. 两汉砖石拱顶建筑探源[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3):291-294.
[9]徐永利. 汉地砖砌穹窿起源刍议[J]. 建筑学报,2012(1):49.
[10]陈晓露. 大佛像源流刍议[J]. 敦煌研究,2012(3):15.
[11]彭明浩. 云冈大佛礼拜空间的转变[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5):48.
[12]李瑞哲. 龟兹大像窟与大佛思想在当地的流行[J]. 西部考古,2016(1):119-123.
[13]孟凡人. 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J]. 新疆社会科学,1982(1):61-62.
[14]羊毅勇. 唐代伊州考[J]. 西北民族研究,1993(1):135-136.
[15]吴玉贵. 西暨流沙:隋唐突厥西域历史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180.
[16]付马. 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27.
[17]李军. 晚唐五代伊州相关史实考述[J]. 西域研究,2007(1):7-9.
[18]王宗维. 五船道与伊吾路[J]. 西域研究,1994(4):24-27.
[19]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029.
[20]季羡林. 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J]. 文史哲,2001(1):7-8.
[21]马德. 从弥勒下生信仰看佛教的社会化:以敦煌石窟唐代弥勒大像相关历史信息为中心[J].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0,40(1):62-67.
[22]宫治昭. 涅槃与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35-338.
[23]李正宇. 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J]. 敦煌学辑刊,1998(1/2):76-77.
[24]惠怡安,曹红,郑炳林. 唐玄奘西行取经瓜州停留寺院考[J]. 敦煌学辑刊,2010(2):38.
[25]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05.
[26]贺世哲. 武则天与佛教[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2):62-63.
[27]歐阳修. 新唐书:卷4:则天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01.
[28]長広敏雄. 永远の相と変化の相[M]//大同石佛藝術論. 京都:高桐書院,1946:14.
收稿日期:2022-02-01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2021年度人文社科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定向探索项目“哈密佛教石窟及佛教遗址考古研究”;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吐鲁番地区佛教遗迹研究(5—13世纪)”(ZZYJC780004)
作者简介:罗尔瓅(1984— ),女,甘肃省兰州市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佛教考古研究。
魏文斌(1965— ),男,甘肃省定西市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石窟、丝绸之路考古及佛教艺术与文化遗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