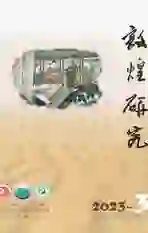麦积山第140窟天人佛塔图考析
2023-07-13张铭



内容摘要:麦积山石窟第140窟是北魏晚期开凿的小型洞窟,该窟窟顶新发现的北周所绘飞天与佛塔组合壁画,是该窟重修的重要历史信息,也是麦积山石窟现存唯一的天人佛塔图像。显示出北周时期,麦积山石窟同时受到来自南朝和北朝佛教艺术的影响,并形成了自身特征。
关键词:天人佛塔图;背屏式造像;北周
中图分类号:K87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3-0026-09
A Study on the Image Combination of Apsaras and a Stupa in
Cave 140 at the Maijishan Grottoes
ZHANG Ming
(Maijing Grottoes Art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Tianshui 741020, Gansu)
Abstract:Cave 140 at the Maijishan Grottoes is a small cave built in the lat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newly discovered mural on the ceiling of the cave, which dates to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is a combination of apsaras and a stupa, and is the only extant image to contain such a combination at the Maijishan Grottoes. The image is also notable for providing researchers with important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history and renovation of the cave. Research on the image combination demonstrates that during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the Maijishan Grottoes was influenced by Buddhist art from both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image combination of apsaras and a stupa; statue with a back screen; Northern Zhou dynasty
(Translated by CHEN Yueying)
麥积山石窟第140窟位于麦积山西崖东侧上部,其上方为俗称“天堂洞”的第135窟,下方为第154窟,西侧与第139窟相邻,东侧与第141窟相邻。该窟为小型平面方形平顶窟,窟高2.10米,宽2.25米,进深2.20米,地面塑出低坛基,上塑胁侍像。窟内原造像组合为三佛八胁侍泥塑造像,现存三佛五胁侍,其中正壁左侧及前壁两侧造像缺失{1}。左右壁主佛体量小于正壁主佛。窟内造像均有不同程度损毁,整窟烟熏严重,壁画漫漶,历代游人题记杂乱刻画于壁面。前壁左侧坍塌,上世纪麦积山山体加固工程时用水泥补封后形成现在的券顶形窟门,窟门宽度较原窟门有所增加,现窟门高1.46米,宽1.20米,深0.65米。该窟下与第154窟、东与第141窟有洞通连,系人为凿通(图1)。
麦积山第140窟的开凿年代,学界一般认为是北魏时期,但在具体年代判定上则存在两种观点。以史岩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该窟开凿年代要早于云冈石窟的开凿{2},其余大多数专家学者则认同北魏晚期开凿的观点,特别是以石窟寺考古中的类型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诸如董玉祥、达微佳、陈悦新、八木春生等专家学者,都将该窟的开凿年代比定在北魏晚期{3}。日本学者八木春生发现第140、85、122窟内造像单足轻举,膝部露出的造像形式与特征基本一致,而且第122窟的如来坐像上身单薄,凹胸前倾的坐姿也与第85、140窟的造像相仿,说明这三个窟的工匠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认为第140窟出现这些特点明显为麦积山原有工匠延续迁都以前传统所造[1]。这一观点值得注意。
一 麦积山第140窟窟顶壁画
关于第140窟壁画,特别是窟顶壁画,因受客观条件限制而具体内容识读非常简单,记录较少,学界关注很少。1953年麦积山勘察团经过现场辨认对该窟壁画首次记录:
壁画多为烟熏黑,石绿部分尚显,顶壁绘有飞天五身,即从石绿飘带辨认。右壁上半近门处画有房院一所,砖瓦均用石绿。[2]
张锦秀在《麦积山石窟志》中记录:
窟顶正中绘一宝珠,五身飞天环绕。三壁有火焰纹背光和圆形头光,残存庭院树木及比丘、供养人十余身,其中的屋宇建筑是所见最早的工笔界画。[3]
张先生认为这些壁画是北魏原作。需要说明的是,张锦秀所撰《麦积山石窟志》中对第140窟的壁画说明前后表述有所不同,在麦积山石窟壁画一览表中将该窟壁画时代记为北魏,并无重绘。但在文中进行具体描述时,认为第140窟壁画为北魏原作,北周重绘,除了将窟顶正中所绘形象由宝珠改为宝莲外,对该窟原作壁画和重绘壁画并未进行说明,因而无法确定北魏原作壁画与北周重绘壁画的具体内容和情况[3]。
笔者经过现场仔细辨认,发现之前诸学者的描述说明都有一定缺失和遗漏,虽然窟顶壁画烟熏严重,但是大致内容却基本可以识读,且窟顶壁画有叠压关系,存在重绘现象。按照叠压关系,分为底层和表层分别予以叙述(图2—3){1}。
底层壁画主体内容:窟顶中央和四角分别绘一大朵莲花。
表层壁画主体内容:为重绘层,与底层中心大朵莲花可见叠压关系。该层壁画呈中心对称分布,中心为一佛塔,位于正壁主佛舟形背光的顶部,佛塔为四面方形,底部装饰覆莲瓣,塔身上下分别有三层和两层叠涩塔台,方形塔身可见两面,均开有圆拱形小龛,推测为四面开龛式方塔,塔顶四角绘山花蕉叶,三个塔刹一字排开,两侧塔刹刹杆上串有五层相轮,中间塔刹为七层相轮,刹顶均装饰有尖头宝珠,并系有缯带向上飘起(图4)。佛塔两侧各绘数身天人,整体呈对称分布,以佛塔为中心围绕排列,天人衣带飞扬,自然灵动,下身穿赭色长裙。从衣带遗存和走向判断,至少绘有10身天人形象。
二 天人佛塔图
天人与佛塔的组合图像,目前在麦积山石窟中仅见于第140窟。
麦积山第140窟窟顶表层壁画所绘的这种天人与佛塔组合的供养图样,是南北朝晚期非常流行的一种组合样式,特别是在背屏式佛教造像中有数量众多、细节多变的表现,并且呈现出不同的年代和地域特征,西魏北周时期的造像碑中也有表现。对于这一形象,国内外学界有系统和全面的梳理研究{1}。韩国学者苏铉淑根据东魏北齐时期的造像题记,认为东魏北齐时期称这种塔为“宝塔”,进而将这种雕刻于造像顶部的单层塔纹的图案称之为“宝塔纹”[4]。考虑到目前南北朝时期遗存的佛教造像中,将这种塔称之为“宝塔”的情况仅出现在东魏北齐时期,具有一定的时代和区域性,而这种天人与佛塔组合流行的时间和区域要更为长久和广阔,因而笔者沿用学界的通用称呼,将其称之为“佛塔”,将天人奉托或围绕方形单层塔的组合简称为“天人佛塔图”。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根据韩国学者苏铉淑的研究结论,现将天人佛塔图在南北朝时期的流行时间、区域及特征予以简要说明。
根据现存有纪年的佛教造像可知,这种造像顶部的天人佛塔图在南朝梁天监十年(511)和北朝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已经出现(图5),并且在北朝造像中,天人与佛塔的组合出现时间要晚于南朝,应该是受到了南朝造像的影响[5]。
南朝时期,出土于四川成都的梁天监十年王州子造释迦像是目前已知天人佛塔图出现的最早实例(图6)。该背屏式石刻造像中,正面上部的佛塔为三层楼阁式塔,其背面礼佛图中也有楼阁式佛塔,属于传统楼阁与佛教的塔刹组合,显示出汉式传统建筑与佛教结合的特征。在此之后,传统式佛塔很快被单层方形佛塔所取代,梁代中后期背屏式造像中出现的就全部是单层方形佛塔了(图7—8)。
北朝末期,天人佛塔图是东魏北齐佛教艺术中最为突出的组合样式,广泛出现于单体造像的背光和造像碑的顶部,其中佛塔的形象主要以覆钵顶单层塔为主,属于该时期和区域的典型特征。青州龙兴寺出土的北魏晚期到北齐的石刻背屏式造像中,天人和佛塔的组合多有表现(图9)。邺城北吴庄出土的东魏到北齐的背屏式佛教造像,天人佛塔图均雕刻于背屏上部,塔基底部饰覆莲瓣,塔身开龛,塔刹部分则有数种变化(图10)。同时期的石窟寺中也有不少,南响堂石窟、北响堂石窟、水浴寺石窟、小南海石窟等都有相类似的表现。
有着明显差别的是西魏北周时期的造像中,这种顶部佛塔的组合很少出现,现存的几件主要藏于陕西耀县药王山博物馆和美国、日本的美术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的北周倚坐菩萨残碑像背面的上部,就雕刻两身飞天和佛塔的组合图案,塔顶有茎叶相连的三个相轮(图11)。西魏北周时期,佛塔形式较为多样,覆钵顶塔、屋顶塔和帐形单层塔等都有出现,佛塔也是只有天人组合,没有出现龙等其他图像组合,可以视之为是对南朝和北朝其余地区佛教艺术的兼容和选择,显示出西魏、北周造像的自身区域和时代特征。
总之,天人佛塔图主要流行于南北朝末期,分布范围广,且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区域特征较为集中和明显。通过比较,南朝与北朝天人佛塔图像共同具有的基本元素包括莲花座、塔基、方形塔身、山花蕉叶以及塔刹等部分;最大的差异和区别在于南朝佛塔为平顶,没有出现覆钵顶,而北朝特别是东魏北齐则流行覆钵顶。南朝佛塔的塔刹表现突出,主要为三刹并列,也有四刹和多刹,未出现三叉形的塔刹组合。南朝为天人与佛塔组合,北朝则还有佛塔与龙、怪兽等组合形式。在石窟寺中,北朝不大流行三刹并列的形式,云冈和龙门石窟中三刹并列非常少见。
三 第140窟天人佛塔图的绘制年代
根据上文对麦积山第140窟窟顶天人佛塔图的描述,以及对南北朝时期这一图像和组合的时代及地域分析,第140窟所反映出的莲花底座、塔身开龛、塔顶为平顶、三刹并列、天人左右对称排列的特征,属于典型的结合南北方佛塔图像特征的新式组合。
对照已有明确纪年的背屏式造像以及上文所述南北朝天人佛塔图的特征,可以看出,麦积山第140窟窟顶所绘佛塔的基本特征与南朝梁和北朝的东魏北齐年代相近。具体来说,邺城北吴庄出土的佛教造像中,被定为北齐时期的菩萨三尊像背屏式造像,在背屏上部雕出飞天托塔的组合,佛塔也是蓮花底座,莲瓣为覆莲形,方形塔身开尖拱形龛,龛内有坐佛,佛塔上部四角饰摩尼宝珠,塔刹部分为底部用莲茎相连的三座相轮,两侧为七层,中间为九层,相轮顶端也是饰桃形宝珠,整体呈现中间高、两侧低的组合特征(图12)。除去覆钵顶不同外,其形制和特征与麦积山第140窟的佛塔最为接近。考虑到同时期天水所在地的归属,麦积山所对应的时代大致在西魏北周时期。
因为麦积山石窟和秦州地区这样的天人佛塔图目前只有这一例,西魏、北周时期虽也有实物的佛塔遗存,但形制相差较大,佛塔的年代比定特征不明显,因此尚需从天人的形象进一步去考订该壁画的绘制年代。
第140窟窟顶天人形象,虽然因为烟熏导致具体细节特别是头部特征无法辨认,但是身体和衣带的基本特征却仍可辨识,部分天人长裙所用的赭色也可以看清。通过对麦积山第4窟前廊顶部北周壁画(图13)和第26、27窟窟顶(图14—15)北周壁画中的天人形象进行比对,发现三者之间的形象特征、衣带的施色等一致,特别是飘带和衣裾的边缘走向,身体的姿态和比例等方面皆相同。就麦积山同一时期壁画艺术基本的表现特征来说,三窟壁画的绘制年代大体一致。据此,第140窟窟顶天人的绘制年代也应是北周。
结合前文对佛塔绘制年代的大概判断,基本可以判定,麦积山第140窟窟顶的天人佛塔图是北周时期的重绘壁画{1}。
四 余 论
麦积山第140窟窟顶北周天人佛塔图丰富了麦积山石窟的北朝壁画内容,也为这一图像在南北朝时期的流行区域和样式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对于麦积山石窟北朝艺术的发展特征提供了新的佐证。
麦积山第140窟窟顶北周所绘的天人佛塔组合图样以及单层佛塔,在麦积山尚是首次注意到,秦州(天水)地区的北朝佛教造像中,也没有发现相同的图像组合,因而显得尤为重要。
北周是麦积山石窟发展史最重要的阶段之一。据统计,北周时期麦积山开凿的洞窟数量多达四五十个,特别是以第4窟为代表的仿宫殿式建筑以及“薄肉塑”飞天等,都彰显了麦积山北周佛教艺术的繁盛和极高水准。北周时期的麦积山石窟艺术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经过长期积淀和多方吸纳,形成了全新的风格特点,成为北周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七佛是麦积山北周最为流行的题材,将七世父母这一中华传统孝道文化中的概念与佛教七佛予以对应和组合,也是北周时期秦州佛教试图与传统文化更深层次融合的重大理论探索和实践,是秦州佛教思想的一大特点。
在当时中国南北都流行有着长期、广泛和多样化的天人佛塔图,而在麦积山却只发现了这一例,还是在一个北魏开凿的洞窟中以重绘的方式予以表现,只是昙花一现,随后便湮没在了历史的尘迹中。
首先,该图像未能在秦州地区和麦积山石窟得到流行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以单层佛塔为核心的这一组合所蕴含的佛教思想与当时秦州地区主流的佛教思想不同,因而未被接纳和广泛传播。说明秦州地区与南朝四川地区以及北朝的东魏北齐地区的佛教思想存在明显差异,也反映出在北周时期,以麦积山石窟为代表的秦州佛教有着较为统一和完整的区域特征。
其次,佛教艺术中某一题材的产生、流行以及选择,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和土壤中发生的,其中关键在于文化和民族构成。我们在考察和研究石窟寺的时候,必须认识到不同区域和民族所固有的差异,导致了佛教艺术发展的不同特征。同时,同一区域,只要主体的文化基调和民族构成没有大的明显变化,除非强有力的外力推动或者政令影响,该区域的佛教文化特征以及佛教艺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具有一定的连续和稳定性。也就是说不一定随着朝代的更替随之变化,这在政权并起、更迭频繁的南北朝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对于石窟寺考古和研究,这一点需要特别关注和仔细分析,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的不同历史背景,即使是在南北局部相对统一的背景下,也需要综合考虑。单靠一种方法进行研究和断代,会产生只重共性而忽略个性的误差。
{1} 通过对胁侍菩萨身后桩孔及残存泥皮等细节所做现场勘查可知,第140窟现存正壁右侧胁侍菩萨应为原正壁左侧胁侍菩萨,现存正壁左侧菩萨应为原左壁右侧胁侍菩萨。该窟与第154和第141窟的打破关系,造成窟内胁侍菩萨的扰动。
{2} 1953年文化部勘察团认为该窟开凿于北魏早期(麦积山勘察团《麦积山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第89页);史岩先生认为该窟造像的制作年代为北魏太武帝灭法开始之前,即5世纪50年代以前(史岩《麦积山石窟北朝雕塑的两大风格体系及其流布情况》,《美术研究》1957年第1期第15页)。
{3} 董玉祥认为第140窟开凿于北魏孝明帝煕平至北魏灭亡即516—534年(《麦积山石窟的分期》,《文物》1983年第3期第22页);达微佳认为第140窟大约开凿于北魏正始三年至北魏延昌元年(506—512)左右,也大致就是张彝担任秦州刺史时期(《麦积山石窟北朝洞窟分期研究》,《石窟寺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陈悦新认为该窟开凿年代为景明时期至北魏灭亡,即500—534年(《从佛像服饰和题材布局及仿帐、仿木构再论麦积山北朝窟龛分期》,《考古学报》2013年第1期第55页);八木春生认为第140窟开凿于北魏后期即510—534年(《天水麦积山石窟编年论》,《石窟寺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1} 从窟顶烟熏层破损处可以看出,窟顶两层壁画均是在同一白灰底色层上绘制,从两层壁画之间的叠压现状和壁画表面的颜料分布可以看出,表层壁画是在原作壁画上直接进行重绘,并未重新涂刷白粉层。
{1} 主要研究成果有唐仲明《中原地区北朝佛塔研究》(《考古》2016年第11期),唐仲明、王亚楠《东魏北齐响堂石窟与邺城造像比较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2期),管厚任《青州北朝背屏式石刻佛教造像研究》(中国美术学院2018年博士论文,第41—47页),金建荣《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背光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15年博士论文,第22—136页),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中华书局,2013年,第210—225页),符永利《南朝佛教造像的考古学研究》(南京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第65—126页),雷玉华《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成都考古研究》,2009年总第1期第621—648页),易立、张雪芬、江滔《成都市下同仁路遗址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坑》(《考古》2016年第6期第55—81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53—65页),夏名采、王瑞霞《青州龙兴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文物》2000年第5期第50—61页),王峰钧《西安地区西魏石刻佛教造像的类型及特征》(《文博》2011年第2期第62—68页),郝德深《邺城北吴庄出土的北朝佛教造像中飞天图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论文,第22—29頁),许韦玮《四川南朝背屏式石制佛教造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论文,第12—45页),李雪茜《四川南朝佛教石造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论文,第35—80页),李婧《再论东魏北齐背屏式佛教造像分期问题》(《中国美术》2022年第1期第86—93页)。
参考文献:
[1]八木春生. 天水麦积山石窟编年论[J]. 李梅,译. 石窟寺研究,2011(第2辑):122.
[2]麦积山勘察团. 麦积山石窟内容总录(五)[J]. 文物参考资料,1954(6):99.
[3]张锦秀. 麦积山石窟志[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14,130.
[4]苏铉淑. 东魏北齐庄严纹样研究:以佛教石造像及墓葬壁画为中心[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83.
[5]许韦玮. 四川南朝背屏式石制佛教造像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2:68.
收稿日期:2022-1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麦积山石窟第74—78窟考古报告”(20BKG022)
作者简介:张铭(1983— ),男,甘肃省庄浪县人,历史学博士,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石窟寺考古及佛教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