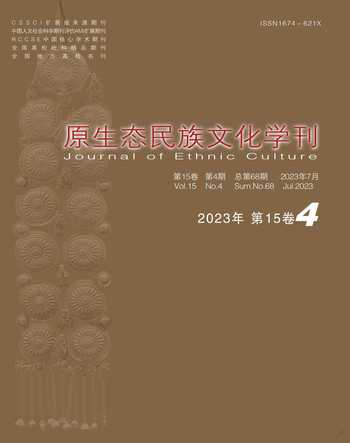企业民族志的书写:田野实践和理论反思
2023-07-13田絮崖
田絮崖

摘 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尽管企业民族志的书写对象已经由小型社区如工厂的研究,拓展到关于跨国市场、跨国网络和全球金融等的讨论,然而,人类学整体观的研究视角,以及将民族志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于企业人类学的发展和创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和取向决定了企业民族志的研究视角和书写路径,也决定了企业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分类依据。国内企业民族志发展不仅是对企业人类学理论和范式的本土化诠释,也是对民族志方法的本土化实践及反思。
关键词:企业民族志;田野调查;企业;整体观;范式
中图分类号:C912/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3)04 - 0115 - 12
一、民族志、人类学和企业研究
与人类学众多分支学科的发展历史类似,企业民族志的实践直接推动了企业人类学作为独立分支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早期的企业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自20世纪80年代起,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东亚、东南亚地区企业人类学的兴起1。 如今,企业人类学不仅在美国、欧洲,也在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等设有专门研究机构2 。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企业人类学又称“工业人类学”“商业人类学”等。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企业人类学的概念内涵,认为企业人类学和企业民族志的研究范畴,不仅包含具有经营行为的盈利主体,如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商品交易市场、期货和金融组织;也包含发生经营活动的非营利主体,如博物馆的经营性活动等;涉及参与主体则不仅包括企业所有者,也包括普通员工和其他参与企业活动的非正式成员3。
从学科缘起上看,人类学的企业研究始于对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经济人”假设的反思。在霍桑实验中,研究者即指出该研究开展的背景之一,是美国大工业企业中普遍信奉“经济人”假设,也就是将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经济诱因的观点,作为推动企业发展和提高员工效率的动力1。 然而,人类学家梅岳和娄特利斯伯克等人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正如娄特利斯伯克指出,“我们现在的工业文明是在浪费它生存所寄的资本,这笔资本就是多少世纪的定型的生活成规所遗留给我们的人类的善意和自制”2,由此强调了工业文明以外的文明和文化传统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所在。从这个层面上说,人类学的企业研究,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对企业组织和效率的探讨,而是将企业活动视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尝试在多元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呈现企业和市场主体的行动逻辑及其象征意涵,将其作为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整体建构加以诠释。
将民族志作为研究方法对于人类学的企业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意义。一方面,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张,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加速流动,传统的地方社会与新兴的全球市场更为紧密地交織在一起,原本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体开始融入世界市场,地方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快速的变迁。另一方面,基于本土文化的行动逻辑也被更加强调。在全球化时代,地方社会的经济、市场和知识体系都产生了不同的调适和发展路径,在地方文化趋于同质化的表象下,呈现出更具多元化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独特性3 。另外,包括海外华人企业和华商文化发展等案例也进一步证实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能够相融合,全球化的后果可能是本地文化的复兴,而非全球文化的同质化4 。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植根于“他者”视角的民族志方法的重要意义也更加凸显;企业民族志研究者也试图通过对企业和市场主体——不仅包括封闭的工厂社区和企业组织,也包括跨国企业以及全球金融等,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描”,最终目的是呈现出地方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总体逻辑。
二、企业民族志的视角和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人类学有关文化和社会的研究传统和取向划分,不仅决定了企业民族志的文本表述方式,也是人类学的经济和企业研究对于人类学范式的呈现,是人类学整体观视角的具体表达。
人类学有关经济和市场研究的民族志成果中,有着较为明显的文化取向和社会取向的分别。格尔兹在其对摩洛哥集市经济的研究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或经济类型,摩洛哥的集市经济与海地、印度尼西亚、印度、危地马拉,还有不同地区华人的集市经济有基本的相似性,然而,作为一种文化表达,则呈现出了独特性,具体表现为阿拉伯文化的总体情境,经济活动和伊斯兰制度的融合,以及犹太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5。格尔兹认为,集市经济的兴起虽然受到了诸如殖民主义等外在因素的影响,然而其兴起过程仍然是源自于本土的,与摩洛哥自身文化传统息息相关1。 格尔兹描述了区域性的现代集市如何基于复杂的多元文化和族群互动得以形成,探讨了伊斯兰文化情境下的财产所有权及其象征意涵,以及在以洁净和肮脏为分类原则的宗教观和世界观基础上构建的职业体系,是较为典型的文化取向的研究。另一方面,同样对市场和经济拥有浓厚研究旨趣的人类学家西敏司则更强调对于社会的关注,西敏司指出。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中的合作过程所呈现出的相似性并不是文化的,而是社会的——在这些合作中,相比于如何处理与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与那些由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导致的社会变迁的关系更为重要。换言之,社会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在具有文化多样性的族群中,往往能够导致结构上相似的改变。而这并不意味着减少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的关注,而是意味着,我们有了更好的理由来询问为什么对文化的和社会的过程加以区分是有用的2。
尽管格尔兹和西敏司对于社会和文化取向的研究各有强调——如果说格尔兹更加偏向于对文化特征的表达和描述,西敏司则更强调对于经济和政治力量所形塑的社会关系和过程加以呈现,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市场主体在地方变迁的过程中有着相似的遭遇,而这种相似性又是个体、民族和国家受到文化以外的经济和政治过程影响所致;然而,从文本的呈现方式和路径来看,文化取向和社会取向的研究,其实质均是对结构和意义、行为和观念、实践和认知相互关系的整体性论述。
具体而言,格尔兹所谓文化取向的民族志研究,是通过对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类型的描述和分析加以呈现的,其中包含了对结构性因素的讨论。而在西敏司所谓社会取向的研究中——无论是有关波多黎各的蔗糖工人,或是加勒比地区蔗糖全球贸易的研究,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族群或个体的生命意义也有深刻的关照,其中包含了对文化及其象征意义的阐释和深描。因此,从文本表述的路径来看,文化取向的研究需要对结构性的政治和经济过程加以关注,实际上是对文化在结构上的延续性的解释,而社会取向的研究需要对特定的文化及其象征意义加以阐释,事实上是对地方社会文化变迁过程意义的表述,二者都体现了对人类学整体观的关照。
企业民族志的书写同样是对人类学整体观视角的具体实践。全球化的过程,尽管企业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已经由传统的小型工厂的研究,拓展到包括对跨国金融、全球市场、跨国商业网络的讨论,然而,植根于人类学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民族志方法的实践对于相关现象的解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类学研究传统中关于社会取向和文化取向的划分,和民族志文本中对于结构和意义的阐释及表达的整体性关照,已有的企业民族志成果实践主要可以从4个维度进行分类。
下文将从不同维度对企业民族志的研究内容、理论范式和方法路径进行说明,其中不仅涉及对企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也涉及关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视角的运用,以及对民族志方法在现当代人类学研究中的意义反思。
三、人类学企业研究的田野实践、理论范式和方法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商业和人际网络研究。从人际网络和社会关系视角下开展的企业民族志研究,始于对工厂或企业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研究,如1930年代,以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研究所工业研究部开展的系列研究作为主要民族志成果1,不仅标志了工业民族志的起点,也是人类学家尝试从人际关系的视角对企业内部管理加以研究的最早实践。霍桑实验的主导者之一梅岳博士,也是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者2。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多的研究将视野拓展到企业或市场组织之外,对跨越空间和边界的企业和市场主体,包括跨国公司和跨国市场进行研究,试图探讨企业行为在更为宏大的政治经济和权力过程中的实践,及其与社会秩序、权力生产和参与者的主体性之间的关联,下文以对跨国公司和跨国市场的研究为例加以介绍。
其一是对跨国公司的研究。较早从人际网络的视角对跨国公司进行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70年代,以人类学者沃尔夫对非洲矿业跨国企业的研究为主要民族志成果。沃尔夫强调了“网络”对于非洲矿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南部非洲矿产业的组织和运作是基于复杂的社会体系,而不是政治权力或官僚权威,他指出,具有不同社会结构和功能的群体——包括公司、国家、家庭等,其内部成员能够在网络中得以整合,形成系统运作的商业组织1 。沃尔夫认为,城市的发展和更多复杂社会现象的出现,是网络分析方法获得较快发展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将社会网络作为分析视角有助于理解城市发展等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2。 此外,沃尔夫还探讨了网络分析视角对于从事社区研究的方法论意义3 。人际网络的视角和民族志方法也为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所采用,例如巴奈特和穆勒对跨国公司的经理人群体进行了深入访谈,描述了经理人作为权力主体如何在跨国管理的实践中重塑全球性的理性观念和应对来自非西方国家“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质疑,以及通过怎样的策略维持在全球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这些战略又如何加速了全球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4。
其二是对跨国市场的研究。在跨国市场和人际网络关系的研究中,以卓家健对非正式的跨国金融活动的民族志研究为例,卓家健以浙江柯桥纺织市场为田野点,对存在于迪拜的印度裔批发商和柯桥纺织城的中国供货商之间的非正式金融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印度裔批发商通过赊欠的行为与柯桥供货商之间建立起非正式的信用和信任关系,从而解决了资金周转的问题,获得了生存空间。而非正式金融系统也构成了维系包括迪拜内的中东地区,以及南非和拉美等地和柯桥之间跨国商业网络的重要支撑。卓家健的研究描述了非正式的跨国金融活动如何在国家正规金融之外得以开展,也相应地探讨了全球经济“非正式化”等问题5。
除了以西方社会为情境展開的田野调查,相关研究也拓展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吉尼格对工业人类学在阿根廷的历史和实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其中也提及了对阿根廷的工人活动和组织控制,以及对失业工人的非正式就业关系等问题进行的多项研究6 。龚宜君则对马来西亚劳工控制政策下,在马台湾企业工人关系进行了研究7。
总体上,在跨国商业和跨国市场的民族志研究中,企业不仅是经营的主体,也是全球秩序和结构重塑的主体,与此同时,也是受其影响的客体。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或是跨国市场等的个案研究,实质上是对全球市场体系、民族国家及权力运作以及个体的主体性建构的整体呈现。
第二,地方变迁和认同建构视角下的企业和商业研究。企业实践与地方变迁和文化认同关系的研究是企业民族志的另一研究范式。受全球市场扩张,民族国家兴起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市场主体的族群性、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表达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下文以两类民族志的研究为例加以说明,其一是跨国商业流动和文化变迁的研究,其二是全球化背景下市场主体的族群性表达和认同建构的研究。
其一,在跨国商业行为和地方社会文化变迁关系的研究中,有诸多丰富的成果。在《金拱向东》一书中,人类学家华生和多位研究者对麦当劳作为全球化的文化符号在东亚的扩张,和由此呈现的全球化背景下本土文化变迁的过程进行了讨论1。 陈志明、张展鸿和吴燕和以华人饮食文化的传播为背景,呈现了传统华人饮食文化在东南亚和全球的流动和变迁,以及华人文化适应和文化重塑过程2 。张展鸿还对食物生产的工业化、全球化及其与地方经济和文化传统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观察,包括对南京小龙虾养殖作为新型农产品和地方社会关系的研究3,对传统客家菜馆的变迁与香港社会生活方式变迁关系的研究4,以及探讨了香港的养蚝业如何作为地方性知识融入地方社会经济关系,从而对本地文化和社会变迁产生影响5 。在张展鸿和陈志明编写的文集中,也有不少关于饮食商业和文化变迁关系的讨论,例如,陈国成以对华人传统菜肴“盆菜”的观察为例,探讨了盆菜作为乡村传统美食的商业化过程,以及盆菜的消费习惯变迁和香港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6 。马克·华生则以日本阿伊努人传统食物在东京的生产和制造过程为例,探讨了阿伊努人如何在地方社会之外重塑生存空间,对由此呈现的空间政治和地方性等问题进行了反思7。
其二,在企业活动中的族群性和认同建构的讨论中,通常的观点是企业家或工人的商业行为和实践与其族群性相关。一部分体现在对移民企业家或离散族群的研究中。以对华人商业和企业的研究为例,早期华人的迁移和适应中,基于亲属、地域和宗族关系的商业和企业实践被认为是华人在海外立足的文化策略8 。无论是向美国、东南亚或欧洲等地迁移的华人,都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这种相对传统的以经济资源和民族(族群或族裔)经济为基础的商业模式9。在全球化背景下,族群性和文化认同通过商业实践,以更为复杂的形式呈现出来。王爱华在对生活在美国洛杉矶的香港精英企业家的研究中,关注了企业家如何通过利用家庭企业策略实现跨国资本的积累和身份流动,并且提出“弹性公民”的概念,用以解释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家公民身份建构的现象1 。桑托斯在对葡萄牙华人商业和在葡乌克兰移民商业的比较研究中,阐明了西方多重现代性视角、国家权力和西方对于华人的想象及其表达之间的关联,探讨了上述因素对族群商业模式和文化认同的影响,由此呈现出商业与族群性,国家权力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联系2 。因此总体上看,人类学针对商业行为和文化变迁及认同的研究,已经由单一的族裔经济的视角过渡到对全球化、地方文化变迁、身份认同重构等复杂议题的省思。
第三,商品和金钱的全球流动及其社会历史和象征意涵的研究。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人类学关于物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意义的研究旨趣,逐步由对简单社会经济交换的研究,扩展到对商品交换、金融制度、股票市场、期货交易和全球市场体系的反思中。事实上,从马凌诺斯基对“物”的交换模式及功能的观察3,莫斯将互惠作为社会团结象征的理论建构4,道格拉斯和伊史武德对不同文化情境下商品购买行为的文化意义的阐述5,到西敏司6和阿帕杜莱7等有关商品和消费的历史和社会意义的研究,以及布迪厄关于品味的社会象征意涵的解释8,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被合理地应用于金融制度和股票市场等的研究中。下文将通过具体的民族志研究个案加以介绍。
其一是对商品的全球流动及其历史和象征意涵的研究。如前文所述,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体现了对文化象征和历史记忆的关照。例如,杜·博厄斯、陈志明和西敏司主编的《豆子的世界》一书,讲述了豆制品在世界各地的多样化呈现和具有的不同类型的用途,将大豆置于全球历史的情境中,对其如何成为能够影响世界经济的主要消费品进行了解释,认为大豆在不同国家能够成为主流食物的种类之一,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情境的演绎有关——在中国,发酵的豆制品作为文化和象征符号融入传统社会结构当中;在日本和韩国,对发酵豆制品的习惯性食用也与家庭和民族情感相关9 。类似地,黄鸿森对新加坡的历史主题餐厅进行了研究,探讨了社会记忆和自我感知的关系,认为历史记忆通过历史主题餐厅的建立及其商品化过程被加以呈现和再造10。
其二是对金钱的全球化和商品化过程的研究,包括了对全球金融、资金期货、股票制度等的民族志研究。例如,扎鲁姆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以期货交易员的身份,进入位于芝加哥和伦敦的期货交易市场进行参与观察,对芝加哥和伦敦的期货交易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扎鲁姆描述了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是如何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外部建筑,以及交易场所之内,交易员、办事员、电话银行经理之间面对面的竞争和互动得以实现,从而形成了有利于交易开展的社会场所和空间。扎鲁姆认为,在新技术情境下,交易员和市场经理人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个体意识和自我日常空间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定义1。
另一成果是由何凯伦经由17个月的田野调查完成的华尔街金融家的民族志研究。相较于扎鲁姆的研究更为侧重于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反思,何凯伦的研究更加强调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建立的过程。以美国社会为背景,何凯伦对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华尔街企業股票的上涨和就业动荡、失业加剧的同时发生进行了研究,探讨上述现象是如何通过银行投资人和国家,以及不平等的政治秩序而实践,最终使得经济的繁荣越发倾向于为投资人,而不是普通人获得利益。何凯伦也指出,在这种金融和市场秩序之下形成的具有华尔街特色的文化体系和文化意识,不仅不会随着投资银行的发展而减弱,相反会被持续地实践和再造,在更大范围内生产出不平等的市场秩序2。
受到全球化过程加深的影响,对金融市场和金融经济的研究也拓展到非西方社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黄应贵和郑玮宁主编的《金融经济、主体性、与新秩序的浮现》。书中对会计制度的建立和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新兴债务人群体——“卡债族”面对的债权人压力及其遭遇的社会伤害,布农族的土地征税制度及其正义性,以及对鲁凯族如何在金融化的过程中重塑主体性,共四个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呈现和反思3 。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社会或非西方社会,金融、会计、股票等制度均与国家、权力以及社会主体的实践联系起来,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以及个人认同和主体性的重构产生影响。
第四,企业和市场主体的个人生活和生命叙事研究。企业民族志的第四个范式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主体——既包括企业家,也包括普通工人——的个人生活和生命历史叙事的研究。生命历史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在人类学领域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从克鲁伯4到克拉克洪等5,再到本尼迪克特6,都指出将生命历史作为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全球叙事的背景下,西敏司还强调了将生命历史叙事作为方法论,通过对不同个体生命历史的跨文化比较,从而发现文化之外的社会和经济进程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阐明了该范式和方法在调和人类学研究传统中“文化”和“社会”“结构”和“能动”关系,以及在超越个体的结构和历史过程的总体建构中的作用1 。企业人类学研究中,有关个体生活叙事的范式和方法论实践,主要基于对不同类型民族志材料的应用,包括对口述历史、日记、自传、人物传记等资料的应用,下文将重点以对企业家群体的研究为例,对两类民族志资料的运用和成果加以介绍,其一是对自传资料的运用,其二是对口述历史资料的运用。
其一,企业民族志对于自传资料的运用,事实上是从反思性的视角,将自传作为民族志的第一手材料,对其进行文本的解构。在企业民族志研究中,自传资料既能够体现出企业家对于自身认同的自反性观察,又能够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对企业家的活动加以呈现,对自传的分析能够将个体的生命历史和社会经济历史联系起来。近年来,自传作为民族志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从方法论层面对于如何使用自传资料从事企业家精神等的研究和讨论也逐渐增多,例如有研究指出,自传资料有利于研究者将企业家的内在经历(内心活动、奋斗、成功、失败的经历和目标以及所经历的困惑和渴望),以及企业家的外在经历(与家庭成员和亲属的关系,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进行整体的了解,由此也体现了定性研究方法所具有的优势2。在使用自传作为第一手材料的民族志个案研究中,较为典型的研究是瑞福里对法国籍殖民企业家朱伯特作为“冒险家”的身份建构和企业家声望获得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的分析3。
其二,在企业民族志的研究中,相比于对自传资料的运用,利用口述历史资料开展的研究更为普遍。仍然以对企业家群体的研究为例,在企业家群体中所开展的田野调查,通常是从对其创业历程的了解入手,首先对其创业动机加以描述,继而探讨创业初期的困难和获得支持的途径,创业过程中的风险控制,以及企业家的个人生命和生活历史与企业传承关系等,以上也涉及对企业家的个人性格和个体认知,企业家的家庭和社会网络等的关注。事实上,在企业民族志的研究中,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不限于对企业家的研究,而是包括了对企业的所有者,经理人和工人,以及女性企业参与者等不同维度下企业参与主体的研究。
基于自传资料和口述历史资料的分析,也能够对企业民族志研究的“真实性”问题加以回应。由于从事企业民族志研究较难做到长时段地居住在参与观察对象的家中或社区,研究者通常需要面对跨国或跨界移动的群体,同时有可能需要采用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方法4 。而对自传或口述历史资料的运用和呈现,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保证调查资料的广度和深度,这是由于只有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建立充分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才能获取充分而真实的资料。也就是说,科学而真实的口述历史资料的获取,以及对于自传、日记、传记资料的客观评价和使用,仍然需要以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
四、国内企业民族志的发展和创新
国内企业民族志的发展不仅是对企业人类学理论范式的本土化诠释,也是对人类学视角和方法的具体实践和反思。相较于国外企业民族志的发展,国内企业民族志的兴起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本土化特点,包括个案研究的本土化以及理论范式的本土化两个方面。总体上看,国内企业民族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20世纪30年代至建国之前的探索和初创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承前启后阶段,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的繁荣发展和创新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之前,这一阶段可以视为国内企业民族志的探索和初创阶段。这一阶段内,尽管工业人类学或企业人类学作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尚未建立,然而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民族志成果,主要集中于对我国工业化早期,家庭企业、家庭工厂、低收入群体,以及劳工关系等议题的研究上。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教授对于乡镇企业、家庭企业的发展,及其同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1 。同时期,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特定职业群体中的低收入劳动工人,较有代表性的如言心哲对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研究2,伍锐麟等对广州市人力车夫和全国人力车夫的调查3。此外,在对工厂劳工关系的研究中,包括陈达、何德明和吴泽霖对工人生活状况的研究4,史国衡对昆厂的工业组织和工人关系的研究5,都是较为典型的作品。这一时期的诸多成果也影响到了国内企业民族志后续的发展,例如改革开放之后,费孝通教授继续开展有关家庭工商业和农村城镇化的研究,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导致的社会波动的影响,总体上企业研究的民族志成果较少,主要集中于译著成果和海外学者对亚洲经济发展的研究。在译著成果上,费孝通教授于1964年首先将梅岳所著《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进行了翻译,将美国工业人类学的早期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另外的成果则更多来自海外学者对于亚洲经济崛起现象的观察,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东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由此促进了学术界对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社区经济繁荣和发展动力的探究。不少研究集中于讨论中国文化传统和华人经济发展的关联,例如伯格在对促成东亚新兴诸国经济起飞因素的讨论中,特别提到了东亚民间宗教的实用主义所发挥的作用1 。以上讨论也影响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对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动因的研究,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研究者也尝试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对我国经济发展现象作出解释2。
第三阶段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伴随着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企业民族志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中外企业人类学成果交流的增多和专业企业人类学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外成果交流和引入方面,包括前文提及的华生、何凯伦、桑托斯等人的相关研究已经被翻译为中文。日本学者中牧弘允的《经营人类学序说——企业的“民族志”和工薪族的“常民研究”》《日本人类学三讲——中牧弘允在北大的演讲(连载之三):日本的企业人类学》3两篇文章,和滨田友子的《家族企业的人类学研究:亲属和商业的比较分析》4也已被翻译为中文。2008年,中加“企业人类学:案例研究”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召开5,和首届国际企业人类学大会的召开,促进了海内外企业人类学的交流。2009年企业人类学专业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则标志着国内企业人类学作为独立分支学科有了进一步发展6 。其二是本土化的企业民族志成果的快速累积。2007年,费孝通教授走访浙江温州后,将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进行了比较,指出家庭工商业在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潜力7。与此同时,研究者对族群经济和民族企业8,老字号企业9,移民商业10,都市商业11,家庭企业12、海外中资企业13等本土化商业模式进行了丰富的个案研究。其三是本土化的企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例如,王兴周对人类学方法在少数民族市场、族群市场和消费市场等不同类型市场中的应用进行了讨论14,殷鹏以霍桑试验和曼城工厂研究的比较为例,对企业人类学的方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1,庄孔韶和袁同凯等从组织人类学的视角对企业现象进行了研究2。张继焦试图从新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建立中国特色的企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并且从范式转变的角度,提出了企业人类学的“四层次分析法”3。以上研究对于企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本土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体而言,国内企业人类学的发展有着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其中既包括具有地方性知识背景的民族志个案的积累,也形成了对本土化理论范式的发展和创新;既有关于企业民族志理论和方法的专门讨论,也有应用研究的探索和拓展。国内本土企业民族志的发展,日益对世界企业人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成为促进世界企业人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五、结语
企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源是人类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范式和方法传统,企业民族志书写的基本视角植根于人类学对文化整体观的关照,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为人类学的工商业和企业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全球化背景下,尽管企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已经由小型社区拓展到跨国市场和全球商业,然而,与田野对象长时段的互动,由此而建立的默契和信任,以及将此作为获取研究资料的方法、技术和途径仍然重要。企业人类学作为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也能够与组织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展开对话,由此推动人类学理论和范式的创新和發展。
企业民族志的相关议题也体现出人类学的学科关怀。企业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不仅停留于对经济发展相关议题的关注,就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经济发展如何避免类似于西方国家由于自由调节的市场制度或逐利动机的驱使所出现的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现象,进而探索出具有本国或本地区特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做到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内在和谐统一发展,仍然需要从地方性知识和自身的传统中找寻答案,这不仅是企业人类学和企业民族志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人类学学科的总体关怀所在。
[责任编辑: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