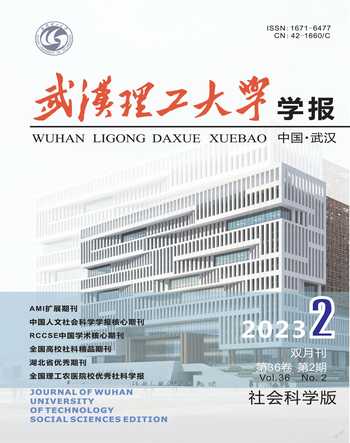承典与塑新:21世纪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马克思主义
2023-07-12甘文平郑晓曦
甘文平 郑晓曦
摘要: 彼德·巴里的《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和罗伯特·帕克的《如何解释文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批评理论》是21世纪西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双子星”。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部分不约而同地做到了“承典”和“创新”,而且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及其文学文化批评实践,为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两本专著既彼此呼应又相互补充,共同为读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批评理论中的经典价值与地位及其在21世纪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的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 彼德·巴里; 罗伯特·帕克; 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 I0; I109.5文献标识码: A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3.02.016
一、 引言
进入21世纪,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出现了两部重要著作,它们是彼德·巴里(Peter Barry)的《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2002)》①(以下简称《理论入门》)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的《如何解释文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批评理论(2020)》②(以下简称《如何解释文学》),迄今为止,中国读者对这两位西方学者及其文学理论著作的关注仍然处于初期阶段。
《理论入门》的“目录”包括引言、“理论”之前的理论:自由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解构、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批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理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酷儿理论)、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批评、文体学、叙事学、生态批评、附录。《如何解释文学》的内容涉及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酷儿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包括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后殖民与种族研究、读者反映批评、近期出现的理论发展:环境批评与残疾研究、诗歌形式术语、结语。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位居两本专著目录的中间。
《理论入门》中的“马克思主义”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入门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通论”“‘列宁派马克思主义批评”“恩格斯派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阿尔都塞的影响”“停下来思考”“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做什么”“马克思主义批评实例一则”“文献选读”。③《如何解释文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构成要素有:“关键概念”“卢卡奇、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阐释”“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动作用:阿尔都塞”“如何阐释:一个来自大众文化的例子”“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变体”“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更多例子”“延伸阅读”。可以看出,两本著作的“马克思主义”体例设置基本相同,即包含“经典马学说”、部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学与文化文本批评实践中的运用三个部分。
通过对比分析两本专著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我们发现,其中的“马克思主义”部分在兼顾“经典马理论”和“新论”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存在相似性,同时又各有侧重。两本著作既彼此呼应又相互补充,为读者呈现了21世纪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与此同时,本文结合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著作,进一步阐明这两部著作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赋予“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承典”和“塑新”的两大特色。
二、 理论维度的“承典”与“塑新”
《理论入门》和《如何解释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兼具“承典”与“塑新”两大特点,“承典”表现为传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学文化观,“塑新”体现在突出重点和引入新见,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当下意义。
第一,“承典”的第一种表现是两本著作都引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术语,如“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基础与上层建筑”、“异化”、“物化”等,它们是我们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语词,也是把握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与文化理论诸流派的出发点。这些术语分别来自以下相关论著: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述了劳动、劳动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等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聚焦唯物主义历史以及将意识形态看成是耸立于社会生存条件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对意识形态内容的具体化——创建于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上的各种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马克思的《政治经学批判(1859)》在社会结构视角下讨论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意识与权力、意识与语言、艺术形式相对独立性等。此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也收录了以上术语的相关内容。与此同时,两本著作都援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观。《理论入门》重点提到优秀艺术作品的自由度、伟大艺术和文学的阶级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艺术的社会性、作品形式和内容与政治的关联性。这些概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学评论的核心思想,其部分内容被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④和《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⑤里面。
第二,“承典”的第二种表现是两本专著同时简要地梳理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它们依次是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英美马克思主义以及每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和关键词。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看,它包括“经典/传统马”、“西马”、“当代马”、“新马”、“后马”,从文论融合的角度看还包括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可谓“旗号”众多,蔚为壮观。从时间维度看,马克思主义批评自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整个20世纪(20-30年代、50-60年代、80年代以后)直至21世纪。此类文献比较多,几乎所有的20世纪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著述都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它们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上面提到的两本译著;第二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文集,如《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⑦《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⑧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⑨等译著;第三類是国内学者的专著,如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⑩等,它们都是集中研究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第四类是一些单篇译文和研究论文,在此暂不赘述。
第三,《理论入门》和《如何解释文学》两部文学理论著作重点突出,新见迭出。它们在兼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批评家——卢卡奇、葛兰西、威廉斯、伊格尔顿、詹姆逊之时,重点突出了几个批评家的新观点。首先,《理论入门》借用了西方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两大流派——“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马克思主义[1]108。前者强调艺术独立于直接政治决定论,后者坚持艺术服从于左派政治事业。接着,《理论入门》沿着“恩—马派”从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的差异以及语言与现实之关系的视角依次引出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语言“陌生化”、20世纪40年代左右意大利戏剧家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以及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影响下出现于20世纪30—50年代美国新批评的语言自身特征。它为读者理清了该流派发展的内在逻辑。斯坦纳在谈到“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时认为此派学者“在研究一部文学作品时尊重它的完整性及其存在的有机中心”[2],但是斯坦纳没有对该“谱系”进行历时性的梳理。这或许给了《理论入门》以启发,成为它创造性“演绎”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源头。
其次,两本著作都强调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理论入门》“马克思主义”下面的标题之一是“当下:阿尔都塞的影响”,提到了“多元决定论”、“相对自治”、“意识形态”、“去中心”、“压制结构”、“意识形态结构”或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与“霸权”和“统治”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安东尼奥·葛兰西和雷蒙德·威廉斯)、“询唤”(阿尔都塞的影响绵延至20世纪70—9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如何解释文学》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动作用”标题下集中讨论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询唤”、“主体/臣民”、“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动作用”和“相对自治”、“主体”和“主体性”、“虚假意识”。这是两本著述的最大共性之处。目前,在所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论专著中,似乎没有哪本著作能够像这两本书这样如此详细地介绍阿尔都塞。总之,两本著作同时给与阿尔都塞足够的空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拓展。
再次,两本著述的创新点非常显著。《理论入门》结合提问法与问题扩展法,通过设置思考题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为文学批评实践作好铺垫。它的思考题包括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例如,前者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要观点之后开始设问:“你准备采用‘决定论立场,并认为文学是社会|经济力量的被动产品,或者你将执行一条更加‘自由的路线,把社会|经济影响看得更加遥远和细微吗?”[1]112。这个问题直接对应“恩—马派”和“列—马派”。后者与具体文学文本(莎士比亚的喜剧《李尔王》)有关:“下面的例子采用了‘决定的路线或是‘自由的路线?它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批评家是从戏剧的内容、人物刻画抑或文学形式中读出了社会|经济的影响?如果是,如何读出来的?”[1]112。《理论入门》没有给出答案,而是让读者去思考。这些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具体化,也是启发和指导读者从事批评实践的方法论,颇具创见。
《如何解释文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阐释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阿尔都塞思想关键词的深度阐释。帕克认为阿尔都塞构建了三个对立统一体,即相对自治|意识形态、能动作用|询唤、干预|虚假意识。关注相对自治(上层建筑部分地独立于经济基础)、能动作用(让事情发生的能力)、干预(改变或试图改变现存的制度)的文化批评家是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意识形态、询唤、虚假意识则是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读者将阿尔都塞置于不同的位置。三组词语中前者都受制于后者,它们是被压制与压制或者被统治和统治的关系。这也是“询唤”的核心旨意。帕克认为,阿尔都塞的“询唤”指的是“保持制度复制它自身的引擎……是[将人们]被动和无意识地带入统治性的社会假设中……是一代又一代地复制认为理所当然(无意识)的文化假設,从而阻止出现激进的变化”[3]285|287。这恐怕是对“询唤”最简明而清晰的定义。阿尔都塞本人也没有如此清晰地定义“询唤”。孟登迎的专著《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和金瑶梅的《阿尔都塞及其学派》同时论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唤(询唤)与主体建构,但都未涉及上述三对语汇,帕克的创新思想可见一斑。
第二,《如何解释文学》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布迪厄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资本观点扩展到“文化资本”——“我们无法自由地选择我们的审美风格、音乐、衣服、电影或者家庭装饰甚至我的说话方式。相反,阶级地位不是由经济资本决定的,而是由家庭和正规教育的相关品质决定的,它们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影响我们的审美趣味”[3]296。布迪厄认为,由于存在以上不同的限制性因素,工人阶级的审美趣味与精英阶层的审美趣味存在差异。一言以蔽之,在布迪厄看来,艺术执行一项社会功能:复制和合法化了社会等级。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与《理论入门》中关于文学的社会|经济“决定论”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例如,如果说后者强调作者和作品的社会|经济背景,那么前者强调读者的社会|经济背景。
除了布迪厄,《如何解释文学》也引介了朗西埃。他在《感知分配(2006)》中提出“影像的伦理机制”、“艺术的再现机制”、“艺术的审美机制”,它们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核心——全体人的平等观,打破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二元对立。朗西埃认为,20世纪以来,类型的规则消失了,因此审美机制是现代的、民主的、平等的。艺术不再表达其他事物,也不是再现,而是关于它自己的语言和表达。在审美机制里面,审美形式是关于形式自身,但它没有脱离社会世界。相反,形式、语言以及艺术和政治的视觉影像重塑社会世界看待和理解它自己的方式。最终,“艺术能够随心所欲地削弱限制自由、政治、审美想象压制性的等级制度。因此,朗西埃从艺术的审美机制里面看见了一扇通向没有压制的民主和平等之门”[3]301。朗西埃的艺术平等观既是对“经典马”消灭差别、追求平等以及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之构想的继承,也是对阿尔都塞“二元论”思想的发展。丹尼尔·哈特利(Daniel Hartley)在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导览(2019)》一文中仅对朗西埃一笔带过[4],而没有提及布迪埃。综上所述,《理论入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发展的概览以及《如何解释文学》对布迪厄和朗西埃的论述是“塑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三、 实践维度的“承典”与“塑新”
《理论入门》和《如何解释文学》在理论传承与创新之后又将二者用于文学与文化文本批评实践,既提出了批评之“论”又提供了具体文本细读之“法”,做到传承与创新相互融通,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学与文化文本世界里的“诗意栖居”。
《理论入门》的批评实践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提出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五个方法(论)。第一,区分文学作品的“公开”(明确或表面)和“隐秘”内容,然后将文学作品的隐秘题材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题相结合,例如阶级斗争;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进步相结合,例如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因此,《李尔王》中的冲突可以被读解为“真正的”关于上升阶级(资产阶级)和没落阶级(封建主)之间的阶级利益冲突。这个方法论是对《理论入门》中“马克思主义基础入门”的继承与发展——恩格斯于1888年在评价英国小说家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小说时说道:“作者隐藏的观点越多,作品就越好”[5]。第二,将作品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地位联系起来。如此情况下,读者可以假设(与心理分析批评家的假设相似)作者没有意识到他或她在作品中准确地说了什么或者揭示了什么,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具体体现。第三,从“产生”作品的社会时期角度解释整个文学类型的本质。例如,伊恩·瓦特(1917—1999)在《小说的兴起》中把18世纪小说的成长与当时中产阶级的壮大联系起来。小说为那个社会阶级“说话”,如同悲剧为君主制和贵族“说话”。这也是意识形态批评的具体实践。第四,在文学作品和“消费”作品的特定时代的社会假设之间建立联系。该策略更多地被用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后期形式——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文化唯物主义者乔纳森·多利摩尔和阿兰·辛菲尔德合编的《政治的莎士比亚》提出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方法的四个特征——“历史语境”、“理论方法”、“政治倾向”和“文本分析)”[1]121|122。第五,“文学形式的政治化”,即主张文学形式自身由政治环境决定的。例如,在某些批评家看来,文学现实主义间接地验证了保守的社会结构。对其他批评家而言,十四行诗和抑扬五音步的形式和韵律的复杂性是社会稳定、礼节和秩序的表现。这印证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总是历史化!”。以上五个批评原则是宏观指导与微观路径的结合体。
第二个部分是巴里在方法论引介之后,运用其中的第一种方法详细解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第十二夜》。巴里首先介绍了关于该剧本的权威性解析,即剧本展示了自我沉迷的各种极端现象(奥西诺公爵沉迷于浪漫爱情的自爱自怜,托比·培尔契在身体欲望方面的自暴自弃),然后将它们与极端的清教主义和对快乐的抵制进行对比,藉此建议一种平衡和体面,避免极端,各类人物都能实现理想的满足与成功。但是巴里话锋一转,认为以上解读只是触及剧本的“公开”的层面,却忽视了其中“隐秘”的阶级问题:“只有特权阶级能够利用道德的放纵……统治阶级的所有成员通过过度沉迷欲望找到了自己的身份”[1]113。这体现在贵族阶级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私密但不会轻易被人发觉的“第二世界”。例如,托比爵士通过酗酒达到一个无禁锢的世界,利用醉酒后的无能而强迫他人照顾自己,从而在逃避关照他人的同时保护了自己。同理,奥丽维娅通过退避到丧友悲痛的私人世界而无视别人的需求,实现对自己的保护。奥西诺和薇奥拉使用不同的方式进入到自己的“第二世界”。此外,剧本中像玛丽娅一样的仆人们都心怀向上流社会移动的“渴望”。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读者就无法揭示剧本中主仆之间的鸿沟和身处不同阶级人物的心理状态等“隐性”主题。这种批评之“法”赋予经典剧本以崭新的意义。
如果说《理论入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经典文学文本,那么《如何解释文学》更加注重传统以及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文本的批评实践。具体说来,帕克运用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解读流行音乐、电影、小说、诗歌五个文化与文学文本。
第一个文本是帕克对美国音乐制作人特里西娅·罗斯的《嘻哈之战(2008)》的“询唤”式解读。首先,帕克介绍了罗斯的观点。她认为近年来最流行的厌女嘻哈音乐因为其越来越多地集中宣传地痞、皮条客和妓女而引起尤其喜欢该音乐的非裔美国人的堕落。然后罗斯发问:是谁在做出这些决定?谁是能动者(agent)?嘻哈音乐的文化环境——包括经济环境、听众环境、音乐制造者和发行者(音乐工业、无线电台)是什么?为此,罗斯视能动作用(agency)为不仅仅是听众的更多能动者,他们被动地认为选择嘻哈音乐是他们自己的决定。罗斯最后总结性地认为“嘻哈音乐的出现不仅仅是音乐家或者听众的个人选择,相反,许多文化能动者(cultural agents)促成了音乐和歌词所谓的直接表达”[3]292。显而易见,嘻哈音乐的流行是其背后意识形态操控的结果。
接着,帕克从悲观和乐观两方面将阿尔都塞的上述三组词语用于解释嘻哈音乐。他假设一个叫丹尼尔的十三岁女孩特别喜欢听嘻哈音乐。从悲观的思维方式来看,丹尼尔是虚假意识的受害者,被消费主义的商业意识形态询唤后导致去购买和倾听厌女音乐,而且甚至可能与她的女友一起分享该音乐。这又导致询唤她和她的女友从意识形态上无意识地接受关于女性、黑人和商业文化的侮辱性假设。从乐观的思维方式上讲,丹尼尔有可能下载了厌女音乐并和她的女友一起听音乐。但她不关注歌词,相反,她甚至将歌词视为讽刺和嘲笑厌女思想。无论关注与否,丹尼尔把听音乐等同于抗议权威。这个权威形式的代表是父母、老师或者认为自己应该如何成为其他类似之人。丹尼尔的抗议也许不成熟,甚至是自我毁灭,但是她开始和开创了一条包含能动作用、干预、相对自治的真正文化批评之路。在她成熟之时,她有可能在该音乐的鼓励之下尝试制作自己的音乐和创作自己的歌词——一种具有令人信服的讽刺意义且不带厭女思想的歌词。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愿景,但是帕克认为这种乐观解读法几乎不存在。换言之,虚假意识、询唤、意识形态会分别战胜相对自治、能动作用、干预。
第二个文本是帕克解读英国影评家和电影制作人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1975)》。她为了揭示经典好莱坞电影询唤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本质而另辟蹊径,制造干预,打破该意识形态的外壳,产生足够的相对自治去抵抗诱惑。第三个文本是帕克解析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1811)》。帕克认为,瓦尔特爵士在外出时屈尊向他的佃农们鞠躬,使后者感觉到(被询唤而导致)自己在前者心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正是这个动作掩盖了瓦尔特的虚伪、阶级差别与统治阶级的特权。第四个文本是美国诗人埃德温·罗宾逊的诗歌《理查德·科里(1896)》。帕克在诗作中发现富人科里向工人打招呼的问候语“早上好”具有强烈的询唤功能。它一方面掩盖了资本家的虚假、资本特权的神秘以及阶级不平等的本质,另一方面误导了工人阶级相信并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就能像科里一样致富。然而工人阶级不明白他们的贫穷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他们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现实。第五个文本是美国作家凯特·肖邦的《一个小时的的故事(1894)》。帕克发现该小说通过对女主人公的不同称呼(询唤)展现她的命运变化。首先,她被称为“马拉德夫人”,说明她的身份是马拉德的妻子。后来,她成了“露易丝”,显示她反抗父权意识形态的女性独立(“女性的干预”)。然而,路易丝最终走向死亡,这是对女性追求自由与独立的讽刺,对女性依附男性的肯定。正如帕克所说,小说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压制了抵抗、批判性思想和女性的独立”[3]308。
从《理论入门》和《如何解释文学》的文本细读实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方法具有科学的指导性和鲜明的实用性,能够为读者打开一扇揭示文学与文化文本更多意义的新窗户。
20世纪后期,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文学的专著。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集中讨论了“文学与历史”、“形式与内容”、“作家与倾向”、“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它们涵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学观、基本概念以及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代表性人物,每个部分几乎都有文学文本简析。然而,伊格尔顿没有提到阿尔都塞的“询唤”,文本分析也不够细致。雷蒙德·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包含“基本概念”、“文化理论”、“文学理论”三大部分,是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具书,但很少指向具体的文学或文化文本批评。戴维·福加克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诸流派”中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分为五种模式——卢卡奇的反应模式、马舍雷的生产模式、戈德曼的发生学模式、阿多诺的否定认识模式、巴赫金的语言中心模式。在“生产模式”部分,福加克斯介绍了阿尔都塞的“表征阅读”[现在通常译成“症候阅读”]和文本的“缺口”观点[6],但没有引入“询唤”。以上五种模式与《理论入门》有相似之处,但其“理论味”更浓,“实践味”较淡。
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西方学界出版了若干部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文学与文化理论著作。卡里·尼尔森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合编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阐释》汇聚了近40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论文,其中涉及了阿尔都塞的“主体性”、“多元决定论”、“询唤”,但都只是片言只语。同时该论文集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实践。莫利娅·哈斯利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与文化理论》包括“理论关键词”、“应用与阅读”以及“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它给与阿尔都塞足够的空间,但是没有提及阿尔都塞的“相对自治”和“询唤”等关键词。它集中分析了20世纪前的英国文学作品,鲜有涉及具体的文化文本。以上两本著述都没有从方法论上考察文学作品。当然,这些著述不同程度地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学与文化领域更多更新的含义。芭芭拉·福莱的《当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阐释了修辞与“询唤”之间的关系,颇具创见,但没有提供实例分析的路径[7]。总之,读者在浏览以上专著之后可以更好地把握《理论入门》和《如何解释文学》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继往”与“开来”,同时还可以感受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文学及文化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强大影响力和现实指导性。
四、 结语
《理论入门》和《如何解释文学》从“承典”和“塑新”两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跨学科性、现实性与创新性特征,揭示了它在文学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双重场域中强大的生命力。近几年来,英美学界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专著和论文,其学术触角伸向实用主义、生态学、电影等领域,为读者带来了更多的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8]。它们无论从《理论入门》和《如何解释文学》中受到文论思想启发还是接续中对其做出拓展与延伸,皆为读者理解与把握文学和文化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可以想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学和文化批评实践双重领域,未来必将产出更多富有价值与意义的思想成果与实践成果。
注释:
①本文参考该著作的第二版,见Peter Barry.Beginning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second edi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它的第一版于1995年出版,它的最新版第三版的中译本于2014年出版,但其中“马克思主义”部分的内容没有变化。参见彼得·巴里的《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一书(杨建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
②本文参考该著作的第四版,也是最新版。见Robert Parker.How to Interpret Literature:Critical Theory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fourth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③除了“停下来思考”,其他表述均参考了杨建国的译文。
④参见让·弗莱维勒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书(王道乾译,平明出版社1951版)。
⑤参见格·索洛维耶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一书(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版)。
⑥参见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一书(陈昭全、樊锦鑫、包华富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版)。
⑦參见陆梅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一书(漓江出版社1988版)。
⑧参见汤姆·博托摩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一书(陈叔平、王谨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版)。
⑨参见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书(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
⑩参见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4年版)。
文中译文皆为本文作者所译,下同。斯坦纳在其发表于1958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家》一文中表达了上述的观点。该文除了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外还提到日丹诺夫、托洛茨基、卢卡契、布莱希特、戈德曼等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参见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语言、文学和非人性论文集》(2013)第315|325页。
阿尔都塞没有直接释义,而是采用上帝与臣民类比大写的主体与小写的主体的方式详细地阐释了“询唤”的内涵。参见Louis Althusser.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Ideology and Ideology State Apparatuses. Translated by G.M.Goshgarlan.London,New York:Verso,2014:261|272.
参见孟登迎的《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一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版)以及金瑶梅的专著《阿尔都塞及其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2010版)。
参见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
参见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参见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eds..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Hampshire: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8.
参见Moyra Haslett.Marxist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ies.London:Macmillan Press,2000.
[参考文献]
[1] Barry,Peter.Beginning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
[2]Steiner,George.Language and Silence:Essays on Language,Literature,and the Inhuman [M].New York: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2013:321.
[3]Parker,Robert.How to Interpret Literature:Critical Theory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fourth edition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4]丹尼尔·哈特利.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导览[J].宁艺阳,陈后亮,译.国外文学动态,2021(3):16|2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90.
[6]戴维·福加克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诸流派[M]//安纳·杰弗森,等,主编.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陈昭全,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61|212.
[7]Foley,Barbara.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Today [M].London:Pluto Press,2019:123|126.
[8]曹順庆.近五年英美学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叙事[J].人民论坛·学界前沿,2020(21):51|58.
(责任编辑文格)
Inheriting Marxist Classics and Shaping New Ideas:
Marxism in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Literary Theories
of Peter Barry and Robert Parker
GAN Wen|ping, ZHENG Xiao|x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
Abstract: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and How to Interpret Literature: Critical Theory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written by Barry Peter and Parker Robert respectively are two important books on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They,with one accord,show many similarities i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when they introduce Marxist view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That is,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Marxs and Engels and other Marxist critics,the two books creatively expand the scope of Marxist theory and its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ractice,they also provide a good guidance for readers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grasp Marxist theory and practice.The two books echo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Together,they show readers the classic value and status of traditional Marxist criticism theory and its strong vitality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riticism; Marxism;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methods and pract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