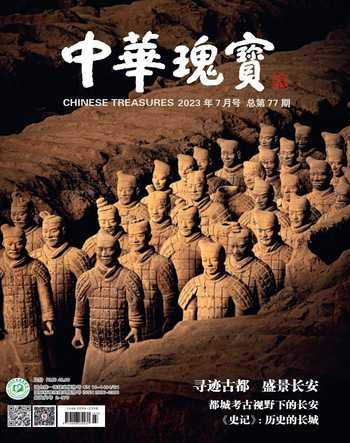周昉:富贵丰秾 肌胜于骨
2023-07-12羊砚云


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了唐代人物画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以『丰肌秀骨』营造出众多经典人物形象,展现出唐代女性的丰腴与健硕之美,『为古今冠绝』,对后世工笔人物画的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盛唐之后,仕女画在人物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作列女、神女不同,其画面主角变换为宫闱丽人、贵族妇女,仕女画走向了世俗化的发展方向。其中以张萱与周昉画作最为知名,画史称他们的作品为“绮罗人物画”,周昉的作品更是被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一书列为“神品中”,赞其“又画士女,为古今冠绝”,周昉地位在诸多唐代画家之上,仅次于吴道子。
宣州长史笔有神
周昉,字仲朗,一字景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主要生活在唐代宗至德宗时期,历任越州长史、宣州长史。《唐朝名画录》记载其兄周皓擅长骑射,曾随哥舒翰出征吐蕃,收复石堡城,很受皇帝赏识。周昉本人则是游于公卿之间的贵公子,擅长丹青和文章。除仕女写真外,周昉亦擅佛道像。唐德宗修建章敬寺,宣召周昉画章敬寺神像。周昉画完后,京城之人竞相来到寺院,纷纷提出意见,有赞美周昉神妙的,也有指出他不足的,周昉公听并观,随意改定,经过数月,是非议论之语俱绝,时人无不叹服于其作的精妙程度,推其为当时第一。周昉还曾创制“水月观音”佛画,成为长期流行的标准像,时称“周家样”。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周昉最初师法张萱,“后则小异,颇极风姿”,成就超越了其师,变化之处在于周昉所创作的仕女形体更为丰腴,这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及他的官宦身份密切相关。宋代董逌《广川画跋》中谈及周昉的《按筝图》:“尝持以问曰:‘人物丰秾,肌胜于骨,盖画者自有所好哉?余曰:‘此固唐世所尚,尝见诸说,太真妃丰肌秀骨。今见于画,亦肌胜过骨。”长安妇人在杨贵妃的引领下,以体态腴润为时尚,周昉亲眼见到的纤细女子少,筆下的仕女便流露出意秾态远的韵味,这与韩幹不画瘦马是一个道理。
周昉的画作见于著录的很多,《宣和画谱》著录御府所藏就有七十二件,包括《五星真形图》《杨妃出浴图》《妃子数鹦鹉图》《扑蝶图》等,其中描绘“簪花”“挥扇”“游春”等题材的仕女画占半数以上。周昉的真迹今已难确认,幸运的是,尚有几幅典型周昉风格的画作传世,以《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内人双陆图》等为代表,从这些作品中足以一窥唐代仕女画达到的惊人成就。
簪花楚楚绝凡近
《簪花仕女图》今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全长近两米。这幅工笔重彩的长卷上,共绘制五名贵族妇女和一名打扇婢女,构图上从右至左可分为三段,场景分别为嬉犬、拈花和引蝶,间以拂林犬、仙鹤、湖石和辛夷花,展现了宫闱生活的一个剖面。
画面中人物体态丰盈,神采奕奕,均身着薄如蝉翼的外纱,肩环披帛,内裙上有的饰有大朵晕缬团花,长可曳地,可谓“绮罗纤缕见肌肤”。仕女面庞饱满,以白粉敷之,作浓黛蛾翅眉,眉心贴圆金钿,双目狭长,瞳如点漆,高鼻檀口,独具安恬柔静的感官之美。高髻上簪有荷花、牡丹、芍药等硕大花朵。画家描绘人物轮廓和衣纹时,均采用细劲匀淡的线条,用色大胆浓艳,符合画史所说“衣裳简劲,彩色柔丽”的特点。
此画目前所见最早收藏印为“绍”“兴”联珠印,可知最初归属南宋内府,后经贾似道递藏,有“悦生”朱文葫芦印。元明时期不见于文献著录,也无相关收藏印记。入清后被梁清标收藏,有“蕉林”印文,后入清内府,有乾隆、嘉庆、宣统诸印。安岐在《墨缘汇观》中将此图定为周昉所作,《石渠宝笈》沿用了此判定。20世纪初此画被溥仪携至长春伪满宫中,新中国成立后为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所收藏。
学术界对《簪花仕女图》的创制年代看法不一,主要有四种观点:中唐说、中晚唐说、南唐说和宋代说。
中唐说的代表为杨仁恺先生。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首先,在人物造型、妆饰及服装等辅助材料上,其完全符合唐德宗贞元年间崇尚奢靡的时代特点;其次,作品本身的构图、线条、色彩等处理技法与中唐背景一致;再者,从作品形制和尺寸上看,此画原由三块绢组成,推断是由唐时流行的离合式屏风改装;最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绢画《引路菩萨图》右下角,宽袖大衣的供养人形象与《簪花仕女图》中妇女形象一致,可作为佐证。
徐邦达先生考证了妇女衿袖的演变和高髻戴花的习尚,认为《簪花仕女图》应为中晚唐时期创作。盛唐之前,妇女的衿袖都偏窄小,发髻一般为低鬟和重鬟。中晚唐以后,妇女的衣袖逐渐变得宽大,也出现了高巍的发髻,戴花为一时所尚。白居易有诗云:“时世高梳髻,风流淡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这与《簪花仕女图》中所见一致。因此,徐邦达先生认为,此图画法生动,应为创作而非后世摹本,时间上属于中晚唐,晚于周昉生活的时代,是周昉传派的作品。
南唐说的持有者是谢稚柳先生和孙机先生。谢稚柳先生认为关键不在于是否梳高髻,南唐二陵出土的女俑也梳高髻,说明从中唐到南唐一直流行高髻,而在陆游撰写的《南唐书》中记载了大周后“高髻纤裳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说明与《簪花仕女图》中女性形象一致的“首翘鬓朵”与“纤裳”方为要紧。同时,画面中出现的辛夷花是春花,只可能由于南唐僻处江南地区,气候早暖,妇女可着纱衣。孙机先生也认为其是南唐作品,一个重要的证据是仕女发髻上的花钗与合肥南唐墓出土的花钗样式相同。
沈从文先生从服饰史考证的角度,认为图中妇女蓬松义髻上加金翠步摇已是完整配套的装饰,画面中却还要再加花冠,显得不伦不类,在唐代画迹中绝无仅有。唐代的花冠是以罗帛制成,满罩于头顶,戴真花是北宋时才流行的做法。因此,沈从文先生推断此图是宋人用宋制度绘唐事,据唐旧稿有所增饰。
笔者认为,《簪花仕女图》在构图、敷色、人物形态、服饰等方面所具有的特征均交汇于晚唐,也有一些延续到五代,推测应是晚唐之后某位周昉传派的画家原作,仕女高髻上的花朵显然为后添。
芳姿挟扇问秋寒
《挥扇仕女图》今藏于故宫博物院,为绢本设色长卷,引首有乾隆御题“猗兰清画”四字。此图鉴藏印众多,经明韩世能、清梁清标等人递藏,后入清内府,钤有“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隆鉴赏”等印文,著录于明张丑《清河书画舫》、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清阮元《石渠随笔》等书。
长卷共绘制了十三名仕女,分为五个段落,分别为执扇慵坐、解囊抽琴、对镜理妆、绣案做工和挥扇闲憩。“执扇慵坐”一段以头戴莲花冠、身着晕缬团花裙的女子为视觉中心,她斜斜闲坐于腰椅上,左侧站立着两名手捧洗漱器具的侍女,右侧则是一名两手执扇的男装女官;“解囊抽琴”组绘一女子抱琴,另一稍矮女子抽琴;“对镜理妆”部分亦为两人,一人手捧大圆镜,另一人则对着镜子整理发髻;“绣案做工”段绘三人围绕绣床坐于地毯之上,一人手持小扇正眉头紧锁,另二人对坐引线刺绣;最后“挥扇闲憩”部分,一人背对观者而坐,手挥小扇,另一人抱着梧桐树,似正聚精会神地看向背坐之人。
作者十分注重画面横向排布的韵律变化,同时也十分重视纵向陈列的高低错落,从而使得画面结构井然有序,避免了构图上的枯燥单一。图中色彩丰富,衣纹线条圆润秀劲,富有力度和柔韧性,较准确地勾画出了人物的种种体态。整幅长卷对几组人物的描绘细致入微,使得画中女子既彼此形成独立的章节,又都紧紧围绕宫闱生活这一共同主题。图中仕女忧愁下垂的双眉、数次出现的秋扇意象,以及孤零零的梧桐等,隐寓着深宫内苑里妇女哀愁孤寂、身不由己的无奈之状。
毫端图写富贵女
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内人双陆图》同样是一幅宫廷题材的仕女画。“内人”即宫内之人,尤指女性,此画主要表现宫廷贵妇下棋嬉游的日常。双陆棋是一种掷骰行棋的游戏,魏晋时期经由印度传入我国,被称为“波罗塞戏”,盛行于隋唐,皇室贵戚、闲雅人士等对此项休闲活动乐此不疲。
此卷画幅较短,共画了八名女子形象。画面中央是两名正在全身心投入棋盤对弈的贵妇,一女举棋欲落,一女坐而凝思。旁立一名观棋贵妇,正斜倚在女僮肩头,另有两名侍立一旁的宫人和两名正在劳作的女僮。《内人双陆图》留给观者的不再是顾影自怜的落寞或苦大仇深的哀怨,而是生动活泼的日常情味,与前述《簪花仕女图》和《挥扇仕女图》流露的情感分外不同,这在传为周昉的作品中是独有的。
整幅画面设色明艳而不浮躁,线条精细典雅,刻画贵族妇女秾丽丰肥之态入木三分,作者若无对日常生活和女性情态的长期深入观察,断不能将其表现得如此得心应手。谢稚柳先生经过考证,将此画定为北宋摹本。图中诸仕女的发式、服饰和器具等都属于周昉生活的中唐时期,故母本为唐人旧迹无疑,能临摹到如此程度,也非高手不能为。
艺术审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氛围的熏陶。唐朝开放的时代风尚不仅造就了诗文的高峰,也带来了人物画的革新,以周昉为代表的仕女画家真实反映了当时官僚贵族的审美趣旨,展现出唐代女性的丰腴与健硕之美,对后世工笔人物画的创作有着深远的意义。驰目域外,唐代的仕女画也影响了日本早期的浮世绘美人画,今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不仅题材借鉴自唐代仕女人物,画中女子的造型更是极有可能直接出自周昉所作的粉本,成为唐代艺术样式在海外的生动遗存。
羊砚云,供职于无锡市东林书院和名人故居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