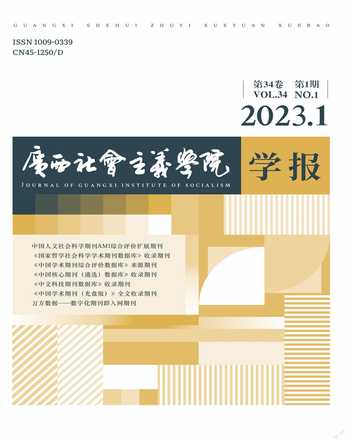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建构
2023-07-12覃玉荣马晋芳
覃玉荣 马晋芳
摘 要: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形成于“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重大历史过程,根植于中国与马来西亚民众记忆中。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记录了中马经贸往来、社会互动、文化与教育交流合作历史,经过时空的历时、共时建构与立体审视,通过文本、意象、仪式系统的型构,以及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画、故事、场所、纪念活动、表征实践、仪式等,记忆得到强化。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是在与文化制品和文化活动的互动实践中得到建构和拓展的,始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交往实践,筑牢于中马共同文化根基,推动着中马两国友好往来、和平相处、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进而实现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
关键词:马来西亚;海丝文化;文化记忆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1.014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1-0096-05
海丝文化是在大陆文明东渐与河海文明相互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时间上可追溯到秦汉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开放包容”的精神凝练。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记录了马来西亚社会、中马交流合作等历史发展。从已发现的文献档案资料、图画、祭祀、节日仪式、纪念碑、考古遗迹、文学故事及作品等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马来西亚经济贸易、建筑、宗教、习俗、饮食、中医药等发展,是马来西亚人挥之不去的印记。重拾记忆,对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加强中国与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价值。
文化记忆是在集体记忆概念基础上产生的,是记忆研究领域新兴的理论,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并取得丰硕成果。在理论层面,学者们创新性地开展了跨学科(文化记忆与传播学)、跨方向(文化记忆与翻译)的探究。但在应用研究层面,多针对地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身份认同、民歌、文学等进行研究,鲜有人结合海上丝绸之路及其他国家或民族文化记忆进行相关探究。
一、文化记忆相关概念阐释
文化记忆这一概念是扬·阿斯曼(Jan Assmann)于1988年在《文化记忆与文化身份》一书提出的,缘于哈布瓦赫(Halbwachs Maurice,1985)关于集体记忆中的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研究。交流记忆是指一个集体成员通过日常接触和交流建立起来的记忆,交流记忆的承载者是个体,其存在和延续的手段是口传,主要依靠见证者维持,持续三到四代人时逐渐消失,因而它属于短时记忆。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强调的重点是作为记忆载体的符号媒介,它通过社会交流的、处于运动之中的集体符号建构, 包括个体记忆得到强化,被个人记忆所使用[1];一个社会在一定时间内必不可少且反复使用的文本、圖画、故事、场所、纪念活动、表征实践、仪式等,正如生物记忆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得到形构和拓展一样,文化记忆也是在与文化制品和文化活动的互动实践中得到建构和拓展的。其核心是让所有成员分享有关政治身份的传统,相关人群借助它确定和确立自我身份或形象。基于此,该集体成员们意识到共同的属性和与众不同之处[2]。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区别,一是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二是客观化的文化型构(文本、仪式、纪念碑、建筑等)和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经验和意义在时间维度和组织化情景中得以固定从而连接起过去、现在与将来。各种材质的书面文献、碑文、日历、家谱、图书馆、博物馆、建筑物、仪式和节日等构成了文化记忆的一系列制度性实践表征,它是一套可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3]。
二、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的建构
(一)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的历史建构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文化性的长时记忆。文化记忆的内容通常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其中既包括传说中的神话时代也包括有据可查的信史。由于在内容上可直接回溯到远古,而不受一般三四代人时间视野的限制,因而文化记忆在时间结构上具有绝对性[4]。文化记忆有固定点,它的范围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这些固定点是一些至关重要的过去事件,其记忆通过文化形式,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而得到延续[5]。马来西亚海丝文化正是这样的固定点,而依据固定点的文化记忆在时间上既可回溯到2 000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也可从当代文化积淀中挖掘。
根据国内学者的考证和研究①,马来西亚海上丝绸之路属于南海丝路的一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汉书·地理志》对汉使下西洋的路线记载被认为是最早记载中国与马来西亚来往的史料。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中国就以徐闻、合浦等港口为始发港,经由海上交通路线与马来半岛的婆利等古国开展商贸往来。唐朝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深水航线的开发与拓展、南海丝路向海岛国家倾斜,中马往来更甚,马来西亚地区凭借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优势,与中国的中介贸易十分发达,且开始与中国开展佛教方面的交流。宋元时期,随着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的发展,马来西亚海上丝绸之路得到繁荣发展,中国与马来半岛狼牙修、渤泥等古国的接触更多,出现派遣使节出访及回访的情况。明清时期,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创举使马来西亚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时期,中马在经济、文化、族群、宗教等层面上的交流愈加深入,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出现统一的国家,如满剌加等,与中国互派使者来往频繁。满剌加王国是东南亚各国经济联系和交换的中心,瓷器、绸缎、香料、棉布等货物在此地进行大宗交易,这些都扎根于马来西亚人民历史记忆中。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开始殖民统治马六甲,明朝统治者回绝葡萄牙的建交要求。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马海上交往逐渐减少乃至中断,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式微。
1957年马来西亚宣布独立,1974年中国与马来西亚正式建交,1988—1989年两国签订《海运协定》《贸易协定》等一系列重要协定。1990年之后,双方互访频繁,双边关系密切,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马来西亚联合公报》《中马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促进中马体育交流、提高体育水平的谅解备忘录》《中马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马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等重要文件,在贸易、科技、体育、教育、卫生、环保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2013年,马来西亚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确定两国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加大对华直接投资,加快推进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中马关丹产业园区建设,与中国往来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中马关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往来,长期形成的经济贸易、文化、教育交流环境等的社会互动,政府机构与媒介宣传的支撑及信息传递,代代相传的文化客体、符号、人工制品和媒介、社会化的仪式实践等(它们比个体寿命更长),在中马两国政府政策引导下不断得到加深。通过经贸合作、教育交流、文化交往等符号,两国不断创造群体对海丝文化认同身份,逐渐使这些符号成为参与改变、 更新、重新激活其文化的工具,并使参与这些符号的不同个体成为海丝文化记忆历史建构的维系者与支持者。
(二)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的空间建构
文化记忆空间建构,与一个群体或群族自然、人文环境及行为内在特点相联系,深入人们的心理、行为、文化等空间环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群体记忆丰富多彩的空间呈现,是地理、气候、经济、文化等自然与社会综合作用与交互的结果。一个群体或群族聚落而居,宗教、血缘关系成为维系人们关系的纽带,宗祠则成为节点形态中心。祭祀、节庆、婚俗、葬礼、诉讼、故事传说等大事记忆,通过文字记载、图画、故事传说、歌谣、牌坊、纪念活动、表征实践、仪式等实体性、象征性形式进行编码或演示,逐渐形成区别于沟通记忆文化循环意义的交往空间。
马来西亚海丝文化空间记忆建构,不可避免地包含自然地理、社会与文化因素。公元2世纪和郑和下西洋时期,大批中国移民从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迁徙至吉隆坡、怡保、森美兰、槟城、吉打、马六甲、柔佛、沙捞越等地定居,与本土文化相撞相融,闽南、客家、广府的饮食、婚嫁、建筑等文化,女儿“出花园”、关帝庙中敬关帝、除夕初一拜老爷等成人礼、出海祭祖仪式等文化习俗,盛行大马各地。
宗祠成为马来西亚土生华人的政治、文化和精神中心,牌坊则成为一个村落或群族界标、心理分界点或地域象征,体现族群、团体观念,而贸易交往(日用、布匹、菜市店铺)、行政集会(信息与命令传达、布告通知、意见反馈)、庙宇(妈祖庙、关帝庙、观音庙)、文化活动(上演戏剧、戏曲、电影、舞狮舞龙、宗祠认祖)等,都是马来西亚海丝文化独特的文化记忆空间的建构元素,记载了马来西亚人与华人自然、人文环境及行为内在特点与相互认同的交往空间。
三、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的型构
(一)文本系统的型构(书面文本、口传文学)
作为外置性的存储工具,文本可将记忆的内容固化保存,供后来者整理、研究、阐释等。文化记忆理论中的“文本”所包含的不仅有书面的文本,而且还有口头的文本,即口传文学。二者综合起来,就是扬·阿斯曼所谓的“文化文本”,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4]。作为深刻影响中马往来的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海上丝绸之路是马来西亚文化记忆中不可磨灭和不可消逝的固定点,通过书面文本与口传文学型构的文本系统得以固化保存,并建构相关文化记忆的联结。
印刻文化记忆的书面文本,为具有奠基意义的经典化后的文本,一般由统治阶层所筛选和阐释,以示其规范性。编纂于1612年的《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 叙述了马六甲(即满剌加)王朝的兴衰发展、政策、礼制以及与邻国的交往等。该书引经据典,涵盖600多年的历史,被奉为马来西亚历史的经典著作,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马来西亚文献中仅有的史书,它明确记载了其时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建立起的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友好往来活动。如,第十一章中记载满剌加王国第三代国王Sli Maharaja学习中国明朝的政制与礼制,在满剌加王国进行政治改革,设立首相、司刑、司财、各部首长等,再下设第二、三、四级官员;仿照明朝的伞盖之制,按伞盖颜色划分官吏等级; 第十五章中则记载了中国汉丽宝公主前往满剌加和亲等中国与满剌加邦交的故事。这类经典的书面文本记载,一方面固化存储了其时中马友好往来的历史文化记忆,使其极具真实感和说服力;另一方面供后来者回顾历史,重现重构中马亲善邦交记忆,增强对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的认可与认同。
较之于文字文本的經典、规范、上层精英特有性,口传文学则扎根民间,依靠人民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等留存。郑和下西洋历史事件成为海丝文化故事传说的记忆中心,为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建构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郑和于1405至1433年7次下西洋,历时28年,不仅使马六甲海峡恢复畅通,更推动马六甲古国发展为南海丝路的必经之地,成为繁荣一时、络绎不绝的“诸番之会”。郑和下西洋不仅传播了中国的生产技艺、工艺制作、建筑风格、文化习俗等,深刻影响了马来西亚诸地风俗人情,更将中华文化及和平友好往来精神深植于马来西亚人民心中。马来西亚民众对这一段历史传奇颇为看重,民间流传着许多与郑和有关的传说故事,如现在马来西亚的火葬、禁食节等习俗相传为郑和下西洋时所教授;又如,相传郑和船队航行至马六甲时一条大鱼(被称为“郑和鱼”或“三指鱼”)以身补船,挽救郑和船队于海上危难。为表示对此鱼挽救郑和的感恩与尊敬,当地人不会将其食用[6]。郑和所掘“三宝井”中的井水被称为“多情水”,当地人认为取之泡茶、冲凉等可祛病延年益寿。沙巴地区有杜孙族,相传为郑和船队士兵与当地居民的后代,与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习俗相同等[7]。这些故事流传在马来西亚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同时也将有关郑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记忆深深烙印在马来西亚人民心中,使中马海丝文化记忆永葆鲜活与深刻。
(二)意象系统的型构(历史建筑、文物遗迹、博物馆等)
与文本一样,意象系统也是外在的、客观的文化符号载体并被用以保存、固化和延续文化记忆。海丝文化记忆的建构与相关意象系统的型构密不可分。海丝历史、文化寄托于物化留存下来及专门予以维护、展示的历史建筑、文物遗迹、博物馆、纪念馆等,这些物化实体及场所等提供了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口中的“记忆之场”,型构起有关海丝文化记忆的意象系统,唤起了马来西亚人民有关海丝之路的记忆,增强了对海丝文化的集体认同。
历史建筑作为中马友好往来的见证者,承载着中马建筑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如马六甲苏丹王宫受郑和时代建筑风格影响,采用中式传统建筑的榫卯结构,未用一颗钉子,宫内亭台楼榭、雕梁画栋无一不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修建于15世纪的马六甲青云亭,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中国庙宇。该亭飞檐反宇,五脊六兽, 宏伟庄严,采用了浮雕、泥塑、剪陶、彩案等高达七种的装饰手法,集中展现了中国建筑艺术之美。乐圣岭天后宫是马来西亚华人为供奉妈祖等神灵而建造的,采用了清式勾栏的栏杆样式,以及龙凤雕刻、彩梁、彩画等中国传统建筑符号,巍峨壮丽,古朴典雅。马六甲鸡场古街内,展现中国建筑风格的宗祠、庙宇、同乡会馆等保存完好,古色古香的楼宇比比皆是。
作为历史的直接表现物,文物遗迹的物化实体是海丝文化记忆的依托,具有保持紧密的情感关联、唤起相关记忆等作用。马来西亚沙捞越群洞(Nian Caves)里留存下来的铜棺葬与中国广西等地战国时的铜棺葬相似,彭亨地区(Sungai Tembeling)发现的铜鼓为中国汉代铜鼓,山都望矿场发现了精致的唐朝瓷器和石器,丹章古堡贫民墓场中发掘出了金器、小珠、唐朝石器、瓷器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钱币,柔佛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明代瓷器碎片。这些文物遗迹说明马来西亚与中国交往由来已久,邦交关系密切且逐渐加深。相关海丝文化经由文物遗迹得以留存,建构了中马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根基。
不同于历史建筑与文物遗迹,博物馆、纪念馆是人为、专门地建构出的一种纪念之地,其将海丝文化遗留下的珍贵遗迹、文物等进行收藏、集中展示,以纪念相关历史,将记忆“档案化”。马来西亚吉隆坡国家博物馆与沙捞越博物馆收藏、陈列着大量中国宋元明时期的瓷器,是中马海丝密切交往的重要佐证;吉隆坡博物馆还陈列着“郑和龙泉号”“都灵号”“南洋号”等沉船的文物;为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专门在马六甲郑和官仓遗址修建的郑和文化馆,展示了郑和访问马六甲时带来的瓷器、海产品;雷佛士博物馆现存的在马六甲地区发掘的仿铜钱式样的锡币,证明了马来西亚满剌加王国曾学习中国的铸钱技术。峇峇娘惹族群建立的峇峇娘惹遗产博物馆,集中展示了19世纪末峇峇娘惹服饰、房屋的装饰、风俗用品、雕花艺术品等生活用品,体现了峇峇娘惹兼容并收、独具一格的文化,同时展示了中马民间的频繁交往、民心相通。
(三)仪式系统的型构
在有文字的社会阶段,仪式在构建文化记忆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视听文化日益发达的当下,仪式早已突破所谓的时空局限,借用各种手段传播发展,使只能存在于文本上的知识可见可感、活灵活现。有关马来西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记忆并非经由仪式系统得以保存,而是基于当下得以重现与重构。如马来西亚已将农历正月初一和初二定为全国性公共假日,当地华人合家欢聚、吃年夜饭、发压岁钱,举办舞龙舞狮、灯会、庙会等庆典仪式以庆贺新年,还会在正月初七时“捞鱼生”,边捞边说吉祥话,且越捞越高,以取其吉祥寓意,祈求在新的一年捞得风生水起、步步高升。又如马来西亚槟城地区每年会在农历正月初九时设长桌团拜以恭迎天公诞(即玉皇大帝的诞辰),这是来自中国福建的移民后人对敬天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并通过天公诞仪式表达祛灾祈福的美好愿望。在神诞、庙会、做寿、婚嫁、乔迁等特殊时节与场合,马来西亚华族会安排闽剧、粤剧、潮剧、琼剧等戏曲演出,以表达庆祝、祝贺。而在举办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时,人们也会专门举行戏剧节以激发马来西亚华语戏曲这一传统礼仪的活力。马来西亚也会举行相关仪式以重现马来西亚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重现中马海上友好往来的历史。如将中国皇室汉丽宝公主与马来西亚和亲通婚的故事改编为歌剧《汉丽宝》,在马来西亚进行展演;举办峇峇娘惹文化周、制作峇峇娘惹文化介绍与宣传视频等,以便更多人了解峇峇娘惹文化。马来西亚丁加奴则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九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来纪念郑和的诞辰[8],以重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等。
[參考文献]
[1][德]阿莱达·阿斯曼.个体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陶东风,译.文化研究,2020(3).
[2]Assmann,J.Kollektives Gedchtnis und kulturelle Identitt[M].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8:15.
[3]连连.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J].江海学刊,2012(4).
[4]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J].江西社会科学,2007(2).
[5]Assmann J. Das kulturelle Gedchtnis:Schrift,Erinnerungund politische Identit?覿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1992:54-55.
[6]李菁菁.马六甲的郑和余韵[J].华夏人文地理,2001(2).
[7]唐玲玲,周伟民.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375.
[8]施雪琴.东南亚华人民间信仰中的“郑和崇拜”[J].八桂侨刊,2006(1).
责任编辑:何文钜
①参见卢苇:《南海丝绸之路与东南亚》,载《海交史研究》2008年第2期;赵明龙,等:《南海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范若兰,等:《新海丝路上的马来西亚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
收稿日期:2022-11-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63004)。
作者简介:覃玉荣,女,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英语语言学、跨文化交际、东盟国别与区域研究;马晋芳,女,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东盟国别与区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