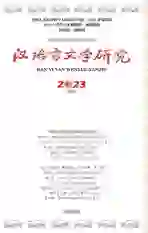引言:精读三文,如何?
2023-07-05陈平原
陈平原
连续18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讲授“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自我定位是:配角,但并非无足轻重。此课程虽无关专业知识的培养,但有益学问境界的提升。这是因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拥有5个本科专业、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二三十个研究方向,各专业之间隔行如隔山,学术趣味相差甚远。能讲且必须讲的,应该是共同的理念与信仰、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以及一些基本相通的治学方法。另外,是我特别看重的,那就是如何经营学术论文。
指导研究生,犹如老话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相对来说,容易传授的是具体的专业知识,导师们大都会很在意;至于会不会写论文,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有的一点就通,有的则死活不上道。因此,我一般会在最后一讲,引入自以為颇有心得的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形成与嬗变(参见《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本学期也不例外,至于期末作业,很简单:选择你心仪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某前辈学者三篇文章,从学术史或述学文体角度加以论述。为什么规定只谈“前辈”(我临时下了个定义——已退休的教授),其实年轻导师的志趣及方法,更容易被学生们接受与模仿。除了学术史方面的考量,还有就是拒绝或明或暗的阿谀。研究生写导师,可能真的很崇拜,但也不排除某种利益计算。干脆拉开距离,摆脱师承的纠葛,尽可能独立地思考、理智地判断。
为什么就选三文,全面阅读与评述不是更好吗?在我看来,即便是了不起的大学者,也不能保证每篇文章都很精彩。能兼及学养、才华与境界,且在学术史上留下深刻印记,这样的好文章、大文章,一辈子写不了多少篇。因此,我才会在《“三联人文”书系总序》(2008)中提及:“对于一个成熟的学者来说,三五篇代表性论文,确能体现其学术上的志趣与风貌。”问题是,要通透地了解一位学者,准确判断哪几篇是他的代表作,需下一定的功夫。而且,与其粗粗翻阅、人云亦云地表彰,还不如仔细琢磨这三篇你选定的论文,如真能读进去,触类旁通,可能更有收获。
更何况,我要求的不是笼统地表彰,而是落实到这三篇文章,“从学术史或述学文体角度加以论述”。前者好说,容易找到参考资料;后者则往往被忽略,或虽可意会,却难以言传。作为“述学文章”,第一要务是解决学术史上关键性的难题,既要求“独创性”,也体现“困难度”,最好还能在论证方式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这对作者的学识、修养、洞见、才情乃至“智慧”,有很高的要求。
品鉴此类相对而言的“大文章”,最好兼及大目标(如学术史意义及学问的境界)与小技巧(如构思之妙与细节之美)。撰述中之“腾挪趋避”,既为了学术思路的推进,也是文章趣味的体现。在内行人看来,好的考证或论述(无论文学、史学,还是数学、物理),用如此简洁的笔墨彻底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难题,这本身就是“优美”的。
比起文学作品来,述学文章的“美感”,更是言人人殊。今天很多学者迷恋陈寅恪的文章,当初胡适、钱穆可都是一口咬定陈寅恪学问好,但不会写文章。这种事情,很难说谁对谁错。今人欣赏的,古人或后人未必喜欢;反之亦然。在我看来,因各自性情、学科及教养的差异,谈论作为“文章”的学术著作,可以有“偏见”,但不能没有“自觉”。会不会写文章,是否此中高手,一出手,明眼人就能看出来。不要说一两本书、三五篇论文,有时就是那么几段话,聪明人“闻”都能“闻”出来——尤其是坏文章,更容易露馅。
要说学术训练,比起具体学识,品读/撰写好的学术论文,其重要性一点都不逊色。眼看当下中国学界,述学文字日益僵化,陈陈相因,了无生趣,虽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但起码告诉有理想、有灵性的学生,述学文体是值得认真讲究的。
这个话题我多次涉及,也做了不少试验,且得到媒体的支持。10年前,我选择了16篇由课程作业修改而成的专业论文,请《文史知识》连载,每期一篇。连载结束时,我撰写《学会写文章——写在“规范与方法”结尾之后》(《文史知识》2014年第2期),提及自己带研究生阅读好书好文,不只关心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更努力领略其论证方式、写作技巧乃至文章的气势与韵味等。那一次是以学者及著作为研究对象,这回变个法子,要求学生选择、精读、评说三篇代表作。虽说作业完成于特别时期(疫情汹涌,不少学生提前离校),但56篇小论文大都写得不错。只是因刊物篇幅,加上考虑学界已有论述,我选择了以下三则。
2023年1月28日(大年初七)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