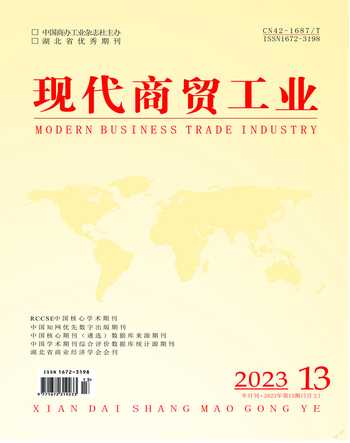网络平台经营者对用户虚拟财产的安全保障义务研究
2023-06-28杜育涵
杜育涵
摘 要:我国《民法典》第127条通过一个宣示性条款确定了网络虚拟财产的合法地位,但并未进一步确认虚拟财产的权属问题、划归虚拟财产的保管责任以及解决虚拟财产的继承难题,使得不同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作出了不同的判断。文章通过讨论虚拟财产的内涵与外延来确定虚拟财产的范围,并通过设定网络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来划归虚拟财产的保管责任,解决技术难题,最后按照虚拟财产性质来分别确定其继承条件与继承路径,促进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关键词:虚拟财产;继承;安全保障义务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3.13.054
随着虚拟财产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司法实践中也不断涌现出请求继承虚拟财产的案例。而目前,《民法典》继承篇的司法解释并未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可继承性以及继承路径做出回答。因此,厘清虚拟财产范围,解决虚拟财产保管技术难题并寻找虚拟财产继承的法律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1 虚拟财产的界定
1.1 虚拟财产的概念
虚拟财产,又称“网络虚拟财产”,是指一定主体对存在于网络环境下、经一定的程序指令生成的、模拟现实事物的数字信息所享有的权利。我国《民法典》第127条通过立法明确了“网络虚拟财产”的合法地位,肯定了其财产属性。因而应当认为虚拟财产属于“财产”这一概念范畴,与“财产”之间是种属关系。
纵观“财产”这一传统概念的发展历史,其在不同时期具有符合历史阶段特性的不同法律内涵与形式。大多数国家并没有通过立法来对其进行固定。但无论其如何发展,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始终都认为“财产”应当与“所有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认定财产时,主要强调具有绝对支配地位的主体对物的支配权力,并对主体具有一定利益,并未对财产的流通性作出过多的要求。因此,在划定虚拟财产范围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1.2 虚拟财产的外延
结合学界的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本文讨论的虚拟财产的外延包括域名、网址、电子邮箱、网络店铺、社交账号、网游账号及其所包含的游戏装备、虚拟货币。有学者将用户在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机构中储存的电子货币也认作是虚拟财产。实际上,电子货币只是法定货币的一种数据化表现形式,其本质上仍然是可以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普遍流通的货币而非物,具有购买力。电子货币无需考虑变现的问题,与寄存在信用卡、流通票据的货币没有本质区别,在继承上也应当视作一般财产予以继承。
2 虚拟财产的可继承性
虚拟财产根据其性质可分为一般财产属性的虚拟财产和兼具财产和人身属性的虚拟财产。
2.1 一般财产属性的虚拟财产的可继承性
一般财产属性的虚拟财产具有一定的市场价格标准,有稳定的变现途径,具备较强的流通性和可交易性的特点。如网络游戏平台中的游戏币、游戏装备等。这类虚拟财产有些是用户通过法定货币充值购买得来的,与法定货币之间存在有一定比例的价值兑换关系,是被明码标价的。基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法定货币的获取需要公民付出一定劳动。所以被明码标价的商品也应是公民合法劳动所获取的,应当被视作具有价值予以保护。
部分虚拟货币可由玩家完成平台关卡后赚取得来,其在最初生成時不具备价值,但通过玩家在时间、精力和智力方面的付出,会使该虚拟物件的品质变化,市场价值提升,玩家在过程中始终在创造价值。不论是通过法定货币购买来的还是游戏过程中掉落的装备,都可以流通和交易,应承认其存在有真实价值。
《民法典》第1122条第一款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一般财产属性的虚拟财产是公民通过合法途径、手段取得的个人财产,应当被准许继承。
2.2 兼具财产和人身属性的虚拟财产的可继承性
兼具财产和人身属性的虚拟财产指抖音直播账号、社交账号等。如今这个流量当头的数字时代,有大量粉丝的社交账号暗藏着巨大的经济效益。直播带货、平台打赏、广告推销等各种途径使得流量变现,人们对其继承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这些账号里面包含有大量的个人信息,以及照片等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个人信息具有人格利益性和财产性特征。社交账号中存储的聊天记录、文档对个人具有利用价值,在其过世之后对其亲友具有纪念价值,这类虚拟财产对主体存在有较强的利益,符合财产的利益本质。
(1)司法实践中的保护。
司法中,有法院将社交账号、手机号码等认定为虚拟财产。如朱琳继承纠纷案中法院认定手机号码具有财产利益,随人的使用逐渐具有人身属性,是一种用益物权。支持将手机号码的使用权过户到朱彬名下。由于立法没有明确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学界也无统一标准,导致法院认定和判决标准不一。
在顾光超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可双方将QQ号作为买卖标的物的行为并认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有效。该判决尊重当事人意思,承认账号的财产价值以及可以进行所有权变更。对于社交账号能否买卖,法官主要考虑的是其交易目的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例如在赵春飞与程卫红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买卖标的物是微信账号,法院认定其买卖合同的目的是获取账号内大量的个人信息,构成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应当归于无效。实践中也存在有当事人要求继承亲属社交账号的情况,但因为涉及当事人隐私等原因并未公开。不过从各个媒体的报道推断,这类案件的数量逐年增多。
(2)学界的不同观点。
传统学术观点认为网络账号只是一种身份识别手段,或是用户的一种操作权限,是基于合同关系由网络平台经营者向用户履约的依据。但这并不影响社交账号类虚拟财产因具有财产利益而可以被继承。
有学者认为死者自去世后不再享有民事主体资格,因而不再享有隐私权。死者由于已经去世,不再需要隐私权所保护的不被侵扰的权利。只有行为人对死者的隐私侵害造成了其近亲属的强烈痛苦,或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才被认为是侵权行为。不得以社交账号涉及逝者隐私权而拒绝其近亲属进行继承。
因此,社交虚拟账号的继承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就应当被准许继承。接下来是虚拟财产继承的技术障碍问题。目前用户虚拟财产的保管是用户与平台因使用协议引发的保管义务,平台对用户财产无偿保管,只需做到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即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显然是一种薄弱的关系。因此应当设定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来明确平台的保障义务。
3 网络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3.1 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与内涵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为了使特定的人免受人身与财产的损害,而由特定的人所负有的义务。这一学术概念来源于德国法上的“一般交往安全义务”,并广泛应用于交往安全领域。主要目的是在交往的过程中防止和避免危险发生,安全保障责任人应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防止给他人造成损害。安全保障义务的实施需要经营者或管理者的积极作为,要求其主动提供具有合理保障功能的配套设施和管理人员进行维护。
3.2 网络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依据
(1)危险控制说:网络平台具有公共性和经营性。根据学界提出的危险控制说理论,即经营者因经营活动开启了对进入其经营场所者的危险,故负有控制该危险以避免其实害化的义务。经营者在开启经营活动时享有了获取收益的权利,也应当承担防止危险发生的义务。该学说强调公众进入到经营场所领域,会引发经营者对危险管控的义务。网络服务平台的进入一般不具有特殊的限制,具有面向不特定多数人的非排他性、非禁用性性质。用户仅需注册登录后即可浏览网页内容、发表评论、进行交易,由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网络平台作为交流活动的载体,应当被视为具有公共属性。另一些网络平台如淘宝店铺、抖音直播间等,平台本身的流量经济和用户借助平台这一工具进行交易并向平台支付报酬都体现出了平台的经营属性。因此网络平台也属于经营场所,用户进入网站浏览、交易的行为属于进入经营场所领域,由此引发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
(2)控制力学说:平台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控制力学说认为公共场所或活动的经营者、管理者或因对服务设施、设备及场地的实际控制,或因对直接造成损害结果的第三人具有管控能力,负有对损害的防控义务。用户在登录使用平台时,需同意平台拟定“一切解释权归平台所有”的条款。用户的行为也会受到平台的严格限制,只能在平台设定的情形下活动。而平台作为经营者,比用户更加熟悉平台的操作系统,对系统进行操控,及时修复系统漏洞便可保障用户的虚拟财产安全,且平台对可能造成的侵害结果具有更强的预防和控制能力。用户可以做的仅仅是设置安全强度较高的密码,无法对防止虚拟财产被技术黑客窃取或者平台漏洞导致的虚拟财产丢失作出更加有效的防护措施。虚拟财产的维护一切都有赖于平台的积极作为,因而从控制力大小的维度来看,平台应当担负起用户财产的安全保障义务。
(3)依赖性学说:用户行为对平台设置的高度依赖。依赖性学说是学者依据网络平台与用户之前的密切联系提出的专门针对网络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依据。用户基于对平台的合理信赖,相信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利益不会受到侵害。因此平台有义务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这一学说包含了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思想,很好地解释安全保障义务中“经营者或组织者应防止自身行为对特定的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的侵害”。
4 虚拟财产的继承路径
4.1 建立与完善网络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1)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启示。《民法典》的第1198条明确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并给出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一般性适用主体和范围。第1038条也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的特殊情境,规定了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由此认为安全保障义务的客体可以是本质为二进制代码的虚拟物和电子数据,安全保障义务也可以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中。
网络平台经营者对用户虚拟财产的保护同样可以借鉴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模式。《民法典》第1038条给信息处理者设定了不得泄露或篡改个人信息、未经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采取技术措施和手段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以及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的义务。这符合安全保障义务“防止特定主体自己以及第三人对特定的人的人身和财产上的侵害”的设置思路。对比来看,网络平台的管理者对存放在其平台中的虚拟财产也应承担不随意封号、删除、篡改的义务,并采取必要技术措施和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来保证虚拟财产的安全。另外,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5条第一款的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个人有权撤回其同意。网络平台经营者在管理兼具人身和财产属性的虚拟财产时,还同时作为虚拟财产包含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因此平台安全保障义务还应当包括允许用户撤回或删除已提供的个人隐私或个人信息,不得擅自保存或恢复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等。
(2)司法实践中平台安全保障义务适用的启发。司法中,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早已扩张到了网络虚拟空间。例如在牛某某网络服务合同案中,牛某某在某GAME游戏平台上寄存了一批游戏饰品,后平台以STEAM市场政策和规则变动引发为由封禁了牛某某的账号,导致游戏饰品无法取出。平台提出将牛某某的游戏饰品进行市场价格评估,以等价的游戏币补偿,但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法院认为平台作为管理者,应负有保障用户虚拟财产不受其侵害的安全保障义务。从司法实务中看,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还应包括“不得擅自变更、修改”,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况下应当由无过错方来选择赔偿的方式。
(3)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变通。不容忽视的是网络平台与传统实体场所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如安全保障义务时间长短的不同。现实中,用户一旦在平台上注册账号,即被视为长久地進入到了该领域活动,成为平台的长期使用者,直至账号注销。而“一旦注册便不会刻意注销”是网络服务行业一种商业习惯。在此期间,平台始终负有保障用户虚拟财产不受平台直接损害以及防止或制止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义务。网络服务平台的用户数量比传统实体场所庞大,因此其保障难度也就相对更大。
用户在网络服务平台上的活动通常不面临人身危险性,还可以通过设置高强度密码对自己的虚拟财产进行保护,且大多数平台是无偿提供虚拟财产的存储服务的。为促进虚拟财产可继承的发展,可以通过限定网络服务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责任限度来解决我国目前安全保障义务内容泛化导致的管理者义务过重的问题。
4.2 不同类型虚拟财产的继承方式
(1)具有一般财产属性的虚拟财产继承。具有一般财产属性的虚拟财产可以同其他财产一样被全部继承。结合司法实践发现,这类虚拟财产在侵权损害赔偿中无法采取恢复原状等补救措施的情况下,可以参考市场成交价格,考虑偶然因素和交易对象的缔约能力后折算为法定货币赔偿。被继承人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将自己的虚拟财产赠予他人或由法定继承人继承。网络平台可以收取一定手续费,将虚拟财产直接转移至继承人账号,由于其不涉及人格利益,也可以将被继承人账号交由继承人自己转移。
(2)兼具财产和人身属性虚拟财产的继承。这类虚拟财产涉及公民的个人隐私保护、个人信息等权利,在伦理上存在一定障碍。社交账号要求注册人以其个人的身份在网络平台上活动。账号平台也要求用户实名认证,并声明账号仅对其本人开放使用。如果继承人以被继承人的身份在网络上活动,会违背社交基本原则和公序良俗,其在网络上做出的民事行为也很难认定有效,存在有欺诈的嫌疑。司法中社交账号继承纠纷案件的解决方法是将社交账号的本身的控制权与社交账号内容分离。继承人只能继承账号中的内容,不得以被继承人的身份进行网络活动。这与人格权篇中规定的“身份是不得被继承的”具有一致性。
继承上,还应注意尊重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网络平台应当允许用户自主决定是否保留其去世后服务器中的数据。
参考文献
[1]林旭霞.虚拟财产权性质论[J].中国法学,2009,(1).
[2]李威.论网络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J].河北法学,2015,33(7).
[3]岳林.网络账号与财产规则[J].法律与社会科学,2016,15(1).
[4]李雅男.民法典视野下社交网络账号的继承[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24(01).
[5]王利明.人身賠偿损害疑难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