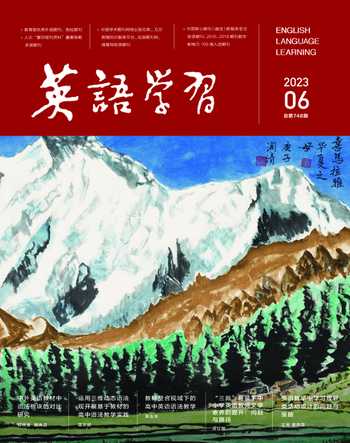《长日留痕》与隐性帝国主义话语
2023-06-27曾远卓
曾远卓
摘 要:《长日留痕》是当代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怀旧文化浪潮的产物。作为一部关于英国帝国主义历史的寓言性作品,该小说一方面展现了帝国霸权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对帝国往日辉煌的赞美和怀念。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分析小说中对帝国主义罪恶的描写,认为其主旨是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但却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它与帝国主义话语之间微妙的重合关系。本文旨在揭示该小说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隐性支持,并对其话语机制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解读视角。
关键词:《长日留痕》;石黑一雄;帝国主义;历史小说
《长日留痕》与帝国主义
《长日留痕》是石黑一雄创作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89年。该书时间设定在1956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史蒂文斯是一个步入暮年的英国管家。史蒂文斯自青年时期跟随父亲步入管家行业,并树立了效力于一位伟大英国贵族、维护帝国稳定进而使全世界受益的人生理想。为此,他进入了热衷國际事务的达林顿勋爵府中,全身心投入服务工作。然而,其主人在多年的秘密外交中被纳粹政客洗脑,说服首相采取绥靖政策。小说的内容是史蒂文斯驾车旅行期间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
英国帝国主义是贯穿作品的一个隐性主题,达林顿府是大英帝国的一个缩影,史蒂文斯和达林顿勋爵两个主要人物的人生轨迹象征着帝国的兴盛与衰落。Lang(2000)和McCombe(2002)均注意到小说叙述开始的时间是1956年,即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之年。他们认为这一时间选择绝非巧合,因为苏伊士运河危机标志着英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衰落,所以小说从一开始就与后殖民主题产生了联系。Terestchenko(2007)指出,史蒂文斯全身心为大英帝国的权贵服务而丧失了个人幸福,他的悲剧代表帝国主义官僚体系对劳动阶级造成的危害。王烨(2018)认为,这部小说通过主仆二人的悲剧性结局讽刺与质疑了民族主义与父权制。还有相当多的文章剖析了史蒂文斯的心理活动与叙述风格的关系,指出其中包含大量的不可靠叙述元素,如矛盾、回避、否认等,反映出他受到帝国主义体制压迫而产生了痛苦与悔恨(MacPhee,2011;Khosravi & Barekat,2017;邓颖玲,2016)。总而言之,相当多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这部作品是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然而,小说对帝国主义是否持彻底的批判态度?这一问题涉及小说隐含的政治话语,本文将对此作进一步探究。
本文认为,《长日留痕》是一部对帝国主义持矛盾态度的历史小说:它在表层揭示出帝国主义的危害,却在深层与帝国主义话语形成了某种“共谋”(complicit)效应。主人公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机器对他的异化和剥削,但他从未想过辞职,且在回忆叙述中始终表现出无怨无悔的态度,这说明了他对帝国主义价值观的深刻认同。尽管他在达林顿府工作期间察觉到了主人与纳粹的勾结,并受到了主人独裁的压迫,却从始至终坚持履行一个“完美管家”的职责。因此,史蒂文斯绝非仅是帝国体制的受害者,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帝国事业的支持者。
帝国理想的美化书写
本节探讨的帝国理想是指史蒂文斯和达林顿致力于让英国保持强盛,将全世界控制在其设计的“理想”秩序之中,从而使全人类受益的“乌托邦”情结。达林顿是一个世袭贵族,本可以养尊处优,却自愿为国际事务终日操劳,渴望恢复一战前由英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史蒂文斯立志成为一名杰出的管家,渴望投身于一位伟大的英国绅士门下,为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帝国主义理想成功将他们个人与社会层面的追求绑定,使其心甘情愿为大英帝国工作。在整个故事中,小说有意识地在史蒂文斯的政治理想、英式田园风光和女管家肯顿小姐三者之间搭建起联系。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实际上将帝国理想隐喻为自然和爱情意象。
研究表明,英国文学中的英式田园风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传统的紧密关联(Mitchell,2002;蒋怡,2013)。正如Mitchell(2002:1—2)在《风景与权力》(Landscape and Power)中指出的那样,景观“不仅仅体现或象征权力关系;它本身就是文化权力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对自然元素的刻画反映了文学作品中深藏的文化社会建构,透露了融入作品创作过程中(不论有意或无意)的一些政治情感。在《长日留痕》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风景与史蒂文斯的帝国主义思想之间的联系。作品对英式乡村的描写始终是正面的,而且主人公对风景的欣赏与其帝国理想时常并置。田园风光是贯穿史蒂文斯旅行的一条重要线索,作品对风景的刻画反映了其对英帝国的情感态度。
以故事开头部分的一个情节为例。史蒂文斯在驶离达林顿府不久后停车休息,在当地人的建议下登上一处山顶俯瞰田园风光。登山远眺激起史蒂文斯的豪情壮志,他借景抒情,进行了大量赞美:
英格兰的风景是无可媲美的……相对而言,在诸如非洲、美洲那样的地方所呈现的种种风情毫无疑问会让人非常激动,然而我却很肯定,由于那类风情过于不恰当地外露,反而会给实事求是的评论家留下稍逊一筹的印象。(26)*
史蒂文斯在赞扬英格兰风景的同时贬低其他国家的自然景观,这体现了一种过度骄傲的民族主义。Trimm(2009)指出,史蒂文斯视为等而下之的自然景观来自非洲和美洲,是英国曾经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地区,这并非巧合,而是暗示了英国对本国殖民历史的骄傲心理。也就是说,史蒂文斯身上体现了鲜明的沙文主义情结。
小说刻画了史蒂文斯的沙文主义思想,但并未对其进行讽刺或否定。史蒂文斯认为英格兰有全世界最优越的景观,这一观点虽然主观,但其实得到了文本的支持。小说用大量篇幅刻画了英式田园“静穆的优美”和“高贵的克制”的特点,这与美学家温克尔曼提出的“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相吻合(胡继华,2016:78—81),体现出西方古典美学的典型特征:
正是因为缺乏一目了然的刺激,或者奇观,才使我们国土美丽得超凡脱俗。也正是那种静穆的美丽,以及它显示出的那种严谨的感觉才是最贴切的。这片土地似乎了解自身的美丽所在,亦知道自身的宏大,它才感到无需招摇。(26)
古典审美注重情感表达的克制内敛,赞美艺术形象蕴含的平衡与稳定。这种美学特征在近现代欧洲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它代表了人们对古代欧洲的审美想象,象征着崇高与优美、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胡继华,2016)。史蒂文斯认为英式田园优于非洲、美洲等“让人非常激动”的天然奇观,因为它是宁静质朴的乡村景观,也就是经过充分“规训”的文明景观。小说用田园牧歌式的风景象征大英帝国,建构了后者的古典美学形象,诱导读者产生怀旧情绪。小说通过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具有前现代特点的景观,间接抬高了宗主国的文化艺术品位,塑造了稳定和谐的帝国正面形象。
史蒂文斯对英国民族性的赞美逐渐滑向了种族主义,在抬高英国的民族形象的同时贬低其他民族。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话语的核心之一,史蒂文斯对英国风景的抒情称颂最终指向的是种族主义,小说对帝国主义话语的支持在此表露無遗。小说运用诗化的语言描绘英国的自然风景,隐喻英国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主体地位,旨在引发读者的共情效应。文本间接鼓励被统治者认同并实践帝国理想,从而使其得到帝国主义体制的承认,从帝国整体的价值中分得自己的价值。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在英国海外殖民时期屡见不鲜(卡尔德科特,2021)。
英国在史蒂文斯旅行开始时已进入了“后帝国”时代,由于帝国的衰落,“怀旧”(nostalgia)一词在英国文化中经常指向对帝国全盛时期的夸张与想象(Trimm,2009)。甚至一些英国史学著作关于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书写也融入了浪漫主义式美化(卡尔德科特,2021)。以这种方式描绘帝国鼎盛时期的文学和历史作品忽视了帝国统治的霸权、剥削等罪恶,因此与帝国主义形成了隐性共谋关系。《长日留痕》通过主人公的不可靠叙述高度美化了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发生的事件和场景,流露出史蒂文斯对帝国往昔的强烈怀念,从侧面渲染了帝国曾经的“宏伟理想”。然而史蒂文斯记忆中的场景并不真实,因为他已经将自己的帝国理想与自身理想融合,成为叙述的一部分(邓颖玲,2016)。英国帝国主义在二战后彻底破产,但是本书的主人公在追忆帝国鼎盛时期时依然处处流露出对帝国理想的怀念与支持。
史蒂文斯的父亲曾经是一位优秀的管家,史蒂文斯在他的影响下步入管家行业并一直视其为模范。然而一天在给喝下午茶的达林顿和客人服务时,他因为突发中风在草坪的台阶处跌倒,打翻了盘子中的物品,成为其职业生涯的一次尴尬事件。史蒂文斯父亲对那次事故耿耿于怀,独自在台阶处重复上下楼梯的动作。这一幕被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看到,于是有了一段诗化的描写:
只见夕阳射出的缕缕橙黄色的光柱如箭一般刺破了走廊里的朦胧。过道里的每一间卧室的门都半开着,在我走过那些卧室时,我透过一扇门瞥见了肯顿小姐的轮廓,她的侧影印在一扇窗户上……我们能看见我父亲的身影,他好似陷入沉思之中,慢慢地踱着步——也宛若肯顿小姐那逼真的描绘:“似乎希望找到那些他丢在那儿的珠宝。”(46)
这一事件在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的叙述中多次出现,并且深刻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结合上下文我们不难发现其原因:史蒂文斯的父亲在小说中一直以雷厉风行、不苟言笑的形象示人,多次以言语和行动教导史蒂文斯要忠于主人和国家而牺牲自我。他是父权制文化的典型人物,也是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敬畏并模仿的对象。如今他年老体衰,在服务中出现重大事故,这一形象变化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不小的冲击,尤其是史蒂文斯。有学者指出,“珠宝”象征着英伦三岛,史蒂文斯父亲中风跌倒象征着大英帝国维持殖民体系已力不从心(鲍秀文、张鑫,2009)。因此,这一情节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即史蒂文斯父亲作为榜样与依靠的形象的衰落象征着父权制传统和帝国统治的衰落。
达林顿府发生的变迁是大英帝国兴衰的隐喻象征,小说对其进行了浪漫化的诗意描写,呈现出凄婉幽怆的氛围。这段描写组合了一系列凄美的意象,如夕阳、薄雾、草坪、恋人的侧影、柔声细语等,令帝国的衰落变成一曲令人惋惜的田园哀歌。小说将帝国的衰落与爱情和亲情的逝去相结合,增强了感人的效果。此处的情境呼应了书名“长日留痕”,象征着帝国鼎盛时代的终结。作品富有悲情色彩的环境描写显然没有引导读者为帝国时代的终结欢呼,而是希望读者跟随史蒂文斯的视角对帝国盛世的终结产生同情:帝国衰落意味着父权制文化带来的稳定和依靠不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传统温情的消失。怀念帝国盛世同样意味着怀念帝国强盛时期的价值观,帝国鼎盛时期在小说中被赋予了一种社会较为稳定、人际关系充满关爱的“前现代性”特点。
肯顿小姐在一封信中也仔细回忆了这个场景,她的叙述充满同情与感伤。和史蒂文斯一样,她也用细腻优美的语言从自己的角度描绘了在三楼窗边看见的落日美景(45),显然这包含了对达林顿府,即大英帝国缩影的浪漫化环境描写。通过史蒂文斯可知,女管家的日常工作是充满辛劳和不悦的,肯顿小姐曾多次抗议工作量过大,甚至一度想要辞职。但是在她的叙述中,这些不愉快的记忆都被掠去了,剩下的仅是充满诗意的场景,激发了读者的怀旧情绪,尤其是“带着几分魔力”的夸张表述增添了浪漫化想象。肯顿小姐以前从来不会向史蒂文斯示弱,并声称自己比史蒂文斯更加全心投入工作。但她在这封1956年前后的信中却坦率地承认自己曾经在工作期间“浪费时间”欣赏庄园的景色,并用大量诗意浪漫化的语言来描述。这说明二人的隔阂后来已经彻底消除,共同为逝去的美好岁月和帝国的衰落惋惜。小说前文交代美国人法拉戴买下达林顿府,并因为客人稀少而将三楼的房间全部封闭。这意味着能够从三楼窗户看到落日美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隐喻理想的生活也随着帝国衰落而尘封。
当二战结束、达林顿府内一片萧索衰败之际,史蒂文斯由信中透露出的怀旧情结推测出肯顿小姐“重返达林顿府的强烈欲望”,所以主动前去和她会面。这种怀旧情结是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共有的情感,也是文本自始至终努力向读者表现的主题。在小说结尾处,两人虽终于互表爱慕之心,但却由于现实羁绊而无法产生任何结果。这一结局无疑增添了主人公命运的浪漫主义悲剧色彩,引发读者的共情。小说通过肯顿小姐向史蒂文斯的表白直接挑明了一种对过去岁月的留恋和对当下状况的不满,将怀旧情结推向高潮。这种叙述方式将大英帝国的统治理想化,向读者透露出这样一种感觉:帝国体系的益处远大于弊端,个人情感的创伤会被治愈,而帝国秩序的崩溃才带来了真正而持久的苦难。
帝国历史的辩护书写
达林顿在从事政治活动的二十年里犯下了两项严重错误:打压民主制度、推行绥靖政策。他是大英帝国统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的错误象征着二战前英国政府的重大决策失误(Lang,2000;McCombe,2002)。对于这段不光彩的帝国历史,小说在艺术加工时进行了一些辩护,体现出修正主义(revisionism)历史观。
达林顿代表着精英主义政治家,他认为民主制度效率低下,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因此决定绕过议会直接干预政治。小说通过以下情节支持了其精英主义思想的合理性:某天晚上达林顿和几位朋友在客厅讨论一些重大议题,其中涉及是否应该继续维持民主制度的问题。为了证明普通民众的“无知”,有客人故意刁难史蒂文斯,问了他三个政治经济方面的专业问题,令后者无言以对。事后达林顿向史蒂文斯解释道:“面对每一个新时代的那些挑战就意味着要抛弃过时的、曾几何时爱不释手的方法……民主是某种适合过去时代的东西……德国和意大利已经以实际行动将其内部整顿好了。”(185—186)他列举了苏联和美国等国采取的激进手段,批评英国民主制度低效且不合时宜:“甚至连罗斯福总统,你看看他,他代表人民的利益义无反顾地采取了若干大胆的措施……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只是辩论、争吵以及因循守旧。”(186)
史蒂文斯面对刁难虽感不悦,但始终理解并支持达林顿的亲纳粹政治倾向,自愿被排挤到国家权力的边缘,并在叙述中积极为主人辩护。他认为精英政治比民主政治更加理想,只有达林顿那样的大人物才能创造历史,而自己在帝国中的角色注定是坚定地服从领导:“让我们非常明确地对此加以界定:男管家之职责便是提供良好的服务,而不是干预国家大事。事实上,这类大事将总是超出你我这类人的理解能力……”(187)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民主制度一度遭到严重打压。这既是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造成的,也是英国帝国主义对内剥削加剧的结果。在小说中,达林顿有时以一个独裁者的形象出现,单凭自己的意志干涉政治,全然不顾他人的反对。但他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没有成家,终日操劳,以至于健康受损——“他那一向纤细的身躯已瘦削得令人吃惊,某种程度上已变得畸形,他的头发过早花白了,面容憔悴而又显得紧绷绷的”(185)。达林顿在此被塑造成了为帝国利益事必躬亲、力排众议,却不幸犯下错误的悲剧英雄形象。
除了打压国内的民主制度,帝国的统治阶级还犯下了另一个重大错误。20世纪30年代,许多英国贵族对纳粹德国持积极态度,希望与纳粹德国合作以克服大萧条造成的停滞。英国默许纳粹德国向东扩张,这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妥协,因为英国对德绥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要以最低的成本维持其全球帝国的稳定(奥弗里,2019)。小说以一种修正主义的态度书写这一时期英国与法西斯主义的共谋,将达林顿的亲纳粹思想与行为描述为一项旨在解决国家问题的尝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的描述与真实历史也存在较大出入。史蒂文斯称,达林顿等政客与纳粹德国的来往即使在事后看来也并非不可原谅,因为纳粹政客善于伪装,欺骗了大多数英国人;他们在小说中的形象刻画相当正面(王卫新,2010)。例如:“而事實上,在整个1930年代,那些最显赫的府邸都将里宾特洛甫先生视为颇受人尊重的人物,甚至是富有魅力的人……这个国家里许多最显贵的女士和绅士都非常爱戴他。”(129)然而历史事实是,里宾特洛甫在英国并不受欢迎,许多英国政治家都看穿了他的面目而对其加以提防(Wilkinson,2001)。
有学者认为,史蒂文斯悲剧的根源是他对自身命运和政治环境缺乏独立思考,因此最终与个人幸福和职业理想失之交臂(Rushton,2007;Terestchenko,2007)。MacPhee(2011)认为,史蒂文斯这一角色象征着对独裁专制的愚忠,是法西斯阵营中“平庸之恶”的化身。然而本文认为,小说虽然将史蒂文斯塑造成对勋爵唯命是从的工具人,但对他的态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认为史蒂文斯作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允许的最好选择,将史蒂文斯持有的帝国主义理想塑造为相应历史条件下最合理的思想。史蒂文斯多次表明自己愿意绝对服从帝国统治阶级的原因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即服从帝国权威的指挥来建设一个美好的帝国和世界。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贬低自身而尊崇权力,视前者为“边缘”,视后者为“中心”。在英帝国的历史中,统治阶级一直努力向被殖民者灌输这种意识形态,使后者驯顺地服从殖民统治(俞可平,2022)。每当史蒂文斯陷入怀疑和犹豫时,都会向自己灌输这一思想,从而使自己回归对霸权的服从。林萍(2018)运用霍米·巴巴的“模拟”(mimicry)理论来解释史蒂文斯的忠诚,认为史蒂文斯对达林顿勋爵的绝对服从代表了“精英即是标准”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现在从思想到行动都以后者的表现为准则。
在民主还未普及,普罗大众(proletariat)未能充分参与政治的时代,小人物的声音总是被边缘化、被压抑,例如小说的叙述者史蒂文斯。他的自我意识并未觉醒,因而成为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话语的拥护者,为塑造英国殖民主义时代“完美管家”的形象,进行自我压迫与异化,并从中寻找意义。尽管史蒂文斯的命运令人惋惜,但他对帝国的忠诚毋庸置疑。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斯虽然经历了个人理想与帝国理想的双重幻灭,但是他成功坚守住了自己的情感与尊严(石黑一雄,2018),并未否定自己的追求。综合前文的分析,笔者发现小说透露出这样一种态度:达林顿虽然遭到纳粹利用而成为其帮凶,但始终拥有良好意愿,因而不应遭到全盘否定;而史蒂文斯虽然曾经压迫下属、漠视感情,甚至纵容纳粹,但本质上是为一个美好宏大的目标努力,因此也不应遭到全然批判。史蒂文斯对帝国的忠诚保持到了全书结尾,并没有随着殖民帝国的崩溃而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服务美国新主人)延续下去,并成为其对抗社会巨变带来的现代性冲击的精神支柱。
石黑一雄与英国历史书写
《長日留痕》一书反映了二战后英国各种政治思潮相互碰撞的社会环境。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动荡,传统英式社会价值观,即维多利亚价值观(Victorian values),面临严重挑战。在如何处理英国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遗产问题上,英国社会陷入了一定的矛盾(梅丽,2018)。撒切尔政府呼吁英国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政治上倡导新保守主义,经济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希望英国国力能够再次迎来“觉醒”。这种政治宣传迎合了一些英国人的怀旧心理,催生了一波怀旧风潮。然而,一些人担心这种怀旧会为帝国主义“招魂”,因此主张抵制这种怀旧文化。石黑一雄也受到了这场文化论战的影响,而他的态度更倾向于支持怀旧文化。他曾经在采访中坦言自己不认为英国社会应否定历史的意义,而应积极面对历史,多维度发掘其价值,并在文艺作品中体现出来(谢弗、黄,2021)。从这一角度看,书名“长日留痕”隐喻英国如日中天的帝国时代已经逝去,但残留下来的“余晖”却值得思考与回味。小说作者的态度也支撑了本文对小说主题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帝国主义话语重合并不意味着其为帝国主义正名。石黑一雄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探索人对历史与当下的新思考与感受方式——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石黑一雄在面对历史的阴暗面(同时包括个人和国家层面)时也带有矛盾态度,他深知“自我欺骗”式回忆对于维持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信仰的重要性(谢弗、黄,2021)。正如他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所说的那样,“是否在某些时刻,遗忘是终结冤冤相报,阻止社会分裂瓦解、陷入战乱的唯一途径?”(石黑一雄,2018:32)他说自己想在文学创作中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但“很不幸,我想不出我该怎么做。”(石黑一雄,2018:32)作者的这种困惑有助于解释小说中体现的对帝国主义主题的矛盾态度。
小说的一个隐含主题是希望人与世界的不完美和生命的缺憾和解并对未来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我们从石黑一雄诺贝尔文学奖致辞中不难发现,他认为仅仅批判邪恶可能无助于消除它,欺骗和遗忘有时是更具人文主义精神的选择。他多次在访谈中坦言自己经常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文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地反映并批判历史中的恶(石黑一雄,2018;谢弗、黄,2021)。他认为对历史之恶的现实主义描绘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会巩固其存在,因为此类书写可以使不堪的记忆停留在人类的意识中,不断揭开历史遗留的创伤,甚至为类似罪恶的再次发生提供土壤;而篡改和遗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人治愈精神创伤、实现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从而能更积极地面对未来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对帝国主义的矛盾态度也可以理解为主体在应对现代性危机与创伤时进行的修正主义式审美加工。另外,石黑一雄曾说世界本质上是难以被主体理解的,绝对可靠的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自我欺骗是认知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状态,而管家这一角色正是人类这一生存境遇的一个隐喻(谢弗、黄,2021)。因此作者对有着良好意愿却犯下错误的人有着异常宽容的态度。他曾说:“我们都是管家”(谢弗、黄,2021:145)。这种带有强烈不可知论色彩的世界观不禁让人想起诺贝尔奖委员会给他的评语:“石黑一雄的小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展现了我们与世界相连的幻象之下的深渊。”综上所述,小说隐含的帝国主义话语应当被批判,但其包含的美学价值与哲学思考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结语
《长日留痕》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正值英国怀旧文化盛行时期,因此作者带有对帝国时代荣光的向往和赞美是不难理解的。本文指出小说以达林顿府的兴衰折射大英帝国的兴衰,从小人物的视角叙述历史,含蓄地为英国帝国主义者的理想及其实践进行辩护,美化了帝国,特别是帝国贵族的形象。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小说对英国帝国主义的负面描写,认为它是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本文承认小说的确揭露了英国帝国主义历史的阴暗;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其关于帝国主义的矛盾叙述和暧昧态度(ambivalence)。因此,本文旨在识别和分析文本中的隐性帝国主义话语,从而提供一个不同的阅读视角,以加深我们对小说主题的理解,并希望对未来相关方向的研究有所启发。
石黑一雄善于在小说中运用不可靠叙事手法,将历史中有争议的方面带入审美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视域(沈安妮,2020),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治问题转化为美学问题,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他希望鼓励读者更好地与现代性带来的创伤和解,以更乐观的态度与方式生活下去,就像这部小说结尾处的史蒂文斯一样(谢弗、黄,2021)。在后殖民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的时代,这部小说对英国帝国主义历史的独特书写值得更广泛的重视与研究。
参考文献
Khosravi, S. & Barekat, B. 2017. The suppression of meaning in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A narratological study [J]. Modern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7(4): 222—234
Lang, J. M. 2000. Public memory, private history: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J]. Clio–A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29(2): 143—165
MacPhee, G. 2011. Escape from responsibility: Ideology and storytelling in Arendts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J]. College Literature, 38(1): 176—201
McCombe, J. P. 2002. The end of (Anthony) Eden: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and midcentury Anglo-American tensions [J].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48(1): 77—99
Mitchell, W. J. T. 2002. Landscape and power [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ushton, R. 2007. Three modes of terror: Transcendence, submission, incorporation [J]. Nottingham French Studies, 46(3): 109—120
Terestchenko, M. 2007. Servility and destructiveness in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J].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5(1): 77—89
Trimm, R. 2009. Telling positions: Country, countryside, and narration in The Remains of the Day [J]. Papers on Language & Literature, 45(2): 180—211
Wilkinson, R. 2001. Joachim von Ribbentrop ‘the most brainless boy in Hitlers class? [J]. History Today, 51(11): 18—22
奥弗里. 2019. 二战爆发前十天[M]. 吴奕俊,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鲍秀文, 张鑫. 2009. 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象征[J]. 外国文学研究, (3): 75—81
邓颖玲. 2016. 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回忆叙述策略[J]. 外国文学研究, (4): 67—72
胡继华. 2016. 浪漫的灵知[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蒋怡. 2013. 风景与帝国的记忆——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视觉政治[J]. 外国语言文学, (2): 124—131
卡尔德科特. 2021. 大英殖民帝国[M]. 袁炜, 译. 沈阳: 沈阳出版社.
林萍. 2018. “英国性”的拷问: 后殖民视域下的《长日留痕》[J]. 当代外国文学, (1): 126—132
梅丽. 2018. 从《长日留痕》看英国“二战”后的文化困境[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 15—21
沈安妮. 2020. 跨媒介的审美现代性: 石黑一雄三部小说与电影的关联[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石黑一雄. 2011. 长日留痕[M]. 冒国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石黑一雄. 2018. 石黑一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M]. 宋佥,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卫新. 2010. 试论《长日留痕》中的服饰政治[J]. 外国文学评论, (1): 216—223
王燁. 2018. “后帝国”时代英国乡村神话的祛魅——石黑一雄小说《长日留痕》的空间权力分析[J]. 当代外国文学, (3): 137—143
谢弗, 黄. 2021. 石黑一雄访谈录[M]. 胡玥,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俞可平. 2022. 帝国新论[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7(2):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