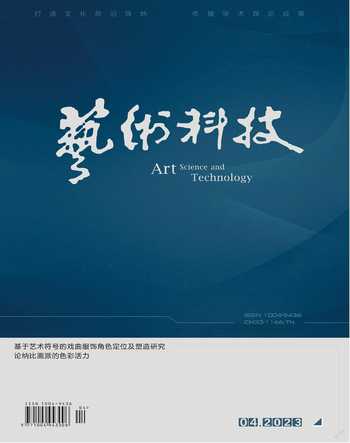论《女贞汤》中女性话语的喧嚣与沉寂
2023-06-22李俊
摘要:《女贞汤》是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刘索拉的长篇小说,作者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对历史与革命、神话与女性进行了想象与评述。小说既可看作一部关于历史及其真实性的作品,更可看作历史中“看不见”的女性群体的故事。文章首先借用“女贞汤”这一具有深层意义的象征物,以希撒玛的个体命运和娇艳、京之、莫姑娘等女性的群体遭遇为对象,还原了女性形象和女性个性被歪曲和泯灭的历史现场,深入分析身陷“女贞汤”桎梏中的女性群体的悲剧命运及造成这一悲剧的历史根源——父权制文化。然后结合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女性话语实践,发掘大量零散存在于小说文本内部的女性声音,试图寻找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对抗的可能性。一方面,那些曾经被主流所忽略和淹没了的女性的感受、经验与思考得以重见天日,女性话语在短暂的喧嚣中彰显力量;另一方面,女性言说自我与历史却必须以死亡为前提,小说中的女性群体只有化为魂魄后才能真正地开口,短暂的喧嚣最终归于沉寂。这意味着女性话语权的争取往往伴随着极其沉重的代价,最后也往往以失败告终。小说文本不自觉地呈现出女性话语从可能到无效的信号,对反思女性话语中的抵抗力量和构建新的女性话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女性形象;女性话语;《女贞汤》;刘索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4-0-03
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它向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发起挑战,力图寻找女性在历史、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并以女性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挖掘长期被父权制文化压抑的女性文学和文化传统,构建新的女性话语,重塑女性主体。
《女贞汤》是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刘索拉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百年孤独》式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了公元4000年后一个从西边来的游牧部落在大岛上的传奇故事,呈现出继氏家族六代的兴衰荣辱。表面上看,小说的时间设定在遥远的未来,实际上作者是通过陌生化的方式,以女性的视角重新阐释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在历史中沉默的女性终于开口了。刘索拉在小说中塑造了近20个女性形象,并且专辟章节让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些长期以来被历史与文化所压抑的女性的欲望、经验与思考开始浮出历史地表。然而有意思的是,那些能够开口吐露真言的女性大多以鬼魂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处在一种非现实的空间内,女性话语才是被许可的,而且它往往是一种单向的输出。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刘索拉站在女性的角度自觉地创作,书写女性经验,表达女性的思考,争取女性话语权,但不可忽视的是,小说文本又不自觉地呈现出女性话语注定失败的信号,这种矛盾的存在对我们反思女性话语与构建女性主体具有重要意义。
1 “女贞汤”的象征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在她看来,性别角色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性那些不同于男性的心理或身份都是父权制对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因此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体现为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且这种权力关系不只体现在经济压迫上,还充斥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女贞汤》中的那一味草药——女贞汤便是大岛上文化、权力的象征,具体来说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对女性的教化与束缚。
1.1 从“妖妇”到“天使”
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两人合写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总结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传统下的文学作品中两类比较极端的固定的女性形象,一类是集美丽与善良于一身的完美女性形象——“天使”,另一类则是集邪恶与灾难于一身的“妖妇”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天使”往往是顺从忠实、委曲求全的客体,而“妖妇”身上具有的不受父权控制的独立人格和思想则充满了危险性。在《女贞汤》中,从希撒玛到莲英呈现出“妖妇”向“天使”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关键是香囊道士的女贞汤。女贞汤是一味草药,经常服用便可以祛除妇人的阴烈之气,“这药可灭她虎豹之心,软其尖牙利爪,散其眼中凶光,抽其丹田壮气,造出个淑女佳人来”[2]49。
希撒玛原本是女人寨里最漂亮的女人,因为从小和豹子一起长大,和豹子玩耍、练功夫,所以浑身上下充满着豹子般的野性气息和原始的魅力,此时的希撒玛在男人的眼里如同“妖妇”一般。遇到从大岛上来的继合并与之结合后,继合给她改了名字,唤作莲英,名字的替换是父权制下女性变得无名的第一步。之后,希撒玛和继合回到大岛上生活,岛上的居民便开始猜测和造谣希撒玛是豹子。对大岛上的汉人来说,豹子象征着原始与野性,是未被驯化的野兽,潜藏着许多危险因素,其中包括取代男人位置的威胁性,所以必须寻找各种理由将其驯化并同化。面对强大的父权制文化和习俗,希撒玛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和反抗的机会,最后只能服用香囊道士的女贞汤,变得眼中无光,行动迟缓,终于变成所谓的淑女,变成男性所期待的“天使”。无论是“妖妇”还是“天使”,都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想象,都是男性作家笔下被歪曲的女性形象,模糊了女性真实的模样和姿态。
1.2 从无名到无声
在希撒玛—女贞汤—莲英的这一套文化规训中,女性先是无名继而无声,永久地陷入沉默中。希撒玛的临終遗言道出了一个更加可怕的事实,即她已经完全被汉人的文化规训所同化,认为自己无用、无价值,落得喝女贞汤的结果是因为自己太出风头了。显而易见,身陷女贞汤的藩篱中,女性的命运极其悲惨,意识不到自己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又使得这种悲剧周而复始地延续了下去。女贞汤就如同一种慢性的毒药,不仅禁锢着女性的身体,还侵蚀着女性的思想与灵魂。
父权制社会中存在的种种规范女性的社会标准,是套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束缚甚至隐蔽了女性的语言和行为,使女性长期处于男性的他者地位。而这种文化规训以一种看似合理又隐蔽的方式完成,持续了几千年。女性被钉死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内,成为没有危险性和抵抗力量的客体,长时间被压抑在历史幽暗处,沉默不语。
2 女性声音的消长
2.1 女性群像——无声的悲剧
刘索拉在《女贞汤》中塑造了近20个女性形象,其中着墨较多的是莲英、娇艳、京之、莫姑娘和继红女,小说第四部“在阴间里”完全没了男性的踪影,全是娇艳、京之和莫姑娘这三个人的魂儿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三个女性角色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身份、性格和际遇,但最终的命运却相差无几——惨死。娇艳是张大文人的小妾,平时受尽了张大文人凌辱,只因在春游时遇到继合并夸了一句“呀,好风流少年”[2]30,便被张大文人视为淫妇,并用一把巨斧砍死。京之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想的新女性,追求自由恋爱,一开始单恋继天未果,后来和继书开相恋结婚,在继书开死后,因为经常与其弟弟继书主聊天,久而久之萌发了感情,被人说成是勾搭小叔子的淫妇,后来被飞机轰炸致死。莫姑娘被胡子来强奸后委身于他,后来又受他的牵连惨遭杀害,舌头被割,身体被砍。不同的女人,却有着相同的命运,一起被推到了历史的悬崖边上。
小说中的女性在生前基本上都处于沉默的状态,偶尔的言说也是隐蔽的,如娇艳对母亲哭诉无果,京之对爱情的感受与经验是通过日记的形式记录的,而莫姑娘的申辩则是刑前的口供。从娇艳到京之、莫姑娘,时间跨越了三代人的距离,但女贞汤的效用却丝毫不逊于当年,女性无言的困境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女性的解放也并未与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同步。
2.2 女性个体——短暂的喧嚣
作为群体的女性形象在小说中是无声的,但作为个体的女性,却有机会吐露真言。刘索拉在《女贞汤》中单辟一章“在阴间里”让这些女人畅所欲言,而且她们谈论的基本上都是被社会禁止的内容,如大胆直白的性话语,无论娇艳还是京之都直言情爱与欲望,袒露自己对性的体验与感受。再如对政治与革命的看法,尤其体现在对革命英雄继天的功绩评价上。可以看到,女性声音涉及的范围不仅局限于狭小私人空间内的个体经验,还体现在对整个社会现实空间及对过往历史的重新评述。
娇艳、京之直言自己的欲望,王秀儿则通过婆婆莲英的宽慰从过去顾影自怜的愁绪中挣脱出来,她换上了莲英从女人寨带来的衣裳,瞬间变得侠气十足,非常气派,开始大声说话、开怀大笑,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模样。跳出了“女贞汤”的藩篱,希撒玛得以重生,换上了女人寨的衣裳,王秀儿获得新生,她们以女人寨独特的语言表述自己,以本真的姿态面对生活,全然一副崭新的女性面貌。
3 女性话语的失效
3.1 女性话语
福柯的哲学体系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话语,在福柯看来,话语在本质上是人类一种重要的活动,即话语实践。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启发和波伏娃关于性别建构观点的影响,认为人的性别是通过话语在社会和文化上建构的,社会将女性置于相对于男性的他者地位,女性话语处于主流话语的对立位置。如此一来,争取女性话语权力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因为这意味着争取平等的文化地位和政治权力。女性话语的争取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重视话语中的抵抗力量,对抗并解构主流话语即男性话语;二是试图建立新的女性话语,以重塑妇女主体。
女性话语是指女性出于对自身话语权的醒悟,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自觉用语言塑造自我,诉说自己的经验、对世界的感悟以及对社会历史的评价与思考。在法国派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女性话语被理解为女性身体话语或性话语,如西苏的“身体书写”、伊瑞格瑞的“女人腔”,她们认为越是被禁止的话语越能显示女性独特的话语。翻开《女贞汤》,字里行间仿佛都流淌着女性坚定的声音,特别是前文提到的“在阴间里”这一章,那些被历史长期忽略的女性经验与欲望得以显现。刘索拉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反叛和抵抗男性中心话语,力图还原女性成为“他者”“第二性”的历史现场,努力建构女性独特的话语。
3.2 女性话语的失效
从某种程度上讲,小说中女性话语的建构是失败的。因为小说中的女性在言说自我时都存在一个前提,即死亡。希撒玛的自我叙述在临终前的遗言中体现,娇艳、京之和莫姑娘都是在成为魂魄之后才吐露真言,说明只有处在一种非现实的空间内,女性的叙述才是可能且被允许的。而且,女性的叙述仅仅在一个隐蔽的空间内展开,如卧房。此外,说话人和听话人无一不是女性,或者没有听话人,如京之面对孤河诉说。如果把小说中的所有女性当作一个整体的女性形象来看,显而易见,女性的言说是封闭式的,是单方向的,甚至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话语。她们仍在自说自话,仍在历史深处低语,仍然在主流话语的边缘徘徊,得不到应有的回应,实际上就是失效的话语。
再者,也可以通过继家第五代人继红女的故事印证女性叙述历史的失败。继红女是京之和继书开的女儿,父母死后,被继书主收养,后来以革命义士遗孤的身份出国留学,深造回来之后在出版社上班,并着手书写大岛的统一历史,结果书一发表,就惨遭批判,说大岛的统一史是捏造的,充满虚构与夸张的成分。一开始,继红女怀着对大岛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力图以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语言去书写真实的历史,但在父权制阴影的笼罩下,她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最后红女也“从此消停,再不提她那本书的事了”[2]215。小说最后,大岛真的消失了,所有的书籍都没有记载与大岛有关的任何故事,继家的人也没有了大岛的回忆,历史的真实性变得模糊不清,这实际上也“寄寓着作者对百年中国历史内在荒诞性的独特体认”[3]。如果说女性鬼魂之间的话语是被允许的“恶魔的低语”,那么红女书写历史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尝试,因为在女贞汤的桎梏下,女性仍然没有掌握真正的话语权,仍然不能也无法叙述真实的历史。
4 结语
在《女贞汤》中,刘索拉以有着明显象征意义的女贞汤贯穿全文,勾勒了一幅女性悲剧命运的群像图,谱出了一首女性声音短暂喧嚣又瞬间归于沉寂的摇滚曲。小说的时间背景设定在遥远的公元4000年以后,其中关于革命的故事固然可以看作历史的隐喻,但关于女人的故事或许可以视为对历史的重现,甚至可以看作未来的预言。对话语的控制往往伴随著权力,当然这种权力是福柯所说的动态的多元化的权力,而不是传统的单一的压制性的权力,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未来,女性话语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失效的,这大概是因为女性仍然游离于社会权力机制之外,仍然处于权力运作的边缘地带。所以小说其实是在给读者以警醒:女性掌握真正的话语权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2] 刘索拉.女贞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49,30,215.
[3] 刘郁琪.历史隐喻中的女性悲歌和文化反思:评刘索拉长篇小说《女贞汤》[J].当代文坛,2004(1):44-46.
作者简介:李俊(1997—),女,湖南常德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