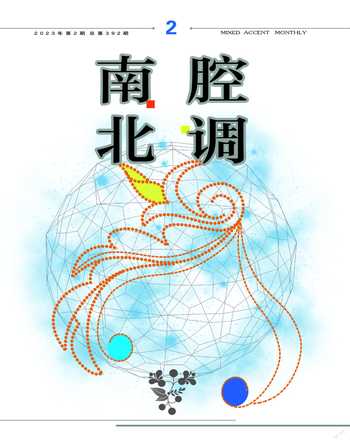代际视野下的“北京”叙事研究
2023-06-15汤静陈佳冀
汤静 陈佳冀
摘要:作为高产的“70后”作家,徐则臣在“北京想象”的命题中,呈现了理解文学北京的新特质。其作品借助“新北京人”的身份视角,将乡土与现代、时代与个体、漂泊与追寻、自省与重塑等诸多矛盾体,放置在同一坐标轴中并向深处延伸,以期探讨文学中北京的文化性格,以及北京居住者、写作者与这座城市的多种精神联系,深入挖掘现代北京图景,解读北京的“根文化”。
关键词:徐则臣;新北京人;乡土;到世界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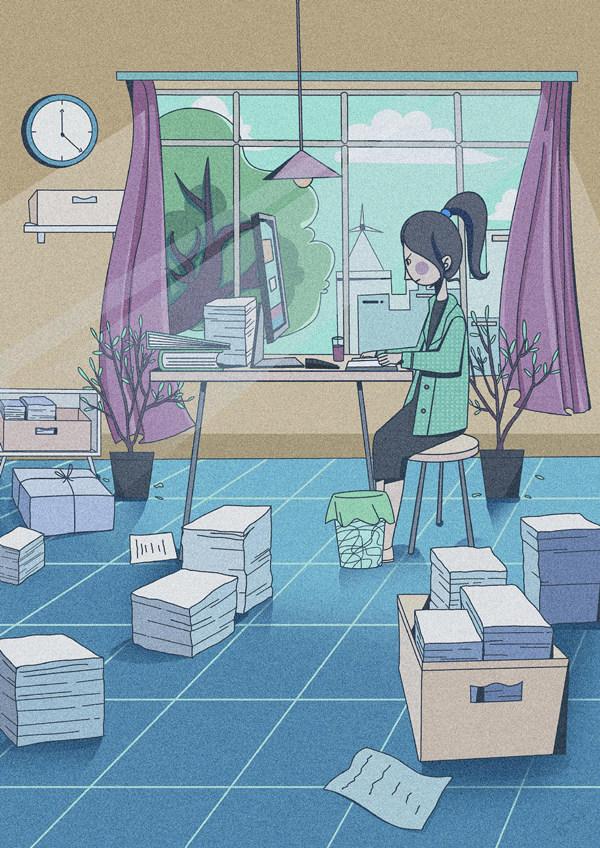
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北京”的构建逐渐向着“现代性”与“国际化”迈进,国际化都市随之成为“新北京”的代名词。伴随这一新的城市形象的产生,有关文学中的北京也呈现了不同的叙事分支:“由徐星等人对于城市青年反叛文化的叙事开始的而后由王朔在‘消费意义上的文学中展开,并在邱华栋的北京系列小说中达到高潮。”[1]这类作品以都市景观、消费主义与欲望化作为北京“现代性”与“国际化”的诠释,并通过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标志性符号的展现,建立与同时代读者的情感联系;而以徐则臣为代表的“新北京”叙事,则在延续传统京派的书写路径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对话“北京人”与“京漂群体”,并将之拓展至关于现代人、现代城市乃至世界的反思,建构起崭新的文学中的北京形象,也正是在这种理性的对话中,我们得以走进这座怀着乡土记忆的城市内里。
一、聚焦与反思:“我们这一代”
“代际”,源于社会学用语。“社会学家称这些世代群体为‘年龄同期群,它是指仅仅因为出生在差不多同一时代而具有相近年龄并因之而具有类似经历的一群人”[2]。随着各类写作群体的出现,不同的标签被分属在中国当代作家身上,“代际”的分化问题在文学领域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近年来,诸多学者都自发地选择用“文化代际”的视野去探究不同作家群体在审美观念和价值趣味上的异同。当然,每一个作家都是一个个体,用“代”来笼统地归纳作家创作的特点并不十分严谨,但由于多样的文化形式、生活方式和道德评价常常形成于同一时空维度内,因此,采用代际概念来进行文学研究,为我们探讨同时代作家创作的整体性精神提供了一条宏观的思路。
从文化代际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作家可以被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四个群体来进行研究。在这四个代际群体中,“50后”“60后”作家大多已功成名就,“80后”作家在网络大发展时代具有光明的市场前景,而被夹在其中的“70后”作家是目前看来商业价值最低的群体。然而实际上,“70后”写作者依旧是目前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70后”的尴尬处境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其中一项最不可忽略的就是时代语境。
沙蕙在《七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阐述道:“经历过动荡和过渡时期的70 后是拥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现实主义者”[3],对比“60后”“80后”,“70后”的小说创作在主題书写上呈现了不一样的气象:在成长书写方面,他们善于建构“断裂”社会中的“青春迷途”,试图寻找精神层面的寄托;在城市书写方面,他们集中精力地表现都市背景下精神分裂、错位的荒诞景象;在乡土书写方面,他们常常充当“沉默地在场”,以边缘人的身份和视角观看乡村的变化;在历史书写方面,他们自觉地追溯历史、探究历史和书写历史,试图以“70后”的话语体系还原历史的真实。特殊的时代经历给“70后”写作者带来了特殊的心绪,并让他们能够将这种成长体验灌注于小说创作中,形成迥异于其他代际的写作风格。
在“70后”的代际语境内,大规模的城乡空间流动在全国范围内涌现,无家可归的漂泊感成为集体感受,并转化为复杂的代际症候。尽管多数“理想主义”的“70后”脑海中缺乏系统的地理知识,但那些繁衍在都市土地上的热烈和喧嚣,催生了他们内心强烈的出走冲动,这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他们普遍将“到北京去”“到世界去”视为进步的象征。在他们眼中,出走意味着财富和机会,拥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青年人摇身一变的理想,他们试图幻想出一个独立的现代化空间,将自己的激情与理想置于这一空间内施展。作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进入北京城的革命干部及其后代(比如王朔等),而是在全球化时代进入北京城的那一批”[4]新北京人,徐则臣从江苏的小镇到北京求学后留在北京工作,这种亲历性也放大了空间流动带来的身份认同困境,转而定位了其北京叙事的主要维度。
作为“70后”作家的代表,徐则臣用平静而真实的话语,不遗余力地搭建着这样一个理想的成长平台,探索着一代人精神漂泊的轨迹,他的创作表达了“70后”群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徐则臣的叙事将关注的焦点放置于个体的精神世界,尤其是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70后”群体。“70后”群体所面临的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它盘根错节地连结着诸多细小的问题,并逐渐延伸到更为精密的大问题。这使得对于“70后”的文本研究不能仅仅依靠机械地粘贴和复制,不能仅仅通过单纯的艺术想象来重建能够容纳这一代人生活经验的文本空间,它需要从一个更核心的角度切入,来展开对“70后”的书写。
二、城市生存与现代人的身份焦虑
徐则臣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讲道:“我至今没有弄清楚‘边缘人的确切概念,但我清楚他们和所谓的‘有为青年不一样,他们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正式工作,除了身份证,很少有拿得出手的证明,时常也需要躲躲藏藏。他们基本上是金领、白领、蓝领之外没有‘领的那个阶层。”[5]对于这些城市中的“无领阶层”而言,他们的身上背负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小城镇人们的眼中,到大城市去工作意味着成为“城里人”,成为出走成功的故乡人代表,而现实并没有期望般美好,带着憧憬进城的青年人,必须直面身份转变和不被认同所带来的与日俱增的焦虑感,必须接受他们成为边缘人的尴尬处境。
徐则臣的作品选取了来自乡野的外来者作为北京故事的主人公,以人物自身所带有的乡土记忆来关照北京,并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展现北京。有所不同的是,这一身份认同不再是北京人的身份认同,而是在北京生活的外来者的身份认同。这些外来者是城市的“他者”,他们在北京的遭遇,展现的是北京的另一种形象:冰冷、坚硬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北京需要外来者提供劳动、服务,但排斥这些为北京的繁荣洒下汗水和泪水的外来人真正进入北京,他们是北京的“他者”,而北京却不会属于“他者”。然而,尽管北京是冰冷、坚硬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但它确实为无数外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想象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这些外来者呈现了努力、向上的生活姿态。这使得以往被忽略的北京侧面得以展现,隐藏于国际大都市的北京形象背后,还有一个“他者”的城市,避免了传统路径下在新与旧、中与西、文化与政治等二元对立的框架内来理解北京。
在徐则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中,咸明亮、冯年、天岫、王枫、张大川、李小花、戴山川等所有生活在北京西郊的外来者,他们能够“近入”北京,但无法“进入”北京。尽管如此,却并不妨碍所有拥有美好理想的青年人冲进北京,北京给予了这群理想主义者一个想象的空间。北京似乎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城市,一方面它试图拒绝将这些外来者作为城市构成的一部分,这些外来人聚居的北京西郊的混乱、阴暗,似乎是和北京的繁华、现代分裂的,它只是西郊而不是北京的西郊;但另一方面,北京确实又提供给这些外来者像北京西郊这样的生存空间,它需要这些外来人的助力来建构自己。北京西郊作为北京现代化的一部分,在其落后中隐藏着北京传统的乡土经验,它并没有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消失,反而成为北京城市背后的根基,支撑着北京在国际都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6]乡土社会一整套以关系作为根基的文明体系,在北京其实是被切断的。这群在乡野长大的外来者来到城市,别人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是谁,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是被切断的,他们迫切地需要重建一种新的联系,以改变孤身一人的生活状态。因而,在北京西郊的平房内,自发地形成了外来者聚落,而外来者的流动性,导致因聚落建立的社会关系是易变的。这种易变性加之现实生活的压力,带来了外来者梦境中的窒息感,逐渐使外来者的理想精神轰然崩塌,使他们的故事被赋予了悲凉感。而这些焦虑的、困惑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对北京发出声嘶力竭地控诉,以及失败后无法释怀的绝望。相反,他们在无奈的处境中,相互传递底层间的温暖,这也使得这些失落的理想主义者的故事不至于是一种无尽的悲凉。
事实上,“70后”的出走遍布中国乃至世界的每一寸土地。他们希望能夠在城市立足,抓住机会实现梦想,并以在城市生存下去的方式来完成精神的逃逸与疏解。显然,他们小看了城市,面向城市的探寻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城市生活的压抑、紧张,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狭小,不断加剧着现代人的身份焦虑、自我认同感的缺失,“活下去”逼迫着个体一次次地扭曲变形以适应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尽管他们或学业有成,或经商成功,但迷茫与不悦依旧刺激着他们的神经,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终究是漂泊无依的,自己的灵魂终究是无处安放的。他们带着自己的身体走出故乡,但自己的灵魂却始终没能和身体一起在城市立足,成为身份模糊的隐形人,并在单调的生活状态中失去精神自由,失去了最初的批判与反思能力。尴尬而畸形的现实处境,扼杀了他们的美好生活愿景,并剥夺了他们选择的权力,这对于有批判和反思能力的人而言是痛苦的,因而直接促发了他们的出走:到世界去。这个世界能否让他们心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找到精神的落脚地之前,毫无疑问,他们会继续到下一个世界去。
三、放逐与守护:现代人的精神“再出发”
“原乡神话”的瓦解和现代性的迷失是“70后”精神困境的根源,在现代化急速发展的背景下,“70后”如何确定和坚守个体的信仰,如何寻找和确认个体的精神定位,又将以何种姿态与世界交流对话,是徐则臣一直思考和探索的根源。徐则臣从“70后”的群体经验出发,并没有片面地将精神困境的突围寄托于某种宗教信仰,而是试图寻找可能存在的多种途径。
从徐则臣的小说文本来看,故事的发生和结束是一个出走、返乡、再出走的循环,讲述者从回忆历史和展望未来的角度,去牵涉出从花街到北京,从北京到耶路撒冷再到世界,从祖辈的历史经验到当下的现实体验等诸多的精神困境,如此繁琐和复杂的关系被放置在短暂的回乡之旅中,使得“70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世界得以开放地展现。从“花街”到“北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耶路撒冷”,它们各不相同,或是一种信仰,或是一种救赎,或是一个自我妥协、从容放松的精神之乡。他们的人生历程清晰地证明,口号式的信仰是空泛的,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起困境中的人类,而源自内心的真实信仰却能够引导人类,从当下的历史中去弥补历史苦难造成的精神失落。当徐则臣说出“掉到地上的都要捡起来”时,我们似乎也明白了其想要表达的是:内心的安宁源于信仰,唯有寻找和确认了内心的信仰后,我们才能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坦荡地活着。
这种信仰的力量,在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的主人公初平阳选择前往耶路撒冷求学,是因为受到了基督教徒秦环的部分影响。当他第一次从秦环的口中听到这个词时就被吸引了,它的音节如此独特、神秘而遥远。徐则臣并没有刻意地点明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徒的意义,它对于初平阳的吸引单纯地源于自身的美丽与圣洁。在初平阳的眼中,耶路撒冷不仅是宗教的圣地,更是信仰的发源地,它超越单纯的地名,变成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象征了初平阳实实在在地追寻信仰的过程。对信仰的探析,使耶路撒冷逐渐沦为背景,而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初平阳,则在不断追寻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填补了现实带来的失落感。
故乡,漂泊者的根,重返故乡,是落叶归根。在徐则臣的文本中,对原乡的影子并没有进行大篇幅地细节刻画,但无论是花街上那条熙熙攘攘的运河,还是伫立在运河边的太和堂,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则臣巧妙地将人物的情感介入故事的发生地,使人物与地点产生了某种内在的联系,尽管他们始终保持着出走的状态,但并没有割断与故土间的情感共鸣,这种与生俱来的牵引力甚至使他们更加主动地维持与故乡的关联。而这样的情感体验是多数“70后”的真实写照,“70后”对故乡的情感隐秘而复杂,不易察觉且难以用只言片语去表达,这是一种虔诚而安静的情感,它被放置在内心的深处,成为纯粹意义的乡愁。通过回忆故乡,他们抛开浮躁的精神污垢,明确个体的身份认定,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短暂的心灵慰藉。
徐则臣将故乡作为起点,不断回溯这一代人精神信仰的构建,并企图进行新的定位。在出走与回归的过程中,这些城市的漂泊者追寻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发出了灵魂深处的呐喊,他们努力让自己去寻找人生的原点和心安的答案。短暂的停留,使城市的漂泊者在故乡的土地上寻找到了记忆中的相似点,这些虚构的重塑和想象,使得故乡的生活变得理想化,因此,他们再一次短暂地将故乡作为精神的原乡,重新审视自我,想象与探索生命的意义。停留过后,他们又会作出选择,或是再次出走到更远的世界去,或是留守故乡。
徐则臣的“北京书写”在放逐与守护中,展现了“70后”集体出走的背后深刻的历史根源;其可以视为个体与城市在空间上的交换过程,城市借助个体的力量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个体借助城市的空间来实现自我的价值创造,这种交换使两者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契约关系,明确了双方的责任与义务。但现代的城市生活没有憧憬中的美好,冷漠和残酷逐渐摧毁了个体的幸福感,使个体在城市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并给他们的精神带来了持续地刺痛。在迷茫和困顿中,他们开始回忆故乡的一切,惊奇的是,故乡的一切并没有因为距离的遥远而变得模糊,反而愈加明确和清晰。个体与故乡的暗合关系,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抗击着城市空間的外壳,并携手个体的生存经验和精神信仰,带着“70后”一代人走出精神的困境,寻得一条精神“再出发”的道路。
作为“新北京人”的徐则臣,在从“乡土”走向“世界”的路途中,书写了“70后”一代人的复杂的现实境遇和精神世界。他的小说创作撇开了自身对人物狭隘的文化身份的认知,以平等共存的姿态去寻找突围精神困境的道路,有效地剖析和反思了一代人的信仰问题,并借助追忆的方式对历史苦难造成的信仰缺失进行了揭示,通过一代人信仰再追寻的旅程,引出物质崇拜、经济先行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并尝试性地对其进行解答。
基金项目: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代际视野下的‘北京叙事研究——以‘70后作家为主体”(编号:KYCX22-2407)。
参考文献:
[1]张鸿声,等.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1949-197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4-25.
[2]洪治纲.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2008(04):160-175.
[3]沙蕙.七十年代生人成长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24.
[4]徐勇.出走与回归:猴子、面具与精神分裂——论徐则臣的《王城如海》[J].当代文坛,2017(6):86.
[5]徐则臣.创作谈:跑步穿过中关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134.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