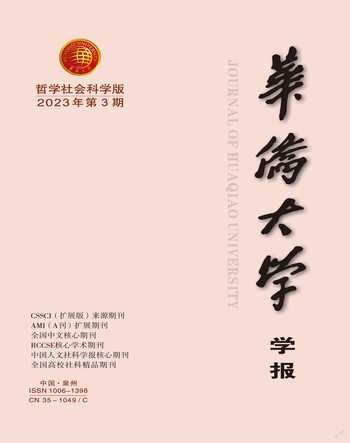“村改居”居民文化认同的消解与重塑
2023-06-14杨绘荣刘佳佳
杨绘荣 刘佳佳
摘要:“村改居”社区作为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过渡的特殊样态,因其“亦城亦乡”的独特性而为学界所广泛关注。在“村改居”社区这一过渡型社会形态中,受文化延续性、稳定性的影响,社区意义空间、交往空间、权力空间的重构远滞后于生存空间(物质空间)样态的变化。从空间变革的视角审视“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现状,可以发现社区居民面临着文化记忆断裂、文化归属感消解、社区情结转化艰涩、主体意识薄弱等多重瓶颈。有鉴于此,基于物质空间、意义空间、交往空间和权力空间之界分,重塑公共景观这一空间之“基”、深挖符号资源、完善社会关系网络、推行网格化管理等则是纾解“村改居”社区居民文化认同困境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村改居”社区;多元空间;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杨绘荣,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文化、认同理论(E-mail:yang_ivy@qqcom; 山西 太原 030006)。刘佳佳,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治仪式中集体记忆的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强化研究”(22YJC710082);山西省科技战略研究专项课题“山西省‘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202104031402032);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乡村振兴中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问题研究”(2022Y054)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3)03-0034-11
文化建设与文化认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向来为党中央所重视。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由此,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近些年来,在城市化过程中,“撤村并居”作为推动个体获得现代性的有益探索,它在促进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引发了“村改居”居民的文化认同危机,很显然,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此外,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空间社会学逐渐成为显学,空间的社会性意义也随之得到重视,但现阶段有关“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研究大多将空间视为承载“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纯粹物质性场所,极大地遮蔽了空间所蕴含的秩序变迁、关系重组等丰富内涵及聚合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共同体等深刻价值,而空间的这些内涵与价值皆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认同关涉居民的价值认知与主观能动性,系“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内驱力所在,加之它与空间关系甚密,因而基于空间之维建构“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是促进“村改居”社区善治和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创新举措。
一空间建构文化认同的意涵与理路
现代化进程中空间格局不断嬗变,空间的多义性得到了更为深刻的阐释。“村改居”社区作为特殊的社区类型,关涉空间样态的变革、社区关系及社区秩序的重组。文化认同作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是理解“村改居”社区治理的重要维度。实际上,空间与文化认同具有极为紧密的逻辑契合性,前者不断为后者注入社区记忆、文化符号、社会资本等资源,并经由物质、意义、交往、权力等具体空间向度对居民文化认同进行多维建构。
(一)多元空间论
空间是理解城市发展的重要视角及浓缩、聚焦现代性问题的符码与经验现实之表征,法国政治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反对将其视为静态存在,而是将它视为“社会的产物”及“社会秩序的空间化”,这种空间化关涉人类社会关系的建构与重组。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进一步阐释了有关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思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它作为根植于马克思、黑格尔及尼采哲学的三重唱,具有极强的哲学思辨意味。大致而言,空间实践指向物质领域,是一种自然的、物质性的客观存在;空间表征指向抽象精神领域,通常与社会生产关系及由此所强加的“秩序”相关联;表征空间则指向社会领域,乃系一种象征性的空间形态。实际上,三类空间辩证统一于社会生产与发展,列斐伏尔通过再绘马克思的商品生产模式阐释三类空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其中,空间实践是商品生产及社会关系的基础与载体,为进一步实现商品交换及社会关系存续,需运用表征空间内的各类符号表象,而生产关系的诸多表象之中又内含权力关系。由此可见,社会生产与发展有赖于空间实践之基础、表征空间之介质,而空间表征蕴含的权力性思维则贯穿于社会生产与发展的全过程。具体到“村改居”社区中,空间实践与“村改居”社区的物质自然空间(物质空间)相对应,如农田、祠堂;空间表征与福柯的“权力空间”相类似,意指“村改居”社区中由政府、社区管理人员与社区居民互动形成的一种权力空间;表征空间与“村改居”社区中经由社区庆典、节日纪念等仪式活动所构成的场景(意义空间)相契合。基于空间三元论思想,加之吸收借鉴其他学者有关空间的界分以及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关系”的阐释(涉及到交往空间或关系网络),大致可从物质空间、意义空间、交往空间、权力空间四个向度理解“村改居”社区的生产发展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系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亦即物质空间、意义空间、权力空间三者辩证统一于“村改居”社区的生产与发展过程,而所谓“交往空间”即由社会关系所构筑的空间,它与各类空间关联密切,它们共同构成理解“村改居”居民行为逻辑(包括居民文化认同)的空间面向。居民作为“村改居”社区的行动主体,其思维观念、行动逻辑深受物质空间、意义空间之影响,并由此生成新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为“村改居”社区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当前,撤村并居过程中空间的急遽转变与居民文化变迁的滞后性形成张力,致使“村改居”社区常表现为“城市的躯壳、农村的精神内核”,居民文化认同日渐消解,这极大阻滞着“村改居”社区善治。因此,为有效实现社区善治,需审思居民的文化认同问题,充分发挥文化认同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内在动力价值。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空间是文化的表征,而文化认同作为个体对共同文化的确认,亦可放诸空间之中加以理解。
(二)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意指个体或群体将某一文化系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内化于自身心理与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进行认知评价、规范行为的过程,这种文化系统涵括各类物化形式与精神指向,而与之相关的文化认同能够促使某些文化符号得以运用、共有的文化理念得到秉承、个体与群体间关系得到确认、共同思维模式及行为规范得以生成与遵循。在文化建设日益重要的当下,文化认同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高度耦合性,它能够唤醒居民主体意识、聚合社会资本,助推“村改居”社区共同体之培育,因而在研究“村改居”社区治理时需关照社区的文化转型及居民的文化认同问题。纵观文化认同的两大主流阐释,它既是个体对自我知觉与自我定义的反映,又是个体与文化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皆深受空间之影响。蒋福明在阐释“村改居”社区文化转型问题时,将社区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制度文化四个面向。有关“村改居”文化认同的研究亦可从这四个向度加以探讨,同时基于“空间”之维可以发现,物质文化作为最易被感知的物质实体,它与物质空间最为接近;精神文化关涉居民精神风貌、共同信仰,意义空間与之关联甚密;行为文化涵括居民的生计生活模式及人际交往,可将其放诸交往空间展开分析;至于制度文化,权力制约监督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是现代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为保障权力的正常运行需诉诸制度化的程序和规则,可见权力与制度关联密切,因而可将制度文化放置于权力空间加以考察。简言之,文化认同可具化为物质、精神、行为与制度文化四个面向的认同,而物质、意义、交往、权力这几个基本空间类型大致与之契合,故而可将空间作为审思文化认同建构的新理路。
(三)空间建构文化认同的逻辑理路
美国传播学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立基于文化属性,将认同视为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在他看来认同是建构起来的,而文化认同系最深层的认同所在,同样经由建构而来。基于空间视角审思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可从文化认同的结构要素——认知、情感与行为加以阐释。其中,物质空间因其记忆载体属性,主要作用于认知层面;意义空间与交往空间凭借丰富的象征性资源(文化符号)与行动资源(社会资本)主要在情感层面发挥作用;权力空间关涉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深刻影响着居民的主体意识与行为。最终,经由四个向度空间的共同作用,居民的文化认同逐渐强化。
具体来讲,首先,物质空间充当文化记忆的载体,能够经由文化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影响个体的认知,最终作用于个体的文化认同。从记忆附属论的视角来审视记忆与认知的关系,可以发现记忆是认知的来源与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个体认知提供了经验材料和历史积淀。物质空间的选址、规模、形态等物质性材料能够为文化记忆的生成提供叙事语境与背景,当个体进入特定的物质空间场域后,便会依循物质空间的建筑样态以及附着其中的道具引导建构相应的文化记忆,并凭借已有的文化记忆对所属共同体进行认知与想象以建构自身对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其次,意义空间与交往空间涵括众多文化符号与社会资本,它们为个体情感的凝聚、文化认同的生成与强化汇聚了大量的文化性材料——象征性资源与行动资源。一方面,文化符号的互动与联变特别是作为符号聚合体的仪式展演,能够促进个体间的意义共享与情感交流。在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看来,人类是“感情的动物”,而诸如此类的仪式互动会产生高度积极的情感能量,最终形成群体团结。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动物,自出生伊始便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交往,在人类交往空间中潜藏着大量的“社会资本”,如信任、互惠等,它们能够促使个体生成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结,潜移默化地强化其文化认同。
最后,权力空间中充斥着认知与意识形态,暗含服从之逻辑。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向来为学界所乐道,众所周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绝对的腐败乃系民心所背,是文化认同解构的“催命符”。为此,党和国家不断探索出“人民当家做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性材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体权利、主体意识之觉醒。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意识的觉醒与强化,促使个体与所在群体形成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激励他们为维系共同体的稳定发展而自觉行动,从而使得文化认同真正落地生根。
二“村改居”居民文化认同消解之表征:基于空间表象的多维诠释
个体无往不生活在空间之中,个体行动也与其所处空间紧密相连,并随着社会空间形态的变迁而变迁,从而为个体的行动逻辑镌刻了“空间性”之烙印。作为由传统乡村向现代城市转型的过渡形式,“村改居”社区一改原有村落的建筑样貌、空间布局,面对这种空间样态的巨变,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个体交往互动、社区参与意识等皆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并且体现出深刻的空间性。
(一)物质空间:文化景观变迁,居民文化记忆断裂
“村改居”社区作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同样未能幸免于城市同质化带来的楼宇林立,而自然性、人文性等乡村地域特色景观的消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村改居”居民乡愁无处寄托的尴尬境况。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人们通过地标建筑、历史遗产等文化景观记住城市之时,文化记忆便成为人、场所与城市之间的枢纽所在,成为三者交流的共同“语言”。不言而喻,“村改居”社区的建成伴随着空间布局及公共景观的变迁,而这种由相对开放的村落和农田向封闭性强的楼宇和绿地的转变过程便内含着居民文化记忆的断裂。这种断裂对个体的影响是绵长而深远的,它可能致使个体产生一种失落感,即便处于新的生存空间,但因文化记忆断裂带来的持续性影响,使得“村改居”居民仍以一种“客居他乡”的心理感知这一新的空间,难以对该空间产生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
村改居作为一种被动城市化现象,在这一进程中,“时间性”效应会导致村民文化认同的转换远远滞后于物质的变迁,而“空间性”效应则会带来强烈的相对剥夺感,阻碍村民文化认同系统的转换。在乡土社会中,土地作为融汇于村民血脉基因中的重要元素,始终是村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和经济之本。彼时,村落的景观面貌除却自由开放式的住宅便是集中连片的农田,农民傍土而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生产生活与时令节气紧密相连。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种瓜,立夏开花”等,种种农事谚语皆点明了农田景观的季节性以及村民与土地紧密的依附关系。然而随着“村改居”社区的建成,居民被迫失去了早已融于自身血脉基因中的土地,一改其傍地而生的生活习性与生计模式。此时居民心理层面的身份认知与角色转换远远滞后于客观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由此产生茫然、不适等不良心理状态以及病理性焦虑。譬如,福建省龙文区蓝田街道在对“村改居”社区的农村“小菜园”进行集中整治时,发现类似的菜园多达412个,这一案例从侧面反映出“村改居”居民在撤村并居后其生活习惯与物质空间的不相适应性。可见,“村改居”居民这种相对稳定而持久的乡土情结容易致使其身份认知混乱,亦不利于他们建构对社区文化的认同。
(二)意义空间:符号表征渐逝,居民社区情结转化艰涩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指出,人与其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人是创造符号,并以此创造文化的动物。从中,符号对人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传统乡村中,通常建有表征特殊意涵的公共空间。例如,祠堂通过村志和一些仪式等方式展现居民的同根同源性,用以充当血缘关系的符号表征;村委会作为村集体事务的处理中心及村庄治理的权威所在,通过选址于村庄中心,实现了地点的中心性与权威的崇高性之融合。再有,景觀等符号是建构地方认同的重要途径,文化认同作为共同体认同的重要一极,与景观符号有着深层的关联。社区景观符号的存在并与之互动能够强化居民文化认同,而景观符号的消失则会导致社区居民文化认同式微。例如,有学者在对宁夏W村撤村并居过程中的寺坊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后发现,在W村“村改居”过程中寺坊走向分化,其所承载的宗教文化也走向断裂,居民在自由、自主愈增的同时,也面临着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衰落的危机。可见经由撤村并居的系列举措,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景观符号走向沉没,伴随而来的便是社区文化认同因象征性资源的流失而趋向式微。
另外,仪式作为一种助推群体团结、提升群体凝聚力的符号集合,它能够经由仪式展演呈现一种瞬间共有的现实,在这种“公共在场”的现实情境与场域氛围内,它得以发挥情感动员与意义共享的功效,助推居民认同感、归属感的生成。然而,随着“村改居”社区的建成,诸如祠堂、戏台、庙宇等村民们赖以举行祭祀典礼、进行各类仪式展演的场所因与现代文明理念冲突而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则是健身场所、活动中心、公共绿地等现代化公共活动场地的建成,虽然它们能够发挥促进居民交流交往的公共空间平台作用,但其独特象征意义的匮乏使得社区居民难以形成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此外,在由相对开放的传统乡村迈向封闭性较强的单元楼房的同时,村民为庆祝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彼此合作互动举办包粽子、做月饼等节日仪式活动,以及互相分享美食的共享仪式也因受限于显性空间的阻隔趋向消减,这意味着一种富有人情味的、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或将被拆散,居民的生活秩序也因此受到影响,他们对“村改居”社区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等趋向下降。
(三)交往空间:社会资本下降,居民情感归属式微
从心理学视角来看,文化认同指涉个体对文化的归属感与内心承诺。文化归属感作为个体对其所在共同体的依恋、忠诚等情感倾向,对共同体的存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阶段,“村改居”社区作为传统乡村与现代城市的夹心层与过渡带,居民的无根感加剧。其原因在于,传统乡村基于血缘、亲缘建立起的社会关系网络走向断裂,加之“村改居”社区充当着流动人口的“蓄水池”,社区居民身份的异质性、复杂性给社区信任、互惠规范等的建立带来诸多挑战,致使“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不断流失,由此导致社会资本之凝聚、整合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居民的社区文化归属感随之弱化。
在言及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时,费孝通提出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差序格局,用以形容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推及开来,伸缩自如、能收能放的人际关系格局。在撤村并居以前,村民多以务农为生,对土地的依赖性极强,安土重迁构成其重要的文化心理表征。由于祖祖辈辈皆扎根于此,累积而来的人际关系使得村民间的交往甚是密切,村落内部表现为典型的熟人社会。然而在“村改居”之后,社区固有的血缘、地缘关系遭到极大破坏甚至不复存在,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更导致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利益权重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人伦“差序格局”转向利益“差序格局”,维持居民交往的情感纽带演变为工具型表演关系,社区交往空间也由亲密化趋向疏离化,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归属感亦因此不断弱化。
此外,信任作为构成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在社会共同体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充当社会良性运转的道德价值基石。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基于新功能主义角度,将信任界定为用以减少社会交往复杂性的机制。福山则立足于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将信任视为促进经济繁荣的文化基础。帕特南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指出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信任范围越普遍,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间的信任与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进而越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繁荣发展,而且合作本身也能带来信任。由此观之,信任发挥着简化社会交往、降低社会交往成本、增强社区成员凝聚力等诸多功能。区别于传统乡村基于熟人关系、血缘关系建立起的社会信任,“村改居”社区的居民信任感的生成极具复杂性。一则,“村改居”社区居民处于一种被动安置状态,居民对拆迁政策颇具微词而相关部门未加以重视,后续补偿条款的落实不到位致使居民对基层政府、居委会不信任,阻滞着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如有学者在研究杭州某一“村改居”社区时指出,该社区在回迁时因选房规则相对不公及补偿款未到位,致使居民最终做出了“集体讨说法”的行为,毫无疑问这致使社区信任遭受极大流失,且不利于社区共同体的构筑。二则,“村改居”社区居民构成的复杂性以及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刻板印象,如惯性地为外来人口贴上“爱惹事”“素质差”等负面标签,这种居民间身份差异及偏见的存在同样不利于相互信任感的建立,且亦使外来人员萌生一种不平等感知,消解着他们对于社区的归属感。
(四)权力空间:权力格局不平等,居民主体意识薄弱
福柯作为20世纪非常权威的理论学家,其有关权力、社会的论述总是充满着空间性的寓意和洞见,他指出,社会并非仅有一种权力运作的单一体,而是彰显着各有特性的不同权力间的并置、联系、调和以及等级化,由此可见,社会实则是由不同权力所构成的一个群岛。具体到“村改居”社区,毋庸置疑,社区工作者为居民提供了许多优质的服务,但这种服务通常是基于一种“改善”的逻辑和不平等的关系。他们习惯性地将居民视为被管理、被教育的对象,缺乏对居民因空间样态急遽转型所产生的迷惘、不适等心理状态的感知与同情,只是一味基于极端现代主义的立场进行社区管理。这种过度追求现代文明理念而对传统风俗嗤之以鼻的观念,使得管理者与居民在诸如晾晒被子等日常行为范式方面存有冲突,即追求规范秩序的现代化观念与享受自由安逸的传统理念发生对抗,从而造成了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同危机。另外,在“村改居”社区中,居委会干部与社区工作者主要源于之前的村干部和村委会工作者,在他们继续为“村改居”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时,这种基于旧有的人情关系所形成的社区治理模式,可能会因缺乏公平、公正而产生不良影响,如深圳市宝安区在“村改居”后仍面临着换届选举的“人情票”,小族、小姓的候选人无论能力多强、品质多好,皆难以当选,显然这种有违公平的选举会为后续社区治理带来诸多弊端;同时,该社区存在新老居民“两张皮”的问题,他们在政治、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享有不平等的权利,极易致使外来居民陷入一种感知上的不平等状态,解构着他们对社区的文化认同。
三“村改居”居民文化认同重塑之空间策略
空间充任着承载定位功能、情感联结及诠释社区共同体价值意蕴的工具性媒介,经由内含其中的符号联变与互动、场域氛围的形成与感染以及对重大历史时刻的情境化再现,可多面向地形塑“村改居”居民的文化认同。由是观之,空间为强化“村改居”居民文化认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空间重构”作为一种在具体情境中展开的空间实践,它通过采用公共景观再造、呼唤部分传统文化符号及仪式复归、完善社会关系网络、推行网格化管理等诸多策略,能够有效消弭“村改居”居民在多个空间向度上的文化认同困境。
(一)物质空间:公共景观再造,重构居民的文化记忆
从时间向度来看,居民因生存空间、交往空间的变迁而产生的迷惘不适等心理变化,可诉诸历时性的社区记忆建构来得以慰藉。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可充分发掘空间建构社区文化记忆、最终重塑社区文化认同的功能价值。
在人类悠久的社会生活中,记忆始终是最为重要的权力资源之一,布迪厄在研究符号暴力时提及记忆的作用,他以黑人与白人的交谈为例证,指出双方交谈时不单单是两种集体记忆的交流,更是两种权力的争锋。换言之,社会记忆既受制于权力,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作用于记忆客体,使之按照它的意愿记忆、思考或行动。因而,应充分挖掘物质空间在实现社区记忆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指向意义,以契合社区治理主体的现实需要,促使“过去”契合“现在”的需要,利用社区文化记忆引导社区共同体意识,推动个体基于社区记忆框架展开回忆与思考,形成对社区共同体的体认与想象及自我在社区共同体中的坐标定位,从而强化其社区文化认同。
地理空间作为一种记忆生发场域,其被结构化和整理的地方,通常潜隐着特定的记忆。以上海市嘉定区陆巷社区为例,它是一个典型的“村改居”社区,鉴于该社区大多居民都是由附近乡村搬迁而来,在社区现代风貌建设的同时乡村记忆愈加失落。受乡土情结的影响,居民将自己的乡村记忆浇筑于有失美观的“菜园”之中,这一种菜毁绿现象虽寄寓了居民的乡愁与惯习,却破坏了现代社区的整体美观。本着留得住乡愁和“堵不如疏”的原则,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在走访后发现许多居民对于儿时家中围墙边的蔷薇花情有独钟,便巧妙地将一处社区废弃用地打造为蔷薇花墙,并在此过程中积极鼓励居民参与蔷薇花的种植,由此居民的乡村记忆得以存续,而闲置的公共用地也因充当乡村文化记忆的载体,而为“村改居”社区共同体之构筑提供了记忆与认同的塑造点,继而强化了“村改居”居民的文化认同。
(二)意义空间:深挖符号资源,构筑居民的社区情结
“村改居”社区作为一种由传统鄉土社会向现代文明城市转化的过渡状态,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在此交织,而各类符号、仪式作为承载、展现文化的载体,对社区共同体文化的存续与发展、社区情结的构筑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如此一来,推动景观符号的传承,深挖仪式资源成为构筑社区情结、强化居民文化认同之意义空间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祠堂、村志等符号作为社区共同体文化的载体,能够为“村改居”居民文化认同的建构提供记忆融汇点,故而应对这类文化符号加以承继。例如,福建省漳州市碧湖街道在“撤村并居”、开展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传统建筑及历史文脉的保留与承继,而诸如蔡氏宗祠、萃英庙、古榕树等历史文化符号的存续,既构成了碧湖街道独特的社区景观,又使得原有的社区文化习俗得以延续。碧湖街道“村改居”社区居民进入宗祠、古庙后,在独特的场域氛围中经由图腾、雕塑等各类符号的互动与联变,实现了社区共同体记忆的唤醒与固化。此外,还可通过将古榕树所在地打造成人工岛屿,使其成为见证社区变迁视觉形象上的“城市之眼”,使居民在人工岛屿休憩、观赏古榕树景观之余得以追古抚今,感受历史悠久的社区文化,不断提升自身对社区文化的认同感。
其次,仪式作为一种指向性的文化表演活动,它体现着仪式组织者的意图。因而,在“村改居”社区这一相对崭新的社区样态中,社区治理者应创新一些仪式活动,注重与外来人员的精神文化相融合,突出社区某些价值信仰,以重塑社区信仰,强化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譬如,社区可以广泛借鉴蕴含家庭和睦理念的由婆媳共同参与的舞被狮仪式活动、以和为贵的请长者“吃讲茶”而对邻里纠纷加以调节的行为仪式,等等。借由此类仪式的丰富与创新,不断凸显、固化尊老敬老、睦邻友好等价值观念,居民也因相关仪式展演而参与互动,实现了社区价值观的内化和社区情感的凝聚,有助于促进自身乡土情结向社区情结的转变,强化对社区的文化认同。
最后,随着信息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地方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仪式也在媒介场的作用下演变成一种新的仪式传播类型——媒介仪式。在虚拟空间中,社区成员得以突破时空局限,通过微信、钉钉、微博等社交媒体参与到媒介仪式活动之中。于是,身处不同时空的居民经由微信的圈群化传播而被连接起来,他们基于数字媒介进行仪式互动,实现了线上空间的“共同在场”。如在春节、中秋节等节日时令中,“村改居”社区居民可通过发送节日祝福、相关表情包等较为灵活便捷的形式实现媒介仪式活动的符码式参与。同时,媒介仪式的出现也进一步凸显了“村改居”社区的价值信仰,增强了居民间的情感联结。例如,山东省西上虞社区在“村改居”30周年纪念日活动中,通过采取“快闪”形式生动弘扬了西上虞社区几代人艰苦奋斗、众志成城的干事创业精神,而这种实体空间的仪式展演经由媒介转播,实现了居民在更广泛时空范围内的线上聚合。在这种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中,原户籍居民与外来居民的身份差异得以消除;而且经由多模态视听符号交织的媒介仪式传播,居民能够深刻感悟西上虞社区的价值信仰与社区精神,并通过观看、点赞、评论、转发等形式参与仪式互动,密切与其他居民的交流互动,加强彼此间的情感联结,进而在更为宏大的“情绪场”与“感染域”中激发情感共鸣,强化他们对社区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因此,应当积极挖掘媒介仪式潜力,丰富媒介仪式活动,以促进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居民聚合,进而拓宽“村改居”社区仪式活动的氛围场与感染域,在虚拟空间内强化个体与社区的情感联结,增强“村改居”居民的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
(三)交往空间:增厚社会资本,强化居民的情感归属
毫无疑问,由信任、网络及互惠规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对整合社区文化资源、强化社区居民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价值。然而“村改居”社区中关系网络的松散、互惠规范的缺失及居民信任感的下降似乎成了不争事实。正因如此,可通过重构社会信任、密切居民交往等方式,来增厚社会资本,强化社区居民的文化归属感。
就重构社会信任而言,首先,政府应建立健全反馈机制,在吸纳民意基础上,科学研判并有效落实“村改居”配套政策,这里,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治理的相关经验可以提供借鉴,该区政府通过探索清产核资摸清家底、制订方案锁定成员等方式保障了居民在“村改居”后的合法权益同时,为满足居民的多元化文化需求,雨城区政府还积极为共享书吧等社区文化娱乐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扶持。经由这些举措,居民得以妥善安置,生产生活得到极大改观,政府由此获得了居民的信任,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也随之提升。其次,社区工作人员应通过调查走访、民主座谈、普及宣传等渠道,及时掌握居民文化服务的需求倾向与需求变化,科学评估居民最为关注和亟需解决的社区文化难题,积极邀请居民共同参与到社区文化建设的议事决策中,以此增进社区居民对自身以及居委会的信任感,强化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再次,物业管理人员应妥善处理、有效化解涉及文化建设的物业管理纠纷,以一种包容平等的态度对待居民在公共场所晾晒被子、种地等行为,积极配合社区工作人员,为其开拓晾晒被子、种植蔬菜等专门性场域,及时就社区居民的物业服务投诉予以反馈。长此以往,社区居民对物业管理人员的营利性及“不近人情”等歧见可以得到极大消解,会逐渐建立起对物业管理人员的信任,助推他们建构对社区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就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而言,应当建立、健全密切社区关系网络的组织载体与交往平台。一方面,积极探索、组建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娱乐组织,将有着不同兴趣爱好的社区居民聚集起来,通过积极组织文化活动等形式密切社区居民间的交往,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同时,还应为社区文娱组织的发展及社区文化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与充足的资金支持,以促进其良性、长效发展。另一方面,重塑社区传统、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同样不失为加强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间的情感联结,完善社会关系网络的突破口。例如,内蒙古包头市某社区巧妙地对传统的“义仓”制度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转换,搭建起诚信友爱的“义仓义集”社区互助平台。社区居民售卖自身闲置物品,将义卖所得捐于弱势群体,经由这一方式,达成了助人自助之目的,也极大增进了个体间的情感联结,这对于重塑居民之间内在关联、完善社会关系网络、强化“村改居”居民文化认同意义重大。
(四)权力空间:推行网格化管理,激发居民的主体意识
“村改居”社区是经由撤村并居演化而来的新型社区,它需要应对新的社区公共事务,然而,无论是政府主导下的“家长制”社区管理模式,还是社区工作人员基于改善的逻辑和不平等的关系而提供服务的模式,实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改居”居民对社区的文化认同。在这种权力不平等的格局下,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地服从,主体意识淡薄,对社区的文化认同感较低。对此,首先,应当厘清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保障社区权益,规避行政色彩浓厚的管理模式对社区居民产生的不良影响。这就需要政府明晰自身的职能定位,专注于提供公共管理与服务,避免过多干涉致使居委会始终忙于行政事务而无暇顾及文化建设。政府还应将自治权归于居委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做到指导而不越位,协作而不越界。就委托社区完成的政务性工作而言,政府也应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避免动用社区集体资产为政务性工作买单,保障社区共同体及其居民的合法权益。
其次,社区应当积极开展网格化治理。网格化管理,顾名思义是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并运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构建管理平台,将社区的楼宇、街道乃至居民都纳入到可被观测的监控平台上,从而形成多元共治的精细化管理网络。它与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通过将异常规训转化为普遍化监视,来促使权力运作更加便捷化、迅速化,从而有效改善权力运作的空间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可大力吸纳社区居民担任网格管理人员或是楼长,以提升他们参与社区治理、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与文化建设,有利于消除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之间的不平等性及心理隔阂,促进社区居民与社区治理主体的关系联结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主体还可以充分发挥网格管理人员及楼长的枢纽中介作用,积极听取他们的意见反馈,以完善相应的社区规章制度,进而有效推动社区文化建设,强化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如此一来,居民在“村改居”治理的权力场域中便不再处于一种消极的失语现象,当他们的意见建议经由多元渠道得以妥善处理后,其社区参与的效能感随之提升,主体意识与参与积极性亦将有所改观,这种由“旁观者”到“主人翁”的角色转变同样会带来文化认同的强化。
结语
“撤村并居”作为中国独特的城市化推进方式,毫无疑问,它在助推城乡一体化建设、改善城乡发展面貌、提升居民幸福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这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过程中,“村改居”社區相应地成为充斥着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诸多矛盾元素的社会空间。加之在“村改居”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治理人员大多仍以传统的“硬治理”方式为主,缺乏有效的“软治理”策略,致使社区居民虽然在人居环境、生活方式、户籍身份等方面迅速向城市社区靠拢,但在文化价值层面却未实现“同步性”,甚至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堕距现象。社区认同作为“村改居”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归属与心理认同,它是社区的向心力、凝聚力及社区发展的内驱力所在,文化认同作为社区认同的内核,更关涉着“村改居”社区的良性持续发展,因此探究“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问题具有独特价值。结合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视为社区治理与文化认同培育的策略装置,并尝试建构“物质空间—意义空间—交往空间—权力空间”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审思“村改居”居民的文化认同困境并探寻适宜解决之策,将文化认同的建构嵌套于空间分析框架之中,不仅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挖掘空间本身的丰富内涵与功能价值,更是在现实层面有利于促进“村改居”社区居民文化认同的生成与固化。
Dispelling and Reshap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Community
of “Changing Villagers into Urban Residents”
with a Perspective of Pluralistic Space
YANG Hui-rong, LIU Jia-jia
Abstract: As a special form of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rural areas to modern cities, the community of “changing villagers into urban residents”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due to its uniqueness of “having both rural and urban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d by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significance space, communication space and power space in the community lags far behind the change of living space (material space)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of community of “changing villages into urban residents”. Examining the status quo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changing villages into urban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hang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are faced with multiple bottlenecks, such as broken cultural memory, dissipation of cultural belongingness, difficult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complex, and weak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material space, significant space, communication space and power space, reshap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public landscape space, digging deeply into symbol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implementing grid management are innovative ways to relieve the cultural identity dilemma of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of “changing villages into urban residents”.
Keywords: community of “changing villagers into urban residents”; pluralistic space; cultural identity
【責任编辑: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