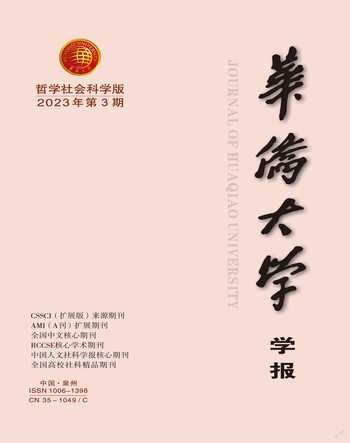智慧城市建设的空间逻辑及正义保障
2023-06-14秦锋砺
秦锋砺
摘要: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空间视为人类活动的场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亨利·列斐伏尔推动了城市空间的认知转向,认为城市的社会空间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一种内含阶级意志的社会关系。社会空间具有抽象的本质,并通过产品等物质实体得以体现。城市空间的非正义源于社会空间所内在的阶级意志并通过物质实体得以感知。城市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城市数字空间是社会空间的新形态,其代码逻辑在体现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却没有直观可考的实体形式。要保证智慧城市建设的科学与民主,就要明确数字空间“使用”优先于“交换”的功能定位,既要保证数字空间内在代码逻辑的科学性,又要在政府的主导下构建数字空间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智慧城市;城市权利;空间逻辑;数字化城市;正义保障
中图分类号:J6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3)03-0005-09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智慧城市的建构逻辑等研究仍存在较大的理论探索与发展空间。自20世纪60年代起,以亨利·列斐伏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空间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对城市的发展逻辑进行了理论探索并提出“城市权利”的口号,以此作为人们在城市发展中所应享有的权利的理论基础。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展开,城市已成为我国人民重要的生产生活场所。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日臻完善,相关技术也开始运用到城市治理中,推动着城市的“智慧”发展。“智慧城市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产生的一种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新一轮科技革命是推动智慧社会产生的技术动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则是其根本特征。”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纷至沓来为人们建构了区别于以往物理空间的数字空间,城市发展具有了数字空间维度。但是,数字化技术在提升城市治理效率的同时也存在许多新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亨利·列斐伏尔以空间为线索的城市权利理论在当今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语境下,面临着理论上的革新。
目前国内对列斐伏尔城市理论的研究主要以“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生产”两种理论为基石,面向不同的社会具体问题而展开:既涉及上述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又涉及对思想脉络发展史、人类解放、都市规划更新、世界化进程等具体主题的研究。尽管从列斐伏尔的理论出发,对城市问题进行研究的作品已经较为丰富且体系繁杂,但却鲜见以此为基础对数字空间这一新的空间形态展开的著述与讨论。事实上,列斐伏尔在其20世纪的作品中就已经对信息技术形成了初步论述,将其作为审视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落脚点,既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延伸,又能够为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理论借鉴,推动数字化城市建设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二城市空间的双重样态:从物理空间到社会空间
城市权利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亨利·列斐伏尔作为城市权利的倡导者之一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改变了空间在传统理论研究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空间的理解也由此具有了物理和社会的双重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城市空间理念
列斐伏尔虽然是城市问题研究空间转向的倡导者之一,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他却并非首个关注城市空间问题的学者。马恩二人虽然未就城市空间问题展开专题讨论,但其著述中早已存在城市空间问题的萌芽。恩格斯在对英国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生存状况考察时发现了该城市存在的空间割裂问题,阶级身份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群体的地理方位和居住环境。“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住宅里。”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住宅匮乏现象。其语境下的住宅匮乏具体表现为“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里的住户愈加拥挤,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等等。马恩对城市空间问题的关注主要侧重于对工人阶级生存空间的考察,在二者笔下,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割裂往往体现出阶级的特性,资产阶级往往集中居住在空间宽敞、环境优异的地区,而无产阶级则聚居在空间狭小且环境恶劣的空间中。
在马恩看来,城市空间的割裂现象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密切相关。在恩格斯的理念中,空间同时间一样,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这种空间体现為一种自然空间。因此大到城市,小到工人个人,其存在和生存都占据了相应的自然空间,这种空间是不可再生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下,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势必会造成城市生存空间的挤压,不同的阶级群体因不同的经济基础而生活在不同的区域。但这种城市空间的挤压并不是造成工人阶级居住空间狭小的根本原因。在恩格斯看来,现代大城市的发展往往会大幅度提升城市街区尤其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原本地皮上的房屋不能提升甚至反而会拉低地皮的潜在经济价值,因此这些房屋会被拆毁而改建其他房屋,工人的住宅会变得更加稀少,因为昂贵的住宅能够提供更为有利的投机场所,工人住宅只是一种例外。因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榨和剥削并不仅仅体现在剩余价值上,还体现在作为人们生存基础的城市空间中。空间为资本生产提供了场所,也决定了生产规模的大小,资本生产占据的空间越大,便能容纳更大规模的资本生产,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也更多。而自然空间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非人造资源,对其占有具有功能上的排他性,机器等生产资料与工人不可能同时占据一处空间。因此,经济效益便与空间产生了联系,工人生活空间因较低的经济效益而被压缩。
马恩对城市空间的关注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发展及其空间规划的规律,其形成并非各种要素自然聚集的结果,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人口、生产资料、交通设施等各种要素在自然空间聚集的结果,而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也决定了城市空间的布局和分配。因此,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作为人们生产生活和资源分配的场所,城市建设与规划的内在逻辑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此逻辑下,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工人阶级居住状况的改善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甚至随着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聚集与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阶级还存在被赶出城市尤其是核心功能区的可能。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注意到阶级矛盾与空间之间的联系,通过对空间概念进行重构,试图探寻一条城市科学民主化的发展之路。
(二)城市空间的社会转向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虽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但在对空间的理解和界定上却与之存在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生产理论认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在提高物质商品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建构或生产的过程。一方面,这種生产的社会空间蕴含在生产的物质商品之中,商店中的各种商品在更深层次上都内含一种生产者建构消费关系的目的性,生产者不仅生产了可供消费的商品,但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社会空间体现在人与人关系的建构中,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关系具体体现为以资本家和工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传统马克思主义以时间为侧重点,注重资本循环的时间维度。而列斐伏尔倡导的社会空间理念改变了传统理念中空间的机械性和空洞性。正如城市社会关系发生的主要场所是街道一样,自然空间在为社会生产提供场所的同时具有了交换价值,并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参与社会空间的生产中。因此在审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问题上,社会空间的提出使“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了“空间的生产”。
社会空间的提出必然要审视其与自然空间的关系,尽管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空间”的理念并主导了其理论建构,但并不代表他对自然空间的存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持否定态度。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虽然都采用“空间”的表述,但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共通性。列斐伏尔明确指出,虽然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正在消逝,但它仍是社会过程的起源,是社会生产力所操弄的物质。社会空间并不是由自然空间转化而来,前者是社会的产物,它“既不是实体性的实在,也不是精神性的实在,它不能被分解为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空间中事物的集合,也不是被占据的空间的集合”,“社会空间最初的基础是自然——自然或物理空间”,“理论表明,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空间会完全消失或者被完全废除——即使是作为这个过程开端的自然空间”。在列斐伏尔眼中,“空间”一词既指涉实体,表现为物质性的客观实在,又指涉抽象,是与生产有关的社会关系的集束。从其构成而言,空间是“三元式”的存在,是个别、特殊和普遍的统一体,其中,社会空间体现了空间的特殊性,而自然空间或“场所”则体现出空间的普遍性。
因此,社会空间并非作为自然空间的替代品出现,二者是列斐伏尔空间理念的两种维度。“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的位置存在很大的不同,因为它们并不是简单并列的:它们可能会互相穿插、互相结合或者互相叠加——它们有时甚至互相碰撞。”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是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理论的重要内容,自然空间作为先验的绝对存在,为社会空间的生产提供了场所,是社会空间生产的起点。总之,从列斐伏尔的理论出发,城市工人阶级生存状况恶劣的原因实则也存在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两个维度的原因:自然空间是生产要素的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当交换与经济价值产生关联,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会使自然空间的交换价值优先于使用价值;社会空间的生产是一种内含目的性的社会关系建构的过程。
三城市的数字化建设及其空间特征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城市建设管理中的运用为城市空间带来了新的内涵,我国城市数字化建设的推进数字空间作为新的空间形式与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存在联系但又有区别。对数字城市时代城市权利保障措施的完善需要对数字城市的本质有清晰认知。
(一)我国数字化城市的构建及其影响
自2008年开始,我国的数字化城市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被称为概念导入期,此阶段的重点技术以光纤宽带、无线通信和超文本传输协议等为代表,是以单个部门、系统独立建设而成的信息系统,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孤岛;第二阶段始于2012年由住建部推动的试点探索期,体现为3/4G、云计算、射频识别技术等的全面运用,此阶段的信息共享以共享交换平台为基础,体现出系统建设纵横分割等特征;第三阶段始于2016年新型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物联网、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是此阶段的重点技术,信息系统也开始向横纵联合的大系统演进,体现为以人文本、为人民服务等特征,并逐步形成了政府指导、市场主导的特征。由此观之,数字化城市并不是被凭空创造出的全新城市形态,正如近代工业城市是在古代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来的一样,数字城市是在现有工业城市设施网络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进而发展出的新型城市样态,这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大致可以归纳为城市整体治理和居民个体生活两个方面。
中科院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数字化城市是“在城市‘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能够有效获取、分类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综合工程”。从城市整体层面而言,这意味着数字化城市的特点更多地体现为信息网络技术对物质城市整体发展的介入,这一过程实则是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在原有城市结点之间进行的关系重构,主要依赖于数字孪生技术的使用。所谓数字孪生,是指通过对物理世界的各种要素数字化,在网络空间再造一个与之对应的虚拟世界,这一技术已经成为当前数字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到城市整体、产业园区、工厂建筑,小到具体的个人或某种具体设备,均可实现“万物孪生”,数字城市从整体而言是物质城市的数字虚拟映射。通过将城市整体及其具体细节映射为数字信息,再通过大数据统计分析、计算机运算等技术手段,便可以为人们展示出被精确量化的城市构成及其运行规律:例如交通部门可以掌握每周、每天不同时段甚至是即时的交通信息,及时进行交通规制以避免道路拥堵;城市规划部门可以精确掌握城市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消费能力等信息,对城市进行更加详细和科学的规划。在城市整体层面而言,城市的数字化能更加精确直观地呈现城市的运行规律,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推动城市的智慧化建设。
城市的数字化除了通过信息技术孪生出数字化城市整体,为城市治理推波助力外,还体现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上。一方面,数字空间的出现重构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工业化乃至更早的城市中,各种资源的流通依赖于管道、电线、道路等设施的铺建,社会关系的生产则依赖于物质的空间和场所,例如工业时代城市的生产和消费依赖于工厂和商场、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依赖于学校等。而在数字化时代,资源则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数字信息途径进行互相传递,网络消费平台在不以物质场所为基础的情况下就具有了与商场相同的社会功效;数字会议、办公平台等软件的推广使足不出户但不影响正常办公成为可能;老师和学生甚至在不进学校、不面对面交流的情况下就可以按时完成教学任务;等等。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使用使“人”这一主体更容易被识别、感知和更加“透明化”。在数字空间到来之前,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物说”,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关系说”,对个人的了解均依赖于对物理意义上的人的行为的考察与规律总结。而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的使用及其对人们生活的主导和更进一步渗透,使数字化生活已经成为人们基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均被数据化并留下相应痕迹,在非接触情况下,对种种数据进行整体分析便能刻画出人物的数字肖像,甚至做到大数据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在当今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最广泛体现为对数字科技的需要。”总之,当今中国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入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城市的高效治理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依赖于数字化技术的推广与使用,这种趋势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数字化空间的特征及其本质
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空间形态:数字空间。数字空间与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相比,既存在功能等方面的相似性,但也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与自然空间相比,数字信息技术创造了一个新的与前者功能类似的“场所”,它容纳了传统人类社会活动的各种主客体,为人类数字维度层面的社会活动提供了载体。但它数字化的特征又消解了自然空间的时空特性,传统物理意义上的距离、速度以及时间等概念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效率的影响已不复存在。这意味着在数字空间逻辑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就资本周转的时间与空间特性进行的讨论已不具备了现实基础。在大卫·哈维的“三次循环”理论看来,在马克思笔下,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而对交通设施、厂房建筑等固定资产进行的扩大投资推动了城市物理空间的扩张,而这些固定资产的规划布局则是通过“空间消灭时间”的方式保证资本循环效率的最大化,资本便以此种目的和方式介入城市的空间规划之中。与自然空间相比,数字空间具有自身特有的代码逻辑,代码的运算规则决定了以数字空间为依托的社会空间的构建。因此,数字空间及其算法逻辑特征将与自然空间内产生的城市实体规划逻辑存在质的区别,算法构建的逻辑考量取代了原本的时间、空间考量并决定了数字空间的运行逻辑。
数字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另一区别在于其产生方式上,这主要体现为数字空间的人造属性,即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因此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它与同样由人类生产出的社会空间的关系问题。根据列斐伏尔的理论,社会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从数字空间的产生而言,数字空间无论是网线、无线电或是终端设备等基础设施的铺设,抑或是由这些设施传递承载的代码逻辑,均是某种社会关系的体现。数字空间既是一种新型的人类产物,更是一种新型社会空间的表现形式。尽管数字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一种,但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空间相比,又表现出技术上的独特性,即数字空间并不以自然实体为依托。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中,社会空间的出现并不代表传统自然空间的消亡,二者存在互相纠缠的关系。对社会空间而言,“用来生产它们的‘原料是自然的”,其“‘现实性既是形式的,也是实体的”。“社会空间既不是一种物,也不是一种产品:相反,它包含了被生產出来的事物,也包含了这些物共存和共时时的相互关系。”就我们购买来的某种商品而言,商品本身的生产依赖于自然,其成品是实体性的自然存在,而社会空间则是这件商品自身所创造的生产、消费等各种关系。可以说,社会空间总是寓居于某项实体的背后,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形式。但数字空间并不存在其所寓居的实体,即便是其底层表现为“0”“1”的代码逻辑,本身仍具有虚拟性。当社会空间寓居于实体时,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空间规划的内容及其科学性。而数字空间的虚拟性隐藏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可感知性,人们无法直接感知数字资源的分布是否失衡,这意味着对数字空间的逻辑建构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可感知的监督方式。
四我国智慧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其保障
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也存在自身社会空间的生产行为。但是二者对社会空间建构所遵循的深层逻辑有所不同,即不同社会制度下对社会空间的功能定位。在数字化城市时代,这种定位贯彻在数字化空间的建构中。与此同时,从数字空间的本质及其特征出发,其自身逻辑及其非实体形式特征决定了要从两方面对城市数字空间的科学运行进行制度建构,即既要保证数字空间自身代码逻辑的科学性,又要针对其不具有可被直接感知的实体形式这一特征建构一种有效可察的监督方式,通过“内”“外”两种路径的建构,才能保证城市数字空间的正义性。
(一)数字空间“使用价值”的功能定位
虽然我国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便利人们日常生活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着矛盾。例如新冠疫情初期部分老年人因无法出示健康码而出现出行难问题,因移动电子支付普及而在一些店铺出现的拒收现金问题等,都表明了数字化的普及与推进往往需要面临与传统生活方式存在的冲突,这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加快推动传统空间的数字化转型还是尊重多种空间生活方式共存?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实则就是要回答好数字空间的功能定位问题。
企业或国家对空间的探索是存在目的的,对于信息空间而言同样如此。明确中国城市数字空间的功能定位,就是要回答数字空间的建构是为了实现何种目的这一问题。社会生产依赖于空间并创造了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城市空间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货物生产和消费地方之总和,它是如同机器一般的生产资料,是一种各种元素都可以彼此交换的商业化空间,这意味着城市空间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外,也同时具有交换价值。在消费社会,空间成为可供交换的资源,加入到商品交换的队伍中。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以生产之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为取向,空间的生产发生了均质化的逻辑与重复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它否定了自然、历史、年龄、性别和族群等各方面的差异,打造了同质化的可用于交换的商业空间,其背后遵循的则是交换价值优先于使用价值的资本原则。
信息作为社会空间的一种形式,同时兼具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在列斐伏尔看来,信息产品来自生产的活动并被消费,其生产需要物质与劳动成本,它是一种具有非物质性的超级商品,所以信息一旦被生产出来,就要参与到买卖之中。它同样面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冲突与选择。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相比,区别之一就体现在两种价值的优先定位上。社会主义的空间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空间,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需要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有接近一个空间的权利,以及拥有作为社会生活与所谓的文化活动等之重心的都市生活的权利”。由此,社会主义的数字空间不能是以资本作为衡量标准的逐利性空间,而是使用优先于交换的差异化空间,社会主义的数字化转型要以尊重不同群体的空间生存模式为基础。
(二)数字空间正义性的内在保障:数字空间逻辑的正义性
数字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区别在于其隐藏在数字代码中的逻辑性。作为人造空间,数字空间的逻辑必然是其生产者主观意向的体现。在数据运算逻辑上存在的非正义问题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大数据杀熟”现象为代表。目前学界并未对“大数据杀熟”有权威的定义,但从其表现特征而言,可以概括为消费者在购买同款产品时存在的价格差异现象,这种现象又以在线旅游、网约车等领域为代表。这种价格区别对待既针对不同群体,例如Android和iOS两种操作系统就同种商品存在价格差异;又针对同一主体,例如同一消费者在同一平台形成消费习惯后,会存在价格上涨等情况等。
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原因在于上述数字空间所内含的非正义逻辑。在我国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中,无论是城市宏观还是居民个体生活的数字转型,均离不开各类企业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既表现为高新技术企业对各级人民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又表现为不同数字平台对人们具体生活的参与。在列斐伏尔看来,信息技术虽然是一种科技,但其内含了一种被论述为实证知识的意识形态,掌握了数字信息生产的技术权威和技术官僚便可以让世界按照他们的指令进行运转。因此,并不存在一种纯正的类似于自然空间的社会空间,与物理、化学等客观中立性的技术不同,城市数字技术的逻辑蕴含了其建构主体的主观意向,当这种主观性成为其自身不可剥离的特征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阶级意志应在数字空间逻辑的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正义实现的根本依据是数字资源的合理分配。尽管当下的智慧城市建设表现为政企合作的模式,但同样依赖于政府对数据主体在资源占有、使用等方面的平等,力图保证数字空间的科学性并以此实现运算的结果正义。
(三)数字空间正义性的外在保障:数字监督制度的建构
当我们吃面包时,这块面包的物质形式蕴含了与其相关的生产、消费等一系列社会关系。同样地,城市发展及其社会空间生产的逻辑同样体现在建筑、场地等一系列物质的外在形式中。只有当某种社会空间依附于实体存在时,实体的直观可感知性才能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空间逻辑提供观察的视野和工具。信息作为一种产品同样涉及劳动、生产成本、剩余价值等内容,作为一种商品,信息具有其他商品都具有的特征,但其表现形式是非物质的。这意味着人们对数字空间逻辑的感知缺乏了可考的直观形式。前文已述,数字空间并非客观中立,它内含其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因此,数字空间运算的正义性还需要外在的监督制度的建构。
一方面,城市数字空间监督制度的推行要使数字空间的算法逻辑适当公开透明化。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是数字正义实现的外在表征。例如在大数据杀熟中,消费者只能感知数据运算的最终结果——价格,并比较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的价格差异,这是人们发现数字空间非正义逻辑的唯一渠道。但人们对这一结果的具体运算逻辑却不得而知,相应的解释权也被掌握在相关平台手中。“算法平台与个人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对于算法运用的知情与同意是构建个人与算法平台之间契约正义的前提之一。”在当前市场力量参与数字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消费者对数字空间建构的逻辑进行监督就显得尤为必要。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算法存在自我学习和自我更新的可能,其逻辑建构在自动学习的过程中存在发展方向的随机性,甚至会超出其生产者的认知范畴,数字算法的监督就显得更为必要。因此,通过对算法的基本原理、主观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能提高人们对算法服务的分享和监督并抑制算法的误用和滥用。
另一方面,政府应在城市数字空间监督制度的落实中起主导作用。城市数字空间的建构依赖于数字技术的运用,而后者作为一门专业技能,对其理解和监督存在技术门槛。这意味着即便将城市空间的数字算法逻辑完全公开透明,普通城市居民也难以理解其具体内容,更谈不上监督制度的落实,而为了监督的落实而让居民都成为技术专家又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换言之,城市数字平台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不可弥补的信息和技术差,而政府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具备弥补差距、落实监督的可操作性,由政府主导的数字空间监督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数字化转型中“为什么人服务”等根本问题的回答。
智慧城市的转型已经成为进行时。新事物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直面并解决这些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面对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以及对相关理论的建构和完善是对目前乃至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进行未雨绸缪的有效手段。近年来,智慧城市在稳步推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现实问题,亨利·列斐伏尔在20世纪所提出的城市空间理论仍能为我们解读城市数字化的本质提供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工具。数字空间作为社会空间的一种表現形式,同样具备后者的阶级意志性,在此基础上,中国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谁主导”和“为了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明确数字空间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在政府的主导下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确保城市数字空间正义的实现。
The Spatial Logic and Justice Guarantee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Starting from Henri Lefebvres Spatial Theory
QIN Feng-li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itie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governance abilities. Traditional Marxism regards space as the place of human activities. Western Marxist scholar Henri Lefebvre promotes a cognitive turn of urban space, believing that urban social space is a product of human social activities and a kind of social relations with class will. Social space has an abstract essence and is embodied by physical entities such as products. The injustice of urban space originates from the inner class will of social space and is perceived through material entities. The urban digital space generated by th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new form of social space, and its code logic reflects the class ideology without intuitive physical form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igital,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use” of digital space over “exchange”,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code logic of digital space, and to build a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spa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smart city; urban rights; spatial logic; digital city; justice guarantee
【責任编辑: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