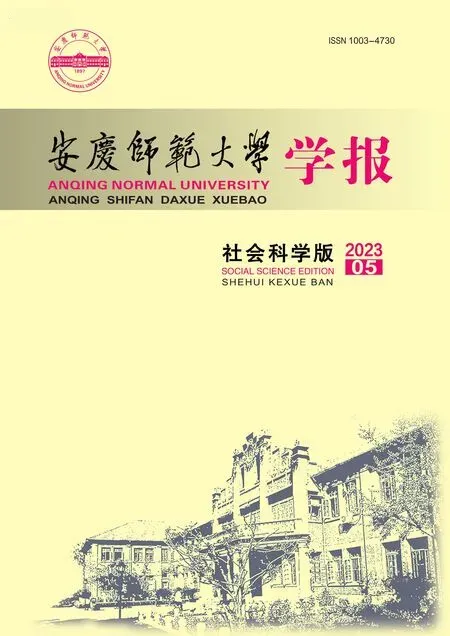失衡与蜕化:民初皖省议会的整体检视(1912—1913)
2023-06-07李贺
李 贺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0)
民国初建时期,作为移植西方代议制重要成果的省议会得到迅速发展,这反映了近代中国政体由专制向民主体制嬗变的趋势。学界成果集中在还原清末民初省级议会的整体发展脉络。虽有讨论省议会与地方行政长官间的博弈,但未充分重视两者的互动对地方政局与政情所带来的多重影响。民初皖省议会与都督间的交涉过程尚未得到细致的考察,部分史论亦有相当程度误读,需重新审视①参见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淮清由咨议局论至省议会解散,但文内多有史实讹误。郭从杰单纯围绕安徽政局与都督人选的变动展开讨论。参见张淮清:《民初安徽的议会》,《安徽辛亥革命论文选》,安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版,第140-148页;郭从杰:《民初安徽政局与都督人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89-92页。。本文一方面着力于从安徽一地的视角,探查民初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情状,厘清模糊史实;另一方面通过展现民初政制设置与实际政情间的困境,试图剖析民国初年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尝试管窥民主政治在民初中国失败的深层因素。
一、失衡的地方权力结构
辛亥革命后,皖省地方政治格局被重构,处于政治体制的转型阶段。1911年12月,孙毓筠任都督后,组建安徽军政府。1912年1 月4 日,省城士绅在安徽咨议局旧址组建全皖临时省议会(以下称临时议会)[1],胡璧城当选临时议会议长,武炎康当选副议长。两人均是前清安徽咨议局的要员,前者曾任咨议局书记长,后者是1910年度议员。时局未稳,临时议会未经全民选举。其成员基本由清末咨议局承袭而来,或由地方士绅直接指定,尚未形成清晰的议员轮转机制,依然是旧式士绅把持着主导权。孙督与临时议会合作,陆续拟定《中华民国皖省临时约法》《全皖临时议会会章》与《皖省临时县议会章程》等,构建起三权分立的地方权力结构。特别是《皖省临时约法》规定,“军政府以全皖人民公举之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员,与临时议会,法院三部构成之”[2],将三权分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
晚清《咨议局局章》规定督抚有“监督咨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并于咨议局之议案有裁夺施行之权力”,“可得令其停会”[3],并对各项事务有唯一决定权。该法赋予督抚极大的自由裁量权限,特别是允许督抚强令咨议局停会或解散,为督抚绝对压制咨议局提供了明确的法理依据。
然而,民初皖省一系列法规改变了这一局面,使临时议会的权力凌驾于地方长官之上,“都督公布议会议决之法案,执行之,但对于议决法案,有认为不当时,得于七日内说明理由。付临时议会再议,以一次为限,……都督为保持公安或遇非常紧要,不及召集临时议会时,得发布代法律之制令。此项制令事后,须得临时议会承认,如不得承认,则失将来之效力。……都督为执行法律,或保持公共安宁秩序,增进人民幸福,得发必要之命令或使行政各司发之,但不得以命令变更法律”[4],这彻底扭转了清末咨议局时期地方长官完全压制咨议局的局面。
双方的权力关系不仅在法规条文中被重塑,而且体现在具体议案问题上。先前清末督抚在议案问题上权力极大,可以“监督咨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并于咨议局之议案有裁夺施行之权”[5],咨议局形同督抚的咨询机构,并无对等的地位,相关议案也仅是建议。《皖省临时约法》大大增强了临时议会的提案权,议员不仅能对都督的行事加以制约,还可向都督和政务会员提出质询,并要求七日内回应。同时,临时议会的职能范围大为扩展,包括设计筹划全皖政务,制定军事法及普通法律,拟定官制及官俸,制定安徽预决算案,税法及公债,与中央参议院保持密切联络等八个方面[4]。这极大改变了咨议局原本的咨询性质。从制度设计层面增强了临时议会对都督的制约,有效防范了都督专权。但依照相关法规,临时省议会权力过大,缺乏相应监督和制衡的议员权势往往超过地方主政长官,为其行事逾越常规,与都督产生冲突和矛盾埋下隐忧①临时议会与孙毓筠在省内诸多事务上,均有冲突,最终被迫辞职。参见李贺《辛亥革命与地方政局:以民初皖督更迭为视角(1911—1912)》,《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第51-60页。。失衡的地方权力结构必然影响都督政务工作的展开。孙毓筠眼见事无可为,选择辞去安徽都督一职②孙氏回忆临时议会称“皖省政治机关人才辐辏,自非同合汙俗,不足容纳群流。况机械日深,竞争益烈,肆应失当,谤议纷乘”。参见《孙毓筠电陈辞职理由》,《新闻报》,1912年5月18日,第2张第2页。。
不久,空缺的皖督一职由柏文蔚接任,柏氏原本无意于此职,但袁世凯下令撤销南京留守府,并将柏文蔚的第一军归陆军部管辖[4],使其再无留驻南京的借口。柏文蔚计划将安徽作为跳板,达到保存革命力量的目的[5]。然而,在柏文蔚到任后,失衡的地方权力结构进一步恶化,致使政令难以推行,加速了时局的崩坏。
二、临时省议会与柏文蔚
(一)皖省预算案
预算案问题,成为柏文蔚与临时议会的首次交锋。临时议会依照先前《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议决本省预算决算案为本会最重之责任。皖省自光复以来,已将周年所有本年预算案及光复以后决算案均尚未准”[6],向柏文蔚去文,要求提交预算案。
出于争夺财权的考虑,柏文蔚故意不上交预算案。议会随即发文通知柏督10月1日召开预算案临时会议,要求必须于当日前提交预算案。即便如此,会前柏督仅提交司法部分的预算案。临时议会发出质询文,要求“亟应专案,咨催务请于文到一星期内,迅将本年预算案及光复后之决算案一并提交到会,以便议决”[7]。议员认为柏督屡次不上交预算案是有意为之,“实为藐视”[8]。柏督为安抚议员,同意提交预算案,但以“各机关或经军事纷扰文卷散佚,或以政局更变手续不同”为由,称仅能提交一部分预算案[9]。
迟至23 日,柏文蔚才将预算案全部提交。议员们审查后,认为该案漏洞百出。首先,该案内并无明确起算与结算时间。其次,该案中的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收入仅有五百多万元,财政支出竟达一千三百多万元,差值达七百多万元。再次,收入竟较前清宣统三年时期的预算减少数十万元。最后,支出项目中,出现大量不合理支出内容。如竟将某学生的学费纳入省级预算案内[10]。
负责回应质疑的都督代表仅能解释部分问题。议员遂拒绝审议该预算案,要求柏督亲自到会回应质疑[11]。25 日的会议,柏文蔚的态度出现重大转变,全部接受了议员提出修改预算案的建议。关于军费支出部分,议员要求将军事经费全部剔除,不应入案。柏督亦承诺将军费归入他项,不计入正式支出之内。原本缺口巨大的预算案账目竟然盈余一百多万元[12]。由此,预算案才得到临时议会的批准。
柏文蔚的态度转变自有其考量。他认为预算案虽由临时议会审议,但待正式省议会成立后,必然重新拟定。而审议预算案的10 月底,皖省正式省议会的选举已进入选举后期,议员的洗牌只是时间问题。
果不其然,1913年2月,距先前审议通过的省预算案下限时间尚有半年,此时临时议会已解散,正式省议会成立未久。柏文蔚见时机成熟,以原有预算案难以满足实际为名,将其废除,而重新拟定半年预算案。新案着重削减各项行政支出,将军费列入支出,并增加至预算总额的一半。临时议会拟定的预算案被彻底推翻[12]。
柏文蔚与临时议会关于预算案的争端实质是双方争夺财政主导权的缩影。依据《临时约法》,临时议会拥有制定全皖预算和决算的权力,对都督任何预算案外的支出,均有同意与否的绝对权力[4]。都督的财权受到极大制约,柏文蔚的行为看似违反法规,但从皖省财政的情况来看,临时议会制定的预算案脱离实际,不具备操作的可能性。首先,预算案内各项理应充分调查后,具情而定。预算案纸面入款较去年爆炸式增长两倍有余,这仅是极其理想的状态,许多收入实际无法进入省府。①如各处厘卡收入,被迫调拨供给周边的驻军,该项详细收入数目尚难统计。参见《本省示令:通令皖省六十等县不得迳拨军饷由》,《安徽公报》,第31期,安徽省档案馆藏,档号:L047-002(1)-0007。省内各地的税收收入金额多有虚报,议员也未按事实,仔细核实,敷衍而定[13]。
其次,在柏文蔚所主导的预算案中,皖省半年财政收入仅为前案的四分之一。两者差距之大,足见临时议会拟定的预算案中存在严重问题,而支出的数字更是极不准确。其支出方面没有包含皖省尚未缴纳的各类赔款,其中仅辛亥壬子洋款赔款一项,就达四百多万元[12]。可见此份预算案之粗糙,这实际反映出临时议会议员行事不够严谨认真,未能尽职尽责。临时议会在省内各项事实未明的情况下,就自行修改预算案条款,暴露出相关议员在政务运行中的随意妄为,不顾实际政情困难,这与临时议会自身权势过大不无关系。
(二)铜官山矿借款案
为缓解财政困境,柏文蔚选择对外借款,将目光投向了铜官山矿。铜官山矿位于安徽铜陵,该矿铜铁资源富集,早在汉代已有开采活动。清末一度因英商介入引发矿权纠纷,激起皖人强烈不满。柏文蔚认为此前与英商订立合同时以矿山为抵本,所以招致反对。因此,再与日商谈判时,他将抵押物由矿权换成矿砂,“借款二十万”[14],并将草案合同交予临时议会审核,议员“将原合同开特别审查会,酌加修正”后通过[15]。
此事公开后,遭到主管铜官山矿的泾铜矿务公司股东的反对。他们称在合同之外,尚有秘密合同,要求中央政府及省议员出面,否决该合同。铜陵县议会同时发文反对,也称“有秘密合同,人言藉藉,不尽子虚。将来假手日人从事兴作,其遗患必较前更甚”[16]。临时议会向柏督去函,要求重新核实合同内容,并称“若有其他改订或着密约,均为无效”,要求将筹集还款办法文件和合同原件交至议会[17],要求都督回应关于该合同有无按照议会的要求修订,借款是否给付,能否于一年内开采矿砂等问题[18]。
依照借款合同,柏文蔚必须尽快开采矿砂,用以垫款,加之以泾铜公司股东为代表的反对声浪日甚,柏文蔚要求工商部取消泾铜矿务公司办理铜官山矿的执照许可[19],并计划与徽南富商程源铨合作开发。消息一出,全皖旅沪同乡会为之哗然,向临时议会发文,称程源铨实为陈麟趾。此人名声不佳,常与外商勾结,出卖本国资产,要求临时议会仔细调查此人[20]。
柏文蔚立刻作出回应,派人与全皖旅沪同乡会开展合作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程源铨和陈麟跖并非同一人,也并无勾结洋商的行为[21]。为弥补泾铜公司原有股东的损失,柏文蔚提议他们可以与新入的资方洽谈合作事宜,共组新公司[22]。但泾铜公司方面表示拒绝同外人和外商共同开矿,向袁世凯发文,“铜官系铜铁大矿,为各种制造之本质”,要求中央出面废除借款合同,可“无损自主之权,大利既兴,外患永息”[23]。
柏文蔚向袁世凯发文,解释此次借款并无损失主权之处,相关传闻经过调查,均属失实,都是“奋私攘利之徒,得以淆乱听闻”,希望“用敢缕陈,乞垂察焉”[24]。但工商部明令柏督将铜官山矿的经营权仍交还泾铜公司,只准该公司开采[25],并要求国务院审议其提出的“明定矿务权限议案”,该案核心内容是在增加工商部对各地矿务公司的控制权,特别是限制各省行政长官对外抵押矿产借款事项上,必须得到工商部的准许。国务院通过这一议案,袁世凯也通过秘书厅发声,强调矿务事宜均归工商部管辖[26]。这彻底否定该矿开发的可能。
此次事件虽以泾铜公司上书成功,合同废止作罢。但事情的经过非常蹊跷。早先工商部审查时认为“详核查合同九条,诚与普通卖买预约无异”[27],遂批准通过。可见合同本身并无问题。该公司看似捍卫皖人的矿权,但又以“若续行动工,引起日人之干涉,是用暂缓,……实为保存矿权,消弭后患起见,未敢遽言兴利也”为由[25],停滞铜官山矿的开发,致使铜官山矿错失发展良机。
三、正式省议会与柏文蔚
随着柏文蔚与临时议会双方共事日久,两方间矛盾日渐激化。省议会常常用《中华民国皖省临时约法》中的法规,制约柏文蔚日常行事,所以柏氏迫切谋求对该法加以调整。正值北京参议院发布决议,称“各省不准自行自定约法”[28]。柏文蔚以该决议,向临时议会去函,要求重新拟定皖省约法。临时议会予以拒绝,称《皖省临时约法》“有与中央约法冲突者,当然失其效力。其中央约法未能包括者,仍须暂行遵守”[29]。因此,柏督第一次调整皖省约法的尝试,无功而返。
1912年6 月起,北京政府颁布一系列涉及筹备国会与省议会的法律条文,如《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及细则等,要求各地省政府加快开展省议会的正式选举。柏文蔚深知此次选举是重新洗牌议员势力,以及调整省议会与都督间关系的好机会,故极为重视,专门设置安徽正式议会选举事务所,用以处理繁杂选举事务[30]。1913年2 月24 日,第一届安徽省正式省议会成立,共选出108名议员。议长为吕志元,副议长为王树功和赵继椿[31]。
4 月2 日,北京政府公布《省议会暂行法》[32]。该法相较于《全皖临时议会章程》而言,最关键的变动在于重新调配了地方长官与省议会间的权力关系。依据新法,安徽省议会的权力被从各层面削弱,失去对行政长官的优势地位,首先是削弱议员监督行政的权力,大大增加省议员进行弹劾和质问的程序成本,更是将弹劾与质问权变为“提出弹劾”权,监督职能大为弱化。其次,议案最终裁定权的归属也发生变更,由省议会变为中央政府。而议案之外的一切事项,省议会的权力也从直接否决权变为建议权。议员的自主性也极大削弱,需要征得地方长官同意后,方可召开临时会议[4]。
总的来说,安徽省议会的权势大大下降,特别是改变《临时章程》及《皖省临时约法》共同搭建的安徽地方政治权力结构,省议会的立法权大大弱化,并削弱地方议会对地方长官的监督权。原先立法权高于行政权的政治运行模式由此改变。同时,对柏文蔚而言,省议会选举中国民党可谓大获全胜,108名议员中国民党籍议员为73人,占议员总数的67%[33]。柏文蔚直呼“对于今日之会,馨香祷祝。而绝挟无穷之希望,以随之也”,可见其对重新选举后的省议会是有所期待的[34],但实际情况是柏文蔚的误判及越轨行为导致皖省议员对他的积怨渐深,最终议员间的分裂加剧,时局走向崩坏。
具体而言,国民党在皖省议会选举上的大胜,通常认为这是“追求民主共和的国民党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的具体体现[35]。或者说这是安徽革命阵营对立宪阵营的胜利,将安徽省议会的主导力量视作国民党领衔的革命派。这与实际不相符合,虽然省议会中国民党籍的议员人数占据多数,但正副议长三人中,除王树功为国民党,剩下的吕志元和赵继椿均不是国民党员。两人均担任过咨议局议员,有着浓厚立宪派背景。而依《暂行法》,省议会正副议长均为议员自行投票选出,必须过半数者,才可当选,可见国民党的势力并非如议员占比那样压倒性,所以国民党籍议员在省议会的运行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值得仔细考量。
此番论断,还可以从同期的安徽公开选举的参众两院议员名单得到印证。参议院议员由一省省议会议员选出,众议院议员由一省人民直接公举。依据议员登记党籍来看,参议院议员共10人,9 人为国民党籍。众议院议员共26 人,其中10 人为国民党籍[36]353-354。按照张朋园先生统计的第一届参众两院议员信息,22 名安徽省两院议员中,议员出身的共有11 人。而从事革命出身的则无一人[36]104。安徽省议会中的力量对比,相较于临时议会时期,革命阵营力量有所加强,但并非是压倒性的。
省议会选举后,有鉴于临时议会的制约,柏文蔚决定先加强自身权力。他将原有的都督府解散,重新组织行政公署,撤销军政司,同时宣布兼任民政长和都督,掌握军政和行政大权[37]。在日常行政上,以行政会议取代政务会,并重新拟定了行政会议的运行规则。该会原本的议事模式是由各司长及都督共同开会,议定皖省政务事项,并将结果交至省议会定夺[4]。新的规定明确“行政会议以多数取决可否,同时由民政长裁决,但议决之结果,民政长因事务之必要,得变更之”,将最终裁定权完全交由行政长官,并且行政会议的审议内容包含“省议会议决案之审查”[38]。这意味着柏文蔚对省议会议决事项,拥有最终裁定权。若不认同省议会的议决案,可以采取拖延的态度,不予以审核。
至此,柏文蔚在与省议会的博弈中占据绝对优势。于是,他在没有与省议会商讨的情况下,私下与日商签定售米合同,并自行拟定预算案,这招致议员的强烈反对[39]。省议会提出质询书,要求柏督到会回复。柏氏以“本无政治知识,不过事事遵照中央命令而已”,将问题丢给中央政府。有议员痛斥“民政长革命伟人,对于本会议决事件不遵法律、不采舆论,概用强硬手段,实与《暂行法》不合,……民政长对于本会是何地位?是何职权?请明白答复”,柏督解释“鄙人对于议会并无成见。凡行政公署答复案件,意谓不在议决范围以内,故无庸公布”[40],质询会便草草收场。
经过此次质询,省议员间围绕反对柏文蔚与否,逐渐分裂成国民党一方与非国民党一方。不久,袁世凯有意清算国民党,许多省议员见中央不利于国民党,宣布“鄙人等素超然主义,所有各党前送证书一概脱离关系”,或将“党证……销毁,脱离关系,已不自今日始”[41]。
四、皖省议会的整体检视
整体上,民国初年皖省议会能够在《临时约法》所赋予的权力范围内,通过制定议案有效限制都督行为,制衡地方行政长官权力。为贯彻民主政治精神,维护本省利益,发挥了正向作用。
具体而言,议员能够依据法规条款,监督都督及都督府属员。临时议会时期,针对都督府内务司长干涉地方人事权的违法行为。议员依据法规,指出“都督各司对于各县,并不得视为直辖之特别机关,直发司令。内务司司长郑芳荪自署理以来,对于各县曾经屡发司令,并谓各该县为本司直辖官厅,误解官制,侵越职权,莫此为甚”[42],要求柏文蔚取消相关法令,严格管理其他各司官员。对于柏文蔚继任初期,长期不驻安庆。省议会以《都督轻离职守文》发起质询,“都督为全省行政长官,负有行政机关完全责任。吾民生命财产赖以保卫,行政机关诚不可一日停滞。若一日无负完全责任之人,则于政治上,地方上均大有关系”[43],要求其尽快赴省府坐镇。
同时省议会活动范围不局限于皖省一隅,积极参与全国性的事务。安徽临时议会主动联合江苏、浙江等省议会发起联合公电,对袁世凯未经国会通过所颁布的独断命令加以抵制,认为袁氏“所颁命令未经议会认可,不能发生效力。此种法律不能以命令代之,……民国政体共和诸凡法令,宜求民意”[44],并共同组建省议会联合会反对对外大借款[45],声称借款“未经议会议决,本会绝不承认”[46]。
皖省议会的巨大进步还直观体现在议员选举人数的跨越式增加。清末民初时段,安徽省级议会由肇兴,发展至中断,可划分为清末安徽咨议局,民初安徽临时议会和第一届安徽省议会三个时期。
这三个阶段的选举参与人数增长迅速,除临时省议会为过渡时期外,议员的选举受时局动荡的影响,未经全省民众公举。而另两阶段的议员均由全省选民通过选举而来。两次选举采取初选与复选结合的制度。两个阶段相比,其参与选举的规模不断扩大,参与选民人数由咨议局时期77902 名,增加至1451063 名[47]。咨议局时期的选举,仅有0.48%的人口具有选举权。而在正式省议会选举时,则增加至8.94%。就数字而言,参与的比例有长足的进步,皖省政治参与的范围大为扩展,开创与进步性仍旧非常突出。但受限于《局章》和《暂行法》内关于选举人条件的限制,普及性仍相对不足。
在具体议员人选方面,每届人选均有更新,连选与包办的比例很低,可见皖省议会选举极大推动议员的换代。皖省咨议员正式成员为88 人,临时省议会为41 人,第一届省议会为108 人。其中咨议员仍入选临时议会的仅有何震和武炎康两人。咨议局议员仍入选正式省议会中仅有7人,分别为赵继椿、吕擢恩、赵文元、王树功、柳汝士、王盖臣和张仲烜。临时省议会成员入选正式省议会的有刘道章、崔翔青、章家祉和章兆鸿四人入选。
不可否认的是,省议会也暴露相当的消极色彩,主要体现在党派不断的倾轧和议事功能的丧失,这影响到代议制机构的正常运作,最终导致民主精神丧失。代表性事件就是1913年初黎宗岳被捕事件。
1913年1 月26 日,正值安徽众议院议员的复选,黎宗岳在选举会场上被柏文蔚派人逮捕,并命令司法司长和高等审判厅长立即在都督府内开始审讯。有得知此事的皖省士绅立刻发文给袁世凯,控诉这一行为,称“柏都督于神圣不可侵犯之选举期间,逮捕无辜”,事态由此扩大[48]。省议员吴尔梅等人收到消息后,认为此举是违法逮捕被选举人,破坏正常选举。对此,柏文蔚称黎在大通军政分府时期曾私吞数额巨大的税款,至今尚未归还。此次并非逮捕,而是邀其暂住都督府,保护人身安全的同时,与黎氏清算核对账目。但是吴尔梅加以驳斥,称“查黎云报销,曾由大总统批交财政部核准,更何清算之可言,且即云清算,亦应发交议会。柏之诡词,搪塞不过,遂其专横违法之私”[49]。此后舆论进一步发酵,甚至有传闻黎氏已病重[50],各界纷纷要求释放黎氏,又有黎宗岳写给族亲黎元洪的私人书信公开登报。黎称自己并非私吞钱款,而是“柏文蔚挟党见以陷平民,与国民党破坏他党之种种横暴手段”[51],言下柏文蔚就是为国民党的选举利益,打击其他民主党派。此书信试图将舆论讨论的视线导向政党之间的矛盾。
黎宗岳的公开信让此事愈加复杂。柏文蔚为正视听,特向袁世凯解释事情原委。袁世凯认可柏文蔚的举动,并强调“(黎)曾于上年五月间,通缉有案。现自行回皖,即由该督勒令清算,以恤商艰而重税款”[52]。因此,黎宗岳的确是携款未还,并非是自述被柏督因党见所诬陷,但在黎元洪的运作下,柏文蔚被迫将黎宗岳释放,税款未能追回[53]。
实际上,柏文蔚的指责确凿无疑。辛亥年间,黎宗岳从大通军政分府败退后,大通督销局长要求公开通缉黎宗岳,预估其侵吞的钱款九万多两,但实际有八十多万两[54]。北京财政部知悉后,命令黎宗岳交还此款[55],但黎氏踪迹全无,此事便不了了之。
细究此事中议员和都督的表现,柏文蔚逮捕议员参选人,自然不符法理,但也并非恣意妄为。他在逮捕前,已经事先通知黎宗岳,要求其尽快偿还钱款,“电请大总统饬令黎宗岳结算追缴在案,并据大通商会转呈各商要求偿还截款,……转饬黎宗岳自行清结”[56]。
省议员方面,吴尔梅如此积极,带头声讨柏督,也并非单纯只是维护选举的正义性。而是他与黎宗岳均为皖省共和党的成员,自然紧密捆绑。吴氏极力鼓噪宣传,联合58名议员,这已经超过议员总数的一半[57],宣称“黎宗岳一日不出省会,一日(省议会)不敢成立”[58],用议会的正常运作,作为威胁都督的手段,用以达成自己的政党利益。黎宗岳释放后,赴湖北黎元洪处,省议员李葆诚等人挟八百余名商界绅界人士举办欢送会[59]。
此事上,省议员所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他们出于政党利益,损害皖省利权,充分暴露多数议员不具备代表皖省民意的公心,不仅不主动保护皖省财产,反而对黎宗岳的窃取行为大加维护。究其缘由,是因在议员们看来党派利益已远超其他一切。《申报》批评道:勿论黎非逮捕,即果逮捕,逮捕而实出于冤枉,亦无以不开会为挟制之必要。勿论黎非议员,即为议员,议员而在开会期内,亦无骤以停会为要索之理由。况省会尚未成立,辄因少数人之意见,致欲将全省最高之立法机关,牺牲于绝无关系之一人,得毋轻视省议会乎[60]。这种以政党利益为首要诉求的组织,已经难以肩负起维护地方利益,监督行政长官,推动社会稳定发展的历史使命。
皖省议会出现的这次乱象并非孤例,其会议运作过程,亦是问题频现。省议会开会人数长期不满额,并且议事混乱。皖省议员总数为108 人,但在常会召开时,不少议员请假不来,迟到早退更是屡见不鲜。如4 月15 日,到会人数为76 人。4月20日,到会仅61人。议员崔翔青不满到会议员太少,要求严格请假制度,不可随意同意议员请假[61]。而开会中“凡提议一事,无不经吵闹之,……各议员之间起立狂叫跺脚,……大声呼闹”,“议长再三央求,秩序稍定。闹声又起,有责议长不能维持秩序者,有责议员太不自爱者,有请议长惩罚,……一哄而散,终未议决一事云”[62],甚至有不少议员于散会时间之前从会场后门溜走,毫无会议纪律,“议事等与儿戏”[63]。
4 月20 日后,更是出现到会人数不足法定人数一半,议会无法开会的窘状。说明省议会的正常运作已经遇到困难,议员懈怠至此,议会能发挥的实际作用显然有限,能否真正代表民意也值得商榷[63]。但在3月省议会选举参议员时,到会人数达105 人,时间仅差一月,人数竟相差巨大[64]。究其原因,对各位参选人而言,如选举参议员成功,加入了国会,其权势将远超普通省议员,故而是次会议议员的积极性非常高。
以上所述乱象引发皖省有志之士的不满,他们认为省议会“虽法定机关,实金钱所构造。即有刚正不阿之士,亦皆牵于党见,迫于权威,仗马寒蝉,积成习惯,贪狼猛虎,恣意横行”[65],实已无法代表全省民意。二次革命后,倪嗣冲取得皖省主导权,顺应袁世凯旨意,认为省议会等机构不应存在,“类系临时组成,其章制非妥善,而人品亦属混淆”[66],解散了省议会。
五、结语
辛亥革命带来政权的更迭和地方权力格局的洗牌。皖省源于其重要政治地缘,自身同全国政局变动紧密相关。皖省政治结构呈现出失衡的状态,柏文蔚到任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省议会同都督间愈发激烈的政争即是具像体现。双方的矛盾不断尖锐,省内历经此番,局势转危。二次革命后,倪嗣冲取消省议会。地方政体的近代化转轨遭遇重大挫折。
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与柏文蔚有密切关系。时人均认为“柏都督志在不皖”[67],柏文蔚任督的本意是将安徽当作跳板与根据地,借此壮大柏系势力,加之其行伍出身,做事向来专断,缺乏平衡各方利益的能力和经验,这极易带来诸多弊病。其次,省议会也并非一直处于正轨,临时议会权势过大,在与柏文蔚的交涉时,政党利益优先,缺乏牺牲妥协的精神,使得地方政治生态不断恶化,引发社会动荡。经济建设难于平稳进行,也就失去了继续推行民主政治的基础。柏文蔚抱怨“所有议决之案,文蔚自有执行之义务。唯有碍于事实者,不得不稍求变通,且又当追不及待,确难交议之时,则唯有于解释条文时,就原案略加伸缩”[68],依其所说,省议会行事多有偏差,从预算案等事件中体现更为明晰,议员虽限制都督的专权,但是常为了反对而反对,特别是省内财政问题,难于主动提出有益的建策。同时,其内部围绕党派利益与政见诉求出现巨大分歧,这无助于皖省政治情势的发展,反而带来更大的混乱,不断增加内耗,致使地方政局暗藏危机。
总之,民初皖省政局混乱的关键原因在于以省议会为核心的地方政治体系是建立在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基础上的,由此导致省议会与都督间的矛盾冲突难以避免。在实际的运行中,省议会无法切实代表民意,难以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地方长官行事难言为民,抱有别种目的。皖省地方民主政治的崩坏是必然的结果。双方政争缘起于人事与权益的争夺,其背后反映出近代以来政治转型的偏轨。这亦是移植后的民主政治难以解决实际面临的政情困境,进而民主政治让位于专制独裁的原因所在。可见代议制的移植与培育,需要在相对平衡的权力关系基础之上,仰仗各方耐心地在民主政体框架下协商合作,才或有平稳运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