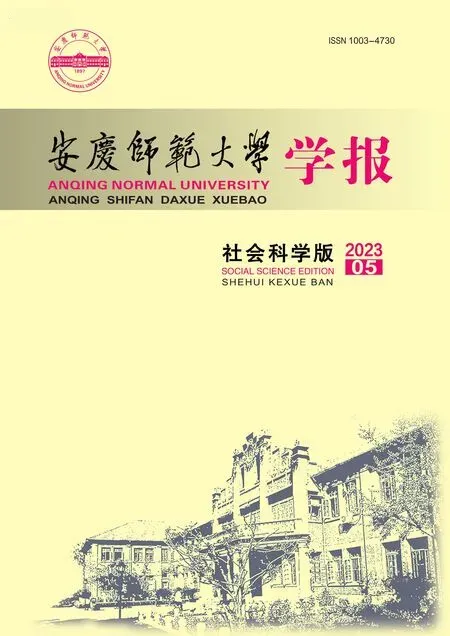论东汉后期夷夏观念中的两种逻辑
——以“弃凉之议”为线索
2023-06-07杨佳将
杨佳将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市 300350)
王夫之曾谓:“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1]976,直至明清时期,夷夏问题仍然是人们在思想上与政治上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在思想上,如何阐释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如何看待夷夏互动,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政治上,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实践、外交战略的制定,乃至对外战争的发动,其背后均隐含着夷夏观念中与之相应的某种逻辑。
基于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丰富内涵,当前学界大致有三种研究理路,各有侧重。其一,从民族史或民族关系史的角度审视夷夏观念。正如孙晓春所说,夷夏观念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2]。华夏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是夷夏观念得以生成和演进的前提。其二,从边疆史地研究的角度审视夷夏观念,解剖夷夏观念与中原王朝的边疆制度、边疆政策以及具体的边疆机构、人事间的联系。其三,从天下观与天下秩序的角度审视夷夏观念。邢义田与高明士便曾致力于将夷夏观念置于“天下”的框架中①相关著作有: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版);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版)。,海外汉学研究亦普遍秉持这一思路②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夷夏观念,可见于:(日)川本芳昭《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版);(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夷夏观念的研究已非常成熟,在各个层面均成果斐然。不过,人们大多是以整全性的视角来理解夷夏观念,而鲜有从夷夏观念内部进行进一步分割者。罗志田曾将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区分为“封闭”与“开放”两种面向,认为封闭的夷夏观念与开放的夷夏观念“犹如一个钱币之两面,共存而成一体”[3]。此说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颇有助益。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东汉后期的“弃凉之议”与汉羌冲突为视角,横向考察存在于夷夏观念内部的争论。
一、“弃凉之议”与夷夏观念的封闭逻辑
夷夏观念中的“夷”,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指对象并不相同。在西汉一朝,匈奴无疑是汉民族最主要的敌对民族。到了东汉时期,经历了南匈奴内附与窦固、窦宪两次征讨北匈奴,匈奴对于中原王朝的威胁大致宣告解除,“羌患”转而成为东汉的心腹之患。
早在东汉章帝、和帝时,凉州羌人叛乱已成为东汉的首要边患。安帝时接连爆发的三次凉州羌人大起义,更是使得“羌患”问题成为关乎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各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对于凉州叛乱的羌人是战是抚,乃至如何防止羌人再度反叛,是当时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弃凉之议”即是在此期间提出的应对“羌患”的一种方略。
东汉中后期的思想家王符世居凉州,恰身处于汉羌冲突的中心地带。在其政论著作《潜夫论》中,王符不仅详细记录了汉羌冲突始末,也亲身参与辩驳了“弃凉之议”。藉由王符的记录,可从中发现当时人们的夷夏观念中两种逻辑的交锋。
所谓“弃凉之议”,即朝议中主张放弃凉州,退守关中三辅地区以回避羌人的一种意见。《潜夫论》载:“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4]336。在安帝年间首次羌人大起义爆发后,“捐弃凉州”甚至一度成为朝堂上的主流意见,而被“公卿师尹”们广泛认同。不过,由于“弃凉之议”最终并未付诸于政治实践,所以在迄今为止的史学研究中对此问题不甚重视,鲜有相关的学术论文,而仅在一些研究两汉凉州地区的专著中有详细探讨①关于“弃凉之议”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知网上仅见一篇,即韩高年《东汉后期“弃凉之议”与马融辞赋创作再评价》(载于《学术界》2021年第6期,第108-115页),且该论文的讨论中心是马融及其辞赋,而非“弃凉之议”。详细讨论“弃凉之议”的专著有: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中国书店2002年版);薛小林《争霸西州: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版)等。。值得注意的是,自汉武帝开拓凉州以来,到东汉安帝时期羌人大起义发生,二百余年间凉州始终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期间甚至经历了新莽王朝迭代。东汉安帝时的“弃凉之议”意欲割弃凉州疆土,且竟能获得多数朝臣的支持,在两汉时期尚属首次②严格地讲,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也有朝臣建议割弃金城以西的凉州,不过光武年间这次“弃凉之议”并无重要大臣带头提出,更未获得广泛支持。,故对此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王符笔下支持“弃凉之议”的“公卿师尹”,具体言之,其为首者是车骑将军邓骘。安帝以幼年即位,朝政实际掌握在和熹邓太后与其兄邓骘手中。在永初四年(110)的朝议上,邓骘主张弃凉州的理由是“军役方费,事不相赡”[5]1866,即军费繁重,朝廷财政不足以支撑对羌战争。此次朝议中其余参与者的论点未见于《后汉书》,不过据《潜夫论》中所述“公卿以为烦费不可”[4]359,财政和军费方面的考虑应当便是赞同“弃凉”者的主要理由。
东汉安帝时的财政状况与“弃凉之议”确实有着紧密的关联。《后汉书》记载,永初年间“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5]614,在羌人起义的同时,内地接连爆发的重大水旱灾害竟致“死者相望”,这无疑是比西北边疆的羌患更加困扰中央财政的严峻问题。安帝永初元年至三年(107—109),仅在都城洛阳便发生了“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京师大饥,民相食”“京师大风”“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5]210-214共四次重大自然灾害,内地其余郡国另有十余次见诸史籍的大灾害。受这些灾害的影响,不仅朝廷的财赋收入大幅缩减,此前的积蓄也多用于赈灾。在中央财政严重透支的情况下,朝廷无力应对凉州边患,乃至于群臣萌生“弃凉之议”,是当时客观政治经济形势的一种反映。
然而,就在朝廷既已克服军费上的困难,且由邓骘亲自领兵赴凉州平叛,决议挽回凉州的情况下,朝中许多大臣却坚持“弃凉之议”不改。甚至王符作《潜夫论·救边》篇的时间为元初二年(115),距离“弃凉之议”的提出已有五年之久,此时的王符仍在与“多恨不从惑议”的“弃凉之议”论者激辩,可见“弃凉之议”并不仅仅是基于一时政治情势而做出的权宜之计,而是有其观念上和逻辑上的支撑。正如罗志田所说,汉代对夷狄的政策固然是主要从“国家利益这一实际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其“思想武器”仍是夷狄理论[3]。基于财政不支等政治现实层面的考量或许是促成“弃凉之议”提出的直接原因,而夷夏观念内在的封闭逻辑则是东汉后期“弃凉之议”得以持续存在的思想土壤。
后来担任护羌校尉的庞参是“弃凉之议”的拥趸,也是王符的主要论辩对手之一。在上呈与邓骘的奏记文书中,庞参曾透露出了他对凉州的看法:“今苟贪不毛之地,营恤不使之民,暴军伊吾之野,以虑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祸乱至今。夫拓境不宁,无益于强,多田不耕,何救饥敝!故善为国者,务怀其内,不求外利;务富其民,不贪广土”[5]1688。
在庞参看来,西域和凉州是“不毛之地”,羌人是“不使之民”。“伊吾之野”和“三族之外”,则是用以形容西凉地区与中原地区的遥远无涉。从表面上看,庞参确实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即指出凉州于国家无用。但实际上,所谓“不毛之地”与“不使之民”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凉州和西域的羌胡兵已经为东汉效力数十年之久,不仅不是“不使之民”,反而是“常使之民”。而凉州的发展水平虽然不能与内地郡国相比,但据西汉末元始二年的人口统计,武都、天水、陇西各郡人口均已逾二十万[6]1609-1612,绝不是庞参口中的“不毛之地”。因此,王符在《潜夫论》中愤怒地称庞参等人“浅浅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为小”[4]341,指斥庞参等人通过歪曲事实降低了朝廷对于凉州“羌患”问题的重视程度。
庞参不可能不清楚凉州的实际状况。他对于凉州“不毛之地”和“不使之民”的论断,固然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同时也应理解为是其主观上建构的一种夷夏想象。就庞参的主观感受而言,即便在东汉时期凉州颇具发展规模,且大量内徙的羌人在东汉“以夷制夷”的方略下被征募为羌胡兵,但夷夏之间的界限却是壁垒严明,不可逾越的。庞参向执政者提出“不求外利”和“不贪广土”的建议,正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夷夏观中固有的一种封闭逻辑,即以一条线割断“夷”与“夏”,避免二者之间发生任何交互和渗透。换言之,在庞参的观念里,“夷”与“夏”是各自封闭,有着天壤之别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夷”与“夏”之间的差别不可消弭,必须将二者彻底隔绝开来。不幸的是,凉州在庞参等内郡士人的夷夏观念中被划到了“夷”的那一侧,被视为华夏天下秩序最外侧的“不毛之地”。庞参所谓的“不毛之地”和“不使之民”,正是他对于夷夏差别的主观想象,是基于其封闭的夷夏观念的夸张表达。
夷夏观念中这一割断“夷”“夏”的封闭逻辑由来已久。班固在总结上古圣王对待夷狄的方略时说:“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6]3834。圣王政治是历代儒家所标榜的理想政治,而班固认为,圣王对待夷狄的手段便是严加防范,对于“夷”与“夏”之间任何可能发生的互动都要竭力避免。如果与夷狄进行友好盟誓,则会浪费财物且遭受欺骗;如果进攻讨伐夷狄,又会劳师动众且招致报复骚扰。因此,最理想的状态便是与夷狄始终保持距离,而并不希冀以中原文明的“政教”“正朔”等理念去影响或改变夷狄。
托名于三代圣王的“外而不内,疏而不戚”的夷夏观念,在两汉时期被反复征引和阐释,其内涵愈加丰富完整。汉昭帝时,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痛陈对匈战争是“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7]445,言下之意即不可以用中国的礼义文化来要求匈奴,更不应该听信“好事之臣”而向匈奴发动战争。汉宣帝时,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降汉,这是汉匈关系史上汉族一方前所未有的胜利,萧望之却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6]3282。
贤良文学与萧望之所面对的匈奴实力与汉匈关系态势截然不同,但在夷夏观念上却给出了一致的评判,即汉匈有别而不可强行混一。以此可知,夷夏观念中的封闭逻辑不完全取决于现实政治的情势和夷夏力量的对比,这种封闭逻辑的基础在于根植于人们心中的观念层面的文化传统,即坚信夷夏之间的隔阂无从消解,唯有保持足够的距离才是合宜之道。
到了东汉时期,夷夏观念中的封闭逻辑进一步被人们广泛接受,并持续影响着王朝政治实践。早在东汉建国伊始,刘秀便采取了“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5]697的收缩性边疆政策,主动断绝了与西域诸邦国政治上、文化上和交通上的联络。以“柔道”治国的刘秀,在夷夏问题与边疆问题上践行了前朝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的闭关主张。虽然后来在窦固、班超等人的军事行动下,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史经历了“三绝三通”的过程,但总体而言,东汉王朝从一开始就并不重视对西域的经略,更不具备开疆拓土的野心,而连通中原与西域的凉州地区随之变得无足轻重。加之以东汉定都于洛阳,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东移,结果正是如钱穆所言,“函潼以西,受不到东方暖气,其本土仅有之人物经济亦不断向东滑流,渐枯渐竭”[8]143。在政治经济方面,凉州对于东方的重要性与日俱减,而在社会文化方面,凉州也与内郡呈现出鲜明的差别。随着匈奴和羌人不断内徙,异族占凉州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凉州的士人与豪族愈益变得“羌胡化”,沾染了不尚文学而尚武的胡风。及至东汉后期,在内郡士人的眼中,羌胡化的凉州与其说是拱卫三辅的华夏边陲,毋宁说是充斥着“不使之民”的塞外蛮方。凉州与中原地区的社会文化差异越是明显,便越是成为了内郡士人眼中的可弃之地。
从王符等凉州士人的视角来看,“弃凉之议”轻易便要割弃广大疆土,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谬见,从而被“西州士大夫所笑”[5]1688。但对于当时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们来说,“弃凉之议”可谓其来有自。在封闭的夷夏观念影响之下,人们迫切希望隔绝夷夏,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羌患”困扰,而羌胡化倾向日益明显的凉州,在中原士人的观念中则被切割到了华夏之外。
二、王符的回应与夷夏观念的扩张逻辑
在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中,隔绝夷夏并不是唯一的逻辑指向。孔子曾有过“乘桴浮于海”[9]62和“欲居九夷”[9]132的想法,时人认为“九夷”鄙陋不宜居,孔子则答之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9]132,言下之意便是君子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九夷”落后野蛮的状况。相对于拒斥夷夏互动的封闭逻辑,承认并主动接受夷夏互动则导向了不同的夷夏观念。“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9]251,用华夏的礼乐道德使四夷宾服,即是展现出了夷夏观念中的开放特征。
比起“以德服人”的柔和开放的互动形式,对“夷狄”发动战争使之臣服,是历史上夷夏互动更为常见的形式。罗志田以夷夏之间“体系开放”为标准,将“柔和四夷”与“奋武卫”的主张并称为“开放的”夷夏观念,与“封闭的”夷夏观念相对立[3]。不过,不同民族间的战争本身便是文化排异与碰撞的结果,战争双方不可能以开放包容的心境去面对彼此间的文化差异,所以将“奋武卫”名之为“扩张的”夷夏观念似更妥。
在《潜夫论》中,针对朝中公卿的“弃凉之议”,王符反驳道:“《易》制御寇,《诗》美薄伐,自古有战,非乃今也”[4]355。儒家五经是东汉时期一切政治主张最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弃凉之议”论者即以三代圣王为标杆,主张隔绝夷夏。王符同样通过征引五经中《易》和《诗》里面赞美对异族战争的内容,呼吁朝廷出兵凉州,连通西域,表达了其扩张激进的夷夏观念。
如前所述,“弃凉之议”的论者反对发动对羌战争的理由有二,在政治现实上是出于节约财政与民力的考量,在观念上则是隔绝夷夏的思想传统。对此,王符亦分别从政治现实层面与思想观念层面作出回应。
对于割弃凉州以节约财赋的说法,王符斥之为“轻囷仓之蓄而惜一杯之钻”[4]359,“但知爱见簿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4]359。在王符看来,对羌战争耗费的财赋是“一杯”,而凉州民众可以创造的财赋收入则为“囷仓”,放弃凉州或可节约已有的财赋收入,长远来看却损失了财赋收入的根本来源。
王符更加关注的是问题是,何种夷夏观念才是应当的、合理的。在思维层面上,王符主要从两个方面阐明了其扩张的夷夏观念。
其一,国家割弃疆土民众本身的不合理性。在王符看来,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割弃土地都是不可接受之举,因为“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4]336,如果割弃凉州,那么三辅就成了边疆;如果羌人进入三辅,弘农、洛阳就成为边疆。倘若因为凉州居于华夏边缘、是汉羌缓冲地带便可以割弃,那么以此相推,三辅、洛阳也终将成为边地而遭受“夷狄”之扰。
王符对国家疆域领土的认识与其夷夏观念密不可分。战国时期,华夏居中而四夷居四方成为了地理上的现实,夷夏之分与地域之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已化为一体。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原地区的夷夏之分进一步被消除,复数的“诸夏”转而成为单数的“华夏”。“华夏”不再仅是一个文化概念,同时也成为一个地域概念。
“地不可无边”,其隐含之意则是“华夏不可无边”。按照夷夏观的封闭逻辑,割弃凉州恰恰是为了划清夷夏之间的边界。而王符却指出,华夏的边界并不是恒常不变的,不可能以一条线牢牢锁定,“齐魏却守,国不以安,子婴自削,秦不以在”[4]339,诸夏之间的边界尚且朝夕可变,夷与夏之间的边界更不可能对异族形成约束。因此,如果说华夏不可无边界,则边界应当拓展至对华夏文明最有利的地带,压缩四夷的生存空间,而不是自身收缩疆土而“促境”。汉武帝“东开乐浪,西置敦煌,南逾交趾,北筑朔方”[4]339,正是王符理想中的华夏君主所为。
其二,王符继承和重申了“王者无外”的思维传统。所谓“王者无外”,即“王者”在统治的地域空间上不分内外,不仅对华夏的民众负有教化的责任,对于四夷也负有教化责任。正如西汉初年贾谊所说:“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10]139按照“王者无外”的逻辑,只要是舟车所能至、人迹所能至的地方,也即当时人们空间想象所能到达的极限,都是属于华夏王者、天子的土地,其居民不论族别都是作为王者、天子的臣民。与贾谊的论述相似,王符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氐羌,莫不来享”[4]347,将活跃于凉州周边的氐、羌等异族也置入成为华夏天下秩序体系的一部分,以此说明东汉王朝出兵凉州的正当性。针对于当时中原士人将凉州视作华夏之外的观点,王符反驳道“且凡四海之内者,圣人之所以遗子孙也”[4]361,如果抛下对于凉州疆土的责任,置凉州民众的安危于不顾,便是“非人之主,非民之将,非主之佐,非胜之主”[4]362,天子将失去其所以为天子的合法性,将领则辜负了其所以寄身的职事。
王符的主张与弃凉主张针锋相对,并在朝中引发了共鸣。郎中虞诩通过向太尉李脩进谏,动摇了朝廷弃凉的决心。在虞诩的建言中,有一条理由便是“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5]1866,与王符“地不可无边”的观点如出一辙。在时间先后上,很难说明王符与虞诩谁是这一观点的首创者,不过可以确信的是,王符的主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据《后汉书·王符传》载,皇甫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5]1643,与王符相见后言谈甚欢,皇甫规正是东汉对羌战争的主要统帅之一。
在边疆政策极度保守消极的东汉后期,扩张的夷夏观念仍然在时人心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虽然朝廷最终决议出兵凉州是以现实政治利益为首要考虑、多种因素交错影响之下的结果,但经由王符、虞诩等人所阐明的扩张逻辑,却是中原王朝对异族用兵的观念基础,并为中原王朝发动对外战争提供了道义上的理由。
三、夷夏观念的困境与东汉的覆亡
根据拉铁摩尔等学者的内亚史研究①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跳出华夏文明或游牧文明的特定立场,从亚洲大陆宏观俯视两种文明间的互动。,如果将东亚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那么长城沿线则是东亚的中心,长城两侧并立着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体。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华夏农耕文明在地理上的扩张是有限度的,长城沿线两侧不同的气候、土壤和植被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划定了天然的界限。
不过,这一界限却并不是静止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并没有被这一界限所束缚隔绝。从长时段历史来看,立足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农耕文明始终面对着与北方游牧文明交互共存的现实状况。正如人类学相关研究所指出的,“游牧社会能够独立于其他经济,特别是农业基础的经济而繁荣昌盛的情况,如果曾经有过,也是很少出现的”[11]201,古代游牧社会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致使游牧文明必须不定期地从农耕文明那里获取维系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资源,这也就在客观上决定了“夷”与“夏”之间的互动将长期存在且不可避免。
因此,主张隔绝夷夏,“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的封闭夷夏观念,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贤良文学在讥刺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时候,他们却并没有意识到,汉兴七十余年间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在中原王朝与匈奴的互动方面,汉初七十年与武帝时期所不同的,只是冲突规模的大小,以及发生冲突时的主动权掌握在哪一方。即使是在文景时期“和亲”政策主导的汉匈关系格局之下,匈奴对汉朝边境的入侵和劫掠也屡见不鲜。东汉时期的羌人在政治军事实力上虽然远不及西汉时的匈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当时的羌人与汉人在生存资源上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难以调和。
从这一意义上说,王符、虞诩等人扩张的夷夏观念是有其合理性的。在夷夏问题上秉持“鸵鸟心态”,并不能带来长期的和平,反而会滋长加剧边境遭受的侵扰。正如王符所说,“地不可无边”,当残破的凉州不能再为羌人提供稳定充足的资源,那么相对富庶的关中地区也将不可避免地沦为被劫掠的目标。
但是,扩张的夷夏观念却未必总是能在政治军事实践上获得成功。就秦汉及以后的历史事实来看,“夷”与“夏”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夏”强则“夷”弱,“夷”强则“夏”弱。西汉时汉武帝决意“奋武卫”发动对匈奴战争,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民生问题,但确实保障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边境安全。相比之下,东汉中后期,中央王朝外戚与宦官间权力斗争频仍,导致了政治上的剧烈动荡失序。而在军事上,自光武帝废郡国武备以来,内郡忘战日久,战斗能力严重衰退。在中原王朝政治动荡、军事孱弱的前提下,东汉后期数次对羌战争的结果便是“军起以来,暴师五年,典兵之吏,将以千数,大小之战,岁十百合,而希有功”[4]325,虚耗国家财政,加剧了东汉王朝的衰亡。军事上的失利,进而为封闭收缩的夷夏观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王符、虞诩等人虽然充分说明了对羌战争的必要性,却并没有预料到战争的惨重代价和惨痛结果。
反思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便不难发现,夷夏问题是历朝历代始终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等民族间友好往来的佳话,但民族关系问题也时常对古代各王朝造成困扰。贾谊曾将汉初政治社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总结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6]2230,其中,匈奴问题便是“可为流涕者”,其关键程度被排到了汉初全部社会政治问题的第二位。东汉中后期的“羌患”在对国家边防安全的冲击力度上虽不及西汉时的汉匈战争,但其持续时间却更为长久,对于王朝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扩张的夷夏观念和封闭的夷夏观念为古代中国处理夷夏问题提供了两种相反的思路。然而,不管是“奋武卫”或是“不与约誓,不就攻伐”,二者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夷夏冲突。是主动进攻还是被动防守,是加以重视还是选择性忽视,都只是暂时减缓夷夏问题对国家和社会的冲击,而“夷”与“夏”的冲突本身却无从回避。西汉文帝时,面对匈奴犯边,朝中也发生过一次“救”与“不救”的争论。晁错曰:“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6]2285虽然晁错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救边”,但晁错上述言论却道出了一个事实,无论中原王朝采取何种夷夏战略,都会伴随着相应的代价和损失,且代价和损失是无可回避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必须承认的是,夷夏问题始终是一个负面消极且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被蔑称为“夷狄”的各个民族给中原王朝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持续应对夷夏问题造成的损耗则使得中原王朝走向衰败。不管夷夏间处于战争状态或是和平状态,人们看待“夷狄”时敌对和仇视的心态都是一以贯之的。
中国古代的夷夏冲突之所以不可回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无论是扩张的夷夏观念还是封闭的夷夏观念,都是以民族不平等作为其认识夷夏差别的前提,本质上都反映了民族间的歧视。王夫之便曾把这种歧视显白地讲了出来:“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1]976出生地不同,则脾性习俗不同,进而认知和行为方式不同,这确实是“夷狄”与“华夏”差异的根源。但王夫之把夷夏之间习俗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理解为贵贱高下之分,无疑是一种偏狭之见。遗憾的是,这正是古代中国思想家们的普遍观点。
历史上的华夏文明相对于周边游牧文明确实拥有着更为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体系,但华夏文明与所谓的“四夷”却并不可能存在道德上的高下之分,夷夏之间在道德价值上是平等的。以汉武帝时马邑事件来说,韩安国在指斥匈奴“怀鸟兽心”[6]2398的同时,王恢却用诈降的手段试图诱骗匈奴人进入包围圈,可见背信弃义、撕毁合约等非道德政治行为绝不是“夷狄”的专利,在华夏文明亦屡见不鲜。根植于夷夏观念深层的道德优越感,只是古时人们的一种主观虚构。虽然夷夏观念也曾持续发挥着守护华夏先进礼仪制度的积极作用,但如果站在华夏主体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立场上看,充斥着歧视心态的夷夏观念则是不可接受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各民族长期和睦共处的可能性。
就“弃凉之议”而言,由狄宇宙等学者提出的生存资源竞争理论,为夷夏冲突何以不可避免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解释路径。不过,还原到东汉后期凉州的社会状况来看,比起汉族与羌族在宏观上的生存资源的竞争,汉人官吏与豪强基于歧视性夷夏观念而对内附羌人民众施行的残酷压迫,无疑是致使汉羌战争爆发更加关键的诱因。反映凉州羌人遭受歧视与压迫的史料繁多不可胜计,在此仅举一例,足以窥其全貌:
建初元年,安夷县吏略妻卑湳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陇西太守孙纯遣从事李睦及金城兵会和罗谷,与卑湳等战,斩首虏数百人[5]2881。
安夷县的县吏由于肆意抢掠羌人妇女,被其丈夫所杀,这本来是一件民间惯见的复仇案件,但该羌人所属的种落却因此担心被灭族,于是攻杀县长,起义为寇。可见凉州地区的羌人一旦犯法,即使其犯法动机情有可原,也可能会遭致灭族的惩罚。这桩案件中安夷县吏有大过在先,最终的结果却是数百名羌人被斩首,东汉凉州羌民所遭受的歧视和压迫可见一斑。
王符长期生活于凉州,对于凉州地区的社会状况了然于心。虽然在羌人起义后,王符一再主张朝廷发动大军平叛,但对于造成羌人大起义的原因,王符却直言不讳:“原祸所起,皆吏过尔”[4]368,王符的这一论断可谓精当,凉州官吏豪强对羌人的歧视与迫害,是导致东汉后期持续数十年的汉羌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弃凉之议”在客观上反映了东汉后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面临着的诸多困难,在主观上则凸显了当时朝廷当权者与士大夫群体在夷夏问题上的进退失据。弃凉州抑或不弃凉州的历史结果或有所不同,但在充满歧视心态的夷夏观念影响之下,汉羌冲突本身是无从化解的。虽然汉羌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东汉胜出,在皇甫规、张奂、段颎等将领的指挥下,东汉王朝以极其暴烈的手段镇压了羌人起义。但是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安顺二代的羌祸简直把东汉开国以来的精力和元气都一齐消耗完了”[12]286。质言之,汉羌战争是将东汉推向最终覆亡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传统的夷夏观念则是汉羌冲突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