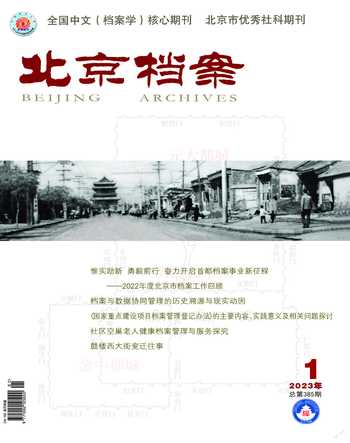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前前后后
2023-06-06刘芳
刘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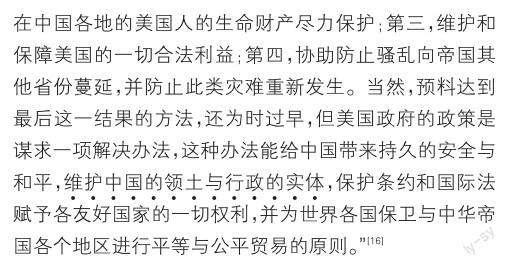

摘要:1900年7月3日,美国发布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首次提到中国的领土与主权问题,是建立在对中外现实局势综合考量基础上的。美国政府意图在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基础上,追逐所谓“机会均等”的商业利益,但美国亦存在趁庚子之乱在华攫取领土之极大可能性,故在照会发布前将文本中有关“完整”之论述改为“维护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实体”。该理念受中国当时的现实环境影响,又反转过来持续地影响着中国。历经庚子事变,它仍旧维持了在华列强的利益分配格局,一定程度牵制了列强趁乱浑水摸鱼的“逐利”行为,但美国也由此成长为一个新型帝国。
关键词:门户开放 主权完整 领土与行政的实体 东南互保
作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对华政策,“门户开放”政策历来备受中外研究者瞩目,成果显著。1899年9月和1900年7月,美国两次发布“门户开放”照会,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转折点。其中,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不仅重申“门户开放”,更首次提出中国的领土与主权问题,尤其受到各方重视,前辈学者们从文本内容及其长远意义分析,对第二次照会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还是“行政实体”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尚未有定论。本文围绕却不仅限于这些争论,充分比照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中美双方档案,揭示该照会出台的台前幕后及其现实影响,认为有必要结合照会发布前后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来重新考量该问题,并在该照会与当时中外局势的现实互动中加深对于这项政策的认识,以期对以往研究和观点有所补证。
一、揆情度势发布照会
1900年7月3日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出台,同6月18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戕密切相关。欧洲各国在获知德使遇害后,群情震动,纷纷有向清政府抗议与增兵侵华的动向。[1]7月1日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政府对于此时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尤其围绕是否要在中国攫取领土,进行了一番针锋相对的研讨与议论。其实早自1898年以来,美国驻华使领就曾多次向白宫提出,希望美国未来能获取一个中国口岸作为海军基地或加煤站。[2]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列强纷纷将八国联军出兵视为侵占中国的绝佳时机。此时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和司法部部长葛雷格(John W. Griggs)亦有此意,主张美国追随各国,相机在中国占据一个港口,但却遭到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的反对。在海约翰看来,时机不合适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始终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应采取这样的措施。他召见了前助理国务卿、杰出的国际律师摩尔(John Bassett Moore),摩尔指出“支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将与我们人民的感情相一致;正是帮助其他国家维持他们的独立和完整的原则使得门罗主义如此受欢迎”,因此他建议发布一份公告宣布美国的政策指导原则是维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并争取获得其他列强的支持。[3]摩尔的论断坚定了海约翰继续支持中国不被各国侵占的决心。故而庚子事变之后,美国虽然参加八国联军的武力侵华,但却不愿在军事上卷入过深,反而在外交方面频频发力,不仅率先答应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派兵进入东南各省的请求[4],而且在6月20日清廷颁布宣战上谕后仍坚持与东南各督抚实行“互保”[5],都是海约翰持续力排他议、主导美国对华行动的体现。
然而这时克林德遇害的消息传出,海约翰心情沉重、忧虑颇深,在当晚给儿子的信件中抱怨说他“一生都在经历战争和困难”[6]。能够让一位久经沧桑、富有经验的外交官无比痛苦的事件确实不一般,德使遇害极可能成为列强对华全面复仇战争的导火索,海约翰苦心经营的对华“门罗主义”眼看就要化为泡影。他深感致力于与东南各督抚的直接对话已远远不够,美国政府必须全面考虑将它此时的外交理念推广至所有“盟友”。因此为了防止各国趁机对华宣战,海约翰率先将美国不会袭击中国东南省份的决定通知了其他列强。[7]
列强的反应如何?英、法两国表示原则上同意美国的提议,但英国宣称它未来的行动建立在中国政府和列强的行动之上,[8]法国也拒绝给出任何可能会限制法国公使和海军将领自由行动的具體指示。[9]德国政府因为公使遇害震怒异常,但美、英、法等国的表态无疑对它是有力的钳制,最终迫使它同样接受了美国的提议,只是明确提出希望得到东南各督抚不支持北京政府的保证。[10]
其中,法国的立场与美国最为接近,法国政府也感到,尽管德国已经声明其目的同列强一致,还是必须趁此机会促成各国联合行动。[11]7月2日,法国给英、美、德、俄、意和奥匈各国发去一封照会,宣称“中国危机发生后,列强须一致同意如下目标:确保在华公使、公民的人身安全;维持中国的领土现状;以足够的保证避免当前的不幸事件再次发生”,而且最主要的是各国的在华军队不能单独行动,应该联合起来朝一个方向前进,同时法国还建议列强向各自指挥官征询进军北京所需的军队总数。[12]尽管各国都认同救援使馆和一致行动,但只有奥匈帝国完全赞同这个照会,其他列强的回复都只同意了法国提议的部分内容,而回避或忽视了那些会有问题的点。[13]比如英国是不愿在军队人数上受到牵制,俄国则是因为其中关于领土现状和避免进一步骚乱会有解释上的分歧。[14]
虽然法国试图联合各国达成统一目标的努力失败了,但这个照会毋庸置疑给了美国国务院启发:其一,确实有必要以一种明确清晰的方式向其他国家传达美国的对华政策,当下正是最佳时机;其二,为了防止俄国公开反对,可以不必像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那样逐个询问各国的意见,而以公开宣言的形式造成一种既定事实,列强自会因在华联合行动而受到约束。
与此同时,刘坤一等东南督抚的期待竟与此惊人的一致。1900年7月3日,刘坤一在联合张之洞致电驻美公使伍廷芳重申东南“互保”的同时,还派其英文秘书暗中拜访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John Goodnow)。该秘书携带有刘坤一的一个秘密任务,即向古纳表明刘坤一对英国意图借机侵占长江流域的担忧,以及他对美国一直不攫取领土的钦佩与信赖,刘坤一请求麦金莱总统像他去年领导“门户开放”协定谈判的时候一样,再次出面以其化解中国当下的危机。[15]可见当时不论是国际大环境,还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都为美国重申“门户开放”创造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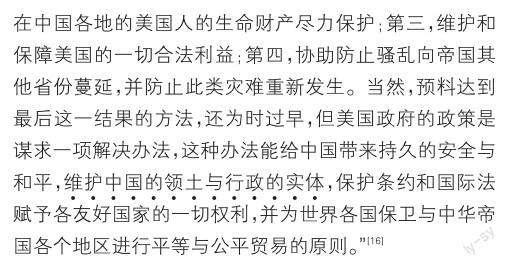
二、“主权完整”还是“行政实体”?
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文本在美国政府的多处政府文件中均可查阅,但由于翻译和研究视角等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围绕照会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1979年,创刊伊始的《世界历史》发表了复旦大学汪熙的论文《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文章称,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并在此前提下,要求美国贸易的机会均等;二是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17]汪文一出,即刻引发了学界热议和争论。随后有多篇文章对其中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张振鹍联名撰文,指出海约翰照会的原文明明白白写的是“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汪文作了两处改动:一是把“保持”改为“尊重”;二是把“行政完整”改为“主权的完整”,擅自改变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含义。[18]武汉大学的美国史研究者向荣也同样指出,海约翰的照会原文应是“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而“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是“门户开放”政策的补充。[19]北京大学罗荣渠特别点明,一些著作中称海约翰提出的这项原则包含了保持中国领土及主权完整的内容,“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错误”,因为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照会,都没有这样的字眼,第二次照会中使用的是“实体”(entity),而且是“行政实体”(administrative enti? ty),根本没有所谓“主权”的字眼,“这字里行间实在是大有文章”。[20]罗文与汪文遥相呼应,被后代中美关系学者共同视为学术思想解放的代表作。
这场争论体现了前辈学者围绕关键议题深入、细致的钻研与力求实事求是的探究精神。就该论题本身,两派学者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美国是否有提出“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反对者主要从两个角度驳斥汪文。一是由文本出发,考究美国照会原文,认为原文中根本没有谈中国的“主权完整”,相反只出现“行政完整”字样。丁名楠、张振鹍指出“,行政完整”无非是指不变更中国自有的一套行政体系和机构,形式上维持中国的政治独立,实际上保持帝国主义在华的半殖民地统治;而尊重中国的“主权的完整”,那就完全不同了。“自鸦片战争到1900年,中国的主权早已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的严重破坏,还有什么‘完整可言”?[21]因此,反对者的第二点理由即从中美交往的史实考察,时间后溯至“门户开放”提出后的半个世纪,列举其间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诸多实例,以证明美国在实际行动上也未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
论点论据相当完备,也未见汪熙再撰文反驳[22],争论暂告一段落。此后研究者每有涉及,或摘选,或混用,甚或如汪熙带头那样将“主权完整”和“行政实体”作为两种不同的译法一并列出[23],均说明分歧并未消弭。
当年虽因汪熙的示弱而暂且中止了论争,但反复重温反驳者之论,笔者深感仍存在两处较大疑点。其一,汪文的表述本就不是引用照会原文,在中文表述中,无添加双引号的概括往往只要不背离事情大意,尚无不可。其二,20世纪上半叶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史实能够说明美国在对华实践中的侵略性,但是否还存在一种客观行动与主观意愿背离的可能性,即门户开放政策本有如此初衷,但美国历届政府在实践中逐渐背离了政策出台时候的目标。因此,先不论结果如何,似乎双方理由仍不够充分。究竟是“主权完整”还是“行政实体”,不仅需要对英文原文仔细核对、准确翻译,更需要结合美国提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当时具体的对华政策与实践。
这样,一份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海约翰档案中的文件就成了问题突破的关键。这个文件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决定颁布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之后于1900年6月30日亲自起草的一份草案,其中海约翰明确提出了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内容。[24]这份草稿完成后,海约翰将其提前知会了陆军部长鲁特(Elihu Root)和海军部长朗(John Long)。7月3日,海约翰还专门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就是为了讨论照会文本。最终版本删除了所有会引起美国政府内部乃至列强之间分歧或误解的文句。其中,在涉及中国的领土问题时,就以“实体”(entity)取代了“完整性”(integrity)。这项修改提议来自海军部长朗,因为他受到了来自海军部中在中国夺取一个海军基地呼声的影响,这个呼声由来已久并极有可能实现,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 Conger)、镇江领事福勒(John Fowler)等在华外交官频频发声,就连海军部设备局长布拉福德(Bradford)都是其热烈拥护者。[25]因此朗在阅读草案文稿后当即提出,必须将“完整性”改成“实体”,因为获取一个港口可能会毁坏中国的“整体性”或“完整性”,但它的“实体”或存在不会被改变。这样才能为美国随时可能做出攫取中国领土的行径留有余地。海约翰在文本通过后以电话形式向当时身处俄亥俄州的总统麦金莱做了汇報。修改同样是为了贯彻总统的指示,不要包含任何类似的可能会在未来自我否定的许诺。在麦金莱的批准下,海约翰发布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倡导“维护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实体”。[26]
至此真相得到澄清,美国政府在照会颁布前主动将“完整性”改为“实体”,可见不仅在中文,在英文的表述中亦容易由“完整”的语境引发误会;且美国政府此时并未提及“主权”。因此,结合照会原文及其颁布前后美国之政治考量,本文认为,将“preserve Chinese territorial and administrative entity”翻译为“维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实体”应该更为准确。而且尤须注意的是,英文文本中“领土”一词使用的是形容词形式,而非名词形式,同“行政”一样乃“实体”的限定语,意在表明维护的亦是“领土”之“实体”,并非“领土”之“完整”,因此在对照会文本进行中文表述时实在不应该笼统称作“领土完整”与“行政实体”,而应是“领土实体”与“行政实体”。此种表述深刻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高层普遍相信,趁庚子变乱之机美国存在获取中国领土的极大可能性,故特有此更改。
但是否应以照会中的这句话来完全否认“门户开放”政策有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内容,光靠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文本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政策涉及的范围远比照会来得宽泛,还须综合考查同时期美国政府对内、对外的所有论述。况且,海约翰本于照会草稿中使用了“领土完整”字样,因海军部长反对而撤回,是否说明海约翰的构想中本是包含完整性的含义?
事实上,在同时期的美政府档案中,还能发现许多关于“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表述。虽然在柔克义(W. W. Rockhill)起草、海约翰审定的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27]中,尚未提及如何对待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但在获得各国赞同后,海约翰显然已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1900年3月22日他在给康格公使的训令中,就要求康格将“门户开放”政策知会清政府的同时,申明美国政府已取得列强保证在其势力范围自由贸易和保持中国的主权(the mainte? nance therein of Chinas rights of sovereignty),以及不干涉中国的完整性(not to interfere with the integrity of the Chinese Empire)。[28]这成为是年7月酝酿第二次照会时添入中国领土完整内容的重要基础。此后同年10月19日,海约翰在给法国驻美公使的备忘录中亦言及,列强在他们最初的宣言中称它们将维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性(preserve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the adminis? trative entirety of China)。[29]1901年3月,针对俄占东三省问题,海约翰电致在北京谈判的全权代表柔克义,再次提到所有列强均已同意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the preserva? tion of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China)。[30]由此可知,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始终存在于美国政府的表述中,并非学者杜撰。而且在中美的具体交涉中,美国亦曾多次公开提出对中国领土完整的维护,并非隐匿不宣。
更确切地说,柔克义与海约翰制定并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初衷和愿望始终包括维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总体而言,维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仍是“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目标之一,根本在为其维护贸易平等而铺路。只是在致列强的公开照会中,为避免与自身未来的行动相抵牾,美国政府在文字上做了一个转换。[31]并且在实际操作中,美国自身同样不愿主动放弃攫取领土。保持“实体”可以做到,但保持“领土与主权完整”,美国在此后五十年始终没有实现。
三、对中外政局的影响
美国政府的7月3日照会本身虽未出现“门户开放”字样,但由于其重申了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要求与中国“进行平等与公平贸易的原则”,被视作“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又由于这次明确提出“维护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实体”,即只有首先“保全”中国,才能谈“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利益均沾”,故被视为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发展。
无须赘言前辈学者已反复述及的7月3日“门户开放”照会成为“后来一切美國政策的根本路线”,[32]此处重点关注的是照会本身针对中国问题的具体内容,以及照会发布后对现实中美关系的直接影响。照会发布乃中外政局作用的直接结果,其文本的大部分内容,除最后关于维护中国实体存在的政策宣言外,都是针对当时中国具体政局的,尤其与“东南互保”密切相关,而照会发布后的结果,更是直接影响了中国与国际局势的走向。
照会中关于“北京事实上已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说法,首先源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对外陈述,从“大沽开炮非奉旨”到“所谓矫诏也”,东南各督抚反复对外开脱称朝廷由于受到端王等人的胁迫,才会做出与列强开战的迷幻行径;而这个解释恰好被美国政府利用,因为要“保全”中国,就不能有两个交涉对象,北京的“无政府状态”,正可让“各省地方当局”成为合法的交涉对象,而要防止中国被瓜分,就必须要支持地方督抚的“互保”政策。因此,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选择在7月3日这个时间节点发布,根本是为现实政治考量,目的在于支持“东南互保”,进而反对各国借口克林德之死向中国全面宣战,甚至瓜分中国。“东南互保”由议约到换文,英、日、德等各国与东南督抚均有过程度不一之配合,唯独美国以政策宣言形式昭告世人,拉拢列强造成事实上的中外“互保”状态。虽然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从未征求过中方意见,单方面立足于本国利益,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对中国地方当局权力以及中外“互保”谈判的承认,客观上稳固了东南各督抚的忐忑之心,限制了其他列强的轻举妄动,法理上为这种奇特的二元外交、战时和平给予了支持。“东南互保”之所以确立,在某种意义上是获益于这次“门户开放”照会。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海约翰颇引以为傲:“要做的唯一之事就是将骚乱尽可能控制在中国北方,这点我们似乎已经做了。所有的国家都赞同我在(中国)中部与南部的办法。”[33]
为了避免矛盾和推诿,海约翰并未要求各国复照。其实除了英国,也没有国家回复。该照会就是一个美国单边的政策布告。但限于当时独特的八国联盟机制,没有国家选择公开反对,就连德皇也附和声明并无瓜分中国之意。[34]因为此时列强深知,“瓜分”一旦开启,必定造成中国局势混乱,这样一来自己的对手极有可能趁机攫取更多的利益,没有哪个国家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35]他们因此被描述为“赞同(海约翰的)方法”。
美国7月3日照会取得了国际层面的初步成功,此后,随着“东南互保”的顺利推进,又进一步扩大了它在中国北方的影响。当时的驻美公使伍廷芳大受照会鼓舞,他主动向海约翰表示,愿意帮助美国联系被围困在北京的驻华公使康格。几天之后,康格的电报几经辗转由伍廷芳递送到海约翰手中,成为列强驻京使馆被围后外国政府首个直接收到的公使信息。[36]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与北上的李鸿章由此形成默契,“目前办法必须由美入手”[37],他们一面通过各地美国驻华领事吁请美国政府充当中外之间的调停者(Mediator)[38],一面接连向清廷上奏“排难解纷,必须由美入手”[39]。美国的和缓、督抚的恳求稍稍打动了清廷中枢,才有了随后总理衙门开启对话向外国使馆送去瓜果[40],并按照美日两国的建议同公使们商讨将他们护送至天津。[41]然而由于清政府突然中断各国使臣与本国政府的密码电报,该提议没能实现。[42]待到清廷重开公使通讯,八国联军已逼近北京,美国试图再度居中调停。在伍廷芳的牵线下,奉命北上的李鸿章与此时代理政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地(Alvey A.Adee)谋划了一个由清军护送公使至通州、联军不进入北京的方案。[43]但他们高估了命令传送到美国指挥官的速度。直到联军攻陷北京的次日,沙飞(Adna Chaffee)将军才收到美国政府发来的与中国协作的指示。
虽然美国在中国北方的两度调停均以失败告终,但可以看出,由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定下的对华政策整体上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美国政府的整体对华目标基本实现。它在中国南部省份的成功改变了一大批清朝实力派官员的对美态度,从而在中美合力的作用下推动了北方局势向符合照会初衷的目标发展,美国宣言事实上在列强相互牵制的格局下,成为造成八国联军即便攻陷北京也无法“瓜分”中国这一历史事实的重要力量。但由于美国政府当时在华政治与军事实力仍略逊于英、德、俄、日等国,以致在中美联动中,以东南督抚为首的清朝官员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美国行动的软弱与迟缓,根本达不到他们心中的预期。故而不论后世史学家如何神话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所谓中美“特殊关系”,至少在该政策发布的开端,不应对此过高评价。
四、结论
“门户开放”政策与中国的时政密切关联。1900年初海约翰宣布他从列强那里收到了关于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保证时,恰值义和团运动爆发。由于门户开放原则精心构造的在华利益格局是建立在列强之间微妙的共识基础上的,实际十分脆弱,中国北方的动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有可能将其摧毁,故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对“门户开放”政策必然造成巨大的冲击,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机遇,就是它给海约翰提供了再次吸引国际社会关注、获得支持的机会。美国政府不愿过度卷入中国的军事冒险,反而积极调停列强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参与避免动乱蔓延到长江流域的谈判,支持东南督抚达成中外协议以阻挡中国被“瓜分”。
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绝非对第一次的简单重复,美国政府选定这一时间节点重申门户开放精神,是建立在对中国的现实局势以及列强的相互状况综合考量的基础上的。既不可望文生义去理解照会文本,更不能脱离照会出台的具体情境来分析它的含义。只有将文本内容、前后语境、现实因素、长远效应等作一整体考察,才能做出较为接近历史事实的判断。
故而本研究得出“门户开放”有关中国领土与主权的论述实际存在三重意蕴的结论。即我们在论及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以及美国公开宣言时,表述为加引号的“维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实体”显然是更符合文本以及照会书写者的当时意图。而当论及“门户开放”政策的整体目标时,不加引号的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表述似乎更能全面地反映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内在全局观与长远考虑。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内部的“门户开放”继承者与执行者实际早已背离了发布者的初衷,深刻反映了美国东亚政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永恒矛盾。而作为后见之明,是决不可将后续成效与发布初衷混为一谈的。
以上讨论均聚焦于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发布前后的历史语境及国际国内的多方互动,以期能为“主權完整”或“行政实体”提供一更贴合的解释。对该照会乃至整个“门户开放”政策意义之讨论,亦更侧重于照会发布的当下,而非久被论及的长远影响。该策于发布当时受中国的现实环境影响,又反转过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00年下半年海约翰写道:“看起来门户开放终于有一些机会了”。[44]它不仅让在华列强的利益分配格局在历经庚子事变后仍旧得以维持,而且一定程度牵制了各列强趁乱浑水摸鱼的“逐利”行为。但它所宣扬的“机会均等”“保全中国”的理念根本是为美国以贸易扩张为主的海外扩张道路背书,美国虽与欧洲老牌殖民帝国策略不同,但终究变成了一个不同形态的新型帝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晚清美国驻华领事制度研究”(19YJC770027)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清末中美交涉史料整理与研究”(2022NTSS2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柏林吕镜宇星使致南洋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处五日[M]//盛宣怀.愚斋存稿(卷36电报十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857.
[2][25]R.B. Bradford.Coaling Stations for the Navy[J]. Forum(February 1899, 26):732-747.
[3]John Bassett Moores Memorandum of Conversa? tion with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Hay(July 1,1900).Moore Papers.Library of U.S. Congress.
[4]Wu Ting- fang to Hay(June 23,1900) [Z] //Notes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De? partment of State(Jan.1,1898-Dec.31).M98,R4.National Ar? 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5]张之洞收江宁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M]//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十六册).河南:大象出版社.2014:9.
[6]Hay to“My Dear Boy”(July 1,1900) [Z]//John Hay Papers.Library of U.S. Congress.
[7]Telegram Hay to Goodnow(July 1,1900) [Z]// Mckinley Papers.Library of U.S. Congress.
[8]Telegram Joseph H. Choate to Hay(received June 23,1900)[M]//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344.
[9]Telegram Horace Porter to Hay(received June 27, 1900) [M]//Diplomatic Despatches: France.RG59,Vol.118.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10]Andrew Thomas.The Diplomacy of the Boxer Uprising[D].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h.D.thesis(1971).p.86.
[11]Note du Ministre(June 23,1900,No.198) [M]//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ais(Series 1,Vol.16):300.
[12]Mr.Thiebaut to Mr.Hay(July 2,1900) [M]//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 317-318.
[13]Delcasséto Montebello(July 5,1900,No.212) [M]//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ais(Series 1,Vol.16):323-325.
[14]Telegram Marquis de Montebello to Delcassé(July 8,1900,No.217) [M]//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ais(Series 1,Vol.16):330.
[15]Goodnow to Hay(July 8,1900) [Z]//Despatches from U.S. Consuls in Shanghai, China, July 5,1899-July 31, 1900.M112,R46.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16]Circular Note of July 3,1900,to the Powers Coop? erating in China; sent to the U.S. Embassies in Berlin, Paris, London, Rome, and St.Petersburg and to the missions in Vi? enna, Brussels, Madrid, Tokyo, the Hague, and Lisbon.Pa? 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1(app.I):12.文本翻譯参照《国务卿海致在华合作各国的通知照会》,1900年7月3日,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齐鲁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仅将“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改为“维护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实体”。
[17]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J].世界历史.1979(3).
[18][21]丁名楠,张振鹍.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J].近代史研究.1979(2).
[19]向荣.论“门户开放”政策[J].世界历史.1980(5).
[20]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J].历史研究.1980(3)
[22]汪熙仅在1984年发表的《我国三十五年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一文中提到,“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历来就有‘是敌人一切都要否定,是朋友一切都肯定的绝对化的倾向。其实历史是复杂的,友好与对抗的关系,在现实的历史中是相互联结、相互交织、相互破坏的。”似乎是对此事的一个侧面回应。参见汪熙,王邦宪:《我国三十五年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
[23]汪熙,鹿锡俊.“门户开放”政策是怎么回事?[M]//上海古籍出版社.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08.
[24]Hay to His Son(July 1,1900) [Z]//John Hay Pa? pers.Library of U.S. Congress.
[26]Rush Telegram from McKinley to Hay(July 3, 1900).McKinley Papers.Library of U.S. Congress.并参见Andrew Thomas.The Diplomacy of the Boxer Uprising[D].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h.D.thesis(1971).p.114.
[27]1898年9月,海约翰由驻英大使任上回国担任国务卿,因他从未去过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解,就将时任希腊公使的好友柔克义召回华盛顿担任远东事务顾问,让其享有白宫的“无限信任”。柔克义即于1899年8月28日草拟了关于美国对外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的备忘录,海约翰只对备忘录稍作修改,形成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最终版本。参见[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36页。
[28]Mr. Hay to Mr. Conger(March 22,No.246)[M]//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111.
[29]Rockhill to Hay(December 10,1900,No.24) [Z]// Despatches from U.S. Ministers to China,October 1-De? cember 15,1900.M92,R109.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 ed States.
[30]Hay to Rockhill (Telegram,March 2,1901) [Z]// Despatches from U.S. Ministers to China,February 5- March 29,1901.M92,R111.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 ed States.
[31]因此,當论及“门户开放”政策的整体目标时,维护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不加引号)的表述实际更全面;但在具体提及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文本以及美国公开宣言时,还应以“维护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实体”(加引号)为准。
[32]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M]//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55.
[33]Hay to Henry Adams(July 8,1900) [Z]//John Hay Papers. Library of U.S. Congress.
[34]无意瓜分[N].申报,1900年7月17日(第9788号).
[35]美国驻英国公使乔特(Choate)也承认,这项政策实际上跟英国一直以来的政策一致。参见Choate to Salisbury,July 5,1900,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 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eries III,the Sino-Japa? 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Vol.5, Delaware:Scholarly Resourse Inc.1981,p.96.
[36]Mr.Conger to Mr.Hay(July 16,1900) [M]//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156.
[37]南洋刘来电并致盛京堂鄂督东抚(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M]//李鸿章全集(第27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47.
[38]Viceroy of Nankin to Consul-General Goodnow(July 21,1900) [Z]//Despatches from U.S. Consuls in Shanghai, China, July 5,1899- July 31,1900.M112,R46.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39]袁世凯奏为代呈伍廷芳电送美国总统覆书事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715.
[40]致各国使臣照会·为请各国大臣暂寓总署覆文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档号:1-01-12-026-0030,军机处电寄谕旨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1]致各国使臣信函·为请各国大臣暂避天津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档号:1-01-12-026-0029,军机处电寄谕旨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2]庆亲王奕劻致美使启·为将原电奉缴致歉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档号:1-01-12-026-0031,军机处电寄谕旨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3]Memorandum(August 16,1900) [Z]//Notes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Depart? ment of State(Jan.1,1898-Dec.31,1901).M98,R4,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44]Thomas J. McCormick.China Market: 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1893-1901[M].Chicago: Quad? rangle Books.1967:175.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