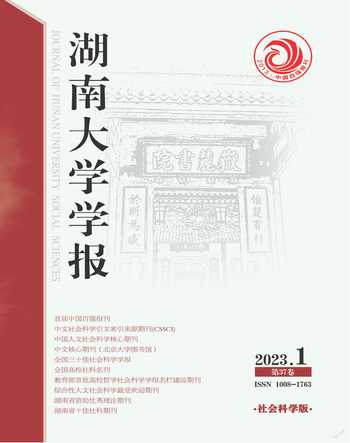辩说与治辨:论荀子之“辩”
2023-06-02孟凯
孟凯
[摘 要] “辩”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重要环节,具有沟通“名”与“事”的作用,然荀子之“辩”无意于构建逻辑体系,展现为“辩说”与“治辨”的统一,是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为目的,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与现实精神。为了使“辩”更为有序有效,“仁”“礼”“义”等儒家价值规范就成为“辩”必须坚持的原则。荀子之“辩”还呈现为“君子必辩”与“小人勿辩”两个层面,在这种“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荀子希望通过“辩”诸子之学为“邪说”,儒家思想为正道,从而说服世人摒弃诸子遵从儒家规范,但政治权力作为决定因素的参与,又使荀子之“辩”蒙上独断论色彩。
[关键词] 荀子;辩说;勿辩;礼
[中图分类号] B2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3)01—0027—07
Argu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n XunZis Thought of Bian
MENG Kai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Bian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XunZis thought of name rectification, 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communicating name and matter. XunZis Bian is not to build a logical system, but to safeguard the Confucian ethics and political ideals. It has a very strong sense of relevance and realistic spirit, which shows the unity of argu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make argument more orderly and effective, Confucian value norms such as benevolence, propriety and righteousness have become the principles that argument must adhere to. XunZis Bian also presents two aspects: a gentleman must argue and a villain should not argue. In this dilemma between arguement and no-arguement, XunZi hopes to persuade the world to abandon the Confucian norms by arguing the learning of various scholars as heresy and Confucianism as the right way,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becomes the decisive factor, which makes XunZis Bian become dogmatic.
Key words: XunZi; argument; no-argument; propriety
名辯是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话题之一,其以“名”为中心,以名实、形(刑)名关系等为论题,以“辩”为论证方式,进而形成了名辩思潮,然秦汉以降则呈现出式微之势终成绝学[1]。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名辩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名辩或名学也被看作是中国逻辑学的古代形态[2],这一研究范式对传统名辩研究的影响极大。但学界对于这种“名辩逻辑化”的研究并不完全赞同,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诠释名辩思潮,在名辩研究转型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卓有新见的学者,如曹峰主张名辩研究应“回到思想史”[3];晋荣东认为与其把“名辩”看作一门学科,不如理解为“包含多重理论内涵的思想史现象而称其为‘名辩话语或‘名辩”[4];苟东锋提出建立“新名学”的构想[5]。这一转向也影响着对荀子的评价,荀子名辩思想研究也日趋多元[6],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他在逻辑学上没有特别建树,只是通过名辩来阐释其伦理道德与政治思想。然而在名辩思潮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对“名”的重视程度要远远大于“辩”。从目前有关荀子名辩研究的成果来看,对于“名”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关于“辩”的讨论则较少,实际上在荀子的名辩思想中,“辩”与“名”同样重要,他对于“辩”的讨论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一
一般而言,儒家较为看重叙事意义上的“言”“说”。《左传》即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7]790之说。在孔子正名思想中,“言”也是重要一环,《论语》记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8]141-142
在孔子“名—言—事”的正名思想中,“言”起到沟通“名”与“事”的作用[9]。孔门“十哲”四科分类中,“言语”占有一席之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8]123说明孔子很注重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但对于论争型的“辩”,儒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尽管孔子盛赞子贡与宰我的语言才能,但他最欣赏的学生却是德行完备而不善言辞的颜回。孟子有“好辩”之名,却更强调“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8]271。与孔孟对于“辩”的态度不同,荀子极为看重“辩”[10]447,不仅提出“君子必辩”与“辨说恶用”相统一的主张,还赋予“辩”以捍卫儒家正道与拒斥异端的重要功用。
“辩”在《荀子》中有多种表达,如《非相》篇之“谈说”“说”“言”,《正论》篇之“议”“言议”,《正名》篇之“辨说”,《宥坐》篇之“言谈”等,相关讨论即构成荀子的辩学体系,本文所谓“辩学”类似于崔清田所说“以谈说与辩论为对象的学问”[11],但讨论范围更加广泛,因为荀子之“辩”的伦理与政治意味更为浓厚。所以探讨荀子之“辩”,首先应该关注两个形似而又不同的概念:“辩”与“辨”。这两个词在《荀子》中通常被认为可以互换,并未引起学者足够重视,相关的训诂注解也相当简略。就其字形字源来看,认为二者可以互换,或许在训诂方面尚且说得通,但是在义理方面却有极大的隔阂。“辩”字在《荀子》首篇就已出现,“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12]17“辩”指“能言善辩”。“辨”字首次出现在《修身》篇,“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12]34“辨”作“分辨”解非常清楚,因此诸家皆无特别解释。由此可以看出,“辩”与“辨”在《荀子》中的差异还是较为明确的,若仅仅把二者看作可以通用,无疑是对文本的漠视,荀子辩学正体现在“辩”与“辨”的交互关系中。具体而言,“辩”一般理解为“辩论”“争辩”,即以语言为主要的表现方式,故而“辩”字从“言”。在这层意义上,“辩”与“言”“说”也即可以合称为“辩说”,荀子经常这么表达:
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12]39-40
其辩说足以解烦、其知虑足以决疑、其齐断足以距难,不还秩、不反君,然而应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12]244-245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荀子的讨论中还有“辨说”一词:
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12]422
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12]424
以上似乎正说明“辩”与“辨”完全相同而无差别,事实上,“辨说”仅在《正名》篇中出现过,且“辨说”的提法也只是对命、期、说、辨的简称,与“辩说”的所指不尽相同。从字形上看,与“辩”的“言”“说”意义不同,“辨”字中为“刀”,主要与“分”相关,其意义在于“划界”“分类”。郭沫若在诠释荀子之“分”时,就认为“分”即“辨”,“是已经具有比较复杂的内含的。它不仅限于分功,它已经是由分功而分职而定分。”[13]174“辨”在《说文解字》中也被解为“治”[14]309,而荀子也常把“辨”与“治”并称,是为“治辨”:
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12]61
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12]211
君者,治辨之主也。[12]374
由“辨”与“治”的合称可见,“辨”与“辩”相比具有更强的实践意味,主要指向伦理与政治。牟宗三在解释荀子“礼者,治辨之极也”[12]281时,指出治辨之极“即类同别异之极则,辨不作思辨解”[15]168。“辨”不仅不能作“思辨”解,也不能作“辩说”解,所以荀子正名“四段论”之“命”“期”“说”“辨”,最后只能终于“辨”(治辨)而非“辩”(辩说),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说”就已经包含了“论说”“辩说”的意义,没有理由还要再强调“辩”。只有明确“辨”的这层含义,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荀子把人的根本特征看作是“辨”而非“辩”,“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并进一步把“辨”引向“礼”“圣王”所涉及的伦理政治之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12]79。如是看“辨”与“辩”的差别非常明显,是以牟宗三认为荀子所谓“辨”应该理解为“分”“义”[15]181。
综上可见,若把荀子之“辩”与“辨”不加分疏,简单看作没有区别可以通用,显然并不合适。即使在荀子思想中,二者都含有“区别”“分别”的意义,也都以“礼义”“王制”等儒家规范为标准,以驳乱世求治世为追求,笼统地认为二者可以通用未尝不可,但却不能有意忽略其差异。广义上可以说,荀子之“辩”蕴含着“辩说”与“治辨”两重含义,后者是前者之目的,由此而言荀子辩学只是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的手段。
二
“乱”是春秋战国显著的时代特征。孔子称春秋“天下无道”[8]171,孟子直言“春秋無义战”[8]364。战国之“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言道:“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册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16]522-523这种乱局被荀子称为“诸侯异政,百家异说”[12]386,“诸侯异政”突显了群雄争霸、礼崩乐坏的社会政治之乱,“百家异说”揭示了百家争鸣、学无宗主的学术思想之乱。“乱”的另一重要表现用《左传》的话说就是“贵贱无序”[7]1190,而“止乱”与“秩序”重建也就成为先秦诸子的共同理想。在探寻的过程中,名实关系则是诸子共同关注的主题之一,在诸子看来,“天下无道”的主要表现就是名实不符,而要恢复秩序必须厘清名实关系。对此先秦诸子有各自的名学主张,荀子正名也是这一目的。一如诸子对于“名”的态度,诸子对于“辩”的意见也不统一,荀子则鲜明地提出“君子必辩”的主张,他说:
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12]83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12]87
荀子试图通过“君子必辩”的方式以儒家规范剖析诸子“异说”为“邪说”,百家“异政”并非“王道”。尽管他把“辩”看作君子必备的德性,但作为儒者,他对“辩”又有谨慎的警惕心理,尽力避免“辩”而不至流于“诡辩”,从他对惠施、邓析为代表的名家的批判可见一斑。荀子评论他们虽然言之成理,但“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12]93-94。也就是说名家的问题主要在于否定“先王”“礼义”“纲纪”等规范,而不在于其辩说有无逻辑。我们观察荀子《非十二子》篇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诸子进行批评的同时基本仍承认其主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反而对同属于儒家系统的子思、孟子没有如此评论,这主要在于荀子认为前十子的主张虽有合理性却与儒家学说不符,而子思、孟子则是学派内部观念的对立。
同时荀子还特别强调“辩”的适度原则,他认为过度就会走向“遍辩人之所辩”[12]122的诡辩境地。但若“不辩”则会流于怯懦,最终也无法捍卫儒家正道,他对“子夏之儒”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点。“子夏之儒”每天只知“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12]105,就如同《周易》所说的“括囊,无咎无誉”[17]45俨然扎起口的袋子一样,什么也不说,的确没有过错但也乏善可陈,他们这类儒者只能算是“腐儒”[12]84“俗儒”[12]138。可见荀子之“辩”的提出既有批判诸子的需要,也有身为儒家的反思,所以他指出“辩”首先要以儒家至高原则“仁”为核心:
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吶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12]87
以“仁”为内涵的“辩”,荀子认为“重于金石珠玉”“美于黼黻文章”“乐于钟鼓琴瑟”[12]83-84。说明合乎“仁”之“辩”具有超越物质财富的意义。以此观之,我们可以说荀子之“辩”既有现实的“功利”诉求,也有理想的“道德”情怀[18]114。基于“道德”与“功利”的双重考虑,荀子把“辩”区分为不同类型:
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12]88-89
从荀子对“辩”之类型的区分,可以看出他对“辩”的功利性的要求非常突出,荀子所说“小人之辩”之所以流于“小人”就是因为“多诈而无功”。从荀子的诸子批判及其后学建构的“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看,皆是“辩”之功利价值的直接体现,孔子判定少正卯罪行之一就是“言伪而辩”: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12]521
借孔子之口指出少正卯之“言伪而辩”具有“饰邪营众”的恶劣影响,而荀子给“恶”的定义正是“偏险悖乱”[12]439。由此自然可以推导出少正卯之“辩”就属于“辞辩而无统”“多诈而无功”的“小人之辩”,无益于“正理平治”(善)的实现。孔子诛少正卯是不是历史事实,对于荀子及其后学而言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他们对于“奸言”“邪说”坚决反對的立场。是以照此逻辑发展,韩非子、李斯见用于秦,“焚书坑儒”必然顺理成章地发生。然而荀子仍是长于思辨的思想家,他还是希望尽量保持公允的理性态度。
因此荀子要求论辩者首先要端正心态,尽量做到“辩而不争”[12]40,面对那些“有争气”之人时,应采取“勿与辩”[12]17的态度。如此就涉及如何“辩”的问题,荀子称之为“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12]86这里的“谈说之术”更多表现为态度而缺少操作方法,荀子对于“辩”所提出的更为具体的原则是“言有坛宇”:
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道德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庭也。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12]146-147
关于“坛宇”,王念孙解释说:“坛,堂基也。宇,屋边也。言有坛宇,犹曰‘言有界域,即下文所谓‘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12]146“言有坛宇”突出了“辩”需要遵守的逻辑原则(界域),“安存”“为士”“后王”则突出“辩”应有的“礼义”原则。与“言有坛宇”相对者即“奸言”“邪说”,在荀子看来,“奸”“邪”的基本特征就是“无坛宇”,即“失中”:
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12]124
荀子所谓“中”就是“礼义”,“曷谓中?曰:礼义是也。”[12]122所以“失中”等于不合乎“礼义”规范,可见“辩”的标准就是“礼义”。“中”在儒家论域里也有中庸、中道的意思,“失中”也意味着过或不及。就“辩”而言,多意味着“过”,过度之“辩”在荀子看来就是“遍辩人之所不能辩”的“玩琦辞”,名家无疑是典型代表,所以荀子对名家的批判往往集中在这方面。有鉴于此,荀子就提出了“辩而不辞”[12]40的主张,“不辞”原则要求“辩”应以实际功用为指向,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8]169,表达清楚想要表达的内容即可,不需要玩弄华丽辞藻,更不需要以屈人为目的。正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8]48,“巧言”过犹不及,于“仁”无益,孔子反对过度“巧言”,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荀子则不然,他直指不合乎“中”的即“奸说”,需要“圣王”禁绝:
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12]98
与“言有坛宇”相关的另一种表达即是“言必当理”,“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12]124合乎“理”的“辩说”是“中说”,合乎“理”的事是“中事”,而“中说”“中事”有益于“理”: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12]124
由是言之,透过“中”,荀子之“理”与“礼”基本相等,并且都有极强的实践意味。在《荀子》文本中,“理”多与“治”相关,据考南宋浙北翻刻熙宁监本《荀子》,“理”即多作“治”[19]。正如前文提到的,“辨”(辩)训为“治”,荀子之“辨”(辩)“理”“礼”都蕴含着实践层面上的“治”的意味,因此唐君毅说:“荀子之言理,复有物理之概念。”以至认为荀子之“理”“属于人之纯知之判断推理方面,而不关连于道德之意志行为”[20]9-10,显然忽略了“理”之于“治”的含义。
与以“理”“中”为“辩”的原则相对,“口不出恶言”即构成了荀子论“辩”的又一原则,他说:
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12]381
“口不出恶言”是对“言必当理”原则的强化,也更突出“辩”以“善”为目的,而且荀子把“言”与“声”“色”并举,也有以此追求“美”的意味。但是“口不出恶言”并不是没有原则的“乡愿”,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荀子又提出了“不傲”“不隐”“不瞽”加以限定:
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12]17
荀子“不傲”“不隐”“不瞽”的原则,也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孔子曾说: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8]163
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8]172
孔子所谓“躁”即荀子的“傲”,孔荀“不傲”针对不当言而言的行为,“不隐”针对当言而不言的行为,“不瞽”强调说话时机的把握。这些看似简单的处世智慧,都不易做到,所以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不当之“言”。“不傲”“不隐”“不瞽”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公心”:
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12]424-425
“公心”与“私心”相对,“私心”的一种表现就是“问楛”,所谓“楛”,杨倞解释说:“楛与苦同,恶也。问楛,谓所问非礼义也。凡器物坚好者谓之功,滥恶者谓之楛。”[12]17“问楛”就意味着出于“私心”谋“私利”的恶行,荀子以“公心”为“辩”的原则包含了对“私心”的拒斥,也蕴含了以“公心”维护群体价值的意义。群体中伦理政治的意义尤为突出,儒家也更为关注它们,是以荀子之“辩”也必然指向这两个层面。
三
荀子之前也有学者冀望通过“正名实而化天下”[21]8,不过在荀子看来,诸子的尝试都归于失败,其思想主张也没有推行于世的可能,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思想都不具备可行性。“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12]426也就是说思想应具备指导人之行为的可能,落于现实之中就要“易知”“易安”“易立”。所以荀子也以此批评不易知不易行的思想流派,并由此推出他们是不可知不可行,最后说明他们的理论不成立。荀子认为诸子之说不仅不易行,甚至与“盗贼”同列,盗贼只是“盗货”,诸子却“盗名”,“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12]52。尽管荀子不满盗名者,但是他仍渴望通过正当手段博得“盛名”[18]128。只有圣人、士君子获得与之相应的“名位”,社会才能得到更为有效的治理,故而在倡导自己观点的同时,如何取得对诸子之学的优势地位,也就成为荀子必须考虑的问题。
说服统治者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是先秦诸子普遍采取的方式,能否获得上层的全力配合是诸家学说得以施行的根本。所以荀子之“辩”中天然地包含着“说服”的意味,能否让他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的观点,是区分“君子之辩”与“小人之辩”的重要标准,荀子说:“辩而不说者,争也”,“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12]54-55。战国时代能言善辩之士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说服工作,都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被执政者采纳,并推行自己的主张。因此说服就展现为“以理服人”的过程,如何向他人正确地传达自己的意见至关重要。与“以理服人”的过程相比,依靠权力、暴力实现说服目的,则展现为“以力服人”。荀子希望尽可能地“以理服人”,但也不完全排斥使用“力”,他同样赞成通过“圣王之诛”等暴力手段达到说服目的:
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12]108-109
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12]278
“孔子诛少正卯”的意义也在于此,其目的就是高效重建良好秩序。而荀子把“礼”看作良好秩序的象征,在他看来,秩序的建立与先王之道的实现,构成相互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展现为以“礼”而行与“礼制”的实现。[22]251这一过程也是荀子“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双重目标的现实化,其中“上”“下”的区分,正显示了“辨”(辩)以儒家规范的实现为指向,以实现“贵贱有序”为目的[23]48。荀子把这一过程的实现称为“王业”,而“辨”正是其开端之一,“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12]422。先秦时期可以承担王道大业者只能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潜在的士、君子”[4],绝非普通民众。所以认为荀子辩说首先并非追求真理的手段,则不无道理;但认为其辩说纯粹是说服民众、统驭民众的手段,就把荀子“辩”的对象搞错了。因为,荀子之“辩”还以“道”为指向,“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12]423“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24]14,在诸子思想中的表现各不相同,而荀子之道即治道,“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12]122由于荀子更多在治道意义上理解“道”,而非把“道”看作超名言领域的存在,是以其“辩”自然以“守道以禁非道”为宗旨。“禁非道”也就使得“不言”“止辩”成为荀子“辩”的一体两面,也就是说荀子之“辩”呈现出言与不言、辩与不辩的辩证统一。在荀子看来,礼义、圣王之道属于不得不言、不得不辩的范畴,但是有时“不言”(默)却也非常必要,这就是荀子所说:
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12]97
“默”正表现了荀子“无辩”“止辩”的倾向,他说:“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12]422“辨说恶用”就意味着“不言”,什么是不当言的?荀子以为“疑”“未问”[12]509都不当言。而且在荀子看来,“不言”也是天地大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12]46。君子在具备了“必辩”品格的同时,也应该具备“不言”的德性,荀子的“不言”主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子的“不言”“不辩”以及庄子“无辩”“辩无胜”的思想。但是荀子与他们仍有很大的区别,老庄的“不言”思想以其“无名论”为基础,更多表现了他们对语言的疏离以及不信任。但是荀子的“不言”思想则是以正名为前提,他不仅反对“无名”,而且其“不言”也只是不言不当之言,以及不言于不当言之人。对于应该说的内容,以及具备辩说资格的人,荀子仍极力主张“君子必辩”。“言”与“不言”的关系,在荀子看来还表现为“多言”与“少言”,“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12]97。可以看出,荀子又把“类”“法”看作是衡量“言”(辩)的标准,而“礼”又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12]12。故而荀子之“辩”与“不辩”“少辩”,皆以“礼”为根据,所以面对“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12]31。也就是说荀子认为不需要“辩”者无非两类:一是“非礼”之属,如诸子学说;二是无关乎礼者,如坚白、同异等名家辩题。但是这些对于一般人而言很难分辨,为此荀子又引入了“师”的角色:
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12]449
荀子也把“师”“法”并称为“师法”,“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畏,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12]142-143。也即是说若人无“师法”根本无所“辩”,即使“辩”也流于“怪诞”。荀子重视“师法”的作用,也表现了他外在化的理论倾向,到其弟子李斯、韩非时已完全流于外在,纯以法、权为用,其“师法”也只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25]452,已然完全摒弃了儒家价值规范。
四
在先秦名辩思潮研究范式转型的背景下,选择“辩”的维度研究荀子名辩思想,对于丰富先秦名辩研究有一定的意义。通过“辩”与“辨”关系的梳理,可以看出荀子辩学极强的伦理政治旨趣,而很少逻辑意味。在对“辩”之原则与目的的解读中,可以发现荀子“辩”仍然围绕着儒家伦理政治思想展开。由于荀子只是把“辩”作为维护儒家思想的手段,并赋予其价值内涵,他在看待“辩”的问题上出现了复杂而矛盾的情感,他一方面高呼“君子必辩”,一方面又主张“小人勿辩”,在“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他寄希望于政治权力的强势介入,不惜以“禁”“诛”等暴力手段减弱诸子百家的影响甚至清除他们。李斯、韩非继承发扬了这一思想倾向,可以说秦统一六国后的诸举措部分实现了荀子的“理想”,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算真正呼应了荀子。
[参 考 文 献]
[1] 苟东锋.名教的内在理路——由此而论儒家的价值理想如何落实[J].社会科学,2015(12):130-138.
[2] 何杨.先秦名辩研究的由来、取向与方法[J].中国哲学史,2021(5):31-38.
[3] 曹峰.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59-64.
[4] 晋荣东.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一种名辩研究的新方法[J].思想与文化,2015(2):20-39.
[5] 苟东锋.“新名学”刍议[J].思想与文化,2015(2):6-19.
[6] 曾祥云.荀子《正名》的现代解读——从语词符号的角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02-105.
[7] 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9] 苟东锋.孔子正名思想探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45-52.
[10]蔡仁厚.孔孟荀哲学[M].台北:学生书局,1984.
[11]崔清田.名学、辩学与逻辑[J].广东社会科学,1997(3):58-63.
[12]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3]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5]牟宗三.名家与荀子[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16]顾炎武.日知录[M]//顾炎武全集: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7]朱熹.周易本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8]陈文洁.荀子的辩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9]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0]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1]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2]林宏星.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3]潘小慧.从解蔽心看荀子的知识论与方法学[M].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
[24]金岳霖.论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