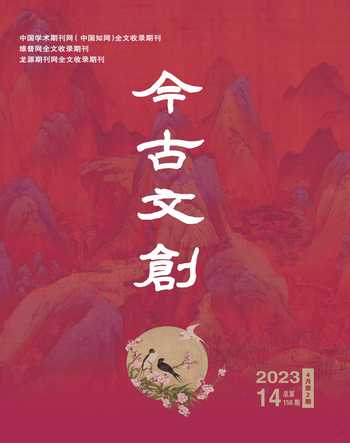沈约四声论与五言诗体的契合性之考察
2023-05-31桑晨杰

【摘要】 作为永明体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根据,以及诗歌格律的诞生的前奏,沈约四声的理论,从诞生时便争议不断。前人对四声之平上去入的研究已近完备,理论的阐述已详尽其体,但太过关注于问题本身,往往便容易忽视问题的本源之所在。沈约在《答甄公论》中曾述曰:“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契。”为何沈氏在此强调五言诗与四声的关系?四声又是如何使得五言诗达到“流靡”与“华契”的地步?或许沈氏的这一段话是依据甄公所问而答,但《答甄公论》的完整文本我们已不可考据,我们不可知甄公完整所论为何,然我们可以窥见的是沈氏的四声论定然与五言诗有着某种特殊的契合关系,这也是本文的论点所在。
【关键词】 沈约;四声八病;五言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4-004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4.012
基金项目:2021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沈约诗声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21Y679)。
一、五言诗的音律传统
沈约所处的时代正是五言诗鼎盛的时期,从诗经流传下来的四言诗传统已经逐渐被文人所抛弃,习作五言开始成为文学正统。五言诗体为何可以取代四言诗体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又为何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五言诗体得以登堂入室成为诗歌声律发展时期的主角?从五言诗的起源便可窥得一些踪迹。
四言体其实是中国诗歌最早的体式,虽然《诗经》中亦有五言句,但其未成诗体。早期的五言多是散文句式,依附四言而存,例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召南·行露》)“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卫风·木瓜》)晋人挚虞在其《文章流别论》中就表达出相同的看法,“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两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虽然诗经中存在着一些五言句体的诗歌,或是杂在四言中,或是五言为主,但都不可看作是真正的五言诗体。五言句真正脱离四言诗的环境而单独成诗体,则从汉代始。清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说:“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就五言中,较然两体:苏李赠答,无名氏十九首,古诗体也;《庐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类,乐府体也。昭明独尚雅音,略于乐府,然措辞叙事,乐府为长。”沈德潜将汉五言诗分为两种:乐府诗与文人诗,也即歌诗与徒诗之分。沈德潜的这种看法也是近世許多学者的看法,认为乐府五言与文人五言是汉时五言诗歌的主要类别。那么,我们首先就需要分清两类五言诗的诞生时间的先后。
依沈德潜之说法,文人诗之代表为苏李赠答诗、无名氏十九首;乐府诗之代表为《羽林朗》《陌上桑》等。无名氏十九首也即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中,李善注《文选》云:“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这十九首古诗萧统并没有署名,但在《文选》同时期稍晚一些出世的《诗品》中,钟嵘却将这十九首古诗中的十四首列为“陆机所拟”,而在梁陈之际出世的《玉台新咏》中,将《西北有高楼》 《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兰若生春阳》 《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皎月光》九首注为“枚乘杂诗”。由此可见,早在六朝时期,关于这十九首古诗的作者与诞生时间便是个疑问。
其次是关于苏李赠答诗的问题。苏李赠答诗最早可见就是《文选》之中,萧统在古诗十九首后所列便为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和苏子卿诗四首。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不仅表达了对苏李赠答诗的肯定,也肯定了苏李赠答诗的诞生时间问题。但是苏李之诗与古诗十九首一样,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全部人的认可,北朝颜延之曾说:“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古诗十九首与苏李之诗的作者及诞生时间问题在六朝时已成为一个疑案。自唐人刘知几始至当代的学者的研究,受限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古诗的作者与产生年代问题至今仍是一个疑问,学界始终没有一个观点可以得到辩论双方的共同认可。但是在众人的讨论研究中,梁启超先生的研究可作一个标准。他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考证了众多材料推出了一个观点:“所以我对于五言诗发生时代这个问题,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仔细研究,要下一个极大胆的结论曰:五言诗起于东汉中叶,和建安七子时代相隔不远——‘行行重行行等九首绝非枚乘作,‘皑如山上雪绝非卓文君所作;‘骨肉缘枝叶、‘良时不再至等七首绝非苏武、李陵作。”梁启超先生的论证得到了后来许多学者的认可与阐述。依照梁先生之推断,那么沈德潜所标注之古诗实为东汉之作,那么从体制上说,可追溯的最早汉五言诗非乐府不可了,也即是说最早的成诗体的五言即乐府五言。当我们了解了汉乐府诗是最早的五言诗体这一现象后,就可以清楚认识到五言诗中所蕴藏的音乐性的基因。而四声理论作用于文学创作的结果或者说沈约对于文学的追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低昂互节,宫羽相变”,这种具有音乐性的声律追求恰与五言诗基因中所包含的音乐性完美契合。
在五言诗的发展早期,基因中的音乐属性表现得较为单一。这主要就体现在乐府诗简单的以诗入乐的特点上。以诗入乐的侧重在乐,即辞要配乐。从形式上看,汉代的乐府五言开始有意识的调配文字以入乐,不像先秦歌诗那般具有原始性,言辞不再随性而发,而是进入到人为可操作的领域。《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武帝重用歌舞艺人李延年为都尉,大肆采集民歌,用新声为宗庙祭祀配乐,并让司马相如等传统儒家文人造新声歌诗。且汉乐府诗的主体是相和歌辞。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解释得较为清楚,“《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为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其后晋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相和歌诗在这里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拥有了清商三调及其他相和调的约束,在采辞入乐时,便不能将原始的民间歌辞一字不差地填入,文字的声音要符合乐曲的调式,所以歌辞的修订与创作逐渐成为一门技艺,同时也使得乐府诗开始具备文学的属性。
在形式上,乐府诗与文人诗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精神上,二者实为一体。朱光潜先生曾说:“乐府递化为文人诗到了最后的阶段,诗有词无调,外在的音乐消失,文字本身的音乐起来代替它。”这句话纲领性地总结了徒诗声律的由来,也向我们说明了文人五言诗与乐府诗的相同精神内核。在诗歌不需要音乐的相和时,寻求文字本身的音韵就成了发展的必然。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云:“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熟是。”汉末时人才开始研究字的音读构成,声韵两分,此后音韵之学大兴,直至齐梁之世,四声被应用于诗文,诗歌的声律才初步形成。而文人诗的产生也在东汉中叶之后,汉字音韵学的兴起与文人诗的发展之间不可不说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这种由乐府诗传承下来的音律传统,才造就了后人对于文人诗的韵律美感的追求,最后起而探寻文字的音韵,一步步发展到后世的格律诗。
所以当我们回顾五言的发展历程,已经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沈约之所以强调五言诗的四声使用,除却当时五言流行的文艺氛围影响外,由乐府发展而来的五言诗早早地拥有了诗歌声律的传统与气质。而清商三调演变至南朝时的主要部分吴声、西曲又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沈约声律理论的创造。所以,沈约对于诗歌声律的追求或者说中国诗歌发展至声律阶段的必然性是由五言诗的文学传统而来,而非个人天才且独特的创新所成就。
二、五言诗体的节奏与句式考察
沈約所提出的四声,即平、上、去、入,在本质上与四声之前的五声论是相同的。五声与四声的分类法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依据音乐上的宫、商、角、徵、羽五类音调而划分汉字的发音,后者则或多受到梵音的影响而创造的新的声调分类法。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根据汉字的“声调”与“韵尾结构”的差异的听觉特征,以声调区分的框架。所以沈约所提出的四声论,在作诗上并不具有指导性,需要有声病说的配合才可以构成一套相对完整的作诗法式。而四声八病的主要作用对象—五言诗,其节奏方面的特点与作诗法式又有着共通性。
首先五言诗的节奏划分与四声的创立有着共同的思维模式,二者都可称作是一种“对偶性思维”。《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载:“沈氏云:‘五言之中,分为两句,上二下三。凡至句末,必须要煞(杀)。”天卷《诗章中用声法式》也说“上二字为一句,下三字为一句(五言)。”可见,在当时沈约已经认识到五言诗的基本节奏划分类型,也就是上二下三。当我们了解到五言的基本节奏型时,便可以进一步分析四声与五言诗体的联系。
平上去入之四声的发现,在学界普遍认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转读”之说法。诚然,南朝是佛教大兴盛的时代,竟陵王萧子良便曾聚集门下文人“造经呗新声”,身为竟陵八友之一的沈约自然对佛教有着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在《答甄公论》中,沈约曾云:“昔周、孔所以不论四声者,正以春为阳中,德泽不偏,即平声之象;夏草木茂盛,炎炽如火,即上声之象;秋霜凝木落,去根离本,即去声之象;冬天地闭藏,万物尽收,即入声之象。”这段话将四声类比周易四象,不可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周易·系辞上》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对于四象的解释,在《正义》中说:“两仪生四象者,谓金木水火,禀天地而有,故云两仪生四象。土则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别,故唯云四象也。”四象即金木水火四行,而不提土行是因为土居四行其中,分管四季。沈约将四声类比四季,四季又分对四象,且在《文镜秘府论·天卷》所载《调四声谱》中云:“诸家调四声谱,具例如左:平上去入配四方。东方平声,南方上声,西方去声,北方入声。”四方与四声的关系又恰好与四声与四季的关系相对,那么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图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并且沈约创立的四声的调值也符合所对应的四季(四象)的特点。在日本沙门了尊《悉昙轮略图钞》一引《元和新声韵谱》云:“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四声的调值特点与沈约所论述四季之象的特点几乎相同:平声之象(春)为“德泽不偏”对应“哀而安”;上声之象(夏)为“炎炽如火”对应厉而举;去声之象(秋)为“去离根本”对应“清而远”;入声之象(冬)为“万物尽收”对应“直而促”,这种契合关系也佐证了沈约四声之说是来源于对周易四象理论的思考。
而周易的四象理论所带来的思维模式,其实就是一种“对偶性思维”。《周易·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对于宇宙生成的思考是最原始的对偶性思考,宇宙是有最原初的“太一”划分成“阴阳”,阴阳二仪又各自分化成“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种爻象,继而分为八卦。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种“一生二,二生三”继而生万物的思维在数量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强烈的对偶性。
沈约用这种“对偶性思维”模式成功反驳了甄思伯的“不依古典,妄自穿凿”的诘难,并且这种“对偶性思维”模式极大地影响了诗歌声律理论的发展,后世的格律诗在“对偶性”方面更加突出,不论是语言、格律,或是句数,都达到了对偶性的顶峰。
其次再来关注五言诗的节奏特点。日本学者松浦友和在其《中国诗歌原理》一书中,对五言能够流行做出了这样一种解释:“而且五言诗,(正如已部分接触到的那样)由于以上一拍、下二拍的节奏为基调,一句自身就包含着奇数(阳)和偶数(阴)的对比感觉。不待征引阴阳五行说和《周易》八卦就清楚,这阴阳(奇偶)对比的感觉,对于古代到中世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生理上可以体验到的平衡感。”松浦友和的这种说法虽然有些主观臆断,但是不可否认,《周易》对于中国古代的儒家士人来说影响巨大,且这种影响是深植于文化传统中的。
松浦氏将五言诗的上二下三的节奏划分看作是阴与阳的对比,这种看法在宏观上是合理的,但是在五言诗体节奏的微观表现上,对比性却没有凸显。中国的文字是单音节文字,尤其是古典文,表现在节奏论上即是一个字便可成一个音节节奏,一个字就是意义节奏。那么为何五言这种看似不对称的句式结构会取代四言诗体成为诗歌文化的主流呢?松浦友久在《中国诗歌原理》中分析五言诗的节奏时,引入了休止音的概念。松浦氏将五言诗的节奏分为三拍子,即oo oo ox(x为修止音)、oo o(x) oo,松浦论述第二种句式时,认为这是将句末的休止音拿到了句中一字,从而造成句中一字的长音,“……实际朗读时,不少时候由于意义节奏的影响韵律节奏产生某种程度的变化,显示了微妙的节奏变相……一般如‘擢——素手、‘花——溅泪、‘连——三月那样,第三字稍读为长音;而有时句末半拍的休音移到第三字之后,几乎稍成接近于‘oo ox oo的形式。”松浦提出的休止音的概念,可以将其理解为读诵感受中的停顿。因为中国古诗的节奏基本是以二音节为一拍,所以不论是句中或者句末的停顿的加入,都必须与一个单音节组合成一拍。这种偶数音节的拍节构成方式与前文所述中国人的周易文化传统相关,且一句中三拍子的奇数构成,又与偶数音节形成了对比,这种对比的感觉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镌刻在基因中的,也就是松浦所说的一种“生理上可以体验到的平衡感”。
五言诗除了一句之中三拍子的节奏构成之外,更重要的特点体现在它的句式结构。沈氏所说的“上二下三”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具体还可表现为二 一 二与二二一句式。在魏晋时,五言多是二 一 二句式,譬如“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曹植《公宴诗》)、“衰草蔓长河,寒木入云烟”(陆机《尸乡亭》)诸句,这个时期的二一二句式中的句中一字已经摆脱了虚字,开始使用动词。动词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诗行的节奏感,诗人们更加注重练字,句腰一字开始有了高下低昂的音节变化,如明谢榛所说是也:“子建已有响字,‘朱华冒绿池‘时雨静飞尘,‘冒‘静二字是矣。”至六朝前期,二 一 二句式仍是主流用法。譬如谢灵运,他所作五言诗歌多用标准的二 一 二句式,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登池上楼》)。齐永明声律论提起后,二二 一的句式才被诗人们广泛运用。不同于二一二句式的平衡,二二 一句式在读诵感觉上更加流动。虽然如松浦所说,句末一字有休止音的搭配,看似形成了稳定的二音节拍,但是在实际的诵读感觉中,不发声的休止音并不会使诗行具有平衡感,实际的节奏感觉也就形成了崔融所说的“散”的效果,这种不平衡的感受也就造成了五言诗节奏的流动。
二二 一句式的头重脚轻之感,极易造成节奏的流动。但是只依靠节奏很难将诗歌的韵律之美表现出来,还需要有“和声”的加入使得诗行体现出语言的音乐美。这里的“和声”所代表的就是文字声音的调和。而沈约所提出的四声与八病,本质上就是一套“和声”的法则。如“上尾”与“鹤膝”声病,“上尾诗者,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名为上尾。”,“鹤膝诗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以其诗中央有病”(《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如犯诗病,皆用同声,则第一句与第二句的两个节奏点上就没有高下交错之感,如此节奏的流动便会得以收束,而第五字与第十五字亦是同理。再如“平头”病,讲求诗行前二字互不同声,这是因为不论是哪一种句式,五言的前二字都是意义与音节相连的节奏,它与“上尾”声病相搭,在两句之中,务求首尾声声相异,声音可以在两行之中承接转折,即“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之理。最后如“蜂腰”,便是看重一句之中声音的变化。五言诗的第二字与第五字均是节奏点,二字的同声极易造成声调的板滞阻塞,这种病犯无关句式,二 一 二句式中间一字只有转承句意之用,或者说它是意义节奏的转折点,并无关声音节奏之变。这是因为中国古诗诵读的拍节节奏固定为二音节一拍,二 一 二句式中句腰一字并不是完整的一個拍节,即便有休止音的加入,停顿感也无法落到句腰的单字上,所以它无法在声音节奏上起到转折作用。
纵观而言,声病说的实质就是五言诗的作诗法则,通过种种声病的限制来使得诗歌达到“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的效果。五言诗的节奏、句式特点与声病说的规范共同使得古典诗歌达到“圆美流转如弹丸”的审美目的。
三、结论
中国诗歌的声律化是诗歌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尤其沈约的理论对于诗歌声律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沈约处于五言诗鼎盛的时代,但是五言诗的发生原因及文化传统与声律的关系必然有深层次的关联。由五言的发生发展起追溯,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五言诗自有的音乐传统,这也是五言替代四言成为主流诗体的原因,便如余冠英先生在讨论七言时说道:“二是七言歌谣在汉时不曾有一首被采入乐府,没有音乐的力量来帮助它传播,自然难于普遍。后者应是最主要的原因。”乐府不采七言而钟于五言,其原因应是五言的节奏体制更加优于七言,可以自由存在的单音节字的存在,构成富有变化且简单的三拍子节奏,并且四声的调配运用使五言体诗在写作上易于操作,也是如胡应麟所说,“七言浮靡,文繁而声易杂。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盖莫尚于五言。”沈约所提出的四声与八病的理论在与五言诗体的相互匹配过程中,完成了进化,最终在唐人手中浓缩为平与仄的二元对立,在诗歌的实操性上进一步提高。纵观整个文学史,四声的发现与五言诗的发展二者之间很难说谁前谁后,谁是为了谁而服务,声律运动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五言诗的节奏特点与体式又契合着声律理论,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让中国古典诗歌焕发出别样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笺.文镜秘府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9.
[2](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9.
[3]王弼,孔颖达编著.周易正义[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
[4]魏克宏.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
[5]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6]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7]林家骊.沈约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8]陈寅恪.四声三问[J].清华大学学报,1934,(02).
[9]钱念孙.朱光潜论中国诗的声律及诗体衍变[J].文学遗产,1999,(03).
作者简介:
桑晨杰,男,汉族,安徽淮南人,昆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