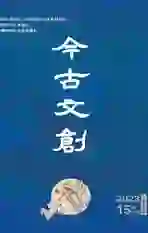从个人主义角度看“五四”以后的爱情悲剧
2023-05-31蒋巳阳
【摘要】“五四”以来,个人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其两大基石——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人。个性主义色彩在《伤逝》和《青春之歌》两位女主人公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彰显,而她们所经历的爱情悲剧中也能找到个人主义的作祟。《伤逝》所刻画的爱情悲剧中主人公涓生便呈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色彩;以往的研究对《青春之歌》余永泽和林道静的爱情悲剧归因中倾向于抨击余的私欲,却忽视了林道静的身上也有着同样的功利主义诉求。且林道静更进一步地体现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歧与皈依。试图探寻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背景创建后传入中国的个人主义思想该如何进步地生发在国人身上,及文学创作中该如何理性地对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共通与分野的答案。
【关键词】个人主义;功利主义;集体主义;林道静;涓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5-005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5.017
“五四”一代纷纷通过创造新文学来表达一种全新的人生伦理观念:个体本位主义,在他们看来,“伦理觉悟”是比“政治觉悟”更重要、更根本的“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一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超越前贤,对“个人主义”的宣扬达到更高的地步:鲁迅倡议“个人的自大”,陈独秀鼓动“个人本位主义”。
而有学者认为其间能称得上“主义”的还属《新青年》同人代表的启蒙阵营。这一阵营的个人主义有两大基石——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个性主义自五四新文学以来,一直到后来的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都得到了强调,挣脱一切形式的压迫,在个性主义者眼中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的追求是思想进步的表征。这种个性主义表征也出现在《伤逝》和《青春之歌》中,无论是子君振聋发聩的呼喊,还是林道静从离家出走到踏上革命道路,20世纪以来许多作家都刻画出了一个个力图打破封建罗网,追求个体的独立和发展的个性主义角色。而子君和林道静都分别有着一段著名的爱情悲剧,溯其悲剧原因,可以发觉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特质在其中作祟。后创作的《青春之歌》更进一步地反映了革命岁月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歧与皈依。
一、涓生:始终没有走出个人需要局限的忏悔者
以往许多研究从性别出发,强调了涓生的男权思想,其很多时候将子君作为自己生活的附属品去对待,同时要求这件附属品在能够为他打理家庭琐碎之时兼能彰显出新女性的光芒。然而,大家仍然是可以从涓生的一些观点中看出他对于中国女性的骐骥与肯定态度的,在一定程度上其有着迈出男权社会,为女性意识的萌发做努力的倾向。譬如,涓生在听到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后,有着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加之他对娜拉的果决的肯定等处,无一不彰显着涓生在男女地位差异问题上,是进步的,并希望唤醒子君的个体意识。而他的种种虚伪和冷酷地对待这段感情,究其原因,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基石。
涓生掌握着《伤逝》全篇的话语权来告诉我们:于他而言二人的结合只是丰富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于子君则成了她全部的生活。二人精神层面上客观存在的差异,使他有理由为自己的厌倦寻找开脱与借端,因而变得愈发冷漠。涓生子君二人的感情,从一开始便不对等了,涓生从自我出发,在破屋的空虚之中,他需要一抹生活的新气息,所以此刻他选择了子君,这份“爱”是建立在子君可以冲淡其原本生活的乏味功效上的,“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子君在他的引导下对着叔父喊出了振聋发聩的“我是我自己的”,决然地孤身选择了涓生,然不过三个星期,在“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后,涓生认为他们之间出现了隔膜。与其说是双方的隔膜,不如说是单向的厌倦。子君出走后,将伴侣视为全部的生活,因而倾泻所有地去爱自己的伴侣,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但这样的子君是违背涓生需求的,他认为婚后的囿于柴米油盐的子君已不是那个受他启蒙引领的新女性了。涓生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和他谈易卜生谈雪莱的“新”女子,他有着启蒙他人的知识传播欲望,但子君的“堕落”宣告他启蒙者身份的崩塌,这是不符合涓生的个人需要和幸福追求的。所以他单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子君作为自己“开辟新的生路”的拖累,他们的分离才能带來生活中新鲜的希望。他向子君提及娜拉是有意的,希望子君能够领会他对娜拉的赞扬,果决地再度出走,离开自己。直到无计可施,要坦白分离的诉求时,涓生仍旧用一种表面上是为对方着想,实际上为自己找说辞的口吻说道:“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这样的坦白方式不正是体现了涓生需要维护自身的正当性,其选择一直是在为自己抹去负罪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营造二人最终的分离是子君的主动离开导致的假象,使自己在这段感情中落得一个正面形象,这种正人君子的深情形象是他对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建构需要。
在表面上看,涓生不爱子君的原因是子君“堕落”了,实则不然,其间涓生对子君感情的淡化发生在子君成了一个彻底的家庭主妇,操心着日常琐碎从而无法像原来那个对娜拉充满好奇的女孩一样去热情倾听他了,子君无法满足涓生的在新思想的分享欲上的需求。涓生失业后,在家中学习办公,埋怨子君未能足够体贴地为他营造一个清幽的环境。他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断然地把生活过成一个人的,子君所处理的繁琐是子君的家务,他需要子君安静勿扰时,子君便该保持幽静。当二人的生活遇到瓶颈,子君在日夜操劳着家中琐碎时,涓生想的是“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涓生在悔恨与子君的结合,在他心目中,此刻这个收入微薄的家庭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为他的生计谋出路的价值了,他只担忧自己的存活,也把自己所遭受的苦痛的责任推到了子君的身上,然而子君却因为着爱,在苦苦坚守。涓生最后突然选择离开吉兆胡同也是利己的——满身灰土的可怜的阿随回来了,涓生是利己的,他无法在这种时刻再去顾及他人,何况是一条狗呢?
他需要逃避这里——逃离照顾旧日宠物的责任、对子君的愧疚。他的离开也是从为了自己获得更好更“坦荡”生活的需要出发。种种个人需要的压迫和负罪感也催生了这篇为自己找说辞的《伤逝》。本来,涓生是厌弃与抛弃行为的主动者, 而在他的自叙与独白中,却将自己开脱为一个被弃的形象:“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字里行间传递了一种受虐的心理 ,这与作家鲁迅本人惯常的刻薄文风不无关系,却形象地塑造出一个在感情中少自我反省的个人主义男性形象,一个五四以后许多新文化人身上功利主义作祟的缩影。
二、林道静:出于本体需要赖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皈依路上个人主义的消解
1920年到1930年中期(《青春之歌》故事背景),社会中一再出现诸如“团体”“集团”等提法,并形成了一种“主义”,“个人主义”也常常被视作处于“集团主义”的矛盾位置。有人直接指出: “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是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的分野,而从个人主义到集团主义,则是现代思想的一个特征。”《中华教育界》杂志的一篇文章将“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划为两大对立阵营,作者把“儿童本位的教育与民族主义的教育之争论”归结为“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的争论。肯定了“团体主义”的正面意义,“个人主义”带上负面色彩,被挤压出主流舆论。舆论界的宣传,使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仿佛站在了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落后的对立面上。因而,动荡年代的人们便面临着“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皈依的大趋势。
小说开篇描绘了“浑身上下全是白色”的林道静,她的行李是“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如此形象,显露出林道静的浪漫气质与个性色彩。她逃离出一个无亲情的压迫的家庭的开局也无疑张扬着浓烈的个性解放色彩。这种敢于反抗,追求自由的需求,是个人主义中个性主义的呼之欲出。然而继之于其个性意识喷薄后,面临着“娜拉走后怎么办”的传统女性困局。林道静带着原生家庭的痛苦谋生存、寻出路,她自我探寻的结局是选择投海自尽。因为在其所以为的独立生存之路上她的生存是处处存在危机的,逃离了家庭压迫,又孤苦无依地面临着社会、工作中的压迫。孑然一身的林道静发现她源于个性解放的出走之路通向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走投无路的危机。此时余永泽的出手相救为何能迅速地俘获林道静芳心的?余永泽关于文学的侃侃而谈营造出的罗曼蒂克氛围与志同道合的“他乡遇故知”情愫是无可置疑的两个原因。但除此之外,余永泽能够在林道静走投无路之时给予其绝处逢生的希望,能够解决其一时的生存危机——被余敬唐作交易品。因而,在遇到余永泽后,林道静有了当下生存的依靠和她一直向往的所谓“自己自由选择”的爱情。
与余永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不同,有着个性解放思想色彩的林道静是会为“整天是涮锅、洗碗、买菜、做饭、洗衣、缝补等细碎的家务,读书的时间少了”的生活感到空虚与乏味的。长此以往,卢嘉川的突然出现便给林道静琐碎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她为卢嘉川等人的热血、爱国热情、青春激情所感召,便渴望加入他们之中。这种向往是集体主义思想第一次在林道静心中起作用。“一个木字是独木,两个木就成了你那个林,三个木变成巨大的森林时,那么,狂风再也吹不倒它们。你一个人孤身奋斗,当然只会碰钉子。可是当你投身到集体的斗争中,当你把个人的命运和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你就再也不是小林,而是——而是那巨大的森林啦。”这是卢嘉川对集体主义的重要性做出的解释。而结合林道静的出生背景,不难发现,她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处于集体中的安全感,在这种安全感中寻求生存的力量。可以得出,卢嘉川指引的这条革命路,对于当时的林道静而言,源自处于集体之中的安全感的吸引力是大于真正意识到“如何正确地挽救民族于危亡之时”的。因为此时林道静对于革命的认识是远不深刻的,她视革命为一种丰富生活、填充空虚的手段。她说:“卢兄,替我想个办法吧!这生活实在太沉闷了。憋得出不来气。”“你介绍我参加红军,或者参加共产党,行吗?我想我是能够革命的!要不,去东北义勇军也行。”在这种不成熟的想法中,有着一个初步踏上个性解放之路的女性的爱国热情,更有着一个长期以来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单纯女性寻求集体力量支撑的渴望。
规避个体危机感寻求集体依托的安全感需求是最初激发林道静走上从个体走向集体的道路的诉求。而后续的坚定与思想转变、阶级转变的持续的一大推动原因是忏悔与救赎意识。在与江华谈及出身时,林道静说:“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所以我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虽然生母的身份和经历“减少了白骨头成分”,但这种地主家庭的出身让林道静始终怀着“我的家庭不断地剥削和压迫着工农”的愧怍,她要用自己投身于革命——为工农大众的翻身作斗争的行为来减轻其出身所赋予的罪孽感。
诚然,林道静在革命之路上不断觉醒与进步是无法否认的,在他人的指引与教诲下她逐渐成熟,成了一个热血、坚毅、顽强的革命者。但当人们揭开革命的帷幕和主流政治话语与导向,看到的是一个有着个性解放色彩的女性出于个体危机感对于集体所能给予的安全感的需求,在忏悔与救赎的心灵需求的推动下践行革命。林道静革命的动机中是有着很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需求的。而在以卢嘉川、江华为代表的集体主义的不断规范与制约下,林道静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要求,原有的个人浪漫特质和属性也消解沉淀,脱胎换骨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红色形象。可以看到,在经受“革命洗礼”后的林道静,这个曾经有着很强的个性意识、人文气息的知识分子被彻底转变了。
在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迈进的皈依之路上,可以说是一种集体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意识在个体中的呈现,但这又何尝不是一個鲜活的人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消解个性主义的历程呢?
诚然,在林道静和余永泽的爱情悲剧中,人们看到了两个有着截然不同追求的人物在思想、革命选择上的冲突。林道静投身革命,余永泽独善其身。以往的研究往往竭力批判余永泽的个人主义及其功利主义,却淡化了林道静在革命之路上所体现出的同样的特质。同时,大家更需要跳脱出这样一种裹挟个体的集体,审视这一潮流之中个人本彰显出的积极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色彩,集体和个体,从来不是对立矛盾的存在,而是互相成就、相互依存的联系。
三、小结
个人主义的两大基石——个性主义、功利主义,在不同阶段上分别体现在《伤逝》《青春之歌》的两段爱情悲剧中。从个性解放的宣言,到爱情中一方出于个体需要的“功利”——顾自安然幸福或是寻求化解个体存在危机,再到林道静身上所呈现的对集体主义的皈依。涓生的私欲与利己提醒着人们去反思这样一种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背景创建后,传入中国的思想该如何进步地生发在国人身上;林道静出于本体需要地对个人主义的抨击和集体主义的皈依,提醒着人们进一步地去反思文学创作该如何理性地对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共通与分野。
参考文献:
[1]邹志鹏.从晚清到五四:群己徘徊中的个人主义[J].党政干部学刊,2019,(05):17-23.
[2]杨念群.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兼论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J].近代史研究,2019,(02):4-24+160.
[3]杨联芬.个人主义与性别权力——胡适、鲁迅与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两个维度[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9(04):40-46.
[4]李旭琴.革命·知识分子·女性——重读《青春之歌》[D].华中师范大学,2004.
[5]杨勇.论《伤逝》中涓生忏悔的虚伪性[J].青春岁月,2021,(13):41-42.
作者简介:
蒋巳阳,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