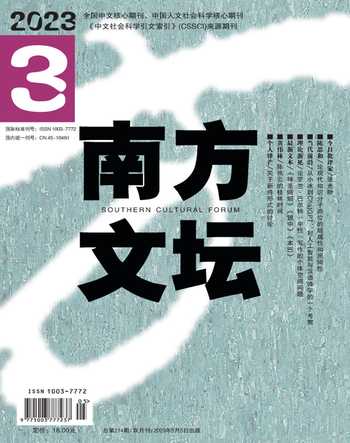话说张光昕
2023-05-31敬文东
张光昕本科阶段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按照这个专业的运行逻辑,他本该进入更费机心、更有前途的行业,而不是到高等学府先当青椒,再当老牛,干起了和文学有关的舌耕买卖。据他回忆,大二第二学期(时在2004年春),他的政治学专业的某位同学选修了一门名叫“新诗研究”的全校公选课。临上第一次课时,这位同学突然去不了课堂,就请一贯乐于助人的张光昕同学——何况他还是班长——前往“新诗研究”课堂,如果授课老师点名(此人当然从不点名),他可以冒充那位不到场的同学答一声“到”。话说这位老师用椒盐普通话朗读了几句柏桦的名作,顿时击中了前来答“到”的张光昕同学。他认为,这就是他后来放弃政治学转而落草文学专业,研究新诗,直至成为现代诗学学者的直接起因。
2010年5月,张光昕完成了名为《昌耀诗歌文本气质研究》的硕士论文,篇幅超过了十万字,远超硕士论文应有的规模和体量。答辩委员会主席黄凤显(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先生称赞说,这篇论文可以直接申请参加博士学位答辩。在答辩结束举办的酒局上,黄先生不止一次这样说起过。我看见张光昕既羞涩又兴奋的神情,很为他高兴。这篇硕士论文先在台湾的秀威书局出了正体字版,后来成为中国大陆版《昌耀论》(作家出版社,2018)的主要底本。昌耀是我特别欣赏的中国诗人,我对昌耀研究的现状一向很留心;就我所见,张光昕的硕士论文——当然也包括《昌耀论》——迄今为止,或许依然是目前这个领域内的最佳之作。记得有一年秋天,我曾和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学员们就昌耀的诗和人,有过一次很愉快的研讨和问答。有学员问:既然您对昌耀评价那么高,为什么不写写文章呢?我只好回答:我如果现在写文章谈昌耀,肯定写不过张光昕,那又何必写呢?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就昌耀写过哪怕一个字。
硕士论文完成后,张光昕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断断续续进行修改和增补。就我所知,他的修订工作进展艰难,但极富成效。说艰难,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工作自始至终,都从没有将昌耀仅仅当作诗学个案,更不会把昌耀处理成一个封闭、自足的诗学空间。说极富成效,这是因为打一开始,他就将昌耀置于整个新诗史甚至中西诗歌史的大框架中,进行整体的透视和考察。这正应了诺思罗普·弗莱的主张:你要想理解一个诗人的某一行诗,你需要读完这个诗人的全部作品。因此,张光昕从昌耀出发,却能得出超越于昌耀之上的诗学成果,并在现代诗学自身的层面上丰富了现代诗学理论。这一结果的确令人振奋。顺便说一句,张光昕在昌耀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却因为这个时代过于粗疏的阅读被轻易地忽略了;而他享受的,似乎正是一个理论原创者在中国本该享受的待遇,虽然这种现状令人寒心和不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和学术决心对于一个学术新手来说,显然是艰难有加的;他一旦越过了这一难关,必定会有脱胎换骨之感,也从此有了一览众山小的眼界。张光昕其后的学术之路,证明和坐实了这个素朴的结论。
做博士论文时,张光昕选择了一个更为艰难的题目:新诗如何处理物?或者说:客观之物如何被新诗所表达?这种表达的机制是什么?这样的机制在何种程度上让新诗具有何等程度的现代性?新诗现代性的指标究竟是什么?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列问题,在在都是现代汉语诗学研究中的“硬菜”,既充满诱惑力,令人食指大动;也让它的研究者(或品尝者)瞠目结舌,不禁心生怯意。张光昕很勇敢地对这些题目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提出过一揽子有效的解决方案。不得不说,这个题目有似于诗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它涉及现代世界的物体系的构成、物体系中暗含的等级制度,还涉及现代汉语在其骨殖深处自带的观物本性,更涉及现代汉语充满自身特色的意向性。现代汉语看见物和古代汉语看见物,绝不是同一回事,虽然从表面上说,它们都不过是看见了客观之物而已。欧阳江河诗曰:
一片响声之后,汉字变得简单。
掉下了一些胳膊,腿,眼睛,
但语言依然在行走,伸出,以及看见。
那样一种神秘养育了饥饿……
(欧阳江河:《汉英之间》)
但神秘和饥饿在更大的程度上,仅属于现代汉语。理由很简单:古代汉语只需看见物——而且是农耕时代的物——就行了;古诗只需要把它看见的写下来,就算情景交融,就算完成了任務,就算了却了作诗者彼时彼刻之心志。现代汉语不仅看见了现代之物,窥见了物体系中的等级秩序,还看见自己正在看见现代之物,两个看见不偏不倚,正好发生在同一时刻。现代汉语永远孜孜不倦地饕餮于物,永远处于因匮乏而来的饥饿之中——这饥饿是神秘的。但张光昕的关键问题是:现代汉语这种既监督自己看见而又看见自己看见了万物的应物方式,又在以怎样或复杂或直接的机制构造新诗呢?如何让新诗迥异于古诗而自带现代性?这是张光昕的博士论文急需解决的问题。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构造博士论文时的紧张、焦虑和兴奋。从目前来看,他还只能说是尝试性给出了初步的解答,就像陈景润完美地论证了“1+2”;但要想完全、彻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仍有一些重要并且复杂、难缠的问题,需要一个紧接一个被荡平、被放倒。但现代汉语诗学研究需要的,正是这种有难度、有挑战性的题目。啃完这样的硬骨头,就意味着我们的现代诗学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又进入了一方新天地。
有了这样的学术训练,让张光昕在做具体的诗歌批评时,总能从大视野出发,总是能够窥察到普通研究者很难窥察到的一个紧接着一个有意味的诗学细节;那些细节不仅总能被他尽收眼底,而且在他的大视野中纤毫毕见,几乎自动显露了它们全部的诗学意义。张光昕那篇《停顿研究——以臧棣为例,探测一种当代汉诗写作的意识结构》(《中国现代文研究丛刊》2016年第12期)的长文,便是这种研究方式结出的诸多果实中,也许还不具有多少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但这篇文章已经能够说明此处想要说明的问题了。看起来,张光昕很早就掌握了将英镑化为便士,同时又从不失却英镑尺度的思维方式;他的每一个段落,几乎都有着英镑和便士之间的不断转换,甚或再三转换。这不仅让他的思维在原始样态上呈巴洛克风格,而且让他文字表达崎岖灵动。一般而言,这种思维方式总是倾向于它的犀利、尖锐、坚定和高效率,有一种“废什么话”的内在腔调和音势,直奔主题和目标而去。在诗人钟鸣看来,音势是先于语言的,它分散在某些幸运者的个人气质和器官里;对这些幸运的写作者来说,音势一贯如一,即使偶尔被蒙蔽,但绝不会消失。这似乎意味着:化整(英镑)为零(便士)后,必须以观察零的方式去完成在现代诗学整体上急需要完成的任务。但这一能力,却又悖论性意味着深入、艰苦的学习。臧棣诗作中看似不起眼的某个特征(比如,作为便士的停顿),在作为整体的当代汉诗写作的意识结构(此为英镑)看来,值得深入研究、精确辨析。因为从现象学的角度观察,停顿本身就很有可能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意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意向结构;分析它的内在纹理和内部机制,极有可能为现代汉语诗学理论贡献新的视界。而有没有这样的新视界,对于新诗理论来说,并非无足轻重之事。事实上,正是依靠这种筚路蓝缕的倔强个性、锱铢必较的研究过程和进程,现代汉语诗学理论才逐步变得丰富、精确、锐利和复杂。
2004年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那时的北京,尚不知雾霾究竟为何物,甚至连雾霾这个奇怪的字词都未曾听说过。即使没有张光昕写于2016年的那篇回忆性的名文(亦即《批评与西门》),我也从来不会忘记那个遥远的春天,和现在比起来,那时的我们多么年轻。我就是《批评与西门》里,被提到的那个口吐椒盐普通话的人。在那个春天,我当然不可能想到十八年后会草就这篇短文。但草就这样的短文确实让我欣喜,让我暗自惊叹命运的神奇,也在暗中感谢它的眷顾和垂青。
2022年12月23日,北京魏公村
(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