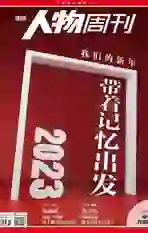朱宪民:我拍了很多这个时代马上要消失的东西
2023-05-30张明萌
张明萌

图/雷宇
2022年11月,摄影师朱宪民出现在成都当代影像馆。他的个展“岁月之光——朱憲民摄影艺术展”与威廉·克莱因、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贝尔纳·弗孔等西方大师的个展同时亮相首届成都国际摄影周。成都当代影像馆展览、收藏了他自1960年代以来拍摄的不同时期黄河流域、北京和珠三角的61幅作品。
开幕活动结束那天,朱宪民在酒店门口送别几乎每一位来参加活动的摄影师。他们亲切地叫他“朱公”,这一称呼突显了他在业内的威望与影响力。朱宪民在“文革”前入行,先后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吉林画报》、中国摄协展览部、《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杂志履职,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
“文革”期间,朱宪民拍摄的照片几乎每年都获奖。“文革”结束后,他将目光对准黄河百姓,开始了五十多年的纪实摄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家朱宪民作品集》,于1989年获“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作品奖,布列松为该作品集题写赠言——“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
朱宪民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过两次观念的颠覆。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朱宪民遇到他的第一个重要导师于祝民。于给了他相机和胶卷,让他在长春逛逛,“愿意拍啥就拍啥”。他把胶卷洗好,几十张12寸照片规规矩矩交给于祝民,以为会得到表扬。于祝民看完沉默许久,告诉他:只要挎着相机站在地上,都能照出这样的照片。“什么是艺术?你拍的和别人不一样,你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才叫艺术创作,才叫摄影创作。”朱宪民懵了。“刺激巨大,他天翻地覆地改变了我的观点,让我之后想办法去感悟,去拍得和别人不一样。”
“文革”结束后,朱宪民从吉林调至北京。1979年,法国摄影师苏瓦乐来中国考察,他负责接待,先后陪苏瓦乐去了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他发现苏瓦乐的工作方法和“文革”时期我们的摆拍完全不同,全是抓拍,画面粗粝、生猛、真实,生命力十足。
得知朱宪民来自黄河边上的村庄,苏瓦乐谈到了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说他就在拍黄河,有河南和山东。也聊到画家怀斯,怀斯画自己的家乡,成了世界知名画家。他问朱宪民:“你为什么不拍一拍自己的家乡呢?”
以前回家他只拍全家福,再次回去,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中原是中国的代表意象之一,在大家心目中山东、河南这些中原地区有着很明显的符号性,我知道时代正在剧变,我要把这种变化拍下来。”
从严格意义上讲,朱宪民的创作生涯从这时才正式开始。他是国内首批将镜头对准平民百姓的摄影师之一,拍摄时间超过四十年。他的作品聚焦于三大系列:一是以故乡为原点、沿着黄河两岸拍摄的“黄河百姓”系列;二是改革开放后记录深圳、佛山等地区变化的“珠三角系列”;三是记录北京市井生活的“北京系列”。朱宪民的照片里,有中国40年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纪实摄影代表人物之一。
从照相馆学徒到《吉林画报》摄影记者
80岁的朱宪民依然有两排整齐的大白牙,咀嚼顺畅。这似乎在用事实证明刷牙无用——17岁离开黄河边闯关东前,他根本没刷过牙。提到故乡,他说得最多的是“贫瘠”。1943年,他出生在当时隶属于山东的范县(后划归河南)。他记得,那里偏僻,封闭,落后。孩子一生下来,就光着身子被接生婆埋在用锅炒过的湿热沙土里躺到一岁。大人要下地劳动,没人照看。
他小时候没穿过袜子,初中毕业才拥有了第一支钢笔。对水果的认知仅限于枣——范县特产。到了外面他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圆水果叫苹果,另一种橙色水果叫橘子。
从东北亲戚寄来的信中,他得以管窥外面的世界,也萌生了离开故乡的想法。“知道他们那里的生活好,能吃饱。”离开前,妈妈在花布包里装好刚做的地瓜饼子,父亲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小儿,你要走了,千万记住,别犯法,别坑人。”
父亲的叮嘱对朱宪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之理解为:“别违法,就是要循例。别坑人,就是要善良,别羡慕嫉妒恨。”有这两句告诫打底,“文革”期间,朱宪民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脑子一直比较清醒”。他住在单位宿舍里,街道红卫兵找上门来让他搬走,态度极差。他菜刀都拎起来了,准备冲上去。“我一想起那两句话,想到我爸我妈还得依靠我,就控制住了。”他放下刀,跟对方说,这是单位的安排,不是自己抢占,要让自己搬走得跟单位沟通。
“我这个年龄,经过这么多运动,看到栽跟头的人多了,犯错误的人也多了。不是说我有多高明,而是我有一个最低的约束,别犯法,别坑人,这是底线。”朱宪民说。
到了抚顺,朱宪民去街道办报到,工作人员介绍工作。第一份是去澡堂子搓澡,学徒一个月工资22元。他拒绝了。第二个是理发。朱宪民老家的人都看不起剃头的。第三个是到钟表店修钟表,他也不肯去。最后对方给他介绍了一个照相馆,告诉他,不去就不管他了。
朱宪民只在中学拍毕业照时见过一次照相机,觉得很神秘。他去做了摄影学徒,成为“光明照相馆”的一员。“离开老家以后,我有一种雄心,一定要摆脱贫困的状况。”
在照相馆,朱宪民比其他人表现突出,别人需要学习两年的印相、修版、拍摄,他半年就掌握了,成了学徒里最早操作大相机的人。他的普通话本来带着山东口音,为了更快上手工作,他听了两个星期的广播,抹去了方言的痕迹。
《抚顺日报》的摄影记者常到照相馆冲胶卷,平时严厉的师父对他们特别尊敬。师父告诉他,人家叫摄影,咱们是照相。这种尊敬传递到了朱宪民身上,他很羡慕摄影记者,觉得他们“可不得了”。他开始干着照相的活,想着摄影的事儿,陆续买了好几本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书籍在家钻研,“我想要是我能当一下记者多好,有这种梦想和野心。”朱宪民回忆。
他意识到在照相馆不可能到报社当记者,就萌生了考学的想法。已经21岁,学历初中。一番研究后,他选择作为插班生考进了吉林省戏剧艺术专科学校舞台美术系舞台摄影专业。考试科目包括摄影操作、作文和历史答辩,他将后两者的顺利通过归因于自己“字写得好”。学院内没有相关的专业老师。时任常务副校长的丈夫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他看到朱宪民拍的照片,让他到摄影车间拍剧照,一边实习一边学习。朱宪民得以参与了《英雄儿女》《青松岭》等样板戏电影的剧照拍摄。
毕业后,朱宪民被老师推荐到《吉林画报》当摄影记者。他回忆,1966年到1976年,全国的摄影记者都是摆拍,摄影作品为政治服务,拍摄后要经过重重审核、挑选,连拍摄者本人都无法确认照片是否可以公开发表,照片大多作为资料存档。
那一时期,镜头里主要有两个表情,一是忆苦思甜,一是欢呼喜悦。拍摄时,朱宪民将摆拍维持在“动作指导”的范畴,表情则通过抓拍完成。所以,他的照片看起来更生动,也因此屡屡获奖。多年后他谈到“文革”期间的摄影作品,“虽然在形式上是不真实的,但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下,这一切又是真实的,的确非常真实地描摹和记录了那个年代。当时拍的这种照片,可能不是当下最客观的一个状态,但其实这事实本身反映的恰恰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片段。摄影最大的功能是真实记录社会的变革,也许现在从照片中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调动与‘修饰,但正是这种有意为之留住了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1963年,河南,黄河大堤的冬天。图/朱宪民

1969年,内蒙古,边疆女民兵。图/朱宪民
最后的农民形象
调到北京后,没有宿舍分配给朱宪民,只能暂住单位图书馆。近水楼台,他因此得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摄影集,开始接触与摆拍完全不同的拍摄手法。布列松的作品充满艺术的力量,他在街头寻找,随时准备记录生活的点滴。史密斯的照片看不出技术性的语言,只看得到感情,一切都源于他对生活的热情。“我意识到我已经走了十几年弯路啦。”直到遇到苏瓦乐,他的摄影观念被彻底颠覆。
他踏上了回家的路,将镜头对准最熟悉的土地和人民。
朱宪民告诫自己:千万千万悄悄回去,别扰民。每次他都在离村子三四公里的地方下车,回家以后换上弟弟的衣服,兄弟俩骑着自行车去黄河大堤上转悠,相机藏在衣服里。拍摄时,他多用长焦镜头,以此规避乡亲们看到镜头的不自在。但实际上被发现时,乡亲们都追着他要给他钱,因为相片不能白拍。他的很多拍摄对象一辈子都没拍过照。“我把他们当成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来拍。”他常常感叹,这不就是年轻时候的妈妈吗?这不就是现在的弟弟吗?
有一次,他看到墙角有个卖豆芽的中年人,很适合拍摄。镜头拉近,发现是自己的中学同桌。他是班长,考试经常90分,而朱宪民只能拿到70分。他连过去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如果公平竞争,如果他正常考大学……我只不过一个瞬间决定走出去,而他留下来了。我常想,我要是不离开这里,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就是那个穿老棉袄在墙根下抱孙子晒太阳的老汉。”
朱宪民的纪实照片发表在香港《摄影画报》上,引来了争议。1980年代初,国内大部分摄影还沿袭着过去十年的拍摄手法,模式固定,多为摆拍,难见变化。朱宪民的照片被认为丑化国人形象,“老穷丑”。他很委屈,也很生气。“我拍的都是我的亲人,怎么会往丑里拍?我拍的老人都是慈祥的面孔,年轻人都是健康可爱的样子。”
1985年,法国《世界报》编辑德龙看了他拍的家乡,带去法国发表。他提醒朱宪民,应该用更宽阔的胸怀拍摄,整个黄河流域都应该关注,而不能只是自己的老家。朱宪民因此扩展了拍摄范围,由故乡拍到整个黄河流域,一拍就是四十年。
国门逐渐打开,世界各地的摄影作品陆续进入中国,人们的审美意识日渐提升,大家开始接受朱宪民的拍摄方式。他几乎每年都回故乡拍摄,照片拿出来,就是一部中国农村变迁史。
“我拍了很多这个时代马上要消失的东西、消失的场景。”朱宪民说。
1980年,范县以农业为主,百姓种地要过黄河,木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他发现人越来越多了,光靠木船已经没法支撑客流量。他想摆渡应该很快就要消失了。果然没几年,浮桥动工了。到1990年代中期,开始修黄河大桥了,他知道浮桥也要消失了。现在,高速公路、八车道大桥修了好几座,摆渡过河、踩浮桥过河的场景已经成为历史。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依旧是清一色土坯房,人们点油灯,在井里打水,用木棒打麦子。家里没有餐厅,大家习惯在街上吃饭,手里拿着粥和干粮,就像他小时候一样。他很喜欢自己的那张《民以食为天》,画面里,爷爷拿着粗瓷大碗吃饭,孙女捧着最新的防摔搪瓷碗,眼巴巴看着爷爷能不能剩下一点东西给她,两个碗正好代表了两个时代。
到了1990年代,楼房开始建起来,电动摩托车、三轮车取代了自行车。2000年后,黄河滩区已经全部都是楼房,汽车、拖拉机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柴火换成了天然气,棉袄换成了时新的夾克……“人们的生活状况天翻地覆了。”朱宪民说,“这个变化太大了,几百年几千年凝固在那里,几十年一下子剧变了。不是说盖了几座大楼,修了几条马路,不是说人们的服装、生活状况,而是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
他发现,年轻一辈的感情比从前淡了。到村子里,聚在一起聊天的通常是老人,年轻人很少。表情变得和城市的年轻人相似。“大家的生活差异、城乡差距逐渐变小,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和人的感情淡化了。但不管怎么说那些老人还健在,我力求通过我的影像,将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的感情传递下去。”
他的摄影半径从故乡扩展到黄河流域,延伸到北京、珠三角,也曾走出国门,记录了苏联解体前的俄罗斯市民状况,还有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态。
这个冬天,朱宪民将再次踏上回乡的路,延续他的故乡拍摄。

1978年,北京,龙潭湖鸟市

1980年,河南,民以食为天。图/朱宪民
人:人物周刊 朱:朱宪民
纪实摄影是今天拍明天看
人:看过您拍的一张1980年代深圳打工妹的照片,感觉那拨人脸上有一种很昂扬的精神气质。但是同样的一个场景,如果放在今天,我们就会觉得那些深圳大厂的年轻人拍下来脸上都是疲惫。不知道您的感受是什么?
朱: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一个试点,我一开始就有这种意识。所以我80年代就开始拍深圳,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拍。它具有典型意义,从无到有,是一个样板,也是一个符号。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深圳一个街上四五间发廊。我不能回避历史发展过程。很少人拍发廊,大家认为那种题材比较敏感。但我必须把它记录下来,还不能拍得太颓废。她们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到深圳来打工,可能也不愿意到发廊里去,但实际上她们也很高兴。除了发廊,那时候还到处都是卡拉OK、夜总会。那是社会发展历程的一部分,你不承认这一现实,你就不客观。
人:您的意思是那个时候的人其实也不都是那么精神昂扬,也有颓废的,只是您没拍?
朱:对。人都是向往美好的,但是我尽量回避他的笑容、回避他的颓废,这是我拍照片的宗旨。常态下人们不经常笑,你非得让人家拍照的时候笑,那就不真实。
人:如果说深圳是典型,持续拍摄北京的原因是什么?
朱:我就是追溯原北京的生活状况,北京我也记录了四十多年。其实白塔寺旁边的几个胡同变化都不大,可能那里很难改造。那里的老百姓也没啥大的变化。白塔寺就是我拍摄北京的标志,以它为背景,我拍了好几年。像老北京人养鸟、老北京的胡同、老北京的京剧等等固有的老北京文化,现在都逐渐消失了。纪实摄影是叫后人回忆的一种影像记录。
人:为什么很少拍摄上海和长三角?
朱:我觉得长三角没有那么强烈的典型意义。拍北京是因为我住在北京,有一个客观的条件。珠三角是因为那里是前沿,从无到有,典型意义明显。上海在我的概念里没有北京或者珠三角的变化那么大。
纪实摄影要记录时代变迁,是今天拍明天看,和新闻照片不一样,新闻照片是今天拍今天看。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师,应该抓住时代的变化,抓住即将消失的东西。
我赶上了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
人:假设一个人在50年前拍了一张成都的照片,记录到当时的风貌,跟一个纪实摄影师50年前拍了一张成都照片,同样是记录老成都的风貌,两个人的拍摄有什么不一样?
朱:纪实摄影师会在拍的瞬间,关注对象的背景、表情、服装的特点,一般人可能不关注这些。如果今天拍的和20年前拍的没有什么差距,这就没有纪实摄影的意义了。我力求拍出的那张照片就是那个时代,任何人看那张照片就能知道那是哪一年。
所以就要抓住这几个元素:背景、服饰、表情。比如拍藏区,藏民磕长头拿着矿泉水瓶子,这就是他的时代的一个细节,如果没有矿泉水瓶子,那和50年前拍的没有差别。现在呢,他磕着长头休息,在那儿发微信,这就是时代。你一定要抓这个时代的细微部分。是不是典型化,你抓这个主题是不是有典型意义?都要考虑到。
人:现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很多城市建设都差不多,导致城市面貌趋同。在这种情况下,纪实摄影师应该怎样把握每个城市的特征?会不会拍出来都一样,每个城市感觉都差不多?
朱:这恐怕是没法回避的问题,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但纪实摄影并不见得非要有什么固有标志,现在纪实摄影的难度越来越大,法国也好,美国也好,拍的纪实感觉都一样。城里人和农村人穿戴都一样,表情都差不多,没什么可拍的。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是现在纪实摄影需要思考的一个新问题。我想还是有细微的不同,怎么去观察、怎么去表现,这需要思考。

1980年,山东,中原黄河摆渡的农民。图/朱宪民
人:现在您对纪实摄影的认知和当年与苏瓦乐谈话后的认知有什么不一样?
朱:我依然坚持自己的理念和观念,没啥大变化。我表现画面、拍摄的观念和外国人截然不同。我是一个中国人,首先要热爱中国人,我力求不管拍中国的哪个角落,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是中国人。我热不热爱自己的民族?热不热爱国家?我为什么不走国外的一些视觉路子?(我的照片)是用有思想、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态去表现。
我经常讲,人和人都是平等的。我拍黄河百姓,如果我不离开那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你喜欢这个民族吗?你希望这个民族好吗?你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一个中国人拍中国应该有什么心态?不光是摄影,任何艺术都一样。
我和美国人接触,要说美国人不好,他马上就翻脸。日本、韩国更严重。但我们一些中国人往往自己恶心自己、窝囊自己,这是很大的问题。
一个追求艺术的人,首先你要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所以我拍黄河中原的老百姓,始终在思考,他们那种朴实、善良、忠厚,那种为生活去奔波的气质一直都在。他们生活不富裕不是因为他们不善良,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才智。我力求表现出,那里的人,从表面上看他们朴实善良,而骨子里充满了智慧。
所以我总结我的摄影理念:我力求表现他们由于社会背景导致了事实上的生活状态,而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性格造成的。在拍照的过程中,我力求从照片的表情来表达他们的智慧、坚韧,那种精神面貌。
人:按您现在的理念来看“文革”时期您的作品,您能理解当时的拍摄吗?
朱:“文革”期间我拍的“乐”的情绪就少了,主要是根据照片主题的内容来表现人的情绪。当时只能那样(擺拍),那时如果不那样拍就不正常了。我觉得是另一种真实。我也没有其他想法。有些人标榜那时候有别的想法,那是胡扯,不可能存在。那时候我是“摆中抓”,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难。
人:在中国当一名纪实摄影师,您的感受是什么?
朱:纪实摄影是最真实的时代记录,就得把真实的老百姓生活状况记录下来。我始终主张一定要拍85%的人的生活状态。20%的人可能富一些,20%可能穷一些,基本上85%都差不多。
我从来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老百姓。社会打造了我。我欣慰的是我赶上了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正好我用我的相机拍了时代的变化。反差太大了,几百年、几千年永远凝固在那里,这几十年一下子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