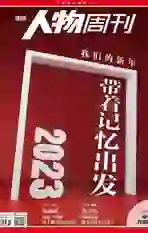每一朵浪花都有自己的宿命
2023-05-30姜晓明
姜晓明

冬之海
潮汐
1月,北戴河进入淡季歇业期。冷清的街道难掩夏日的繁盛,暂停营业的海鲜餐厅、酒店宾馆一家挨着一家。
夏日人潮如海的老虎石公园也暂时关闭了。我走到售票窗口。售票亭里有位老人在看报,他抬眼看了我一下,旋即又垂下眼皮。我只好隔着栅栏门向内窥望:一群形似老虎的礁石卧在海滩上,接受着浪涛的拍击;几艘蒙着苫布的快艇列队岸滩;令我惊奇的是沙滩上几株遒劲古朴的苍松——它们以顽强的生命力征服了沙壤与海风。望着树干上的灰色鳞甲,我想它们或许是龙的化身。
我沿着海滩路向东走,拐过路边那块刻有“北戴河”的岩石,来到紧邻公园的一处开放海滩。
海面泛着金属光泽,沙滩一片银白。
一个老人扣着棉服兜帽,手里拎块素描肖像画板,沿着海滩揽生意。画板上线条潦草地勾勒着一个女孩,秀发绕肩,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您画多久了?”我问。
老人转过身,露在口罩外的脸上布满褶皱与晒斑。
“一辈子了!”他翻了我一眼,倔强地回答。
海边的生意人,见过太多过客。生意之外,他们懒得和陌生人废话。
另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挎着旧背包,拎本快散架的活页影集簿,在海边寻觅着。“快相,快相,照快相……”偶尔,他也会叫卖,“海鸥食,海鸥食。”他经过一个个正在用手机拍照的游客,没人回应他的吆喝。
礁石上有对新人正在海风中拍婚纱照。新郎悉心地呵护着新娘,不时在拍照间隙为她披上棉衣。拍快相的老人背着手,停止吆喝,围着他们转来转去。他看这对情侣变换Pose,看年轻摄影师的装备,以及他如何调度客户:“老妹儿,看这儿。老妹儿,乐一乐。老妹儿太美了……”婚纱照——新娘永远是主角,新郎是配角。
潮水把一些东西留在岸上,也把一些东西带入大海。
退潮后,滞留在礁石上的贝类生物无法返回大海,不幸殒命。日积月累,风吹日晒,附在礁石上的尸骸变成一层厚厚的石灰质。夕阳下,钙化的石灰质迸发出锈色珠光。一双双脚踩在上面,发出沙沙声响。大海见证着爱情与死亡。
壮丽的风景前,从不缺席承诺与誓言。海滩上写着各种心愿:“白头偕老”;“财源滚滚”;“逢考必过”;“永远再见!2022”……明早,这些美好的心愿会被上涨的潮水吞噬,融入大海。
等待
冬季的南戴河夜晚,寂静荒凉。驾车前往业主食堂,我仍需借助导航。尽管昨晚我刚刚去过。路上七拐八绕,其中有段没路灯,要开远光灯行驶。
业主食堂开在临街的居民楼下。方圆几公里内,它是少数仍在冬季营业的餐厅之一。来这里吃饭的除了附近居民,还有许多外地农民工。
今晚,已过飯点。宽敞通亮的餐厅里,只有三桌农民工围坐在冷光灯下就餐。他们的吃喝也进入尾声,桌上的杯碟和酒瓶都空了,只是在抽烟闲聊。
坐在收银台后面的女服务员冲后厨喊出我点的饭菜:“尖椒干豆腐、炸蟹腿,两张葱油饼。”她长头发,鹅蛋儿脸。
我坐在靠门的老位置。门口的长条桌上摆了套带茶台的新茶具,之前桌上摆的温度计和登记簿不见了。
农民工仿佛出土的兵马俑,穿着脏污的迷彩棉服,人人灰头土脸。餐桌边堆着工具包和冲击钻。他们在烟雾中争论不休,然后陷入突然的沉默。他们不时提到附近一个社区的名字,他们都在那儿干活。那是个带有度假村性质的高档社区,社区内餐厅咖啡馆酒吧云集,但他们消费不起。
在海边转了一整天,我饿坏了,肚里泛起海浪般的肠鸣。

画肖像的老人

老虎石公园

五个看海的男人

独自泛舟的男人
女服务员绕过农民工餐桌,把一大盘尖椒炒干豆腐放在我面前,分量足够三个人吃。绿尖椒里点缀着不应放的红干椒。这是一道传统的东北家常菜,其味道的好坏通常不取决于厨师手艺,而由干豆腐的制作水准来决定。我吃了两口,放下筷子,等葱油饼。
农民工摇晃着身体,陆续离开。他们留在坐椅上的余温也随之散去。一个工人出门前,瞥了眼我的餐桌,嘴角露出一抹微笑。餐厅里少了人气,开始变得阴冷。
女服务员空着两手朝我走来,脸上带着歉意。
“饼没放葱花。”她站在餐桌边,捋着胸前长发,“要不,我给你上根大葱吧?你想吃。”
我被她逗乐了。她捂着嘴,也笑了。
我就着油饼吃尖椒干豆腐,时不时望向厨房,等着炸蟹腿。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做事节奏。我学会了等待,在等待中,常有意外发生。
当女服务员再次两手空空、低着头向我走来时,我的心像桌上的菜一样变凉了。
“啥情况?”我问。
“糊了!”她无奈地摊开双手,“要不,你换个吧?”
“今天是咋整的?”我假装生气。
“那啥……”她眼睛望向天花板,眨了两下,“厨师有点儿上火。”
我们又都乐了。这一次,她忘了捂嘴,露出两排银光闪闪的矫正牙箍。
同心圆
清早,我拉开酒店窗帘。窗外大雾弥漫,太阳把天空烧出一个白色的洞。除日出日落外,能够直视太阳的时间少之又少。现在,它像轮满月,明亮却不耀眼。大海方向,四幢公寓楼悬在半空,仿若海市蜃楼。那是昨晚农民工说的高档社区。我决定今天去那里转转。
车驶到社区大门时,被穿蓝制服的保安拦下。他的唐山口音里混淆着声调上扬的葫芦岛方言。
“有门票吗啊?”
“什么门票?”
他让我在手机上花60元买了张参观券。
社区内外判若两个世界。开发商仿佛把电影里某个欧陆风情的场景移植到这里,给人一种置身异域的虚幻感。
街道两侧分布着餐饮店、超市、电影院、美术馆……,人行道上铺着火山岩地砖。三五成群的文艺青年信步街头。近年来,一些文学节和戏剧节经常在这里举办。
成排的别墅掩映树下,多数业主只在度假期间来此小住。隔着上锁的院门与落地窗,可以看到客厅里散落各处的泳具和充气船。
我路过一家带阳台的U形酒店,心头掠过一丝懊悔。之前我预订了这家酒店。考虑到价格不菲,且不带早餐,便退掉了。若不更改,我就可以自由进出该社区了。
步行约两公里,砌石与苇草环绕的海滩映入眼帘。海滩上人影绰绰,脚印重重。每个脚印的阴影里都藏着尚未融化的晨霜。白色秋千架下,父母们低头看手机,孩子们径自在秋千上试探胆量。
穿着体面的游客聚在海边,彼此保持着适度的距离与客气。他们用吐司投喂海鸥。海鸥的聒噪声里混杂着阵阵咳声。这些黑嘴鸥仅栖居在中国东部沿海,紧贴潮汐线扑腾、飞翔,喋喋不休地尖叫,抢夺不劳之食。孩子們亢奋地叫嚷着、蹦跳着。尽管有位母亲不停地纠正,她的孩子仍顽固地喊着:“小乌鸦,小乌鸦……”
我向海边一幢灰色水泥建筑走去。短短的路程中我听到自己粗重的喘息声。自从一个月前阳过之后,我能明显感到体力大不如前,说话快了或走路急了,都会产生过往不曾有过的憋闷感。
水泥建筑是座图书馆。站在落地窗外,我看见入口处立着帕蒂·史密斯的跨年诗歌朗诵会海报;一排临窗座椅全部被人占据,他们面朝大海,却都在孤独地看手机。我在图书馆外的长椅上背对大海坐下,掏出水杯,平复喘息。长椅的另一端,一个戴耳机的男人摘下口罩,奏出一组强劲咳声。我看向他的同时也咳了起来。我们对视了一眼,他戴上口罩,悻悻地走了。

“年轮”
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上午。随着太阳攀升,雾霭散去,冰霜融化,海滩上的游客多了起来。
沙滩上,一栋白色哥特式礼堂被自己的影子切割得棱角更加分明。游客排着队在礼堂前拍照录直播。我绕到建筑后面,在它投向沙滩的浓重阴影里,不知何人留下了用脚蹚出的同心圆。圆心外的圆圈一圈比一圈大,像涟漪般扩散。一对父女在“涟漪”前驻足。女儿蓦地挣脱父亲的手,跑向圆心,蹲在地上,堆起沙子。冰冷的沙从她手中溢出,落在渐渐拱起的沙包上。沙包最后变成沙锥,堆上去的沙开始向下流淌。小姑娘并未放弃,继续徒劳地一把又一把将沙堆上沙锥。父亲歪着头,站在圈外静静地看着。似乎有什么触动了他,他迈开双脚,开始接续起最外围的圆圈,缓慢且专注地蹚起圆圈来。那是一双大脚,白色乔丹鞋看上去有44码。
我走了很远后,回头看。父女俩仍在玩着同一个游戏,涟漪变成了年轮。
一串儿干涩的咳声迎面而来。是一家三口。我想避让,发现自己走在一条被冰泥包围的浅滩上。快接近我时,孩子抑制住了咳声。但我却听到了一句不该他这个年龄说的话:“要是我死了,你们会伤心吗?”孩子戴着无框眼镜,语气平和,十一二岁的模样。穿着黑色同款羽绒服的父母隔着孩子彼此看了眼对方。或许是因为与我擦身而过,或许是这话问得突然,两人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但我注意到母亲下意识地攥紧孩子的手臂。
在穿过社区回酒店的另一条路上,我闻到一股马粪和草料味,然后听到马的嘶鸣。在一栋营房似的马厩前我停下脚步。马厩门窗洞开,几匹毛色光亮的骏马凝神于窗框内,仿佛在沉思着什么;一匹鼻梁上带白星的马将头探出窗外嗅了嗅,随即又收了回去。在对面室内跑马场里,一个穿骑术服的孩子骑在乌黑的高头大马上,在父母的注视和骑师的指点下,小心翼翼地拉着缰绳。黑马驮着对它来说几乎没有重量的小骑手,迈着轻盈的碎步,踏出鼓点般的哒哒蹄声。
我喜欢浪
海洋、沙漠、天空,一旦长久凝视,就会被其捕获,最终将你变成它的一部分。
在海滩的最后一天,我决定把相机留在房间,单纯、不带任何目的地在海边走走。
上午10点,我来到海港附近的金梦海湾。此时,潮水上涨至最高水位。岸滩上,一座废弃的碉堡,一半已浸入水中。
风在海面游荡,筑起浪的阶梯。浪舌舔舐沙滩,将细沙留在岸上、粗沙吞入大海。
大海翻涌着、轰鸣着,发出古老的声音。即使波澜壮阔,也会干涸。今天的海洋,或许就是明天的沙漠。
光刃劈开云层,白银与黄金洒满海面。
冰层开裂,渗出海水。一颗颗破碎的玻璃心,在海上漂流,难舍难分,又不得不分。
大海于我是陌生的。我想起多年前,在连云港的那个冬日黄昏。那天风微浪稳,夕阳微黄,海滩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我踩着礁石,跨过浅滩,拍摄日落。顷刻间,海水漫上滩头。我盯着上涨的海水,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涨潮了。潮水淹没了来时的礁石,没过我膝盖。我举着相机,狼狈地奔向岸边。到达堤岸时,冰冷的海水已湿及双腿。
我沿着海滩步道漫无目的地走,直至港湾地带。此处,沙广人稀,水流静谧。沙滩、浮冰、海水、天际线在这里交织成悦目的色带。海港上,像长颈鹿似的起重机装卸着集装箱,发出富有节奏的金属撞击声。
我戴上兜帽,铺块儿带来的塑料布,躺在午后微温的沙滩上,拿出约翰·班维尔的《海》。
我想,我会记住这个独自在海边的暖冬下午。
临近黄昏,我起身离开沙滩,折回海湾。
海水在一瞬间上涨,又在不知不觉中退去。镶着泡沫的浪裙,在岸滩上留下白色蕾丝边儿。此时,当地居民涌上退潮的海滩。他们提着水桶和盆子,拿着铁锹和手电。在潮间带的泥沙中,掘地一尺,寻找一种像剃刀似的贝类海味——蛏子。
突然,海滩上响起爆竹声。人们停止采挖,集体望向天空。璀璨的焰火在晚霞中绽放,照亮了海滩,照亮了人们的脸,照亮了容器中介壳紧闭的蛏子。
月升日落,海天一色。浮浮沉沉,涛声依旧。后浪催迫前浪,前浪引领后浪。每一朵浪花都有自己的宿命。
我在路灯下的长椅上坐了一會儿,冬之海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我下意识摸向背包,忘记了相机留在房间里。当我起身离开时,习惯性地瞥了眼座椅,椅角上居然刻着一句话:“你不是喜欢海吗,我喜欢浪。”

寂寥的男人

夜晚的堡垒

浮冰与海岛

退潮的海洋

誓言

“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