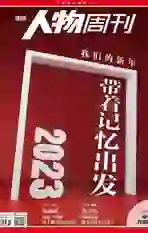一个叫小张的厂二代决定不接班
2023-05-30孟依依
孟依依

小张有一次问父亲家里有没有存款,父亲指了指这些,说,这就是存款。图/受访者提供
江浙一带人经商头脑活络,乃至我的室友、同事张宇欣读完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两年后仍念念不忘,多次复述其中温州人如何在一夜之间以猪皮炮制高端皮衣并在第二天销售一空的情节。她自比老太监得了《葵花宝典》,看得啧啧称奇:“你们浙江人。”
我出生和成长在浙江中北部小城绍兴,听过见过不少办作坊、办厂的创业故事。三年前我去义乌商贸城采访时碰到一位经营伞业的绍兴人张吉英,她在新冠疫情呼啸而过的冷清店铺里招呼我喝咖啡,参观摆在展柜里的精致长柄伞,讲她如何15岁开始跟着修伞匠父亲学制伞、卖伞,如何怀孕时仍整天整天站在当时简陋的露天市场——她个子矮,脚底垫个木箱子,整个肚皮搁在摆货桌子上——越过山一样的伞堆朝顾客兜售。
如今50岁的张吉英已经有了好几家店铺,并立志将此打造为百年品牌,说着将目光投向正在电脑前打理生意的大女儿。
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民营经济中诸多店、厂将出现代际交接的问题。厂一代在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浪潮中以孤注一掷的方式建起家业,他们的儿女是计划生育、义务教育普及时代的造物,一面相信着世界会更开放、包容、和平,一面却在青壮年时期遭遇历史的回环。厂二代们还会选择和父辈一样的生存方式吗?
“也许你们觉得是有得选的,但很多人是没得选的。”小张说,她是我因为看选秀节目而加入的奇妙群组里的群友,南京一家建材厂的二代,每次她一到厂里,大家都喊她“小张”或者“老张的女儿”。
“开厂太辛苦了,在工厂运营比较好、父母也觉得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就希望孩子别那么苦。但是渐渐运营困难,父母力不从心,就抓子女回来帮忙。他们之所以不太干涉二代们的专业选择,让他们趁着年轻做自己想做的,是因为接班以后就会彻底失去自由。很多年轻人别无选择,如果不服气毕业后先去别处上班,这两年疫情连工资都拿不到,只能回来接受现实。”
现实是,根据普华永道曾发布的《2017中国新生代企业家现状调研白皮书》,两千七百多万民营企业中有八成以上是家族企业,其中六成的新生代企业家已经接管了家族企业——但小张属于另外百分之八,犹豫着或者已经坚定拒绝继承家业。粗略估计,像她一样的二代大概有近两百万人。
年前在小红书上,一些“大小姐”回家接厂的贴文引起讨论,各地厂二代建起社交群,小张在的那个群,一星期之内迅速聚集起300人。有家业较大、父母培养方向也更明确的二代从大学毕业后迅速入了厂,也有不少二代像小张一样留学回来,学了与本厂制造管理全无关系的专业,面临父母的期待却不想回应。
“和我其他朋友相比,厂二代们其实更渴望做自己的事业,赚钱,对商机特别敏感。为什么大家拉群特别快,因为对我们来说,工厂其实没有闲钱,所以最值钱的东西是资源。”一些令旁人自愧不如的经商基因很快就在群里显现出来:卖粮食的二代寄了一袋大米和面粉给小张,她带去让做烘焙自媒体的朋友琢磨看能不能用上;牛肉厂的二代听说小张家有机农场要养牛,主动给她介绍养殖场的人;小张懂玄学会看星盘,两天里已经给50个群友看了星盘,这当然也是一种快速建立社交信任的方式。
“大家都来问些什么?”
“都觉得自己很苦,算工作顺不顺利。还有都会想怎么转型。有些人接厂接的确实是个烂厂,管理模式都非常有问题,就很辛苦。和富二代不一样,我们都自称是‘负二代。”小张大笑,“我不喜欢所有工作,也不喜欢负债的感觉,所以我从来不用信用卡。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彷佛一直在为欠债而努力,根本不是在为更好的生活。我爸每年去要钱都要到年二十九才回老家。今年更差,四五百万的工程款只能拿到四十万。”
小张初中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开始学画画,一个人去杭州找画室、住处,被老师赶出门的那天晚上在街上拖着行李箱走了很久,找广告,再联系其他老师和画室。这些事父母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她和父母的联系基本只限于没钱时要钱。工作压力导致家庭关系疲惫时,一家人开车出门,在高速上一两个小时没有人说一句话。小张有一次回家,发现父母已经搬家,却忘了告诉她。
她知道父母很忙,也很少向他们求助。其中一次是考试前要查询各校的校考时间,网吧查身份证很严,她又没有智能手机,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在电话里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懂。小张感到难过,同画室的女孩曾收到一个沉沉的包裹,是女孩妈妈帮她整理打印的所有学校和志愿填报资料。“我真的很羡慕你知道吗?”转而又换了一副习以为常的语气,“反正好多都这样。无论跟他们说什么,我感觉都仿佛一片云飘过去。个人的问题永远排在工厂之下。”
高考结束后小张才第一次去了父母的住处,一间办公室一样的屋子,和车间连在一起,24小时准备应对厂里出现的状况。
“我觉得好压抑,面对着白墙,连株植物都没有。睡觉的地方就只能睡觉,上厕所的地方只能上厕所,它们没有别的功能。”一种牺牲自我的工作方式。那时候小张看父母,固执地认为他们哪有什么梦想之类的东西。
如果说父亲偶有显露出成就感的时刻,那就是走在南京街头看到那些高楼,为曾参与建设它们而满足。在更大的集体中,他能找到自己的坐标。
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小张没有回厂里,她选择开自己的工作室,也不如意。两年后听了一场关于情境主义国际(一个由先锋派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政治理论家组成的左翼国际组织)的讲座,开始意识到对成功的追求或许是资本与政治的陷阱:人为什么需要“优秀”?要学奥数?要成就一番伟业?这些质疑从根本上反对了父亲以成就感和对集体的奉献值来衡量人生的标尺。不顾家里的阻拦,小张学了三个月法语,去了法国留学。
体验派人士小张曾在法国度过了愉快、舒展的五六年,翻看相册,让人想起侯麦的《夏天的故事》。可是待得越久越意识到一种文化差异,她的法国朋友们永远为对方保留空间,极有分寸,略显夹生,她的中国朋友之间则有无条件的信任,互相侵略,根深蒂固。小张倾向后者。
“很多二代是两者兼具的。留学的时候接受西方教育,对自由和个人价值敏感,读完书回国面对的是要为集体做贡献。开厂这件事情不管你是不是老板,都在做一件非常集体主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很分裂。”
劳工将自己的时间投入看似稳定、安全、强调配合、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工作中,他们同吃同住,日积月累出一些自己也讲不明白的感情,是对于这个集体的依赖,也是对那些随着命运半推半就一去不复返的大好时光有个交代。
因此关厂很难。对于一代来说,厂不仅是他们的事业,也是生活,要怎么去结束一种旧的生活呢?何况还有高峰过后经济增速放缓呈现疲态后的不甘心。如何偿还大量贷款?遣散费哪里来?如果关厂,意味着“这个区域就要出现几百个无业游民,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如果经济上没有办法保障的话,很容易成为盲流”。开厂子,成了骑虎难下的事。
是否可以摆脱这些,是否可以选择一条更清晰、不摇摆的路,厂二代们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他们一边在集体中扮演螺丝钉,一边维持着一份副业。小张帮着家里寻找新的销售渠道、参加国外展会,同时在美术馆任职(虽然工资不及自家厂正式员工的一半)、去高校上课。她在群里碰到另一个姑娘,在家里的起重机厂的隔间里做珠宝鉴定和设计,想在自己的领域证明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
“如果你不接班的话,厂怎么办?”
“卖掉算了。”
在传统制造业中,子女若不继承家业,寻找职业经理人也十分困难。二代們“求收购”的不在少数。
话虽这样说着,小张也渐渐理解了永远忙碌、节俭的父母,理解他们从事的重要工作和疏于打理的“表面亲情”,理解他们在追求真正的理想。“但我也想追求我的,只是不在一条路上。我也不想他们被自己的理想绑架,他们老了,真的做不动了,我一起帮他们想办法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