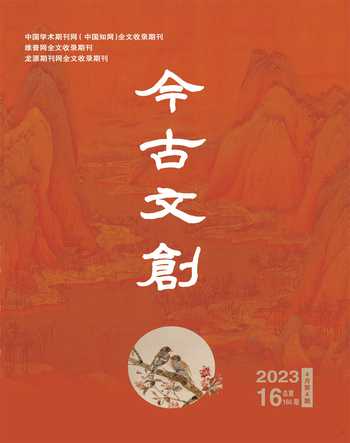从艺先修德
2023-05-30王怡
【摘要】 从艺先从德,从艺先学人。真正的戏剧艺术家,不仅需要精湛的戏曲技艺,更不可缺的是严谨的道德底线。《喜剧》中的贺氏父子三代人的喜剧生涯,老艺人严格遵守自己的喜剧原则,不敢逾越一步。作为传人的两兄弟,贺加贝陷入喜剧陷阱不可自拔,最后被观众抛弃;贺火炬及时悬崖勒马,点燃新喜剧的希望之火。《喜剧》旨在传承真正的喜剧精神,从艺修德,是高概念叙事加喜剧元素的集大成之作。
【关键词】喜剧;丑角;恒常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6-008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6.027
《喜剧》是陈彦长篇小说“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装台》《主角》《喜剧》分别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一群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装台》描写了装台人精湛的手艺,展现的是对普通人在不断寻求“生”的机会的称赞;《主角》围绕忆秦娥的艺术人生,深究秦腔人对秦腔的热爱与不悔;《喜剧》则不同于前两者,既写出了丑角的技艺精湛,也写出了演员在舞台后的常人生活。作家以贺氏父子三代人的喜剧生涯,将艺术与人生结合起来,在“为人”和“为艺术”中阐释个人与时代及传统的关系,追寻‘下苦人生存的恒常价值与意义。
《喜剧》以书写秦腔丑角的日常戏剧生活作为故事主题,将不同人的个性展现在戏剧舞台上从而进行良性对话,描写西京城中的戏剧舞台前后的普通人的内心世界,表现戏剧人在生存“常态”中的喜怒哀乐,用温情书写值得我们尊重和悲悯的普通人生,以舞台人的个性世界,搭建起其特有的历时性的人物生活史和心灵史。
作为老一辈的秦腔丑角名家火烧天(贺少天),他所代表的是传统艺术的追求与坚守。业精于勤荒于嬉,精湛的技艺背后是不断刻苦练习的结果,是在各种精神力高度集中下练就的绝活儿。小小的戏剧舞动动作,火烧天的拿手好戏“毛辫功”,看似简单,实则需要调动自己头皮不断的律动,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能看起来活灵活现。轻松随意的舞扇子动作戏,干净且富有力量,是艺人在练功房埋头苦练的成果。独家技艺体现的是老艺人对舞台与观众的尊重,可这正是当代许多艺人所缺失的,同样的,作为艺人,不仅需要对待戏剧舞台艺术报以严谨之心,入世生活同样需要智慧,正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剧团众人都知道,世上的事,没有是火烧天看不明白的。丑角可以在舞台上嘻嘻哈哈,可若要在生活中做人,平常就不能嘻哈。戏是戏,只是一时的,而生活才是人永久的存在。当喜剧红火的时候,不在人前显摆,记得提携同行,耍丑也不能忘本。做人与艺术同样都是修行,没有人会是舞台上永远的赢家,“人生如戏”,生活亦是如此。
作为火烧天的传人,《喜剧》展示了贺氏兄弟两种不同的人生状态,贺加贝因为爱情从而陷入喜剧的魔怔,终以悲剧收场闭幕;贺火炬及时悬崖勒马,遵循喜剧本心勤练戏剧技艺,成为喜剧的新的可能。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中,人们承受着消费所带来的快感,但同时也被“价值观”所“消费”。时代带给人们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时代的开放给予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自由,但自由背后夹杂着的是不容忽视的生活焦虑。快节奏的生活,大众、通俗、娱乐化的文化背后时时流露着作家的忐忑不安的心态。时代让人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中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性,昔日的小跟班也会一夜暴富,为自己朝思暮想的角儿一掷千金;曾作为“背景板”的丑角转头成为万人追捧的明星,出入于更高阶层的社交场合。时代带来了福音,同时也引发了人的不安与焦虑。作家将时代的弊端与积习呈现在大众面前,但他没停留于表层的描述上,而是在大众在笑声中去提醒并更正。
贺加贝对万大莲近乎偏执的爱,让贺加贝沦为情欲的傀儡,这种情欲操纵着贺加贝作为人的意志。为了得到万大莲的爱,贺加贝陷入自己编织的情欲牢笼,甘愿成为受到“无形的手”所操纵下的工具人,任性的仅凭自己所认定的道德行为准则行事。为了能娶到万大莲,抛弃一直支持自己的妻子潘银莲,不顾一切去追寻自己心中的真爱。“想得的,得不到”是人类痛苦的根源。疯魔的爱让贺加贝丧失了人的价值观,没有了善恶的观念,做事行为没有底线,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浑浑噩噩,穷奢极愈,最终陷入“黑天鹅”事件,更是坠楼疯傻,这已然是一种悲哀。
贺火炬是与贺加贝截然不同的人格,用戏剧来说,加贝是“热料”,而贺火炬则是“冷彩”。尽管在戏剧舞台上贺加贝认为弟弟是不如自己的存在,但火炬练功开窍是比贺加贝要早的。丑角的“动作戏”,从“小翻”“死人提”,再到小磨三年的《时迁盗甲》,火炬总是尽心的努力完成父亲的教导。在前期,火炬总是在父亲和长兄的安排下演戏,没有自己的主见。可经过摸鱼儿的事件后,他开始冷眼旁观贺加贝的“三角恋”,在随着贺加贝喜剧艺德的逐渐堕落,他有了自己的自主意识,选择前往戏剧学院求学。在学院的生活是痛苦的,但也正是这些磨难,火炬加强了自身对丑角之道的追求,明白了何为人所需要的喜剧。懸崖勒马,勤练戏剧技巧,走出了不同加贝的喜剧之路,为未来的喜剧带来了希望。
《乐记》说:“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1]244“喜”为人带来欢乐、畅快的心情。喜剧,寓庄于谐,笑看人生。喜剧将普通人的生活习俗搬上了舞台,是照出生活百态的“镜子”;是“人从激情中解放出来,对自己的周围和自己存在永远进行明晰和冷静的观察”[2];是鲁迅先生说得“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喜剧是令人身心愉快的艺术,是人在笑过之后能引发深思的艺术。但当喜剧趋于低俗化与夸张化时,也就成了闹剧。
贺加贝的喜剧生涯,是赶上了电视喜剧的热度,踩在了时代的节点上,但他失去了对正向喜剧的判断力,走向了观众所需要的那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有些已经成为社会庸俗落后的东西,为了吸引观众,贺加贝还是拼命地给这些观众制造一种失去理智的笑声。不断地无下限的去迎合观众的低俗的喜好,随之贺加贝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逐渐地背离了自己生命的轨道,违背了火烧天为贺氏喜剧制定的喜剧底线,他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可他的荒诞的戏剧人生是值得反思的。失去理智的喜剧,导致了贺加贝命运的坠落,笑声的低俗化、娱乐化支配了“精英化”的西京市民的审美趣味,破坏了传统秦腔戏剧的美感。
当作为传统艺术的秦腔舞台上出现了流行音乐、扭起了外国舞蹈甚至是让小狗成为主角时,当现代都市的流行文化逐渐在不知不觉中取代了戏曲在传统民众的道德教化作用时,人们就会在这不知名的社会大潮中迷失自己,表演者也会忘却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为何物。这时,人们所面临的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精神困境: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前往何处。基于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作家将自己的写作初衷投注到普通人的人生。尽管潘银莲是一直活在万大莲“名旦”光环下的一个比较卑微的人物,但却是小说中活得最有光彩的人。潘银莲不是戏剧艺人,可她对秦腔戏曲艺术的素朴理解和生活观念,倾注了作家自身对生活与艺术的理解。
在镇上柏树给贺加贝的辞别信上,他写道:“弟妹潘银莲是个忠诚、本分、懂礼、谨严的好女人。美貌自不必说,单就为人,时下绝对是凤毛麟角,难有出其右者”。[4]134潘银莲老家在河口镇,虽不比西京城的现代繁华,但承接了民间传统生活现实和道德经验。无论生活艺术如何发展变迁,人也不能忘“本”。潘银莲并不赞同“梨园春来”低俗的喜剧观念,变相迎合观众的需求。在她看来,嘲弄普通人的不幸是错误的,长兄潘五福努力维持生计,赡养老人并供给后代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戏剧传达的不是普通人生存的无聊与空虚,更不是将普通人的痛苦嘲弄在舞台上,制造各种庸俗的噱头,而是承担民间的“教化”与“净化”作用。
今日之秦腔,不仅需要艺人有精湛的过人的独特的技艺修养,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道德底线。贺少天(火烧天)师从“热料”与“冷彩”两位大贤,更有过人的“硬功夫”,精妙绝伦的“辫子功”让他一出场就赢得观众的喜爱。他自小经历时代风云变幻,遍历世间冷暖,懂得世间人事起落,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在喜剧如火中日的时候,不忘提携剧团同事,教诲贺氏兄弟喜剧“三不为”“三加戏”“三不演”,深知“严谨,是一切艺术的生命线,包括喜剧”。[4]22作为“师爷”的南大寿,更是秉承传统秦腔艺术的教化功能,担当起时代伦理道德陶染人的处世之道的功用,让观众在喜剧作品中领悟“做人”的义理。这就需要研讨“喜剧的本质”问题,何为喜剧?贺火炬在农业学院学习技艺时,结识的研究中外戏剧的老教授认为喜剧是“一千个学者,会解释一千个喜剧和悲剧的本质,不可执其一端。强行把喜剧和悲剧解释成某种样貌,都是对喜剧与悲剧的简单化。”
陈彦认为“秦腔是对命运、人性的深层呐喊”,是“对弱者的同情抚慰,对黑暗官场的指斥批判”,更是“对善良的奔走呼告,对邪恶的鞭笞棒喝”[5]。喜剧之“道”,喜剧天分固然重要,需要承接和延续传统秦腔技艺,更需要历经世间冷暖的人生阅历。“为人”和“为艺术”不可或缺,时代发展变迁,传统技艺如何适应万千变化,这都是需要我们不断传承和研习的。
20世纪80年代,喜剧精神和悲剧精神的复苏带来了喜剧与悲剧的春天,喜剧负载着对社会伦理、社会秩序的重建的责任担当,关注社会问题,带上了哲学的含义, “依惯例,被众人嘲笑的,必然是荒谬绝伦的,将为社会所不容;引起欢快笑声的,必然是值得赞美的,代表了希望和未来”[6]。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公共理想转到日常生活,消费意识形态使社会价值转向实用,因此,一些学者断言这个时代是告别崇高与悲剧的喜剧时代,同时“喜剧”被牢固的与消费文化联系了起来。
喜剧以势不可挡之势迎来了它的春天,丑角走向了舞台中心。但在这个时代要获得某些物质存在,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传统戏剧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包括人性的精神道德危机,陈彦认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们更要坚守恒常价值,“恒常价值是指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所有民族,都为人类探索贡献了公平、正义、善良、仁爱、和谐、诚信、正直、民主、自由、互助、谦卑、礼让、怜悯、扶弱以及敬畏自然等价值谱系与道德范式,这些称为恒常之道。”[7]
在《喜剧》中,恒常价值是喜剧的“丑角之道”。火烧天提出的“三不为”“三不演”“三加戏”的演戏原则,认为唱丑是角儿一辈子的修行,“看着是唱戏,其实是唱道”。[4]389喜剧是幽默的艺术,嬉笑放诞的背后是浓浓的人生哲思;喜剧是语言的艺术,机趣缜密的逻辑展现的是艺术美感;喜剧是狂欢的艺术,表达的是人最大众、最通俗和最本质的人生诉求。剧作家南大寿是火烧天的“师爷”,经常给火烧天编的戏润色,在火烧天逝世后曾两次出山为贺加贝的喜剧创作剧本,但因为谨守自己的喜剧立场,认为喜剧是“高台教化,不能让台底下的笑声掌声牵着鼻子走。”[4]63戏词更是要“字斟句酌、精雕细刻”,民俗俚语的巧妙运用,会让戏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但他不愿为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所妥协,在他看来当今的喜剧就是“佛头着粪”[4]67。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能坚守自己的艺术道德底线,不为市场和金钱所妥协,火烧天和南大寿对戏剧艺术美感的守望,正是作家对人的恒常价值的坚守。
关于恒常价值的坚守,最不容忽视就是潘银莲这个角色。潘银莲一直是生活在万大莲明星光环下的一名普通女性,但她最终活得是所有人物中最精彩的。在红石榴度假村做服务员的时候,因容貌长相出众,经常受到好多领导、老板的“点名服务”,但她能恪守自己的底线,没有为金钱和权势出卖自己肉体和灵魂。贺加贝认为与潘银莲的婚姻有点像在演秦腔小戏《拾黄金》。《拾黄金》在秦腔戏剧中是乞丐“胡来”大梦之后明白踏踏实实生活和过日子才是获得“黄金”和幸福的真谛。可荒唐的是,贺加贝是在“演”,“戏中人”成了戏中人。但善良的潘银莲始终在家孝敬婆婆,为贺加贝打理剧场生意和照顾幼子,在面对镇上柏树的诱惑时,也能坚守本分,不为所动。潘银莲是出生在农村的普通女性,没有太多的知识背景,但她知道的是,喜剧不是贺加贝现在演绎的这样,传统的戏剧是“干干净净”的,是教人“积德行善”“行侠仗义”的。镇上柏树将夜壶故事搬上舞台,王廉举在戏台上讲脏话、怪话,史托芬将普通人的不幸作为笑话来说,这些都是不对的。在她看来,城中村巷子中,普通人演绎的《三娘教子》《祭灵》《河湾洗衣》等折子戏,都比成名的贺氏喜剧演的有意义。喜剧是在乖谬的境遇中显示小丑的各式各样的荒唐行径,于讽刺人性的同时讽喻时事,是戏剧对于普通大众的思想启蒙和精神引领。纵使是大多数缺乏一定的知识文化教育的人,也能明白做人的良知,坚守做人的底线。
“良知正,则嬉笑怒骂皆成喜剧;良知歪,讽刺、调侃、幽默,皆失之油滑,变味走行”。[4]334喜剧是严肃的艺术,没有人会是舞台上永远的赢家。要敬畏舞台,“戏比天大”,“在一出好戏中,‘笑是诗的成分。它的幽默与哀愁都属于虚构的生活,我们从中得到的快乐在于那些为我们理解力创造出来的东西,而不在于那些直接对我们情感发出的刺激。” [8]当代的喜剧是有相当多缺失的部分,观众笑是笑了,可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对于戏剧工作者来说,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喜剧是需要思想的,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这是我们要警惕和重视的。
从艺先修德,立德树人,站在戏剧舞台上的文艺工作者,要对舞台心存敬畏,一言一行都会给人民带来影响。真正的戏曲是在唱念做打中“汇千古中孝节义成一时聚散悲欢”,是对恒常价值的坚守,是人间倡导的公序良俗,是折射生命风华的反光镜。欢颜如炼,好的喜剧,带给人的笑颜不是一时的,而是在经历过磨炼后获得的愉悦且坚定的生活的勇气。《喜剧》是中国化的巴尔扎克式的悲喜剧,是洞察在人时代巨变下的世间万象,是悲悯世人世情的心灵史。
参考文献:
[1](西汉)戴圣编著.礼记[M].张博编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9:244.
[2](德)席勒.秀美与尊严[M].张玉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294.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再论雷峰塔的倒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92-193.
[4]陈彦.喜剧[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
[5]陈彦.坚挺的表达[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3.
[6]张琦.知识分子的精神断章:中国当代喜剧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8.
[7]陈彦.现实题材创作更需厚植传统根脉[N].人民日报,2013-2-22.
[8](美)蘇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95.
作者简介:
王怡,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