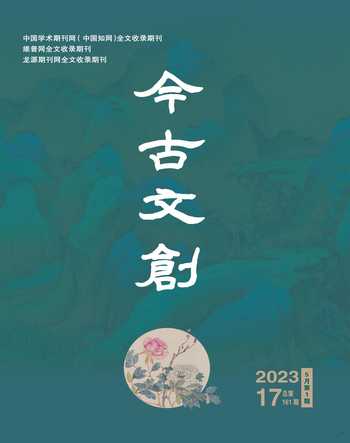堀田善卫:越境者的战争反思
2023-05-30高心雨
【摘要】 发表于1953年的《时间》是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堀田善卫的长篇小说,他以中国人的视角,以日记的形式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正面描写。本文以此为文本,着重分析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日本作家——堀田善卫对近代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以及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促使堀田善卫对日本战争责任进行反思的是他长久以来的越境经历,而《时间》则高度凝聚了堀田善卫对于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关系的反思与认识。
【关键词】 《时间》;南京大屠杀;越境;他者;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4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15
近年来,中日两国努力营造良好氛围期以改善两国关系。
但是,长久以来,在以否认南京大屠杀为首的日本历史观阻碍下,中日关系难以有质的跨越。虽然南京大屠杀是铁一般的史实,但是由于幸存者数量少,再加上日本政府对历史事实的否定、模糊和漠视。时至今日,调查数据显示仅不足三成的日本国民将南京大屠杀视为应该解决的历史问题。而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持否认、逃避与无视的态度,使得正面书写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文学作品就更加难能可贵。其中《时间》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以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视角直接描写的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长篇小说,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主要题材书写的日本长篇小说。
一、《时间》中的战争反思
在《时间》中,堀田善卫将主人公陈英谛一家安置于一座拥有三层楼、十九间房的空荡的大宅院中。这座宅院后来被日军情报官桐野占为己有。而这座宅院则代表了当时的金陵城,“在主人离去的这段日子里,不明就里的人们走进了这里”。这句话既是指桐野将主人公的宅院占为己有,也是指南京大屠杀时,日本军队将南京占为己有。
堀田善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中参考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小说中描写的很多场景都是在材料中证明的事实。堀田善卫作为侵略战争的加害方,选择了以被害方中国人的视角来揭露日军的暴虐无道,讲述中国普通民众受到的心灵创伤,这是作为一部日本战争文学作品的《时间》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视角的互换,既表明堀田善卫勇于正视历史和自我批判,也代表他拥有对于他者的想象力。
在主人公陈英谛的9月18日记录的日记中,他惊异于桐野对日本主导的一起爆炸案并不了解。他感叹道:“天下人知之事,除日本人外,他(桐野)不知也。”如此看来,南京大屠杀,恐怕也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知。如果不去抗争,我们连“真实”都无法守护,也无法将它告诉给历史学家。这也是堀田善卫当初创作《时间》的初衷。而创作《时间》的契机与一次南京旅行有密切关系。他在《反省与希望》一文中写道:“俯瞰南京城区,城区无疑是美丽的,但一种强烈的人去楼空的感觉却在我心中萦怀不去。这是一座空荡荡的大宅,空荡荡的古城。主人去了哪里……在主人离去的这段时间,不明身份的人们纷纷入内。关于中日关系,我的思考。对于东方命运的哀恸,愈益强烈,这渐渐演变成了我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悲恸,甚至是绝望。那个时候,我明确感到,中日关系、东方的命运这类庞大的问题已经与我自己渺小的人生、生存的苦恼连为一体了,这使我自己都感到相当惊愕。”
小说为展开对惨无人道事件的可信叙述,采用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南京沦陷后,主人公历尽劫难、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小说是由陈英谛在南京大屠杀前后的10个月左右的一篇日记写成的。
在按照时间梳理出来的情节之上,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自白使得《时间》变得更加真实可信。主人公通过不断地思考加深对于人性的见解,也从中树立了敢于直面残忍的现实的主体意识,并在心灵的伤痛中自疗。因此,对他者的观察审视,对自身境遇的体味自省,对哲学命题的深刻思考,如战争、生死、人性、道德等,在小说中占有很大篇幅,使作品有了“思想小说”之势。除了受害者这一身份外,主人公也有作为思考者的一面,同时也是作者自我思想的投射,堀田善卫借着陈英谛之口重复自问:“为何一定要将如此的惨状记录下来呢?明确地说,那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身的复生。”这里的“自身的复生”对于陈英谛来说,代表着他在目睹了人性的暴虐与邪恶之后,直面民族苦难,重新获得生存勇气的精神“复生”;但是对于堀田善卫来说,这代表着对作为加害方的自己,自觉承担起道义责任。不论是《时间》还是堀田善卫本身都受时代局限性的影响,但由于对历史的感悟和理解方式,注定了《时间》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与大屠杀受害者的实际感受还是有所不同的,与受害方的认知也永远无法完全吻合。但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在于叙事方式以及小说采取的视角上的独特。堀田善卫以超强的文学想象力,超越自我身份和视角的局限,让自己回到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直面这次属于中国的劫难,正视战争后果。以反思战争为前提的加害方和受害方的视角转换,它的意义就在于是一次对历史和战争思想深化思考的实践。所以《时间》是日本战后文学史上颇具深度的作品之一。
堀田善卫在《时间》中,不经意间把“我”转化为“我们”。这样的文字转换,更像是一种提示,提示那些不分国界的子孙后代该如何面对这段历史。《时间》中多次出现的“鼎”既意味着对历史的永久铭记,同时,它又是后人以自己的良知,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历史对话的媒介。
《时间》能够成为影响深远的战后文学作品之一,这与堀田善卫自身的文学素养以及自身经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中堀田善卫的他者意识、受害者意识,与他从小以来的越境经历息息相关。
二、堀田善衛的越境人生
堀田善卫(1918—1998)是日本的小说家、评论家,战后长年担任“亚非作家会议”日本代表,是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之一,作品先后获芥川龙之介奖、每日出版文化奖、大佛次郎奖、和辻哲郎文化奖等众多奖项。
“越境”原意是指非法出入边境和国境,但是,近年来在文学研究语境中使用的“越境”这一概念,早已远远超出了其原本的含义,具有了“跨界”或“越界”之意。中国学者长安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异邦异域书写、文学研究中的跨域跨国探索、作家学者的跨国跨域移动以及非母语写作、文本内部研究与文学外部研究的交错、文学与音乐美术电影的交融等都可称作“文学的越境”。
日本学者小泉京美认为如今的“文学的越境”研究有两个趋势,一个是肯定不同语言与文化间的越境,从超越各国文学领域的视角解读多语言、多文化的世界文学状况。另一个是在对一国主义的文学研究注入反省的目光的同时,为了不陷入伦理上裁决帝国主义侵略这样的简单结论,在留意多样的历史文脉和地域性的同时,进行个别作家以及作品的解读与评价。前者追求跨界和翻译带来的文学可能性,对文学环境的全球化发展表现出更灵活的应对,而后者则与之相反显得更加谨慎与怀疑。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越境”都是在复杂的交织中发展的,所以区分这两种趋势只是为了方便,但是要想复眼地把握事态,就必须同时掌握这两种趋势。
1918年出生的堀田善卫,因为家族从事的事业需要频繁接触到外国人,这让堀田善卫从小就身处充满多元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而这样的人生经历也培养出了堀田善卫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与异国他者进行对话的意愿。
堀田善卫中学时期寄居在美国传教士的家中,接触西方文化较多,并学习英文和钢琴。1936年,堀田善卫离开家乡来到了东京,在庆应大学求学期间,他发现,政治系里到处都是盲目崇拜德国法西斯、狂热支持日本对外战争的“皇国青年”,而一片冷清景象的法文系教室里,只能看见文艺青年三三两两地小声念着诗文。于是十分反感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堀田善卫很快地便从当时热门的政治学专业转入颇为冷门的法国文学科。转专业后的堀田善卫完全变成了学习象征主义诗歌等的西欧派。至此,堀田善卫与中国并无交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反感战时体制的日本青年知识分子在想尽一切方法逃避兵役,而堀田善卫也通过国际振兴会调查室申请到了外派上海的公函,并于1945年3月24日抵达上海。
这时候的上海正处于被侵华日军占领的时期,在被“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主导思想的意识形态管制下,上海一边实行“去欧美化”的文化政策,一边对当地的中国文化界又实行由军方主导的言论审查。而正是这种基于日方侵华战争需要的排他性言论管制损害了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原有的多元文化优势。此后,堀田善卫在上海街头遭遇了日本士兵欺辱中国新娘的一幕,令堀田善卫意识到自己既没有逃离战争,也没有远离日本。堀田善卫在《在上海》中提及这件事时写道:“战争时期,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面对时局的变化,总觉得自己是个文艺至上的人。而我的这个框架,在这个时刻被打破了。”
在这件事之后,堀田善衛又在上海亲身经历了对日本人来说非常具有屈辱感的日本战败,从此他开始反思这场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日关系。战败后,堀田善卫不愿意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最近陆续听到有关日侨遣归即将开始的传闻。我自己是一点也不想回国。比起回日本,我更想继续留在上海。如果必须要回去的话,那我就等到最后一趟船再回去。” 于是,堀田善卫就暂时留在了上海,一直到1947年1月才最终回到日本。
这一年多在上海的经历,对于堀田善卫在日本战败后的文学生涯乃至整个人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国以后,堀田善卫将他在上海期间的种种经历以及观察、反思结合在一起,陆续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以小说为主要形式的各种文学作品。堀田善卫也凭借1952年获得芥川奖的《广场的孤独》这部文学作品奠定了他作为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的地位。1947年之后,堀田善卫陆续发表的《波涛之下》《共犯者》《无国之人》《被革命的人》《祖国丧失》《彷徨的犹太人》《齿轮》《汉奸》《断层》《历史》《时间》等大量以中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足够证明堀田善卫一年多的上海经历存在的意义及价值,同时也是我们解读堀田善卫对中日关系的认识的第一手文献。
在这些作品中,《时间》出版后并没有引起日本读者的巨大反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也没有引起日本文学界的重视。而1989年,《时间》的中文译本得以出版,书名译为“血染金陵”,虽然这部译本中有许多部分错译漏译,但是它的出版为后来的秦刚译本奠定了基础,使得《时间》和堀田善卫的名字在国内渐为人知。
三、越境者的他者意识
堀田善卫与武田游历南京之时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九年,彼时的南京城的荒凉之景与日本人歌颂之景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让堀田善卫感受到这两者之间横跨着的是巨大的名为“时间”的鸿沟,为了尽力弥补这种差异,只能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因此,在《时间》中堀田善卫借主人公陈英谛之口说出:“人世的时间和历史时间,加重了浓度,加剧了流速,在他国异质时间的侵袭与冲撞之下,强迫人们瞬间便与相爱之人永久诀别……”这句话既点明了《时间》的主旨,也指明了小说名称由来的原因。《时间》想要强调的是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对于时间的不同感受:原本悠然自得的中国人、本可以随着时间流逝,在平静悠长的日子中慢慢形成中国独特的历史,却在日本这本不同于中国时间的蛮力碰撞下,被迫让人们在一瞬间就体验到了与亲人骨血的生离死别。而这种痛苦只有日本人抛弃日本“时间”并且站在中国的“时间”角度,才能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堀田善卫希望通过这种与其他日本战争文学作品不同的他者视角,将日本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加害,自白于人类历史当中。如此一来,日本的这种加害不会因为受害者的逝去而消失,也不会随着时间的风化而飘散。
堀田善卫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是未来,日本与中国关系,绝非只是国际问题,而是与每个日本人都息息相关的国内问题。如果日本国民不能从内心去感受每个因为战争而失去生命的人,那么日本永远不可能得到受害国家的原谅,也永远不会迎来属于日本的真正的美好未来。
南京大屠杀——深刻于中国历史与每一位中国人民内心中,而这却是日本战争文学作品当中至今没有面对也不敢面对的话题,而描述南京大屠杀这一时间的《时间》则显得难能可贵。特别是《时间》启笔于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的第二年。也就是说,《时间》是在日本自以为即将完成战后重建,已经摆脱战争阴影、是在全国人民都准备告别战争、迎来新时代的氛围中完成的。堀田善卫想借这种形式的小说来不断提醒国民,如果没有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反思战争,并清算战争责任,日本则永不可能向战争告别,也永不可能摆脱战争带来的阴影。在中国总共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的前后经历,让堀田善卫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与大部分日本作家迥异的写作特质。使他能够借助外界的他者视角,在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的加害,对中国人民的加害,从而反省日本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
截至2022年6月7日晨,幸存者余昌祥(95岁)辞世。目前,在南京侵华日军受难人援助会登记在世的幸存者只剩下55人。在此背景下,分析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日本文学作品以及日本知识分子的战争反省,有利于完善日本人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认识以及进一步促进中日关系的和谐发展。历史正在不断远去,但维护历史真相的脚步无法阻挡。铭记历史并非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谋求发展。但是,传承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历史记忆,引发日本人对战争责任的自我反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杨秀云.近20年来南京大屠杀历史在日本的传播及日本民众认知状况分析[J].档案与建设,2020,(05).
[2]徐静波.《时间》:堀田善卫对南京大屠杀的解读及对中日关系的思考[J].日本问题研究,2013,27(04).
[3]堀田善卫著.时间[M].秦刚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4]柴红梅.政治地理学视阈与“越境的”日本现代主义诗歌时空叙事——以安西冬卫的诗为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6).
[5]长安.“越境”的中国文学[J].书城,2018,(7).
[6]小泉京美.〈越境〉から〈跨境〉へ,『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J].2014.
[7]陈童君.在华日侨文人史料研究——堀田善卫的上海时代[M].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8]堀田善衞.上海にて[M].东京:集英社,2008.
[9]紅野謙介.堀田善衞上海日記 滬上天下一九四五[M].东京:集英社,2008.
[10]陈童君.《时间》与堀田善卫的战后警世钟[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03).
[11]堀田善卫,陈童君.反省与希望[J].世界文学, 2018,(03).
[12]秦刚.堀田善卫《时间》:用“鼎的话语”刻写复生与救赎[J].文艺报,2017,(004).
作者简介:
高心雨,女,汉族,江苏扬州人,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化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