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林外史》中的逆反式写作策略
2023-05-30林雨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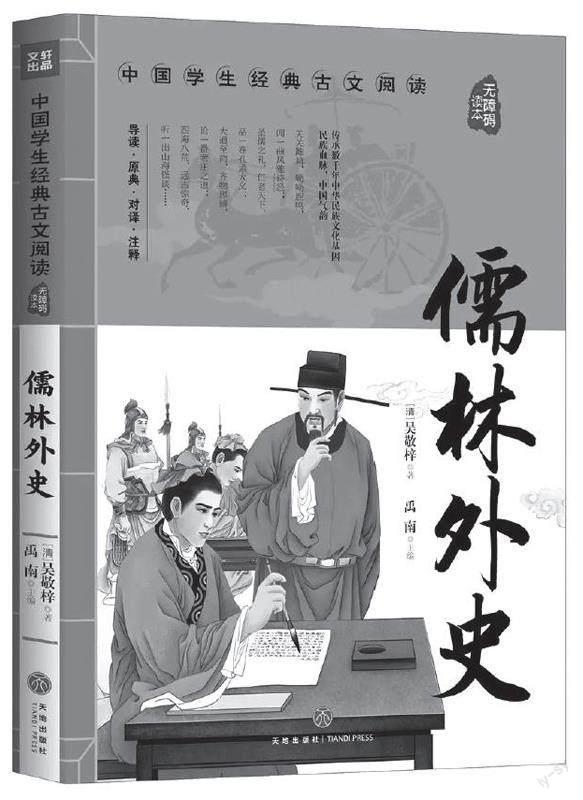
清初社会的繁荣昌盛,只是一种表象,一种相对于战乱和朝代更替期间社会混乱、经济凋零、民不聊生状况而存在的暂时稳定状态,如果从深层次去看待问题,那么这种“繁荣”的现象并不是社会制度本身的“优越”所造成的繁荣。从春秋战国时期就逐步形成,并从秦始皇开始确立的封建社会制度,到清朝时“已处于即将走完它的漫漫历史长途的阶段,其腐烂衰朽已达到非垮不可的地步。”[1]而所谓的“康乾盛世”也只不过是封建社会即将衰亡的回光返照而已。在所谓的“繁盛”背后,是难以言喻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间各个阶层的对抗,有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反清势力与清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有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剥削与反剥削的矛盾,有统治阶级中满族官僚与汉官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无法得到调和和解决。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我们看到的是18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虽然吴敬梓把故事安排在明代,但小說所反映的时代却是清代前期,特别是康、乾时代的社会现实,这是独属于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短暂的“繁荣”。功名富贵本并不单单只是纯粹的利禄,它曾带有伦理和信仰的色彩,效忠皇帝、忠于国家与获取功名富贵是相互吻合的。但在吴敬梓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制度早已走过了它的青年和壮年,已经到了垂死的阶段,一切都在散发着末世所特有的陈腐、破旧的气息。伦理和信仰日趋颓侵,内在的建功立业的意蕴已剥落殆尽,徒有外在的利己主义的空壳。[2]
一、《儒林外史》中展现的逆反描写
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移家南京后的吴敬梓在那生活了有二十一年之久。在“坚卧不赴”雍正乙卯(1736年)所举行的博学鸿词科后,吴敬梓开始反思从前的生活,生平碰到的一幕幕不公对待又一一在眼前掠过,这种愤慨的思绪,使小说处处闪烁着批判的火花,时时渗透着辛辣的讽刺。活跃的江南思想界,明清实学思潮的余波,都对吴敬梓的眼界开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使吴敬梓从自我的不幸中跳脱开来,进而将目光转移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不幸,对某些乡绅高官的不满,转而变成对异化的社会和扭曲的制度的不满。
虽然吴敬梓能在小说中比较有节制地控制自己情感的外露,然而,人的克制总是有限的,他的激愤之情仍不免时时地表现出来,有意识地对立,强烈的愤懑,很自然地造就了一种逆反精神。就《儒林外史》而言,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有关逆反式的描写。
(一)做官与举业
人们常道做官好。文人在那个时候更是把科举视为唯一发达的途径,一经考中,便意味着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一旦名落孙山,就只能在社会最底层穷困潦倒。吴敬梓就偏要表示:“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德行若好,就没有饭吃也不妨。”这些绝对化的调子,正是逆反精神的一个特征。在《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了举,范母喜极而死;鲁编修升了侍读,喜极发病,顿时呜呼哀哉;蘧景玉年纪轻轻就死了,他的父亲蘧太守说:“只怕还是做官的报应。”王惠官职升得快,俨然“江西第一个能员”,可好景不长,吴敬梓立即便给他安插了一个降顺宁王的称号,王惠在事情破败之后仓皇逃走,从此更名改姓,削发为僧,只有遁入空门的惨淡结局;荀玫仕途得意,一帆风顺,小小年纪便中了进士,作者便给他设计了一个“贪赃拿问”的结果,并通过金东崖之口,得出“旦夕祸福”的结论。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也是文人举业做官的最主要途径。尤其是在清代,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模式,并发展到了极致;同时,科举制的弊端和罪恶也暴露到了极致。许多文人一辈子揣摩八股制艺,到老也进不了学,或虽进了学,但考不上举人、进士,自己则反而变成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担的废物。为了它,许多文人丧失了自尊,虚度了年华,变得更蠢、更贪、更侥幸、更无耻。做官表面上的风光与最后做官下场的落魄,在吴敬梓逆反式的描写中变得滑稽可笑。正当被描写的人物风光得意之时,作者突然安排的一个情节,让其发生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通过逆反式的描写一下子把被描写对象捉弄得狼狈不堪,从九霄云外跌入万丈深渊,吴敬梓之意,不言而喻。
(二)恭维权势
人们常常恭维权势,鄙视失败者,吴敬梓一反常态,偏要蔑视权贵,同情失势者。王惠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当他失势后,吴敬梓就让其安然逃走,并让蘧公孙给他二百两银子。王惠的后半生,是一个凄惨的受害者的形象。臧三为了巴结王知县,要让杜少卿这个世家子弟去会会王知县,杜少卿对王知县表示出了极大的轻蔑,说像王“这样的知县不知见过多少”,“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并要臧三转告王知县“叫他把梦做醒些!”但是,时隔不久,“县里王公坏了,昨晚摘了印,新官押着他就要出衙门,县里人都说他是混账官,不肯借房子给他住,在那里急得要死”。杜少卿听说后,立即叫人转告王知县说:“王老爷没有住处,请来我家花园里住。”不一会,王知县纱帽便服,来到杜家,对杜少卿十分感激。杜少卿客气地安慰他说:“老父台,些小之事,不足介意。荒斋原是空闲,竟请搬过来便了。”杜少卿对王知县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王得势时,众人巴结他,杜少卿偏骂他是“灰堆里的进士”;王下台了,狼狈不堪,杜少卿反而改称他为“老父台”“王老爷”,并热情地请他来家中住,一切都是反常人之道而行之。
锦上添花的事情偏不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却一定要做。王知县的人品没有,但他的地位变了,从一县之主一下子变成一条丧家之犬;而杜少卿对他的态度,却由轻蔑冷淡转变为热情相待,这也是吴敬梓的一种逆反精神在起作用。杜少卿性格中最根本的东西,也是吴敬梓性格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弃绝功名富贵,像他所钦慕的魏晋名士那样,无拘无束地生活,不趋炎附势,不落井下石,为人处世,实实在在,光明磊落。吴敬梓看到了儒林上流社会丧失信仰和丧失道德,所以他在小说中时不时写出“势利之徒”的对立人物,以逆反式描写道出那个时代人们骨子里对功名富贵的信仰,并严词厉色揭露了这种悲剧性的社会本质。
(三)以自我独特方式进行有限反抗
《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写了一个虞华轩。虞华轩是书中的一个正面人物,经史子集,礼乐兵农,无不精通。虞华轩痛恨五河县势力虚伪的社会风气,但却又无可奈何。他和书中其他一些被作者称誉的正面人物不同,虞华轩并不是一味忠厚,而是懂世故,有心计,会捉弄人,自然,他捉弄的是小人。他好像是在一种逆反心理的支配下,倒偏偏要叫那些势利的人吃些势利的亏。
虞华轩手里苦积下一些银子,“便叫兴贩田地的人家来,说要买田,买房子,讲得差不多,又臭骂那些人一顿,不买,以此开心。”兴贩行行头成老爹就是十足的势利眼,只认方府、彭府,认为这两个府请他吃饭便是他最大的荣耀。虞华轩摸透了成老爹的毛病,精心设计了一场恶作剧。他先请唐三痰打听好“方家哪一日请人,请的是哪几个。”然后,伪造了一张方家的请帖,“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觉的房里书案上。”势利愚蠢的成老爹果然中计。到了那天,成老爹早早地就去方家,一本正经赴宴去了。谁知到了方家,“也不见一个客来,也不见摆席”,只好有口无心地和方老六乱扯了一会废话,扫兴而归。白走一趟倒也罢了,虞华轩又为成老爹设计了第二个陷阱。他故意在同一天,大请宴席,准备了鱼肉酒水,并特意将这一消息预先让成老爹知晓。于是,成老爹在方家败兴而归后,怀着猜疑不定的心情,又算计到虞华轩家里吃现成酒席。谁知虞华轩一见成老爹,马上就说:“成老爹偏背了我们,吃了方家的好东西来了,好快活!”以此抢先一步来封住成老爹的嘴,不但不给他吃,还特意让人“泡上好消食的陈茶来与成老爹吃。”虞华轩和几个客人“大肥肉块、鸭子、脚鱼,夹着往嘴里送。”虞华轩他们越吃越尽兴,成老爹却越看越上火,“气得火在顶门里直冒。他们一直吃到晚,成老爹一直饿到晚。”
虞华轩又假说要买田,“叫小厮搬出三十锭大元宝来,望桌上一掀。那元宝在桌上乱滚”,引得“成老爹的眼就跟这元宝滚”。要成交的那天,虞华轩又故意在厅上“捧着多少五十两一锭的大银子散人。”他预先声称事成之后,要给成老爹五十两报酬,结果却又说“那田贵了!我不要!”“成老爹吓了一个痴”,“气得愁眉苦脸”。
虞华轩作弄成老爹的几次恶作剧,对成老爹并没有造成多大损害,对彭府和方府更是没有造成一根汗毛的伤害。他只是为对立而对立,以对立为快乐。身在恶俗地方,无可奈何,激而为怒,寻求小小报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反抗,这不正是一种逆反精神吗?
二、封建社会的逆反者
逆反一词有不合时宜的意味,但是在吴敬梓所处的风雨如晦的士人社会中,逆反之人往往是独具眼光的社会观察家。之所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批判性小说,不仅仅因为小说批判封建制度和醉心于功名富貴的士人,还因为小说的作者吴敬梓本人就是封建社会的逆反者。
(一)逆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吴敬梓,成长在“科第家声从来美”的科举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早年热衷于科举举业。由于吴敬梓的生父和嗣父相继去世,以及嗣父背后的无故免职,使青年吴敬梓初步体会到社会的腐朽昏聩,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昏暗的时代是难以有出路的。吴敬梓的生活面临一个转折,从此开始明显地踏上了逆反的路途。
之后,多种矛盾集于一身。首先是在吴霖起去世后爆发起来的家族遗产之争。吴敬梓的族兄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描述当时的情况:“……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身后何含!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刘翁为人好心事,谯翛与我忧如惔。外患既平家日削,豪奴狎客相钩探。弟也跳荡纨绔习,权衡什一百不谙……”[3]从这可以看出家族之间争夺遗产的激烈程度。其次,几乎与此同时,吴敬梓岳父家里也发生变故。层层的打击,让其妻陶氏不堪重负和悲伤,终于病倒,不久也撒手人寰。这些变故,使吴敬梓经历着别人难以想象的悲痛,这种打击对于个人来说无疑是残酷的。
吴敬梓在其二十九岁时,参加了当年的科考,他在科考前后,与几位朋友相聚饮酒,且“酒后耳热语諵諵”,大发牢骚。后来被人认为“文章大好人大怪”,虽然“录科”取了,但在次年的乡试中终被淘汰下来。这对于此时期的吴敬梓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父亲过世,族人争产,家族衰败,妻子病故,科名蹭蹬,在郁闷激愤的心境中,吴敬梓开始沉湎声色,由于沉湎于声色之中,交往于文士之间,加上遇贫即施,花费极大,吴敬梓便开始出卖祖上留传下来的田地房产。吴敬梓对梨园优伶情有独钟,并于“家难”后,经常在家中宴请宾客,邀约戏班子来唱堂会,有时竟会通宵达旦,丝竹管弦之声于外,男伶女妓,喧闹歌舞,不分上下。这样的生活很容易招致非议。就如金两铭说的“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少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4]在上述种种遭遇下,身为故乡人所不齿的败家子,吴敬梓无颜继续待在全椒。1733年,吴敬梓携续弦夫人叶氏与乡中亲友一一告别,离开了全椒,移家南京。
1735年,清帝下令再次举行博学鸿词科试,当时唐时琳、郑江就将吴敬梓推荐给安徽巡抚赵国麟。1736年春,吴敬梓乘船从南京赴安庆参加预备考试,结束考试后,他沿江而下,游览名胜,拜访友人。回到南京后,吴敬梓感到同去应考之人,有些是欺世之徒,不屑与他们为伍,而自己此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便辞去了赴京参加廷试的举荐。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吴敬梓后来在《丙辰除夕叙怀》《元夕雪》两首诗中都有抒发为此而感到懊恼的情绪,直到看到吴檠等人虽赴京考试却未被录取,心里对统治阶级笼络士人的手段以及对科举功名才有了新的认识。吴敬梓也从这些文士的落第中了解到本次“鸿博”之试的内幕,即弘历帝举行此科是为了延揽虚誉;而主持这次廷试的张廷玉、鄂尔泰这两位汉满大臣早已各树门户,彼此水火不容。人主为虚誉,大臣为结党,广大士子必然会成为他们玩弄权术下的牺牲品。这一可怖现实,使吴敬梓深受刺激,也深受教育。应当看到,从此开始,吴敬梓对封建统治者实行的科举考试、博学鸿词科考, 有了进一步的清醒认识;他的绝意仕进, 并批判科举制弊端和封建礼教虚伪、不合理的叛逆思想,开始占据自己思想的主导地位。对科举失望后,吴敬梓唱出了“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内家娇》)的心声。吴敬梓的激愤情绪最终形成了逆反精神,并从封建的泥沼中完全挣脱了出来。[5]
(二)嵌崎磊落 洁身自好
吴敬梓呕心沥血浇铸而成的《儒林外史》是他对社会问题和士人群体命运反思的结晶,全书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展现了作者对封建末世的严峻批判与对心目中理想境界的探索追求。通过对《儒林外史》里的文士科举描写,揭示了其精神状态和日常生活,并以文行出处和功名富贵为核心,站在俯视整个封建文化的高度,对科举制度下的儒林群像和儒林心态作了深刻的剖析,既是一部儒林丑史也是一部儒林痛史。
在作品中,吴敬梓的逆反精神并不是单纯的情绪化产物,而是一位有着良知的正统儒生所发出的来自内心的呼喊。在吴敬梓逆反精神的整个过程中,他逆反的着眼点由对封建宗法家庭转向对社会,思考的范围也由个人自身不幸的命运扩大到整个儒林士人的出路,甚至是民族前途。《儒林外史》关注文人的前途命运,并借第一回王冕的口中直指出对一代文人的担忧。对“礼部议定取士之法,”王冕道:“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针对吴王疑虑的“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问题,王冕就提出“以仁义服人”的治国方略:“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王冕奉行正统儒道,修身齐家,强烈主张治国要以仁义服人,反对酷虐百姓;士子务必讲求文行出处,不可一味追求功名富贵。
同时,吴敬梓对社会的逆反精神也深有体现。吴敬梓的生活年代是改朝换代后的社会逐渐稳定的时期。但是不少知识分子的骨子里还流淌着遗民的思绪,吴敬梓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不满汉家的天下由满人占据,又受困于当时严苛的“文字狱”,只能在文章中婉转地表达出自己的愤慨。《儒林外史》假借明朝故事,实为批判清朝制度,吴敬梓虽为封建文人,却不齿同流合污;同时,他自觉担负起拯救一代文人之厄的重担,犹如一鼎警钟,警醒着深受残害的文人群体。吴敬梓的逆反精神超越了同时代的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限度,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有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意识。他作为一个旁观者,具有崇高的责任心,做到“独善”与“兼济”的完美结合。在高压的社会中不随波逐流,在社会的泥沼中洁身自好,“清醒”却不“清闲”,“独善”却不忘警示他人,他在那个黑暗昏聩的时代中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实为封建社会的逆反者,嵌崎磊落的殉道者。[6]
三、结语
在吴敬梓的筆下,有着不同的社会生活面,不同人物的性格,这些都集中到生存在清朝初期统治阶级实行的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的广大士人身上,书中众多人物形象,所行之事,所收获的结果,实为吴敬梓有意操控,风光无限的人物可以转眼狼狈不堪,饱受侮辱和嘲弄的下层人物也可以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人们待人接物的前倨后恭,跌宕起伏的故事结局,全都巧妙地经由作者笔下的逆反式描写,打破常规,让人并不能顺着惯性思维明晰接下来所发生之事。吴敬梓之所以为对立而逆反,其根本原因在于吴敬梓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他把罪恶与堕落的责任主要归于社会制度,特别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灵魂的扭曲来源于社会环境的扭曲,思想的病源来自社会的病态,《儒林外史》中大量精彩纷呈的逆反描写,使读者能从刻板印象中解脱出来,转向对于社会、对于制度的深思。
作者简介:林雨婷(1998—),女,福建莆田人,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注释:
〔1〕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2〕张国风.《儒林外史》试论[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
〔3〕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清〕金榘.《泰然斋集》卷二附.
〔5〕陈美林.《儒林外史》研究独断与考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赵肖.透视《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意识人生[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9):4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