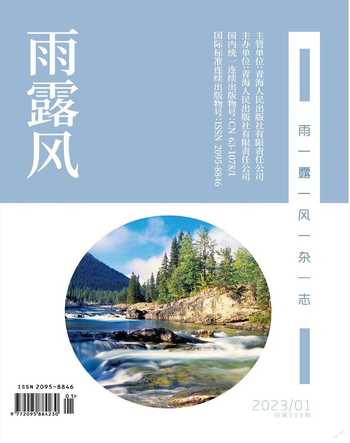歌剧选段《一首桃花》的联觉分析
2023-05-30张倩王建国
张倩 王建国

《一首桃花》分别要从诗词、歌剧、唱段三个部分谈起。《一首桃花》既是我国著名作家、建筑学家林徽因的诗词,也是我国首部小剧场歌剧《再别康桥》中林徽因一角的主题唱段,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周雪石作曲。歌剧《再别康桥》采用徐志摩同名经典诗歌,取材并改编于20世纪初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陆小曼四人的文坛故事。唱段《一首桃花》是歌剧的第五场景,故事发生的背景正是林徽因27岁时,她因工作环境的恶劣加之体质瘦弱得了肺结核,不得不在香山双清别墅养病。本文将从联觉的角度探析歌剧选段《一首桃花》。
通过大量的实验观测,联觉(synesthesia)被认为是一种心理学现象,也被认為是神经学现象。从心理学上讲,联觉是人类心理活动的自然规律,人之各种感觉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的心理现象,即人在单个感官的刺激作用下所触发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感觉的现象。联觉不仅被证实与艺术创造力紧密相关,还应用于身心残障人士(如盲人、自闭症儿童)的日常训练与针对该群体的产品设计,解决感知觉代偿转换不足以及感官交互方式单一问题。
联觉作为一种跨感官通联体验,也是音乐音响与其表现对象之间的中介环节。我国音乐美学家、音乐教育家周海宏教授在其博士论文《音乐及其表现的世界》中详细阐述了对音乐音响与其表现对象之间关系规律的心理学研究。他将联觉的分析概括为六种与音乐听觉相关的联觉对应关系:与音高相关的联觉、与音强相关的联觉、与时间相关的联觉、与时间变化率相关的联觉、与紧张度相关的联觉、与新异性体验相关的联觉。
一、音长的联觉效应
节奏是音乐时间的运动态,强调时间的长短。《一首桃花》A段“桃花/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中:“桃” (两拍时值)、“春” (两拍时值)、“话”(三拍时值);B段的“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中:“看”(三拍时值)、“那”(一拍半)。长音表现出林徽因对桃花乃至世界万物之美的执着与追求,仿佛陷入其中,久久不能自拔。在联觉的感官体验上,长音、慢音在运动属性上有暂时静止的效果,具有开阔、舒畅的空间延展度,使听者有内心安静、平和的情绪体验,最终产生端庄、深情、稳重的情感体验。此外,从时间变化率来说,此处起音速度是慢起,给人以柔软、平坦的触觉,所表现出的角色特征也是温柔、宽容、和善的,从而成功塑造出含蓄与柔婉、典雅与多情的女性形象。
A段的“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中,“凝”使用了附点八分音符与十六分音符,“是一些”使用了四个十六分音符,“字眼”使用了前十六后八等等节奏型,大量短音的设置位置与诗歌文本相契合,将桃花的娇艳与精美衬托得呼之欲出,令人怦然心动。相对于长音而言,短音就具有拥挤、局促的空间延展度,在事物运动的属性上来说是动态的、变化多样的,给人以“赶”“激动”“兴奋”的情绪体验。与此同时,变化多样的节奏型也是短音联觉效果的体现形式。
二、音高与音强的联觉效应
毋庸置疑,“高、低”是用于描述空间位置与地面距离的形容词,“强、弱”是用于描述物体形状与体积、事物变化程度、活动范围、对主体的意义、心理感受等事物或情境。音高与音强各有不同的联觉对应关系,但都涉及物体质量和形状这两方面的联觉。高音体现的物体质量轻、飘,物体形状小;低音体现的物体质量重、沉,物体形状大;强音体现的物体质量重,形状大;弱音体现的物体质量轻,形状小。简言之,音高与其联觉的物体质量、物体形态成反比,音强与其联觉的物体质量、物体形态成正比(见图1)。
有趣的是,作曲家在处理音乐的过程中,从未机械遵循声音联觉本身的规律,而是把轻、飘的高音强处理,重、沉的低音弱处理,使得音乐在表现性上给人带来更丰富的审美体验。《一首桃花》中,开头部分“桃花桃花”:“桃”的高音(d2)和“花”的低音(g1)在视觉亮度上形成了先明后暗的对比,在情态活动上形成了先相对积极后相对消极的对比,在物体质量上是先轻后重的对比,而此刻作曲家对高音的“桃”是强处理,“花”的低音是弱处理,于是“桃”的强音和“花”的弱音产生的空间距离的联觉是先近后远,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三、紧张度的联觉效应
纵观《一首桃花》,几乎每个乐句是整体下行,局部上行。通常旋律上行使人感觉积极、兴奋,而旋律下行使人感觉抑制,这样的联觉效应营造了淡淡忧伤却不至于悲戚的情态,这与林徽因在香山双清别墅养病的真实情况相契合。无论是旋律上行还是下行,在旋律进行中,存在少部分的高紧张度,而协和性是影响紧张度最重要的原因。“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的“看”(g2)和“那”(ba2)是小二度上行;“在三月的薄唇边”的“在”(be2)和“三”(d2)是小二度下行。音乐音响的紧张度与人的心理体验的紧张与松弛具有成正比的对应关系,然而,这种高紧张度不是持续的,随即在接下来协和的低紧张度的音程里得到缓解。高紧张度音程的少量使用“增加了体验的丰富性和微妙性,避免了过于单纯的空泛感”。[1]局部的高紧张度不会过分影响到整体的歌曲风格,整体的纯净、松弛、低密度表现出林徽因清新脱俗、绵绵深情的女性形象以及她对生活、自然的热爱之情与从容态度。
四、联觉对演唱者的启示
声乐表演的最终目的是带给听众美的享受。从声乐表演到作品欣赏至少要经历两重联觉效应——演唱者自身的联觉效应以及听众的联觉效应。
就音乐欣赏角度而言,由于音乐本就是能产生明确审美反应和情绪体验的艺术,而联觉效应的核心在于让身体说话,即人们以“耳朵(局部)—听觉”与“身体(整体)—体验”一并作为最直接的方式面对音乐、迎接音乐、感受音乐,从而避免去凭借文学化、美术化等非音乐的方式舍近求远或是弄巧成拙地解释音乐,造成“听众在音乐中无法听出解说者指明或暗示的内容,于是广大听众就认为自己不懂音乐,从而更觉得音乐‘太高深,难以接受,严重地忽略了什么是音乐传达给我们的,什么是我们赋予音乐的”。[2]周海宏努力打破表演者与欣赏者之间的隔阂,并且告知读者不必为音乐理解“加码”,真实且多元地看待音乐——感受到什么即什么。这一阐释是音乐审美的“祛魅”,是对音乐本体的反思和追问。
就音乐表演的角度来说,实现演唱者与欣赏者的同步在场,营造出一个双向交流的、彼此互动的完整的审美空间是实现有效审美交流的关键。细腻、精准的表演和表达考验了歌者自身对联觉效果的理解,意识到这一点,歌者必须更加清晰的审视对作品的处理。
还是基于《一首桃花》探究。首字“桃”是阳平声调,即二声,需加入倚音的技巧以避免容易唱成一声的直白感。“桃” 字在演唱时,舌尖点到上颚后立即送出声音,要注意字腹,即“t-a-ao”——先说到韵母“a”再快速过渡到“ao”,這样声音能够靠前且容易打开。长音的“桃”在产生的联觉效果上也更能做到暂时静止的效果,具有开阔、舒畅的空间延展度,使听者有内心安静、平和的情绪体验,最终产生端庄、深情、稳重的情感体验。开篇的这两个“桃花”彰显意境,在重复两次的“桃花”中,两个“桃”的处理是相对强的,两个“花”字要唱成弱音,显然弱音对气息控制力和表现力的要求更高,在强弱对比中体现主人公的感慨之情。此外,两个桃花的处理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桃花”要在语气上更强调。
“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中,有十六分音符、八分音符、四分音符、附点八分音符以及附点四分音符等多种节奏型交错使用,要求在语句完整连贯的基础上,在舒缓递进的感觉里还要有充分的流动感。
“朵朵露凝的娇艳”里,最难唱的字是“露”,因为在八度预备后“露”是最高音,且“lu”容易把字“咬死”,原因就在于归韵时候从口腔开度说,u的口腔开度小、从色彩上说,u较其他元音是最黯淡的。所以,在演唱过程中,可以把“lu”往开口音“la”的倾向上唱。同时需要避免的是,许多演唱者很容易全身铆足劲儿在此处发力,给人“重”“急”“用力过猛”的不适感。
“含着笑”要与前面三拍的“息”相连,一气呵成。“含”也是“h-a-an”的发音过程,在字正腔圆和腔圆字正中达到统一。同样,“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的嘴唇不要用力,先找“a”母音的腔体,然后再加字头“k”,完成完整的k-a-n的归韵。“看”还需保持上口盖的抬起以打开喉咙,在建立空间感的基础上,切忌使出全力,尽可能松弛、自然,于内部依然保持在腔体里,于外部依然保持在氛围里。
联觉作为经得起逻辑推敲且通过实证获得现象属性的研究,能够使声乐表演者脱离朴素、盲目的音乐感受力,严谨按照音乐表现规律,善于思考地去处理音乐作品。对于演唱者来说,更是强化审美体验,获得了演唱上的明确的表现性。同样是演唱歌剧咏叹调《一首桃花》,不同歌者的理解、处理都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只有歌者对作品“敏感”起来,充分意识到每处旋律与音高、音强、音长以及紧张度等因素对应的联觉关系,且经过反复对比、细细揣摩把握好“度”,努力做到真实性与创造性相统一,技巧与表现相统一,才能演唱出“韵味”和“情境”,才能引领听者进入别有洞天、引人深思、耐人寻味的艺术境地。
五、结语
无论是作为表演者还是欣赏者,联觉活动仅仅是身体活动中感觉活动的一部分,而作为联觉活动的承载、中介的身体以及身体间性有着更大的视域。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强调了“思”与“在”的同一性,却忽略了分离的绝对性,走向了唯心主义。梅洛·庞蒂提出的“身体间性”超越了“身心二元论”弥补了笛卡尔哲学的矛盾与分裂,通过“身体”与自身、与他人、与世界实现对话和交互性作用,共同存在于一个整体中。胡塞尔的现象学派主体间性指出主体间性代替了主体性的个体部分而表示的是群体性,否定孤立个体的概念而实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互和共存。而“身体间性”同“主体间性”的相同点在于二者同为生长域,联觉正是各个感官的同时作用以及表演者和欣赏者的双重联觉的生发交互。按照伽达默尔的阐释,既然交互主体性是理解的先决因素,文本、读者和作者三者之间能够构成效果历史,那么与之类似形式的曲谱、歌者、听众三者之间一定也能构成效果历史。正如历史是历史与对它的理解的统一体,音乐表演是歌者与听众的统一体,是剧院这一场域中双方联觉的统一体,更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表演者深刻理解身体间性的意义才能实现与欣赏者的有效交流,实现剧场演唱里的效果历史。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声乐艺术中的哲学思维(YCX22054)
作者简介:张倩(1995—),女,宁夏银川人,回族,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艺术硕士,研究方向为声乐表演与教学研究。
通讯作者:王建国(1962—),男,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声乐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声乐教学与研究。
注释:
〔1〕周海宏.音乐与其表现的世界 对音乐音响与其表现对象之间关系的心理学与美学研究[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2〕周海宏.音乐何须“懂”——重塑音乐审美观念[J].发现,2007(2):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