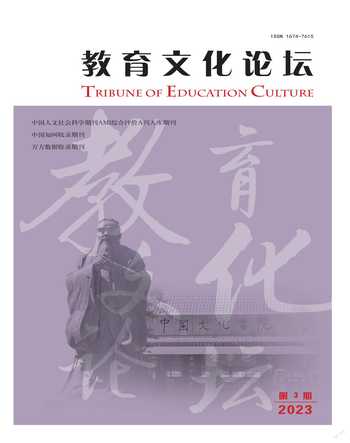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立场、价值与路径
2023-05-30周晔何畔
周晔 何畔
摘 要:建设乡土课程是乡村学校阻遏“离土性”冲击的必要路径。在乡村振兴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要坚持既回归乡土又面向未来的立场。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有利于践行在地化发展理念,赓续优秀乡土文化根脉,助力乡村学校高质量发展,增强学生的乡土认同感。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路径应为:明确乡土课程建设育人和结合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目标,通过选择适宜课程内容和协调课程内容组织以完善乡土课程内容体系,转变课程实践观念和优化课程实践过程以实现乡土课程实践变革,构建多主体参与的乡土课程建设共同体。
关键词:乡土课程;课程建设;乡土性;乡土文化;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3-0036-11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3.00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在“十四五”时期为促进乡村文化振兴,要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把乡土特色文化融入乡村建设。但在城乡教育一体化浪潮中,乡村学校教育因物理空间上移、教学内容城市化、学生精神情感背离乡村等问题呈现“离土性”趋势,导致当前需直面乡村文化根脉如何在濒临断裂中重建自身,以及乡村学校教育受到“离土性”冲击等重大问题。显然,乡村学校教育既不应该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盲目追求城市化,也不应该无视城市化进程而陷入乡土性的浪漫主义想象中。需明确意识到,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和乡村教育近年来面临的重大变局中,乡村学校教育物理性的“离土”趋势已势不可挡,要确保乡村学校教育中文化不离土,就需要乡村学校教育在不可避免的潮流和应承担的责任之间找寻出路,即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乡村学校教育需在守护乡土文化及教育价值中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而乡村学校的乡土课程建设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载体和实现路径。因而,本研究试图厘清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立场和价值意义,提出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路径。
一、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立场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乡土课程因被赋予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價值期待而逐渐走入众多研究者的“法眼”。目前,学界关于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价值定位有“离农”“为农”“兼农”三种倾向[1]。“离农”倾向是在城乡二元对立思维下重视教育教学的基础知识与统一标准,呈现逃离乡村的课程目标印记;“为农”主要针对“离农”倾向的不良影响,强调课程建设与乡村社会发展和乡土文化的紧密关系;“兼农”倾向试图超越“离农”与“为农”的简单二元对立,在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过程中重建乡土课程。可以看出,乡土课程建设的目标、内容、价值取向等都跟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十四五”规划和“2035目标”等新的时代背景下,乡土课程建设需要在教育现代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中呈现新的样态。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立场,是讨论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价值与路径的前提性、方向性问题。厘清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立场,有利于在学理层面重新认识乡土课程并赋予合理价值期待,并为实践层面更好地建设乡土课程提供方向引领。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这是费孝通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基本性质所作的精辟判断。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存续必然离不开根植于其中的社会形态。“乡土”指个体或其族群生长、居住于这个地方,并在这个地方的地理和生态空间区域里形成共同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其他特质的聚合体[3]。“乡土”既指涉区域地理空间,又蕴含在区域地理空间之上所生发的具有文化特性的内容,这些具有文化特性的内容即为“乡土文化”。乡土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在乡村社会中具有自身独立的生命、品格和气息,它不仅是乡民精神世界的寄托,而且可以使乡民产生对乡村以及乡村文化的自豪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主要包含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明显的乡土性。以自然环境、乡村聚落、民族服饰等物质文化作为传承乡土文化的载体,以年俗、民族传统节日、民间艺术所形成的行为文化作为乡土文化的有力支撑,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建立的村规民约等制度文化作为乡土文化的组成内容,以孝悌文化为开端、以敬畏文化为维系、以文化认同为目标的精神文化作为传承和发扬乡土文化的精神支柱。由此,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不只是地理区域的区分,更是不同文化存在的方式。乡土课程作为一种特殊的教学内容,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课程内容所蕴含的被内化的文化特质彰显为外在的文化性。因此,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要以“乡土”为基,充分彰显“乡土性”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村落共同体的维系、情感和道义上的认同,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乡土性”的重要理解,精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及其文化的基本特征。而本文则更侧重讨论以乡土文化为本的“乡土性”。 。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不仅要立足“乡土性”,同时还要彰显“时代性”。在全球化及城市化挟裹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离乡弃土,乡村社会暗藏着文化失却与社会秩序失谐的混乱[4],乡村教育呈现出去乡土化的态势,乡土文化的边缘化以及呈现出的凋敝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产生了影响。因此,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既要直面城市化和现代化潮流带来的问题,还要承担守护乡土文明及其价值的职责,其基本立场和原则是不应囿于“乡土”特色,一味追求“乡土”特色的保存与传承,使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陷入固步自封的狭小领域,无法实现其真正的课程价值,桎梏乡村学生和乡村社会的发展,而是需立足“乡土性”,彰显“时代性”,并处理好二者关系:一方面,乡村学校教育的文化性本质上是乡村学校教育的乡村性,即乡村学校教育只有在“在乡”的基础上才能有“文化”[5]。只有乡村学校乡村课程建设“在乡”并以乡土文化为基,乡村学校乡土课程的本真意义才能凸显,乡村学生才能接受可感知的、获得的、体验的、满意的乡村教育。另一方面,尽管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需要依托乡土,展现鲜明的地方特色,但还需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反映时代发展的需求,在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开放、过去与未来之间实现乡土课程的创造性发展,如此才能坚定文化自信。同时,乡村学校也需要依托乡土课程在“普遍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契合与转化中,在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6]。这也是当下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应体现的时代特点。
二、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价值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想抓住乡村的“根”,留住民族的“魂”,乡村学校教育就是先手棋。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之基石,维系乡村血脉传承的乡土课程不仅是乡村教育之灵魂,更是承载着传承乡村文明复兴之使命[7]。立足“十四五”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时代背景,厘清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价值,是正确认识、实践、建设乡土课程的前提。
(一)发挥课程育人功能,践行在地化发展理念 在国家三级课程管理框架下,乡村学校拥有自主设置课程的权利。乡村学校乡土课程作为国家三级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课程整体目标上凸显国家层面的统一性,并在课程内容设计和开发、课程实施上存有相对自主空间。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应始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培养学生综合核心素养为重点,充分调动乡土课程的育人功能,这既是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延续,更可以培养乡村学生认识、热爱家乡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同时,乡村学校通过乡土课程建设,融入经由筛选、改造后的乡土文化内容,使乡村学生对“乡土”的认识实现从抽象、模糊、不可感知到具体、明确、可感知的转变,这既有助于发挥乡土课程育人的功能,又有助于提高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在地化教育是以学生的生活圈或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精神、自然、生态等环境为基础,在全部课程中探索教育教学内容同地方教育资源和儿童社会经验的联结、课堂教学与当地社区的联结[8]。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在秉持课程育人理念基础上,以整体性思维方式,通过将乡村学生的文化知识、日常经验与在地化情境联系起来产生共鸣,在课程建设和探索中感知家乡的真实情境,以乡村学生的具身体验、理解性参与为基础,切实将优秀乡土文化和在地化环境融入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体系中,在课程实施中注重“家校社”合力育人的教育生态观和格局观,这既可以提升乡村学生综合核心素养能力,又有利于充分践行在地化教育理念,彰显乡土课程建设的整体性、生态性和在地性。
(二)发挥教育文化功能,赓续优秀乡土文化根脉 随着乡村城镇化建设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大步推进,城市文化以不可比拟的优势不断摧毁着乡土文化的自信,乡土文化逐渐被打上“落后”“封闭”“低劣”的价值烙印。在乡村社会内部,乡土文化自身的相对封闭性和依赖自然的独特生产生活方式,使其在与以效率、物质为表征的城市文化相互博弈、退让间价值意义开始崩溃,根脉逐渐趋于弱化甚至断裂。对乡村教育而言,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是乡村学校的文化解体,这不仅使乡村学校失去了立身之本,更丧失了前进的不竭动力。乡村学校教育的文化解体,恰恰是对其自身教育本质的否定,现代学校教育作为一种“超地方知识”,将乡村学校教育带入一个“异己”的脱域世界[9]。
乡土文化是承载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既担负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又维系着乡村、宗族、社会经济与文化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发展[10]。因而,乡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根脉,还承载着人们的家园幸福和民族信仰的根基。课程起源于传承文化的需要,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基于教育的文化功能,能够实现传递保存、传播丰富、选择提升、更新创造优秀乡土文化的功能,不仅可以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中重拾优秀乡土文化的价值,还可以为乡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概括来讲,传承乡土文化是指乡村学校乡土课程能够将优秀的乡土文化根植于心,并将其流传于世;丰富乡土文化是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通过多样的组织形式,赋予乡土文化生命力和活力的过程;选择乡土文化是为了适应乡村振兴的社会发展要求而去粗取精,需要对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内容方面进行筛选;创造乡土文化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如此,一方面既发挥了乡村学校教育的文化功能;另一方面又通过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彰显乡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以此提振文化自信,同时实现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普适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补充和相得益彰。
(三)彰显课程乡土特色,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 当前,乡村学校大多筑起围墙、设立门岗,物理空间上的隔绝造成了心理上的疏离。与祠堂、宗庙不同的是,乡村学校并未成为融入乡村社会的一部分,而是更像有組织、有秩序的政府机构,只是单纯地教授科学知识,也不再担当教化一方百姓之责,而且乡村学校传授的也是自上而下的统一要求,无法体现乡土特色并满足地方需要的城市化知识。这套体系默认乡土文化是土气无用的,对课程中出现的人文和地理等方面的乡土特色不求甚解。当“乡土特色”和“文化气息”在乡村学校中已经荡然无存时,乡村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将无从谈起。
“优质”“特色”和“个性”等话语构成了推动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以及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时代性话语[11]。乡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关涉乡村学校特色化发展,乡村学校特色化和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是乡村学校课程的特色化,乡土课程通过彰显区域特色和地方性知识与文化实现乡村学校教育特色化发展:一方面,乡土课程通过面向乡村,挖掘可以利用的优秀乡土文化资源,以文化性的课程内容建设和联结乡村社会的课程实践,以整体性、生态性、建构性的思维回应与担当起挖掘、传承与发展乡土文化的使命,在平衡回归乡土与面向未来之间发挥其文化价值与教育意义。乡土课程在教育性、文化性、发展性方面既可以彰显其独特价值,又可以助力乡村学校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学校生源流失、乡村学生向城流动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乡村学校要在此困境中突围,需不断变革自身,既要关涉优质,还要彰显特色,最大程度上使乡村学生能够在乡村学校中发现兴趣、全面发展、快乐成长。而乡土课程以培根铸魂为目标,在保持和发展其特质的前提下,通过课程实践在乡村学校内部发挥辐射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乡村学校课程建设水平。同时,乡土课程在思想性、实效性、社会影响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可以让乡村学生在乡村学校中寻回自信,感受乡村学校教育的优质特色发展,并在乡村学校场域中实现自身整全发展。
(四)培育文化自觉意识,增强学生乡土认同感 近年来,在乡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之下,乡村学校教育的相关内容大多与“乡土”无关,乡村学生厌学、辍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础教育课程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无法满足他们带有地域性和学校特色的发展需要[12]。这样的学校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乡村少年缺少了乡土的哺育,只是“在乡村”的少年,没有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和对乡村社会的热爱,何以振兴乡村?
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发展,乡村教育课程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乡村少年的健全人格,这不仅指向乡村少年作为普通个体的健全发展,同时还指向乡村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文化断裂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格自信的缺失[13]。在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乡村学校课程不仅肩负着乡村学生德、智、体、美、劳五育协调发展和提升核心素养能力的使命,还承担着夯实乡村学生乡土文化底蕴的责任。乡村学校要利用乡土环境、乡土文化来实现育人的目的,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可以帮助乡村学生了解和掌握乡土知识、乡土文化,逐步实现对乡土的认同。乡土认同主要涉及地域、精神归属等方面,是对乡土文化、乡村地域、乡村身份等的认同。乡土文化认同是乡土教育真正有实效、有意义的动力和永葆生机的源泉[14]。在新型城镇化影响下,乡村学生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向城流动,加剧了其对乡村、乡土文化的不认同。只有当乡村学生认识、理解并接受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时,乡村学生才能在乡土文化的滋养中沁润自身精神世界,在情感层面上对乡土文化自觉和自信,理解与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等问题并形成服务本土的意识,真正成为“是乡村”“在乡村”“为乡村”的少年,从而建立乡土文化自信和自觉意识。
三、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路径 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立场及其价值蕴含了建设乡土课程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向。为更好促进乡村学校乡村课程建设能够真正落地实施,真正惠及每一位乡村学生,真正契合时代发展需要,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现实路径,使其既符合促进乡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普遍期待,又满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时代诉求。
(一)明确乡土课程建设目标
当前,受外在客观条件和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制约,乡村学校在乡土课程建设目标方面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情况。有学者认为,当前乡土课程建设中存在三种境界:“参观展览”境界、“局部添加”境界和“化民成俗”境界[15]。其中,“参观游览”往往秉持功利性价值取向,以搞活动、作展示等博人眼球的方式为学校争取资源、名声等,显然背离乡土课程建设育人的初衷。“局部添加”通常以国家课程或地方课程为依托,将地方乡土资源嫁接至个别科目课程中,虽取得部分成效,但未形成系统完整体系,长此以往,将影响乡村学生核心素养能力的综合发展。这些境况背后,无论是乡土课程的同质化建设,还是空有乡土课程之名而无乡土课程之实的做法,反映出对乡土课程建设目标、定位和意义的蔑视与误读,将忽视培育乡村学生的整全发展。
总体而言,乡土课程建设要始终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依托乡土教育教学资源并结合乡村学生的已有生活经验,倡导探究式、开放式、项目式学习等方式,通过联结乡村学校与乡村社区的关系拓宽实践场域,以体现乡土课程建设的总体要求。
一方面,乡土课程建设应当始终彰显育人的价值取向,乡村学校乡土课程目标也应导向乡村学生身心自由全面发展——这里所提到的身心自由全面发展是让乡村学生既可以“向下扎根”,又可以“向上生长”。“向下扎根”指对乡村学生乡土情怀的培育。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应该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乡村的美好想象为基础激发乡村学生个体发展价值,培养乡村学生的乡土情怀,乡村学生唯有在乡土情怀的感召下,才能获得精神的归属和慰藉,并反哺和维护乡土,将乡土特质的文化进行延续和传承。“向上生长”指向乡村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乡土课程建设在课程内容组织、课程活动实施中应注重培养乡村学生的团结、协作、创新、批判意识,以提升乡村学生核心素养,使其获得健全的人格、自由的意识和把握幸福的能力。
另一方面,乡土课程建设要彰显乡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目标。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应该引导乡村学生面对现实,在对时代和乡村社会的整体体认中关爱乡村、理解乡村,在促进自我认同和乡土认同的过程中,提升乡村学生置身乡土世界中发展的可能性。乡村学生具有双重身份属性:其一,乡村学生的身份是由鄉土中蕴藏的文化内涵所赋予的,意即乡村学生扎根在乡村的生活、生产、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中,乡土为乡村学生提供游戏、成长和发展空间;其二,乡村学生也是生活在现代性语境之下的,乡土课程建设不应只局限于乡村,局限于把乡村儿童培养成适应乡村、建设乡村的人才,而应放宽视野,引导尽可能多的学生关心、重视、思考乡村发展问题[16]。这就意味着乡村学校建设乡土课程不仅要不断充实乡土文化,增强与乡土的联结,还应反映社会整体价值期待,努力达到国家统一规定的教育要求。只有在结合乡土性和时代性的目标导向之下,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才能真正完善乡村学生的人格,影响学生的情感发展,促进乡村学生的身心自由全面发展,真正体现乡土课程的育人价值。
(二)完善乡土课程内容体系
毋庸置疑,当前,乡土课程整体建设和课程内容设计被经费、师资队伍水平、考试制度等内外部要素共同制约着:要么对乡土资源挖掘和利用不充分,导致乡土课程建设不接地气,无法培养出了解、认同、热爱家乡的乡村学生;要么在接地气之余,未与乡村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发展相结合,使乡土课程囿于乡土而无法体现时代性、超越性。为防止乡土课程建设走样、变形,需在乡土课程建设中选择适切的课程内容并重组课程内容的排序。
1.选择适宜课程内容
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在课程内容选择上,应秉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所选择的课程内容应当反映本乡本土资源的特色。乡村学校乡土课程重在“乡土”二字,乡村社会以广袤的地域环境和丰富且独特的自然、文化资源而区别于城市社会,而乡土就恰恰根植于乡村社会中,根植于这些独具乡村社会特色的环境和文化中。二是经过选择的课程内容应当具有教育意义。诚然,并非所有乡土资源都可作为课程内容,唯有贴近乡村学生日常生活、形式丰富且内容多样、积极向上的乡土资源才可选为课程内容。
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在城市化和现代性的影响下,为唤醒乡村学生对乡土的认同和归属感,乡村学校乡土课程需要在课程内容中建造和维持一个乡土知识世界。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性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属性,乡土社会知识构成了乡土社会的文化网络,它规定着乡土社会的价值规范、伦理道德和行为规则[17]。中国社会原本就是乡土的,乡村学校教育不应成为与乡村社会脫域的“文化孤岛”。所以,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内容应当结合乡村学校教育内容和乡土资源实际,从优秀传统文化内部体系性和全面性的追求出发,以教育主题为纲,纵向深入进行传统文化要素的构建[18],将乡村本土所繁衍的民俗习惯、风土人情、天时地利的生产劳动等特色利用起来,并以乡村学生和乡村学校建设的实际所需为基础,充分挖掘自己的文化特色,诸如乡村社会中所蕴含的山川河流、地理风貌、花草植被等自然资源,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勤劳质朴、邻里和谐、诚信友善等道德文明资源,农耕制度中蕴藏的农耕文化,乡庙、宗祠、戏台等公共空间所承载的价值观念等,都是应当在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内容中体现的乡土元素。当然,课程内容选择乡土资源并不意味着排斥城市文化资源以及普适性知识,而是需以开放、接纳的态度对待城市文化和普适性知识,在交流、互动、融合的过程中,实现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普适性知识和地方知识的交互创生。
在课程内容的获取上,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有赖于新颖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在“互联网+”背景下,可以通过云端资源共享的模式,譬如“公有资源云+私有资源云”的模式,在吸收城市标准化资源的同时融入地方性的乡土知识[19],从而突出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内容与本地社会文化的联系,为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建立乡土课程资源库,帮助乡村教师精准科学地把握乡土课程的起点,通过共享优质乡土课程资源和教学经验,促进乡村教师教学和乡村学生对学习的理解与把握。此外,在学情分析、学习环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乡村学生的实际情况,使教学资源最大程度地支撑乡土课程内容重构。
2.协调课程内容组织
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在明晰所选择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还需要将课程资源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组成乡土课程内容的组织排序,不仅要由浅入深,还要协调不同科目、不同学习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让丰富的乡土内容与统一规定的学科教育内容有机融合,更应立足乡村社会发展和时代发展内涵,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背景下考量。
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内容的组织应当明确其在乡村社会发展以及乡村学校乡土课程中的价值立场,以连续性、顺序性、整合性为原则协调课程内容组织。从横向上看,乡土课程内容组织并不囿于单一学科,而是以问题和主题为导向,注重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和知识的广博性。从纵向上看,乡土课程内容组织按照知识的逻辑序列,并根据乡村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按照从已知到未知、从具体到抽象、从过去到未来的方式组织课程内容。同时,乡土课程内容组织还要秉持顺序性的原则,使后面学习内容是对前面内容的深化、拓展,展现层层递进的关系。在地化教育改革需要重构当前乡村学校的课程体系,处理好通用性与乡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这两对关系[20]。因此,乡土课程内容组织应在回首过去、立足现在和面向未来三重时间维度上考量。具体而言,首先,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内容应当回首过去,通过挖掘乡村学校所在区域已有的特色乡土文化、风俗活动所蕴含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注重对历史文化知识和民风民俗的介绍,在面向过去中探寻规划未来的思路。乡土课程首先应当贴近乡村学生日常生活经验,以由简到难、由远及近的方式组织课程内容。其次,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内容应当立足当下,通过乡村学校和所在乡村区域的特色地理风貌、经济人文优势,培育乡村学生热爱家乡的积极情感。最后,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内容既需要回首过去,也要面向未来。尽管需要基于乡土重构乡村学校乡土课程,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乡土资源,都应当时刻与现代化发展、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为乡村学生提供更广阔空间的同时,助力乡村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这就需要综合地理、科学、历史等多学科内容,将课程内容与不同学科融合,真正激活乡土经验的教育价值。
(三)变革乡土课程实践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现代学校教育的理念、目标、发展模式不断影响着乡村学校教育的发展。但从乡土课程建设的初衷到建设的路径,从建设的成效到价值的追求,从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到与乡村学生的关系,乡土课程建设的差异是全方位的,在课程实践中亦如此。乡土课程实践方式的变革,既要避免整齐划一的方法逻辑,又要结合课程实践变革的思路,通过转变课程实践观念和优化课程实践过程,使乡土课程更符合乡村学生学习和实践经验。
1.转变课程实践观念
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过程,不仅需要对乡土课程资源的选择、乡土课程体系的逻辑作系统分析,还需要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转变观念。无论是多样化的课程实践方式,还是课程实践过程的创生,都离不开从根本上转变课程实施观念。学校课程实践是作为客体的课程与作为主体的教师、学生等之间发生交互作用,从而将“理想的课程”逐步转化为“经验的课程”的过程[21]。因而,在乡土课程实践中,要将乡村学生作为经验建构的主体,尊重乡村学生的已有经验,并将课程实施建立在已有经验之上,引导乡村学生更好地建构新的经验。乡土课程实践还要有意识地引导乡村学生在与环境、他人的互动中创生新的经验,通过积极参与课程实践,在实践建构中助推乡村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发展。同时,在乡土课程实践中,需要将乡村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凸显出来,以乡村学生为主体,培养其自主探索、感知体验、实践创新能力;乡村教师作为乡土课程引领者和支持者,在乡土课程实践中承担为乡村学生提供情境和发展空间的责任。
2.优化课程实践过程
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离不开课程实践过程的创新。《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尤其强调聚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强化课程实践性的要求。因此,乡土课程建设在实践过程中,既要将地方文化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空间与乡土课程体系整体进行有机结合,又要变革体现探究、过程、体验式的课程实践方式,充分给予乡村学生自主探索、自我发展的空间,在引起乡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好地提升乡土课程建设质量。
首先,乡土课程实践不应囿于乡村学校,而应将乡土课程实践拓展至现实乡村社会生活,深入社区、社会,建立校社联结。从单一的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拓展,将乡土课程实践的学校教育空间延伸至社会中的博物馆、生态区域、历史遗迹等场地,以便在系统化、网络化、合理化的课程实践体系中形成合力,实现乡土课程实践的变革,使乡土课程在與家庭、学校、社会的互动建构中,促进乡村学生在真实而整全、贴近生活经验的情境中获得乡土学习体验。譬如,在乡土课程实践过程中,乡村学生既可以走出教室甚至走出校园,在山间田野感受昆虫、花草植物及家乡地理地貌、土壤、森林等乡村自然资源,在参观博物馆、历史遗迹中了解家乡名人、红色基因等;又可以在家庭生活中感受了解乡音乡情、饮食文化等乡村人文资源,还可以在参与乡村集会、庆典等活动中了解民间艺术、民间舞蹈、民间风俗等乡土资源。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让乡村学生充分接触与认识乡村地理环境、人文风貌,既可拓展乡土课程实践的场域,又可将知识学习与乡村学生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环境相联系,实现乡村学生对乡土知识的整体性理解和感性体悟以及知识与个体生活世界的互动与接触。
其次,乡土课程实践过程中要注重活动、实践、探究的课程实践方式。在实践体验中,乡土课程实践主要通过乡村学生亲身体验、感知以获取相应知识经验。例如,在了解家乡名人、历史古迹、红色基因的过程中,乡村学生可以通过访问长辈、参观博物馆、观看视频音频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乡土知识,既能培养乡村学生科学探究的热情,又能培育乡村学生对乡村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的亲近。在实践探究中,乡土课程实践应与乡村学生当下的生活和社会生活相联系,以培养学生发现和解决乡土情境中问题的能力。例如,可以通过开展直播带货、服饰设计大赛、科学实验、保护生态环境等活动,培养乡村学生创新、思维、动手、协作等核心素养。
(四)构建乡土课程建设共同体
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离不开一支扎根当地、熟知并认同本土、具有乡土自信和情怀、多主体参与的乡土课程建设团队,而且团队应秉持多主体参与的原则,发动具有乡村知识、了解乡土文化的乡土文化学者、地方文化传承人、乡绅、当地村民等积极参与,积极争取乡村校长、乡村教师、专家、校外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支持,构建乡土课程建设共同体。
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要紧紧围绕“乡土”为基本内容作设计。具体而言,乡土文化学者、地方文化传承人应利用自身的知识及专业,确保乡土课程的科学性及有效性。当地乡绅作为乡村社会有声望和知识人的象征,不仅见证了乡村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生活方面的变迁,同时还熟知当地的自然景观和精神风貌,对乡村社会、乡土文化具有浓厚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感,这种丰富的乡土知识以及热爱家乡的情感使其成为乡土课程建设不可或缺的一员。村民的生活经验、知识来源、文化感知等都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和乡土文化,在建设乡土课程时,村民也能为乡土课程的开发提供基于当地特色的第一手资料。地方性知识必须在地方人民的文化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若将地方性知识与其文化背景相分离,就会忽视它在社区生存和团结中所发挥的作用[22]。乡村校长要整合多方力量,统筹协调课程建设团队的其他主体和学校内外部资源,为乡土课程建设提供大方向,充分释放乡村学校内部的课程建设力量。乡村教师需要充分考虑乡村学生的群体特征、身心发展阶段特点、日常生活经验及独特需求,发挥自身专业知识和能力,使乡土课程建设能够更加“接地气”,在适合乡村学生学习的同时促进乡土课程落地实施。专家则主要为乡土课程建设的内容开发、实施路径提供专业论证和支持。同时,校外机构和社会公益组织可以在活动组织、资金筹集、实践机会等方面为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提供外在资源保障。通过构建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共同体,推进多主体间信息畅通并达成共识,共同为乡土课程建设贡献力量。
四、结语
乡土课程蕴含着乡村社会精神与文明、习俗与传统、道德与历史,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和文化意义。城市化对乡村学校发展的冲击,表面上体现在生源流失、课程内容偏重城市教育等方面,背后反映的则是乡村学校的同质化发展以及自身特色的丢弃,导致乡村学生在乡村学校中无法享受适宜、优质的教育。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中,乡村学校乡土课程建设迫在眉睫。只有将乡土课程建设放在乡村教育发展整体布局的战略高度看待,才能使乡村学校成为联结、守护乡村社会文化的桥梁,才能彰显乡村学校自身的文化属性和教育特色,才能提升乡村学生的获得感、满意度和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丁学森,邬志辉,夏博书.农村学校在地化课程建设的问题、价值与实践选择[J].中国电化教育,2022(5):59-65+74.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0.
[3]李新.百年中国乡土教材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4.
[4]吴杰.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乡土教育想像[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14-119.
[5]薛晓阳.乡村学校“在乡性”的危机与应对——以“乡村文化教育”作为一种应对战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84-95.
[6]车丽娜,傅琴.乡村学校课程建设的空间悖论及其消解[J].课程·教材·教法,2021(12):33-39.
[7]袁利平,温双.乡土课程开发的文化价值与实践选择[J].中国教育学刊,2018(5):80-85.
[8]邬志辉,张培.农村学校校长在地化教育领导力的逻辑旨归[J].教育研究,2020(11):126-134.
[9]汤美娟.“小历史”的书写:乡村民众教育观念变迁的民族志研究——以苏北M村为个案[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71-176.
[10]吴惠青.农村学校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90-98.
[11]袁利平,姜嘉伟.中国乡村教育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及其现实启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69-83.
[12]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0-105.
[13]刘铁芳.回归乡土的课程设计:乡村教育重建的课程策略[J].现代大学教育,2010(6):13-18.
[14]纪德奎,赵晓丹.文化认同视域下乡土文化教育的失落与重建[J].教育发展研究,2018(2):22-27.
[15]段会冬.乡土课程建设的三种境界及其反思[J].当代教育科学,2020(7):17-19.
[16]孙宽宁.乡土课程的困境及其超越[J].课程·教材·教法,2021(9):29-36.
[17]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观察社,1947:6.
[18]田慧生,张广斌,蒋亚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体系的理论图谱与实践路径[J].教育研究,2022(4):52-60.
[19]田俊,王继新,王萱.“互联网+在地化”:乡村学校教学质量提升的实践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9(10):38-46.
[20]陈时见,刘雨田.乡村学校在地化教育的价值与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5):75-80.
[21]胡守敏,李森.论课程育人生长点的困境与变革[J].课程·教材·教法,2020(7):4-11.
[22]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336-347.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rriculum is the necessary way for rural schools to stop the impact of "alie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rriculum in rural schools should adhere to the position of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and facing the future. Rural loc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 rural schools is conducive to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local development, continuing the roots of excellent local culture, helping rural schools to develop with high quality, and enhancing students' sense of local identity. The path of rur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 schools should be as follows: defining the goal of educating people in rur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combin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times, improving the rural curriculum content system by selecting appropriat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coordinating curriculum content organization, changing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concept and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process to realize the reform of rural curriculum practice,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rur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with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Key words:local curriculum;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locality; local cul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責任编辑:杨 波 蒲应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