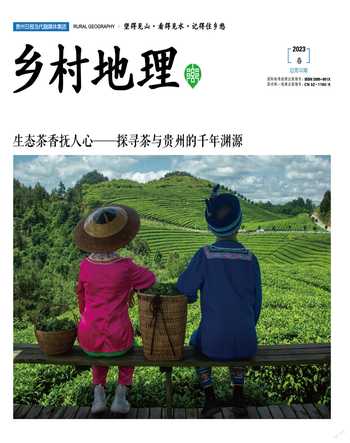明清时期: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苗疆防御体系
2023-05-29王东图片除署名外皆由作者提供
文/王东 图片除署名外皆由作者提供
自秦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我国的边海防治理一直遵循“守中治边”的方略。明以前我国边海防“重北”,至明代确立固守疆域的边地戍守战略,形成“北防、东守、南进”的格局,建立了北方长城防御体系,东部沿海防御体系,西南苗疆防御体系(简称“三防”体系)。至清代,统治者源自北方,长城防御体系功能弱化,来自海上的“外患”强化着东部海防的建设,并向近代化演变。在西南苗疆,土司叛乱、少数民族起义一直存在,明代“南进”防守策略得以延续,并成为不断推进西南苗疆国家化、内地化进程的重要保障。

贵阳市花溪区青岩古镇。

南方长城。
公元1253-1259 年蒙古铁骑采取“迂回西南,包抄后方”的战略灭亡南宋后,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苗疆地区国防战略显著提升。元明清三朝皆十分重视对贵州及其相邻的滇东、湘西的经营。元代修通了连接湖广(常德)至云南(昆明)的驿道,并设立站赤。人类学家杨志强教授称其为“苗疆走廊”。苗疆走廊官道的修通,使贵州成为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军事格局从此改变。从明初“太祖平滇”起,西南苗疆土司叛服无常、少数民族起义频繁,攻击官道,威胁王朝统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清两朝。针对苗疆叛乱,中央一方面采取“加意抚恤,以称朝廷柔远至意”的“柔远抚绥”的民族政策,但是在“抚之以仁义”的同时,也“摄之以兵”,在“顺者以德服”的同时,对“逆者以兵临”。为充分发挥“兵临”之力,明清两代在元代的基础上不断加强西南苗疆军事聚落、防御工事的建设。从明初边防建设看,主要防御对象为分布于北方漠北和西南滇云的蒙元残余势力。因此西南苗疆防御体系与北方长城防御体系均为明初同期建设。明廷在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苗疆营建的军事聚落、防御工事主要沿着苗疆走廊主驿道,即“一线路”和“乌撒道”进行布置。沿线密布卫城、所城、屯堡、关隘、寨堡、哨卡、驿铺等军事聚落与防御设施。在苗患最突出的滇黔交界的腊尔山区修建了与“北方长城”齐名的“南方长城”,南方长城始于贵州铜仁亭子关,北至古丈喜鹊营,沿线布防军堡、哨堡、炮楼、碉卡等防御工事,极大的丰富了西南苗疆防御体系的内容。北方长城防御体系主要沿着九边重镇设防,故将其归为“重镇型”,而东部海防体系沿着海岸线布防,称为“海岸型”,西南苗疆沿着官道分布,则称之为“交通型”。为了在西南苗疆建立长久的军政统治,明廷通过“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移民就宽乡”等措施从湖广、江西、南京、浙江、河南等地征调大量的军队和民众进入云贵地区,沿苗疆走廊官道两侧进行屯田戍边。明永乐十一年(1413)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标志贵州建省。贵州建省的目的是为保障苗疆走廊官道的畅通,保障国家统治秩序的顺利推行。明前期在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苗疆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营建防御工事、屯田戍边、设置行政机构等措施基本奠定了明王朝在西南苗疆的政治军事统治地位,并形成了沿苗疆走廊官道布防的线性军事防御体系。

古代平越府卫城图
然终明一代,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苗疆“民居其一,苗居其九,一线之外,四顾皆夷”,明廷在西南苗疆的军政统治秩序并不稳定,万历年间爆发“播州之乱”,天启崇祯年间爆发“奢安之乱”,明末清初爆发“沙普之乱”等,给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苗疆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明帝国的灭亡。因此,整个明王朝都没有放松对西南苗疆走廊官道的军事防御建设。至清代,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苗疆防御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相反由于平西王吴三桂的武装割据,以及清廷“改土归流”,武力“开辟苗疆”力度的加大,西南苗疆的边防压力不断加剧。因此清廷在苗疆腹地的贵州一边推行营兵制的同时,还延续了“明制卫所制度”,形成新旧两个朝代两套军事制度并存一世的奇特景观。明制卫所直到雍正五年(1727)裁卫置县才结束,但各地苗患问题并未停息,于是清廷陆续在黔东南、黔东北战事频繁之地仿“明制卫所”设置“清制苗疆卫堡”,这一军事政策延续至清末。相比较,明代国家建立的北方长城防御体系和东部海防体系随着明帝国的灭亡而瓦解,而沿着苗疆走廊官道营建的西南苗疆防御体系非但没有瓦解,而且在局部地区得以强化。如顺治年间清廷在黔中设巴香卫。乾隆至嘉庆年间相继在黔东南苗疆设“新疆六厅”,内设九卫一百零八堡,大兴屯政。在黔东北设石砚卫,合称“苗疆十卫”。民国《贵州通志》记载:“乾隆二年,仿照明代卫所屯田制度,在黔东南苗疆设立八寨、丹江、台拱、凯里、黄施、清江左、清江右、古州左、古州右等卫”。乾嘉苗民起义后,在《苗疆善后章程六条》中提出“清厘界址”“营讯联动”“设置土弁”“修理城垣”等善后措施,军事上重提南方长城修筑,经过军民的苦心经营在明南方长城的基础上建成“汛堡一百三十五座,屯卡一百五十一座,碉楼七百二十九座,哨台九十九座,炮台十座,关厢十座,关门三十八座。总共一千一百七十二座。又,凤凰厅接连乾州厅沿边,开筑长墙、壕沟一百一十馀”的清代南方长城防御工事,成为明清西南苗疆防御体系的重要补充。

隆里所城青阳门
以上防御体系由国家力量主导修建,构成西南苗疆防御体系的“主线”。此外,明清中央王朝在防御土司叛乱、少数民族起义的同时,也利用土司力量和民众力量维护统治。因此元明清土司修建的防御性寨堡也构成苗疆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典型遗存物如播州土司海龙屯、毕节大屯彝族土司庄园、开阳水东宋氏布依族官寨等。西南多山地,自古就实践着“守城不如守险”的军事思想,民间形成“据险设寨、因山设堡”的传统。各民族充分利用山的险峻、巍峨,营造山寨,耕战自保,以避兵祸。清咸同年间以贵州为核心爆发的各民族大起义,将民间营盘的修建推到高潮,在官方的默许、支持下民间修建防御工事遍布城乡各地,形成山囤、洞囤、水囤、山洞囤结合四类民间营盘。典型案例如遵义凤冈玛瑙营盘、六枝板梅营盘、安顺屯军山营盘、花溪摆念洞囤(亦称躲匪洞)、安顺周官村水囤等。土司寨堡和民间营盘营建主体多元,从大地理视角看,缺乏整体规划,呈现为分散状,但其选址与战事频率呈正相关,而战事则主要围绕着苗疆走廊官道而发生,故土司寨堡与民间营盘分散中蕴含着秩序,即主要围绕着苗疆走廊官道而建,其构成西南苗疆防御体系的“辅线”。“主线与“辅线”在地理空间上大致呈叠加之态。二者彼此配合,共同维护着西南苗疆的稳定。
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苗疆防御体系为明代国家主导营建的三大防御体系之一,是明初同一时空语境下的产物,在经过清廷的接续经营,积淀了厚重的军事文化内涵,作为重要的线性军事文化遗产,在我国边海防史上的军事地位不容忽视。然而从学术界看,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方长城防御体系和东部海防体系,对于西南山地的苗疆防御体系研究成果极少,仅有的研究以“散点”式呈现,忽视了对明清西南苗疆边防建设的“大地理、大历史”的整体关照。这也导致了极具遗产价值、地域特色的西南苗疆防御体系的社会关注度较低。本文抛砖引玉,期寄社会各界关注并整体研究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山地苗疆防御体系,梳理其防御聚落与建筑的形态特征,挖掘其所蕴含的遗产价值,服务于当代“乡村振兴”与“城市双修”战略,使明代所建的“三防体系”研究真正呈鼎足之势。
本成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西南苗疆走廊屯堡聚落与防御体系整体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镇远古城烽火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