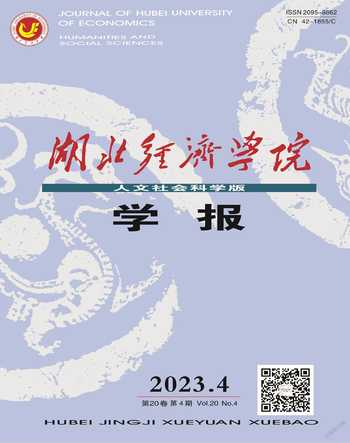青年学视角下青年毛泽东诗词中的青年形象
2023-05-26张晶王淼
张晶 王淼
摘 要: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团结带领着中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道路,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途。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革命政治生涯中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具有恢弘意境、雄健风格、崇高美感的古体诗词也足以令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政治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是如何在毛泽东的人生中并行不悖的?政治家的雄韬武略和诗人的文采斐然是否可以相互重叠?结合对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诗词创作的审美鉴赏,从社会学视角观照诗词中自然属性、实践属性、文化属性的青年形象,为了解毛泽东诗词中青年形象的美学内涵与精神价值提供了可能路径,为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青年提供了坚定信仰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毛泽东诗词;青年学;青年形象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毛泽东历来重视青年的力量,他说:“青年乃国家之精华”[1]78,他赞颂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将希望寄予青年:“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2]121。作为独树一帜的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不仅起步于他个人投身革命伟业的青年时期,也恰与蔚然成风的新文化运动、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同步。正是这来自自然、社会和文化的三股青春力量合力孕育了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诗词创作,奠定和造就了毛泽东诗词豪迈乐观、气象恢宏的美学风格。
人们对“青年”的年龄划分常因种族和时代的不同而标准各异,依据社会学对“青年”的定义:“人生生命历程(或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阶段”[3]5,难以把握“青年”的具体内涵。事实上,学界对于“青年”本质属性的讨论却大体未脱离自然、实践和社会三个维度。在自然属性的维度下理解“青年”,更侧重于对青年身心发展规律的认识,强调在其从生理与心理的不成熟走向成熟,特别是在自我意识和性意识的觉醒下,青年的思维呈现出跳跃性、抽象性、超前性、创造性等特征。在实践属性的维度下认识“青年”,强调随着活动空间的拓展,青年逐渐与现实的社会环境产生连接,在政治环境中开始认识自我、改造自我,适应政治、参与政治。而从社会属性的维度理解“青年”,则认为青年的本质是青年社会性的发展,尤其是当青年选择性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时,兼具开拓性与继承性。近年来,也有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青年的本质视为青年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实践活动中的辩证统一,是青年自我与社会逐步协调统一并成为社会主体过程的诸因素总和[4]73-74。由此,笔者选择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创作的古体诗词为研究对象,尝试从青年的自然属性、实践属性和文化属性等社会学的视角入手,论述青年毛泽东诗词创作中青年形象的审美蕴含与时代意义。
一、“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自然青年形象
在青年的属性研究中,青年的情绪、情感和思维等心理特征被看作更具共性的自然属性。区别于幼年、老年等其他阶段,青年对未来充满向往,对世界充满想象,思维活跃、情感丰富[5]54。《青年学概论》明确指出,“这个时期(青年时期),(青年)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都有显著提高。”[6]46青年毛泽东在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上不仅较同时代其他中国青年更加突出,而且鲜明地呈现在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诗词创作中。
(一)灵动的意象表达与新奇的典故化用
青年毛泽东的创造性思维体现在他偏爱将平凡的意象与传统的典故,融入古体诗词创作中,从而焕发其穿越古今的文化魅力。在象征、比喻、用典,寄情于情、借景抒情等中国古典诗词创作手法基础上,青年毛泽东创新地运用了传统的“水”“风”等意象、经典的“鲲鹏”“高山流水”等典故。
天地、江海、山川、花草等意象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诗词创作中常常出现。《菩萨蛮·黄鹤楼》中,“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将“水”的意象融于江景,惊心动魄、层层递进的气势在“江”与“浪”中呼之欲出。面对大革命的失败,青年毛泽东始终坚定革命理想。《忆秦娥·娄山关》中,更是借“风”“霜”“月”“残阳”等意象,勾勒了第五次反“圍剿”失败后的低潮形势。即使“雄关漫道真如铁”,青年毛泽东依旧怀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勇气。《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借“山”与“原”的意象,以静衬动,暗示中国革命的沉寂终会因工农革命之星火再次澎湃,写活了一位胸怀革命理想、渴望实现抱负的青年形象。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善于化用传统典故来创造诗词的崭新气象。《五古·挽易昌陶》中,“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抒写毛泽东失去知己,独自面对“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困顿时局的迷茫与失落。《沁园春·长沙》中,“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则圆融地化用了“祖逖北伐、击楫中流事”(《晋书·祖逖》)和《逍遥游》中的鲲鹏南翔“水击三千里”的两个典故[7]。
(二)巧妙的承旨发问与论辩的哲学思维
善于提问,长于论辩是青年批判性思维特征的重要体现。“(青年)在学习过程中,喜欢怀疑和争论,喜欢探求事物现象的根本原因。”[6]47青年毛泽东哲思充溢,这使得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诗词创作充满了设问与“隐问”。在上下呼应的线索、直抒胸臆与蕴含丰富的提问中,毛泽东诗词抒表了青年敢于开拓的气魄与勇于进取的决心。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创作的诗词有些以直接的问题作为串联诗词创作的叙事逻辑。《沁园春·长沙》中采用自问和设问的两个问题串联起上阕与下阕,连接了现实与未来。“怅廖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看似无须回应,实则呼应下阕。“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看似是提问,实则是论辩。一来一回,勾勒出了一位身处革命动荡与挫折,却依旧志向远大、风华正茂的青年形象。《念奴娇·昆仑》中,“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接连两个设问,节奏紧凑,回望历史,畅想未来,描摹青年“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开阔视野与格局。
而那些暗而不表的隐含问题则凝注着青年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情感线索。《清平乐·蒋桂战争》中,无直接的问题书写,但充盈犀利的论辩思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看似肯定的语气,实则隐含设问的逻辑:为什么会风云突变?重新出现的黑暗现实会长久吗?不会!这不过是短促而虚幻的一枕黄粱梦。隐形的论辩思维透视了军阀战争的本质与结局,勾勒出了一位身处变局但坚韧清醒的青年形象。
(三)充盈的情感能量与澎湃的革命气质
青年研究的心理学派对青年的情绪和情感特征作过准确的描述,他们认为青年的情绪具有突出的两极性,既有活泼、愉快、奋发向上的积极倾向,又容易出现低沉、悲观、颓废等消极倾向。此外,情绪的延续时间更为长久,开始形成稳定的心境。而青年的情感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不仅出现了多样性的自我情感,而且随着生活、学习和劳动范围的扩大,社会情感也日益丰富。另外,情感的表现具有内隐性的特征,即往往表露出一种与内心体验并非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情绪状态[6]48。尽管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屡遭失意和挫折,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诗词创作却往往情感充沛、积极向上。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诗词创作中饱含青年人充盈的情感能量。在《虞美人·枕上》中,那个思念恋人、相思愁苦的青年形象正是青年毛泽东的投射。1920年冬日,新婚燕尔之时相爱的青年不得不与爱人分别,继续踏上革命征程。“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泪”字收笔,无奈尽显:即使再思念,也只能自己在夜色中独吞苦涩。青年男女难舍难分的离愁别绪在《贺新郎·别友》中同样有抒发:“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在《五古·挽易昌陶》中,“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充分表达了青年对友人离去的悼念与哀思。“愁杀芳年友”“杀”作拟人,既写出了诗人怨恨疾病无情带走密友的心境,更表达了诗人愤懑面对挚友人生变故而无力拯救的无奈。无论是在《五古·挽易昌陶》中,“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泪”等诗句,还是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毛泽东早期与友人湘生的通信:“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8]38,都勾勒了一位重情重义的青年形象。
除了写亲情、友情和爱情,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诗词创作还流露出青年毛泽东忧国忧民的社会情感。《五古·挽易昌陶》中,“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说尽青年毛泽东心怀国之大者的抱负。“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更是勾勒出青年毛泽东的高远志向与卫国决心。“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前,都令我来何济世……”[9]121的悼词中,心怀大志、独立坚定的青年群像更是跃然纸上。
当代青年正在遭遇传统信仰的后现代解构。他们过于追求以否定的批判来对待一切传统信仰,错误地与传统和历史割裂,而这样的困惑造成了当代青年的信仰结构危机。毛泽东诗词中的不惧黑暗、不畏挫折、不怕动荡的青年品格都是激励现代青年的不朽财富。
二、“问苍茫大地”的政治青年形象
“青年”的内涵之所以会因时代而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青年人都以自己的实践方式保持着和社会环境的互动,呈现出青年的实践属性,“他们(青年)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充满朝气的新生力量,是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10]54毛泽东同时代的青年在现代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之时,理所当然地承担着救亡的历史使命和复兴的民族大任[11]。在历史与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小写的个人“青年”不断成长为大写的中国“青年”。斯诺在《西行漫记》(也译作《红星照耀中国》)中指出:“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历史记载了”[12]毛泽东青年时代创作的诗词与蔚然成风的新文化运动、20世纪初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交融相生,大写的政治“青年”形象在其中并不少见。
(一)心系人民、体恤群众的热忱品格
毛泽东向來将人民与群众置于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他坚信“人民是上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3]90-91。出生长大在湖南偏远乡村的毛泽东,目睹农民被压迫的苦难时刻,对劳动人民有极为亲密而深刻的情感。“民为邦本”是贯穿毛泽东全部政治实践的一个核心政治理念[13]31,人民情怀是毛泽东诗词的核心属性。在青年时代创作的诗词中,毛泽东将对人民的重视映射在了其中所言的青年形象。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诗词创作使用了不少与“民”相关的表达。《西江月·秋收起义》写于1927年秋日,此时正当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在“重重”“个个”两个叠词的穿插、“压迫”“同仇”两个动词的强调下,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深刻矛盾,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血泪现实拨人心弦。青年人面对此时中国严重的社会阶级矛盾,深切同情人民水深火热的生存境况。“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湘江直进”“霹雳一声暴动”,上下两句中的“不停留”“直进”“霹雳一声暴动”相互呼应、一气呵成,表达了青年为民爱民的坚定信念与体恤群众的热忱品格。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诗词创作中,常用隐喻的文学手法,表达与人民荣辱与共的决心。诗句中,虽未见“民”字,但同样充溢着深深的为民之情。在写于1928年秋日的《西江月·井冈山》中,“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四句,尽显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局面和军民团结一心的决心之间形成的张力,颇有剑拔弩张、虎口脱险之感。如诗所述,1928年7月,湘赣敌军利用我军守备空虚,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我工农红军31团的一个营对阵抗衡敌军四个团的精兵,足以见得黄洋保卫战的惊险艰难。“众志成城”四字更是在剑拔弩张的硝烟气味中,刻画出全军将士依靠人民、热爱人民、团结人民的青年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4]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深知底层人民生活艰难,“看到他们受苦,我(毛泽东)忍不住要掉眼泪。”[15]3在毛泽东诗词中,特别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诗词创作中,这样的情感熔铸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诗句中依靠人民、热爱人民、团结人民的青年形象中。
(二)心怀国家、改造世界的青年心境
青年作为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参与者,同样也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6]61。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与中国革命的兴起、发展密切相关。在落后动荡的旧社会里、在艰难的革命岁月中,青年毛泽东宠辱不惊、坚毅果敢,在挫折和逆境中练就了他心怀国家、改造世界的开阔心境。
处逆境而不放弃,这是青年毛泽东诗词创作中常常书写的青年底色。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党对红军必须要实行集权制,党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并对毛泽东以“警告处分”[16]86。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青年毛泽东被迫“赋闲”。遭受挫折的毛泽东,于1929年10月写下《采桑子·重阳》。尽管人生蹉跎、低谷难眠,但那又怎么样,即使是战地的黄花也分外芬芳,令人神醉。纵是秋风萧瑟,“不似春光”,却“胜似春光”。诗人用“易老”“黄花”“战地”“秋风”等看似伤感、衰颓的意象与景色,表达了青年不惧挫折、勇往直前的决心与勇气。毛泽东于1933年夏写作的《菩萨蛮·大柏地》,若不深究其背景,很难察觉毛泽东当时真实的处境。事实上,早在1932年10月,毛泽东就被免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党内毫无话语权。在这样的暗淡时光里,诗人却用“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样明亮的色彩,“雨后复斜阳”这样充溢希望的景象,回忆昔日战争的胜利成果,展望中国革命的光明未来。
于变局中不慌乱,这是青年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追求的青年品格。1928年前后,刚刚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遭遇湘赣敌军的会剿,党内有人开始质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在这样的质疑声中,毛泽东先后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革命可以继续并终将走向胜利。1929年秋,毛泽东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中接连使用的“变、战、怨、现、跃、下、拾、忙”等八个动词,使一个拓新奋进、乐观向上的青年形象跃然纸上。
(三)反抗压迫、救亡图存的革命自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身处时局的青年们,在历史的潮流中,挺身而出、奋勇向前。这样反抗列强压迫、不惧黑暗时局,渴望前进、拯救中国的青年形象,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诗词创作多有生动刻画。
20世纪初,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救亡与启蒙的现代大潮。青年深处黑暗与黎明间的缝隙,思索民族未来的命运,寻找国家前进的方向。日本倭寇独霸中国的蛮横之举,沙皇俄国瓜分中国国土的无耻行径,北洋政府的落后与卖国无能,种种历史语境交汇,青年毛泽东悲愤交加,爱国忧民之情全然倾注于友人病逝的痛苦之中。《五古·挽易昌陶》中,“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更是将失友之悲化为反抗的决心与救国于危难的志向。
1925年春,因为在家乡韶山建立党支部,号召群众参加“雪耻会”,毛泽东无奈被追捕。青年毛泽东故地重游,面对这时这景的长沙,心中感慨千万。“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看似写景,实则暗含对受尽屈辱的祖国、受尽压迫的人民的同情与共情。“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是回忆,同样也是激励。澎湃情感、豪迈志向,写尽青年的拳拳报国心。
1927年春,北伐战争胜利之时,蒋介石背叛革命,毛泽东在中共五大上提出的“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建议被否决,革命成果几乎快要毁于一旦[16]71。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青年毛泽东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寥寥数句却写出了迷茫的中国、痛苦的民众、悲愤的青年。“茫茫”“沉沉”“莽苍苍”“锁”,用压抑的笔调抒发着青年满腔的愤懑。“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更是将青年心中“誓与恶势力奋战到底的志士豪情”[16]73推向高潮。
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文化青年形象
青年研究的社会学派中有一种“传承—更新”理论,认为“青年”与社会文化之间相互关联,青年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本身是双向互动的传播过程。在社会变迁中,青年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自身社会化不断实现,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因此得以延续、甚至更新[17]。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青年”从诞生之初就处于国家、社会的夹缝中,“依附—反抗”是深入“青年”的内生性命题[18]。“依附”内含着青年对传统文化底色的内化与继承、对新文化精髓的学习与开拓,“反抗”则是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其中糟粕的剥离与过滤。青年既身处传统,同时又在现实的社会状况下创造新的可能。“青年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社会变革的有力推动者”[10]64,新文化运动中的青年在新与旧、西与中的文化激烈碰撞中生长。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诗词创作中的“青年”,是青年毛泽东,更是五四运动后大写的中国现代青年。
(一)文学表达的新与旧
毛泽东认为:“新诗应该精练,大体整齐,押大致同样的韵。(新诗)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詩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求得新诗的发展。”[19]80他坚信旧体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20]3,他喜爱李白、李贺、李商隐,痴迷《楚辞》,熟练掌握古典诗词的格律,灵活运用赋比兴、用典的创作手法。
形式上,遵照古典诗词的形式。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种类丰富,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四言、六言,沁园春、西江月、菩萨蛮等等词牌均有涉及。《五古·挽易昌陶》五字成句,排列整齐,形式规整。新文化运动前的青年毛泽东虽接触到了反对封建糟粕的思想,但新思想还处于萌芽。尽管“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表达了青年新的气象,但《五古·挽易昌陶》中的青年“新”声仍尚未完全突破古体诗词的遣词用句。相较之下,《贺新郎·别友》的词句排列与押韵明显生动灵活。字句长短交错,用词也更有新意:“台风”“寰宇”充满了新文化运动后破古求新的魄力。
内容上,继承古典诗歌的用典。毛泽东诗词偏爱典故的化用,有的典故更多的是借用古义。比如在《五古·挽易昌陶》中,“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中就借伯牙、子期的知音之情,表达青年毛泽东对友人昌陶因病逝世的思念与惋惜。此外,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诗词创作也偏爱借用传统典故,并赋予其新的含义。《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不周山下红旗乱”就用到了“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共工”本是古代神话中的帝王、也被称作水神,毛泽东将其比作开天辟地、破旧立新的革命英雄。
毛泽东诗词的语言简练准确、出其不意。《沁园春·雪》中,“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动静结合,勾勒出一幅辽阔、壮丽的北国冬日风光。《沁园春·长沙》中,“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动静结合、色彩斑斓,写活了南国秋景。诗人寓情于景,忧国忧民、心怀大志的青年形象在典雅考究、精炼简洁的字句中鲜活了起来。
(二)地方气质的新与旧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湖湘文化在青年毛泽东的骨髓中注入了一种特有的“霸蛮”气质。这种气质贯穿在毛泽东诗词中,特别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诗词创作中。所谓“霸蛮”其实是湖南方言,“刚毅果敢”“坚忍不拔”“不怕鬼、不信邪”“打脱牙齿和血吞”等等都可以用来解释它的内涵[21]2-3。
不畏权威,敢于挑战的青年形象活跃于诗词。《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的“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沁园春·长沙》中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寥寥数字,气象广阔、格局远大。就算时局动荡、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青年人也应有“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的宏大格局。《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横扫千军如卷席”,《念奴娇·昆仑》中的“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都写出了面对变局,不慌不乱、从容不迫、敢于担当的青年形象。
湖南人特有的“霸蛮”气质镌刻在毛泽东的基因中。出乡关后,毛泽东身上的“霸蛮”品质有了更加自由的生长空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就立足人性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全面阐明与肯定了叛逆与反抗的必然性与重要性”[20]15。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旧的地方“霸蛮”气质与新的时代自由主题碰撞中,不畏权威、不惧敌人的青年形象被写活了。
(三)文化品格的新与旧
毛泽东出生、成长在中国社会由旧向新的转型时期。青年毛泽东处处能够感受到封建压迫的落后思想与自由民主的新思想之间的拉扯,西学东渐与中西文化的对立冲突,“士”之大我与个人之小我的矛盾纠结。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诗词创作记录了青年毛泽东和当时许多青年的真实感受。他们变身为“新青年”,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治愈矇昧的思想、传播启蒙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传统底蕴的精华、吸取外来文化的优长,担负起时代大任。
“敢于革命、反抗權威”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青年的群像。青年作为连接新与旧的桥梁与过渡,“现代性让人们相信进步的可能性蕴藏在青年之中,未来世界归属于青年”[18],五四运动中的进步思想、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塑造了进步的青年。通读毛泽东诗词,《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的“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丈夫”“宇宙”与“稊米”之间构成的弱与强、小与大的对比,衬托出青年的革命气质。《沁园春·长沙》中的“粪土当年万户侯”,《西江月·秋收起义》中的“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粪土”“霹雳”“暴动”更是充溢着青年对权威、对封建压迫的不屑与挑战。中国台湾作家李敖指出,“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的精神……,它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21]12
毛泽东青年时代写作的诗词中的真挚情感与宝贵精神是帮助当代青年建构青年信仰的精神良药。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22]精神信仰的建构,能够充分动员青年发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激情,自觉投身到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中来。
四、结语
毛泽东在诗词中呈现的活力与勇敢、激情与乐观的青年气质,穿越时空、激荡历史、振奋人心,具有独树一帜、大气磅礴的美学风格。毛泽东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23],这是支撑毛泽东一生的最强大的精神力量[20]199。毛泽东一生所为都未离开他深爱的中华民族,毛泽东诗词中更是书写了不少心怀国之大者的中国青年。毛泽东诗词中凸显的青年品格,为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青年,提供了坚定信仰、激发力量的宝贵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刘海飞.毛泽东的青年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2] 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 见共青团中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 刘海飞.毛泽东的青年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4] 王仕民.德育研究(第4辑)[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
[5] 张良驯.青年发展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6] 万美容.青年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7] 杨钊.对“不自觉的象征艺术”的超越——毛泽东诗词中的神话典故与豪放诗风[J].电影文学,2009(18):113-115.
[8] 胡为雄.毛泽东诗传[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9] 臧克家.毛泽东诗词鉴[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5.
[10] 张良驯.青年发展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11] 陈映芳.青年与“青年”的解体[J].南风窗,2008(10):44-47.
[12] 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小我大我[N].学习时报,2020-09-04(004).
[13] 戴立兴.毛泽东人民观及其当代意义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4] 习近平.求是.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3/31/c_1127274518.htm.2021-03-31/2021-07-26.
[15] 權延赤.领袖泪[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16] 胡为雄.毛泽东诗传[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17] 姜楠,闫玉荣.场域转换与文化反哺:青年群体与变迁社会的信息互动[J].当代青年研究,2020(2):39-45.
[18] 邓蕾.“重返”文化:青年研究未来发展的进路探寻——国内青少年文化研究前沿报告(2008—2015)[J].中国青年研究,2016(1):84-89.
[19] 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20] 周甲辰.毛泽东诗词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1] 周甲辰.毛泽东诗词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2]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2-05-12]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2/0511/c117092-32418944.html.
[23] 宋俭,孙康,丁俊萍.毛泽东精神刍议[J].中共党史研究,2005(2):97-104.
作者简介:张晶(1982- ),女,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王淼(1998- ),女,陕西咸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