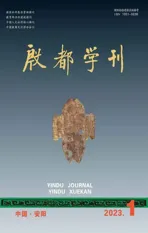甲骨卜辞“体用合一”的文体观念
2023-05-23李安竹
李安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80)
目前学界对卜辞文体的研究大多是通过卜辞不同的言说方式抽绎出多种文体(1)徐正英:《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36-41页;梅军:《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如梅军将甲骨刻辞的文体分为“占”“告”“命”“卜”“表”“记”几类,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若干潜隐于文本中的文体史线索。但是,这种做法却不利于我们对卜辞所蕴含的文体观念的理解。因为,整体性思维方式一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最根本特征(2)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页。,中国古代文体首先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它在具体语境中呈现出丰富的特征、构成及层次(3)姚爱斌:《“体”:从文化到文论》,《学术论坛》2014年第7期,第93页。。对甲骨卜辞文体观念进行探讨,也应将其置于占卜活动的整体乃至与之相关的其他活动的更为广阔的系统之中。把握卜辞这一特殊文体,需要将文本生成与功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这一文体的区分,不仅要凭借文体内在的语言、结构等形式特征,更需要凭借文体所依附的行为方式。
甲骨卜辞和殷商铭文、《商书》文诰相比,虽然都是殷商王朝具有实用性的文体,但也有各自的文体特征和文体观念。殷商时人实际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卜辞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体制特点,并在频繁的占卜活动中加以重复使用,但尚未抽象到理论形态,也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在殷商人那里,卜辞主要是用于仪式场合以“沟通人神”的,本质上是特定职事或权威人群的话语方式,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卜辞的文体体制产生于仪式场合之中,体现出“体用合一”的文体观念,这种文体观念既表现在具体的文本形态之中,也表现在文本之外。也就是说,仪式场合中的行为方式或言说方式决定了卜辞的文体特征。
一、占体:卜辞文体的整体存在和本质规定
殷商时期的社会活动大都需通过宗教的方式来谋划或施行,为此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卜辞便是对这些占卜、祭祀等活动的记录,因此我们看到卜辞中“卜”“贞”“占”之类的表述都属于动词,一开始往往是对行为的记录。卜辞的行为方式我们可以概括为“干支卜,某,贞……某占……”与“卜”“贞”“占”,相对应的是商代占卜集团中占卜人员的分类。殷人于卜事有分工,并非由一人包揽(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16页。,如刘学顺认为,商代占卜人员可以分为卜人和贞人两种,“前辞中的‘卜’‘贞’当属两件事。卜人和贞人也是有别的。卜人是管灼龟呈兆的,需要时便契刻卜辞”,“贞人是商王左右、常奉旨代商王卜问吉凶的近臣,虽然他们偶尔也灼龟卜问,但和专以灼龟见兆的卜人还是不同,他们是命龟者。”(5)刘学顺:《关于卜辞贞人的再认识》,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17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我们可以看到,在占卜活动中,卜人的灼龟呈兆活动用“某日卜”来表达,贞人宣布命辞称为“某贞”,以“贞”字引起其所宣布的具体贞问事宜。然后占人根据烧灼后呈现的兆纹来判断吉凶,预知事端,用“某占曰”来引起所占断的结果。在卜辞中,“某占曰”主要是记录商王察看卜兆判断吉凶之文,即“王占曰”;少数为记载 “叶”“子”等人察看卜兆判断吉凶之文, 而叶、子二人也是武丁时期地位显赫、权力甚大的人物。如:
(2)丙寅卜,叶,王告取兒□。叶占曰:若,往。 (《合集》20534)
以上辞例中“某占曰”这类表述出现在卜辞中,应合着命辞的设问,显陈着验辞的判断(6)林甸甸:《从贞人话语看早期记录中的修辞》,《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175页。,是卜辞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在占卜活动中,“某占曰”意味着占人(主要是商王)作为“神”的代言人在说话,这是一种神圣性在场,久而久之,“某占曰”就成为一种行为或体制的标志。
另外,商代语言的特色之一是一个词兼有名词与动词两种词性(7)赵诚:《甲骨文动词探索(三)——关于动词和名词》,《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557页。,卜辞中一个词兼具两种词性即两种文法功能的现象非常突出(8)陈炜湛:《卜辞文法三题》,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18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商人在对不同的言说方式、行为方式进行区分以后,辅之以动作的发出者或接受者、动作产生的地点等相关因素,逐渐派生出相应的言说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来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基于此,“占”这一行为逐渐发展成“占体”这一文体结构,这是卜辞文体观念明晰的重要一环。
卜辞所依赖的宗教背景,是其文体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文体的性质和功能也由此而决定。从文体分类来说,卜辞是一种占体,它是占卜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包含在行为仪式这一整体之中,又是行为方式文本化的结果。将卜辞的文体确定为“占体”,而非“卜体”或“贞体”,是因为在整个占卜活动中,“某占曰”是对卜兆的判断,是个人意志(主要是商王)在神圣体制中体现的关键,也是神权的中心环节,由此也决定了占辞在卜辞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四部分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卜辞是“占体”,最能体现其宗教内涵和文体特征,这事实上也暗合了卜辞“体用合一”的文体观念。
二、功能性重复:“体用合一”文体观念的产生
商人占卜频繁,记录者于频繁的占卜活动中无意识形成了记录的定式,因此,卜辞的结构体式、句式套语等都呈现出程式化的特点。卜辞文体产生于频繁的占卜活动中,其结构体式、句式与套语等方面的重复运用,对卜辞文体观念的明晰至关重要,吴承学将这种重复称为“功能性重复”(9)吴承学:《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第42页。。正是在频繁的重复之中,殷商人开始认识到卜辞区别于铭文、《商书》文诰等的特点,对卜辞特殊的体式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卜辞的文体观念也一次次得到确认,从而固定下来。
首先,对卜辞的程式化结构体式的重复运用。甲骨卜辞是程式化的语言,卜辞结构体式的程式化早已被学者所认识,如陈梦家指出:“卜辞是王室占卜的文字,所记载的内容是有局限性的,格式是程式化的,又多是问句和事后的应验。”(1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85页。管燮初称:“卜辞的体例由于内容限制了它的形式,虽然也有记载详略的不同,总脱不了一套公式。”(11)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中国科学院,1953年,第4页。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前辞(或称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四部分。如:

四月。二告。
其次,卜辞中还有表不同行为方式或言说方式的套语的重复使用,这体现为行为方式或言说方式的类别化。这类套语除了上述“卜”“贞”“占”之外,还有“告”“祝”“令”“曰”“言”“乎”等等。比如“告”所引起的都是报告之辞,做祭祀动词时,多数用于殷王告祭神祖,既反映祭祀目的,又说明祭祀内容。如:
例(5)为臣属对商王的报告,所报告之内容是有关邻邦敌人的入侵。此外,卜辞中“祝曰”所引起的都是祭祀活动中的祝辞,表达某种愿望。如:
(6)癸亥卜,王贞,旬日八庚午,又祝方曰:在……(《合集》20966)
例(6)“祝方”应是向方神祝祈,“在……”当是祝辞。又如,卜辞中记录“令”“乎”的卜辞,多为商王对臣属的发号施命。如:
(7)丁未,贞,王其令望乘帚其告于祖乙。 (《合集》32897)
裘锡圭认为这版卜辞中的“帚”应该读为“归”(14)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312页。,因此,例(7)是卜问把命令望乘回去这件事报告给祖乙。

甲骨卜辞用言语活动的动词来引起言语行为内容,揭示了所引言语的言说方式、功能和性质,具有一定的文体意义。这说明了早在商代,卜辞对言辞的引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言语、行为的文体性质的认同。
甲骨卜辞结构体式的程式化、行为方式或言说方式的类别化都在频繁的占卜活动中被重复运用,当这些固定的体式、特殊的言辞被反复运用时,人们对卜辞“体用合一”的文体观念也随之逐渐形成。虽然当时人并未直接从理论上对卜辞文体及其文体观念加以表述,但已经在他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显现出来。
三、探究“人神关系”:“体用合一”的功利观
卜辞“体用合一”的功利观,不同于以典册为主的经典文献的实用性记载,而是通过对占卜过程和占验结果的记载,积累占卜经验,以探求“人神关系”,指向的是占卜规律和“人神关系”的探索。这是商人记载占卜之事的目的,也是卜辞“体用合一”之“用”的核心诉求,即商人为何要对占卜进行记录,尤其是为何要补充记录验辞。

为何要补充记录验辞?这是因为在所卜事件发生后,将已经记载的占卜活动与其进行对比,即将占辞与验辞进行对比,不仅可以发现日子的吉凶,还可以发现哪些事情应验。《周礼·占人》记载:“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15)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9-650页。《周礼》所记载的在占卜之后将记有卜辞的甲骨收藏入府,以便考察占卜的应验与否,这一制度正是来自于商代。众所周知,较之筮占有一套系统的逻辑可以推衍,占卜更重的是占人的经验。因为龟甲占卜主要是通过灼龟观兆来判断吉凶,而兆纹变化无常,即使是商代后期已经开始人为控制兆纹的走向,但也不可能完全把握呈现兆纹的规律,由此可见兆纹的变化还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对兆纹进行判断时,吉凶判断与占人的经验密切相关,它更看重经验的因素。而在占卜之后补记上验辞,将之与占辞对照,就可供占卜者参验,发现并总结兆纹和占卜应验与否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占断的准确性。也就是说,卜辞记载的虽然是眼前的现实,是实际发生的占卜行为,但其目的并不是在所占卜事情本身,也并非出于记录史实的目的,而是看占卜行为应验与否,更多的意义是探讨占卜规律和“人神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商人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
将同样记载占卜文化的甲骨卜辞和《周易》进行对比,其差异是明显的,前者记录了大量的占卜活动和当时的占卜结果,记载的是具体的占卜事例,而并没有记载殷商时人的占卜制度、具体的占卜方法和基本原理,更别说有关的理论和经验总结了。这些内容直到《周礼》才有所反映,但《周礼·大卜》还载有“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的说法,贾公彦疏引郑玄《易赞》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16)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635页。。可见,《归藏》是殷商时期有关占卜的著作,应是与《易经》一类的占卜经验。或许,在商代,龟甲是专门用来记录具体占卜事例的,而关于占卜的经验总结则载于典册文献《归藏》。周人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周代的卜筮进一步总结出了卜筮的集大成之作《周易》。
上述我们主要论述了占卜活动中记录验辞的目的是为了将事实与占卜结果进行对照,看是否应验,反映出商人在占卜活动中探索“人神关系”的努力,揭示了商人的鬼神信仰。这种对“人神关系”的探索正是卜辞这一文体的具体功用,与铭文颂美记功之用是显然不同的。卜辞的这种将文辞运用于宗教礼仪场合最终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客观上开启了后世“文以载道”“讽谏政治”等文章为王朝政治服务的传统。
四、辞尚体要:“体用合一”的文辞观
文体特定的表现内容与措辞相关,不同的文本导致不同的语言风格与大旨。由于卜辞是运用于仪式场合“沟通人神”的,甲骨只是记录与占卜有关的内容,每片小小的甲骨容纳不下较长的叙事,所以卜辞也体现出辞尚体要、质简无文的文辞观。
与同时期的铭文、《商书》文诰、颂诗相比,卜辞简要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卜辞记载简短,如命辞,仅是贞卜之事的极其简单的提纲挈领的记录。卜辞常常在有限的篇幅内,用极简之笔把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件记述清楚。一般来说,每片甲骨载有十字左右。目前所见字数最长的一篇卜辞,为《合集》137正、反。学者考证正、反是一篇卜辞,补足残缺文字后,共有14行154字。在这条仅154字的卜辞中,记载了众多人物,记载了纷繁的灾难事件,而且还已经注意遣词造句,用字也非常考究(17)黄天树:《论字数最长的一篇甲骨卜辞》,《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辑,中华书局,2016年,第21页。。
卜辞语言精炼,篇幅短小,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受限于甲骨文字书写的载体。殷墟出土最大的龟腹甲,长44厘米,宽约35厘米,背有凿孔204个。牛胛骨之最大者,长43厘米,宽28厘米,此骨最早为罗振玉收藏,著录于《殷墟古器物图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甲骨载体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殷商时期的贞人只能简要记述某件事。
卜辞叙述简要的关键原因除了书写载体的局限之外,更在于其使用环境。卜辞运用于占卜或祭祀的仪式活动,是一种相当独特的言语形式,它是以商王为代表的集神权与政权于一身的“天胤神嗣”,通过灵龟这种往还于天渊两界的媒介,向“祖先神”或“至上神”询问未来行动之吉凶休咎的语言活动。探寻“神意”、预知吉凶、了解未来,获悉“天命”以指导人类行为,既是卜辞的目的和功能,也是占卜最核心的动机所在。在这种强烈的功利动机下,卜辞自然以叙述精约为主要标准。而占卜的结果会对商王的决策发生影响,即使不能直接左右商王的意志(因为如何解释卜兆毕竟取决于商王自己),但至少提供了来自“神界”的信息,此在当日之分量不言自明,即就心理的效果而言,其影响也不容低估。因此,在此心态之下,华美的言辞纯属赘余,要言不烦才是合理的选择。
在商人的意识中,人间的理由与“天命”没有直接的关系,“天命”无条件地主宰一切,不能以任何的人间理由来推断、判断“神意”,因此,人只能永远保持一种戒惧的姿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叙述,只能是一种见证性的载录。因此,卜辞里极少有评论和说明,也不抒发感情。虽然我们能从卜辞的记载中感受到贞人的浓厚的宗教信仰,但卜辞在整体上仍是不反映情感的,也不给出理由和解释,在文辞上呈现的是一种唯命是从的姿态。
除了强烈的功利性目的外,卜辞作为占卜组成部分被赋予的神秘和神圣性质,也是造成其质简无文、辞尚体要的原因。在绝地天通之后,占卜活动意味着一种莫大的特权,是保持“人神之间”精神联系的主要沟通形式。其言语者之尊贵的身份与地位,其贞问对象的无上威力和权能,它那既为超越的需求提供强烈的精神满足,又为其行为的合理性提供权威依据的双重功能,都使得甲骨卜辞成为殷商社会言语活动中的一种具有神秘色彩和神圣地位的变体形式。贞人不仅掌握着占卜和祭祀的口头话语,还对其进行书面记录,并加以保管。他们根据龟卜、骨卜对人事、自然界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征兆向神灵寻问,将“问神”的占卜言辞刻写记载在占卜用的龟甲、兽骨上。所记载的并非人世间发生的事情,而是将人们“问神”的言辞即命辞作为中心内容,同时将进行占卜的时日和贞人名一起记录下来。因此,卜辞并非是“俗界”的记录,而是“人神之间”的神圣的记录。占卜是为了祈求灵验,祭祀是为了求得保祐,两者都属于祈祷的范畴,是“祈祷记录”。仪式中,祈祷不仅仅是说话,还“以言行事”,是人在与神灵沟通时恳求能从神灵那里得到帮助的一种虔诚的语言表达方式,起“沟通人神”的作用,将仪式推向高潮。在这里,仪式中的符号(即文字)具有行为的力量,言语和行为是不可分离的,文字在这里实现了“以言行事”的功能。因此,刻于甲骨上的卜辞在商人心目中的神圣性和神秘性自不待言。当然,卜辞的神秘并不必然导致形式的润饰,恰恰相反,言简其辞正是增加神秘感的适当方式。
运用于仪式场合的卜辞,由于其神秘和神圣性,再加上文体的简质或文例的限制,在实际应用中不得不力求简短精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散文在发轫之初就体现出了“辞尚体要”的特点。这种“辞尚体要”的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推崇的“尚简”传统,即以简练精当的文辞传达出充实、概括性的内容。这一要求,后来成为古文写作的基本要求,对文学创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结语
综上,我们认为,卜辞是一种特殊的运用于仪式场合的占体文学,其“体用合一”的性质决定了结构体式的程式化和语言方面的“辞尚体要”。这种具有极强功能性目的的应用性文体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文学体裁。卜辞将文辞运用于宗教礼仪场合以探求“人神关系”,并最终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后世“文以载道”“讽谏政治”等文章为王朝政治服务的传统。具体而言,卜辞文体的程式化特征,也影响了后世公文的写作模式;卜辞体现出来的“辞尚体要”观念也成为后来古文写作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