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忘乎道术”
——我的学思历程
2023-05-18杨辉
杨 辉

动念写作此文时,正是感染“新冠”的第二天。头痛欲裂,咽似刀割,浑身如同燃起大火。读书已属不能,更遑论写作。此后数日,卧病在床,诸事皆废,整日昏昏欲睡却难以入眠。半睡半醒之际,思绪纷纷,莫有定时,倒是此前问学时的数个“路标”渐次呈现并愈来愈清晰。
一
我做当代文学研究及批评,始于2013 年,但追溯“缘起”,却还需上推数年。2009 年秋冬之际,因突然意识到路遥逝世二十周年将近,坊间却无一部系统、完整的“路遥传”,遂发愿为之努力。其时,由王西平、李星、李国平撰写的《路遥评传》已出版多年,但该书“评”多于“传”,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价值极大,但于热爱路遥作品并对其人生兴致甚浓的普通读者而言,却颇有些难度。宗元所著《魂断人生——路遥论》中,对路遥生平行状也有较为细致的描述,因并非全书重心,极多细节未曾展开,读来颇以为憾。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梁向阳《路遥传》的出版,尚在数年之后。在通读(绝大多数作品是重读)路遥的全部作品及相关回忆和研究文章之后,我编撰了《路遥年谱简编》,以为日后写作时查考的方便。这样的案头工作持续了近一年,虽然琐碎、辛苦,但收获极大。此后,我觉得资料文献的阅读工作应该告一段落,下一步的重心应该转向实地走访。2010 年8 月,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后,我列了一份详细的实地考察计划。考察的第一站,是去延安拜访曹谷溪先生。
8 月的延安,酷热难当,凤凰山上绿树虽多,却连蝉鸣也无,空气似乎凝滞,人也约略有些恍惚。而在曹谷溪先生的住所,我却从他关于路遥的生平写作等方面的详细讲述中知晓了他人难以尽知的路遥的思想和心路历程,大受震撼,也使我对即将展开的写作有了新的认识和考虑。此行更为重要的收获还不止于此,曹老师对他所藏重要史料的毫无保留,让我有幸也极为惊喜地读到《人生》发表前后路遥与他的书信数通。其时,这些书信并未公开,其间所涉之具体人事足以为读解此一时期路遥作品的重要参照,自然叫人惊喜万分。惜乎其时我并无“史料意识”,也未觉得以之为基础拓展研究思路的意义,自然也未有论文写作的动念。所幸三年后,这数通书信经路遥研究专家梁向阳先生疏解后公之于众[1],也果然产生了较大影响。
让我更觉始料不及的重要收获,发生在接下来的延川之行中。辞别曹老师,我继而在梁向阳先生的带领下参观了位于延安大学的路遥文学馆。特意登上文汇山拜谒路遥墓后,我们联系到曹老师介绍的延川作协的诗人白琳。在白琳的带领下,我们从延川县政协的一位工作人员处拿到了《延川县志》,也去到路遥学习过的延川中学体会多年以前青年路遥隐微的心迹。而当置身于延川县前郭家沟的路遥故居时,我更为深切地意会到70 年代初期路遥何以在作为知识青年返乡之后痛感其青年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就此式微,也进而明白促使他不息奋斗的动力究竟何在。是日晚间,我在延川县一家十分简陋的宾馆中翻阅县志,回想起下午从郭家沟一位早年与路遥交往甚厚的老人口中得知的路遥少年时期的若干故事,不禁感慨万千……
此后年余,我陆续走访了路遥的出生地清涧县石咀驿镇、其写作《人生》和最后完成《平凡的世界》的甘泉县宾馆、写作《平凡的世界》初稿时所居之榆林宾馆,以及他在榆林写作时为休息而短暂游玩过的神木县(今神木市)尔林兔等地。至于他长期工作和居住的陕西省作家协会,我更是去过多次,也拜访过多位与路遥交往甚厚的前辈,获得极多路遥生前重要的生活细节且从中体味到其令人唏嘘感叹的隐秘心迹。反复酝酿、调整构思的过程中,个人身在乡间的生活和生命经验也被空前激发。梳理路遥令人为之歌、为之哭的生命遭际和心路历程之际,也融入了我自身因文学而改变的人生道路中的思虑种种。如此已近两年,计划中的《路遥传》逐渐由模糊到清晰甚至于呼之欲出了。
二
孰料就在写作《路遥传》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之时,受一位朋友的邀约,我接受了曲江出版传媒集团策划的“大道楼观”系列丛书之一种的写作任务,原计划只能暂且搁置。如今回想起来,虽然有些临时救急的意思,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写作任务落到我头上,也不能说毫无来由。自少年时起,我便对中国古典传统及其所持存开显之生命境界心向往之,中学时便反复阅读《道德经》,《庄子》中《逍遥游》《齐物论》《秋水》诸篇也几近成诵,并深为之心折。后来所学专业虽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的比较诗学方向,也自然在西方文艺理论的研习上用力甚多,但始终持续关注古典思想、文学及文论的研究现状,尤其对道家思想用心颇多。时日既久,约略也有些心得。差不多十年后,在为《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写作“我的批评观”时,首先跃现于脑海的便是当时在道教及道家思想虚心涵泳上所作的功夫,以及其时断无法料及的对自己文学和生活观念长久的影响:
因缘际会,转事文学批评之前,我做过一段时间的道教研究。其时早已对昔年用力甚勤的理论研习深感厌倦,心里渴望投入广阔无边的生活世界,却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犹记当年细读《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甘水仙源录》《西山群仙会真记》及皇皇四十九大卷《中华道藏》所载之道门玄秘时所意会精神的震撼;也曾在终南山古楼观、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大重阳宫、佳县白云观等洞天福地摩挲古碑、徘徊流连,遥想历世仙真于各自时代精神证成而至于凭虚御风、纵浪大化的超迈风姿。当此之际,约略也能体味目击道存的大寂寞、大欢喜;再有《中华道藏》收入儒、释典籍且将之融汇入自家法度的博大的精神融通之境,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形塑了我的文化观念:不自设藩篱,有会通之意,常在“我”上做功夫,向内勉力拓展精神的疆域,向外则完成“物”“我”的辩证互动,不断向“传统”和无边的生活世界敞开。此番努力,论表象似近乎儒家所论之“为己之学”,究其实当归入道门“天”“我”关系之调适。
事后回想起来,上述理解似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但当时却下过极大的功夫,说是“脱胎换骨”也不为过。就外部而言,为搜集资料,便颇费了一番功夫;就内在观念而言,如果仍在现代以降之观念中理解道门仙真的生平行状,又如何可以明了其修其行之现实和精神价值?故而作观念的自我调适分外紧要。此前因个人性情所使,我对与“逻各斯”并行的“秘索思”思想心有戚戚,故而用心甚多。细读道家文献,于周至楼观台、西安鄠邑重阳宫、佳县白云观等地寻觅仙真遗踪,自不难意会灵性生命之超迈境界。而不以现代以降之观念成规唐突古人的思路,大致就在某一日身在白云观文昌阁外遥望黄河远上、大地苍茫之际顿然成形。这当然有政治哲人列奥·施特劳斯以古人的方式理解古人的思路影响的痕迹,或也不乏明儒常论之成圣工夫的潜在成就。有了这个想法做底子,后来的写作出乎意料地顺利。计划中的15 万字变成了25 万字,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当时的感觉,真如打开了水库的堤坝,思绪纷纷如水涌出,随物赋形不可遏制……如果不是责任编辑及时“叫停”,这一部小书估计会有50 万字左右的篇幅——其时所作的资料储备颇为扎实,至全书完成时也不过使用了十之四五。这一部主述终南山古楼观历世真仙体道经验的小书《终南有仙真》,所涉时间起始自春秋战国,结束于明末清初。所写虽集中于道教人物,却不可避免地需要涉及千余年间儒道释三教关系及其与时俯仰的复杂论题。因此机缘,我用心读了些三教的核心典籍及相关史料,尤其对佛道二教关系史颇多关切,多少也能窥得其表面的观念纷争后所涉的复杂时代命题及其隐微义。原计划在《终南有仙真》完稿后,再写一部《终南山古楼观历世仙真行状考辨》,但仍是临时插入的写作任务,中断了其时已然准备充分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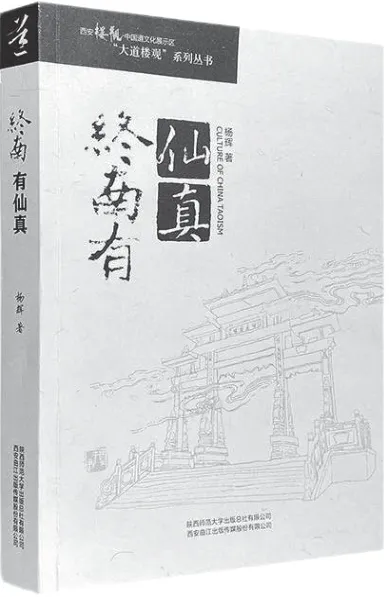
杨辉:《终南有仙真》
三
2012 年秋,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之邀,我有了一个编选《贾平凹文论集》(以下简称《文论集》)的机会。我读贾平凹,始自90年代初,算来已二十余年矣。大学一年级时,我几乎读完了贾平凹的所有作品,包括孙见喜先生所著之两卷本《鬼才贾平凹》等资料,也读过一些研究文章,但并未有惯常所谓的“研究”计划。只是喜欢,别无他图,也便读得随性,读得自由。这样漫无目的的阅读“坏处”当然很明显——难以窥得作家写作的整体面貌;“好处”也同样显明——不受约束,个人的心得感受便多。其时既有《文论集》编选的机缘,我便想通过编选工作,将自己多年阅读贾平凹作品的心得灌注其间,不独将其类乎“文论”的作品编辑成书而已。
此后两年余,我全力以赴地投入编选工作。说来惭愧,此前我从未受过专业的文献史料学术训练,所能依凭的不过是为写作《终南有仙真》做准备过程中“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尽可能“穷尽”史料的些许经验。当然,我也悉心学习了前辈学者史料整理的观念和方法,其时对己启发甚大的是王风先生自述其编辑《废名集》的思考的文章《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在我编选《文论集》的过程中,此文稿常置案头,随时翻阅,获益良多。既然不愿所编《文论集》不过是作家类乎“文论”的文章的简单合集,便也需要有新的思考,要能显现出编者自身对所收文章价值的整体考量。搜集文章的辛苦无须多论,《文论集》编选真正的难度,主要即在此处。
或是潜在得益于《终南有仙真》写作过程中观念的自然变化所致之阅读作品重心的转移,此番再读贾平凹作品及相关序跋、书信等自述写作经验的文章,我更为注意的是其间所彰显出的贾平凹赓续中国古典传统的努力,及其之于作品境界和审美表达方式拓展的意义。这种意义当然不局限于贾平凹一人,由之上溯,可知孙犁、汪曾祺、沈从文、废名,甚至包括鲁迅、周作人等作家作品与中国古典传统间之承续关系。如孙郁先生所言,“五四”一代人服膺近乎“全盘反传统”观念者居多,但要以此为圭臬概而论之,却也并非文学史事实。若注目于此,或能打开读解“五四”以降新文学的新进路也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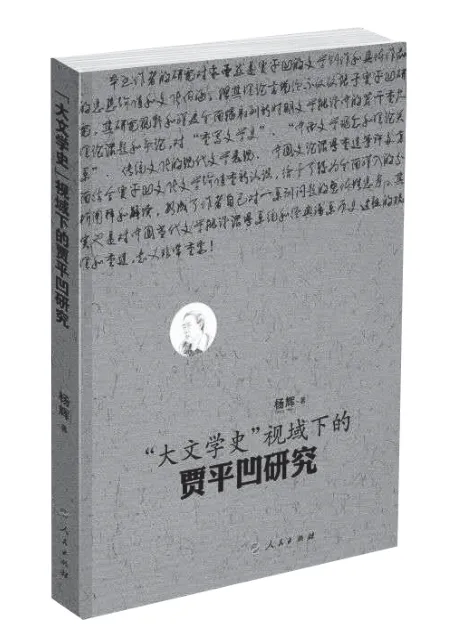
杨辉:《“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
也是机缘巧合,就在我为编选原则而颇费思量之际,王德威先生应邀来陕讲学。在陕西师范大学逸夫科技楼北报告厅中,他以“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为题,作了极富观念拓展意义的报告。其以“抒情”二字在中国古典传统之意义流变为切入点,广泛论及“抒情传统”在中国文学(不拘于古典文学)中因应时代的不同变化。而在现代以来百年中国文学中,“抒情传统”则以沈从文始,以贾平凹终。此种宏阔思考让我为之一震,原本关于编选原则的犹疑不定,顿然消隐。我决定以古典传统赓续的显隐为核心,编辑这一套书。
又一年后,《文论集》分《关于小说》《关于散文》《访谈》三卷出版,也基本贯穿了打通古典传统和现当代传统的思路。三卷编讫,我仍觉未能充分体现贾平凹融通古典传统的多样面目,于是再编《贾平凹书画论集》(未刊)。编辑过程的一些未必成熟的想法,差不多都写进《从“史料”到“文献”——以贾平凹〈文论集〉〈书画论集〉的编选为例》(《文艺争鸣》2016 年第8 期)及《文论集》的编选说明中了。也因有了全面、系统地阅读贾平凹文论文章的机会,一些原本模糊和不自觉的想法渐渐如一颗种子发芽、生长一般,变得清晰起来。而有了一定的自觉意识,“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便在前辈和同代学者中寻找观念的“同道”。古典文学及文论界会心于此者颇多,故而后来的数年间,我在阅读古典作品及相关研究文章上用力甚多。如此,尝试性打通中国古典传统和现当代传统的“大文学史观”(《“大文学史观”与贾平凹的评价问题》,《小说评论》2015 年第6 期)的想法逐渐发生。后来发现,这一种自己劳心费力甚多所获之体悟并非“空谷足音”,在港台地区及海外汉学家那里,早已有较为成熟的形态,只是不曾将之广泛延伸至现当代文学而已。如王德威以陈世骧所论之“抒情传统”说打开重解现代文学的新路;浦安迪以中国古典文论之核心概念、范畴和术语读解“四大奇书”的阐释方式,以及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界柯庆明、颜昆阳、郑毓瑜等学者“重解”古典传统的努力等,虽未以“大文学史观”名之,却确实在作着古今、中西融通的探索,成果也堪称斐然。以他们的研究为引导,我随之有计划地阅读古典文论的重要典籍,虽未必全然弄通,收获却是极大,也深感自己逐渐走出了自晚清开启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藩篱。当此之际,真如令狐冲在华山后山偶遇前辈高人风清扬,得受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之效的提点,胸怀因之大畅,眼前逐渐现出“一个生平所未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天地”。
四
此“天地”之新,不独方法的转换,更含思路的调适。有此做底子,再得机缘谈《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及柳青、路遥的文学观念问题,想法自然与前不同。古典传统与现当代传统的融通当然重要,“延安文艺”与共和国文学的贯通也不可不察。更何况此前在为“路遥传”写作准备的过程中,已感“延安文艺”“十七年”与“新时期文学”“断裂”思路的局限。仅以路遥论,其创作起步于60 年代至70 年代之交,发展于70 年代至80 年代初,“集大成”于80 年代中后期,其间虽与当代文学史的数个分期“合拍”,思路和方法却并不相同。概而言之,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甚或“延安文艺”的超克关系,在路遥的写作中并未发生。换言之,即便身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力几乎无远弗届的80 年代,路遥的写作仍然扎根于柳青传统的观念和审美方式之中,并成为“延安文艺”精神在80 年代延续的典型。由此,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以降文学观念的连续性意义上读解柳青、路遥的写作,其意义便不仅止于“重解”陕西文学经典,而是蕴含着打开理解当代文学新路径的可能。即便自谓以“剥离”柳青影响而完成《白鹿原》写作的陈忠实,其人其作仍可放入柳青传统的延长线上理解。其他如贾平凹、陈彦,早期写作也皆受以柳青为代表的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即便此后有基于自身心性、才情的进一步发挥,仍可归入现实主义因应时代和现实之变的自然调适。颇具意味的是,柳青、路遥作品对中国古典传统的“不见”,在陈忠实、贾平凹、陈彦作品中得到了路径不同却大义相通的发挥。由《蓝袍先生》至《白鹿原》,儒家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的渐次式微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一曲“挽歌”而不作进一步的反思;贾平凹《废都》《古炉》《老生》《山本》及新作《秦岭记》将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传统大加发挥,遂开当代小说以中国思维书写中国经验的重要一维,其意义也不局限于文学资源的个人选择,乃是有表征当代文学整体经验的重要意义。陈彦先以现代戏名世,其“西京三部曲”影响遍及大江南北,转事小说写作后,《装台》《主角》《喜剧》及新作《星空与半棵树》不仅表明其融通自身此前生活和写作经验的努力,亦呈现出会通以柳青、路遥为代表的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打通中国古典传统的多元统合以开出新境的努力。至此,融通中国古典传统、“五四”以降之新文学传统及《讲话》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思路几乎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如不以这种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史思路读解作家作品,则虽有“洞见”,但“盲见”和“不见”更为突出。数部当代文学史在柳青、路遥、贾平凹评价上的“困难”,原因盖出于此。

杨辉:《陈彦论》
上述论题,基本划定了我晚近十年研究的基本范围,而数个论题从创生到发展的基本过程与个人生活和生命经验的深层“互动”,更说明此间“问题”并非仅具学术意义,而是在多个层面上涉及更为广阔的生活和时代议题。此属现实主义的世界关切要义之一,亦是古典传统所述之文化“因革损益”观念的基础。进而言之,无论《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山本》《暂坐》还是《主角》《喜剧》《星空与半棵树》及《太阳深处的火焰》《少女萨吾尔登》所影托之世界和精神论题,哪一个又是可在单纯的文学范围内得到“解决”呢?有此感受,或许还是施特劳斯观念的潜在影响使然。而皮埃尔·阿多所论之“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在此亦可转换为“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学研究”。学术与广阔的生活世界的交相互动,也因此必然开出儒家“内圣外王”的论题——即便不依赖儒家思想以及与之相应之概念、范畴说明,也在精神意义上切近其中论题。如此,论述《应物兄》及其所涉之儒家知识人的当代境遇的小文便有了落脚处——落在观念传统之现代境遇上,这既是学术议题,亦是无从回避的生活难题。此难题不仅关涉到古典传统观念意义上的现代转换,更关涉身处其中的个体得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人格的建构问题。梁任公在20 世纪初即忧心于此,并有专书申论发明,惜乎其时及后世皆应者寥寥。窃以为,若不着意于此,则在古典传统的赓续上即便用力甚勤,也难以全功。
如是思考,最后仍需落实于当代文学史的观念问题上。时至今日,简单地持守“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之说未必合宜,但当代文学史撰写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性”,也日渐显明。如张均所论,当代文学之所以应“暂缓写史”,重要也难解的问题之一,是“源自‘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启蒙文学史观对当代文学的宰制与遮蔽”虽“久遭诟病”,但“如何调校启蒙史观”以“有效兼容‘人民文艺’”,“恐怕是需要20年才能切实解决的理论难题”[2]。罗岗在《“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境遇》中,对此亦有论说:

2020 年,本文作者参加陈彦《喜剧》分享会
在新形势下重提“人民文艺”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并非要重构“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的二元对立,也不是简单地为“延安文艺”直至“共和国前三十年文学”争取文学史地位,更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学的“人民性”高度,在“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相互缠绕、彼此涵纳、前后转换、时有冲突的复杂关联中,描绘出一幅完整全面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图景: 既突破“人的文学”的“纯文学”想象,也打开“人民文艺”的艺术空间;既拓展“人民文艺”的“人民”内涵,也避免“人的文学”的“人”的抽象化……从而召唤出“人民文艺”与 “人的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五四文学”与 “延安文艺”在历史叙述上的前后贯通,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转折意义上的重新统合。[3]
此中思考,意义颇丰,绝非学术研究范型转换所能简单涵盖。回想起来,我近十年间思考的问题的重心虽屡有转变,但基本的方向或许正在此处。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贯通,必然涉及与“五四”以降之新文学传统,以及中国古典传统的关系问题。此问题的解决,也必然需要扎根于新的时代观念和现实经验之中。如此,“古”与“今”、“中”与“西”的观念藩篱一旦破除,眼前自显障蔽尽去的活泼灵机,亦有学术观念全新视境的展开。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不是矫情,亦非故作姿态,乃是“用世”之心屡屡受挫后的自然感发。晚近数年,“入世”愈深,愈发觉得由贺照田发起并持续推进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背后的精神和现实关切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其价值并非仅止于学术观念的选择,而是包含着学术与生活世界、与大地、与他者、与无穷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血肉相关的具体性。这里面有友爱和同情的政治学,有内在的、充盈的、沛然莫之能御的巨大的振拔力量。如果说以学术为志业能够安妥身心的话,窃以为,其根本的依托或在此处。
五
2022 年年底,再逢个人生活道路转折的重要机缘,孰料“惶惑”实多于“欢喜”。近一个月间,头脑中时常映现那个尚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在月牙山下灞水边苦读中外文学名著且萌发最初写作欲念的形象。那时虽心性未定,却已有寄身于文学的坚定信念。数十年过去了,年龄渐长,成绩有限,生活道路也屡有变化,爱文学的初心却未被消磨。遥想当年,读《庄子》,至“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颇有些心动,以为窥得学术与人生的真义所在。此后多年,虽自西方文论研习转至道家、道教研究,再至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区分颇大,心思却始终如一 ——俯仰于天地间,感通多样消息,于被给定的时代和现实中上下求索,勉力开出自家面目,若能稍窥“相忘乎道术”之境,则吾愿足矣,不复他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