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昌祯的法学人生
2023-05-18汪琬琦
汪琬琦

1949 年10 月1 日,开国大典,大学生队伍载歌载舞走过天安门。时代的光芒照耀着新中国,也照耀在巫昌祯年轻的脸庞上。这年她20 岁,刚到北京不久,还沉浸在新生的喜悦中。天安门广场上群情振奋,欢歌沸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1]。
巫昌祯,1929 年生于江苏句容,是家中唯一的女儿,一头短发,聪颖开朗。1947 年,家道中落,母亲病逝。一年后,她千里远走,北上求学,考入以法科闻名的朝阳大学。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会去向哪里。
共和国需要新法律
共和国初创伊始,百废待兴,国人婚姻生活的封建底色依然非常浓厚。20 世纪40 年代的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1951 年改编成风靡一时的评剧《刘巧儿》)中,女主角满面愁容叹道:“姐妹们哪,我好心酸,我的婚姻父母一手包办。临上轿还未见过新郎面,一生的依托心上悬。”这种情况在当时仍旧十分普遍。
1950 年5 月1 日,《中 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律性质的法律,颁布时间比1954 年的宪法还要早四年。用巫昌祯的话说,婚姻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头生子”[2]。
这部婚姻法共8 章27 条,第一章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部婚姻法彻底颠覆了我国延续数千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传统,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男人随意停妻休妻等封建婚姻制度的糟粕,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四大基本原则。有了法律的保障,婚姻自由的观念逐渐被国人接受,“刘巧儿们”终于可以“自己找婆家”了。
1950 年的婚姻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当时正在读大学的巫昌祯,也在高校院系调整中几经辗转。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人民政府接管朝阳大学,成立了干部培训班性质的学习队,巫昌祯在革命队伍中接受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朝阳大学的基础上,一所新的学校——中国政法大学诞生,巫昌祯被保送编入该校三部,主要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和法学理论的学习。1950 年3 月,中国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等革命学校合并组建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巫昌祯又进入该校法律系求学。1954 年,巫昌祯以全优成绩毕业,成为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法学毕业生。毕业后,她与在校相识的庚以泰结为夫妻,并被一同分配至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不久,巫昌祯迎来了第一次参与立法的机会。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通过不久,即组织民法起草。巫昌祯作为民法教研室的业务骨干,被选进了民法典起草小组,小组成员还有著名法学家芮沐、佟柔、杨怀英等。在主要由全国人大立法部门的领导和政法院校学者构成的民法典起草小组里,巫昌祯是最年轻的成员[3]。起草小组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隔壁就是周恩来同志和宋庆龄同志的办公室。据当时起草小组的成员金平回忆:“总理还主动过来询问我们的生活,关心我们的工作。”[4]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民法典起草工作甚是艰难。起草小组不仅要参考苏联、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条款,还要翻阅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资料,然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项目分解组织起草。起草小组经常加班开会,会后还要整理总结,工作量很大[5]。
为了完善立法工作,巫昌祯去往武汉、广州、上海作调研。她称这次实地走访“很锻炼人”,“了解了一下实际,对我讲课有很大影响,回来以后学生反映就很好,至此也形成了我讲课的风格,从不照本宣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6]。求真务实、活学活用也成为了巫昌祯一生研究与教学的基调。
当时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共525个条文,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部法律没有公布即被搁置,但这也加深了巫昌祯对包括婚姻法在内的民事法律的了解。然而,还没来得及有所作为,时代的洪流便滚滚而至。

青年时期的巫昌祯
1958 年,北京政法学院的民法教研室被撤销,巫昌祯只好改教毛泽东著作和古汉语等课程。“文革”期间,巫昌祯受父亲的旧官吏身份影响,只好“靠边站”。1970 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庚以泰被分在安徽省公安厅工作,巫昌祯回京留守,照顾孩子。情势所迫,从教16 年的巫昌祯只得放下教鞭,提前退休,在一家校办工厂的会计室谋职。当时,四十岁出头的她远离了自己的专业。
参与婚姻法修改
国家的立法建设一度陷入停滞。“从1959 年至1977 年,整整19年基本没有立法活动。”[7]直到1978年,春回大地,北京政法学院复建,巫昌祯的退休令被撤销,她才得以重回讲台。就在这年年底,婚姻法修改被提上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有起草民法的经验在先,巫昌祯被北京政法学院派去参加婚姻法的修法小组,这让她错过了几乎同时启动的民法通则起草项目,自此正式转入婚姻法学的轨道。

孙丙珠(左一)、巫昌祯(左二)、薛梅卿(左三)、严端(左四)被称为中国政法大学“四大才女”
在巫昌祯看来,修改婚姻法也有现实原因。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爱情要以政治为基础。”有的夫妻感情不和,法院却说:“你们都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子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离什么婚呢?不许离!”[8]由于社会压力,很多人不敢离婚,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特别是离婚自由的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9]。
所以,这次修改婚姻法,巫昌祯观点鲜明:要解放离婚。据巫昌祯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讲,这在当年可谓“石破天惊”[10]。当时修改婚姻法,有人主张“理由论”,只有理由正当,才能提出离婚,否则就是为婚外恋等不道德行为大开方便之门;有人主张“感情说”,并引用恩格斯的名言:“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11]巫昌祯是“感情说”的拥护者,且非常反对“好人不离婚”的说法:“我一直主张离婚不是悲剧,而是悲剧的结束。人们应该有离婚的自由。”[12]对于这一条文,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整整讨论了两个小时[13]。最终,婚姻法的判决离婚原则修改为:“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高速公路软土路基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这是因为软土的核心构成成分是黏土以及淤泥颗粒,其中有一部分颗粒的有机质因为在各种地质环境中沉淀,就让软土内部形成了絮状的结构,这种结构的空隙是相对较小的,不过更多的软土其内部结构还是具有较大的空隙,含水量也比较高。
从实际出发,是巫昌祯一以贯之的原则。这一点也体现在她对修改法定婚龄的态度上。1950 年的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是女性18 周岁、男性20 周岁。1980 年,为响应计划生育政策,不少专家建议将婚龄推迟至女性25 周岁、男性27 周岁。巫昌祯很不赞成:“婚龄过高不符合女性身体成熟的‘自然属性’,法律应该关注民生,温和稳健。”[14]正是参考了她的意见,1980 年的婚姻法将法定结婚年龄改为女性20 周岁、男性22 周岁,且沿用至今。
也是在80 年代,巫昌祯组织创建了公益性质的北京第八律师事务所,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服务。每天都有很多妇女上门求助,有些甚至跪到了巫昌祯家门口。巫昌祯并不嫌烦:“对受苦受难的妇女我就两句话:有求必应,不讲价钱,尽量地满足她们的需要。你要求我‘走后门’,我走不了,但我可以在法律方面提供一些帮助。我是尽力做到这些,当然还需要努力。”[15]面对妇女工作,她永远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保障妇女权益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很快,巫昌祯又迎来了新的立法课题。20 世纪90 年代初,为迎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全国人大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规划,巫昌祯任起草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谁知,从一开始,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就阻碍重重。众多反对意见中最突出的观点是认为宪法已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单独搞妇女权益保障法呢?面对质疑,巫昌祯从我国妇女入学难、就业难、参政难等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16]。“‘重在保障’的立法思路是1992 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主要特色。这部法律……在保障妇女权益的基础上重申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同时,为解决‘三难’问题,设定了更具针对性的规定。”[17]
为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巫昌祯带着学生开展调研,发现部分偏远、落后地区女童辍学率非常高。因此,在1992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写进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履行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等条文。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妇女的就业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人身权等合法权利。巫昌祯对这部妇女权益保障法满怀信心:“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制定出这样较为完备的专门保护妇女的法律。”[18]
1997 年,巫昌祯又参与了婚姻法的第二次修改。1980 年的婚姻法出台时,许多详细的内容被删除,最后只剩37 条。巫昌祯认为“法条疏而不密,一些制度没有成龙配套,留下了诸多立法上的空白,带来了执法上的随意性”[19],导致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要远多于本身条款的情况。
再次参与婚姻法修改,巫昌祯准备充分。早在1995 年,她便参与发表了中国法学会的“八五”课题成果《走向21 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该书提出了新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模式和体系结构,对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亲权、监护、扶养、有关离婚理由的列举性规定、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等,提出了具体方案[20]。
修改稿试拟稿出来后,巫昌祯作为人大法工委立法小组的专家,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广东进行执法检查。她在调研中发现,某些地区婚外性关系比较严重,不仅从隐蔽走向公开,有时甚至引发犯罪,因此她提出:“夫妻应互相忠实,有过错就要付出代价,无过错方可以请求赔偿。”寥寥数语却激起千层浪,一时间,“保守”“倒退”的指责声不绝于耳,一些社会学家将此斥之为“法律道德主义”[21]。

巫昌祯主编:《中国婚姻法》
以国家立法干预家庭暴力
在婚姻法之外,巫昌祯也持续关注家庭暴力问题。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将家庭暴力的概念正式引入中国。此前,社会上普遍认为所谓“家庭暴力”只是家务事而已。巫昌祯开始关注家庭暴力受害群体,并和一批有识之士一起着手反家暴工作,并推动相关立法。
巫昌祯总结了家庭暴力行为的五个特点:手段残忍、后果严重、方式隐蔽、时间连续、原因多样。一些施暴者甚至采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毒打、毁容等方法虐待妇女[23]。虽然家暴的严重程度超乎想象,但推动相关立法却异常困难,很多人意识不到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和社会的危害,坚持将家庭暴力定位成私事,认为以法律干涉家庭暴力是十足的越界。
巫昌祯并不理睬这些落后的观点,和一些同道提议在婚姻法中“对家庭暴力予以规制”。最终,于2001年争取到将“禁止家庭暴力”写入婚姻法的总则,并且家庭暴力可作为离婚的法律理由和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这是我国国家立法突破传统观念,第一次明文干预家庭暴力。”[24]
巫昌祯在反家暴道路上的努力,并不只在立法工作上,也在司法实践中。2001 年,巫昌祯收到一个杭州小女孩寄来的信:“我的爸爸虽然被妈妈杀了,但妈妈杀他是有原因的,他有了第三者,又残酷地打骂妈妈。妈妈虽有罪,但罪不当死呀!我已经没有爸爸了,如果再失去妈妈,我就成孤儿了。”当时,这名涉案女子已被一审判处死刑。巫昌祯通过调研发现:被害者生前确有严重虐待妻子的事实。巫昌祯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不应在量刑时忽略了这一情节。在她的关注下,这桩案件引起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最终,该女子被二审法院改判为死缓[25]。
2005 年,巫昌祯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此次法律修改,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还规定了“多机构合作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干预模式”,再次推动反家暴立法建设。2008 年,也是在巫昌祯的提议下,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提出建立“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度”,当事人因遭受家暴或面临家暴危险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遏制了家庭暴力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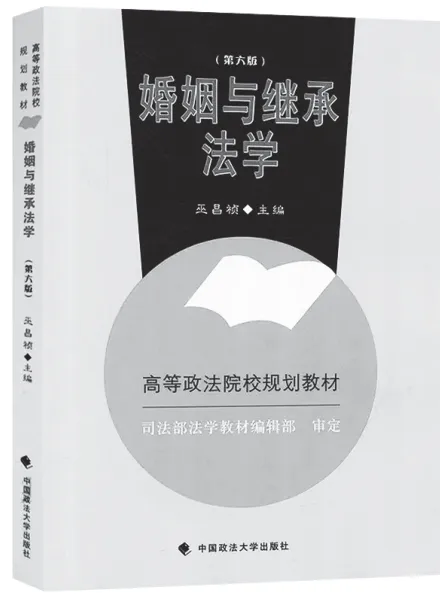
巫昌祯主编:《婚姻与继承法学》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2015年12 月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此时,距1995 年在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家庭暴力”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反家庭暴力法通过前夕,因为在婚姻家庭法、妇女权益保障、反家暴立法等领域的杰出贡献,时年86岁的巫昌祯当选为“2015 年度法治人物”。颁奖词中这样写道:“关注女性命运,保护弱者权益,八十六年风雨人生,六十年初心未改。你用爱的力量彰显了法律的尊严。”巫昌祯为她的法学人生写下了最灿烂的注脚。

巫昌祯当选“2015 年度法治人物”
白头虽老 赤心仍存
六次参与起草或修正立法,作为婚姻法学界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巫昌祯在法学界日复一日的努力让她的荣誉接踵而至,头衔纷至沓来,而她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这些。她曾有过多次工作调动的机会,但都婉言谢绝了:“我不愿意抛弃法律,到妇联或者到人大,我都没有去,我还是愿意搞我的法律。”[26]几十年间,巫昌祯始终不愿离开的是她的讲台、是她的法律教学工作。
种桃种李数十年,巫昌祯弟子满天下,很多已成为法学界的中流砥柱。无论学生是电大学员、郊区农民,还是硕士博士、函授律师,巫昌祯均一视同仁,还先后为不同学生群体撰写了八九种教材。“我是一名服务员,我把一半的时间和心血给了学生和书,另一半给了社会和妇女。”[27]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卧病在床的巫昌祯依然不忘妇女权益。据夏吟兰回忆:“巫老师在患病期间一直强调,妇女的好多权益保护要落到实处,比如离婚损害赔偿要设立兜底规定,家务劳动补偿要去掉限制性条款。”[28]
2020 年3 月25 日,巫昌祯于北京病逝,永远地走入了时代的折痕。而关于巫昌祯的种种,我们始终没能说完。她重视普法工作,提出以法律来保障女性参政比例,为老年人和儿童权益保护建言献策,还曾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农民权益保障法[29]……而她自己的人生则藏在枯燥的论证里,藏在繁多的课题下,藏在无数次的调研中。人们只能在一次又一次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中,寻找她的姓名与踪迹。
这条朴素却坚定的法律之路,从1948 年进入朝阳大学,到2020年去世,巫昌祯走了整整72 年。她以拓荒者的操守和法律人的专业,推动婚姻法走向制度化与体系化,保障妇女的人格不被侵害,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地位。当种种被湮没的细节重新喷薄而来,我们见到一位勤恳的劳动者、一个稍显朴素的形象,却有一种永远焕然的精神,在时代中坚定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