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创作伊始
2023-05-18晓苏
晓 苏

我正式公开发表小说,是在1985 年。当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正准备考硕士研究生。在恶补英语的间隙里,为了缓释压力、消解苦恼、调整心情,我不禁心血来潮,一口气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楼上楼下》。小说写完后,我马上寄给了在《长江文艺》当编辑的大学同学吴大洪。那时,《长江文艺》杂志的主编是著名作家徐迟先生。吴大洪算是一个“文二代”,读大学时就发表过评论文章。其实,我们在大学期间接触并不密切,只是点头之交。寄小说给他时,我没抱发表的奢求,只希望他提点意见。哪曾想到,我把小说寄出去不到一个月便接到了用稿通知。当年12 期,《长江文艺》刊登了我的那篇小说,并且还发在“新人第一篇”的头条。
《楼上楼下》毫无疑问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尽管在此之前,我也曾练习过小说写作,还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两篇,但那些显然都称不上文学作品,说到底也就是习作。因此,我特别看重《楼上楼下》这篇小说。主人公名叫胡有水,是一位满腹诗书的青年教师,可他口齿笨拙、不善言说,所以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师生们都说他“壶里有水倒不出来”。后来再看,小说的立意并不新,也没有多大深意,但吴大洪觉得小说中的形象十分鲜活,语言也很生动,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潜质,所以就立即送审了。发自肺腑地说,在文学创作上,我应该感谢吴大洪。如果不是他当初的鼓励和相帮,我后来也许不会再写小说。那个时候,我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小说,如《黄昏》《苦李子》《太热的夏天》等,基本上都是由吴大洪担任责编。坦率地说,吴大洪并没有因为我们是同学而对我的作品放松要求,每一篇都进行过认真修改。因此,我在心里一直将他视为老师。
回想起来,在1985 年秋和1986年春,我和我的同学、同事兼室友何大猷都是下了决心要考研究生的,并发誓一定要考上。结果,我不久便打了退堂鼓。原因之一,正是《长江文艺》刊登了我的小说处女作,让我受到了文学创作的诱惑,觉得创作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而且比做学问搞研究要有趣得多。从那以后,我虽然还在继续补英语,但热情已经锐减。何大猷发现我的兴趣转移后,一再劝我,希望我能坚持考研,认为我已经准备了大半年,突然放弃很可惜。在他的劝说下,我又重新鼓足了勇气,去食堂排队买饭也拿着单词本。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坚持下来。1985 年年底,我回老家过年。为了向父亲展示我的科研成绩,我回家时把当年发表的一些小论文都带上了,大都是关于作家的研究和作品的赏析。回家当晚,我就把这些文章拿给父亲过目,以为他看了会兴高采烈。没想到,父亲看后却不以为然,用手指着杂志上的作家和作品,冷冷地说:“你不是说这个作品好就是说那个作品好,为什么不自己写几篇,让别人说你的作品好呢?”父亲这席话对我触动很大,让我对写作越发有了兴趣。
因为受到父亲那番话的影响,我此后许久都对考研究生缺乏热情,心思几乎都转到了小说创作上。尤其在1986 年春,我像着了魔似的迷上了小说,每天起早贪黑,一边阅读中外作品一边埋头写作,差不多每两天就可以完成一个短篇。小说写出来后,发表也比较顺利,除了《长江文艺》,武汉的《芳草》《当代作家》《布谷鸟》,当时都刊登过我的作品。
在我创作的起步阶段,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大学老师王先霈先生。王先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同时也写过小说。他很关心我的创作,我在《芳草》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他推荐的。我记得那时《芳草》的主编是朱子昂先生。王先生亲自给朱主编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着稿子和信去汉口拜访朱主编。不久,《芳草》就刊登了我的那篇小说,题为《老屋》。我在《当代作家》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墓地》,是作家周百义先生从自由来稿中发现的。小说发表前夕,周先生约我去编辑部见了一面,还邀我到他家里吃了午饭。那餐饭说不上丰盛,但无比温暖,令我至今难忘。当年湖北还有一家刊物叫《布谷鸟》,我在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运气》的小说,责任编辑是热心快肠的李家容女士。
刚开始写作的那两年,我的作品都发表在湖北的杂志上。后来,我便尝试着朝外地的刊物投稿,陆续在河南的《百花园》《牡丹》、山东的《当代小说》《山东文学》、江西的《星火》《小说天地》上发表了作品。著名选刊《小说月报》第一次转载我的小说就选自《小说天地》,题目叫《吃的喜剧》。目录广告最先刊登在当年的《中国青年报》上,我爱人发现后兴奋不已,拿着报纸一路狂奔到了我的办公室。我见自己的作品被《小说月报》转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仿佛在做一个梦。提到《吃的喜剧》这个作品,还有两个插曲值得一提:一是在我发表拙作的那期刊物上,居然还有著名作家苏童的小说。能与苏童同期,我感到非常荣幸;二是《吃的喜剧》被转载不久,责任编辑黄岭老师专程从南昌来到武汉,除了看我,还郑重地向我约稿。那个年代,编辑与作者的关系真是纯粹!如今,有些刊物的编辑,对刚起步的业余作者往往不屑一顾。
前面提到,在公开发表小说之前,我曾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两篇带有小说雏形的作品。那是大学期间,我们学校团委主办了一份名为《摇篮》的文学刊物,主要发表在校大学生的习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还有文学评论。虽然是学生刊物,但从编辑到印刷都有模有样,对稿件的要求也比较高。主编和编辑大都是从社会上招考来的,他们阅历丰富,文学修养很高,不少曾经当过语文老师,有人还公开发表过作品。像我这种直接从高中考上来的愣头青,压根儿没有奢望在《摇篮》上发表作品,甚至也没敢动过笔。
大三的时候,我们班上一位自称“青年作家”的同学忽然找到我,让我帮他抄写一篇刚完成的小说。他觉得我的钢笔字写得比较规范,一丝不苟,易于辨认,而他的字有些潦草,看起来颇为吃力。这位同学比我大五六岁,还是班上的一个干部。碍于情面,我只好答应了他。那篇小说有一万两千多字,我加了两个夜班才抄写完。大约过了三个月,这篇小说被一家名为《艺丛》的杂志刊登了。之后,这位同学得了一笔稿费,具体多少,我不清楚。收到稿费的那天晚上,他决定请一次客。我想,作为帮他抄写稿件的人,他请客肯定少不了我。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他没请我,请的都是班上的几个头面人物,还请了年级的学生会主席。
这件事情对我伤害很大。我并非想吃那顿饭,主要是觉得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无情无义。一连好多天,我都心里堵得慌,气不打一处来。为了出这口恶气,我也悄悄地写起了小说。说到这里,我还要感谢一下这位同学。在帮他抄写稿件的过程中,我发现写小说并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抄写完他的稿件,我觉得自己也可以照着葫芦画瓢。经过三天的构思与练习,我终于写出了一篇《竹笛声声》。作品写的是老家的一个少年伙伴,双眼失明但聪明过人。他屋后有一片茂密的竹林,其中栖息着各种鸟,比如斑鸠、画眉、八哥等。盲人少年心灵手巧,自己用竹子做了一管竹笛,经常去竹林里吹奏。起初,那些鸟儿听到笛声都吓得四处乱飞,后来居然都喜欢上了他的笛声,一听见悠扬婉转的笛声响起,马上都聚集到他的身边。这篇作品有纪实的成分,还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写好之后,我很快将它塞进了《摇篮》的投稿箱。我至今记得那个上锁的投稿箱挂在中文系门口的一棵樟树上,樟树很粗,三个人都抱不住。我是天黑以后趁人不知鬼不觉地将稿件投进那个箱子的,生怕被人看到了。
自从给《摇篮》投稿之后,我心里便揣上了一个秘密。每次经过那棵樟树,我的心就怦怦直跳。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接到学校团委的一个口信,让我抽空去取《摇篮》样刊。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看着我的名字和作品,我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次在《摇篮》编辑部,我还有幸见到了《摇篮》的执行主编唐老师。其实他也是在校学生,不过已经读到了大四,学校团委正准备将他留校工作。我的《竹笛声声》就是他从大量的自由投稿中发现的。唐老师对这篇习作给了许多好评,同时还约我有空再给杂志写稿。在唐老师的热情鼓励下,我很快又写了一篇《弯弯的月亮》,发表于《摇篮》随后一期。据我所知,《摇篮》虽说只是一份内刊,但投稿堆积如山,偶尔发一篇已经很不容易。可我十分幸运,居然连续发表了两篇小说。当时,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有一天,让我帮忙抄写稿件的那位同学在路上碰到我,还祝贺了我几句。我说:“这还得感谢你让我为你抄稿,我从你的作品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听了哭笑不得,以为我在讽刺他。其实,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如果要追根溯源,我从小就对文学创作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情结,或者说从骨子里热爱和迷恋文学创作。从读小学开始,我就喜欢写作文,盼着天天上作文课。我读小学和初中是在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学校教育受到冲击,已经很不正规了。不过,语文课还是隔三差五会上几堂,老师也教我们读作品和写作文。作品大都是从报刊上选出来的,其中不乏文采斐然之作,我还背诵了好多。写作文主要是模仿报刊上的文章,当然也有个别老师比较灵活,鼓励我们联系生活自由写作,特别强调我们写生活中的真实体验和独特感受。比如读小学四年级那年,教我们语文的尚宗莲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放学以后》,要我们写自己的亲身见闻。我写的是我们班的班长,他在学校表现很好,可一出校门就变了个人。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他家门口。他家有一条狗,见到生人就张牙舞爪地往上扑。我们都害怕那条狗,经常都是从他家屋后绕道走。有一天,他与我们同行,我们便没再绕道,而是直接从他家门口经过,以为狗扑上来时他会把狗拦住。令人气愤的是,当狗突然扑向我们的时候,他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看见我们惊恐万状,居然还咧开嘴巴大笑。幸亏邻居及时跑过来把狗赶走了,否则我们就会被狗咬伤。在这篇作文中,我如实地写了自己的见闻与感想。作文交上去后,尚老师给予了充分肯定,还在全班读了我的作文,说我刻画了一个两面派人物。
到了初中,我有幸遇上了语文老师程家箴。当时没有正规课本,程老师便经常从报刊上选一些好文章,用钢板刻下再油印出来给我们读。其中有三篇我至今记忆犹新,分别是《珍珠赋》《东方红》《春满鄂城》。这些文章语言都很美,用了很多修辞手法,结构也十分巧妙,有的层层递进,有的一波三折,有的先抑后扬。程老师把文章发给我们之后,会先给我们读上一遍。他的声音不高不低,不快不慢,不温不火,具有一种特殊的节奏和韵味,能让我们的心灵深处荡出涟漪,翻上浪花,涌起波澜。读完之后,程老师接下来便抓住文章的关键段落给我们仔细讲解,讲语言,讲结构,讲意蕴,讲得我们心领神会。把文章讲透之后,程老师总是趁热打铁,马上安排我们写作文。这个时候,我的写作欲望都很强烈,往往文思泉涌。为了让我们写好作文,程老师还经常带我们去校外开展活动,看望过老红军,参观过修水库,采访过劳动模范。每次参加活动后,我都要写一篇作文,因为有了生活,有了感受,所以写起来特别得心应手。有一次,程老师把我们带到修梯田的工地上,让我们自己选一位有特点的农民作为观察对象,再与他交谈,然后写一个人物。我那次选的是一位名叫胡明尊的老人,他下巴上留着一撮长胡须,看上去很老很老了,搬石头时却浑身是劲,砌出来的梯形石坎像艺术墙一样特别好看。最让我好奇的是他的胡须,那是我见到过的真正的山羊胡。我问他:“您为啥留这么长的胡子?”他说:“胡子可以当口罩,用它挡灰尘。”听他这么一说,我当时就忍不住笑。回到学校,我很快写下了《留山羊胡的胡大爷》,受到程老师高度好评。

本文作者摄于1985 年
我读高中已到了70 年代末,那时各行各业都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教育也逐步走上了正轨。我的高中位于县城东沟,许多任课老师都是前些年从武汉来的,差不多都读过大学,教学水平相当高。我们的语文老师姓顾,毕业于早年的武汉师范学院,学识渊博,出口成章,而且写过小说,曾以谷川的笔名在《芳草》上发表过作品。遗憾的是,他没过多长时间便调回了武汉。顾老师虽然调走了,但他说过一句关于文学的话却让我永远铭记于心。他说:“文学既要讴歌光明,也要鞭挞阴暗。”顾老师调走不久,我遇到了一件令人非常愤怒的事。理科班有一位干部子弟,绰号“花花公子”,平时不住校,吃住都在县委大院。他留大分头,穿喇叭裤,喜欢一边甩头发一边打响指,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一帮人前呼后拥。有一天中午,他没有回家,像发神经似地潜入了我们寝室。我睡下铺,床上铺着一张旧床单。他先在我床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就从身上摸出一把水果刀,明目张胆地将我的床单划了一道口。我顿时气炸了,拉着喊着要他赔我的床单。同学们都劝我说,算了,人家的父亲是县里的大官儿呢,鸡蛋碰不过石头的。我说:“我才不管什么大官儿呢,损坏东西必须赔。”他对我冷笑说:“你试试?”恰在这时,正在值勤的方副校长经过窗口,看见了这一幕,快速跑了进来,声色俱厉地对“花花公子”说:“快回去把你父亲叫来。”“花花公子”问:“叫他干啥?”方副校长说:“让他来商量赔偿的事。”“花花公子”说:“他今天不在家。”方副校长说:“那让你母亲来。”“花花公子”威胁方副校长说:“我看你是不想转正了!”方副校长坦然一笑说:“为了主持公道,我宁可副校长也不当。”见方副校长态度如此坚决,“花花公子”只好派人叫来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还算通情达理,来时随身带了针线,一到寝室就给我道歉,随后便把我床单上的口子补好了。事发当晚,我就抑制不住地虚构了一篇具有小说元素的文章,题为《床单上的刀口》。在文章中,我着力刻画了一个不畏强权的副校长形象。可以说,那是我最早的小说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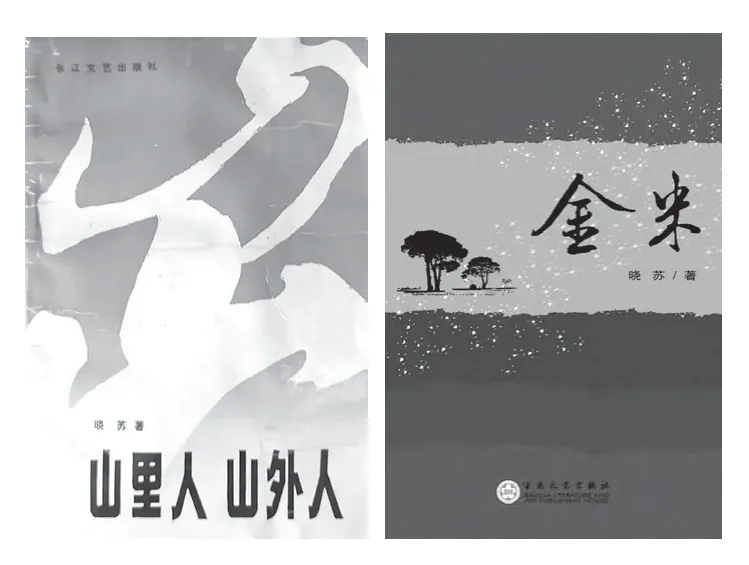
晓苏:《山里人 山外人》《金米》
对一个具有一定时间长度的写作者来说,如果要对他的创作历程进行一个阶段划分,我想绝大多数写作者都少不了起步这个阶段,或者称为起步期。于我而言,我的起步期为时较长,从上学读书开始做作家梦,直到1988 年才算画上一个句号。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个带有标志性的事件,我幸运地加入了湖北省作家协会。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候的湖北省作家协会叫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我入会的推荐人是我的恩师王先霈先生,他后来还当过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王先生对我可谓恩重如山,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山里人 山外人》,就是他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赵国泰先生推荐的。据说,他还向当年主持湖北省作家协会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刘富道先生推荐过我,刘先生随后便在《文艺报》上连续刊登了两篇介绍本人的文章。后来,我去武汉大学文学院攻读樊星教授的博士,按规定要有两位专家写推荐意见,其中一份就是王先生写的。前些年,湖北省作家协会换届,我被选为副主席,听说王先生也向有关部门推荐过我。如今,王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还能作报告和著书立说,但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