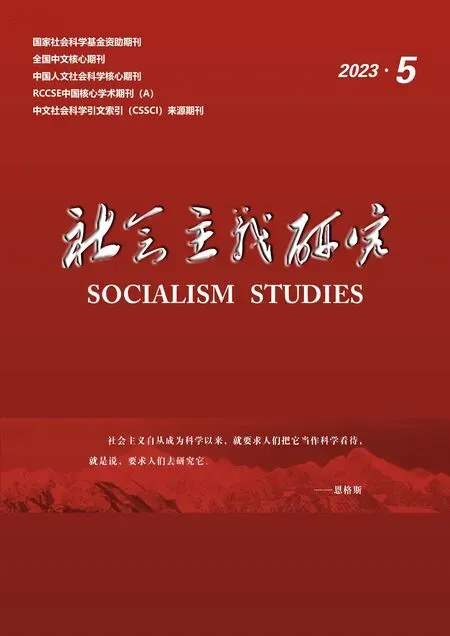全球治理视野下美欧金融制裁泛化的挑战与应对
2023-05-15王达坡胡加祥
王达坡 胡加祥
“制裁”意味着强力约束,“金融制裁”顾名思义是从金融领域进行强力约束,是通过一种或多种惩罚性经济金融手段,包括阻碍金融流动、冻结扣押资产、降低信用许可等方式,进而达到扰乱被制裁国金融秩序、增加经济压力、阻断投资收益等效果,迫使被制裁国改变特定行为、接受制裁发起国政治意愿或条件的政策性工具1参见Elliott Kimberly Ann,Schott Jeffrey Joseph,Hufbauer Gary Clyde,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3rd Edition,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pp.1-42.。根据有否多边国际条约的授权,国际法上的金融制裁可分为“多边金融制裁”与“单边金融制裁”2参见霍政欣:《〈反外国制裁法〉的国际法意涵》,载于《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4期。。多边金融制裁一般指联合国安理会基于《联合国宪章》第41条授权发动的涵盖金融手段的非武力制裁;单边金融制裁则多由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基于国内法授权对外发起,被制裁主体涵盖国家、个人与实体。
当前,单边金融制裁已成为全球经济制裁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美国与欧盟是单边金融制裁的主要发起方,截至2023年1月,仅美国财政部实施的单边制裁就涉及约6300个个人和实体3参见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Where is OFAC’s Country List? What Countries Do I Need To Worry About in terms of U.S.Sanctions?,(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financial-sanctions/sanctionsprograms-and-country-information/where-is-ofacs-country-list-what-countries-do-i-need-to-worry-aboutin-terms-of-us-sanctions.),欧盟的单边制裁措施则涉及近40 个国家和地区4参见EU,EU Sanctions Map,(https://sanctionsmap.eu/#/main?search=%7B%22value%22:%22%22,%22search Type%22:%7B%7D%7D.),其中绝大多数制裁均将金融手段纳入其中,或是专门针对被制裁国金融领域施加。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联手对俄罗斯发动了数轮制裁,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金融制裁高峰,开创多个先例,对俄罗斯经济金融产业造成严峻冲击的同时,也撼动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底层秩序5参见Allen Susan Hannah."The Uncertain Impact of Sanctions on Russia",Nature Human Behaviour,Vol.6,No.6,2022,pp.761-762.。“金融武器化”快速响应并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中的极不稳定因素,金融制裁泛化所显露出国际体系中金融权力的扩散和转移,也给多边主义合作、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以及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参见宋晓燕:《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与法治化》,载于《东方法学》2023年第2期。。在此基础上,美欧仍在不断联合盟友采取一系列国际法与国内法上的制度再塑和规则修正行为2参见任琳、孟思宇:《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载于《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旨在修复与稳固自身不对称金融权力,持续运用金融制裁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塑造和改变未来全球治理秩序走向。
二、金融制裁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力关系
“金融”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面向。二战后,美国依托美元-黄金本位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三驾马车”,初步建立起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囿于彼时全球金融联结程度与经济体量的限制,金融制裁的理论与实践并不丰富,主要应用于战时的简单封锁,且制裁本质上是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破坏,这使得观察者们似乎很难将金融制裁与全球经济治理联系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美国单方面决定不再承担美元与黄金的汇兑义务并取消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解。然而,由于国际贸易的惯性、美国所建立的金融优势及其对其他货币国际化的持续打压,世界各国仍然依赖失去金本位约束的美元,美国具不对称性地位的全球金融权力缓慢塑成。在此基础上,美国顺势联合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成立G7,并将全球经济治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硬制度”逐渐转化为由软法规制的“软制度”,以此增加治理灵活性,便利美西方式金融政策的渗透3参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28-35.。在此过程中,欧洲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得到快速发展,美欧金融联系与协作愈加紧密。全球性系统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爆发,但各种区域性金融危机,诸如墨西哥金融危机、拉美主权债务危机等开始层出不穷。美欧发达国家依靠经济金融优势,转嫁自身危机并借机篡取利益,利用境外市场平摊风险,金融开始“工具化”。20世纪80年代后,冷战结束,现代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发生深刻转变,区域共同体及新兴经济体接连崛起,G7治理模式日渐式微并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被G20所取代。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应对危机能力得到检验。危机过后,全球经济治理中心逐渐转变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合作治理模式4参见仇华飞:《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国际体系中金融权力发生根本性扩散和移转,以美元货币体系、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及其规则、WTO贸易投资便利化一同,基本形成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秩序5参见范晓波、陈曦笛:《美国金融制裁法律限制的再检视》,载于《人文杂志》2023年第2期。。
梳理全球经济治理秩序沿革可以发现,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结构、以美欧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市场布局、以美欧为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治理秩序变换过程中,基于“优势地位”生成的金融权力逐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俱乐部”群体中生成并进行分配与分工,换言之,金融权力国逐渐完成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布局,并异化出“自我优待”“胜者恒定”“本国优先”等秩序表征6参见Amitav Acharya,"The Fu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Fragmentation may be Inevitable and Creative",Global Governance,Vol.22,No.4,2016,pp.453-460.,金融权力实现机制化、制度化与实体化,单边金融制裁的发明与应用便是最好例证。而在经历早期对前南斯拉夫、古巴及苏丹等国的成功实践后,单边金融制裁逐渐成为美欧国家利用金融权力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武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按“西方方案”变革的威慑方法7参见戚凯:《美国“长臂管辖”与全球经济治理》,载于《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4期。。
美欧将“金融权力”实现由“工具化”到“武器化”的最终转型与全球部署,离不开其对金融权力的确立、分配、运用与维护。“金融权力”的内涵界定至少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指因金融实力、影响力等而拥有的优势地位或能力;另一方面指运用金融实力的政策行为,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没有褒贬之意;后者对他国具有一定的伤害性而具有贬义色彩8参见胡键:《大国成长的困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杜牧陷阱”?》,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多数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学者认可金融权力是金融制裁的发起基础,且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决定了金融权力本质上具有“不对称性”1参见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页。。不对称性权力是指一种形式的权力对其他形式权力的制约、控制乃至支配2参见邵辉、沈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非对称性金融制裁反制理论及中美金融脱钩应对》,载于《财经法学》2020年第6期。。金融权力的不对称性可具化为“国际货币权力”“金融霸权”“国际金融话语权”等。作为金融权力国的工具3参见Juan Carlos Zarate,Treasury’s War:The Unleashing of A New Era of Financial Warfare,Public Affairs,2013,p.423.,金融制裁尤其是单边金融制裁自然被赋予了应用不对称性权力的许可,并为维持不对称性而服务。因此,有学者将金融制裁界定为“利用货币权力发动的制裁”4参见陶士贵:《国际货币权力下美国对外货币金融制裁泛化及应对》,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利用金融市场优势地位发动的制裁”5参见靳风:《中美关系中的“灰色地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论文,2020年。“利用经济优势发动的制裁”6Robert A.Pape,"Why Economic Sanctions Still Do Not Work",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1,1998,pp.66-77.等,并总结出金融制裁发起方需要具备的要件(实际上也构成金融权力国的基本特征),包括:(1)强大的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货币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军事实力的衍生权力等。(2)有效的金融制裁传导路径。包括货币的国际主导地位、在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的影响力、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3)完善的金融制裁立法与制度,以及对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参与影响能力等。
从金融权力理论出发,上述要件可进一步制度化与体系化。金融制裁所倚靠的金融权力可被区分为“关系性金融权力”“结构性金融权力”与“制度性金融权力”三种理论范式。具言之,关系性金融权力是一国通过施加金融压力或者提供金融激励直接影响他国的能力,主要生成于要件(1),包括他国对金融制裁发起方创造信贷能力的信任、金融制裁发起方所具有的债权国地位以及其他经济金融能力要件。结构性金融权力被视为一国通过国际金融体系结构间接影响他国的能力,主要生成于要件(2),权力多来源于一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在全球金融体系结构的领导地位等。制度性金融权力则包括一国国内金融法律制度水平,以及一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决定作用直接或间接影响他国的能力。制度性金融权力的行使在多数情况下也是间接的,如通过在国际金融机构投票、在IMF和世界银行(WB)中本国职员和管理层的代表性、国内金融立法对外影响力等进行实施,可被视为要件(3)所形成的权力类型7本文主要参考苏珊·斯特兰奇、乔纳森·科什纳、桑德拉·希普等学者的观点,相关理论探讨参见[英]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2版)》,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英]苏珊·斯特兰奇:《疯狂的金钱》,杨雪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美]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德]桑德拉·希普:《全球金融中的中国:国内金融抑制与国际金融权力》,辛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
金融权力范式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权力架构具有一定耦合性。全球经济治理本身便是权力博弈、移转之下的产物8参见胡键:《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载于《国际经贸探索》2022年第8期。。当前由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根本共性是:该治理是以美欧为权力中心,将美欧的统治意志通过各种途径向其他参与方贯彻。在和平时期,美欧便频频发动金融制裁,对不遵守其所制定的治理规则、影响其权力地位的国家进行“惩戒”与“打压”;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欧不仅紧密联手对俄罗斯进行严厉的金融制裁,开创多个先例,不惜动用“金融核武器”,将金融制裁的广度与烈度显著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还将制裁主战场视为炫耀实力与权力威慑的“舞台”,屡屡对中国等坚持独立和平自主的国家表达潜在威胁,试图拉拢并迫使接受其政策主张。美欧频频发动金融制裁不仅体现制裁对维护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工具价值,还表明其对金融权力的“信任”。实际上,作为金融制裁的基础,美欧早已在全球经济治理环节中深层次嵌套、培育与运作金融权力,并在金融护持(关系性金融权力)、政策主张(结构性金融权力)、法制架构(制度性金融权力)等诸多环节予以体现9参见[美]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等著:《反思经济制裁》,杜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9页。。
第一,金融护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冠肺炎疫情与局部冲突等外部冲击使传统金融强国复苏乏力,美欧等国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金融政策,试图缓解经济压力转移风险,以高成本代价维护自身关系性金融权力地位,保持金融实力、货币权力、综合国力与军事实力等。面对2022年的全球性通货膨胀,美欧一改此前长期维持零利率的政策,采取短期、大幅、高频的加息举措,试图用无限量化宽松政策等激进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输出到全世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动荡。2022年3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之后连续加息,至2023年5月已经连续10次加息。欧洲央行亦紧随其后,2022年7月,欧洲央行开启加息进程,之后连续8次大幅加息共计400个基点。这些举措在短期内虽然为美欧争取了较多资本回流,遏制通货膨胀,并利用货币金融市场一定程度上转嫁危机,维持汇率稳定,减缓经济复苏压力。但从长期看,对美欧自身乃至其他国家的金融安全与经济增长产生巨大下行压力,全球金融风险显著提升。
第二,政策主张。一是将金融制裁提升到关乎国家整体安全的战略高度。金融制裁是美欧实施外交政策、实现国家安全目标、进行国家间博弈、巩固在盟友间以及全球影响力的工具。美欧对外金融制裁的核心政策逻辑是针对对手国家实施报复性制裁措施,逼迫其改变损害美欧利益的行为,一般均宣称是在紧急状态或是重大威胁等背景下实施的,突出对具体议题的“反击”“威慑”与“治理”。如美国《通过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就突出“反击”的战略目标,强调通过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一切措施对竞争对手的长期威慑和打压,保持在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的领导地位。欧盟同样是全球金融制裁泛化与金融权力滥用的重要推手。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以来,确立了“强大欧盟金融影响力”的执政理念,并将负责欧盟金融安全执行工作的欧盟委员会下属的“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联盟总理事会”的权限不断扩大,将金融制裁纳入事权范围。冯德莱恩在写给该总理事会专员的使命信中强调“为巩固欧盟的经济主权,希望总理事会可以提出确保欧盟对第三国的金融制裁更具韧性(Resilient)的提案,并确保金融制裁的执行,尤其是通过欧盟金融体系进行的金融制裁的执行”1Ursula von der Leyen,Mission Letter to Mairead McGuinness,Commissioner-designate for Financial Services,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Union,(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commissioners/sites/default/files/commissioner_mission_letters/president_von_der_leyens_mission_letter_to_mairead_mcguiness.pdf.)。俄乌冲突中,欧盟接过美国制裁大棒,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金融制裁发起方2参见王达坡、彭德雷:《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及其镜鉴》,载于《德国研究》2023年第2期。。二是通过与盟友“金融少边合作”共同筑起金融“护栏”(Guardraily)。“护栏条款”出自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是指为保护美国芯片技术核心利益,限制获得美国政府补贴的科技企业赴境外投资与技术转让行为,该规则主要针对中国。实际上,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及其盟友便开始在金融领域“静悄悄”构建起独立于世界金融秩序以外的闭合排他型少边金融联盟,并通过双边、少边安排制定金融“护栏”规则,服务于金融“脱钩”乃至“去风险”的政治目的,金融权力呈现“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的变化。一方面,美国通过与部分盟友央行签订美元互换安排(Swap Arrangements)方式,或者是将原本临时货币双边互换安排固定化,在IMF国际货币体系下建立新的美元流动机制,打破美国在二战后所制定“大多边主义”的全球货币合作体系。另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国家正不断升级金融制裁协作程度。美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就将对外金融制裁相关内容置于第二部分“巩固盟友及伙伴关系”下的第一节“战略与外交事务”中,明确联合欧盟、印太区域国家、“四边机制”国家联合制裁,突出金融制裁由单独向联合制裁的转向,并在俄乌冲突中由G7集体金融制裁俄罗斯等形式进行了实操。
第三,法制架构。当代国际法下金融制裁的法律结构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以联合国、IMF、W B等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层面,法律依据主要源于《联合国宪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等。二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集团层面。金融制裁是欧盟基于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权事项,欧盟的对外金融制裁决定对各成员国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前欧盟金融制裁的法律依据涵盖欧盟基础性立法《欧洲联盟条约》《欧洲联盟运行条约》,以及欧盟分别于2003年12月和2004年6月通过的《欧盟限制性措施实施和评估指南》(2018年更新)与《欧盟关于限制性措施实施的基本原则》等制裁实施细则。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个体层面。美国对外金融制裁立法始于20世纪中期,1950年美国财政部制定《外国资产管制条例》,明确规定美国政府可以冻结相关国家资产并禁止金融交易。后随实践变化及修法完善,1976年《国家紧急状态法》和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形成了美国现代对外金融制裁的基础法律。“9·11”事件后,美国国别与事项专门制裁立法持续丰富并转化为一般法,如针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恐怖主义制裁法》、针对人权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针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自由法》等,这些立法均将金融制裁措施纳入其中并具域外影响力。
三、金融制裁挑战全球经济治理的具体方式
在充分渗入金融权力的基础上,美欧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具体实践措施,将金融权力具化为各类金融制裁行动进而产生有效性。其中,关系性金融权力主要通过“域外管辖”的方式予以运作,结构性金融权力主要依靠“全面制裁”予以实现,制度性金融权力则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不断升级。
(一)“域外管辖”干涉金融主权
近年来,美欧颁布的一些涉及金融制裁的立法与政策,均明文规定域外适用效力,赋予自身依据国内法发动单边金融制裁的条件。域外管辖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发起单边初级或次级金融制裁的管辖工具,以“长臂管辖”模式更为常见。其中,单边初级金融制裁禁止本国境内的外国实体和个人,或本国籍的实体和个人与被制裁国开展特定金融活动,法理基础是属地管辖原则和属人管辖原则;单边次级金融制裁则是促使“第三国”或其非国家行为者改变其与被制裁国的经济交往政策或做法1参见郑玲丽、侯宇锋:《俄乌冲突下美国对华次级制裁的违法性分析及对策研究》,载于《国际经济法学刊》2023年第1期。。以美国发动的制裁为例,单边初级金融制裁适用于美国实体和个人,以及位于美国境内的个人和实体,如2022年2月21日,拜登发布总统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进行新的投资。单边次级金融制裁则限制非美国金融机构与被制裁国个人或实体在美国境外进行金融交易,如2022年2月至今,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OFAC)陆续将众多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和阻禁人员”名单(SDN)之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杜马成员、部分金融机构等,禁止第三方与名单中的主体进行金融交易或提供金融服务,否则也将受到美国的制裁。此外,实践中美国还通常援引外国局势对美国领土的影响或任何以美元计价的金融交易在美清算来解释属地关系,并宽泛定义美国人,扩大个人与美国的联系以此最大限度扩张管辖范围2参见杨永红:《经济制裁的法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年版,第110页。。
通过域外管辖施加单边金融制裁可以使管辖的触角直接触及各国经济金融主权事项,达到对他国直接、快速施加“关系性”金融压力的效果,关系性金融权力也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直接作用于金融制裁发起方本土乃至境外领土内。鉴于域外管辖的实际效用,近年来欧盟也持续通过各类渠道扩张金融制裁领域的域外管辖权,增加金融制裁乃至金融权力的作用空间。欧盟过去一直对外宣称其制裁政策是“限制性”的,并以“限制性措施”指代制裁表述3参见Sachiko Yoshimura,United Nations Financial Sanctions,Routledge Press,2021,pp.8-9.。从立法上看,欧盟基本以“发生实际联系”为原则,将管辖范围限定在欧盟境内以及欧盟具管辖权的个人或实体等4根据《欧盟限制性措施实施和评估指南》(2018年更新)规定,欧盟制裁一般适用于欧盟具备管辖权的领土、船舶与航空器、个人或实体,具体包括:(1)欧盟的领土及领空;(2)在欧盟注册的船舶或航空器;(3)欧盟成员国的自然人国民;(4)依据欧盟成员国法律设立或组建的法人、机构或实体,不论位于欧盟境内或境外;(5)部分或全部业务(商业活动)开展于欧盟境内的法人、机构或实体。。然而部分学者并不认可欧盟制裁是“保守克制”的,相反欧盟一直在努力扩大其制裁的域外管辖范围,不断向“长臂管辖”靠拢。欧盟长期通过非正式邀请等政治拉拢的方式,令特定第三国配合其所实施的制裁措施。如欧盟致力于欧洲经济区(EEA)、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 TA)成员国建立制裁联络协作机制5参见Mirko Sossai,"Legality of Extraterritorial Sanctions",in Masahiko Asada,ed.,Economic Sanc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Routledge Press,2020,pp.66-67.。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拉拢盟友对俄制裁更为积极主动,对俄超过十轮制裁彰显了欧盟强调自身实力及打造新欧洲关系的野心。2022年3月18日,EEA联合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由欧盟委员会主持。会上EEA与EFTA代表们纷纷表态支持欧盟对俄制裁的决心,并通过了《担保债券条例》(EU 2019/2160)以增强欧盟与EEA、EFTA经济体成员国的融资协作,扩宽融资的渠道以抵消欧盟对外金融制裁可能带来的“反噬”后果。
(二)“目标制裁”回退全面制裁
金融制裁起初是作为“目标制裁”(Targeted Sanctions)这一新型工具出现。联合国发动的多边金融制裁通常被定义为“目标制裁”(又称“聪明制裁”),是指该制裁只针对特定的个人和实体而非整个国家,这样对无辜平民造成的损害相对较小,体现制裁兼顾人道主义保护的色彩。在此基础上,美欧最初采取的金融制裁尝试也多声明是“目标制裁”,仅通过列明制裁名单方式对特定对象实施。然而近年来美欧金融制裁实践明显与这些理念背道而驰,不仅毫不避讳地通过受其控制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进行全面金融制裁,还设置名目繁多的制裁名单或制裁机制,肆意扩大金融制裁的覆盖范围,基本将有影响力个人、重要机构实体以及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纳入其中,构成对结构性金融权力的滥用1参见沈伟、方荔:《美俄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之间的拉锯和对弈——理解金融反制裁的非对称性》,载于《经贸法律评论》2023年第2期。。
第一,利用国际金融结算体系(SWIFT)进行制裁。俄乌冲突中,美欧联手将数家俄罗斯重要银行踢出了SWIFT系统,此举被认为是向俄罗斯扔下了“金融制裁核弹”,并将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政治化、工具化风险推向新高峰。美欧通过SWIF T系统实施金融制裁的目的十分明确,即终止俄罗斯的外汇流动与跨境结算,进而将其全面排除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贸易、能源、通信、金融、物流、粮食等体系,封锁国家外部的经贸融资渠道以全面打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SWIFT是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全球金融机构间报文规范和传送处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确立金融机构间信息传输路由及单一编码,实现国际支付清算的一体化与一致化,进而提升跨境经贸往来的效率与安全。SWIFT本身是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被视为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而长期保持中立,但囿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跨境支付需要SWIFT联合“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进行美元清算,这就使得SWIF T无法脱离CHIPS单独存在,美国具备通过美元控制SWIF T发动制裁从而打击制裁对象的能力,欧盟也具备配合美国运用SWIFT发动金融制裁的条件2参见王达坡、彭德雷:《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及其镜鉴》,载于《德国研究》2023年第2期。。
第二,利用他国外汇储备进行制裁。自拉美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外汇储备同样被视为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对一国外汇储备进行制裁因可能造成重大的民生问题、违反人道主义保护等习惯国际法而被国际社会所禁止。历史上,美欧等国在多数金融制裁行动中也极少大面积冻结一国的外汇储备,因为这也将直接透支本币与国债的信用水平。俄乌冲突中,美欧创纪录地冻结了俄罗斯近30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俄罗斯外汇储备总额过半。尽管自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为应对西方的常年经济制裁,俄罗斯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自给自足的“脱钩型”经济体系——“俄罗斯堡垒”(Fortress Russia)用于抵御制裁,该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5%;国家债务低于GDP的20%且只有一半是美元债务;拥有6430 亿美元外汇储备以及丰厚的石油及天然气收入。但遭受外汇储备冻结制裁之初仍然使俄罗斯国内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包括汇率调节失灵、卢布汇率暴跌过半、主权债务评级下调、股市停摆等,进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
(三)“金融创新”抢占数字霸权
伴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交易、金融结构、金融网络出现了重大变革,金融创新快速席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美欧抢占数字高地、争夺数字话语权、围绕科技进行限制性竞争等措施愈发激烈,开始运用金融制裁手段对他国金融创新领域进行遏制打压,并将制裁与科技手段结合,加快金融制裁的数字化转型,制度性金融权力呈现新的特征。最为突出的实践为数字金融服务商频繁成为美欧金融监管机构的执法对象,数字货币、加密资产、金融数据、虚拟交易、金融评级等纳入金融制裁范围。实际上,以金融数字化为主的金融创新正不断侵蚀着美欧金融权力。如前所述,金融制裁的后盾之一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以及美国对国际支付结算系统的控制力,然而以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数字资产的兴起,以及与之而来的替代性支付体系的革新,将严重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催生规避金融制裁的多种方式,进而影响美欧金融制裁的有效性。美欧在此次对俄制裁中,开创性地在金融制裁名单中追加数个俄罗斯数字金融实体,如美国将俄罗斯虚拟货币巨头Bitriver公司列入SDN名单之中,创造了“数字金融制裁”的先例,并开始将金融制裁与技术手段相结合,通过金融交易结算、大数据筛查、人工智能监管等新型情报收集系统,查找、锁定并冻结被制裁主体全球虚拟资产,使金融制裁更轻易延伸至他国数字金融主权领域。此外,美欧还通过限制科技类企业美元结算、限制跨境融资、限制发行和交易数字货币、限制本国高科技类企业或技术出境等方式1参见刘威:《美式金融制裁的实施体系、功效评价与可能趋势》,载于《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1期。,限制被制裁国与第三国有关电子贸易、数字金融产品、智能产业等的经贸金融往来,如2023年3月1日OFAC发布制裁条例禁止有关主体进行涉俄科技产业交易,严防金融科技和资本流向被制裁国2参见张春生、牛飞亮等:《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金融制裁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及应对》,载于《国际贸易》2023年7期。。
四、美欧金融制裁泛化的中国应对
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贸与政治形势,美欧等国希望突破现有法律体系,不断充实国内政策工具,对其他国家采取更快速、有效的遏制方式,促使改变政策以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企图明显,制裁成为首选项。当前美欧等守成大国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就是要利用俄乌冲突把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推向两极化,试图通过强力推行“以我划线”的金融权力价值观,将金融制裁打造成维持其全球金融乃至政治霸权的竞争工具,遏制新兴大国发展,以此强化由其所主导的传统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从现有全球治理格局看,有且仅有中国可依托自身实力,代表新兴经济体表达立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多元化、平等化与共同化方向发展。如何应对美欧对关系性金融权力、结构性金融权力与制度性金融权力的控制与滥用,抑制金融权力横行与金融制裁泛滥,成为亟待中国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完善中国金融反制裁法律制度体系
面对实力完全不对等的关系性金融权力国,处于弱势方的被制裁国并非毫无出路,破局的关键在于构建完善的金融反制裁法律制度体系,在立法、司法和行政层面形成组合拳,为依法采取有效反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基础。我国于2021年6月10日公布并实施《反外国制裁法》,与《对外关系法》《出口管制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一道初步构筑起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雏形,该体系仍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当前我国反制裁法律制度体系对金融制裁的整体关注度较低,更多立法重心放在贸易制裁议题上。未来,应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逐步构建起金融反制裁法律制度的具体政策机制,可以包含国际法合法性审查、金融反制裁信息通报、金融反制裁救济等机制,并应开始关注“数字金融制裁”新动向,在银行、证券、基金、科技等行业领域加大风险意识普及与反制准备,可开创性设立数字金融反制裁应急机制、多主体协同机制、保险机制等,以此增强反制的快速响应与协作能力,保证反制有效性。另一方面,探索构建专门的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主管部门。基于金融制裁体量大、风险程度高、制裁烈度强、破坏性严重等特点,以及金融制裁实施具有较强专业性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实力雄厚的管控机构,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主管专门化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与美国设立OFAC、欧盟设立“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联盟总理事会”主导域外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事项不同,中国目前没有独立的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主管部门与执行安排,通常以多部门联合行动的方式执行制裁决议,制度安排整体较为庞杂,容易影响效率3参见袁见、杨攻研、杨牧、付强:《美国对他国金融制裁的法律基础、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载于《国际贸易》2021年第7期。。中国可以尝试建立金融制裁与反制裁相对集中的主管部门或工作小组。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这一部门或小组可以置于202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新设立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系统,不仅可以较为便利地进行金融领域的情报收集、信息处理、协调决策、执行分工、风险评估等工作,也可以快速衔接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人民币管理体制、人民币国际化、金融运行监管体制等改革进程,形成防范域外金融制裁的单一口径与系统核心4参见陶士贵:《主权国际货币的新职能:国际制裁手段》,载于《经济学家》2020年第8期。。
(二)发挥域外司法对金融制裁的压制作用
从美欧公然动用SWIFT进行金融制裁的霸权行径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不再中性,国际金融规则可以根据金融权力国的意志随意修改,结构性金融权力泛滥,全球经济治理制度非中性程度加剧,亟待引入“司法型反制”破解难题。尽管美欧极力褪去制裁“司法审查”的参与以保证制裁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但现行立法仍然为司法干预留有一定空间,针对部分类型的金融制裁案件,法院有权审查制裁决定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受制裁主体可以运用金融制裁发起方国内司法制度解决制裁争议。例如,2021年,我国小米和箩筐技术公司依据美国《行政程序法》相继向美国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将其纳入美国“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行为缺乏证据,这些案件均成功获得美国法院签发的临时禁令,以避免“无法挽回的声誉和经济损失”,并最终成功从制裁名单中移出。欧盟《里斯本条约》虽然将制裁所属的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事项移出欧盟法院的管辖范围,但《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63条第4款和第275条规定:欧盟法院可以对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旨在对自然人和法人采取的制裁决议进行合法性审查,被制裁对象可以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1参见《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程卫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44页。,这成为欧盟司法干预欧盟对外制裁事项的法律依据。在过去几年,欧盟法院越来越频繁行使审查权判决欧盟理事会制裁决定与条例无效。俄乌冲突爆发后,一些被欧盟制裁的对象便通过向欧盟法院起诉的方式,成功实现了中止制裁的效果。如2023年3月1日,欧盟法院发布临时司法命令,要求暂停对俄罗斯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车手尼基塔·马泽平的部分制裁限制,此前他在意大利的金融资产被欧盟当局冻结2参见王达坡、彭德雷:《欧盟对外经济制裁体系及其镜鉴》,载于《德国研究》2023年第2期。。
(三)促进金融创新发展与数字治理变革
数字领域的快速变化不断冲击着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新的数字治理规则虽未建立,数字保护主义、数字鸿沟、数字霸权问题却已抬头3参见姚璐、何佳丽:《全球数字治理在国家安全中的多重作用》,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9期。。当前,金融创新领域的制度性金融权力还未完全塑成,中国应在不断提升自身金融科技实力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数字金融治理国际规则的谈判与制定进程,代表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治理权与话语权。一是积极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数字化革新背景下的新模式。金融科技创新正逐渐改变全球治理方式与秩序,金融权力开始流散稀释,技术化程度不断加深4参见刘彬、陈伟光:《区块链技术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基于权力、制度和观念的分析》,载于《学术界》2021年第1期。。中国应加入全球金融科技融合发展浪潮,抓准IMF、WB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平台建设启动契机,代表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倡导以数字货币为基础的国际货币治理机制的创建,开辟新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领域。加快区域数字金融监管协作体系建设,消弭区域乃至全球数字金融监管异化问题,探索在多边主义制度下促成去霸权主义的数字金融协同治理与监管模式,增强全球金融稳定。二是稳步增强自身金融科技创新实力,加快我国数字金融治理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一方面,加快建立我国金融数据治理体系。数据是驱动创新发展的核心动能,完备的金融数据治理体系成为未来“数字金融制裁”的反制基础。应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立法实践基础上,加紧在国家层面对金融数据确权、金融数据流通、金融数据使用、金融数据要素化等议题进行立法研究工作,明确各类主体的金融数据使用权责义务,规范金融数据使用流程与相应救济程序,主动与国际规则对接,构建满足境内外市场供需的安全可信的全国金融数据共享平台,有效规制金融数据的境内外流动。另一方面,应加快数字人民币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探索替代性人民币支付系统,充分运用RCEP、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与G20 合作平台,加强数字金融领域的合作,扩大以人民币结算的双多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范围,采取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行动,及时防范数字资产、数字系统、数字货币、金融服务等被制裁的风险5参见符妹:《数字全球化:世界历史逻辑与中国应对》,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