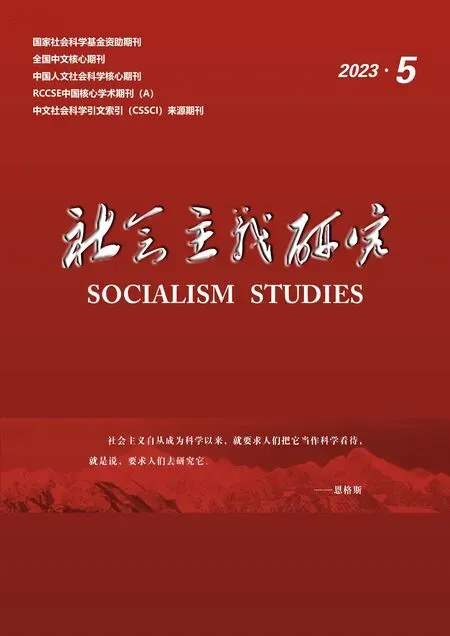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疏解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话语纠缠的中国方案
2023-05-15马英杰
马英杰
民族国家是近代欧美秩序影响世界的基本框架。当我国在清末遭遇西欧霸权并融入这一秩序后,民族及其民族国家概念便引入。梁启超开始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与欧美话语对接;孙中山为了凝聚国人,推翻腐朽清朝统治,摆脱西欧列强殖民,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率先将“中华民族”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也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但意义却有别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按照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实际,识别中华民族成员,实施民族政策,保障民族平等,推动各民族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此过程中,传统上的“五方之民”和现实中的“多民族”是推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依据,历史上“夷夏之辨”和现实中的民族发展差异也是演化“民族问题”的重要缘由。但国内一些学者却仍然按照清末民国时期单一民族国家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问题,多种话语1西欧话语与中国话语,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与多民族国家话语,历史话语与现代话语等。相互纠缠,这不可避免的产生理论与现实的悖反:学术界一边强调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另一边却仍然沿着欧美民族国家的思路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向借鉴经验,建构中国民族理论。尽管其一贯声称中国“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为“中华民族”,但受欧美民族理论的思维宰制,话语体系又导入新的“悖反”:一方面强调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统称,另一方面却朝着曾被中国共产党扬弃了的“国族2国族是中华民国时期常用的概念。式”单一民族国家方向复归。这种话语纠缠与逻辑悖反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使中国民族理论的建构左右摇摆;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民族地区治理实践造成干扰,甚至以“正确”的方式伤害着新中国几十年经营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这种困境导致我国民族理论的研究瓶颈凸显,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及其实践转化力受困,难以为“中国善治”提供应有的理论支撑。而此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出现,突破了民族国家话语系统遮蔽多民族国家现实的窘态,实现了民族国家话语下多民族国家的语境转换,为解开多民族国家现实问题提供了中国式思路。基于此,探讨欧美主体民族塑造国家及其后果,探讨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内涵,梳理我国建构民族国家理论的“想象”与多民族国家事实上的话语纠缠,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出现的语境、内涵及其导向,从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上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拓力。这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初心,夯实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增强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而且对于破解欧美民族国家理论困境,探究新时代背景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民认同有一定启发。
一、作为欧美社会秩序的民族国家:主体性民族塑造及其后果
“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1[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民族(nation)—国家(state)这一本身带有欧美话语权的学术用语起源于美洲2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8-62页。,孕育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实践中,其形成与“二战”后欧美各民族国家对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及其“权”“利”的讨论有关。从欧洲民族国家的起源来看,它是在传统国家基础上,经由民族主义兴起而成。欧美民族国家发展过程就是一部完整的“民族国家建构”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1648年)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体系形成新的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欧式国际关系”准则,为世界各国通过协商,签订条约解决争端开创了先河。
这种模式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海外殖民推进,国家观念和主体民族利益不断得到强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研究表明,随着资本主义上升,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使资源非均匀性流动,“必然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域缔造强大国家,而在边缘区域缔造弱小国家”3[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资本主义伴随民族国家之兴攻城略地,形成了全球性的制度革命,并产生出了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表述,即“将民族国家视为主权的惟一合法的表达形式”4[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并以主权民族“代表”人民的国家形式变换角色,扩展权力。欧洲本土的区域民族国家战争推动民族与国家边界的重合,使“主体性民族”身份不断得到塑造。1857年,根据马志尼划分的地图,欧洲是由二十个国家与联邦组成。“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欧洲被划分为26个国家,一“主体民族”建一“主权国家”(单一民族国家)的实践借着民族国家外壳登上国际社会的舞台,成为现代国家的“模型”。
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来看,欧洲民族国家的现状以国家既有法律为框架,以地域空间认同为范畴,以大众彼此间的交往为中介,以通用语言和共同生活方式为基础,塑造“主体民族”意识形态上的认同结构。此种建国理论滥觞于霍布斯的“公民”论和洛克的“自由主义”,而哲学的思考力则把“阶级国家”独占社会共有资源的“自在传统”逐渐转化为公民“让渡”权力以成民主国家的“自觉追求”。其产生的动力来自文艺复兴后人们对“现代”这一哲学概念的求新意识。在群体认同基础上,新型的“民主”观念冲破原有国家秩序,让民众与某种意识形态结盟,参与公共权力,以选举的方式干预国家政治,赋予特定政治共同体来实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保护更多群体权益。于是“由国家公民组成的民族(Staatsbürgernation)和由人民组成的民族(Volksnation)之间的差异,也体现了民主的民族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但即便如此,这依然无法绕开“民族利益”问题,暴露出其难以回避的制度缺陷6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159页。。尽管单一民族国家宣称其拥有民族主义“族性”7安东尼·史密斯、汉斯·科恩和厄内斯特·盖尔纳关于民族主义概念的探讨,引起人们对“族性”政治的关注,他们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世界由不同历史、特征和认同的民族组成;二、民族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源泉;三、对民族的忠诚超出所有的其他忠诚;四、为赢得自由,个人必须从属某个民族;五、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决和自治。的意义,但民族作为一个现代集约化的认同形式,在族裔民族想象的建构性和公民民族的合法性结构之间徘徊,造成“主体性单一民族国家”应对公民国家多样性群体诉求的困境。
事实上,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路径来看,无论是从国家到民族,亦或从民族到国家的形成过程,其特征都基于塑造某一个民族为“主体”的国民国家(民族)认同,用“主权民族”或“国族”的话语建构语言、文化、历史,甚至人种与信仰的同质化,其后果必然使人口较少和话语权力较弱的民族权益受到侵犯。“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公民身份的制度安排将社会成员从‘集群化’状态打碎到‘原子化’的境地,继而通过一族一国的‘国族建构’实现单一民族国家的构建”,即“致力于以‘民族’为单位建构‘国家’(事实上更多是以‘国家’为单位建构‘民族’),致力于创建内部共同体的个体化同一,消灭差异”1关凯:《传统与现代:民族政治的中国语境》,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1期。。以主体民族为实体区分的单一民族国家存在着忽视其他民族(族裔)权利的思维缺陷,这种以“群体主次”为层级逻辑的国家建构形式,自然不愿正视本国历史与现实中形成的多民族的现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形式平等”的外衣下掩盖了各民族发展上的“内容不平等”。在这种国家理念下的政策运行,加剧了不同族裔(民族)在教育、经济上的分化。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多都是建立在‘少数民族’被同化、压迫和边缘化的基础之上的……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就是残酷的流亡和驱逐过程,就是强迫迁徙和剥夺权利的过程,就是消灭肉体的过程,直至种族灭绝。”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页。
当下,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都沿袭了英国宪章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后由“自由民联合”所签订“契约国家”的路径。按照宁骚先生的概念,“就是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3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在这一理论规制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与“同质的国民文化”就需要把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都置于形式相同的起跑线上展开生存竞争,其最大的局限在于系统性加剧了对弱小族群的不平等。
二、词义、事实与趋势的共有逻辑:民族国家的多民族
按照已翻译的既有概念,理解当下“民族国家(Nation-state)”需要从名称词义、现实本身和全球化趋势中去看。
其一,民族国家名称词义中的多民族性。按照拉丁文拼音传统,Nation起源于拉丁语的“natio”,词根为“nat”,强调人的“出生”和“根源”,“单一性”非常明显,而当“nat”与“ion”合成一词就指“出生之处”,进而引申为“国民”“国家”时,则又具备了人“出生之地”族裔的多元性。在中文语义中,从“民族国家”的词汇构成本身来看,“民族”应指代无数量限定的“国家政治认可的民族”。因此,仅从字面看,无论是英文语境下的“Nation-state”,还是中文语境下的“民族国家”,其共有逻辑都表明: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应包括“单一民族”和“多民族”。吴文藻先生早已指出:“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4吴文藻:《民族与国家》,载于《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基于此,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均可属于民族国家范畴。按此推定,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但其引入中国后,由于清末民国的历史情境5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以汉族为中心推翻清朝的过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汉族同化其他民族的国族建构过程。,“民族国家”往往被理解成有“主体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在此惯性下,单一民族国家的思维话语常掩盖了多民族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应有的含义,这在中国民族理论上极易造成混乱。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用中国民族6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3-66页。来指代中国境内各民族。
其二,民族国家现实本身上的多民族状态。在欧洲范围内,所谓“公民民族主义”国家实际上更接近多民族国家,而“族裔民族主义”国家更接近单一民族国家。这种划分在欧洲民族国家渐变中边界也不断模糊。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早期的秩序划分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不断冲击着单一民族国家。他们在经济交往的需要下,实现了民族互动和文化交流。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就指出了欧洲事实上的多民族现象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上世纪九十年代,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通过开展“欧洲共同体”建设,从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6 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拥有27个会员国的大联盟22020年英国脱欧。。其从经济上打破了国家壁垒,实现自由贸易;在文化上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就官方语言也有24种,实现了与“美利坚”相呼应的经济共同体。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欧盟体”正好体现了单一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窘态。基辛格说:“传统的民族国家认识到它们幅员太小,无法在全球发挥重大作用,因而寻求彼此组合成更大的集团。欧盟迄今为止最广泛地体现了这一政策。”3[美]亨利·基辛格:《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21世纪的外交》,胡利平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7-8、7页。尽管这种跨国经济联盟是基于欧洲民族国家经济类型互补、生产模式互嵌的形态下形成的,但在实际运作中,其所呈现出的功能已远超过了经济联盟的范畴。如欧盟成员国之间高效的协作机制在促进人口流动、文化交流与民族共生上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再一次深刻触动了欧洲原生民族国家的传统边界。当消费品、旅游资源、货币成为经济联盟的共同要素时,传统单一“民族-国家”也得益于不同国家公民、各民族交往带来的多样式发展成果,提升了欧盟成员国的国际竞争力。
其三,全球化趋势下的多民族现象。从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讨论4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到全球化促使下的多族群、多文化、多意识形态的出现,纯粹单一民族国家也更加成为东方想象西方和西方自我想象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单一民族国家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多民族国家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传统单一民族国家高呼的平等、自由、人权、博爱等政治口号,在遇到少数族裔生存境况时呈现出了两难局面:一是当他们否定国内既有的其他族群的政治特性时,就违背了其建国之初所秉持的价值观和在国际上试图变现的民主形式;二是他们总想通过各种方式,固守其单一民族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利益,排挤其他族群的“天赋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信息技术的持续影响,交通革命的升级换代,人口流动的频繁增长,全球化进程中纯粹单一的民族国家只能是一个想象概念。面对自我喧嚣的文明尺度,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国内移居族群问题5参见[美]亨利·基辛格:《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21世纪的外交》,胡利平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7页。。解决多民族问题的许诺也成为政治博弈的话术之一。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化对单一民族国家的现实提出了各种诘难,国家的多民族形态将持续发酵,“使西方各民族国家不得不放弃‘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以及同化政策,转而采取更为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满足各族裔群体的权利要求”6朱联璧:《“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兼评威尔· 金里卡的〈少数的权利〉》,载于《世界民族》2008年第1期。。这相对逐渐消解的单一民族国家而言,民族国家中的多民族国家内容将越来越成为世界秩序的主流。那种由想象的单一共同体组成的政权组织正经受全球化的挑战,正如基辛格所言:“民族国家这一主导概念本身也在发生变化。”7[美]亨利·基辛格:《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21世纪的外交》,胡利平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7-8、7页。
民族国家是一个非常容易把人们引向歧义的概念,通常会被理解成“单一民族国家”或者“国族一体”的民族国家。前者往往声称某一个民族的主体地位,后者通常会在国家名义下,以形式平等的名义推行非平等内容政策,悄然把某一民族推上国族的地位。如果说前者是民族主义先天性的道义缺失,而后者则更多的是民族主义绑架爱国主义的非正义。因此,朱伦在1997年所写的文章中主张将“nation-state”译为“国民—国家”8朱伦:《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载于《世界民族》1997年第3期。;2014年复旦大学举行的“跨学科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国族’论坛”上,纳日碧力戈主张把民族国家直接译为“多民族国家”,李红杰也主张翻译成“国民国家”9参见林青、祁涛:《“跨学科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国族’论坛”综述》,载于《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7期。。实际上,1926年,吴文藻先生就对多民族国家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后果作过一个前瞻性判断:“万一无数民族,不能在此大一统之民族国家内,享同等之自由,则任何被虐待之民族,完全可以脱离其所属政邦之羁绊,而图谋独立与自由,另造一民族国家也。”10吴文藻:《民族与国家》,载于《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这就从政治正义的角度指出单一民族国家中“被虐待之民族”的政治诉求,以此警醒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平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那些先入为主的以“整合”手段创造“国族”来抹杀国家既有的多民族事实的论调,无疑是对多民族国家内涵的误用,同时也为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实践设置了一个必跳的理论陷阱。
三、单一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的话语纠缠
欧美世界在现代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的形成都曾打上欧美国家殖民的烙印。“对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亚洲所有国家来说,现代化进程要求它们按照少数西方国家首先采用的技术模式和制度模式对自身进行修改和调整。”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清末民初的社会运动始终把中国置于欧美话语语境中展开,民族国家建构也在这种碰撞中拉开帷幕。中国的很多政治术语也是在接触欧美国家时逐渐形成的,特别是《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被动加入了欧美国家秩序。在此期间,一些借用的术语有普适性,但也有些术语却仅限于欧美社会语境。比如“民族”“民族国家”就属于这一类2参见马德普:《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载于《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期。。
在此情景中,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名称使其在继承清朝疆域版图和包摄境内群体上合理合法,承载民族国家概念的“民族”(nation)就逐渐被“中华民族”所代替。不过,其一开始就面临着单一民族国家思路在解决多民族国家现实问题上引发的争议和纠缠。尽管经历了宪政时期的“五族共和”和学术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但“中华民族”仅指汉族的思维惯性始终在孙中山先生早期驱逐鞑虏的思维世界里运行。在这种话语体系里,效仿欧美“一族一国”模式,建立民族国家以“图强保种”的理念,在政学两界“几成宗教”3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8页。。梁启超原初的学术概念——“中华民族”也上升为固定的政治话语。作为中国导入欧美秩序的国家理念,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或汉族同化其他群体以成国族的“中华民族”,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时期和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时代被视为“政治正确”。由于其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这种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过程必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理论的局限性,无论是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还是汉族同化其他民族以成“国族”的思维,必然也会步入欧美单一民族国家建构的车辙,在面临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统一多民族事实时必生窘态。“民族主义者……在追求自己利益或宣称本民族自己的利益时,压制其他民族的自决、自治,甚至否定其他民族的特征等。”4[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在这种话语辞藻形成的上层建筑体系里,民族的多样性被“国族”单一性遮盖,多民族话语的动态性被单一民族规制的静态性所埋没,多民族国家本有的理论活力也受困于民族与国家的纠缠话语中,从而失去应有的张力。这既为南京国民政府退出历史舞台埋下伏笔,也为当下中国探寻多民族国家建构之路提供了经验教训。
对之,吴文藻先生早已指出,“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必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5吴文藻:《民族与国家》,载于《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探寻救国方向上始终坚持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新中国成立后,在尊重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论,为更好地执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的同时,赋予少数民族担当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责任和义务,并将其转化成主人翁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推动各民族发展的文明进程。无论是从党史,还是从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史来看,新中国都是按照多民族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来设置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背景的复杂变化,除了国内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客观问题外,互联网、全球化、市场化、民族主义与极端分裂主义的出现又引发了新问题6参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在强有力的市场经济与欧美主导的国际话语背景下,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民族学与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相遇后,在解释共有的“民族”概念时出现不同语境,“民族”一词对应的英文翻译也在“nation”“minority group”“ethnic group”“ethnic minority”等7参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英译问题》,《中国民族报》,2013年03月22日。和汉语拼音“Minzu”之间讨论。作为“nation”的“民族”再次与“中华民族”语境下的“民族”对接。这似乎成为学术走向国际,塑造中国话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在学术建构上,《宪法》中规定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被悄然塞进了“单一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于是中华民族(中华诸民族)蜷缩在欧美话语下成为类似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和德意志等情境中的民族了。学术界对中国涉民族界定时,也是按照语境需要在“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之间切换,进而造成“民族国家”概念的混乱、纠缠和理解上的偏差,即“民族国家”经常被理解成了“单一民族国家”,而非多民族国家,似乎“多民族国家就是‘非典型’的国家,因而使这个不正常的国家‘典型化’,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治理难题”1陈建樾:《民族国家:认识、分类、治理及其争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讨论的背景与前景》,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同时,多种话语撕扯、纠缠,把原本清楚的理论浑沌化,导致在阐述我国“民族国家建构”时,一些学者思维结构中已植入一个潜意识的逻辑:把“国的主权唯一性”等同于“族的唯一主体性”,把“主权中国”置换成“单一民族国家”,甚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若从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思维去理解,此表述无可厚非;倘若从中国现实去理解,则似乎在本然、实然和应然上混同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是中华民族“滚雪球”的核心,而非“中心”2参见苏航:《“汉族中心”还是“汉族核心”: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新探——兼评新清史的内亚王朝史观》,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9期。,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成员以不背离国家统一为前提的经济、文化、教育等进步发展,非但不会对中华民族整体性“产生解构”,而且还会增强共同体的“短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总钥匙的基本逻辑,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之“纲”的原因之一,更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内涵的应有之义。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的词义逻辑和宪法规制都表明,中国为“人民共和”的国家,而非“民族”的国家。这种话语下,“人民”自然是构成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石,而非“民族”。这种在单一民族国家观与多民族国家观的表述交错、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时空交汇下的话语纠缠,撕裂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求解中国民族问题的合力。为了破除这种理论思维带来的困惑,寻找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国家民族整合之间的关系,建构政治认同体系下的民族认同,形成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沟通方式,学界出现了少数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观点3参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后,单一民族国家思路为理解中国多民族现实的错位,把视线转向了对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实践成效的凝视上,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话语也相继出现4参见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关于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间的理论纠缠,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中国古代一直把‘华夏’与‘夷狄’之间的差异理解成‘人种’之别,虽然后来又有人主张用文化的力量去消解这种区别,但论辩的着眼点还是落在了人种之上。但中国人对族类历史演化的理解与西方大有不同,那就是中国基于血缘与人体解剖学关系的认识不是固化的,与之相关的共同语言、宗教、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民俗也不是固化的,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就使得那些想用人类学式的单一‘民族’理论解释‘中国’与‘夷狄’关系的观点很难奏效。”5杨念群:《重建“中华民族”历史叙述的谱系——〈重塑中华〉与中国概念史研究》,载于《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按照欧美国家话语理解中国,若用意识形态划分的角度看,这就是用资产阶级理论理解社会主义现实,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治理的理论支撑时必然捉襟见肘,甚至会产生干扰。“西方大多数阐述或参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作者同时暗含着一种种族的或民族的身份(identity)……在中国,把这种话语改造成为一种在竞争时代能够发动(国民)竞争的学说,当然需要建立一个机关,建构一个特殊的历史主体,而这样的主体在当时世界秩序中只能是民族国家。”6[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在现实话语中,这种用“单一民族国家”等同“民族国家”的思维逻辑,助推了普通民众理解民族国家含义的碎片化,为现实的政治运行带来诸多困扰。正如吴文藻先生所言:“今之人舍本逐末,竞言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而不明其最后之用意所在,宜其思想之混乱也。”7吴文藻:《民族与国家》,载于《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本文认为,“中华民族”中的“中华”也非“中原河洛地区与华夏子孙之地”的合成,而指传统上中国“五方之民”所在的疆域。“中华民族”中的“民族”不同于民族主义中的“单一民族”,而本身就是“多元一体”。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47页。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有必要从历史、现实所呈现的联系和态势中找寻。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疏解话语纠缠的理论拓力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宪法》不仅在序言开篇就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3、96页。,而且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3、96页。。党的十八大以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新疆工作座谈会,特别是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多次强调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丰厚遗产,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疆域、书写了历史、创造了文化、培育了精神。
在世界史视阈下,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一致性的时代里,中国就已经有了与中原相区别的族群了。当西欧以基督教皇为象征,分邦割治时,东方的中原正经历着魏晋南北朝“五胡入华”的时代,少数民族已经自觉融入到中原文化海洋中,继承并发展着中国传统的政治、历史、文化,即便“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4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8日。。而元清时期设置宣政院、理藩院“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使大一统中国治理模式达到了一种新的状态,这种历史变迁不仅没有使中国如美洲和欧洲那样出现宫廷选择方言、印刷传播“官方民族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5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6-80页。,反而在这样的格局中缔造了客观存在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清末民国时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作用下,国家衰弱,社会精英以“民族主义”为旗,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发挥过重要的凝聚作用,塑造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层次涵义。尽管中国共产党早期就发现了此概念的局限性,并为其赋予了“新内涵”6“党的二大”后使用了“中华民族”指代中国境内各民族,接着又改用“中国民族”概念,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其后“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概念交替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文件和各种指示信中。且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使用“中华民族”的频率增多。,但是经历那段苦难岁月锤炼而成的新概念,在历史记忆和思维惯性下,中华民族这种复杂而又充满歧义7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族概念经历了汉族、国族同化下的大民族涵义,而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则指“中华各民族”。的“群体指代”仍然长期存在。
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共产党推动各民族发展的理念提出8《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14年05月30日。。同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阐释:“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9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2019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和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不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主线、道路、制度到民族工作,全面系统地指明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所蕴涵的治理逻辑。这都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多民族凝聚的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应该包含多民族国家的事实,同时又要将中国各民族整合在一个共同体的范围内,厘清了一体和多元的内在逻辑关系。此哲学根基是唯物辩证法中整体与部分范畴的应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涵续着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国家的思路,又解决了多向度上的理论纠缠,彰显了其疏解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话语纠缠的理论拓力。
“中国作为一个有别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传统多族群国家”10[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页。。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一些学者企图把中国“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设想改造成一个“只有一体”的“民族国家”显然是不现实的。反过来说,“国家-民族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国内各民族的同一”1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114页。。一些学者所谓的“‘多元’价值文化伸张的背后实则潜藏着对整体民族的解构性风险”2王翔、李慧勇:《“中华民族”入宪: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文本轨迹和演化逻辑》,载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他们仅仅看到了“多元”外向的扩伸,却没有看到“多元”内向的张力;而“‘一体’价值的扩张往往会淹没各民族群体发展的特殊性”3王翔、李慧勇:《“中华民族”入宪: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文本轨迹和演化逻辑》,载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也仅仅看到了“一体”的价值“整合力”,却无视“一体”的价值建构性。实际上,“一体”和“多元”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中,“在承认和尊重各民族差异基础上的中华民族统一性,确立了中国人民独立自强的民族属性和国家归宿”4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114页。,这才更加符合二者的良性互动。如果说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来理解这种平衡系统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蕴含的理论拓力就更有条理地疏解了单一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引起的诸多话语纠缠,把“一体”与“多元”导入善治秩序中。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还为“一体”(中华民族)与“多元”(各民族)的协同推进提供了明显的价值指向:“多元”铸牢“一体”意识,“多元”为“一体”建设贡献力量,才能实现“一体”伟大复兴,也自然实现了“多元”健康发展。这种理论的伸张力足以化解“潜藏着对整体民族的解构性风险”。同时,基于多民族国家凝成的“一体”是一个有明确指向、多民族有机结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避免了凸出或凹陷某一民族的可能性,从而承续了按照社会发展和民族发展实际进程来实施的区域化民族政策,规避了“淹没各民族群体发展的特殊性”,强化了“各民族发展”对“一体”价值的建设性。当民族群体发展到达一定程度后,民族共同性就会不断增多,这也是我们各民族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展中所呈现的特征。
语境词汇的转换必然与深刻而复杂的内外环境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时代变化凸显诉求的诠释与回应。西欧“民族-国家”模式下的“主权民族”或者“一族一国”完全可从国际关系角度去理解,即体现国家主权独立意志的国家-民族的身份同一性5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那么,作为“上层位”认同来凝合国民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世界政治话语下的各民族的“身份同一”,这种缓冲性就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特征的一个新诠释,也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理论突破口。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拓力正好解开了学界关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还是民族国家这一模棱两可的纠缠,其既有多民族统一的内涵,又有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指向,既防止了各民族发展凸显个体以冲淡中华民族整体繁荣的隐忧,也防止了“主体民族”塑造以消解各民族发展的担心,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产生釜底抽薪的冲力。
在构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话语体系中,只要涉及民族国家内容时,有必要将其固定在“多民族国家”的话语结构中解析,其不仅有理论意义,更有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里的“中华民族”(中华诸民族)共同体,而不是中华民国“宗族论”话语下的“中华民族”(汉族或国族),虽然二者使用名称相同,但实质却大相径庭6参见马英杰:《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语境下“中华民族”语义脉络》,载于《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五个认同”维度下的中国“家底”,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时代话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通过民族识别赋予了各民族的“身份”合法性,这既不完全是族群视角下的“文化民族”,也不是民族国家视野下的“政治民族”,而是中国“家底”所特有的家庭成员。其在认同层次上,中华民族是“上层位”认同,中国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和相互认同是“次层位”认同。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能把中国“家底”中的“多元”(各民族)内置于“一体”(中华民族)格局内的理论根基。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质。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涉民族的话语表征来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不断的深化、丰盈。“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已长期内嵌于政治话语逻辑之中,并在法律法规、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及习近平总书记公开系列讲话文稿中有不同程度的显示。”7王翔、李慧勇:《“中华民族”入宪: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文本轨迹和演化逻辑》,载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当下中国多民族格局是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多民族的样式正好适合科技革命兴起,加速人口流动1这个流动指企业全球化的人口移动,个体自由选择性的移民和战争被迫下的难民。而形成的多元文化的国家形式。当全球化、信息化、交通便利化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同时,极端民族主义也有抬头的趋势。在此情境下,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显得亟为紧迫。在较多的、具有累积性的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也被学界广泛接受,而面对当下国际环境的骤然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更能从大众的角度表征民族团结与社会聚合的语境,同时又完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价值指向。由此可见,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的语境转化,既化解了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对“中华民族”歧义的困惑,又为其他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中国方案。
随着科技发展,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单一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会走向多民族国家形态。由血缘而成的种群,由文化而成的族群,由信仰而成的教群都会以各自方式参与社会事务。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多民族国家才是国家的基本生态,这既是当下的事实,又是未来的趋势。因此,处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民族的关系将是人化自然界的一个普遍问题。如果上层建筑忽视特定生产力下的这种生产关系总和的客观存在,可能不利于疏导社会基本矛盾的有序运动,而且还会导致社会肌体受到伤害。文化求异、文明求同是信息化时代的主旋律,多民族国家将会是未来的客观存在形式。谁能秉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增订本)》,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第84页。的原则,处理好多族群、多文化关系,谁将会在政治文明上引领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善治理念所昭示出的理论拓力不仅疏解了我国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各种话语纠结,而且也能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本国民族问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