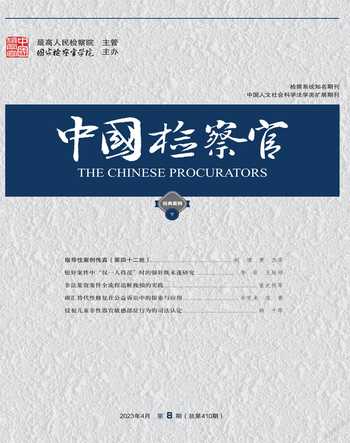侵犯儿童非性器官敏感部位行为的司法认定
2023-05-15韩千张纪娜李正源
韩千 张纪娜 李正源
一、基本案情
刘某某自2021年9月1日起在某乡村小学支教,任班主任、数学老师。2021年9月至10月期间,刘某某在教室内当众多次对班内多名不满十二周岁的幼女进行猥亵。上课期间,多次趁A女生站起来回答问题时,站在旁边用手隔着裤子摸其臀部至回答完问题;课间休息时,多次用手隔着裤子捏B女生的大腿根内侧和屁股;课间及看管学生午休期间,多次以未遵守课堂纪律需要以示“教育”“惩罚”为借口,躺在躺椅上让C和D女生按摩其大腿根内侧,有时按摩至午休结束。案发后,4名被害人均表示,刘某某的上述行为使其产生了“厌恶”“害怕”“变态”“羞耻”等消极情感,甚至催生出厌学情绪。
二、分歧意见
对于刘某某实施的上述行为能否构成猥亵儿童罪,存在如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猥亵儿童罪。理由为,对于本案涉及的三笔案件事实,在前两笔案件事实中,刘某某触摸、捏拧女学生的屁股以及大腿根内侧,但两处部位均不属于通常理解意义上的“性器官”,且刘某某实施上述行为时隔着裤子,属于间接触碰,行为时间较短,难以认为造成了侵犯儿童性自主权、陡增儿童性羞耻感的损害结果;而在第三笔案件事实中,刘某某要求女学生为其按摩大腿根内侧的行为,也难以符合猥亵“对他人实施”的基本特点。综合来看,刘某某的涉案行为,在情节上显著轻微,不宜按犯罪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理由为,根据猥亵的基本内涵以及猥亵儿童罪的保护法益,结合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基本要求,只要相关行为使未满十四周岁儿童的健康成长受到性行为的不当妨碍,就必须考虑是否有必要发动刑法第237条猥亵儿童罪这一儿童性禁忌规范加以规制。就此而言,一方面,本罪“猥亵”的侵犯部位不能仅限于“性器官”,而是应当涵摄一切具有性象征意义的身体部位,侵犯的方式也不能仅限于亲肤接触的直接侵犯,还应包括相隔衣物的间接侵犯甚至不发生触碰的“隔空”侵犯;另一方面,所谓“对他人实施”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行为人需朝向被害人施以‘物理力”,而是应当被实质地理解为“行为人将对性自主权法益的侵害施加于被害人”,就此而言,行为人要求儿童对自己施以猥亵的行为亦应包含在内。除此以外,综合考虑到本案中刘某某利用教师这一负有照护职责人员身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于教室这一公共场所当众且多次地针对多人进行猥亵,造成了涉案女童性厌恶与性羞耻的损害结果,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宜以猥亵儿童罪论处,并适用“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这一加重处罚情节,提档量刑。
三、评析意见
上述分歧意见中,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刘某某的行为应当以猥亵儿童罪论处。理由如下:
(一)“猥亵”概念应涵摄侵犯儿童非性器官敏感部位的行为
一般认为,所谓猥亵,即除奸淫以外能够满足性欲和性刺激的,侵犯他人性自主权,有损他人身心健康的行为。[1]但对于未满十四周岁的儿童,为了确保其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发育过程不因过早牵涉性行为而遭受不当妨害,因此在猥亵儿童罪中,刑法将未满十四周岁的儿童视为不具有性承诺能力者,只要对儿童实施的相关行为带有性的意义,具备能够满足他人性欲与性刺激的属性,就认为其足以构成对儿童性自主权与身心健康的侵犯。故对于猥亵儿童罪中猥亵的界定,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满足他人性欲与性刺激的属性,这取决于社会一般人的判断,即相关行为在普通成人的性观念看来,具有刺激、兴奋或满足性欲的性质。[2]当然,如果结合被害人陈述,能够确证行为人的行为导致被害人产生性羞耻与性厌恶,实际造成了其身心健康受损的后果,则可以进一步地说明相关猥亵行为适宜且需要被列入到猥亵儿童罪的规制范围。因此,根据上述定义要求,可知:
首先,对于猥亵行为的侵犯部位,既包括“广义”的性器官,亦应当将所谓的性敏感部位、性争议部位纳入其中。具体而言,对于“广义”性器官,如女性阴道、男性阴茎、乳房、肛门等,由于具有最强的性象征意义,只要不加遮掩,单凭注视就足以引发他人性欲,故对其加以实际侵犯的行为,属于猥亵行为的典型类型;但除此以外,对于所谓的性敏感部位,如屁股、大腿根部、唇舌等,亦具有次强的性象征意义,通过接触能够引起性欲望、性刺激,因此对其加以侵犯的行为一般应被纳入到猥亵的评价范畴;对于性争议部位,如腰腹、肩颈、腿部等,虽不具有明显性象征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多加以遮掩,通常也不会与他人发生接触,是否能够作为猥亵犯罪的侵犯对象,则需要结合其他要素加以综合评估;而对于明显不具有性象征意义的,如手足、胳膊等性中性部位,在社会生活中会较多地与他人发生接触,通常也会暴露在外,则无法被视为猥亵行为的侵犯对象。[3]
其次,对于猥亵行为的行为方式,既不能局限于亲肤接触这一直接侵犯类型,也不能仅包括行为人朝向被害人施以“物理力”的情形,而是应当包含亲肤的直接身体接触、相隔衣物的间接身体接触以及隔空的无身体接触三类情形,这三类情形的法益侵犯程度依次递减。对于直接身体接触与间接身体接触,又可包括直接对儿童实施猥亵或使第三人对儿童实施猥亵,以及使儿童对自己或第三人实施猥亵两类情形,前者的违法性高于后者。对于无身体接触,则可细分为使儿童自行猥亵,使儿童观看自己或他人性行为、猥亵行为或淫秽物品以及在网络上隔空要求儿童裸聊或发送裸照三类情形,前两类情形可称为近距离非身体接触型猥亵,第三种情形可称为远距离非身体接触型猥亵,对性自主权与性羞耻心的侵犯程度亦由高到低依次递减。[4]
当前的司法实践,已经普遍承认网络隔空猥亵的行为可以构成猥亵儿童罪,如指導性案例“骆某猥亵儿童案”[5]以及典型案例“蒋成飞猥亵儿童案”[6],明确了借助网络手段强迫或欺骗儿童发送裸照、与之裸聊的行为可以构成猥亵儿童罪。相比而言,根据体系解释举轻以明重的解释原理,实际构成了对被害人的接触,只不过因相隔衣物而“间接”、因由被害人实际执行猥亵而逆向的猥亵行径,更应被纳入到猥亵儿童罪的评价范畴,这也符合了当前刑事司法不断通过实质解释的方法拓展“猥亵”外延、强化打击力度以全方位保障儿童性权利的发展趋势。
最后,结合本案中相關被害人“心里特别害怕”“他的行为挺变态的”“这些地方都是不能让外人碰的部位、都是人的隐私部位”“厌恶”“心情很难受”“脸红红的”的陈述,可知刘某某的行为使被害人感到羞耻、难以接受、甚至厌学,侵犯了未成年人的性羞耻心,已经给被害人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进一步地确证了刘某某行为的“猥亵”属性。
(二)侵犯儿童非性器官敏感部位行为的定罪量刑应结合具体情节谨慎考量
侵犯儿童非性器官敏感部位的行为,即便是以非亲肤接触的间接方式实行,且部分情形下乃是通过对儿童发送命令,以使其对行为人实行猥亵的方式为之,仍足以被纳入到“猥亵”基本文义的涵摄范畴内。但相较于行为人以直接接触的方式、面向儿童施以物理力以侵犯其性器官的典型入罪类型,该类型在违法与有责程度上明显更低,二者分别属于猥亵概念的“边缘地带”情形与“核心地带”类型,如段卫利博士所言,其彼此之间在法益侵犯性与可责难性上的量度差异,需要在刑法的评价中加以体现。[7]
与此同时,也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即便行为在字面上形式地符合构成要件,也需要实质地分析其违法与有责程度,将在本质上不具有可罚性、难以在实质层面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从刑法的规制对象中剔除。[8]因此从刑法谦抑性原则出发,类似于本文案例的情形,不可不加区分地一律入罪,而是应当综合考量加害人的身份、实行场所、手段、次数、受害人人数、持续时间、所造成的后果、加害人的前科记录等情节加以综合判定,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明确了猥亵儿童罪四大加重处罚类型的背景下,在相关猥亵行为的违法性无法明显达到入罪的要求因而存在定性疑问时,应当重点观察其是否具有这四类加重处罚事由。识别仅宜通过民法典第1010条第1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加以规制的性骚扰侵权行为以及猥亵行政违法行为类型,与需要发动刑法第237条的猥亵儿童罪加以规制的猥亵犯罪行为类型之间的界限。
在本案中,刘某某在主体身份、手段、次数、被害人数量、持续时间以及行为环境等方面均存在从重处罚情节,因此综合评定而言,应以猥亵儿童罪论处、加重处罚。具体来说:
首先,在主体身份与手段类型上,刘某某身为教师,对于被害人负有照护职责,然而却滥用基于该身份所形成接触儿童便利以及被害人无条件的信赖与服从,为实施猥亵行为提供方便,严重侵犯了被害人的性权利与对教师的信赖和尊重情感,使其陷入到极为无助的危险境地与伤害中。同时刘某某打着从事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幌子,以未遵守课堂纪律从而“教育”学生为借口,要求学生在午休期间为其按摩大腿根内侧以示“惩罚”的行径,对被害儿童形成了一定的强制力,结合上文的被害人陈述,能够判断其行为显著违背了被害人的性意志,因此可被评价为采取了强制手段。
其次,在次数、被害人数量及持续时间上,通过已经查证的三笔案件事实,可知刘某某曾至少三次,针对四名女学生实施猥亵,属于“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且其中部分猥亵情形在“学生回答问题期间”甚至“学生课堂休息与午休时间”持续进行,并非“短暂、瞬时且偶然”,不宜被评价为仅构成民事侵权或行政违法的“咸猪手”性骚扰行为。
最后,在行为环境上,刘某某在教室环境中,于课堂进行、课间休息以及午间活动等其他多数同学均在场的情况下对被害人施以猥亵,根据《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3条,“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均可以依照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237条的规定,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其行为已构成“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此外,刘某某的这一行为不仅在客观上使被害人在可能大概率受到同学注视的情况下遭受公然猥亵,从而导致其性私密情感被严重侵犯,且在主观上体现了刘某某无所顾忌,甚至追求被发现、围观之刺激感的严重恶性,彰显了刘某某对于公序良俗的蔑视、挑战以及对被害人的侮辱,具有典型的流氓性质,亦属于作为加重处罚类型的刑法第237条第3款第(二)项所言的“情节恶劣”型“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
(三)侵犯非性器官敏感部位行为的入罪路径已形成一定的司法共识
案例检索显示,在与本案具有相近案件事实的“周某某猥亵儿童案”中,周某某利用担任被害人班主任以及数学老师的便利,对女学生采取搂抱、摸屁股、摸大腿内侧部位的方式进行猥亵,考虑到其具有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特殊身份以及在教室这一公共场所,当着多名同学的面针对多人加以多次猥亵等从重处罚情节,故以猥亵儿童罪论处,并适用加重处罚条款[9];在“杨某某猥亵儿童案”中,杨某某利用担任班主任身份的便利,对两名女学生分别采用强吻、触摸大腿与臀部的方式加以猥亵,最终考虑到其具有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的特殊身份、采用强制手段以及在办公室这一公共场所,于有其他同学在场的情况下实施猥亵等从重处罚情节,对被告人以猥亵儿童罪论处[10];在“刘某某猥亵儿童案”中,刘某某采取捏拧大腿、触摸臀部的方式猥亵女童,考虑到其具有在校园环境为之、先后对4名被害人多次猥亵以及造成被害人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内心害怕的身心健康受损后果等从重处罚情节,最终法院亦是通过适用猥亵儿童罪及其加重处罚条款的方式加以定罪量刑[11]。由此可见,对于侵犯儿童非性器官敏感部位等非典型猥亵行为是否应以猥亵儿童罪论处、如何确定入罪标准以及能否适用加重处罚条款等问题,已经在实务中形成了一定的司法共识。
综上,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猥亵行为进行类型化划分,关注不同行为在法益侵犯性以及可责难性上的量度差异,并根据具体情节作出罪与非罪、轻刑与重刑判断的差异化处理方式,能够有效实现并促进定罪量刑的精准化、均衡化和科学化,避免不当入罪、量刑失衡等问题的出现,这应当在日后司法实务人员办理猥亵儿童案件的过程中,被进一步地沿用与改进。最终,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刘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胶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6年,同时禁止被告人刘某某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5年内从事教育、训练、看护等与未成年人有关的职业。一审判决后刘某某上诉,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266061]
**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一级检察官[26633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430073]
[1]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4页。
[2] 参见阮齐林:《猥亵儿童罪基本问题再研究》,《人民检察》2015年第22期。
[3] 参见彭志娟:《猥亵儿童行为违法性评价要素分析》,《犯罪研究》2021年第5期。
[4]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145页。
[5] 参见北大法宝:《检例第43号:骆某猥亵儿童案》,北大法宝https://www.pkulaw.com/gac/f4b18d978bc0d1c7abfe5e1ef86dbd35ad38d151d24852efbdfb.html?keyword=,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2月5日。
[6] 参见北大法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性侵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之三:蒋成飞猥亵儿童案》,北大法宝https://www.pkulaw.com/pfnl/a6bdb3332ec0adc41d046879616bc9de44376e2671216ce8bdfb.html?keyword=,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2月5日。
[7] 参见段卫利:《猥亵儿童罪的扩张解释与量刑均衡——以猥亵儿童的典型案例为切入点》,《法律适用》2020年第16期。
[8] 参见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9] 参见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皖0521刑初30号。
[10] 参见湖南省泸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2)湘3122刑初27号。
[11] 参见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皖03刑终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