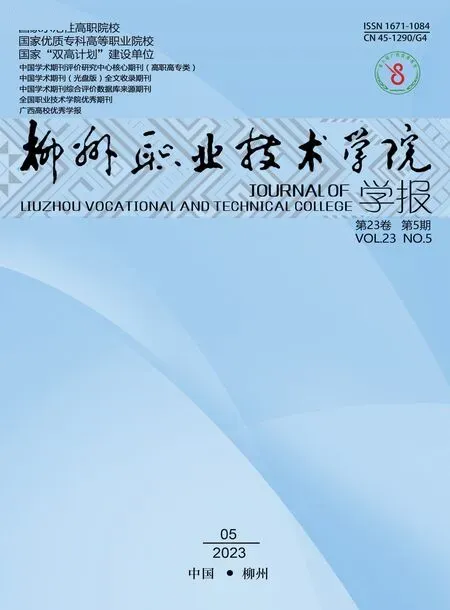《西瓜船》语境差探析:错位与颠覆下的多元人性
2023-05-14肖祉烨
肖祉烨
(福建师范大学,福州 350001)
引言
《西瓜船》是中国当代作家苏童香椿树街系列故事之一。香椿树街是苏童少年时期的居所,他事无巨细地在纸上温习他的家乡,在一声声吴侬软语和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中勾勒出江南小城里的众生相。香椿树街上人世轮回,《西瓜船》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松坑人福三来这里卖瓜,却阴差阳错被叛逆的十七岁少年寿来捅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松坑人与香椿树街的接触和碰撞。以“松坑”为代表的乡村叙事元素进入“香椿树街”的封闭叙事空间,完成了文本结构中的多重语境置换。西瓜船上留下了少年人成长的荒诞和人性善恶的对垒,错位的生存与毁灭,在姑苏文化的抒写下架构起文本叙述中复杂而微妙的修辞性语境差。
语境差是修辞学语境研究提出的重要概念。语境可以分为语符层面、认知层面与审美层面。在同一界域内,语境各层面的要素间出现了不平衡状态,就会形成语境差。而文本间各因素的这种不平衡,看似背离了语境表层,但背离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深层的适应。从美学层面观之,语境差正是通过陌生化审美的操作来展现表达者的修辞意图,给读者以全新的审美感受[1]。苏童在《西瓜船》中便以他与生俱来的艺术感觉和审美趣味,实现了人物与结构、画面与情境、叙事与意蕴的最佳平衡。
一、人物认知错位形成语境差
小说语境的认知层面对话语的解读会综合语境各要素,并关联着表达与接受的相互融合。在特定语境下的言语代码所指往往会超越日常约定俗成的含义,带有特定语义[1]。当文本中由语符构成的言语内容与事理逻辑发生错位时,就会形成前后文的逻辑颠覆。在《西瓜船》中,这种逻辑颠覆大多来自文本语境下人物之间存在的不平衡状态。
(一)共知前提缺乏造成认知错位
在西瓜船的杀人事件中,起因是买瓜人陈素珍因买到了张老头的白瓤瓜,愤愤不平之下赶去换瓜。基于当下情境中的愤怒和城市人对乡村人惯有的偏见和鄙夷,陈素珍临时选中了福三讨要“公道”。“她印象中福三是松坑人中最不爱说话的一个,不爱说话的人要么是最憨厚的人,要么就是最精明的人”[2]5,然而换瓜行动最终失败了。陈素珍以为福三是个好糊弄的老实人,于是耍起无赖,拿着一块瓜皮就来换瓜。可实际上福三不仅精明得很,还会欲擒故纵,陈素珍也只能感叹“好你个福三,长了一副老实人模样,没想到这么精明的”[2]5。共知前提是一种隐含的语境要素,如果人物之间缺乏这种共知语境前提,就会颠覆人物的认知和行为,形成语境差。陈素珍和福三之间正是缺乏了共知前提,仅凭刻板印象下定义,造成了交流过程中出现认知偏差。由这种粗浅的认知所支配的行为,导致了预想结果的偏差,形成了故事中的第一层语境差,福三和陈素珍及儿子寿来间矛盾激化的伏笔就此埋下,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一环,福三错位的命运也从这里开始一步步走向深渊。
(二)听者与说者的认知偏差造成认知错位
“陈素珍从不向儿子倾诉心中的冤屈,因为儿子从来不听她的。陈素珍习惯在厨房里自言自语,一顿饭做好,唠叨结束,心中对一切的不满便也排遣得差不多了”[2]5,陈素珍换瓜失败,牢骚满腹,这是小城镇妇女最常见的发泄方式。说者陈素珍的话语意图指向的仅仅只是吐槽。作为一个爱唠叨的妇人,陈素珍话语编码、传递、发送的环节是趋向正常的。然而,陈素珍无意的唠叨在儿子寿来耳朵里,却成了一声声催命符,酿成了一场临时起意的杀人事件。
听者寿来,在作者视角下被描述为“他当时杀过猫杀过狗,还没有杀过人,有人说他迟早要杀一个人的”[2]5。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崇尚暴力,迷恋蛮力,在母亲的自言自语中化身为一个病态的“瓜的复仇者”,由此终结了福三的性命。寿来作为话语的接收方,在解码过程中形成了认知偏差,说者与听者的交际间出现不平衡,产生了文本叙述中的第二层语境差。
陈素珍由于错误认知,换瓜失败,激化了矛盾,又与儿子寿来无形中形成了认知偏差,致使“张老头卖白瓤瓜”与“陈素珍换瓜”及“福三不赔瓜死亡”之间构成荒诞的因果关系,一个西瓜取走了一条人命,前后文的逻辑由此被颠覆。看似武断和错位的逻辑判断融合在双层语境差的叙事之中,推动着故事的纵深发展。然而,在这些不平衡的语境因素之下蕴含的是意味深长的城乡隔阂、少年人的病态成长和人性的复杂,荒诞的逻辑因果也因此被弥合。
二、文本情境转换形成语境差
小说语境的认知层面通常有着语符表层与深层的语境因素相融合而构成的深层意蕴。当语境间各因素互不平衡时,原有认知被颠覆,同时打破读者预期,然而这些不平衡的因素之间又自发地相互作用,实现深层意蕴的建构[3],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和审美内涵。
“每逢七月大暑,炎热的天气做了西瓜的广告,城北一带的人们会选一个清闲的黄昏,推上自行车,带着麻袋或者尼龙网兜到铁心桥去买西瓜”[2]5。作者开篇即描绘了一个闲适的夏日傍晚,“西瓜”“黄昏”“打瞌睡”,这一个个语符堆叠,一幅慵懒的小城夏日景象渐次铺开,作者亲自带领读者进入乡间和谐的语境之中。按照故事线性逻辑,和谐的语境应当勾勒出平凡而温暖的市井故事,可画面一转,陈素珍买瓜被坑,城对乡的偏见与歧视乱飞;寿来激情杀人,福三鲜血直流,冷漠的路人和凑热闹的居民逐一出场,城乡的冲突、人性的复杂与卑劣尽显;松坑人齐聚,大闹香椿树街,乡人的粗俗野蛮和重情重义跃然纸上。派出所的到来终结了这一场闹剧,化工厂的卡车带走了松坑人,却留下了激化的城乡矛盾。开头的语境与生成的故事错位,小城夏日的温馨叙事置换为城乡暴力冲突,文本语符搭建起的画面情境完成第一次坍塌与重构。
小说至此描绘了一场莫名的少年杀人事件,一个在街头巷尾被人津津乐道的八卦闲谈,一次发生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却被咀嚼多次的城乡矛盾。然而,这个远离了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古老故事只是小说情节的前半部分,作者笔锋一转,顺着连接城与乡的那条河流,福三的母亲踏上寻船之旅。
“那天黄昏我们看见一群人抬着一条船橹向酒厂码头方向而去,傻子光春骄傲地走在最前面,尾随他身后的队伍组合得非常牵强,王德基的小儿子安平、李金枝、光春奶奶,还有头上包着一块毛巾的松坑老妇人”[2]5。香椿树街上找船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福三母亲最终被城市人所接纳,人们以各自的方式传递着歉疚和善意。金色的余晖映照在这个寻船队伍之上,画面中的暖意涓涓流淌,浸润着这条曾经被血腥和暴力充斥着的复仇之路。寿来向福三复仇,松坑人又替福三向香椿树街复仇。贯穿故事前半部分的复仇语境被消解,这个最有资格复仇的老妇人,用她巨大悲伤之下一颗柔软和慈悲的心将城乡间对抗的情绪调转为同情与歉疚,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心中最原始的“善”[4]。这个温情动人的画面建构于血腥野蛮的复仇语境之下,故事的展开游离了惯常的叙事逻辑而完成了第二次置换。
文本叙述的画面与情节,不断扭转、跳脱,从小城夏日的和谐语境置换为被血腥和误解充斥的城乡暴力语境,再置换到黄昏下善意弥漫的温情语境。两次置换,将文本叙述语境分割断裂,故事与常规线性逻辑背向发展,造成不平衡。但正是这些不平衡因素缔造的语境差,建构了跌宕起伏的故事。
三、人物形象的对转与颠覆形成语境差
在文本叙述中,除了依靠画面与情节推动故事发展之外,贯穿故事中的人物同样也在文本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并拥有着强大的情感力量,被赋予不同程度的文本作用,对读者的鉴赏接受活动有着重要意义。在具体文本语境下,人物形象被凸显放大,而在《西瓜船》中,松坑人和香椿树街上的人们在故事的推进中纷纷呈现出表层形象的不平衡,人物形象间互相对转,在转变中呈现对立的群体形象,而这种颠覆下也暗含了文本的主题意蕴。
(一)乡村人形象的对转与颠覆
松坑作为文本乡土元素的代表,开篇就强势进入城镇——香椿树街的故事话语之中,以福三为核心人物,拉开了这场城乡暴力冲突的序幕。福三的死亡,把城乡对立的情绪拉到高潮,仇恨与隔阂之下,人性中最原始野蛮的恶意肆意生长。
“大多数人一看就是临时从地里上来的,面孔很凶恶,身上则隐隐地散发出田野或泥土的清香,有的挽到膝盖上的裤腿管忘了放下来,小腿上还结着水田里的泥浆”[2]5,松坑的男人,带着最朴素的血亲复仇观念,满腔悲愤,来到了香椿树街。他们是作者笔下一个个鲁莽的、野蛮的、不知法的暴力分子形象。
“她记得福三的兄弟先是抢过饼干扔在地上,用脚踩得粉碎,然后他对其他几个人吼道,砸了她的床,看她怎么在床上吃饼干”[2]5,“高级的床”“饼干”“花床单”,这一个个城市生活的象征再次点燃了松坑人的怒火,他们的恨不仅因为福三的死,还有着对城市富足生活的愤怒[5]。乡村人暴力破坏了这些城市文明的象征,也宣告着松坑人正式成为城市人的敌人。
比起男人,松坑的女人们则更是把“闹”发挥到了极致,“她躺在卡车轮子前面,衣衫零乱,胸口湿了一大片,肚子极不雅观地袒露出来,圆鼓鼓的,悲壮地起伏着”[2]5。这场冲突最后的本质已经脱离了复仇,成为松坑人暴力示威和情绪宣泄的手段。这些乡村刁蛮的妇女形象和作风也成为香椿树街上人们津津乐道的槽点和谈资。
然而,因福三而来的,除了这些野蛮暴力的闹事者,还有一个慈祥的老妇人。这个与福三最亲近的人却不是来复仇的,而是来找船。与前文所呈现的松坑人的野蛮暴力形象不同,她一反常态,卑微而虚弱,谦卑又和善。
“福三人不在了,船要摇回去还给旺林的”[2]6。“妹妹你帮帮我,我眼睛不好,看不见的”[2]6。“弟弟你行行好,帮我找找船吧”[2]6。
“阿姐,你不要和他们吵”[2]6。
福三的母亲不哭也不闹,因为眼睛快哭瞎了,再哭眼睛会疼,头也会疼。人们无法理解她是在怎样极度的悲伤与痛苦中还坚持着强颜欢笑,最后完成了这趟寻船之旅。在这些松坑人中,她最怯懦,却也最坚韧,呈现出一种平凡中苦涩却不绝望的生命质感,而极致的柔反倒比野蛮的哭闹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与此同时,除了自身形象与力量的不平衡之外,她与前文所勾勒的松坑人形象也大相径庭,松坑人的形象由此发生对转。她以最纯朴的信念和一个母亲的宽厚与温和跨越了城乡的重重沟壑,人性深处的温润和善良从松坑乡下流向了城里的香椿树街[4],松坑人形象颠覆背后的不平衡也因此别具美感,意蕴悠长。
(二)城市人形象的调转与颠覆
当善意从乡村流向城市,香椿树街上人们冷漠而鄙夷的形象因此被颠覆。而城市人内心的纠结和外在表现的矛盾,也在表层的不平衡中升华为深层的平衡,一条不可思议的寻船队伍就此集结。
故事的前半部分,在福三被刺的求生路上,原本热心肠的谢胖子无动于衷,货车的司机也不肯停车救人,不断说着“抓革命促生产比救人更要紧”。这条路上充斥着这些“城市人”的好奇心和窥私欲,他们对生命的漠然和麻木,把人性的自私与残忍彰显得淋漓尽致。但故事的后半部分,作者打破了读者的心理预期,随着“乡村人”形象的对转,福三母亲用她的慈悲与质朴也促成了“城市人”形象的内在颠覆。
城市人内心的“恶”被福三母亲突如其来的“善”消解[6],浩浩荡荡的寻船队伍无形中与丢船的肇事者重合。从安平开始到李金枝再到光春奶奶,他们起初也是城市人冷漠形象的副本,以李金枝为例。
“李金枝又被吓了一跳,缓过神来就更气愤了,拿着量衣尺朝安平肩上啪啪地打,骂道,该死的小畜生,你到我家来找那死人船,怎么不上你家找去?触了霉头看我不找王德基去,打死你”[2]6。
“等等,我带你们去光春家看看”[2]6。
“李金枝站在码头上,手指着运酒船大声批评那些船户,怎么这么缺德?好好一条船,给你们弄成这样,你们自己船上倒是干干净净的,怎么把人家船当垃圾船呢”[2]6。
李金枝从起初的极不耐烦,感到晦气,躲躲闪闪,到逐渐软化,开始破冰,再到最后俨然已经化身为一副正义使者的形象。
寻船队伍一点点壮大,前文所描绘出的城市人群体形象由此对转,而以李金枝为代表的市民,在寻船过程中也完成了自身形象的颠覆,自私转换为热心,冷漠转换为温暖。文本前后,不管是群体形象还是人物自身形象都显示出其逻辑逆转,而这种逆转形成的语境差又在破裂、疼痛与愈合的善恶对转中趋于合理,展现了人性层层递进与转换的复杂。
四、语境差下的陌生化审美
当文本叙述中的言语代码突破所处语境的线性逻辑,呈现出表层的不协调时,语境下的各因素会互相调节,在深层转化为统一的审美平衡,生成特异性美学信息[3]。同时,这种修辞性语境差的审美层面会渗透着表达者的语义升华和接受者审美体验的有机结合,是文本话语价值的最大体现。
小说全文充斥着语境内各因素的不平衡,从认知层面的错位开始,小说就将城乡对立的话题探讨植入其中,而城乡的隔膜背后又渗透着作者对人性的窥探。当城市某种程度上比乡村优越时,城市人自然而然产生了优越感,傲慢与偏见便在人的劣根性下演化为歧视和嘲讽。与此同时,乡村人的内心是不平衡的,当表象的和谐被鲜血和死亡戳破,人性中最原始野蛮的愤怒便倾泻而出。城乡间互相复仇的错位,实质是地域环境带来的人们伦理观念、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上的隔绝[5],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乡村人还是城市人,在前文的叙述中都呈现“恶”的形象。
但作者在《西瓜船》中所表达的远不止城乡的对立和人性恶意的来源,他安排了福三母亲的出场,开启了寻船的故事情节,无形中,文本画面情节被置换,人物形象被颠覆,上下文各因素趋于混杂。而这种颠覆的背后,其实是作者渴望用“善”来解构“恶”,用善良和温情去弥合那些血腥与暴力,由此在文本中形成修辞性语境差,给读者带来不同寻常的审美体验。
而小说的最后,作者又亲手打破了读者的期待,颠覆了他理想中善良化解一切的主题。奇怪的寻船队伍暗示着善良拥有绝对力量的不现实[7]。西瓜船上干涸的血迹在阳光下被照亮,福三母亲为了感谢香椿树街上的人们,要向大家磕头,却因为眼睛不好,出现了向黄酒坛子磕头的荒诞一幕,这其实是指向了福三母亲感谢这群人的荒诞性,这个慈悲的老妇人欲感谢而不能,善良有时候在消除矛盾与隔膜上是充满无力感的;而香椿树街上的这些人欲接受则不能,因为“阳光下的血迹”寓意伤害已经留下[7],它应当被看见、被铭记,而不是轻易被消解。故事的尾声,众人目送她离开,留下来自小城的绵长而无声的忏悔。
五、结语
苏童的《西瓜船》在语符表层和深层共同构成的认知层面中,呈现出由认知偏差和共知语境缺失而导致的逻辑失衡,从而推动了小说从情节到人物的颠覆。这一颠覆又在小说对城乡对立和人性善恶的主题解读中得到合理消解,达成语符编码与解码的衔接。小说最终在语符深层的认知和审美感受上得到了新的平衡,从而达到了不同于其他篇章的陌生化的美学韵味。这条船带着西瓜的清甜而来,却被鲜血浸染,最后载满伤痛与慈悲而走,留下作者关于人性残酷而温暖的诗意抒写和适度的暴力表达。